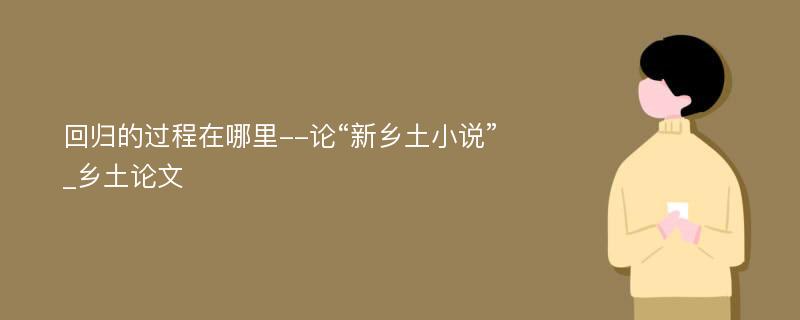
何处是归程——“新乡土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程论文,乡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6)03—0106—04
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展开,世代祖居乡土的农民日渐被纳入宏观的社会经济交换体系之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恢弘的景观便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讨生活”,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营①。这一现实迅速进入小说叙事,成为当前最具产出性的文学主题之一。
然而,评论界对于这一已然蔚为壮观的创作潮流尚未形成有效的把握视角,虽然已有众多研究者分别以“乡下人进城”[1]、“打工文学”[2]、“城市异乡者”[3] 等等概念对之做出尝试性地概括与阐释,但是,上述概念都因为存在种种指意偏差从而难以准确地把握解说对象:“乡下人进城”难以区分“进城”的具体动机,务工经商是“进城”,而走亲访友、观光旅游、赶集购物同样是“进城”,但是这些“进城”行为及其可能生成的叙事景观,无疑不是上述创作潮流的关注之所在;“打工”喻指市场经济条件下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经济契约关系,这一概念所关涉的主体不仅止于入城务工的农民;“城市异乡者”的内涵同样超出入城农民的范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止是农民,城市人同样广泛地参与人员的流动过程,从而在非出生地获得“异乡者”的身份。
如果试图从宏观上概括这一创作现象,“新乡土小说”概念的提炼可能具有更为恰切的意义:一、以农民为表现对象无疑承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形成的“乡土小说”的核心视角,所以仍然可以将之归入“乡土小说”的范畴。二、由于它所表现的对象往往在宏观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下往返于城乡两域,其思想和行为展示着异质性文化价值的冲撞,从而使得这一创作在叙事空间、价值判断等方面体现出新的特点,所以,又须在“乡土小说”之前冠之以“新”。不可否认,合适的概念可以有效地整合复杂的创作现象,并使得整体性的价值判断与理论引导成为可能。
一、乡与城:“新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最为显著的文类特征就是对于具有空间自足性的乡村世界的书写,作家在叙事中所展开的生活空间往往限定于乡村。这主要因为城市化的进程尚未大规模启动,城市无法大量吸纳乡村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农民进城并未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从而无法支撑文学创作在这一维度的广泛展开——阿Q进城后除了行窃无以谋生,最终也只能返回未庄。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建构,使得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发流动近乎中止,乡土世界的空间自足性更趋强化。梁生宝只是在买稻种的时候才会短暂入城,而城市之于梁生宝的影响丝毫未见于叙事之中。
与此相比,“新乡土小说”打破了乡村世界的空间自足性。“新乡土小说”仍然保持了对于乡土生活的呈现,这种呈现展示了当代乡村令人震惊的贫穷。在李肇正的《傻女香香》(《清明》2003年第4期)中,由于贫穷所迫, 香香同村的女孩以每晚五元的价格在村内卖淫,而香香的母亲竟然逼迫香香从事同样的营生,并亲自把一个男人领到家中。胡学文《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飞天》2004年第3期)中的老六承包土地种胡麻亏损,种甜菜亏损,种地越种越穷,结婚的钱总是凑不齐。项小米的《二的》(《人民文学》2005年第3期)则叙述了小白家连孩子学费都交不起的赤贫状况,等等。在此情况下,当城市需要农村劳动力资源并能实现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值之时,农民进城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所以,孙惠芬在《上塘书》(《当代》2004年第3期)中写道:“反正,出去变得越来越容易。反正,不出去越来越不可能。”
随着香香、老六、小白们的进城,特定的城市生活空间由此展开。建筑工地、工棚、小餐馆、发廊、合资企业的生产车间等等,是农民进城后的存身之所。毫无疑问,带着乡土记忆的农民们的城市体验必然不同于城市人的生存感知,从而生成城市空间无法同化的异质性空间。
一、动荡感。安土重迁的农民背井离乡的事实本身就是生活动荡的写照,进而,城市高速发展所造成的变迁从四面八方危及他们脆弱的生存。在荆永鸣的《北京候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中, 门面拆迁的传闻始终是惨淡经营着饭馆的“我”挥之不去的梦魇,而“我”的侄子来泰倾注全部积蓄盘来的饭馆开张刚刚三个月便在拆迁之中荡然无存。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生活方式的农民而言,“城市就是一个变数。”而在鬼子的《走进意外》(《花城》1996年第3期)中,动荡更是一种宿命的力量,车祸、中奖、 工地受伤,福祸瞬间转换,完全非人力可以预料。除此之外,在孙惠芬的《民工》(《当代》2002年第1期)、孙春平的《包工头要像鸟一样飞翔》(《钟山》2003年第2期)、李肇正的《姐妹》(《钟山》2003年第3期)、 陈武的《换一个地方》(《青年文学》2004年第4期)等众多作品中,都描绘了进城农民们惊惊咋咋的动荡体验。
二、隔膜感。正因为农民的大规模进城,才使得城乡差别成为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的赤裸裸的现实。这种差别源自不同的伦理观念、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谋生方式、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所造成的城乡不同群体在体貌、言谈、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差异,并使得进城的农民总是与他们处身其间的城市隔着无形的壁障。虽然融入城市是他们最大的渴望,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可是结果却总是令人失望。
李春平的小说《玻璃是透明的》(《上海文学》1997年第3 期)题目本身就暗示了壁障的存在。孟虎子(李铁《乡间路上的城里女人》,《青年文学》2002年第8期)虽然事业成功并得到了他神往半生的城里女人杨彤的身体, 可是“杨彤的感情是个谜”,他也无法阻止杨彤最终的离去。在邵丽的《明惠的圣诞》中(《十月》2004年第6期),嫁给城里人的女主人公最终未能免于自杀的命运。 所以有论者指出:“我们在主人公走向死亡的最后时刻,看到的是肉体上已经成为城里人,而精神与灵魂还不能被城市文明所包容的悲剧下场!”[3]
上述独特的感知性内容,使带着乡土烙印的乡村人因为在城市谋生而形成的特定空间无疑不能被简单纳入都市文学的考查范围,毋宁说,这是乡土记忆被置入城市后所形成的“都市里的村庄”,是乡土意识在城市空间中的延伸。
无法真正立足于城市也无法真正脱离乡土的农民们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两域,成为转型期身份特殊的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这一群体的追踪,必然使“新乡土小说”描写的笔触广涉城乡,从而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边界,并且能够更为完整地描述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及于乡土中国的深刻影响。
二、文化价值立场的游移
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同派别的乡土小说在文化价值立场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每一乡土小说派别都有着自身明确的文化价值立场:鲁迅、彭家煌、蹇先艾、鲁彦等等坚执启蒙主义精神审视为封建伦理所笼罩的暗昧的乡村大地;沈从文、废名、师陀等作家则秉承现代性批判立场,发掘文明侵袭之外的乡土世界的醇美风情;茅盾、吴组湘、叶紫致力于对乡土世界阶级压迫的描写并以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而在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作家的笔下,对于乡村必须在合作化原则之下实现重组这一宏大社会规划的认同,无疑体现了作家坚定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化价值立场。不同于上述乡土小说的各个派别,从整体上看,当代“新乡土小说”正处在深刻的价值悖论状态之中。如同作品中游走于城乡之间因为体验着异质性文化价值的牴牾而困惑重重的农民们一样,作家也深陷于时代性的精神困惑从而未能形成明确的文化价值立场。
具体看来,由改革开放启动的市场经济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这一历史过程的进步意义无疑得到了作家们的普遍认同。所以,表达乡土社会的现代渴望,进而依托现代性价值对于传统乡土伦理做出批判性审视,便是“新乡土小说”一个鲜明的价值维度,因而,农民们必然感应于时代的召唤而离乡进城。但是,由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失范、社会机制不健全等现实状况所导致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及其所造成的进城农民城市生存的梦魇,使得“新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现代景观一经呈现便同样成为批判性审视的对象,而这一批判的价值立场往往又回复到对于乡土伦理的想象之中。这种自相矛盾、自我解构的价值悖论状态在“新乡土小说”中是一种普遍现象。
王祥夫的中篇新作《流言》(《长城》2005年第4 期)以女主人公桃花的现代渴望作为叙事的起点:她嫁到刘家甸子,是因为“刘家甸子紧傍着城市,”“她喜欢城市,尤其是喜欢城市夜里的灯光。她常常站在村子里往城里的方向看,看那边的灯光。”城市当然是现代化最为耀眼的物质和精神表征,一个乡下女人在乡村无边的暗夜中眺望城市的华彩,这一意象蕴含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进而,为了“让自己彻底成为一个城里人”,她用市政府支付到户的城市扩建征地款买了一辆夏利车在城市里跑出租,她的丈夫天生则买了一辆“蹦蹦蹦”,“专门干起了往城里送菜的买卖。”正是城市提供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告别辛勤的农耕劳作,以现代的方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
然而,精神层面的现代转换却远远没有如此简单。当桃花被歹徒强奸的消息传开之后,尽管桃花是受害人,可是在传统的贞洁观念作用下,丈夫天生还是陷入近乎疯狂的绝望:“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自家女人让别人搞了更丢人的事?”一旦身体被玷污,她的人格立刻受到怀疑,种种基于桃花是个不正经女人的想象便以流言的形式在四乡八邻传开,并且被作为事实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天生怒斥桃花:“母狗不撩尾巴公狗能上得身去?”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天生数次逼迫桃花自杀:“你还不如去死,你不去死,要不就我去死吧!”桃花因为舍不得两个孩子而不愿意去死,可是天生却真的喝农药自杀了。于文明昌盛的21世纪,性侵害还会导致当事主体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足可见传统伦理的强大与狰狞。
进而,桃花之受到侵害,恰恰是现代生活的代价。正是作为现代性核心支点的市场经济对于个体利益冲动的强烈召唤,才导致欲望之兽呼啸出笼,所以,抢劫、强奸、诈骗、肉体买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大规模地进入当代文学叙事,并使得作家投向现代的眼光自然而然地充满忧惧。在小说的结尾之处,初聆丈夫凶讯的桃花瘫软在地下,“远处,是城市那边的灯光,那么密,那么亮。”这一句作者刻意为之的陈述,与小说开头桃花对于城市灯光的眺望恰成对照,可是此时的桃花已被击倒在地。如果事先知道投身现代的代价如此惨烈,她还会保持对于现代的向往吗?进而,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现代不假思索的向往还能具有不证自明的意义吗?与此同时,通过压制欲望所实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伦理想象无疑作为小说叙事的画外之音为人们批判意识的生成提供参照。所以,“对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抛弃的农耕文明的深刻眷恋似乎成为作家别无选择的选择。”[3]
在创作后记中,作者写道:“这篇小说要说什么?一下子好像还说不清。”[4] 泥沙俱下的社会现实导致作家主体价值的迷失,这种迷失几乎是“新乡土小说”的共同特征。例如在王梓夫的《死谜》(《北京文学》2000年第12期),刘玉栋的《跟你说说话》(《人民文学》2001年第5期), 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艾伟的《小姐们》(《收获》2003年第2期), 谢友鄞的《逃离煤井》(《长江文艺》2004年第2期),胡学文的《目光似血》(《人民文学》2005年第7期)等作品中,离乡入城的现代冲动和对于保守的乡土伦理的批判总是构成小说叙事的价值起点,进而,城市现代生活的展开必然造成主体的累累创伤,并使得作品自然而然地转向对于淳朴乡情的向往。这一价值表述过程已经成为“新乡土小说”的叙事成规。
三、在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会中想象未来
可以看到,在“新乡土小说”作家的深层判断中,传统与现代仍然是尖锐对立不可通融的,虽然作家自身不断地变换着文化价值立场,但每一次变换只不过是将批判者和批判对象的位置作一颠倒,丝毫未曾弱化二者的根本对立性。然而,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使得20世纪不同派别的乡土小说作家无论是基于传统价值的现代批判还是基于现代价值的传统批判,都无法免于“虚假意识形态”的特征,而“新乡土小说”则由于作家主体文化价值立场的游移导致两种意识形态描述在叙事中同时存在。所以,当作家将现代价值作为叙事前提审视乡土现实之时,乡土世界总是保守落后,极端贫穷,完全忽视了市场经济展开过程中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正面景观。反过来,当作家秉承传统人伦观照城市现实之时,种种丑恶、黑暗完全充溢其间,包工头总要拖欠工资、官员总要腐败、民工总要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这无疑也不是农民进城谋生的全部现实。
有评论者在谈及当代小说对于民工生活的反映时认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渐行渐远的、带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开始在这一描写领域复苏。”[3] 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尽管“新乡土小说”中充满着来自于现实的细节,可是它们对于现实的把握并不完整,从而无法达到批判现实主义应有的精神深度。
事实上,由于处身于现代性价值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组织原则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所以,这一价值应当成为作家表述现实的话语基础。尽管社会文化规范的宏大转型不免于光明与龌龊的交织,并因而导致种种伤害与沉痛,但是,表现在作家笔下的社会丑恶现象在不能见容于传统人伦美德的同时,同样不能见容于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原则,它们更是由于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充分形构才获得了短暂的生存空间,从而不必然成为现代批判的理由。进而,现代与传统也非全面对立的关系,传统价值中有悖于现代社会民主、平等原则的消极性内容自然必须清除,但是,淳朴良善的人伦风情未必不能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超越的价值支撑。因而,对于当代现实的批判性呈示只有基于传统与现代的正面价值的充分融会,才能因为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理解而免于主体价值的混乱以及对于现实描绘的片面与偏执,从而能够在准确把握当下的基础上提供关于未来的明确想象。其实,这一思路在当前“新乡土小说”创作中已有零星显现。
在孙惠芬的短篇小说《狗皮袖筒》(《山花》2004年第3期)中, 主人公吉宽最初作为传统伦理价值坚守者的形象出场,这就不免造成主体意识与当代社会存在的紧张状态,所以,吉宽性格暴躁,“一说话就是发火。”进而在整体性的社会现代变迁背景中,单纯的传统价值坚守势必难以持久。吉宽外出打工的弟弟吉久杀了工头连夜潜逃回家,犯罪原因是工头不让民工们在寒冷的工棚里烤火,可是他“自己还在轿车里开着暖风玩女人。”
以性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不公,激发了主体对于自身价值坚守的怀疑与否定,吉宽迅速认可了弟弟的行为并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准备与自己视之有罪的社会同流合污。当他在小酒馆中为弟弟叫了一个小姐,并暗示弟弟连夜潜逃之时,实际上便已经陷入了价值迷失之中。
然而,恰恰是吉宽的行为所蕴含的亲情意义唤醒了弟弟的良知,“俺知足,是你暖了俺的心,像妈一样……”所以,他投案自首,认罪服法,体现了对于自己处身于中的现代社会原则的认同。由此,传统伦理成为通往现代价值的桥梁,而现代价值又使传统伦理获致社会性意义,传统与现代便在叙事中达成了和解与交融。其意义正如孙惠芬所言:“我努力用我的笔,打开一个乡村通向城市的秘密通道”[5],从而为个体提供足可仰赖的价值支撑, 这是片面的传统坚守和单纯的现代认同所无法达到的。正是这一和解与交融拯救了吉久的灵魂,使他摆脱了暴戾和恐惧,能够勇敢地以生命担当道义,并转而完成对于处在价值迷失状态的吉宽的精神救赎。最终,兄弟二人在派出所(现代法制场域)握紧了对方的手,此时,母亲的遗物(传统伦理象征)——“狗皮袖筒”——正温暖地罩在两个人的手上。
此外,在张重光的《尘缘》(《电视电影文学》2001年第2期)、胡学文的《三月的秋天》(《作品》2004年第8期)、北村的《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9月版)等作品中,一个共同的叙事起点就是当代社会现实中局部性的正义缺失导致主体反社会犯罪行为的产生。而在叙事的进一步发展中,主体最终摆脱价值的迷失走向对于现代法制的认同,在此过程中,传统伦理或隐或显,或有意或无意地产生了作用。
寻找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会点的创作尝试,体现了作家对于建构理想文化模式的深入思考,不过从当前“新乡土小说”的整体创作表现来看,这一文化思路尚未获致作家的广泛接受,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而在已有的创作尝试中,这一融会的广度与深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扩展:首先,实现精神救赎乃至于超越是当代众多社会成员面临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实际有罪的社会个体的独特需求。其次,作家无论是对于传统还是对于现代的理解与把握都还流于浮泛。特别是就后者而言,这种浮泛更为明显。例如在上述作品中,可以作为精神依托的现代价值仅仅是一种符码化的存在,即静态的、前提性的、外缘性的可以为个体不假思索地接受的法律体系,其内在的机理及其作用于个体的复杂影响并未获得深入地分析。
在根据孙惠芬的两部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人民文学》2001年第12期)和《民工》(《当代》2002年第1 期)改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民工》(编剧:陈枰,导演:康洪雷)的结尾之处,父亲鞠广大与儿子鞠福生由于生活变故离开他们打工的城市,担着行李在落日的余晖中沿着高速公路步行向前。他们归程何处?在可以预见的不远的将来,他们必然继续游走于城乡之间,体验着与昨日相似的艰辛与快乐,激动与忧惧,自尊与屈辱。然而,如果将眺望的眼光放得更为长远,那么,建基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之上的社会现代性工程的充分展开,才是他们乃至于全体国人物质与精神的“归程”所在。对于“新乡土小说”而言,只有依托这一宏观价值展开叙事,才能真正书写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所导致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民族心灵的秘史”,并因此深刻参与新的时代精神的生成。当然,对于作家的这一要求未免苛刻,但是,有力量的作品必然建立在作家强大的思想力量之上,我们期待这一类作品的出现。
注释:
①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3年为1.1亿,2004年为1.2亿(《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数量、 结构与特点》见河北劳动保障网调查报告,网址:www.he.lss.gov.cn,2005年10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