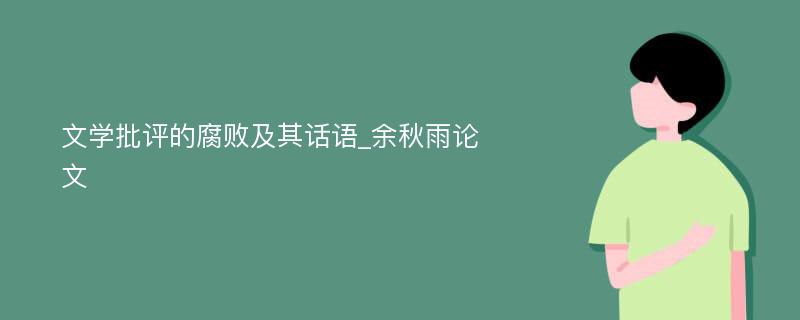
文学评论及其话语的腐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腐败论文,话语论文,文学评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评论腐败,令人痛心疾首。它使文学评论失去可信性。很大一部分的文学评论早巳脱离了广大读者,变成了台里的喝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所谓“版面费评论”。这是专业评论刊物内部体制的腐败的毒瘤。哪怕是一部极其幼稚、粗糙的作品,只要付出一定数量的版面费(实际上是变相的、体制化了贿赂),吹捧的文章也会堂而皇之地刊出。评论作者常常是精心物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指定评论作者,也就限定了评论者的观点,这本身就注定评论失去了客观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地方性的专业刊物上,而是经常地发生在全国性的刊物,如《文艺报》《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上。这是因为出资的一方,并不以地方刊物的影响为满足,而是以中央级的权威为目标。
应该说明的是:许多被这些权威刊物推出来的作者和作品,并非都是下品,但是一旦与金钱排上了钩,就很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评论的名声败坏了,即使有才气的新进作者,也难以通过这样的评论得到读者的信任。
但是,由于这类的权威,这种指定评论家的运作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奉行的模式,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模式被广泛接受,逐渐就变为一种潜在的常规。
正是这种常规,掩盖了贿赂的性质,使这种胡乱吹捧的评论具有了话语的霸权。
和这种模式近似的,是所谓的“研讨会评论”。这种研讨会评论和“版面费评”在操作上有所不同,版面费评论是个别运作的,而研讨会评论则是以组织的名义进行的。堂而皇之地发请柬,与会的都是知名评论家。但是,名为研讨,实质上,不同的评论家,慷慨陈词,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不同的意见,充斥会场的是一片溢美的赞扬之声。其奥妙在于,所有参与者,均有为数不菲的“车马费”,这是半公开的红包。和版面费评论一样,这样的运作,也大多发生在中心城市,由比较权威的刊物主持。据云,知名评论家,有时一天要赶几场这样的研讨会。作品根本来不及看,但是,吃人的东西嘴软,拿人家的东西手软,研讨变质为吹捧会就是必然的了。这种恶劣作风,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对梁凤仪的所谓“财经小说”的廉价赞扬。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蔚为风气,成为另一种模式,往往是由大款出资,或者通过权力募集、摊派经费。
这两种模式在操作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运作中,有时,还有一点羞羞答答,而在内部策划中,则有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陷入这种层次,道德底线的降低,是不可能避免的,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可能就是沦落的问题了。
所有这些文学批评,虽然能够热闹一时,但是,在作品的鼓吹者和作者看来,都有一个缺点,不管你请来多少知名评论家,影响毕竟很小,会上热热闹闹,会外冷冷清清,所造声势,如过眼烟云,不可能给广大读者留下多少印象,难以为作者营造名声。为了扩大影响和知名度,研讨会批评,往往和另外一种形式的批评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传媒批评”。这种批评和学理性批评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毫无严肃性,要害在于抓住一点刺激性的新闻,不及其余,在大众传媒上营造轰动效应,耸人听闻,从而扩大发行量和收视率。只要城市晚报、电视屏幕,充斥着此类新闻,就算达到了目的。其结果是传媒批评和文化明星的生活琐事的炒作合谋。其极端者,可以余秋雨和《上海宝贝》作者卫慧为代表,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炒作中,几乎放弃了对于文本的分析,尤其是对于余秋雨的散文的历史性成就,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认真的分析,炒作的潮流就过去了。但是,传媒却从中获得了商业化的利益。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传媒批评是最商业化的,也是最不负责任、最腐败的批评。
传媒批评的盛行,和炒作的市场价值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宿命的。在文化产品最为商业化的美国就有例外,《纽约时报》的读书版,每周一次,几十页,就很严肃,享有权威性。在人家的操作模式中,作者是无权指定评论者的,编辑倒是有权选择资深的阅读者和撰稿人,但是,他并不是只给指定的书籍,而给于许多书籍,这就排除了对某一作者的特殊关顾,同时,作者完全有自由确定自己的观念,这是编辑无权干预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正直的评论,不管是褒是贬,都是在大量阅读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没有选择,就谈不上评价。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版面费评论和研讨会评论,从一开始就剥夺了评论作者选择的自由,其次,孤立地评论作品,离开了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历史水准,失去了比较的准绳,只能降低视点,把作品人为地抬高,制造假象。而对于水平很高的作品,又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加以极其苛刻的挑剔。
大量的文学评论就这样堕落为商业广告,可悲的是,只是低级的广告,空虚的赞美和无限的拔高,一眼可以看出其的假冒伪劣。编辑部内部的腐败机制跟商业化的炒作合谋,形成恶性循环。近来每年年初,都要出现一批某某年度“最佳散文”“最佳小说”“最佳随笔”“最佳童话”“最佳寓言”。所谓“最佳”并未经过任何评选,本就令人怀疑,可是偏偏又有数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年度最佳”,不同出版社的“最佳”,所选篇目又相去甚远,那些主编多少会写一些文学评论文章,有些还是挺活跃的,这就不但损害了文学评论家的声誉,而且连广告的声誉也损害了。几个系列的“最佳”的发行量并不高就是证明。
二
所有胡吹瞎捧的评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充满流行的、关键的术语,这些术语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引进的词语原来都有严肃的、确定的、一定的历史的含义,胡吹乱捧的评论经常将些词语加以任意的、反复的使用,一直用到这些词语像磨损了的铜币变得模糊,失去其原本的严肃意义。
应该承认,当代文学批评的腐败现象并不都来自传媒,有时,其作品倒是出自学院派之手。但是,没有新颖的思想,也就没有新颖的话语,思维不着边际,也就只能在腐败的话语中兜圈子,陈词滥调不但是个语言现象,而且是个思想现象。许多关键词的内涵在反复使用中,不断萎缩,其外延则连理论所要求的起码的全面涵盖都做不到,这可能有私人的、派性的原因,凡我小圈子的,被捧上了天,戴上最流行的桂冠,非我族类,则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不顾学术规范,使用率相当高的关键词,缺乏严格的定义。这种文风的流行,正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生命力的馈乏,这种馈乏特别表现在艺术分析上,有效的准确的艺术量度,甚为稀罕。
这种缺陷在散文评论中最为明显。这也正是散文评论落伍于小说诗歌评论的证据。一般地说,小说和诗歌评论大致还能在当前最有艺术成就的作品上达成共识,而散文评论则不然,同是一篇宏观总结性的散文评论,往往是在上海的评论认为最值得称赞的一些作家,而在北京的评论则提出了另一批作家,二者互相重合的,廖廖无几。例如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等作为文化散文的重要收获[1],而北京的的年度评论,则对潘只字不提,对余秋雨则提出严厉的批评,李元洛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则被认为是文化散文的重要成果。这种现象,在小说中是很难见到的。
散文艺术评价评论的随意性,广大读者已经见怪不怪。最为令人不安的是,这种随意性已经浸入了散文史的写作。由于大学的职称晋升体制的缺陷,一些缺乏散文艺术的鉴赏力的人士轻易地进入了散文史的作者行列。这些人士不但对于散文艺术缺乏见解,而且对于历史缺乏修养,至于何种散文作家可以进入历史,何种不够资格,往往心中无数。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部插图本《当代散文史》,在写到福建散文家的时候,作者居然没有一句提到南帆、朱以撒、萧春雷,给予舒婷的篇幅只有短短的两行,而给予朱谷忠的篇幅则长达五六百字[2]。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很难以私人关系来解释。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罗致了大量当代散文中的二流、甚至是末流的散文作者,这些作者既未为中国当代散文创造出新风格,也未没有起码的知名度,诸如张汉青、李玲修、夏坚勇、吕锦华、叶梦、廖化歌、和谷、刘成章、李天芳、陈长吟、周彦文等等,不要说入史,就是进入全国性散文评论的视野都很难。这说明作者的散文艺术观念处于不及格的水平。堂堂的散文史的作者,对于散文的艺术水准缺乏起码判别力,读者怎么可能指望从中获得对散文从文本到历史的可靠的、有效的阐释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所依据的理论、所使用的逻辑就是腐朽的,在阐释新时期的各种散文潮流的时候,确立一系列标题的时候,只有零碎的、意识形态的内涵,散文作为一种艺术文类(或者文体)的特点根本就没有进入他的视野。散文作为一种艺术,什么时候出现了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有突破性的作家,在作者看来,根本就不值得去研究。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水准的散文史和专著,却在批量生产,读者已经习以为常。
水平低并不奇怪,但是,把低水平当作高水平去仰望,就是评论的腐败了。
缺乏起码的艺术鉴赏力的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散文领域,在诗歌领域同样存在,甚至在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都闹了很多笑话。最明显的一次,是2000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出现了一个完全是外行的问题。试题是郑敏女士的诗,题目叫做《金黄的稻束》:
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暮色里,远山/围着我们的心边/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考题要求考生对这首诗的四项解释指出不恰当的一项。标准答案是如下一项:“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一句涉及时间,从全诗来看,除了‘秋天’外还隐指‘暮色’降临以前。”命题者的意图显然是让学生明白,这首诗的时间应该是在暮色降临之时,或者以后。因为,诗中,已经明确指出是在“在暮色里”,而且还点明“收获日的满月”,但是,这种咬文嚼字,是毫无意义的,腐朽的。关键在于要理解这首诗的真正含义:从金黄的稻束,想到疲倦的母亲,母亲的皱了脸,为什么是“美丽”的,她的疲倦为什么是“伟大”的。这一点如果不理解,字斟句酌地吹求有什么意思呢?何况,诗中同时又明明说是在“黄昏路上”,“黄昏”是在暮色降临以前,还是以后呢?这就很难说了。再说,这首诗写的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场景,而是一个概括的场景,暮色只是一个黄昏的背景,从这出发,延伸到“历史”:(“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和“人类”(“站在那里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显然,这是超越了时间和场景的具体性的。确定的时间根本没有意义。在具体的时间上纠缠,暴露出命题者在诗歌艺术分析上的外行:抒情诗与散文不同之处之一,就是它是高度概括的,超越具体时间的确定性,有利于它的深邃概括。除了特殊的例外,在时间、地点上过分的确定,不利于它的想象,时间、地点、条件越是具体化,越是可能为散文同化。不论是艾青的《乞丐》、《手推车》、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还是臧克家的《老马》,郭沫若的《骆驼》,不论是戴望舒的《雨巷》、舒婷的《致橡树》,还是雪莱的《云雀》、普希金笔下的大海,不论是李白的月亮,还是苏东坡的笔下的长江,大凡诗人笔下之物、之人,只有超越具体时间、空间的才有利于诗人的想象的自由展开(注:参见孙绍振《标准答案还是荒谬答案》,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12日,这个问题在文中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以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贺之章的《咏柳》为例:“碧玉妆成一树高,万千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并没有点明柳树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也没有暗示是早晨还是黄昏的,正因为它时间、地点的不确定性,才有早春气象的普遍性和想象的自由。如果点明是某一地点,某一时间,某特殊的柳树,那就得交代,不管是何处的,何时柳树,其细叶都是由春风裁剪而成的。对艺术家来说,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时间、地点、人物具体性的递增,导致想象的自由的递减,抒情性也相应递减,抒情事性的递减必然导致叙事性的递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沙场君莫笑,自古征战几人回。”不但现场的时间的因素是淡化的,而且未来的时间,都是虚拟的。难道经过行军的漫长过程,到了前线还不醒?如果真是这样,还有可能上战场吗?诗人与散文家之不同,就在于把这一切留空白里。又如:“谓城朝露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间和地点倒是有了,但还是比较虚的,如果一定要问在“谓城”的什么方位,“朝露”是日出之前,还是日出之后,把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就可能成为散文了。又如:艾青的《乞丐》:“在北方/乞丐徘徊在黄河两岸/徘徊在铁道两旁”不但时间、地点是不确定的,连性别、年龄都是没有的。诗中的乞丐是整个黄河两岸的乞丐的概括性的意象,而不是某一个乞丐的具体描写,这就是艾青在《诗论》中所说的“灵魂的雕塑”的艺术效果,如果把性别年龄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有年龄、性别、时间、地点、人物一一详加描述,就必然失去诗的概括性,也失去想象的自由。)。
命题者明显不懂诗,却要给出标准答案。所出的问题,完全是个伪问题,其答案是个荒谬答案。这个问题一经指出以后,第二年的语文考卷就把古典诗歌从标准化客观化的题型中取消了。但是,这个影响了当年许多考生命运的试题包括它的题型,为什么要取消,却没有任何解释。这种不明不白的、偷偷摸摸的修正,恰恰是文学评论界所特有的。与之相对照的是自然科学的试题,南京市自出的一题数学考题,对其正确性,发生争议,一直闹到多名院士签名,非要闹个水落石出,让命题者公开承认错误不可。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学评论话语的腐败的一个极端,是它不但被商业的实用性所腐蚀,而且受到体制的保护,在实际操作中是和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纠正它的错误的前提,就是体制的改革,这比之改变潜在的成规要复杂得多了。
三
问题在于,体制并不绝对是最终的根源,体制是人制定的,体制是人的思想成规的外在形式。从80年代以来,我们引进了一系列的西方文论。到上个世纪末,西方文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作为一种思潮,文化批评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重视文本的意识形态,成为不同文论流派的共同倾向,文学与哲学、文化之间的区别遭到轻视。这本是一个历史的片面性,是相当深刻的。但是,我们在接受这种潮流的时候,忘记它的历史局限,幼稚地把追寻文学的特珠性,尤其是文类的(形式的)特殊规律,设想成幼稚可笑的问题;第二,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西方文论的相对主义对绝对僵化的话语霸权的反抗,对于学术的发展无疑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却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相当一部分批评家们那里,文学性是绝对地不确定的,连起码的稳定性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在共同的历史语境里寻求其相对稳定特征也是幼稚可笑的,文学形式、诗歌、散文、小说之间不同的规范,在前卫理论家那里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对于作家来说,形式或文类之间的细微的差异却是艺术修养的生命线,对于评论来说,他们的艺术鉴别力,包括对形式之间的微妙的差异的敏感却是基本功。近年来,我们培养了大批的文学硕士、博士,他们西方文论的修养是不容怀疑的,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年青评论家的艺术修养、尤其是微观的艺术鉴别力却不容乐观。在高等学校中文系的课堂上,能够深入浅出地分析文本的艺术奥秘的年青教师真是凤毛麟角,在生动的形象上贴一些陈腐或者时髦的标签却成为时髦,但是,不管是陈腐的,还是时髦的话语,其缺乏生命,其脱离文学生命,其腐败和苍白却是共同的。
这当然不能全怪西方文论,主要的还是要怪我们自己。我们引进西方文论,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局限,我们回避了它与中国文学实践、经典文本之间的矛盾,满足于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文论,只看到西方文论澄明了的方面,而忽略了它遮蔽了的方面,这本身就是违背西方文论的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的精神的。在长期引进的过程中,我们忘却了最高任务不是重复,而是突破、创新;而要创新,不能满足于引进,虽然新式话语令人眼花缭乱,实质上不能掩盖本土性的失语。只有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不但要对西方文论进行证明,而且要对其加以哪怕是部分地证伪,才有可能进入话语创新,获得中国文论的真正生命[3]。
我们的文学批评,比较盛行的是意识形态的文化批评的宏大话语,一旦到了文本的艺术特点,就鲜见精致的分析。这种情况在散文的评论中特别严重。这是因为,在西方,散文的地位不像在中国这样显赫,散文理论,比之小说、诗歌理论,要贫乏得多。可以直接搬用的很少。这就注定了我们散文批评理论基础十分薄弱,幼稚到连最起码的分类都很难符合形式逻辑的规范。当评论家反反复复地使用着“小女子散文”和“学者散文”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如果统一按作者身份,其它的作者该如何分类,才能达到形式逻辑所规定的划分不得有剩余和交叉的标准。当我们使用流行的“文化散文”时,至少也应该考虑到与之相对的是什么样的散文。如果我们所使用的是大文化概念,则与之相对的应该是“物质散文”,“物质散文”如果不能成立,则大文化散文在逻辑上是不是能够成立呢?如果说,我们所说的“文化散文”并非相对于物质,则至少应该有所定义。正是因为这些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含混,我们的基本理论就不能不是比较脆弱的,散文的宏大理论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散文评论就不能不特别混乱。很大一部分的评论,其实不是评论,而是陈腐概念的任意堆砌。一些散文评论家没有什么艺术鉴别力,面对大量作者,根本无法品评水准的高低,就采取了最为庸俗的办法:或是按作者社会地位为准,散文学会会长、出版总署的领导、省级宣传部长,自然就排在前列了;或是,以作者的年龄、资格为准,辅之以见报率,所居住的城市的重要程度来确定。位置一旦确定,即使文章水准与位置不相称,也要强行加上溢美之词。话语的滥用必然带来话语内涵的腐败。
面对凡此种种话语的腐败现象,不能说,所有的评论家都是趋炎附势,其中也当然有一些评论家很正直,力图借助西方文论有所创新,但是,西方文论的话语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能与中国文学创作完全合拍的,则更有限,我们的任务,是在接受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话语,如果满足于西方文论的有限话语,失去了自己创造话语的自觉,也就不能冲破现成的话语,只能在旧的、已经腐败的话语体系中摸索,其结果也就失去了对腐败话语的免疫力。
在余秋雨评论的热潮中,否定余氏的一派,表现了那么大的义愤,表达义愤的关键词,就是“滥情”和“矫情”[4],但是,恰恰是两个关键词,是在最腐败的意义上被反复使用的,既没有进行过起码的廓清,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理论免疫。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没有任何现成的阐释。反复使用的结果,只能是导致话语更加腐败。
抒情是文学最基本的手段,既然文学属于审美,只要审美是与情感与感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则抒情,永远也不会绝对过时。本来,值得研究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抒情是艺术的,什么情况下,抒情是过度的,变成了滥情,在什么情况下,又变成了矫情。矫情的产生,其原因一般都从刘勰那里找根据:“为文而造情”,但是,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从话语学说的角度来看,感情能够造得出来并且能够有相应的话语顺利表达吗?从创作实践来看,恰恰是作者自己特有的情感由于缺乏相应的话语而格格不能畅吐,不是作者把话说出来,而是现成话语牵着作者,像透明的罗网一样把作家束缚住了。明明有鲜活的情感,却历尽艰难,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而腐败的、陈旧的话语却是现成的、脱口而出的。几番挣扎之后,只能将自己真正的感情放弃,用陈词滥调来敷衍。“造情”失败了,结果是,“弃情而就文”,所谓滥情,其实是陈词滥调、腐败话语的因袭,窒息了本来新颖的感情。腐败话语中并没有包含多少真正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滥情从心理学来说其实是矫情,也就是虚情假意。滥情的要害是为文而害情。从话语演说来说,滥情其实应该是“滥语”,正如西方文论讲的:不是人讲话,而是话讲了人。“滥语”窒息了活人。
“滥情”作为一种话语本来的适应性是有限的,但是,由于它被提出时的权威性,在使用过程中其适应性被无限地扩大,结果是能指成为不透气的空壳,其所指不能在交流过程中自由召唤读者的经验,腐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交流的过程,本能是能指获得生命的过程,现在变成了失去生命的、腐败的过程。
这么多作家围攻余秋雨,为什么却没有一个作家对这个用烂了的“滥情”加以理论的免疫,给予新鲜的活力呢?因为,我们失去了话语更新的能力。经典话语,把我们变得聪明了以后,又把我们吓得愚蠢了。我们被他们的话语笼罩住了,只能在它的御花园里窒息自己的思想。真正要研究余秋雨,就应该分析余秋雨在抒情中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特别是他的抒情与一般散文的抒情有什么不同。同时,要警惕西方的审美观念在反复使用中的腐化,对“审美”加以反思(寻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错位)是十分必要的。审美是情感的,这是康德说了的。但是,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他的抒情往往又带着文化历史的深思,文化人格的建构和批判是他散文的一贯思路,这明显是带着智性的。像《一个王朝的背影》那样,把清王朝的君主从开国写到没落,揭示其文化人格从强悍、开朗到怯弱、腐败,辅之以汉族知识分子从抵抗到怀恋,得出了知识分子有文化认同滞后的特点。这样深刻的充满文化人格价值的批判,就不能简单以审美的情感来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审智”作为康德“审美”学说的补充,就避免了审美和抒情话语在反复封闭的使用过程中的腐化。当然彻底地分析起来,余秋雨虽然有审智的成分,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他和现代派的审智,还有相当的距离,说他的历史贡献,就是从审美到审智中间的一座断桥,才是比较确凿的。
真正的文学批评不能是广告式的,也不能是学究式的,二者必然伴之以话语的腐化。对于西方文论的话语,不能是亦步亦趋的地为其寻找证据,应该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在证明与证伪的过程,警惕腐化的危机,衍生出中国自己的话语来。
标签:余秋雨论文; 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艺术评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读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西方文论论文; 历史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