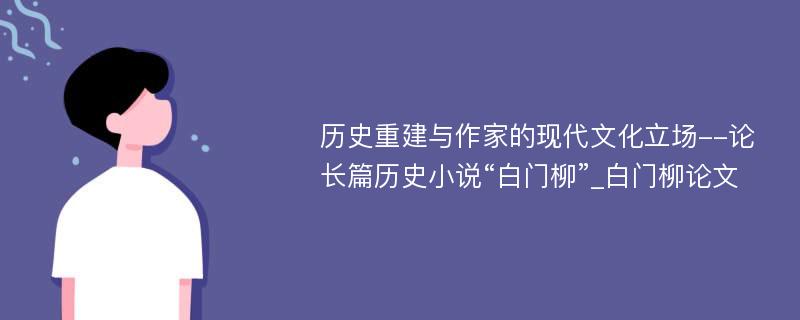
历史重构与作家的现代文化立场——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论文,历史小说论文,重构论文,立场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重构与早期民主思想溯源
提起《白门柳》,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多灾多难的历史,并对小说的真实交口称赞。作者刘斯奋在不同的场合曾反复强调:“我觉得真实的历史给人的联想更多”,(注:刘斯奋、程文超、陈志强:《历史、现实与文化——从〈白门柳〉开始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期。)他明确声言自己在创作时严循历史的真实,而无意于简单比附、影射现实,力图直截了当地将活泼饱满的历史原生状态和盘托出。也许正是在这里,《白门柳》显示出了别样的风采,作者以他那管多姿多彩的如椽大笔,为我们历历如绘地再现了三百年前明末清初的整个社会风貌、经济状态、阶级矛盾、民族斗争、人文景观,包括当时的饮食服饰、里巷百业、典章文物、礼仪乐律;空间上,笔墨广阔地拓展到大江南北、乡村都市、宫廷庙堂,堪称是对这一时代全像式的艺术拷贝。然而,更重要的是突破传统单一的政治真实观,在历史重构时融入了民主思想的内涵,说出了关于历史真实的独特话语,将自己的艺术思考不显痕迹地渗入到文本中,文本通过现实读者充满主动性的阅读,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理性连结。
《白门柳》是属于文化批判与反思的历史小说。作者有着严肃而明确的创作意图,他力图“通过描写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以及其他具有变革色彩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解’的社会巨变中所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来揭示我国十七世纪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注:刘斯奋:《〈白门柳〉的追述及其他》, 《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作者所欲表达早期民主思想诞生的艰难, 从而避开了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话的冲动。治史多年的刘斯奋独具慧眼地看准了这段动荡纷乱的历史,选中了担当守护思想文化重大职责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李自成农民暴动摧毁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宦通途之后,满清民族挟带野蛮彪悍之气践踏着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士大夫在现实权力系统中一无所有的同时精神也陷于一片荒芜,他们的灵魂在大动荡、大变革中漂泊不定,无从归依。这种历史的悲剧具有永恒的价值,足以让当时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反省不已。与此同时,作者一改历史理性主义将人抽象化的偏颇,用平民主义的思想温情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如第一卷描写黄宗羲北上途中,看到榆林中悲惨阴冷的死亡图景,在精神上引起强烈的震撼,表现出救死扶伤、悲天悯人的民本主义的文化立场。而这却是作者与文本双向碰撞的结果。作者选择题材的同时,题材也在选择作者。可能是与生活在岭南宽松开放的文化思想环境不无关系吧,八十年代初期,时值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演进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具有独到见解的作者才会被这段历史所选中;同理,只有像刘斯奋这样独立思考的作者才会根据自己思维向度选择文化的角度契入历史,极具创意地在旧题材中拈出了“民主”这一现代性的话题,从而一下子将小说创作推进到精神思想的前沿地带。
民主话题首先在题材立意上表现出来。明末清初的历史纷繁复杂:农民起义、清兵入关、明朝覆亡、社党之争、儿女情怨……。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兴趣。而作者立足于当代意识,认为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从社会进步意义来讲,最具价值的不是民族的历史遗恨,不是名士名妓的悲欢离合,不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而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诞生。”在他看来,“顾、黄、王的思想,……这也无疑是明末清初值得大书一笔的思想巨变。”(注:刘斯奋:《〈白门柳〉的追述及其他》,《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作者这种尊崇民主思想的观念与五四精神无疑是相一致的。正是这种民主思想富有意味的抉发,使得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味。这里所说的民主思想并不是作者强加的,更非抽象概念的产物,它已内化为活生生的审美表达,甚至与江南日盛的商品世俗文化密切相关。该书开篇,作者有意地展示江南特有的繁茂的商品经济,写出了天下商品集于南京的印象。此处感性的景观文化描写寓含着深刻的思想指向:只有在这种商品经济昌盛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商品意识和民主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为整个作品的思想艺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找到了理想的逻辑支点。什么叫历史真实的还原,这就是历史真实的还原,而且是一种别具新意和深度的历史真实的还原。归落到情节和场面上来,就有了第一部所述的黄宗羲在浙东会馆与毕石湖的交谈时发表的工商皆为本的一番议论:“其实,世上若无工匠,这一应民生日用之物,从何而来?世上若无商贾,这一应货物,又安能转运流通?可知农是本,工商又何尝不是本?”(注:刘斯奋《白门柳》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黄宗羲此说,使商家毕石湖顿开茅塞。这个不起眼的细节昭示着新生思想与新生经济的产生一样,在看似不经意中忽然跃出,实乃是当时客观现实孕育的结果。它是建立在对重农轻商的传统文化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传统文人所没有的思想突破。
最具意义的是小说有关义、利关系的描写与处理,作者在维护义即人文道德基本规范的同时对利的合理性给予正确的认同。他以饱满的笔墨向我们展示:这种义利关系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传统士大夫的生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点上,钱谦益多重身分的安排设计颇耐人寻味:他既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具有文坛祭酒之誉;同时又是一个拥有众多土地的大地主,收取佃户的租金,兼并他人的土地;与此之外,他还在做着海上贸易,又是商人的身份,可说是三位一体的角色。作者对钱谦益身份的如此定位,实质上肯定了商品经济的“温床”作用,这为小说中钱谦益的性格发展和复杂变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当然不同与“思想型”的黄宗羲,钱谦益没有那样有意为之的形上思索,他只是在享受工商活动带来的生活实惠和精神及物质上的欲望满足。黄宗羲与钱谦益两人实际上从两个不同层面讲述着明末清初整个时代的义利观;它揭示了在江南这么一个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标榜的宋明理学,面对资本主义的萌芽,它最终无可挽回地失败和破产。作者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新的思想事变,进而形象地表达出来。在整个小说中,士大夫对妓女的看法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钱谦益公开迎娶小妾,不顾礼法地要求家仆称呼柳如是为“夫人”;冒襄迎娶董小宛则被传为一时的佳话。小说中妓女形象也表现得各有特色,柳如是的精明泼辣,董小宛的温柔体贴,李十娘的善解人意,士大夫在纯然玩乐的心境中衍生出对妓女的欣赏乃至人格的尊重。这一切都是在作者肯定情欲、利欲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认为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存互渗的基础上发生的。用小说中顾眉粗俗的话来讲,就是“如今的世道上,我们当婊子的要走红,自然得有他们的捧场;可他那个大名士,若离了我们婊子,只怕也当不神气哩。”(注:刘斯奋《白门柳》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冒襄想背弃自己娶董小宛的诺言,然而名妓们却撮合了他们两人的婚姻;名士离不开名妓,名士的风流总要借托妓女,妓女的艳名也要借托名士的宣扬,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至此发生了某种结构性的变化。
以往历史小说(包括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真实背后往往隐藏着作者功利性的冲动,文学中的历史几乎等同于政治的阶级斗争史。我们不否认人类历史涵盖着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决不是历史的全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决不是阶级斗争或政治所能包融得了,它的内涵要大得多,包括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白门柳》的成功,从创作论角度讲,首先就在于对这种历史即政治(或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的突破。当作者选择文化的视角取代政治来表现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于是,题材对象就恢复了原有的丰富复杂的貌态,获得了本色的真和自然的美;它不再以绝对的是非、正邪、美丑的两极对立的方式出现,同时也改变了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短视的政治标准放大之后常常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分不开。由此,在他创造的文本世界中,我们看到的钱谦益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叛徒,他在欲望交错斗争中,苦苦挣扎,表现出了精神分裂的特征。至于在通常场合下都是以可耻可悲的叛徒身份出现的洪承畴就更不必说了,他在第三部作品中不仅有劝降复社首领吴应箕等时的苦口婆心,而且还俨然具有站在大汉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同化、征服满清异族的长远考虑,这与坚守高位的汉文化的黄宗羲等人可谓殊途同归。写历史更注重写文化,而在写文化时不忘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内涵;即注意文化共同性,又富有意味地融入高位文化与低位文化、传统文化与新生的早期民主思想冲突方面的新质,以凸现中华民族思想突围的艰难坎坷。这就是《白门柳》历史重构最特殊最迷人之处,也是它之所以能在真实性问题上高标独立的主要缘由吧。
二、知识分子群像及其尴尬的生存状态
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被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阐释得非常精当: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拥有文化知识,一跃而为“统治阶级”;又因为所倚仗的文化资本的抽象,不如权力、经济那样充满世俗力量,而沦为“被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夹缝中生存着。然而夹缝并不一定意味着依附。夹缝一方面意味生存空间的狭窄,受到多方面的夹击;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独立,虽然狭窄却也自足。然而在狭窄的空间自足需要信心。由于文化的差异,与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倔强性格的彻底的个人”状态相比,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缺乏“处于几乎随时与现有次序相对立的状态”(注:张隆溪:《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读书》1997年第7期。)的勇气,剩下的道路便只能是依附了。
传统的士大夫在寒窗苦读、埋首经书的时候,想到的不是用学识来支撑自己的人生信条;在精神漂游于形上之王国时,能够知远而返。在单向的政治入仕选择中,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地将自己的一生寄予政治权利上,对入仕充满了羡慕与渴求。没有摆脱政治权利中心控制的勇气,没有独立于政治与经济之外的价值追求,无论个体具有怎样的才情,具有怎样的探索精神,都不会产生具有真正价值的学统。(注:参见吴炫:《知识分子:批判的立场、对象和方法》,《文艺争鸣》1997年第6期。)这种僵化的学统只能是维护、抱守原本应由学统产生的恒定的道统。当道的内容被确定为封建的宗法制度时,又再一次加强了士大夫们渴求政治认同的热情,更进一步失去了学统独立的可能性。士大夫们在学统、道统、政统的恶性循环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自我赞颂中,隐藏着底气的虚弱。士大夫们一致渴望太平盛世,除了物质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稳定的社会中,有稳定的可以依附的主人,为他们提供人生价值保证。而在社会大裂变大动荡时,精神上首先体验到错位、反差、矛盾的往往也就是这一群士大夫们。凡此这些,在刘斯奋的笔下都有非常深刻精彩的描写。
《白门柳》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是知识分子在大动荡时代自我挣扎心路历程的形象写照。从第一卷《夕阳芳草》开始,以讲述崇祯十五年的有关人事为起点,沿着政治团体“复社”与阉党阮大铖的斗争,以及年轻士子们在陈贞惠领导下与钱谦益作较量一路讲述下去。首卷是灾难潜伏的阶段,在清兵压境、农民起义的压力下,预示了明朝如西下的夕阳不可挽回的衰落;活动在江南一带的复社分子们每每感到时局的危急,但来自北方的灾难毕竟遥远空洞。这从他们频频出入妓院寻求欢娱的信息可以表现出来。他们可以寄托人生价值的明朝及道统毕竟还存在。复社的士人们照样可以充满热情地参加乡试,可以循环着已定的道路。随着《秋露围城》开始,当李自成攻进了北京城,明朝建立的稳定的社会秩序顷刻混乱起来,并无限期的推迟了入仕之途,将读书人的梦想搁置起来;士人们在咒骂“流寇”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有自身的利益被损害的怨恨情绪。而留驻北京的士大夫们他们更是受到了历史的戏弄,仓皇之间辩视不清方向,找不准自己应该效忠的主人:是李自成、南朝小朝廷,抑或是清王朝?如复社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佯装归顺之后,历经千辛万苦,意欲逃回江南证明自己品行的高洁;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先前被心高气傲的冒襄视为榜样的方以智,却遭到了士人们的围攻与唾骂。相反的是龚定孽,在反复无常的纷变中随波逐流,保住了性命,保住了官职。这场历史的闹剧将许许多多的士人悲欢离合、痛苦绝望、欢悦向往等精神上的错位、反差与惶惑表现得入木三分,从根本上消解了他们原先崇尚的“意义世界”。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塑造知识群体形象时,他总是充裕自如地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精神世界的里层细处,大胆还原早已逝去的古人的心迹。这种充裕自如与大胆是基于详尽地掌握史料,清理出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脉络,再造真实的历史氛围和历史情绪之上的。作者不是代古人立言,不是披戴古人的面具言说当下人的心境,而是自我退隐,让古人出场,随着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演绎着彼此的心路历程。这种心理真实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物性格的流露,而是真切细微地指向乱世时代:它写出天崩地解的非常时期,个体在面临飘渺不定而又具有极大恐吓力的生存危机面前的精神心理振荡以及人性的裂变与扭曲。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三卷冒襄偕同家人逃难的有关情节描写。这是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身为贵公子的冒襄坚守名节,带着家眷逃到浙江海宁一带,途中受尽了清兵以及南明官兵的骚扰,将物质的贫寒、困顿、饥饿一一领教,蒙受巨大的耻辱、痛苦、惊惧。逃难的冒襄始终笼罩着死亡的威胁,即将降临却又万幸得以逃脱;死里逃生之后带给他的并不是如释重负,而是心有余悸以及结伴而来的莫大人格侮辱。他眼睁睁地看着清兵强暴自己的女仆,平常的仁义道德轰然解体,人在死亡和暴力面前变得如此的渺小、如此的鄙琐。死亡消泯了人的雄心壮志,剥去了人的虚幻理念,甚至激发起人性深处潜伏的兽性的东西,人在死亡威逼下放弃了道德的规范,死亡使人的生存问题突现出来,变得是那样的现实和具体。作者就是这样,将贵公子冒襄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用近乎新写主义的笔法,以低位的叙述语调揭示了他的怵目惊心的生存状态。这种历史心理化和心理历史的描写,无疑大大深化、细化了他笔下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三、叙述心态的自控与风格的冷静
《白门柳》洋溢着现代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决不是单一的理性批判,而是带有人文的激情、理想的色彩。这是一种复杂的融合,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一种叙述体态的分裂;叙述心态的自控与人物的激情相矛盾。叙述者游离于人物之间,而与隐在的读者结成同盟:人物在叙述者真实的历史氛围中自由地出场,自由地抒发激情。这无疑显示了作者在叙事上的努力,力图用自己的方式说出对历史的独特话语。
通览全书,我们随时可以发现叙述者的露面,他常常在每一个章节的开端走出来,潇潇洒洒地给读者指点江山。从他的口中,我们知道了那一段特定的历史背景,了解了当时的风俗习惯,懂得了历史典故,也知道了即将开始的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及主要人物。叙述者的出现常常意味着小说视觉的改变,焦点的调整,空间的转换,人物的变更。他的魅力无穷,无论故事情节怎样紧张,人物怎样痛苦,他总是显得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悉心用缜密的工笔描摹着精致的画面;他似乎脱离故事,悠悠然有了一种冷静,一种理性的自我控制,避免让自己陷入到激情的泥潭中不可自拔。这与作者避免激情式的政治评判和道德的评判有极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叙述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介入故事文本中,用这一份清醒揭示着读者,这就给读者提供理性思考的保证,从而达到自己预设的文化思考的艺术目的。
这种自控的心态为小说的叙述风格平添了一种冷静的色调。此所谓的冷静包括许多方面。首先表现在叙述频率上的变化。我们知道,《白门柳》每一卷反映的时间都只有一年左右,但人物众多,头绪复杂。面临庞大的叙述体,怎样将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就成了创作中相当棘手的问题。作者将视点集中在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襄与董小宛、黄宗羲三组人物上,对他(她)们进行理性的调配,将主要人物的故事相互穿插;在一组人物故事发展最吃紧的时候,忽然中断叙述,而讲述起另一组人物的故事。这种叙述方式即蒙太奇手法,但在作品中却带有特殊的意义。传统历史小说叙述人本来具有说书人的味道,但经作者这么一改造,叙述人不仅有效地将故事的来龙去脉贯穿起来,将故事的背景、历史知识、典籍掌故说给读者听,而且传统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也富有意味地变成了两朵花同时表述,单向型的时间性向着并置型的空间性转换,古典的叙述方式质变为现代性的叙事策略。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一方面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表达内容,使之出现1+1>2的结果; 同时使用蒙太奇手法也有利于作者的高位叙述:作者站在高于作品的位置,统观全局,进行有利于自己作品主题表达的组接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冷冷地截断一个故事的自由流向,使作者不动声色地去诉说另外的故事。
诚然,蒙太奇式的穿插是指不同情节的相互交融,不过在同一情节中,作者也有叙述与描写的穿插。我们常常忽视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其实在《白门柳》中,这两种方式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叙述者通常以淡淡的口吻叙说,描写往往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或感受或想象等人物的主观视角来传达,从而显得富有激情。因此,在故事的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的进程中作者常常加进淡淡的叙述,或议论或抒情或写景,以淡远闲散的情致将故事隔离开来,从而使整部小说显得有张有驰,疏密相同;不是一味紧张激烈,而是有意识地冷观。
作品的景致描写也别开生面,具有自己的特点。作者常常将景致安排在人物活动中,篇幅不长,并且一般都是通过人物所见所感而出现,如落日、冷月、晚风等意象。在景物的空间,人物通常是抬头望天上的日月,心中想着烦恼的现实,一面感受着嗖嗖晚风的吹拂:这是一幅人物受痛苦煎熬、遥望理想的人间画像。此时的景物多为冷色调倾向。另外,景物描写融入到故事情节中,围绕着人物的活动,也不时地隐现。作者借用古典诗词的意境,采用了象征暗示的方法,以增强作品的不确定性和空白点,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力,追求超越时空、富有审美的艺术境地。随便拈一个例子,如写柳如是伴随钱谦益南京赴任一段文字,其中提到她走下船去,接下来作者有意宕开一笔,描写柳如是举目远眺:看到枯萎泛黄的秧苗,荒芜的田野。她凝视着那一轮被晚霞笼罩的苍茫落日,一任野生吹来的冷风把她的一双雪白的衣袖吹得象鸟儿的翅膀上下翻飞。作者借用落日、田野、晚风等意象,在文本中建构起广阔的景物“场”。在“场”中,人物的静与衣物的动形成极富意味的张力;在枯黄与昏红的铺垫下,白色显得异常的醒目。作者用粗疏的笔致淡淡地勾画,折射的是柳如是在钱谦益即将上任时,由欢悦转至萧瑟冷落的情绪。钱谦益无意中道出的《昭君出塞图》,更具有暗示的功能;苍凉的景致同样带着象征的色彩,这在有意无意中埋下了预示整个江南前景惨淡的伏笔。作者不是一言道尽,甚至连柳如是到底想的是什么都没有细述,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和填补。这种景致的描写无疑渗透着古典文学的美学情愫,它强化了上文所说的淡远闲散的情致,与叙述的冷静相得益彰。
与叙述的冷静相反,是作品中的人物被赋予充沛的情感。且不说激情昂扬的黄宗羲,患得患失的钱谦益,孤独易变的冒襄,易暴易躁的阮大铖等都显得情感丰富。即使是一般人物如黄澍,也有如此的特征。他一出场,作者就把他这种情感状态渲染得淋漓尽致:写他不仅敢于在皇帝面前情绪激昂、语锋凌厉地陈列手握实权的马士英十大罪状,侃侃而谈;说到动情处,泪如雨下。为什么《白门柳》中的人物有如此的激情呢?我们认为除去性格因素之外,恐怕与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面对外界的无序,内心深处浓烈的情感油然而生:可说是人物的激情是时代的折光,是历史情绪的写照。有意思的是,这种激情与作者冷静的叙述心态相互比照,历史的情绪与当下的心态互为补充。作者没有在背后评议他的主人公,而是给人物创造机会,让人物自我展示、自我表达,对主人公的议论了如指掌。作者与人物进行平等的对话,没有强制干预人物的激情抒发,从而获得了抽身于历史之外的冷静反观历史、审视现实的艺术效果。如此这般,抓住了历史情绪,真实地重构了历史图景。
标签:白门柳论文; 黄宗羲论文; 钱谦益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刘斯奋论文; 柳如是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明末清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