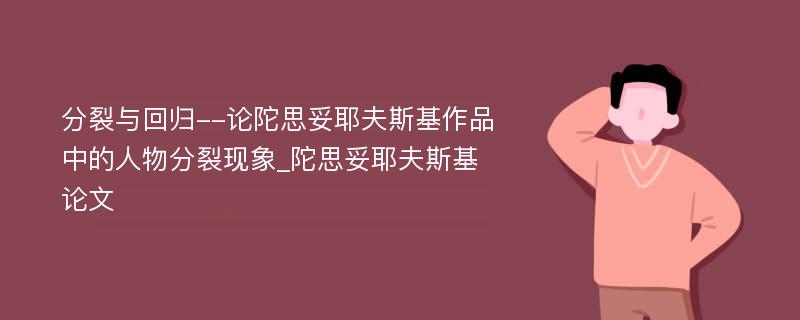
分裂与回归——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性格分裂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基论文,笔下论文,耶夫论文,性格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社会和心灵两个层面,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性格分裂现象形成的原因,分析了这种分裂的真正内涵和性质。文章还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人道主义宗旨、宗教观以及艺术观,指明了回归的必然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大量地描绘了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的性格分裂现象。尽管这一现象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人们似乎并未能揭示出它的真正内涵和性质,往往只看到分裂与病态、压抑与变形,未能看到隐藏在分裂之下的对于回归与统一的强烈冲动与愿望。
一、对分裂现象的误解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性格分裂现象,最早提出彻底批判的是别林斯基,这可以说是误解的开始。1846年1月,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中篇小说《二重人格》,作品第一次描绘了卑贱的小官吏在被压迫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性格分裂现象。作者本人对此很满意,以致在晚年谈到这部作品时,仍很自豪地说:“小说中的思想是相当明确的”,“我从未把任何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1〕。 别林斯基显然没有理解作者本人甚为得意的“严肃思想”,因而对这部作品作了毫无保留的否定,在其所著的《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中,他严厉地指出:“在《二重人格》里还有另外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他的幻想色调。幻想这东西,在我们今天,只能在疯人院中,而不是在文学中占有地位,应该过问的是医生,而不是诗人。”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评论家的这番话等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逐出了文坛,取消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起码资格,这无疑是片面的。但是,考虑到别林斯基所处的充满尖锐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如此断言也并非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一个不仅关心现实,而且参与现实斗争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别林斯基的逻辑显然是:既然有压迫,就应该立刻与之进行斗争。至于这压迫在人的心灵中造成了什么影响,使之产生了何种变化,如何才能得到拯救等,并未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重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别林斯基未能看到这部作品蕴藏在“幻想色调”之下的深刻社会内涵。我们处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当然不能要求19世纪的别林斯基既做到这一点,又做到那一点。然而,别林斯基本人恐怕也没有想到的是,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二重人格》中人格分裂现象所持的否定态度以及其所依据的社会批评原则,由于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不仅影响了与之同时代的人,也影响了随后超过百年之久的人们对此现象的看法。如1913年,高尔基便撰文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津津有味地描写病态的淫虐狂和被淫虐狂的“恶毒天才”〔2〕;在出版于1956 年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中,前苏联著名的研究专家叶尔米洛夫也认为《二重人格》的“意义深长的主题”,被作者从“社会的范围转移到精神病学的范围去了”〔3〕。可见,这种单纯从表面的社会功利角度所进行的批评, 在前苏联的这段漫长的时间内并未得到任何改变。
我国传统上对此问题的研究,基本因循别林斯基等人的观点。近年我国批评界又借鉴西方采取的研究方法,侧重于从现代派艺术理论的视角来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性格分裂现象。如有人将此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联系在一起,以“压抑机制”、“反向作用”、“文饰作用”等精神分析学说中的原理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出现的病态心理问题。应该说,这类研究也是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全面地理解这位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深层含义无疑具有启发作用。但是,如果说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传统批评由于专注于作为群体的社会而对个人重视不够,从而无法认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揭示人的心灵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超前的历史意义的话,那么,这类从西方现代艺术观出发所进行的现代批评,则由于过份专注于心理的病态现象,只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注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派的启示”,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揭示其真实的含义。我们认为,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是应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自身的心灵实际情况出发,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人道主义宗旨、宗教观和艺术观来进行。
二、分裂的双重原因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究竟有哪些人会发生性格分裂。显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发生性格分裂的往往是那些触犯了道德规范,做出了有损于他人行为的人。而且,如果我们仔细地思索一番,便又会发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两类人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一类是真正丧尽天良的恶人。这类人真正具有“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也在所不惜的气概,面对由于自己的行为带给别人的伤害和痛苦,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事后也绝无反悔,有着完全不带形容色彩的铁石心肠。鲁迅曾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要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4〕。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无论如何也无法在这类人的内心深处找出这种“洁白”来。这类人包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罪与罚》中的彼得·卢仁、《群魔》中的强盗费季卡等。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还有另一类被作者本人称之为“罪人”的人。如果仅就他们对别人所犯下的罪这一点来说,这类人与上文所说的恶人并无区别,为了成就自己的私利,也都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牺牲者。这类人包括《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伊凡等。我们常常谈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性格分裂现象实际上只发生在这类所谓的“罪人”身上。为什么恶人与“罪人”犯下同样的罪行,只有后者会产生性格分裂,而前者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这里首先存在着外在的社会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生逢沙皇俄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虽然它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其所带来的对金钱赤裸裸的崇拜已对人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腐蚀作用;而封建的官僚们仍然控制着当时的政局,等级依旧森严。在这双重压迫之下,“基本社会信念摇摆不定”,人们相互隔绝,各行其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翻过来了”〔5〕。 他的艺术创作活动便建立在这样充满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思考之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罪人”往往生活在社会底层,处于毫无保障的社会地位。在饱尝了社会的压迫之后,他们往往极容易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思想发生混乱。但如果我们单纯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是无法解释这些“罪人”的性格分裂现象的。因为在恶人中,也有很多人处于与“罪人”相同的社会地位或陷于相似的生活困境的。如果仅改变外在的社会条件,显然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因此,造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些“罪人”性格分裂的,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另外的更深层的原因。这原因便是在这类“罪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着强烈的能够区分善恶的道德感。正是这种道德感的存在将他们与恶人区别开来了,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所作的是“恶”,从而在内心深处进行着激烈的善与恶的斗争,构成了性格分裂的深层原因。这种使他们有别于恶人的道德感使我们想起了康德的实践理性学说。在康德的眼中,人类的道德意识是先天就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并具有非执行不可的“自律性”。康德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康德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罪人”。在这些“罪人”的心灵深处,良心不断地发出呼唤,呼唤他们的行为与其内在的道德感保持一致,以保证心灵的平静与和谐。然而,他们在现实中的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前,往往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时屈服于社会的压力和个人的欲望,做出了与其内在道德法则相违背的事。
康德在解释人类的道德实践时,也看到了“在现实世界有德之人未必有福,享福之人多系歹徒”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康德作出了“神的存在的公设,以作为实现‘至善’的前提”,完成“德与福的统一”〔6〕。由此可见,康德引入上帝(神)的概念, 是作为不可证明然而也不可怀疑和否定的“公设”,是为了完成人类的道德实践必须如此不可的。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罪人”们显然不像康德这么单纯,不会在消极中等待上帝的奖赏,这些充满思想的人对上帝和宗教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了种种责问。这也是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观点的。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时,曾致信给冯维辛娜,信中言及他对此的看法:“我私下告诉您,我是时代之子,无信仰和怀疑之子,直到现在甚至(我自己知道)直到死。对信仰的这种渴望已经并且现在还在使我受到极其可怕的折磨,它在我的灵魂里愈是强烈,在我身上就愈多相反的理由。”〔7〕 在现实的压迫和对信仰怀疑的双重压力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罪人”的心灵无法承受了,因而各诉其言,呈现出分裂状态,表现出种种疯狂、甚至是病态的举动。虽然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对别人、也对自己的良心诉说着自己的不幸与无奈,可还是得不到良心的宽恕,找不到回归心灵和谐的路,无法实现精神的统一。于是,他们往往在这巨大的心灵冲突与痛苦的矛盾之中毁灭了。这样的结局常常引起人们对他们深切的同情与感叹,而不是如同对恶人一般的仇恨和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巨大的艺术效果也往往由此而实现。
三、寻求解脱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人”在精神上虽然处于病态的分裂状态,但他们无一不深受其苦,渴望统一。为了平息内在良心的谴责,逃避分裂状态,他们试着寻找种种理由,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由此显示出了纵横捭阖的气势,并广泛地涉及到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第一个性格分裂者,《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对达官贵人们由于拥有权势而带来的威风以及处事手段的卑鄙既感不满,同时又企图追随他们,试图能像这些人一样玩弄手段、为非作歹而又逍遥自在。高略德金的这一思想如同巴赫金所指出的那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转化成了形象,于是在高略德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集一切丑恶于一身的小高略德金。开始,高略德金对此似乎非常满意,他对小高略德金说:“让咱们也来耍耍滑头……也来搞阴谋”。应该看到,像小高略德金这样的无耻之徒在当时的俄国社会遍地皆是,这些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阴谋”和“滑头”而在内心产生任何疑虑。他们心安理得地认为这一切都很正常,因为大家都如此嘛!然而,高略德金却因此而产生了性格分裂,直至发了疯。这说明了什么呢?很明显,它表明了高略德金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虽然充满了认识混乱,但无论这种混乱如何强烈,还是无法蒙蔽其内在强大的道德感。显然,以高略德金的身份,如果严格按照内在的道德法则行事,他是无法在当时的社会中像一个人那样活着并与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于是,他试图放弃内在的道德法则,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合污同流”,以争取做人的权利。可高略德金内在的道德感是如此强大,以致于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心平气和地与别人一样做出丑恶的行为。如此,心灵成了充满激烈斗争的战场,争斗的双方互不相让,各据其理,性格分裂已势在必然。这样的分裂状态毫无疑问地带有病态色彩,然而它却对造成这种分裂的丑恶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因此,高略德金的发疯实际上是从心灵的层面对当时是非颠倒的黑暗社会发出的强烈抗议。这一点恐怕是别林斯基未能看到的。在高略德金的发疯中,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些“罪人”内在道德感的巨大力量,它具有冲破一切阻力也要去执行的不可阻挡的冲动。这种对回归的强烈渴望,显然未能被我国的那些受西方现代派艺术观影响的批评者所充分认识,他们往往只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性格分裂现象,并对此作了有悖于作者本人意愿的理解。
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无论什么理由也无法与强大的内在道德感相对抗。如果他们不放弃作恶的念头,是永远也找不到回归之路的。《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以理性法则为支撑,《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以社会压迫为借口,《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以证明自我意志力的无限强大为准则,均无法获得成功。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伊凡·卡拉玛佐夫试图以传统宗教为突破口,以否定宗教以及上帝威力的存在来达到作恶的自由,借以摆脱内在良心的束缚。因此,宗教问题实际上成为全书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上帝的存在与否,成了个人是否有犯罪自由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于宗教的矛盾思想。关于宗教问题,他曾指出:“横贯在全部小说内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就是我一生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烦恼着的——便是上帝的存在的问题。”〔8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作家在这部具有总结意味的作品中所给予我们的关于宗教问题的答案。伊凡痛恨其荒淫无耻、贪婪成性的父亲,又爱上了兄长德米特里的未婚妻卡杰琳娜。因此,当德米特里抛弃了卡杰琳娜,爱上了他父亲也垂涎三尺的格鲁申卡,从而与其父发生激烈冲突时,伊凡是非常愿意看到父兄矛盾深化尖锐,拼得两败俱伤的。然而,内在的道德法则又禁止他这样做。于是,他向传统道德象征的宗教开战了。他用无辜的孩子的眼泪彻底揭露了宗教上帝的虚伪和无能,使他的弟弟、宗教信徒阿辽沙对摧残孩子的凶手,说出了他虔诚至信的上帝以及不允许他说的话:“枪毙”!由此,伊凡彻底摧毁了宗教的束缚,获得了作恶的自由。于是,他暗示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他的父亲,而罪责则由性情暴躁的兄长德米特里承担了。至此,伊凡的阴谋可以说是完成得天衣无缝,卡杰琳娜也当众公开地宣称深深地爱着他。倘若伊凡真是彻头彻尾的恶人,便会愉快地坐享其成。然而,正是在这一阴谋大功告成之际,因否定了宗教上帝威力而得以暂时麻痹的内在良心发出了强烈的声音。这声音又一次变成了形象,出现在伊凡面前,向他昭示了他的全部罪恶。伊凡竭尽狡辩之能,也无法挥去这一如影随形般的形象,于是他的心灵不可阻止地发生了混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性格分裂再次出现了,以致伊凡“渐渐完全失去了知觉”。作者也由此向我们表明了他本人对上帝、对信仰、对宗教的态度:即使我们否定了能够在传统宗教中起惩恶扬善作用的上帝,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可在这自由之中,人还是不能作恶,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无法毁灭的道德感。
四、回归的必然
伊凡的这种结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几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无论罪恶的诱惑来自何处,强大的道德感总是在这些所谓“罪人”的心灵深处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诉说着自己的话语。当这样的话语与罪恶的欲望一时无法决出胜负,处于激烈的矛盾与对抗时,人物的心灵便呈现出分裂的状态。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格分裂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性格分裂只是一段心理发展的过程,一种暂时的状态。这不仅是由于发生性格分裂的这些“罪人”心中存在着具有判别善恶是非的道德感,也是由于这位作家本人的艺术观、审美观决定的。作为一个自称要“刻画人心深处的全部奥秘”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实、对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说:“被大多数人几乎称为幻想的、特殊的事物、对我来说常常是构成现实最本质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地描绘了人的性格分裂现象。但我们认为,他不可能停留在人物性格的分裂状态之中,安于心灵的恐惧、怀疑、苦闷,更不可能“喜爱描绘这种黑暗的、混乱的、讨厌的灵魂”。他所以描绘了这一切,仅仅因为在他的眼中,这是“构成现实最本质的东西”,借以向造成这种丑恶与病态的社会和个人主义的私欲表示强烈的抗议。对此,巴赫金在经过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后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此种做法的最终目的是“以完全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并坚持“恢复一个堕落人的本来面目”〔9〕。
一个作家对美的观点和看法,无疑对其作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以更多的所谓独立“思想”,但作家主观的影响还是存在的。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版前言的撰写者钱中文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复调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仍然处于创作主体的制约之中,“归根到底,主人公总是作者这一主体的创造物,总是受制于作者本人意图的”。遗憾的是,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分裂现象时,以往我们很少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关于美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美就是和谐,是平静的保障”〔10〕,这样的美,“体现了人和人类的理想”〔11〕。显然,美的这种“和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所指的正是精神上的和谐。这种“和谐”是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感保持一致的产物,是所谓受到“保障”的心灵的“平静”。这样的“和谐”与“平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全部人生追求,也是巴赫金所说的这类“罪人”的“本来面目”。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开了美,人也许不愿活在世界上。”〔12〕如此对于美的观念,使他认为艺术的作用就在于“以强有力的方式帮助人类发展,通过美感的印象对人类产生作用”。这作用便是帮助人们实现道德上的完善,使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分裂了的人格能够回归到他们内心善良的本性之中,从而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追求的以“和谐”为核心的审美理想。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有过很好的表达,即“希望在长久的修炼之后战胜自己,克制自己,以便通过一辈子的修炼,终于达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自我解悟,避免活了一辈子还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自我的人的命运”。这便是这位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之为“彻里彻外充满斗争的人”所要明确追求的东西。这是真正的善,也是真正的良知,因为它面对了各种诱惑,战胜了各种借口,甚至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性格分裂的状态,因而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宗旨。
因此,我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在其作品中描绘了大量的人格分裂现象,但这显然不是作者本人愿意看到的,更不可能是他“喜爱”的。它只是一种警示,使我们认识到一切恶的丑陋与无能,即使被它折磨得一时分裂了人格,也是一定要回归的。这样的回归便似一颗已经落地的种子,无论严寒酷暑,也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而这果实便是人的至善与至爱。因此,我们认为,这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人格分裂现象的真正内涵和性质。
注释:
〔1〕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2〕高尔基:《论“卡拉玛佐夫气质”》, 《俄罗斯言论报》1913年9月22日。
〔3〕叶尔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4〕《鲁迅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5〕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学创作》, 《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
〔6〕安倍能成:《康德实践哲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7〕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第151页。
〔8 〕转引自扈娟《浅析〈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6期。
〔9〕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99页。
〔10〕〔11〕〔12〕转引自冯增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观初探》,《苏联文学》1985年第6期。
标签: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别林斯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罪与罚论文; 群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