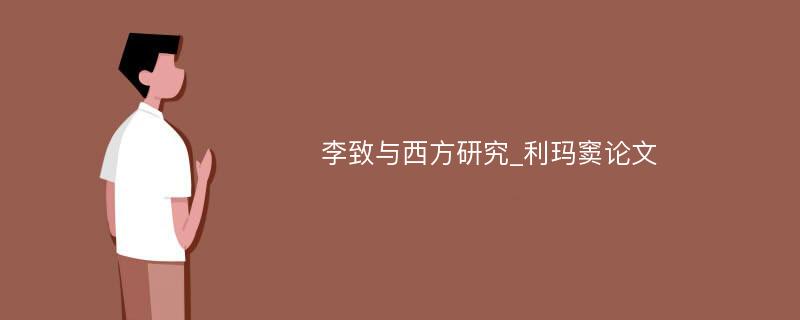
李贽与西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6)04-0110-12 关于李贽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笔者已在《李贽评传》(2006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版)中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和讨论,但对于其晚年思想与西学的关系却探讨不够。最大难点在于,李贽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学的?如果以他与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会见为依据,那就只能定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也就是利玛窦来华17年后,这未免太低估他的信息来源和学术视野了。但定得太早,可能也不合乎实际,因为利玛窦虽然很想把传教事业从广东推进到长江流域,尤其是大明朝的留都,但第一次到南京就遭到了驱逐。虽然李贽的好友汤显祖早在1592年就在肇庆与利玛窦见过面,1595年又再次相遇于江西抚州,但还说不上了解西学。早在1590年就成为利玛窦之弟子的瞿汝夔,虽有“交游遍天下”之称,到处替利玛窦作宣传,而李贽与瞿汝夔之兄瞿汝稷虽有交往,但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证明李贽由此而获得了关于西士和西学的信息。 作为一种比较保守、但却不乏谨慎的立论,我以为可以把李贽接触西学的时间确定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左右。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在南京遭到道学高官徐大任的蛮横驱逐后,却在南昌遇到了与李贽志同道合、且有着极其不同寻常之友谊的江西巡抚陆万垓①。在利玛窦的行李已被南昌旅店老板扔到大街上、即将被赶出江西的紧要关头,是陆万垓亲自接见了利玛窦。乍一相见,他就说,很早就听说了利氏之德行和学识,只是相见恨晚;二人进行了极为亲切友好的交谈,问及利氏今后有何打算,利说将回广东去,陆万垓非常诚挚地挽留了他,让他在南昌自由地从事讲学活动②。陆万垓与李贽早在1572年就已订交而为终生好友,在南京共事五年,离别后两人都写有互相怀念的诗歌,足见深情③。在利玛窦留住南昌的第二年(1596),万垓还与江西宁州知府方沆一起用他们的俸禄为李贽刊刻书稿④。陆万垓病逝后,李贽在南京作《哭陆仲鹤》诗,有“岁岁年年但寄书”之句⑤,可见交往之密切。利玛窦在南昌期间,与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和书院的学子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就一系列学术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在江西及邻近省份的学界皆有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李贽还不知道利玛窦,还读不到传教士写的西学书籍,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儒耶对话作为背景,李贽晚年的一些重要文章和著作中所出现的观点变化和新的思想动向,也就难以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我初步认定,李贽晚年思想是对西学之输入的回应:其晚年阐说《诗》义、发挥《学》《庸》、精研《易》理,是对利玛窦以基督教义来“合儒、补儒、超儒”的回应;以华夏民族为天神之子,是对罗明坚宣扬的“天主造人”和“圣灵降孕而生耶稣说”的回应,亦似可看作力图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初尝试;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之义来批评各种求媚于鬼神的迷信活动和假道学的大言诓人,畅论不可谓祭天为祭理,亦不可谓祭气,是对利玛窦学说的发挥;其《明灯道古录》着力表彰与基督教哲学最近似的墨子学说,似乎也有寻求与西学的会通、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意味;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九正易因》,从“万物统以乾元”推出人人“各正一乾之元”,因而“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更展示了一种以哲学代宗教的新思路。 一、论华夏民族为天神之子及敬天与尊祖的统一——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自古以来,有谁见过借《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来大做文章,说华夏民族都是天神子孙的吗?有之,乃自李卓吾始。自从晚明儒耶对话开始以来,有谁见过通过论证华夏民族皆为天神子孙、把敬天与尊祖统一起来的吗?有之,亦自李卓吾始。 李贽写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冬或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的《鬼神论》一文⑥,明显是在读了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天主圣教实录》和利玛窦《天主实义》以后写的(学界比较认同《天主实义》“1595年初刻于南昌”的说法)[1]。《鬼神论》中关于华夏民族皆为天神子孙之论说,与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讲的“圣灵降孕”说和利玛窦《天主实义》第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第四篇以古经古礼证明有鬼神、驳斥宋儒“理”与“太极”之说,完全是同一思路。但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可以作为李贽确实读过罗明坚和利玛窦著作的佐证,更在于它所具有的独创性,证明了李贽这位自称“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的人,这位被利玛窦称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⑦的人,确有比西方传教士更高的见识,具有西方传教士所不具备的作为中国人追溯自己民族文化源头的伟大历史感。 (一)“夫有鬼神而后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 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后刊刻的第一本中文教理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刊刻于广州(一说肇庆)。该书除了备论“天主制作天地人物”、讲经院哲学关于天主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之外,还讲述了基督教的“圣灵降孕”说,即圣母玛利亚作为童贞女感孕而生耶稣的故事,其说云:“天主选择世间良善童贞女,名玛利亚。是为圣母,不由交感,童身而受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拉丁文spiritus,圣灵——引注)之降孕。圣母玛利亚孕九月而生耶稣。既生之时,并无半点污秽,仍前全体之室女。譬即太阳射光于琉璃瓶中,光虽在内,而琉璃瓶依旧不穿漏也。”[2]类似的故事,古代希腊人也有,即著名的丽达与天鹅的故事,它打上了以“booty and beauty”为追求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印记;但只有中国古代的类似故事,方具有基督教“圣灵降孕”说的圣洁意蕴,而又全然没有耶稣降世为世人赎罪的悲苦色彩。李贽的《鬼神论》一文,就是从罗明坚和利玛窦都没有注意到的中国古代的类似故事说起的。 《鬼神论》开篇就畅论周族的始祖后稷乃天神之子。他说:“《生民》之什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祓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朱子曰:‘姜嫄出祀郊禖,见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祀典,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诗,以推本其始生之祥。’由此观之,后稷,鬼子也;周公而上,鬼孙也。周公非但不讳,且以为至祥极瑞,歌咏于郊禘以享祀之,而自谓文子文孙焉。”[3]85所谓“履帝武敏歆”,那巨大的脚印正是“上帝”的足迹;所谓“周公非但不讳,且以为至祥极瑞”,于是“歌咏”之,“郊禘”之:“歌咏”者,颂天神也;“郊禘”者,祭天神也。这是华夏民族祭祀自己的在天之父的隆盛风仪。 篇末又追溯到殷商的始祖契,认为契也是天神之子,进而畅论华夏民族都是天神子孙。他说:“《玄鸟》之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又曰:‘浚哲维商,长发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鸟降,有戎氏女简狄,高辛氏之妃也,祈于郊襟,鸵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遂为有商氏而有天下。’呜呼!周有天下,历年八百,厚泽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贤圣之王六七继作,鸟之遗也。”[3]87在基督教教义中,圣灵的象征是可爱的小白鸽;在中国古代,是上天在春分时节派来的美丽的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里没有古代希腊人和现代爱尔兰诗人对民间女子与“天空中野性的血液”之销魂结合的刻意渲染,却有对华夏民族子子孙孙生生不息的由衷赞美。 罗明坚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圣灵降孕”说,但却没有发现中国经典中也有类似传说;利玛窦博引“六经”来证明中华先民也有上帝信仰,也没有注意到《诗经》中关于殷周民族起源的诗篇。直到100多年后的西方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才以“圣灵降孕”来阐释“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以如诗如画的语言,描述了姜嫄在春天的原野上与圣灵的遇合,向法国人展现了一位美丽、虔敬、圣洁的中国圣母形象:“她鼓足勇气献上牺牲,内心充满了崇高的爱的激情,这种爱来自意欲拯救众生的天上的夫君。她缓步踏着至亲至爱的人的足迹前行,全神贯注地等待着祂的神圣决定。她内心纯真的祭献之情在上帝眼前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神灵的美德瞬时便进入她的子房。她那处女的身体突然感到一阵骚动,后稷就这样孕育在她的腹中。”⑧[4]在白晋的笔下,中国圣母的美好形象比基督教《圣经》和文艺复兴时代绘画中的西方圣母更动人,这是他对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研究的一大贡献。但与李贽追溯中华民族文化源头的立意相比,毕竟还是略逊一筹。 讲中国先儒的天神信仰必然要与宋明理学家的观点发生冲突。利玛窦《天主实义》回答了中士关于“不知吾国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实为正道”的问题,指出:“异端炽行,譸张为幻,难以攻诘,后之‘正儒’其奈何?必将理斥其邪说,明论鬼神之性,其庶几矣。”[5]他认为要批驳宋儒的观点,只有通过“明论鬼神之性”的途径,而这也正是李贽的思路。在李贽看来,既然华夏民族都是天神子孙,那么,人们就不应当讳言“鬼神”;而后世儒者之所以讳言,乃是由于“未尝通于幽明之故而知鬼神之情状”的缘故。如此巧妙地把传教士宣扬的“天主制作天地人物”与“圣灵降孕”说糅合在一起,来论说“有鬼神而后有人,故鬼神不可以不敬”,凸显华夏民族皆天神子孙之义,把敬天与尊祖统一起来,真可以说是李贽的一大发明了。 (二)“若诚知鬼神之当敬,则其不能务民之事者鲜矣” 由华夏民族都是天神的子孙,合乎逻辑地推出人应当尊敬天神的观点:“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不与祭,如不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夫子之敬鬼神如此。”[3]86此时,李贽已不再讲“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孔子敬鬼神来论证尊天事鬼的合理性了。利玛窦《天主实义》第四篇《辩释鬼神及人魂异论》中亦说:“吾遍察大邦之古经书,无不以祭祀鬼神为天子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岂无其事而故为此矫诬哉?”[5]33比较此二人的论述,何其相似乃尔! 更有甚者,是李贽像传教士们所宣扬的那样,认为人如果不信神就会什么坏事也做得出来。他说:“使其诬之以为无,则将何所不至耶。小人之无忌惮,皆由于不敬鬼神。”[3]86但这里又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所说的小人不敬鬼神而无忌惮的表现,是“不能务民义以致昭事之勤,如临女以祈陟降之飨”,意思是说只有“务民义”——切切实实地关心民众的疾苦——才是真正的“昭事之勤”。他还是引孔子的话来证明这一观点:“故又戒之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事人即所以事鬼,故人道不可以不务。则凡数而渎,求而媚,皆非敬之之道也。夫神道远,人道迩。远者敬而疏之,知其远之近也,是故惟务民义而不敢求之于远。近者亲而务之,知其迩之可远也,是故不事谄渎,而惟致吾小心之翼翼。”[3]86总之,对神的敬畏应当体现在小心翼翼地维护民众的利益上。 与利玛窦着重批评宋儒“将排诋佛老之徒,而不觉忤古圣之旨”不同,李贽着重批评的是宋儒的“假”。从孔子关于“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的观点出发,李贽展开了对各种求媚于鬼神的迷信活动,对与鬼神做交易的渎神行为,特别是对那些既要求神护佑、又要大言诳人曰“佛、老为异端,鬼神乃淫祀”的假道学的抨击。他说:“今之不敬鬼神者皆是也,而未见有一人之能远鬼神者,何哉?揲蓍布卦,卜地选胜,择日请时,务索之冥冥之中,以徼未涯之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其谄渎甚矣。而犹故为大言以诳人曰:‘佛、老为异端,鬼神乃淫祀。’慢侮不信,若靡有悔。一旦缓急,手脚忙乱,祷祀祈禳,则此等实先奔走,反甚于细民之敬鬼者,是可怪也!然则其不能远鬼神者,乃皆其不能敬鬼神者也。若诚知鬼神之当敬,则其不能务民之事者鲜矣。”[3]86这些论述,与传教士在中国所宣扬的观念,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谓祭天所以祭理,可欤?谓祭鬼神是祭良能,可欤?” 在批评了各种求媚于鬼神的迷信活动和假道学的大言诓人以后,《鬼神论》又展开了对宋儒朱熹关于“以天为理”、以鬼神为“二气之良能”的批评。他写道:“朱子曰:‘天即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夫以天为理可也,而谓祭天所以祭理,可欤?以鬼神为良能可也,而谓祭鬼神是祭良能,可欤?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后祭天地,则是必天子而后可以祭理也,凡为臣庶人者,独不得与于有理之祭,又岂可欤?然则理之为理,亦大伤民财,劳民力,不若无理之为愈矣。圆丘方泽之设,牲币爵号之陈,大祀之典,亦太不经;骏奔执豆者,亦太无义矣。国之大事在祀,审如此,又安在其为国之大事也?‘我将我享,维羊维牛’,不太可惜乎?‘钟鼓喤喤,磬箢将将’,又安见其能‘降福穰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也?”[3]86 这段论述,畅论祭天不可谓祭理,祭天亦不可谓祭气,更热烈讴歌古人祭天大典的隆盛风仪,不仅完全是利玛窦《天主实义》的腔调,而且简直是对利玛窦所阐述观点的出色发挥了。利玛窦《天主实义》以主张理本论的宋儒为主要的批评对象,畅论理是依赖者,不是自立者,故不可谓理为万物之本原,对祭天不可谓祭理有很详细的论述;同时亦指出,“所谓二气良能、造化之迹、气之屈伸,非诸经所指之鬼神也”[5]34,因而祭天亦不可谓祭气。后来黄宗羲作《上帝》一文,讲祭天不可谓之祭理,亦不可谓之祭气,论者皆云这是与利玛窦同一腔调,殊不知李贽早已开其先路矣。 传教士们所宣扬的灵魂不灭及天堂说在李贽的《鬼神论》一文中也有所反映,不过,与传教士的观点有所区别,——利玛窦虽然尊重中国人祭祀祖宗的习俗,但并不重视,——李贽却非常重视对祖宗的祭祀。他写道:“《商书》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曰:‘乃元孙不若旦多才多艺,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灵,赫然临女,则尔祖我祖,真同儿戏。”[3]87李贽写《鬼神论》一文时,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已十几年,是该中国化了,而李贽的这篇文章,在当时传教士唯重敬天、不重敬祖的情况下,以论证华夏民族为天神之子孙为前提,把敬天与敬祖统一起来,正可看作是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初努力和尝试。 二、“道无绝续,人具只眼”——《明灯道古录》的创见与西学之关系 与写作《鬼神论》差不多同时,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李贽在山西沁水与刘东星及其子侄秉烛夜话,对话的部分内容由刘东星之子用相、侄用健记录下来,是为万历二十六年刊刻的《明灯道古录》(又称《道古录》)一书。在该书中,李贽从华夏民族皆为天神之子的观点出发,融合儒、佛、耶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进一步阐明了“庶人与天子等”的平等观念,提出了“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光辉命题;又进一步批评宋儒“道统论”之妄自尊大,阐扬了“人无不载道”、“道无绝续,人具只眼”的思想文化多元论观点;似有感于墨子学说与西学最为相似,故大为表彰墨学“唯知神之与民”的特色,盛赞其可以“平天下而均四海”。《明灯道古录》受西学之影响或启迪的方面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的哲学精神。如今很多哲学研究者动辄以绝对真理的化身自居,说到底也就是因为缺乏“认识你自己”这一真正的哲学精神。 (一)“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从区分自立者与依赖者的观点出发,确认人是自立者,理是依赖者,明确提出了“理卑于人”的观点[5]20。但利玛窦也强调了身为人必须正确“认识你自己”的必要性,“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因而不可以人比拟天主。这实际上是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认识永恒、无限、绝对的真理。但像宋儒那样以为“一物之性即天地万物之性”,却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把人性混同于物性了。结论是:“以人为同乎天主,过尊也;以人与物一,过卑也。”[5]44用今天的话来说,人既不能夸大自己的能力,以为人可以像神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又不能贬低人的能力,以至于把人等同于万物,抹杀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 在利玛窦讲“理卑于人”之前很久,李贽在万历十六年(1588)的《初潭集》序言和万历十八年(1590)的《焚书》等著作中就已表达过类似观念。如《初潭集》序言讲“夫厥初生人,唯是阴阳之气、男女二命耳。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等等[6]1。作为儒耶对话的积极成果,李贽晚年的《明灯道古录》在解释《大学》关于“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时,别出新意地提出了“庶人与天子等”、“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光辉命题。他说:“而通曰‘壹是’,何也?且既曰‘壹是’,则庶人与天子等矣。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亦无一人不当立其本者,无是以未能无疑。”[8]353这里所讲的庶人与天子等和以个人为本是否仍是传统的修身意义上的呢?不然,李贽是在借题发挥来阐释近代平等观念和个性主义原则,所谓修身为本是以“无一人不是本”为前提,这是前人从未讲过的;另外,这一点还可以从他讲的人人“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之义见之。明确揭示出以人为本必须落实到个人,这是李贽的一大思想贡献。 进而,他又把利玛窦讲的“以人为同乎天主,过尊;以人与物一,过卑”的说法转化为对“为天子者,自视太高”、“为庶人者,自视太卑”的批评。他说:“观今之天下,为庶人者,自视太卑;太卑则自谓我无端本之责,自陷其身于颇僻而不顾。为天子者,自视太高;太高则自谓我有操纵之权,下视庶民如蝼蚁而不恤。天子且不能以修身为本矣,况庶民耶?”[11]353他认为传统社会的根本弊病就在于天子“自视太高”而庶民“自视太卑”,一切社会罪恶皆由此而来。君主和士大夫的自视太高、自我神化,是专制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百姓的自视太卑、自轻自贱,则又是使专制主义得以维系和持续的认识论保证;而无论是自视太高还是自视太卑,都既不合乎“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的原则,也是缺乏“认识你自己”的哲学精神的表现。 (二)“人即道,道即人,人外无道,道外无人” 反对宋儒的道统论是李贽一生所坚持的观点。早在万历十六年(1588)刊刻的《初潭集》中,李贽就指出,以颜回之死为标志,儒学就失传了。孔子的其他门徒,已被富贵移心,哪里能够传道?从汉儒到宋儒再到明儒,大家都以孔学正统自居,然而却是“人益鄙而风益下”⑨。又说:“孔尼父亦一讲道学之人耳,岂知其流弊至此乎!”[6]216如果说道学与孔学有什么学脉传承的话,那么道学家们恰好是把孔学的弊病恶性膨胀了。在万历十八年(1590)刊刻的《焚书》中,李贽已具有了他晚年所概括出的“人无不载道”的多元论观点,认为“道”在“耕稼陶渔之人”心中,在“市井小夫”、“作生意者”心中,在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千圣万贤”的心中,“吾惟取之而已……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7] 李贽晚年的《明灯道古录》,更为鲜明地提出了“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的观点[8]372。根据这一文化多元论的观点,李贽在次年刊刻的《藏书》中对儒家的道统论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他说:“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也,审矣。而谓水者有不流,道有不传可乎?……彼谓轲之死不得其传者,真大谬矣。惟此言出而后宋人直以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谓为知言云。吁!自秦而汉而唐而后至于宋,中间历晋以及五代,无虑千数百年,若谓地尽不泉,则人皆渴死久矣。若谓人尽不得道,则人道灭矣,何以能长世也?终遂泯没不见,混沌无闻,直待有宋而始开辟而后可也,何以宋室愈以不竞,奄奄如垂绝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传者哉!好自尊大标帜,而不知其诟诬亦太甚矣。……要当知道无绝读,人具只眼云耳。”[9]李贽坚信:学术是多元的,道也是多元的;学不能统,道也不能统。 也许,正是受到利玛窦所阐扬的“认识你自己”哲学精神的启迪,李贽才会如此重在批评韩愈和宋儒“好自尊大标帜”的谬误。自称可以代表天地、生民、圣贤和万世的儒者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对于人的认识能力之清醒的自我认识。韩愈说道统在孟轲以后就不得其传了,目的是标榜自己是直接孔孟的道统传人,而朱熹又通过揭发韩愈与禅师有书信往来,否定韩愈作为道统传人的资格,并由此驾而上之。在李贽看来,这都是“好自尊大标帜”、“诟诬亦太甚”之行为。李贽根本否认“道”有什么绝续,更否认宋儒鼓吹的以理学直接孔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道统说。他认为,“道”就在人民的生活之中,在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之中,“人无不载道”犹如“水无不在地”,无所谓断续。所谓“人无不载道”,“道无绝续,人具只眼”,正是对每一个人皆可以其特有的方式去寻求“道”这一天赋权利的充分肯定,亦即对每一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的充分肯定。 (三)大禹和墨子“唯知神之与民”,其“经纶之术”可以“平天下而均四海” 李贽表彰墨子,从早年就开始了,现存的《墨子批选》二卷就是万历三年(1575)刊刻的,此时西方传教士尚未来到中国。但此后直到晚年作《明灯道古录》以前,李贽似乎都没有特别表彰墨子的言论。《明灯道古录》特别表彰墨子,亦如他此时作《鬼神论》讲中华先民的天神信印一样,皆有儒耶对话的背景。19-20世纪的中国学者多意识到,在中国哲学的各学派中,唯有墨学与基督教最相似,如墨子讲“天志”,讲学者和帝王皆“不可以为法仪”,讲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与耶稣皆具有坚苦卓绝的精神,墨学与基督教皆具有平民性等等。李贽是否亦有见于此而在其晚年又特为表彰墨子呢?如果考虑到儒耶对话的背景,我以为是有可能的。传教士以基督教为普世宗教,故利玛窦《中国札记》亦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而李贽则认为中国自有诸子百家,尤其是《墨子》,其“唯知神之与民”的“经纶之术”可以“平天下而均四海”。这当然不能理解为与西学相对抗,而是寻求更多的相互理解与尊重。 李贽早年表彰墨学,重点集中在阐扬平等观念和批评儒家道统论上。孟子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又说无父者即是禽兽。李贽驳斥说:“兼爱者,相爱之谓也。使人相爱,何说害仁?若谓使人相爱者乃是害仁,则必使人相贼者乃不害仁乎?我爱人父,然后人皆爱我之父,何说无父?若谓使人皆爱我父者乃是无父,则必使人贼我父者乃是有父乎?”[10]儒墨之根本分歧,是要不要讲等级名分。李贽的论说,以很强的逻辑性驳倒了孟子斥兼爱无父是禽兽的不合乎逻辑的谬说。李贽在为墨子的“节葬说”辩护时还指出:“明言节葬,非薄其亲而弃之沟壑以与狐狸食也。何诬人强入人罪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11]孟子是道统论的始作俑者,是为了争取儒家的独尊地位才以如此粗暴的态度对待墨学的,李贽对“儒者好入人罪”的揭露和批判,正是对道统论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有力抨击。 鉴于平等观念的阐扬和对道统论的批评已见于《明灯道古录》的其他章节,所以《明灯道古录》把对墨子思想的表彰集中在提倡勤俭与“唯知神之与民”方面。李贽把中华民族的勤俭传统追溯到被墨子奉为圣人的大禹,说大禹身为舜所任命的大臣,在治理水患时,既不乘车,也不骑马,不辞劳苦地跋涉于九州山川,以至手足胼胝,肢体焦枯,真可以说是勤俭之至了,就连“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夫子也不得不承认大禹的勤俭精神无可非议。可是,后儒却批评大禹“过于俭而不可以垂训”[8]387,真不知是何居心!⑩他又说,大禹的精神是“唯知神之与民”的精神:“夫菲饮食,是其俭也;而致孝鬼神,则祭祀极其丰洁,不俭也。……卑宫室,是其俭也;而尽力沟洫,则一财一力,皆为民费,无一毫而不用之于民者,不俭也。夫舍己之饮食、衣服、宫室,凡所以奉身者无不薄,而唯知神之与民也。如此,是尚可以俭病之哉!”[8]387大禹一心为民,这正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一种精神呵! 从大禹讲到墨子,他认为墨子之学乃是大禹精神的真正传人,认为读《墨子》可以得“经纶之术”。他说:“孔子称禹,而于墨翟之俭,不敢辟以为非,盖信其传之有自也。今《墨子》之书具在,有能取其书读之,而得其所以非乐之意,则经纶之术备焉。断断乎可以平天下而均四海也。虽作用手段,各各不同然,但可以致太平,亦何必拘一律哉?”[8]387他说墨子“非乐”,其实是针对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而言的。如果能够真正理解墨子的深意,就可以用之于治国,以挽救明王朝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早年李贽在《墨子批选》中赞扬下层民众“勤俭致富,不敢安命”的精神[12],与德国大社会学家M.韦伯所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具有相通之处。晚年的《道古录》除了大讲“强者弱之归”的自由经济之外,又赋予《墨子》一书以“平天下而均四海”的意义,使人依稀可见他既要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之新要求的经济伦理、又力图解决社会严重贫富不均问题、“志在救时”的良苦用心。 (四)“尊德性”新解:“德性日新说” 中国古代本有人性发展的思想,如《易传》有“日新之谓盛德”说和“继善成性”说。自李翱作《复性书》而宋儒因之,主张“明善而复其初”的复性论才占据统治地位。利玛窦《天主实义》对宋儒的“复性论”作了批评,指出:“设谓善者惟复其初,则人皆生而圣人也,而何谓有生而知之,有学而知之之别乎?”又说:“性之善,为良善;德之善,为习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无功焉。我所谓功,止在自习积德之善也。”“吾性质虽妍,如无德以饰之,何足誉乎!”[5]74-75总之,人性之善不是宋儒所讲的“明善以复其初”,而是在人的自觉道德践履中不断生成的。 也许正是由于受到利玛窦这一思想的启迪和影响,李贽在《明灯道古录》中阐述《中庸》“尊德性”之义时别出新意地提出了“德性日新”说,认为人性也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日新的;在人性生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有不变的、恒常的因素,是为“故”与“常”;也有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发生显著变化的因素,是为“新”与“变”;并且深刻论说了人性的“新”与“故”、“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他说:“德性之来,莫知其始,是吾心之故物也。是由今而推之于始者然也。更由今而引之以至于后,则日新而无敝。今日新也,明日新也,后日又新也,同是此心之故物,而新新不已,所谓‘日月虽旧,而千古常新’者是矣。日月且然,而况于德性哉?其常故而常新也如此,又不可以见德性之尊乎?”[8]360 他认为,古往今来的人性固然有其相通之处,由今而推古,人性乃是“吾心之故物”;但由今而推至未来,人性只有变化日新才能无敝。自然界尚且处于变化日新的状态之中,人性难道就是万古不变的吗?讲人性永恒不变,不合乎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辩证规律。而讲古今人性的相通之处,也并不意味着人性就是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新”与“故”辩证统一,处于“常故而常新”的辩证运动之中;与时俱进,“新新不已”,这才合乎事物之性质的常住性与变动性之统一的辩证法。李贽所阐述的这一“德性日新”的观点,正是后来王夫之所谓“性日生日成,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说之先声。 三、“万物统体一乾元”与“人人各正一乾元”——《九正易因》对基督教灵魂说的吸取 万历二十八年(1600)冬,李贽在黄蘖山中带病完成了《九正易因》的写作。该书综合从心本论开出人学本体论和从元气本体论开出人学本体论的两条思想进路,从“万物统以乾元”,推出人人“各正一乾之元”,因而“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的论说。通过这一论说,把人学本体论的论证落实到作为社会成员的具体个人,从而与以抽象类精神来淹没个体、扼杀个体精神自由的宋明道学的先验本体论划清了界限。李贽晚年之所以对他的本体论思想建构作出这样的调整,我怀疑也是受到了西方传教士思想的影响。李贽著《九正易因》,是在南京会见利玛窦之后;在济宁潜心写作《九正易因》时,又再次会见了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万历二十七年(1599)与李贽的会见记载颇详,并说此时李贽已认识到“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11)。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亦云:“温陵卓吾李公,时在南都,过访利子,谈论者,深知天学之为真。”[13]但利玛窦也明确地写了,在南京时,他们二人“彼此畅谈宗教,谈得很久,但他(李贽——引注)不肯讨论也不肯辩驳”[14]387。只是不肯辩驳而已,似乎还谈不上认同。但万历二十八年(1600)夏济宁之会时,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他们(李贽和刘东星——引注)热烈接待了神父,然后听他谈了一些欧洲的情况以及总督十分关心的有关来生来世的问题。”[14]386次日,“利玛窦神父……在官府中呆了一整天。和李卓吾和总督的孩子们共同进餐。他发现这次访问是这样愉快高兴,以致他完全觉得自己是在欧洲的家里,或者同他的朋友在他教会的教堂中,而不是在世界的另一面的异教徒中。”[15]312为了使利玛窦能顺利达到在北京传教的目的,李贽和刘东星给予了他许多实质性的帮助(12)。这次会见和畅叙,无疑使李贽加深了对基督教的认识。但必须指出:纵然李贽认同了基督教,按照他的“道非一途,性非一种”的多元论思维方式,也不可能以基督教为“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而只可能把它看作“真正的生命之道”之一[15]332。 基于上述李贽与利玛窦作过多次畅叙和交流的事实,似乎可以说,李贽在此后半年才定稿的《九正易因》,无疑有可能受到了利玛窦思想的影响。当然,这还只是外证;要完全证明这一点,还需要内证或理证,即从《九正易因》的学理上来证明这一点。利玛窦与李贽的对话没有留下记录,只能通过将《天主实义》与《九正易因》比勘来证明。《九正易因》并不是一部宗教著作,而是一部哲学著作,由此又可以看出李贽晚年萌生的以哲学代宗教的新倾向和新思路。 (一)“天为万物中之一物”与“万物统以乾元” 利玛窦将基督教经院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带到了中国,在《天主实义》中以日月星辰运行必有第一推动者、舟渡江海必有舵手、箭矢中的必有射手等譬喻来证明上帝为世界之主宰,但上帝并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而是一个能动的精神实体;又具体辨析了“苍苍之天”(自然之天)与作为主宰之天主的区别,自然之天为有形之物,可以天文学明之,而上帝或天主则是无形的精神实体,是主宰万物的最初之所以然,但又绝不是作为依赖者而存在的“理”,而是创造和主宰万物的宇宙之魂。李贽在《九正易因》中讲“天为万物中之一物”,万物皆统于“乾元”,而“乾元”之中又只有“元”才是终极因,遵循的正是利玛窦追问“所以然之初所以然”(to be as to he,是之所以成其为是)的思路。 李贽首先从宇宙论上把“天”看作是万物中的一物,提出了“天”统于“乾元”的观点。他说:“夫天者,万物之一物,苟非统以乾元,又安能行云施雨,使品物流通形著而若是亨乎?”[18]在李贽的笔下,“天”是自然之天,只是“万物之一物”。他引王畿的话来证明这一观点:“天德之运,昼夜周天,终古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时之错行,不害不悖,以其健也。……尝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无停机,天非有体也,因星以附丽以为体。……天体不动,非不动也,旋转不离于垣,犹枢之阖辟不离乎臼,未尝有所动也。”[18]95天既然是“因星以附丽以为体”,与其他天体同为“物”,那么何以会有云行雨施等各种自然现象的发生呢?李贽认为这是因为万物皆“统以乾元”的缘故。正像西方人认为有一个精神性的“上帝”作为万物主宰、终极原因一样,如果没有“乾元”的主宰,这自然之天就不可能云行雨施、化生万物。在这里,似乎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李贽其实是用中国哲学的“乾元”概念取代了基督教的“天主”或“上帝”的地位。 但李贽又对“乾元”这一概念作了分疏和辨析。“统体一乾元”可分疏为“乾”与“元”两个不同的概念,“乾”具有“元、亨、利、贞”四德,即万物“生、长、遂、成”的自然规律,而“元”才是最终的真正的主宰,万物“生、长、遂、成”的自然规律都在“元”的制驭之下,这就是他所说的“元,非统天而何”、“举四德以归乾,而独以‘大哉’赞元”的意思。只有这作为自然规律之主宰的“元”,才是宇宙的灵魂,才是万物运动发展变化之第一推动者。如果用利玛窦所谓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13)来解释,“乾”似乎只是形式因和质料因,而“元”则具有动力因和目的因的意义[9]12-13。这不仅使他的理论更为精致,而且为他接着论述人的主体能动性作了必要的铺垫,——哲学形上学的意义就在于为人类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终极意义上的合理性依据。 (二)“人人各正一乾之元,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介绍了基督教经院哲学的灵魂学说,这一学说在基督教哲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灵魂,“认识上帝”就是认识宇宙的灵魂。利玛窦讲上帝赋予每一个人以“灵魂”,从而使人具有了超越于草木的“生魂”和禽兽之“觉魂”的特殊性和高贵地位。而李贽讲“人人各正一乾之元”,因而“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这每一个人所具有的超越于“庶物”之上的“乾之元”,其实也就是基督教哲学所讲的“灵魂”。 在《九正易因》中,李贽论证的着重点不在“乾元”、特别是“元”的至高无上的主宰作用,而是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在论述“万物统以乾元”、“元非统天而何”的寥寥数笔以后,他就立即笔锋一转,把“乾元”还原为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精神的能动性,或曰“心之本体”。他说:“人唯不明乾道之终始,是以不知乾元之为大。苟能大明乎此,则知卦之六位,一时皆已成就,特乘时而后动矣。是故居初则乘潜龙,居二则乘见龙,居三乘惕龙,居四乘跃龙,居五乘飞龙,居上乘亢龙。盖皆乾道自然之变化,圣人特时乘之以御天云耳。是故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正也,不可得而同也。万物统体一乾元,是太和之保合也,不可得而异也。故曰利乃贞。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16]93 这里所谓“一物各具一乾元”,是说万物各有其特殊的性质;所谓“万物统体一乾元”,则是指万物皆有一共同之本原、本体或终极因。至于讲到人类社会,则必须把人与“乾道自然之变化”区分开来,而凸显人与自然界之“庶物”不同的主体性: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个不完全与他人相同的“乾之元”,而人与“庶物”之不同,就在于这“乾之元”赋予了他以“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就是: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之灵长。由此看来,把这一让每一个人自作主宰的“乾之元”理解为一个自身具有能动性、同时又能赋予每一个人以主宰自我的能动性的精神实体,也就是利玛窦所讲的人所独具的“灵魂”,似乎也就没有什么疑义了。 (三)人不应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天”和“圣人”去支配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说,由于上帝赋予了人以灵魂,所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具有自由意志,可以“自主”、“自专”;而李贽也讲人人应该自作主宰,而不应把命运交给“天”或者“圣人”去支配,以至于“自甘与庶物同腐”等等,其实正是基督教哲学天赋平等观念和自由意志学说的另一种表达。 李贽在讲了人人具有“首出庶物之资”以后,紧接着就说:“乃以统天者归之乾,时乘御天者归之圣,而自甘与庶物同腐焉,不亦伤乎!万国保合,有是乾元之德也,何尝一日不咸宁也,乃以乾为天,以万为物,以圣人能宁万国,以万国必咸宁于圣人,不亦伤乎!故曰‘乾,元亨利贞。’举四德以归乾,而独以‘大哉’赞元,其旨深矣。”[16]93-94这段话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人不应该把自己混同于自然物,把自己的命运让作为万物之一物的“天”去主宰,把遵循“易”道、“时乘御天者”归之于圣人,“而自甘与庶物同腐”;二是人不可误以为“乾”就是主宰而认可帝王之乾纲独断,也不可误以为只有“圣人”才能使天下太平,把人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寄托在帝王和圣人的身上。李贽反复致意,“易”之道所最注重的,不是“乾”而是“元”,“元”具有比“乾”更高的地位,只有“人人各正一乾之元”,就能“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只有人人自作主宰,才能做到“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因此,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天”或者“圣人”去主宰是可悲的。所以,他感叹地说:“呜呼!乾之群龙,可得而见也。乾之群龙无首,不可得而见也。故用九者,能真见群龙之无首,则自然首出庶物而万国皆咸宁矣,自然时乘御天而宇宙在吾手矣,自然大明乾道之终始,一元统天而万化生于身矣。”[16]94 这一论述,表达了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自然法则”。人人“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不仅意味着人的平等、普通人与圣人的平等,更意味着人的自由,意味着把人学本体论的抽象论证走向并落实到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体的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情感,“不待取给于圣人而后足”;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内,不甘“与庶物同腐”的人们自然会形成调节个体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之关系的社会规范,而形成一种既自由而又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安宁祥和的社会。 与宋明道学“名教之自然”、“天理之自然”的所谓“自然法”相比,李贽所揭示的近代式的自然法乃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变革:第一,宋明道学认为由先验的“天理”所规定的社会关系是第一性的,而李贽则认为现实的人,即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才是第一性的。第二,宋明道学从先验的“天理”或内化为人的先验道德属性的人性之应然存在出发,而李贽则是从人性的实然存在出发。第三,宋明道学认为人只是先验的“天理”所规定的角色,而李贽则认为人具有“首出庶物”的自觉能动性。第四,宋明道学遵循的是从秩序的理念到人的存在的思想路线,李贽则是遵循从人和人性之现实存在来导出人类社会之秩序的另一种思想路线。第五,宋明道学的出发点是作为抽象类精神的“一”,其所谓主体性是非人的“天理”的主体性;而李贽的出发点则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具体的个体精神的“多”,其主体性乃是现实存在的每一个个体的人的主体性。 李贽的启蒙思想早在他接触西学之前就已风行于大江南北,而其晚年阅读西学著作及其与利玛窦的交流,则促使他更加自觉地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对西学之输入作出积极的回应,并通过融会中西来发展自己的启蒙学说。这一点充分说明,中国的启蒙思想本是内发原生的,而西学之输入乃是外来之助因。因此,学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启蒙思想一开始就是在西方影响下产生的观点,是不合乎实际的。 最后,我想再对李贽答某公问利玛窦其人之问题的《与友人书》发表一点看法。某公,不知何许人也。注释者谓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山东济宁与利玛窦相会之后,暂从其说。李贽在回信中盛赞利玛窦熟悉并尊重中国文化,“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是“一极标致人也”,“我所见人未见其比”;但在信的末段却写道:“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17](14)问题是如何理解李贽这段话,我以往也理解得不够准确,如今似乎明白了一点。利玛窦在书信中明确告诉其西方友人,江西巡抚陆万垓之所以支持他在南昌开教,是因为很明白他的来华传教意图(15)。陆万垓尚且明白,给予利玛窦在北京立足以实质性支持的李贽又岂有不明白之理?仔细品味李贽这段话的意思,我想他无非是想通过一种非常委婉的表达方式、一种在不确定中有确定性的表达方式,来打消某公对利玛窦企图以其学说“易吾周孔之学”的疑虑而已。是耶?非耶?尚祈师友明鉴。 收稿日期:2015-03-10 注释: ①陆万垓(1533-1598),字天溥,号仲鹤,浙江平湖人,陆九渊之直系后裔,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福建福宁知州。与李贽于同一年(隆庆六年,1572)被调到南京刑部任员外郎,又于同一年(万历五年,1577)被调外任,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陆万垓出任广西梧州知府。陆万垓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著有《通鉴便象》、《中丞疏稿》、《希高诗稿》、《知非小鉴》等书,多散佚。 ②[意]利玛窦原著、[比]金尼阁整理《利玛窦中国札记》以大量的篇幅记叙了他与陆万垓的会见,并高度赞扬了陆万垓的高尚人格,见该书第296-300页。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参见利玛窦1595年10月28日《致耶稣会某神父书》及同日《致高斯塔神父书》、1595年11月4日《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利玛窦全集》(三)《利玛窦书信集》(上)第177、187、207-208页。罗渔译。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③万历十一年(1583)陆万垓迁云南按察使副使,而李贽此时已弃官三年。这年陆万垓有《癸未春入觐南归重过新嘉驿池亭怀李宏甫》诗:“芳亭春晓忆曾来,千古襟期向此开。鲁酒饮非河朔醉,紊心人是草玄才。层轩秀色仍苍桧,四壁新诗半绿苔。帐望吴鸿天万里,招寻空复意徘徊。”见张建业.李贽全集注:第26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7。万历十五年(1587)秋,李贽在湖北,见鸿雁南飞,不禁怀念起尚在滇南的陆万垓和方沆,作《因方子及戏陆仲鹤二首》,见李贽.续焚书[M]//李贽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4. ④李贽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与方訒庵》信中,说新近编著了《读孙武子十三篇》和《读升庵集》两部书,“此二书全赖兄与陆天溥都堂为我刻行”。见《续焚书》卷一,李贽.续焚书[M]//李贽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8. ⑤1598年陆万垓病逝,李贽在南京作《哭陆仲鹤》诗。其一云:“二十年前此地分,孤帆万里出重云。滇南昔日君怜我,白下今朝我哭君。”其二云:“岁岁年年但寄书,草萍消息竟何如。巨卿未解山阳梦,垂老那堪策素车。”诗中用东汉范式与张劭之典故。范式,字巨卿,山阳人,与汝南张劭(字元伯)在太学为友。后二人并告归乡里。某日,范式忽然梦见张劭死去,便前去吊丧。此时,张劭之丧已发,至圹,将下棺,而棺木不肯进。张劭之母说:“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果见范式驾素车白马号哭而来,“会葬者千人,成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事见《后汉书·范式传》,又见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可见二人之友谊极不同寻常。尤堪注意者,是“岁岁年年但寄书”之句。遗憾的是,陆万垓写给李贽的书信如今已无处寻觅,而李贽给陆万垓的信如今也只有万历十九年(1591)写于武昌的《与陆天溥》,见李贽.续焚书[M]//李贽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⑥关于李贽《鬼神论》一文的写作时间,从张建业主编《李贽全集注》,见该书第1卷第2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⑦对于李贽之死,利玛窦满怀敬意地写道:“一些不知姓名的官员向皇帝上章控告李卓吾,谴责他写的书。因此皇帝下诏把他的书全部焚毁,并把他投入囹圄。李卓吾不能忍受公开地遭到贬抑,以致他的名字成为他的敌人的笑谈。作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他要向他的弟子证明,如他平常告诉他们的那样,他完全不因畏死而动容,并且这样一死来使他的敌人失望,他们想要看到他受辱而死。”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388. ⑧笔者以不影响原意为前提,对译文作了润色和修改,由不押韵改为押韵。 ⑨原文为:“自颜氏没,微言绝,圣学亡,则儒不传矣。故曰“天丧予”。何也?以诸子虽学,未尝以闻道为心也,则亦不免士大夫之家为富贵所移尔矣。况继此而为汉儒之附会,宋儒之穿凿乎?又况继此而以宋儒为标的,穿凿为指归乎?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见李贽.夫妇篇总论[M]//李贽文集:第5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8. ⑩李贽。道古录·卷下[M]//李贽文集:第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7.原文为:“舜之称禹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可知古之圣人语勤俭,莫有过者矣。今观禹之言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夫以帝臣之重,跋涉九州,随山刊木,即大而乘车,小而乘马,无不可者。乃水行则以木为舟,陆行则以木为履;下山则前高后低,上山则前低后高。经言其手足胼胝,不辞劳苦;史称其肢体焦枯,卒受风寒暑湿之患,终葬会稽之山。则当时称禹者,固以俭;而所以病禹者,亦谓其过于俭而不可以垂训也。故夫子独以‘无间然’称之。其意若曰:如禹之俭勤,吾实无间然矣。无间然,言其无间隙之可议也。而敢以议禹,是何心哉!” (11)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358-359.《焚书》卷六有李贽《赠西人利西泰》诗一首。诗云:“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见李贽.焚书[M]//李贽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40.这首诗既表现了李贽对利玛窦的热忱欢迎态度,也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学者面前所具有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12)据台湾译本《利玛窦全集》(二)《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记载:“总督与李卓吾想看一眼神父带的进贡表章,那是在南京采用了许多人的意见写的。总督与李卓吾感到写得不妥,又另写一张,又令衙署中善书法者为之誊清。除此之外,总督与李卓吾又各写了几封介绍信,结果比南京各官员的介绍信更有用。”见利玛窦全集:二[M]//利玛窦中国传教史:下.刘俊餘,王玉川,译.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332. (13)利玛窦论“四因说”云:“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维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质者,有为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为物也;模者,状其物置之于本伦,别之于他类也;质者,物之本来体质所以受模者也;为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天下无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质者,此二者在物之内,为物之本分,或谓阴阳是也;作者、为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于物之先者也,不能为物之本分。……使无天主掌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万物乎?则天主固至上无大之所以然也。故吾古儒以为所以然之初所以然。”参见参考文献[9]第12-13页。 (14)《与友人书》见李贽.续焚书[M]//李贽文集: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4. (15)利玛窦1595年10月28日《致耶稣会某神父书》说,陆万垓“待我十分客气,声称早闻我的大名,来中国只为救人灵魂,熟读中国全部经书,尤通数学”。同日《致高斯塔神父书》亦写道:“巡抚在接见我时,也是十分客气,知道我来中国是为传教救人而来,通中国经书与数学。……准我在南昌定居,享有绝对的自由,虽然我手中并无任何证件。”见利玛窦.利玛窦书信集(上)[M]//利玛窦全集(三),罗渔,译.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177、187.标签:利玛窦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李贽论文; 鬼神论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墨子论文; 国学论文; 传教士论文; 初潭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