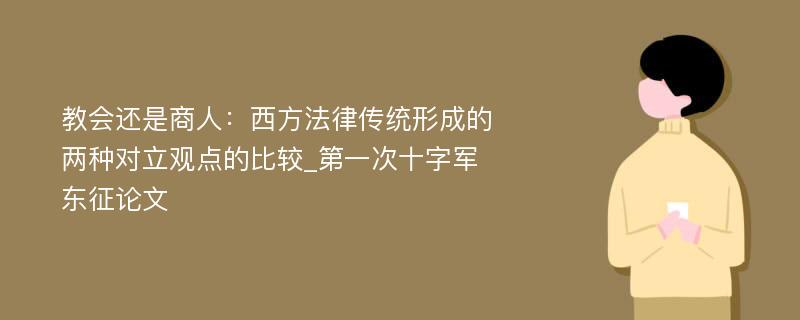
教会抑或商人:两种对立的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对立论文,教会论文,观之论文,商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教会与商人:孰轻孰重
在《法律与革命》这部洋洋七十万言的巨著中(据中译本),伯尔曼讲述的是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末的西方在昔日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重建法律的这一段历史,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探讨了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等问题,该书也因此被誉为西方法律史、法理学的一部力作。
伯尔曼认为,教会法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进而他详细地分析了教会法律体系的结构要素诸如教会婚姻法、继承法、财产法、契约法、诉讼程序以及教会法的系统化特征。关于12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英格兰的托马斯·贝克特(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国王亨利二世之间的并行管辖权之争,伯尔曼的看法是:上述冲突“在实质上是一种关于教会司法管辖权范围的冲突;它因而成为教皇革命的一个范例,这一革命在整个西方建立了两种相匹敌的政治法律权威类型,即精神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注:(美)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316页。)
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伯尔曼的独特贡献抑或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这二百年间,并且将教皇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视为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他对中世纪法学的发展及其与世俗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各种类型的世俗法律体系包括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王室法等的形成、特点的描述,在详实程度上均超过了以往的同类著作。其他如行文的流畅、生动、连贯及引用相关材料之丰富,亦给该书增色不少,显示出作者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
教会和神学的作用是贯穿于《法律与革命》的一个基本论题。为此,伯尔曼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教会法与世俗法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具有全面变革的特性。它不仅构想了一个新天堂,而且也展示了一个新的尘世。正是这次全面的剧变,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法律被看成是完成西方基督教世界使命的一种途径,这种使命就是在尘世建立上帝的王国。
显而易见,在教会与世俗秩序之间、教会法与世俗法之间,伯尔曼更倾向于推崇前者。
伯尔曼明确地告诉人们,他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旨在说明:在西方,近代起源于1050-1150年这一时期,而不是此前时期,这不仅包括近代的法律制度和近代的法律价值,而且也包括近代的国家、近代的教会、近代的文学和许多其他近代的事物。而论及西方的法律“传统”是想引起人们对以下两个事实的注意:第一,从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起,除了革命变革的某些时期,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续发展达数代和数个世纪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建设;第二,这种持续发展的过程被认为(或者曾经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个变化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注:参见《法律与革命》,第6页。)为此,伯尔曼指出:把法律概念界定得过于狭窄即把法律界定为规则体,不利于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和西方历史上数次重大革命对这种法律传统的影响的理解以及对于这种传统现在所处的困境的理解。他呼吁,需要有一种广义的法律概念,并批评了那种过于狭隘的法律观点。
如果说《法律与革命》关注的重点是宗教理念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影响,问题的焦点在于11—13世纪政教两界的争执与冲突的话,那么《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讲述的则是11—19世纪这八百年间商人(包括早期的行商小贩、十字军东侵前后的远航贸易商、银行家以及工业家等各种不同身份的商人)对西方法律体系的影响乃至改造的全过程。无疑,商人是书中的主角:他们初次登上西欧社会的历史舞台时,乃是“社会的弃儿”,将当时的法律制度看作是敌对和异己的,谋求与这种制度妥协,从而牟利。(注:参见泰格、利维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5页。)进而,当他们扩大了活动领域,并创建了一些商业机构如市镇、港口、货栈、银行、工厂之后,使同那些用以保护封建当权者的法律和习惯,产生不断的冲突。最后,当他们夺取了政权,也就是他们为自己制订法律之时。而资产阶级走向最后胜利的斗争被认为始于11世纪的城市起义。
二、十字军东征:两种不同的结论
始于11世纪末延至13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实为一场由罗马教皇、西欧封建领主和城市富商向地中海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注:参见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第127页。)先后共8次(一说9次(注:参见(美)乔治·C ·科恩著:《世界战争大全》,昆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180—181页。), 历时近200年之久。
十字军东征是西欧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对此,伯尔曼和泰格、利维在各自的著作中均有所描述。然而,对于教会和商人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的影响、地位和作用等,双方的结论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伯尔曼只论及了前三次十字军东征,目的在于将其纳入“教皇革命”的范畴。在他看来,这些初期的十字军东征属于“教皇革命的对外战争”。它们不仅增加了罗马教皇的权力和权威,而且开辟了向东通往外部世界的一条新的通道,使地中海从防御外来侵略的天然屏障转变为一条西欧自己的军事扩张和商业扩张的航线。(注:参见《法律与革命》,第120-121页。)至于商人阶级,在1050年还是由数量较少的巡回兜售的商贩组成,而到了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其数量不仅骤增,而且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状况起初出现在乡村,继而又出现在城市和城镇中,此期,陆路和海上贸易成为西欧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集市和市场形成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信贷、金融和保险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伴随着商业的发展,手工制造业也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工匠行会的形成。行会经常在城市或市镇管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伯尔曼指出,对于这一时期(即11和12世纪)商业的扩大和城市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渊源于这个时期;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却认为,这一时期是封建制度的鼎盛时期。(注:参见《法律与革命》,第122-123页。)就伯尔曼个人而言,他是赞同第二种观点的,原因在于庄园制度在当时的西欧农业中几乎成了普遍性的东西。
关于十字军东征,伯尔曼的看法是:这种变化确实转变了欧洲,并在一场兼有军事和传教性质的集体远征中把欧洲联合了起来。当然,实现这种变化花了很长时间。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从一个十字军东征前的欧洲一变而为一个十字军东征的欧洲,其迅速程度是惊人的。更加重要的是,十字军东征自始就成为罗马教皇公开宣称的目标——这一点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伯尔曼所谓的教皇革命的迅速性和暴力性。显然,在这一时期,教会(具体以罗马教皇为代表)居于统帅的地位,十字军东征充其量只是教皇革命的一部分。
与伯尔曼不同,泰格、利维将十字军东征首先定性为“西欧进行资产阶级改造的关键性事件”,(注:参见《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56页。)而其中最重要、最永久的受益者,是西方的商人——他们建立了许多经得起军事和政治变迁、能够长久留存的贸易前哨据点,他们得到了财务利益,学到新的贸易技巧和新的法律体制。
其次,十字军东征将两个很好的目标结合了起来:使“圣地”成为安全地区,既有利于商人经商,也便于教徒朝圣;藉此排除了一个日益桀骜不驯、暴戾恣睢而又无益于社会生产的军人、骑士和小贵族阶层。
此外,利用十字军东征也正好借此机会将当时令人头疼的私斗由西欧转向异域,同时可以解决贫穷贵族及其骑士随从的问题,例如依照长子继承制分配家产的问题。可以说,十字军东征给了这个阶级(或称“贵族非长子集团”)一个大好的机会:他们既可以前往“圣地”取得金银财富,又可以使灵魂得救并履行骑士战斗义务。
泰格、利维认为,十字军东征造成了三大后果:第一,意大利各城邦的商人为了争取执掌政府权力,或者争取受保护而开始进行斗争,以便容许他们从事贸易。第二,这种权力乃是用于认可诸如热那亚“海会”之类的经商方法,以求能够利用增加了的东方贸易所提供的金融机会。第三,罗马法有关契约和所有权的各种原则得到再现和扩散,为扩大贸易关系提供了法律保护构架。(注:参见《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66页。)同时,一个新的专业集团(律师)应运而生,他们既为一个新阶级(商人)效劳,也为教俗贵族领主出力。商人法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地域范围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得以传播,契约观念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并付诸实践。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东方的影响(主要是阿拉伯和拜占庭的文明)要比大多数人所设想的更大一些。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商人在封建秩序中寻求地位的表现。
三、封建法:观点之异同
泰格、利维断言:资产阶级在18世纪为其本身设计的法律体制,主要是根据和承袭六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即罗马法、封建法(或称封建领主法)、公教法(西罗马天主教会的法规)、王室法、商人法和自然法。(注:参见《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8页。)十分有意思的是,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对封建法、教会法、王室法、商法等亦多有论述。
伯尔曼认为,“封建主义”这一术语在18世纪才被发明出来。在此之前——事实上甚至是自12世纪以来——人们所说所写的不是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而是封建法,主要指的是与领主——封臣关系和依附性土地占有权相联系的权利义务体系。(注:参见《法律与革命》,第360-363页。)在1050-1150年这一世纪里,封建主义在西方得以合法化,因为封建法和庄园法在这时第一次被想象为与属于它们自己的一种生活相结合的法律体系,通过它们,封建关系和庄园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获得了自觉的调控。
伯尔曼指出,从公元1000年至1200年间——主要是在1050年和1150年之间,欧洲的各种封建设置(或译:制度)经历了实质性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归结为:(1)客观性和普遍性;(2)领主权利和封建权利的互惠性;(3)参与裁判制;(4)整体性;(5)发展性。 (注:参见《法律与革命》,第370页。)
以领主权利和封建权利的互惠性为例,此期(主要是在1050-1150年间),封臣对领主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转变为各种财产义务;同时,领主对封臣各种形式的直接的经济与支配权转换为征税,其结果是实质上给封臣留下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经济自主。另如撤回忠诚(这里,“忠诚”是两方面的:封臣有忠实地经营采邑的义务,领主有不逾越法律权限和在许多特定方面帮助封臣的义务)是从11世纪开始的西方封建关系的法律特性的一个关键,有关反抗权的整个观念就是这种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高贵者和低贱者之间的契约概念所固有的。
在对前述5个方面的变化作出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之后, 伯尔曼的结论是:较之于教会法,封建法在系统性、自觉意义上的完整性、专业性和精确性等四个方面都更为逊色。原因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法,并因此而比教皇和国王制定的法律遭到更多的批评和怀疑。由于它不仅是与教会的宗教法相对而言的世俗法,而且还只是若干个并列的世俗法体系中的一个,它能适用的范围自然也就十分狭小。所以,伯尔曼宣称,与封建法形成对比的是,教会法被认为是一种完整的法律体系,它解决可能产生的每种法律问题。
泰格、利维给封建法所下的定义是“规定臣服、统领、利用和保护等特殊关系的法规,这些关系是以领主和其臣属之间的封建人身约束为特征的。”(注:参见《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8页。 )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为“考察封建社会的某些方面”而一直追溯到古罗马,将庄园制度的出现,视为封建制度的渊源。据此,他们的结论是:在欧洲一度由罗马统治的部分地区,封建主义实际意味着后退;而在其他地区,封建主义则意味着从田园式、游牧式和受战斗支配的生存,转变为比较稳定的农业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人生活在封建社会之外,即令教会也作为封建主加入了这一制度。
至于法律失去“个人性”发生在11世纪——当时西欧处在由受罗马法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的种种地方习惯拼凑而成的体制的统治之下。世俗封建法庭由于办案十分缓慢,且恣意作为,对社会下属不公正而受到作者的批评,根源在于传统习惯不能成为执法公正的保证。后来,将习俗法转变成著作的工作由两个拥有这类工作所需的财力、同时又希望结束封建地区的各别主义的集团所推动,它们就是教会和王室。
如果说泰格、利维与伯尔曼关于封建法的观点有暗合之处的话,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他们二人认为:领主也有应尽的义务,如在欠收之年开仓放粮,让他的附庸不致于饿死——这一点与伯尔曼所谓的领主权利和封臣权利的互惠性有相近之处。
四、王室法:备受推崇
王室法在两书中均有所论述,但由于作者视野、立意等方面的差异,故而同一话题又呈现出某些区别。
王室法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作为世俗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且与教皇革命联系在一起,伯尔曼写道:教皇革命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王权概念。国王不再是教会的最高首脑,“神圣王权”的时代逐渐结束。不过,王室在教会事务方面权威的减弱由它对有关其他世俗政治组织(部落、地方、封建和城市)方面权威的大大加强而得到补偿。(注:参见《法律与革命》,第489、492 -493页。)并且,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尤其是在16世纪之后,伴随着教会地位的式微和王权的兴起,庄园法几乎消失净尽,封建法亦仅存残余,城市法和商法则逐渐为王室法所吸收。由是,西欧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按照伯尔曼的说法,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于11世纪晚期、12和13世纪涌现出一种新型的政治共同体,即世俗领地王国,概括起来,其有9个重要特点:
1.国王不再是其统治领土上最高的宗教领袖,而是一位世俗(或现世)的统治者,在宗教事务上要服从以教皇为首的罗马教会;2.国王不再只是其主要顾问和武士的最高领主,而且还有权直接统治自己领土范围内的全体臣民;3.作为自己的全体臣民的世俗统治者,国王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安宁和主持正义;4.国王在履行有关职责时,是通过包括王室法官在内的专职王室官吏和通过作为专职王室仆役的职员来统治的;5.国王首次主张立法;6.王室国家借助于审判和立法,发展了自己的法律体系;7.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上,国王的权力受宪法的限制(其臣民甚至有抑制错误的命令乃至诉诸暴力反抗暴君的权力和义务);8.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国王的权力受到国内各种社会共同体的限制;9.国王们构成国际性的职业权贵阶层。他们常通过相互联姻来达成共识和认同。
在当时西欧出现的上述这些新型王权的一般特征,在各国(包括英格兰、法兰西、西西里等)的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
伯尔曼将王室法与当时盛行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教会法作了一番比较,他的结论是:教会法的系统化程度要高一些(它甚至比复兴的罗马法更为系统)。这两种类型的法在系统化的程度与特征方面的差异,应该部分地用精神秩序概念和世俗秩序概念的差异来解释,因而世俗秩序更需要拯救和改造。但是,与其他世俗法相比,王室法则又更广博、更成熟、更进步一些。
泰格、利维对王室法下的定义是:推动建立早期现代国家为求巩固势力而制订的法规。(注:参见《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8页。 )在这一时期,商人再一次处于一个醒目的位置。由于他们的目标与王室相近,故而易于与王室接盟。由此而产生的同盟,无论在新兴资产阶级立法,还是在所谓商人经济向工业经济的演变发展过程中,都显得极为重要。
五、结束语
西方法律传统指源于古希腊、罗马,中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延续到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法律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有不同的内容:如在中世纪,尤其是在11世纪以后,西方法律传统表现为多元法律体系的形成,世俗法与教会法的并存;而在世俗法内部还形成了管辖权的多元化,等等。(注:参见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2页。)
伯尔曼和泰格、利维的著作分别讲述的就是11世纪以后的这一段西方法律传统,但由于思想观念、出发点等方面的分歧,因而各自的著述也就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由此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观——伯尔曼倾向于推崇教会和教会法在此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泰格、利维则看重商人在11-19世纪这八百年间的活动。
也许,伯尔曼思想观念的根源在于他的关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论(这也是他的最引人注目、同时又最易引发激烈争议的观点)。他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也表露出了自己同样的担忧:“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integrity)危机……。 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注:(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5页。)伯尔曼毕其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写作《法律与革命》,正是源于这种深切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希冀通过寻根溯源来求索摆脱危机的途径。
《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则被认为是一本“带有强烈新马克思主义色彩但仍完全符合学院标准的学术著作。”(注:泰格、利维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代序,第3页。 )由于作者侧重于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来评判法律在11-19世纪的作用,因而商人被置于全书的重要位置也就不足为奇。当然,作者在书中也没有忘记告诉读者:“尽管本书一直在谈论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问题,但我们却也对法律意识形态在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中的效用感兴趣。”(注:泰格、利维著:《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代序,第299页。)
对于上述两种对立的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观,似乎很难简单地断定孰优孰劣。因为,宗教与经济、教皇与商人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和塑造力。据此,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从任何单一的角度来真正理解这一漫长、曲折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一种全面的观点似应更为可取。
标签: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论文; 法律论文; 欧洲王室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教皇论文; 基督教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