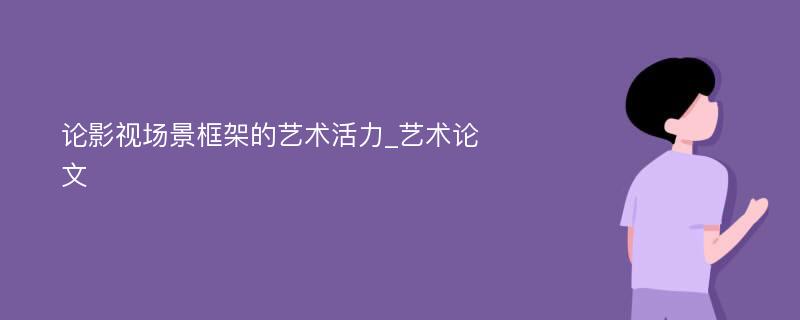
论影视景框的艺术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活力论文,艺术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1)04-0030-08
电影电视的世界是银幕或屏幕上的世界。它以景框的边缘为界限。影视景框犹如照相、绘画、舞台的画框,乃是银幕或屏幕的框架,影像画面的空间界域。然而,对于电影电视的这一矩形空间领域的艺术表现功能不少人却不甚了了。只有影视制作者、评论者乃至影视观众,不断增强与提高对影视景框的艺术地位、美学功能的认识,更加自觉地理解、开掘影视景框的艺术活力,才能不断创新影视话语,提高影视制作质量和全民族影视文化整体素质与整体水平。
一
歌德曾经说过,“显现与分离是同义语”,“那些将要显现的物体,为了将自己显现出来,就必须分离”[1](P92)。影视景框就像一道矩形屏障,一个分离器,它首先屏蔽与分离出景内与景外两个空间,一个显露可见的画内影像世界和一个虽不可视、却能引人想见的隐藏画外的神秘世界。
“景框犹如窗框,而这扇窗户是向世界敞开的”[2]。景框内的影像世界应是制作者从无限大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精心选择乃至苦心创造出来的,它一经同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分离并显现于景内空间范畴,成为幻象,即如云开日出,获得凝聚性与神话性,成为能量动力场,足以唤起观者的视觉注意和读解兴趣。雷利·斯考特执导的《角斗士》十分醒目的第一个镜头画面,就是在深沉幽怨并富有田园风味的主题曲中景框内一只戴着结婚戒指的大手,轻抚黄色麦穗向前移行,并有妻儿欢声笑语迴响天际。它不仅揭示了罗马军队统帅马克西穆斯将军的出身与理想、愿望,并且为全片意识结构部分奠下基石。
景内空间是影视制作者同影视受众进行信息交流的窗口和媒介,也是信息传递和能量散放的一种疆域。如将景内空间分割,这一疆域可分为平面的上、下、中、左、右部位,纵向的前景、中景、后景方位,以及横向与竖向、平面与立面相交叉所形成的诸多部位与方位。“疆域还显示权力和等级”;“一个特定疆域内,生物体所占空间数量和它拥有的控制程度成正比”[3]。被表现的主体与陪体,作为传达信息的不同信息源,为影视制作者置于景内空间疆域的那一特定部位,并形成何种对比关系与支配关系,势将发挥不同的引导、控制作用和心理、情感作用。人们通常认为:景内空间中央部位乃是视觉注意中心,占据支配地位;上下左右边缘部位因远离画面中央而处淡化地位。布里昂·德·帕尔玛执导《嘉丽》,为凸现自我封闭、“灰姑娘”似的嘉丽被蔑视、侮辱、损害的社会地位,在影片前部表现人物群体场景中大都把她置于景内空间的右侧或右上侧边缘部位。就一般状况而言,往往是上轻,下重,前景地位重要、突出,对中景具有解释作用,后景则显次要、疏淡,对中景起着衬托作用。日本影片《W的悲剧》中名演员羽鸟翔劝诱学员静香代她承担丑闻的镜头画面,其前景、后景的鲜花便隐喻着鲜花遮掩丑恶与眼泪的象征意义。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经创造性运用,亦如《认识电影》一书所说,靠近画面顶部的位置可以表现权力、威望和雄心壮志,画面底部可以具有从属、脆弱和无力的特性。大卫·里恩的《雾都孤儿》开头,由于暗夜里电闪雷鸣、风起云涌、池水掀波、树摇叶落这一语境的烘托,在第五个镜头景内空间中,占据画面1/3的顶部所展现的是向画面右方涌动的压顶乌云,占据画面不足1/3的底部则是朝左下角倾斜的山坡暗影,一个小小人影从右下方入画,渐渐显现于山坡斜线上。这分外渺小的踽踽独行的人物剪影,不但立即攫住人们视觉注意力,并且形象地揭示出这一未婚先孕女子此时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
影视世界是运动的世界。与静态造型艺术有所不同,无论影视景框处于何种状态,其景框内的影像世界始终都在运动着,变化着,亦即说,景内空间中的能量动力结构乃处于不断变化与改组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把握影视景框固须注意,依据视觉扫描自上而下、由左向右的通常习惯,相对而言,“一个视觉式样的底部应‘重’一些”,左半部作为“观赏者主观经验中的中心”,而“位于右侧的视像比左部的视像要清楚一些”[1](P28-35),则是视觉中心。在一组由两个或三个演员形成的组合中,位于左边的演员大凡是被强调的角色,而此刻从右方上场的人物又会立即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观赏者视觉方面的反应,应被视为大脑皮层中的生理力追求平衡状态时所造成的一种心理上的对应性经验;艺术家所以要在艺术中追求平衡,也就在于维持人体的平衡乃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即如前面所述,一个演员从舞台右方上台,观众就会立时注意他,然而倘若他上台之后没有继续去占据中心位置的话,人们的注意力便会立即转向左方的活动区域。影视景框就像戏剧舞台。既然艺术欣赏是不断寻求与建立心理平衡的动态过程,影视景内空间也在流动多变,其间诸事物主次关系又不断变化着,因此,影视制作者必须适应变化求得动态中的均衡,依照实际生活和自己独特的表现意图,通过摄影构图技术或数字技术与技巧辩证而创造性地运用景内空间领域。《角斗士》第一镜头中,马克西穆斯将军的左臂虽然居于画面右半部,但他轻抚麦穗向上滑行的左手手掌却一直处于画面中央,又一直呈于动态,并是暖色调长镜头,加之欢语声和主题音乐的衬托,因而令人过目难忘。
影视景框这一结构工具,既构造了一个演奏“主旋律”的有限的画内影像空间,同时又营造了一个虚灵而非虚无的画外想象空间。客观实在空间的无限与影视画面空间的有限,决定了影视画面构图只能在“无限”中选择“有限”,以“咫尺之图,写百里之景”,以个别反映一般,借局部暗示整体。正如格式塔完形心理学认为的那样,视觉并不满足于看到物体的一个局部,而是要把握它的全貌。况且,景内的氛围并不可能脱离景外的氛围而孤立存在。因此,影视景框作为画内与画外、显露与隐藏、视像世界与想象世界的交叉融合处,也就兼具限定与延伸感官的作用以及直露或含蓄的美学功能。
“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4](P71)影视制作同其他艺术形式的制作一样,都应“以少总多”,力求精炼,善于“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恰如契诃夫所说,“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掉罢了”。影视画面构图,不仅要剔掉多余的东西,还要善于把观众的想象力和补充作用从画内的“有限”引向画外的“无限”,使表现内容更凝练、丰富、含蓄,更富有高远的美感。中国导演张艺谋、王家卫分别执导的《红高梁》、《花样年华》,都善用断、藏手法,始终把患麻风病的李大头或另外一对婚外恋人截留于画外空间,既剪除枝蔓,省出笔墨给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又留给观众一份悬想的空间。
画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空间,它应当是贮藏和蕴涵更大能量的动力场。“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5]中国影片《黄土地》中翠巧出嫁新婚夜那一镜头,在房门吱嘎一声响过之后,只让翠巧丈夫的一只黑手伸进画内,其余皆框于画外,这不只在于减头绪,立主脑,并且在于避拙就巧,借助观众审美的主观性与差异性,透过翠巧惊惧无言地哽咽着向后退缩的细节刻画,调动观众参与艺术创造,殊途同归地去充分想象翠巧丈夫的丑老形象,并反思封建婚姻制度违逆人性的本质以及女性的悲剧命运。恰切地利用景外空间,亦可淡化性与暴力场面。
景外空间的精巧运用,还有助于独特美学风格的构建。法国影片《禁忌的女人》展示了不愿说谎的22岁女子米芮儿同不愿离婚的39岁的方斯华在6个月内从邂逅、热恋到疏冷、直至找到充足理由分手的历程。全片除却一个镜中影像和两只手偶尔闪现,男主人公的整体形象始终未在景内空间显现,使这部影片成为迄今罕见的全是主观视角的“第一人称”影片。景外空间完全可以创造为艺术空间、风格空间和美学空间。
断藏结合、“有无相生”乃是艺术创造法则之一。影视制品的画内与画外永远相依并存,互补互动。把握景框亦须注意“画外意”本在“画中态”,所谓“景外之景”须出自“景内”,“象外之象”则源于“象内”。电影电视的美,必须以充斥景内空间的影像、构图技术和技巧以及声画匹配作为火种,燃点观众的思维和想象,艺术审美过程中的美感首先仰赖制作者在“景内”“象内”创造。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编导的《橄榄树下》,运用同期声将噪音、语声乃至摄制组人员对话等多维性画外音录制下来,让人同时感知画内与画外交相辉映的多维空间的真实存在。该片又将“戏中戏”《生命在继续》(即阿巴斯摄制的前一部影片)的场景严格限定在生活中震后重建的两层楼小房子的底楼外景空间,以此作为“戏中戏”的戏剧空间,即前部影片遗留下来的梦,一个虚幻世界;而此时框于画外的二楼外景空间则为“戏中戏”外的《橄》片本文戏剧空间,一个现实世界,却又是前部影片延续下来的艺术世界。于是,景内景外亦幻亦真,相映成趣,全片艺术空间又与现实生活客观空间完全重合,浑然一体,充满张力,从而让全世界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受到阿巴斯纪录风格影片的别样光彩。
二
清人王夫之在《思问录·内篇》中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他认为,动与静都是运动的基本形态,其差异只在“动之动”与“动之静”。绝对的运动与相对的静止,乃是对立的统一。“动之动”与“动之静”的交替变化与复合,亦是影视运动的基本形式。影视景框的相对稳定与变化,也就生化而成场面调度与空间调度两种基本形态。
影视景框处于稳定状态时,其画面边框无异于舞台画框。因此,电影电视与舞台艺术交叉共用着场面调度语言。“场面调度”原出自法语,意为“摆入画面之中”,是戏剧专有名词,指导演对画内空间一切视像构成元素的有机控制。沿用于影视领域,作为影视的再生性语言,必须同舞台场面调度达到“不似而似”,既具规约性,又具非规约性。戏剧与影视的“不似之处”乃在于一个是三度空间内的“实体直现”,另一个则将三度空间的实体事物转变为两度空间内的“影像再现”形态。而二者皆谓“场面调度”,其“不似”而“似”的规约性即交叉点正在于舞台与影视的画框均处于相对静态。
电影的场面调度乃与电影相生相伴。除却普洛米奥在威尼斯船上拍摄的那一镜头段落,电影诞生伊始的卢米埃尔纪录电影和梅里爱的电影戏剧基本都是场面调度形式。场面调度乃是产生最早、生存最久的电影话语形态。伴随影视话语的当代创新,影视制作者可以创造性地透过单一镜头静态画框内的动作调度和构图形式,凭借对人、景、物、光、色等影像构成元素的有效把握,对画内主体与陪体的形状、结构线条、空间位置、透视规律、动静变化、光效、影调、色调及声画配置诸多造型元素的积极驾驭,发挥场面调度其凝聚注意、突现主旨、揭示内涵、转移视点、渲染气氛、推进节奏、创造风格的艺术功能和美感作用。
场面调度的景框及其画内空间因处于静态而以稳定性见长。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将场面调度作为主体调度手段,使之成为影片风格特色之一并把它推向极致,形成“物极必反”的悖论,从而揭示并突现了惟独没有春天的封建大宅院那死气沉沉的氛围,沉重凝滞的生活节奏以及喜庆的大红灯笼也掩饰不住的陈腐僵死的本质。同时,自颂莲夏日走进大宅院做了四太太那一刻起,她就同其他女性一同置身于林林总总的口字型构图样式中:拱形门洞窗口,带有雕梁飞檐张开或关闭的门,方形帐帷,半个圆形镜面,鸟瞰角度的日里夜间的庭院内围轮廓……制作者还有意利用透视焦点和暗调子强化这种口字型与口口相套的构图及其纵深,随着情节的发展,三太太梅珊的惨死,影片以她那“好比杀人场”的唱词点睛,点化出所有女性都在这里吃人、被吃、杀人、被杀的实质。
影视景框及其空间一旦处于运动状态,这便形成电影电视所独有的空间调度话语形式。它是制作者通过摄影(像)机机位及其镜头的运动乃至镜头组接运动,综合运用各种视向、角度、距离、景别、焦距等因素进行运动取景,造成影像画面空间的变化,实现动态构图的影视原创性语言形态。其画面景框与影像空间由于镜头的调度而处于运动状态,因此空间调度亦可称谓镜头调度。它因而也就同影视景框及其空间处于静态的场面调度明显地分离开来。
通过移动摄影造成影视景框及其影像空间变化,可有沿着光学轴线运动的推拉形态,沿着水平或垂直方向运动的摇与甩摇(闪摇)或俯摇、仰摇形态,围绕固定水平轴进行垂直运动的升降形态,跟随被摄体同步运动的跟拍形态,沿其种种规则或不规则路线移动的移拍或旋转镜头形态,不规则运动拍摄的晃动、滚动形态以及综合运动式镜头形态。这些空间调度形式,即可化静为动,使原本处于相对静态的被摄体伴随画面空间的运动产生动势,从而创造出具有影视特性的造型形象,丰富影像画面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活力,又可返动为静,将运动的被摄主体相对地控制于镜头视野中,保持其在画面空间中的视觉中心地位,从而有利于展现被摄主体在运动过程中的形神状貌,并为其完整的表演提供一气呵成的可能性。动态的景框,又可强化电影电视的控制功能。随着动态景框的起幅与落幅、位移路线和运动节奏,它可以凝聚或转移视觉注意中心,强调某一事物,带上鲜明的指示作用和诱导作用,唤起人们视觉的注意或心理上的兴趣,以便深入理解镜头画面的内涵。因而镜头调度还具有强调与突现的功能。同时,作为影视空间调度主要标志的移动摄影,冲破定点摄影的束缚,使每一个在运动中摄取的镜头画面,都成为一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固定镜头画面之和,其间每一位移抑或镜头的每一点改变所获得的每一影像画面,都相当于一个不同视点,都能把握到一个新质的画面空间和具有价值性的新环境,从而有利于展示动态中的事物,并能够富有吸引力地表现某一运动或情节的连贯过程,也就为镜头内部蒙太奇、长镜头和纪实风格美学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影视的艺术表现与美学功能得以拓展。
影视景框乃是银幕或屏幕的整个视域,它还拥有收敛与扩展影视视野、从而具有凝聚或散漫的美学功能。景框从变化趋于稳定,由动而静,或者“推”向被摄体,“跟拍”表现主体,收缩框架必然限定或收缩景内视域,使封闭的影像画面内容紧凑集中,富有张力并能显现影像画面结构的形式美;而随着画内空间的收敛,却相对扩展了画外想象空间,便于画外生情。至于影视景框由稳定趋向变化,由静而动,或者“拉”开来,乃至俯、仰、摇、移,必将画面框架延伸,不断把画外空间内容纳入景内,扩充和延展画内空间,加大与增多画内信息含量,获得丰富的涵盖力和开放性。这样,虽然因景内扩容而缩小和淡化了观众的想象空间,但是却强化了镜头画面舒展散漫的自然形态和真实感。影视制作者完全可以根据内容表现和美学风格创造的需要,创造性地处理影视景框的延展与收缩、变化与稳定、开放与封闭、自然美与形式美的辩证关系。
影视景框可静可动,亦可静动交融,静动相生,张弛有致。中国影片《早春二月》片头就是交叉性调度形式:在一个相对静态的大画框内,套着一个动态的舷窗小画框,沿岸风光景物从中掠过。一个镜头内便融合了场面调度和空间调度两种形态。《橄榄树下》交叉运用两种不同的调度形式。其戏中戏《生命在继续》部分,用的是场面调度,显现其镜头画面的戏剧空间与虚幻空间性质,艺术地反映出大地震后伊朗人民对生命和生活一种淳朴、自然、平和、顽强的心态与生态;而本戏《橄》剧,运用的基本是镜头调度形式,特别是长镜头及其大景深,真实地再现了历经浩劫重获新生命与和平的伊朗人重建家园、追求幸福人生的执着精神。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则是一部艺术化和商业化的武侠影片,其镜头画框一直锁定在主要人物及其动作上,追随李慕白、俞秀莲、玉娇龙穿房越脊、剑飞刀舞、坐卧行止,弹跳腾飞于竹林碧波之间;人物对话则通过静态景框的正反打变换以揭示其内心活动;可谓“人动它亦动,人静它亦静”,流畅,自然,不仅利于突现“人要真诚地对待自己”这一主旨,并且创造出莱辛在《拉奥孔》中所盛赞的“媚就是在动态中的美”。
影视制作者无论运用何种调度形式,自应讲求“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被摄体同镜头距离的远近,既取决于景框内人与物的多少、情节的表现需要及环境空间的具体状态,又取决于外在条件的影响、内在心理与情感乃至社会文化背景状况。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因其自然条件、文化背景的诸多差异,决定了有其各自不同的距离模式,而各自的亲密距离、私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又有各自的尺度与内涵。就一般艺术表现而言,“远则取其势,近则其取质”[4](P53),中景位则兼顾“质”与“势”。摄影(像)机镜头又与观众视点等同,因而景内被摄体越贴近观众、视域越收敛的“紧凑画面”,观众便越加感觉亲近真切;被摄体越远离观众、视野越扩展的“松散画面”,观众情感上就会越疏冷中立。然而,貌似“松散画面”的《橄榄树下》结尾那个近4分钟的俯拍式广角长镜头,先用大全景表现身着白上衣的侯赛因沿着蜿蜒小路冲下山坡,跑进山下眼前的一片橄榄树林;继而景框缓缓升起拉成远景,展现不时闪现林间、渐成白影的侯赛因呼喊着“塔娜莉,塔娜莉”,追赶已经走出树林、成为白点的塔娜莉,期盼获得她的答案。当又一个白点钻出郁郁葱葱的橄榄树林,镜头落幅于大远景,于是,在鸟啼虫鸣和18世纪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契玛罗萨的乐曲声中,只见此时已处于相对静态的景框内,一前一后的两个小白点宛如两只蝴蝶追逐着翻飞于万绿丛中,牢牢吸引观众关注他们的爱情结局,特别是最后侯赛因那一小白点伴着欢快的音乐节奏折身而回,顺着原来方向快速跑回来,更赋予人们美好的想象,发挥了“紧凑画面”和“特写”有时也难以企及的美学功能,因而自树一帜。
三
影视景框也是向人们提供的一种观看方式和视野样式。它如何指引人们观看,又指引人们怎样观看,是客观地还是主观地、忠实地或是变形地观看,便形成种种特定的视野形态、感知关系和美感作用。
镜头是具有仿生眼作用的装置。电影刚刚诞生之时,卢米埃尔和梅里爱的影片大都只是一个镜头,摄影机及其镜头又基本固定不变,因此镜头及其景框就相当于摄影师和观众的视点与视野,其影像画面即为他们目之所见。这时的电影唯有一种场面调度,一种客观视点和客观镜头。然而,自从电影有了移动摄影和剪辑技术,也就有了镜头调度,电影视角获得空前解放,于是伴随景框及其空间的不断变换,动态景框的起幅与落幅、位移路线和运动节奏,又由于镜头的仿生眼作用,便使其影像画面往往成为制作者、观众或剧中人物观察、认识、思维过程的具体反映,因而也就产生了主观视点和主观镜头。所以,影视景框的艺术活力还表现在它能分离和创造客观与主观两种视点、两种视野、两种镜头,并且拥有修饰性和不同的美感性。
通过景框与影像空间的转换与组合及其节奏变化,“从画面的联系中创造出画面本身并未含有的意义”这种特有的蒙太奇技术与技巧,借此再现或表现人类主、客观生活,其多样、丰富的艺术表现功能以及相应的思辨的美感作用,足够开辟专章另述。仅就景框处于动态状况下的镜头调度而言,它即已能够展示被摄体存在与运动的体态、角度、方向、速度及其同环境的联系与关系,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像画面造型、运动节奏及其同前后镜头的匹配,展示人物外在运动形态和内在精神世界。譬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拯救大兵雷恩》中,徐徐推向女兵眼睛或墓碑前詹姆斯·雷恩眼睛的镜头,实则在渐渐推向他们内心世界;而从眼睛特写猛地拉开的镜头,则表示意识活动的戛然而止。至于手提摄影机拍摄的晃动镜头,因其不稳定性和不规则性,不仅可以用之展示纪录片中新闻摄影师的主观视角,并且可以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用以展现准尉瓦斯柯夫押解俘虏途中疲惫不堪、跌跌撞撞状态下的主观视像。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雷恩》中,那抢占俄马哈滩头战役的一场戏20多分钟,始终运用手提摄影机拍摄的摇晃镜头,既创造出枪林弹雨中战地摄影师的视角,强化了景内空间的纪实性,又渲染出抢滩战斗变幻莫测、动荡不安的氛围,并辅以镜头转换和慢镜头及无声,创造出米勒上尉的主观视点及其主观视像,从而突现战争中死亡与生存的残酷搏斗。
景框跟随被摄体运行,或者移、摇、俯、仰、升、降、滚动,甚至居高临下航拍俯瞰,其影像画面原本就是运动视点的产物,因此极易形成一个潜在者的偷窥视角和主观视点。美国影片《与敌同眠》中,罗拉为维护人格尊严佯装溺毙逃至爱荷华州一个小镇,并改名莎拉,而凶残丈夫马田不久即明真相便追踪而至。欢庆地方节日的那个夜晚,莎拉与其新结识的男友从游艺场归来,影片便凭借跟移的画框暗示一个偷窥者的潜在。罗拉旋即发觉居所中的种种异常,不胜惊恐,此时镜头景框一直追随莎拉,而其丈夫马田却隐匿画外。这长达六分半钟的镜头画面,既制造了悬念,又加剧了恐怖感。影片最后的高潮部分,完全由这潜伏的偷窥者的主观视像和罗拉的主观镜头结构而成,形成全片的一大特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影视景框同被表现主体于空间位置方面的联系和关系所形成的观看方向与角度,诸如两极状态的正面与背面,交叉状态的侧面和占据3/4或1/4正面的斜侧面,常人常态的平视角度,非常态的倾斜、仰、俯、鸟瞰角度,均因人类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对不同方向与角度积累了不同的生活感受和心理感受,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因而在艺术制作上各种方向、角度也就具有不同程度亲或疏、尊或卑、褒或贬、稳或乱的表现作用,拥有不同的心理性、哲理性与美感性。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晚年情怀”一集中,在邓小平退休告别讲话镜头画面之后,叠化出景框仰视并摇过湛蓝高天、最后落幅于五星红旗的长镜头,喻示邓小平宽广的胸襟,并把他的主动退休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及祖国前途联结起来。影片《菊豆》在出殡“挡棺”一场戏中,用仰角、逆光和主观镜头反复渲染盛敛杨金山的棺材以及怀抱灵牌端坐其上的杨天白从头而越,具有重压感,却用俯角乃至“无语”表现菊豆和杨天青、即天白的生身父母一次次地挡棺终至精疲力竭的惨状,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无情摧残,传达出制作者富有情感性与哲理性的认识。饱蘸情感与哲理的影像画面,亦是主观化镜头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视矩形景框还具有不容忽视的修饰与美化功能。其高宽之比,一直在追求视觉造型的修饰性与美感性。先前无声电影和有声窄片电影画面景框的高宽之比大都接近或等于3∶4的比值1∶1.33,乃是接近世界几大著名城市的绘画珍藏品画面高宽之平均比值,因而获得绘画画框一样的装饰性能和视觉和谐的美感性能。方今,普通电视荧屏的高宽比则为1∶1.33左右,依然承袭了这一比值及其相应的修饰与美化性能。虽然宽银幕影片景框的高宽之比为1∶2.35,然而,遮幅宽银幕影片已成为当今的常规影片,其景框的高宽之比分别为1∶1.85、1∶1.66,它们连同数字电视屏幕高宽的新比例9∶16(即1∶1.77),都更加接近黄金分割(2∶3、3∶5、5∶8)的比值,因而愈加拥有造型形式的修饰性与美感性。
孟子曾说:“充实之谓美”。影视景框的形式美应当跟画内影像内容的充实统一起来。同窄片景框规格相比较,当今遮幅式常规影片景框规格乃是相对加大了画面空间的宽度,扩容了景内空间,具有更大包容性,更有利于全景画面内容的展现。这也正同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同电影的传播方式和信息读解装置是银幕,其视觉空间广阔、画面信息容量大相适应,相协调。米哈尔柯夫执导的《西伯利亚理发师》就采用了宽片规格。在此规格景框中,影片开头随着人声嘈杂与调试乐器的背景声隐没,字幕衬景则为大剧场中乐队指挥带领乐队奏起《费加罗咏叹调》的全景镜头,两道大幕向旁拉开,所展现的乃是相继叠化而出的航拍的西伯利亚广袤的森林、山川、河流,大远景中有列火车行驶林间,只见浓重的白烟飘浮半空。随即,在又一个化出的全景镜头空间里,表现珍于1905年写信给美国西点军校的儿子,袒露内心的一个秘密,从而奠定了影片中两个历史空间、三条叙事线索、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相结合的恢弘结构基础。其画面与声音、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即产生一种和谐的美。《橄榄树下》所以舍弃遮幅而用35毫米窄片规格,亦适应其人物较少、情节单纯集中、但着墨于人的精神展示的内容表现需要,同时也便于借助电视传播。
相对于电影银幕,一般电视屏幕不大的景框空间决定着它的信息容量乃至场面表现均受到严格限定,因而更适于家庭里以个人读解为主的传播方式。然而,当前一些中国电视剧的制作,力图步电影后尘甚至取而代之,不仅津津乐道于千军万马、大场面、远景位,并且热衷于遮幅形式,有的甚至将某些镜头或段落胡遮一气以示新异,这既浪费电视景内空间,又无形中把电视景框愈加缩小,南辕北辙,悖逆于电视美学原则。它同有些VCD、DVD光盘制作者,削足适履地将遮幅影片改作窄片规格或当下屏幕规格乃殊途同归,同样弄巧成拙。影视制作者把握画面景框,既应考虑内容的表达,风格的创造,亦应关注电影电视媒体及其景框空间承载功能的各自所长与所短,尽可能地避短就长,抑或化短为长,弃旧图新。
影视景框的运用,同样是“有法”而“无定法”。运用上要“有法”,乃是要影视制作者注意景框所以能够成为影视话语中的一种“语言”元素,就在于它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则性,相对稳定的艺术表现基本功能和美感作用,应善于吸纳融合前人和他者的成功经验与语汇,使自己的景框“语言”运用能提升到全球化与世界性的高度和广度,以适应世界影视文化大市场的需要;运用中又要“不拘成法”,就是要敢于发展,勇于创新,以独到的视角不断发现与开掘影视景框的艺术表现潜力,不断为其注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活力,使景框的技术把握科学化、艺术化、个性化、风格化,以确保中国影视文化的独立品格与地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面对电影电视的全球化趋势和进入WTO的挑战和机遇,当代中国影视工作者当会不辱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影视景框这一记录人生、演绎艺术的有限舞台中,创造无限壮美的景观。
收稿日期:2001-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