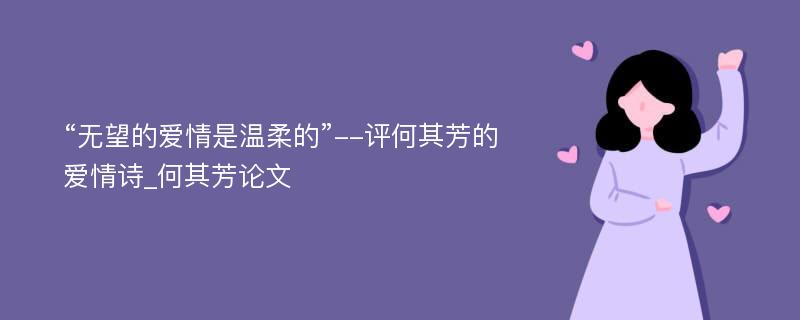
“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论何其芳的爱情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恋论文,温柔论文,爱情诗论文,何其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何其芳在《写诗的经过》中说:“我的第一个诗集《预言》是这样编成的:那时原稿都不在手边,全部是凭记忆把它们默写了出来。”他自己解释是对写诗“入迷”所致,沙汀也有旁证。(注:沙汀:《〈何其芳选集〉题记》,《何其芳选集》第一卷第4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预言》出版于1945年2月, 共收诗34 首, 大部分创作于1932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何其芳在时隔多年后仍对自己的旧作记忆犹新呢?仅仅是对写诗的痴迷,恐怕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爱情、青春和对故乡的歌唱是何其芳《预言》时代诗歌创作的主题,尤其是他对爱情的体验和感悟。是经过灵魂过滤的,是他生命主体意识追求留下的烙印,这种烙印已融入他的血脉,不会因时间流失、环境改变而有所淡忘。
爱情成为诗歌表现的永恒主题,并不足为怪。爱情的个体性,必然造成当事人爱情的独特性。古往今来,诗人对爱情的看法虽然千差万别,然而不外乎,得到爱的欢欣和失去爱的忧伤。新文学诞生以降,诗人个体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反封建礼教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无论是“告白”式的“忆内”“寄内”,还是天真浪漫的为爱情而歌,几乎鲜有触及到生命的本体意识。诗人也并不超脱,在热恋中不会留下忧伤的曲子,在失恋中也找不到对爱情甘甜的咏叹。而何其芳却是一个例外。
考察何其芳本人的爱情经历,再对照他隐讳曲折的爱情自诉,我们就会明白,何其芳的确是一个在失恋中品味爱情本身甘甜的独特诗人,也会对他时隔10多年还能默写出《预言》中的34首诗的说法感到可信。
据亲临何其芳童年故居访问的黄濂清同志记述,自小在何其芳家做工到解放的张兴仁曾回忆,何其芳二外公有个孙女,名叫杨应瑞,眉目清秀,温柔多情。他们自小在一起玩耍,彼此感情深厚。渐至长大,各奔东西,很长时间音讯杳无。1930年秋,何其芳到北京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因没有高中文凭,被学校开除。在失学滞留北京的大半年时间里,何其芳生活闲散,心情苦闷,又处于生性敏感的青春期,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何其芳沉浸在诗歌的幻梦里,在自己的心灵的空间,抒写自己的悒郁和对爱情的朦胧期待。然而,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外地学子,生活无着,人生无望,爱从何来?堂表姐杨应瑞的出现,使何其芳倍感心慰。他乡遇故知的处境和青年男女的热情,使他们交往甚密。特别是杨应瑞的勤奋好学,时常前来夔府会馆,向何其芳请教国文和英文,使何其芳浙至丧失的自信和自尊得到了恢复,何其芳暂时忘却了求学的受挫。“一次,在小房里临窗的书桌前,其芳正在给她讲解英文。她低着头,一大颗泪珠从她的眼里悄悄滴到了书页上。那好似一粒爱的火星点燃了其芳19岁的年轻的心。他第一次产生了纯洁的爱情。”(注:方敬,何频伽:《关于〈预言〉》,《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初恋是难以忘怀的。不同人对初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人生怀有热忱和美好的何其芳,对他的这一次如昙花般稍纵即逝的初恋,始终抱着圣洁的感情,这种感情,并没有因现实的无情而减损丝毫。由于何其芳父亲的封建和守旧,何其芳的初恋没有开花结果。然而,这次不幸的初恋却在他生命的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何其芳在《一个平常的故事》中说:“在北平的那几年,……深入地走到我生活里来的不过是带着不幸的阴影,带着眼泪的爱情。我不夸大,也不减轻这第一次爱情给我思想上的影响。”不合理的社会能摧残他们的爱情,却无法遏制何其芳对爱情本身完美的赞美与追求。因此在他的爱情诗里,纵有对爱情难以圆满的忧伤,但其间流贯的仍然是对真挚爱情的坚信和执着。
二
《雨天》表露了爱情夭折后的心态:“是谁第一次窥见我寂寞的泪,/用温存的手为我试去?/是谁窃去了我十九岁的骄傲的心,/而毫无顾念的遗弃?”何其芳并未象其他诗人那样一味咀嚼爱情失落的忧伤,而是笔锋一转,从感伤的回忆中转向对爱情本身的美好祝愿:“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略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在被忘记里红色的花瓣开放。”《赠人》抒写了处于热恋中的微妙感觉:“你青春的声音使我悲哀。/我忌妒它如流水声睡在绿草里,/如群星坠落到秋天的湖滨,/更忌妒它产生从你圆滑的嘴唇。/你这颗有成熟的香味的红色果实,/不知将被啮于谁的幸福的嘴。”恋爱中的人,往往越是爱对方,越会对对方产生一些莫名的醋意和妒忌,并且变得敏感而脆弱,时刻恐惧可爱的人儿不会长久地依恋在自己身边。何其芳是一位多情的诗人,它的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何其芳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事后缅怀现实中夭折了的爱情时,并没有失望于爱情本身:“对于梦里的一枝花,/或者一角衣裳的爱恋是无希望的。/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再赠》已过滤了不幸爱情的阴影,留下的只是初恋的温馨与甜蜜:“你裸露的双臂引起我/想念你家乡的海水,/那曾浴过你浅油黑的肤色,/和你更黑的发更黑的眼珠。”诗人之所以在历经爱情痛苦后对爱情依然抱有信心,一方面是因为他与表姐杨应瑞分手,并非他们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于何其芳本人的健康心态。他是一位积极进取,有独立思考和见解,不为外界所左右的诗人。这次满怀喜悦的恋情,因父亲从中作梗而夭折,留下的固然有愤懑,有忧伤,有惆怅,何其芳并未在失意中消沉,而是理智地进行了思考,在心灵的空间进行了对话。他在阵痛中获得了新生和爱的真谛:
“说呵,是什么哀怨,什么寒冷摇撼,
你的心,如林叶颤抖于月光的摩抚,
摇坠了你眼里纯洁的珍珠,悲伤的露?”
“是的,我哭了,因为今夜这样美丽!”
你的声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圆月夜》过去的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爱情的美好与甘甜在于信念,在如春风拂面的爱情天空里,瞬间就是永恒!
《预言》一诗,历来的评论者都持受瓦雷里《年青的命运的女神》影响而作。孙玉石最近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从何其芳所写的一篇对话剧式的散文《夏夜》里,中学教师齐辛生与爱恋他的狄珏如的谈话中得出:“《预言》中的‘年青的神’,并不是瓦雷里诗中那位‘年青的命运的女神’的转化,而是诗人自我诗性的化身。”同时,他又肯定何其芳在《年青的命运的女神》关于纳耳斯梭“拒绝”森林女神爱的传说中,找到了自己情感世界共鸣的原素,找到了创作《预言》的灵感。从而认为:“《预言》里传出的是一个少女对于一个男性的‘年青的神’的爱的倾诉。”“是诗人在爱的热潮过去后自我内心两种声音的对话,是诗人情感矛盾中一种心灵的自审。”(注: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的诗》,《文学评论》1997年6期。)这种看法,无疑是有新意的。 但我认为,据此认为“整首诗是一位女性的倾诉。无语而来又无语而去,‘消失了骄傲的足音’的,不是年青的‘女神’是诗人自己”(注:孙玉石:《论何其芳三十年的诗》,《文学评论》1997年6期。), 却未能触及到何其芳《预言》一诗的本意。
要弄清《预言》一诗的创作本意,仍然要从何其芳整个的创作心态出发,仍然离开不他和杨应瑞的爱恋留给他的感触。诚然何其芳并未因现实的爱情受挫而怨天忧人,也未沉缅于失恋的悲伤中一叶障目,对爱情本身不满,他总是在心平气和中咀嚼爱情的夭折,在甜蜜的回味中生出对爱情本身完美的吟颂。然而,对于拭去自己第一滴青春的眼泪的表姐,何其芳却始终难以忘怀。
何其芳在落叶纷飞,万木萧瑟的孤寂中,又沉浸在对表姐相恋的往事里。回想去年的这个时候,孤寂中与表姐相遇了,年幼时结下的情谊,在异乡漂泊中得到催生。川东万县又有表兄妹通婚的习俗,何其芳蓦然发现,表姐杨应瑞,或许就是自己爱情理想中那位“爱情的神”,当那颗晶莹透明的泪珠滴在书页上,何其芳初尝爱情的心激动了:“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告诉我用你银玲的歌声告诉我,/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青的神?”从幻想爱情的美好,追慕爱情的焦渴,到沉浸爱情的满足,何其芳陶醉了。恋人所讲的一切都能激发起自己的想象,遥远家乡的“月色”、“日光”、“春风”、“燕子”、“绿杨”,又回到了眼前,闭着眼聆听恋人的歌,那种温馨与惬意,至今仍有感觉。在恋人讲了家乡和童年的往事后,何其芳又絮絮叨叨地向恋人叙说,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开除学籍、断绝经济来源、人生处处碰壁、前途吉凶未卜。然而,自己从未屈服,如今,又有了你的爱,这一切不幸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诗人沉浸在与表姐相爱的回忆中,对自己的前途,他们爱情的结局,怀抱信念。可是,这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何其芳与表姐暑假兴致勃勃回家,满以为会得到父母的赞同,未曾料到,封建守旧的父亲对于亲上加亲坚决反对,其芳据理力争也毫无用处,于是愤然离家出走。此时,何其芳并未屈服家庭的压力,还奢望凭自己的抗争赢得自己的爱情。可是,经济尚未独立的他,既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也无力顾及表姐的前途。《预言》的第四段,笔锋从欢快转向阴冷,就是现实残酷的投影。当听说表姐无法再来北京,已被家里逼着与一个店铺经理订婚了,何其芳劝道:“不要前行!前面是无边的森林;/古老的树现着野兽身上的斑纹,/半生半死的藤蟒一样缠着,/密叶里漏不下一颗星星。”即是如此,何其芳在心目中仍未放弃这次爱情,他坚定地表白道:
一定要走吗?请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脚步知道每一条熟悉的路径,
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你可以不转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当确知他与表姐今生有缘无份时,何其芳伤心了,这种伤心不仅仅是因他与表姐的爱情之花永无结果之日,更主要是对封建父权和家族的失望。《预言》最后一节,表面上看来,是诗人在责备表姐对自己的爱情信念无动于衷,放弃了昔日相恋时的誓言。实质上,诗人已从记叙个人的爱情经历上升到爱情结局本身的感叹,甜美的爱情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时代,是不能用歌声留住爱情的足音的。爱情——这个年青的神,无语而来又无语而去了。
三
《预言》无疑是何其芳在经历爱情阵痛后结出的一个熟透了的石榴,色彩绚丽,香甜可口。而在此之前创作的《莺莺》和他称之为“幼稚的欢欣”的一些爱情诗,则是一个个尚未成熟的柿子,有一点生涩,也有一点酸甜。
《莺莺》是一首融入民间传说,带有神话色彩的爱情诗。就其表达的浪漫故事本身,确如诗人自己所说:“那首诗的故事平庸。”(注:方敬、何频伽:《早年读诗写诗》,载方敬,何频伽《关于〈预言〉》,《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古今中外,抒写“痴情女子负情汉”的爱情悲剧故事,数不胜数。何其芳沉迷于闻一多、徐志摩的诗风中,跃跃欲试之作《莺莺》被刊于《新月》三卷七期的瞩目地位,不是《新月》主编换了人,不懂诗而伐幸采用的。(注:方敬、何频伽:《早年读诗写诗》,载方敬,何频伽《关于〈预言〉》,《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莺莺》的成就,在于诗人借“痴情女子负情汉”的平庸题材,表达了他对爱情本身的信念与执着。为了爱就是死也无怨无悔。因为真诚爱情的信念并不会随着有形生命的消失而动摇:“我相信他总要来到这村,/他来到的时候,/藉着那桃花的指引,/也很容易找到埋着的坟茔。”这种对爱情的执着信念在何其芳致友人的信中,也有表现:“即使是沙漠,是沙漠的话,/我也要到沙漠里去寻花,/寻来伴我墓中的生涯,/即使一朵,一朵都寻不着呀,/总有风沙来把我埋葬吧”(《即使》)。
何其芳在1930年冬被清华大学开除后,滞留在“夔府会馆”达半年之久,他一边补习功课,准备来年再考,一边读诗写诗,与表姐的重逢,尤其是频繁接触产生的情感,使何其芳苦闷的心又变得开朗了。他在与友人杨吉甫合办的小型期刊《红砂碛》发表的十二首诗,一扫《莺莺》情感的浮泛,而落在实处。“乡情”、“伤春”和“织梦”,共同组成“幼稚的欢欣”,成了他这时写诗的主旋律。对故乡的眷念,是因为与表姐相逢而起,他乡遇故友,乡情自然会成为最初的话题。由此引发他与表姐对儿时的甜蜜回忆:
想起江南的夜曲,倾下屋檐,
夹着一网网雷声,一刷刷电,
楼上楼下,我在雨中走遍,
走过你的门前,不准你听见。
想起堤岸上,我们一排儿坐,
流金万点,是月影掉下江波,
你们挨次说,我静静地听着,
静静地睡着,望天上的星河。
想起你,想起你小小的温存:
半夜里醒来,一粒荧荧的灯,
悄悄地,恰象我梦里的灵魂,
是你,不是窗角儿的那颗星。
——《想起》面对现实,诗人要织一个“美丽的梦,希望“梦象歌一样有声”,“声声跳着期待的欢欣”。初恋的欢乐荡去了现实笼罩的阴影,何其芳沉浸在初恋的蜜饯里。《那一个黄昏》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渴望恋人的到来,久盼不至,于是一声声地呼唤恋人的芳名,一遍遍地抒写恋人的名字,在念叨中进入梦中,恋人的声音又出现在耳际。《昨夜》抒写的惆怅是恋人中常见的,这种失意中仍有挥不去的甜蜜与温馨。而写于当年七月份的《夜行歌》,却因诗人与表姐回家征求父母同意婚事受阻而改变了诗的色调,少了欢欣,多了沉重,纵然仍有“黑暗遮不了草的香”的信念在抗争,仍然笼罩着“黑暗”的阴霾。至此以后,《我也曾》、《我不曾》、《当春》、《青春怨》等诗篇,失落和伤感的词汇比比皆是。虽然何其芳心中并没有完全屈服父亲的反对,却对自己与表姐的爱情结局渐渐丧失信心:“树上的桃花片片飞坠,/夹在书内的也红色尽褪。”(《我不曾》)“在你的青春里是不会开花。”(《当春》)“我的青春象花一样谢落。”(《青春怨》)何其芳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之花凋谢了。他为此痛苦过,更多的是对爱情、青春和生命的思索。他迥异于其他诗人的是,爱的失落并没有使他失望于爱情、青春和生命的本质,反而加深了对此的感触、过滤与净化,使之获得自己独特的美的体验。
后来,何其芳把描写自己爱情经历的诗篇,称之为“未成格调的歌”,把与表姐相爱受阻夭折的痛苦体验,称之为“奇异的风”,正是这种“奇异的风”,才催生了他自己的光辉,“浮夸的情感变为宁静、透明了。”“一种新的柔和,新的美丽”开始了。何其芳认为他的成熟之作,至此以后才“真正的开始。”(注:何其芳:《梦中道路》,《何其芳研究专集》第163页。)
事隔十二年之久,何其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一长段路之后的1942年,仍然未忘记他曾爱过的表姐杨应瑞。在何其芳看来,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会消逝,“但那些发过光的东西是如此可珍,/而且在它们自己的光辉里获得了永恒。”他在《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里继续回忆道:
我又曾沉默地爱着一个女孩子。
我是那样喜欢为她做着许多小事情。
没有回答,甚至于没有觉察。
我的爱情已经如十五晚上的月亮一样圆满。事实上,何其芳难以忘怀的女孩,如今早已作了母亲。但在他的心里,爱情的圆满与否,不在于形式上的结合,而在于是否长驻心间。即使与杨应瑞的爱情之花未曾结果何其芳也未就此失望,爱情的真正含义在于身心的投入。他深爱过,并且对爱情本身依然满怀信心:心中有爱,地上就开花,天上就镶嵌了满满的星星。正因为诗人如此真诚地对待爱情,对待青春和生命,他的爱情诗就别具风味,在酸涩中贮满了甘甜。
四
何其芳的爱情诗,基于个人喜怒哀乐又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经过外界阻碍在形式上夭折的爱情,净化了他的感情层面,而唤发出对爱情本身的生命体验。爱情如一座高山,何其芳的爱情追求,逾越了失落爱情的沟沟坎坎。他知道,看得见的爱情之光,他本人无法企及,但他仍然坚信,只要攀登,就会拉短与爱情之光的距离。基于此,他的爱情诗就有别于真实的爱情和理想的爱情,而介于真实倾向理想的层面之中。
要表达这种层面上的爱情,常规的构思和语言是不行的。何其芳在谈到自己写诗的过程中曾受过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他最初喜爱冰心,泰戈尔等人的小诗,“用小诗的形式写他的天真的感触,他竟写了满满一小本”。(注:方敬、何频伽:《早年读诗写诗》,载方敬,何频伽:《关于〈预言〉》,《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后来,他自认为幼稚而烧掉了。稍后喜欢过闻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喜爱过戴望舒的诗歌,进而又钟爱梵乐希的名诗《水仙辞》和《水仙的片断》。法国象征派的诗歌与他自小受过的晚唐五代冶艳精致的词风熏陶,产生了共鸣,他在自办刊物《红砂碛》上发表的早期之作,就留下了这些探索的印迹。然而,何其芳是一个要求严格的诗人,讲求艺术的完美。他在不断探索、追求、融化古今中外诗歌表现手法中,结合自己的个性、气质,形成了富有艺术魅力的独特诗风。正如方敬所说:“他的诗绝不属于任何中外诗派。他就是他自己,他的诗是他自己心灵的声音,他的诗是他生命的树上自己生长出来的绿叶”。(注:方敬、何频伽:《早年读诗写诗》,载方敬,何频伽:《关于〈预言〉》,《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属于“他自己”的“声音”,是他在对语言的独特锤炼上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我喜欢读一些唐人的绝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我自己的写作也带有这种倾向。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注:何其芳:《梦中道路》,《何其芳研究专集》第163 页。)为表现浮现在他心中的那些颜色和图案,诗人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思。然而,他乐此不倦。诚如何其芳自己所说“我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我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意的幽深和丰富”。(注:何其芳:《梦中道路》,《何其芳研究专集》第163页。)
何其芳早期之作,已注重文字的锤炼与典故的组合。《莺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用桃花来象征青年男女的爱情并不鲜见,唐代诗人崔护已留下“人而桃花”的典故。何其芳则赋予这个老典故以全新意义:为情而死的女子是美丽的,更美丽的是这个传说本身。
何其芳眼中的爱情是“婴孩脸涡里的微笑”。“是传说里的王子的金冠”,“是田野间的少女的蓝布衫。”(《爱情》)消失了的恋人脚步“有如虚阁悬琴,久失了亲切的手指,/黄昏风过,弦弦犹颤着昔日的声息,/又如白杨的落叶飘在无言的荒郊,/片片互递的叹息犹是树,萧萧”。(《脚步》)欢乐的颜色“像白鸽的羽翅?鹦鹉嘴?”欢乐的声音“像一声芦笛?还是从稷稷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欢乐》)银色的梦“如白鸽展开沐浴的双翅,/如素莲从水影里坠下的花瓣,/如从玻璃似的梧桐叶/流到积霜的瓦上的秋声。”(《月下》)诗人把一些抽象的事物变成一些有声有色的图案,具体可感的色彩。这些图案和色彩构成诗人思维运动形态的内核和外在表现。
何其芳“生来具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会把无色看成有色,无形看成有形,抽象看成具体。他那句形容儿童的话很可以来形容他自己:寂寞的小孩子常有美丽的想象”。(注:刘西渭:《读〈画梦录〉》,载同上。)何其芳自小生活在想象中,缺乏温情的家庭,养成了他在想象中释放自己孤寂的思维习惯。他在诗歌创作中,凭借想象的翅膀去思维,就超越了从概念去寻找意象的常规思维过程,浮动在他心中的本来就是一些想象中的意象,而这些意象本身因为脱却了概念,就必然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使人在这些熟悉的图案和色彩背后,去品味和思索隐藏的象征意义。我们读他的爱情诗,总会感受到他创造的意象所带来的独特感味。由于意象之间跳跃很大,意象本身的丰富性和兼容性,就使他的诗有晦涩之感。诚如李健吾所说:“一般人视为晦涩的,有时正相反,却是少数人的星光。”(注:刘西渭:《读〈画梦录〉》,载同上。)试看何其芳笔下的相思:“谁的流盼的黑睛像牧女的铃声,/呼唤着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过了春又到了夏,我在暗暗地憔悴,/迷漠地怀想着,不做声,也不流泪”。(《季侯病》)对恋人的怀想,赋予一件普通的罗衫:“襟上留着你嬉游时双桨打起的荷香,/袖间是你快乐的泪,慵困的口脂,/还有一枝月下锦葵花的影子/是在你合眼时偷偷映在脑前的。”(《罗衫怨》)爱情失落的怅惘是:“寂寞的砧声散满寒塘,/澄清的古波如被捣而轻颤。/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能从这金碧里拾起什么呢?”(《休洗红》)诗人眼中的一些图画和色彩变成了一个个奇特而含意浑邃的意象,意象的含义,则取决于读者对这些意象的理解。不同的读者所感悟的意象,自然是有差别的。因为意象本身具有丰富的蕴籍。既不同于汪静之们自然流露的天籁之声,又有别于那些一味地高唱或低吟的泛情之作。
在“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联串事件来表现某物特定的情感”(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1947年3月30 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时,何其芳是独特的。他不是在现实里或书本中去寻找与自己爱情经历相对应的客观事物,而是凭借语词本身的锤炼去想象,去思维,在想象和思维中把自己的情感沉淀在一些看得见的场景,摸得着的物什么以及具体可感的事件中,从而赋予这些“实物”、“场景”、“事件”以新的象征意义。这不仅仅大大推动了爱情诗现代化进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高峰,我们在陈敬客和舒婷的爱情诗中,也能感到何其芳“他自己”声音的回响。
收稿日期:1998—0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