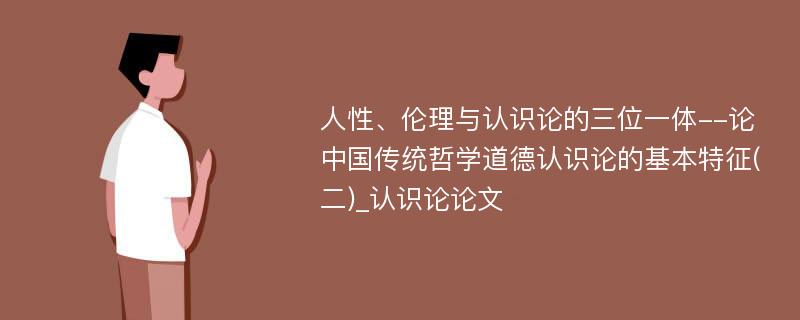
人性论、伦理学、认识论的三位一体——中国传统哲学道德认识论的基本特征刍论(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人性论论文,伦理学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 道德完善是人性论和认识论的共同目标
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它渗透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等各个方面和层面,其渗透在人生层面则表现为一切都是为了主体的道德完善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正因为这样,冯友兰才认为中国哲学对于人的意义及对未来世界哲学的重大贡献不在于给人提供实际的自然和社会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康德对关于什么样的人是“哲学家”也曾说过:“由于道德哲学具有比理性所有其他职能的优越性,古人应用‘哲学家’一词经常特指道德家。就是在今天,我们因某种比喻称指所有理性指导下自我克制的人为哲学家而不问其知识如何。”(《纯粹理性批判》,第570页)也就是说,所谓“哲学家”是指那些有高远深邃的道德涵养的人,对自然和社会有再多的实用知识也不一定成为哲学家,这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尤其是如此。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就是道德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家也就是道德哲学家,他们身体力行地进行道德修养并为社会大众制定了道德修养的一整套规则和原理,而且他们所建构的理论都是围绕以使人如何达致道德完善为最高目标而旋转的。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所构建的人性及其善恶理论,就是为了人的道德完善提供理论基础的。孟子和荀子根据各自的人性理论而分别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和“涂之人可以为禹”就是把道德完善作为自己人性理论的最高目标,同时也表现他们的人性理论为人进行道德修养并可以达到至善提供了逻辑前提。这些往往通过下述问题而体现出来,即人能否成为圣人?这是中国古代哲人一开始便试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换一种提法就是:人怎样通过道德修养,使个体升华为理想人格的问题。这个问题逻辑地包含着需要解决的几个前提,即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善还是恶?人与人在天性上是否平等?人是否有独立的人格?等等。因此,在理论形态上,道德修养论和人性问题紧密相联:人性论是道德修养论的理论基础;道德完善(成圣)是人性论的最高目标和追求。
在儒家看来,达到至善的理想人格就是“内圣外王”。“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4页)儒家的内圣外王就是《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中“修身”是根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道路和手段,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最后完成,这种完成就是“止于至善”。按照儒家祖师孔子所确立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原则,不论是贵为天子,还是平民百姓,由于性相近,因此在后天均须以“修身”为本。在儒家看来,由于人的本性所决定,圣人在内必须加强德性修养,以此为基础,将内圣发用于外便是外王。
孟子从人性同善出发,认为人人可以成圣,他提出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并进一步由“人性平等”推出“道德平等”。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这表明了:首先,孟子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其次,强调了孔子“能近取譬”(《论语·雍也》)亦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思想;第三,孟子发现了人类的通性:既然人之本性相通,那么圣人的德性和德行,我就应该具有;圣人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这样,孟子就从人性的平等,推及道德的平等,又从道德的平等,推及机会的平等和人的潜在能力的平等,从而人人可以达到道德至善的境界,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一样的圣贤,也只是人类之性的再造和升华,而芸芸众生也都具备成为圣人的自然天赋和性之根本。所有孟子常说:“尧舜与人同耳”;“舜,人也;我,亦人也。”(《孟子·离娄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等等。
荀子虽然主张人性恶,即人在性恶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平等”的。但他从人性恶出发,并没有得出人人为恶的结论。恰恰相反,他得出了与孟子从人性善出发而得出的相同的结论,即“涂之人可以为禹”。只是他们在对人性善恶的基本规定和人后天对人性善恶的损益方面有不同的理解而已。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命题是一个普适的命题,它在荀子的人性论中是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因此人要不断的去恶积善;这个命题同样适用孟子,不过其指的是“人性本善,其恶者伪也”,它同样要求人不断的充善去恶。可以认为,孟荀在以人性作为根基而在追求道德至善的目标上是殊途而同归的。
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落实在现实的层面上就是关于道德修养之学。同时,中国哲学家们又总是将道德完善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建立在“人同此性”的基础上,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对人性的解析来解决和证明道德修养问题。正因为这样,孟荀的人性论虽然各执人性善恶张力的两极,但他们的结论“人皆可以为尧舜”和“涂之人可以禹”却不谋而合。实际上,主其它人性善恶理论者均可逻辑地推出这一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道德完善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又具体表现为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对人与道德关系问题的解决是以人为了道德,而非道德为人而设为原则的,这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德是以仁义礼智信等封建纲常为内容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从孔子到近代,甚至到现代,在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其基本倾向是人为道德而生,人为道德而死,为忠、为孝、为贞、为信……而取生死。因此,道德是目的,是归宿,人是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样一种道德至上主义的原则造就了中国代代辈出的“志士仁人”,同时也从未间断地制造着“节夫烈妇”的辛酸故事和“以理杀人”的惨酷毒烈。在西方,其主流则是道德为人而设,而不是人为了道德(当然,宗教道德是一例外)。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历史深沉的呼唤一直主宰着人与道德关系问题的解答。正如弗兰肯纳说的:“道德是为了人而产生,但不能说是为了体现道德而生存。”(《善的求索》,第247页)因此,在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
与将道德完善作为建构人性的最终目标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亦将道德完善作为建构认识论的最终目标。可以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的道德修养和如何达致道德至善等问题的孜孜求索。
孔子自谓人生修养的过程时有一段著名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论语·为政》)这里,孔子把“学”作为自己人生修养的最先步骤,“学”是以后各阶段人生修养的前提。但是,孔子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即增加知识的活动,而是以人生修养和达到理想人格、提高精神境界为目标的认识活动。因此孔子常释“学”为“志于道”,(《论语·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所以,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以“道”为“学”的鹄的。在其它地方,孔子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如他把“多闻”、“多见”的认识方法直接与个人成长及向他人学习做人联系起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
孔子在谈到仁知关系时,又提出知者利仁、知及仁守的思想。作为“克己复礼曰仁”的“仁”,是某种最高修养的完成;而作为“未知,焉得仁”的“知”,则是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即“智”。因此,“仁”和“知”是构成孔子君子人格论的两个并列的基本因素,但二者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首先,知者利仁。孔子认为,知可以辅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利仁首先在知利于仁的养成。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颜渊最能做到以知养仁,他非常聪明好学,“有颜渊者好学”,(《论语·雍也》)“回也闻一以知十。”(《论语·公治长》)因此他在获仁方面成就最大,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知者利仁还表现在,仁爱的施行必须依靠知。孔子“仁”的含义之一即“爱人”,但仁者之爱非无原则之爱,而是区分是非善恶之爱:“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而好其当好,恶其当恶,则须知人。其次,知及仁守。君子人格的培养就是通过知的过程而达到至善的目标。因此,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道德养成中,“知之”只是开始,还须经过“好之”“乐之”,其知才能沉淀为仁。这里的好之、乐之、安之,就是使道德认知、外在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信念的心理机制。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及仁守”:“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
从孔子的人生修养过程和关于仁知关系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明确将个人道德的完善作为认识的终极目标。这成了后来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指向,导致了把认识主体规定为道德主体,把认识客体规定为道德客体,从而把主客体的认识关系等同于主体的道德修养的倾向。这也就是说,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把道德修养及道德至善的达到作为认识的终极目标,从而铸就了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之为道德认识论的基本特质,中国传统哲学道德认识论就是围绕如何达到道德完善这一轴心而旋转的。
三 认识论以人性论和伦理学为基本内容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道德认识论主要把主体的道德修养及致善途径作为反思的基本内容,故自然地,认识论便将人性论和伦理学涵摄其中。
中国传统哲学道德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规定就是把认识对象伦理化。因此,自然客体、社会客体以及作为客体的主体自身并不是中国哲学道德认识论的对象,而是它们的伦理内容才是道德认识论的真正客体。不仅如此,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等等的伦理化是从特定的人性内涵中推衍于外的结果,也就是说,外在对象的伦理性是依据人的道德规定而作的特定敷衍;尽管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其表面文章是从外在对象即所谓“天理”中寻找道德的根据,而其实质是以封建道德去比附外在对象,以此说明封建道德体系的合理性。因此,一切伦理化的外在客体实际上是主体人性的特殊表现。这样,真正的道德认识对象就成了主体的人性自身,理解和认识了人性,那么,一切宇宙原理和社会要义则尽在其中。
在中国传统哲学道德认识论中,对人性的认识通过人性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即“心性关系”问题表现出来。在哲学家们看来,关于心性关系,则或言性在于心,或言性即是心;或言心之知在性外,或言心之知在性内。心性关系问题即人性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53页)对人性与认识关系问题的解证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道德认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
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论“心”及其认识功能者当推孟子。孟子认为心是思官,充当着认识主体的作用。在认识与人性的关系即心性关系问题上,孟子倾向于认为性在于心,作为人之本性的仁义礼智四端皆涵摄于人之心中,“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既然性根于心,那么尽心即可知性而性又外发于天,因此“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由此而把人性与“天理”纳入认识活动的领域。
荀子则认为,性是可以通过心的“虑”、“择”而改变的,所以他便提出“化性起伪”的命题。他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伪是由于积虑的结果,而虑是心(认识器官)的功能;虑的结果即礼义的形成,也是由于心择的缘故。因此,性与伪是对峙的,虑是伪的原因但并不等于伪,也不等于性。荀子并没有明确指出性是否即是心,但他却清楚地表明性的变化是由心的作用造成的。
心性关系问题在宋明道学家那里大放异彩。
张载首先把性作为心的统摄对象。他认为心是总括性情而以知觉为其本质的。他说:“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大和》)“心统性情者也。”(《语录》)知觉是心的功能,而性是心的内涵之一;性是根本的,有性更有知觉,便构成为心。由此言之,心是结构性(性)与功能性(知觉)的统一。
程颢将性、心与人欲、天理联系起来,认为人心即人的认识活动须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务,性中含情,因此养性去情便成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代名词。程颢所说的“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其基本要求就是养性去情、存天理灭人欲。程颐则将心性情合而为一,且把“天”、“心”、“情”等等作为性的不同表现形态:“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二程语录》卷二五)
陆王心学继承了程颐心性情为一体而并无分别的思想。陆王认为,心即性即理即知。在心学家那里,“本心”和“良知”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还是主体的“天命之性”。正因为这样,王阳明才说“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与,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与,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大学问》)因此,人的认识无非是对良知良能的“天命之性”的自我认识;而宇宙之大,亦无非“备于我”而已。
朱熹不同意程颐陆王心性情合为一物,而赞成张载的心统性情说。他认为,“横渠心统性情之说甚善,性是静,情是动,心则兼动静而言,或指体,或指用,随人所看。”(《朱子语类》)卷六三)“性是未动,情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朱子语类》卷五)“心统摄性情,非 侗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同上)朱熹还把性看作理,因此他又说:“性只是理,性是流出运用处;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答潘谦之》)心作为认识器官,包摄了性情。尽管哲学家们对心性关系的理解有差别,但对“性”的内容的规定却是大致相同的,这就是仁义礼智。朱熹对此也不例外,他把仁义礼智作为人性的基本构件;不仅如此,他还把心的认识功能看作是借助仁义礼智而进行的,这就是他说的:“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元亨利贞说》)仁义礼智既是性的根本规定,又是认识主体进行道德认识的基本前提。
总括而言,虽然哲学家们在认识与人性的关系即心性关系问题上,在某些方面各持主张,如陆王主张性就是心,心之知在性内;程朱坚持性在于心,心之知在性外。但是,在下述问题上却是十分一致的,即第一,他们都把“性”的内涵规定为封建道德意识,而且以此泛化到整个宇宙,这是中国哲学家们的共同倾向;第二,他们都把认识的任务确定为对人性的揭示和把握;人性之外的客观对象不过只是人性的外推或对人性的印证而已。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以人性论为基本内容之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伦理学。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都是围绕道德修养这一主题而展开的,而道德修养又是伦理学的基本内容,于是认识论以伦理学为基本内容实即主要以道德修养为内容。
认识论以伦理学为基本内容主要表现为认识活动与道德修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这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道德认识是道德修养的前提和基础;二,道德修养是取得道德认识的要津;三,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四,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就是一事,不可分别为二。
首先,道德认识是道德修养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是修行的结果,心以知为前提。他还说:“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董仲舒将孔子的这一思想发挥为“知先规而后为之”。(《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这一思想得到了更详尽的阐述。程颐说:“须以知为本”,(《遗书》十五)“须是知在所行之先。”(《遗书》三)朱熹亦说:“论先后,知为先。”(《朱子语类》卷九)他在批评“湘中学者”只知教人践履时,质问道:“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未能识得,涵养个甚?”(同上)因此,在他们看来,只要知了,便自然行得,“既知则自然行得。”(《朱子语类)卷十八)不知则行不能久,“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遗书》十八)
其次,道德修养是取得道德认识的要津。《管子·心术》认为,欲求获得知识,必须有虚心的修养,“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虚矣。”孔子一方面把知作为行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以行作为知的基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只有达到了这样的修养境界才能取得道德知识。荀子从人性恶出发强调要“积善成德”,因此,特别强调“行”,认为“学止于行而止矣。”“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荀子还把“日参省乎己”的内省功夫作为“知明”和“行无过”的前提条件,“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为学》)《易传·系辞上》亦云:“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就是说,要了知大化之秘密,必须从事德行的修养。宋儒程颐也认为致知必需道德修养。他说:“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遣书》三)“致知在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二字。”(《外书》二)朱熹也很注重道德修养对致知的作用,认为“欲应事先须穷理,而欲穷理又须养得心地本原清静明澈,方能察见几微,剖析烦乱,而无所差错。”(《答彭子寿》)致知是需要涵养的,有涵养才能穷理。心学家王阳明提出了一个“学须反己”的普遍命题,表达了道德修养对道德认识的必要性。王夫之也提出了“知必明行为功”、“行可有知之效”的命题,强调了道德认识只有在道德修养中才能被真正理解和验证。
第三,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相互为用、互相促进。这是中国古代哲学道德认识论在处理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关系问题上所达到的辩证法的最高水平。这主要是由朱熹和王夫之完成的。朱熹一方面说:“论先后,知在先”,另一方面又说“论轻重,行为重”,就已经表明了他的认识辩证法思想的闪光。朱熹把知行、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看作是相互引发的圆环,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朱子语类》卷九)“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同上卷十四)因此,朱熹认为“为学”必须使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交互为用:“致知以明之,持敬以养之,此学之要也。不致知则难于持 敬,不持敬亦无以致知,二者交互为用。”(《朱子文集》卷四《答程允夫》)王夫之也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的理论。他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各亦有其效,故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卷三一)又说:“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之并进而有功。”(《读四书大全说》卷四)
最后,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本是一事,不可分别为二。上述要么强调道德认识是道德修养的前提,要么强调道德修养是道德认识的要津,要么强调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相互为用、互相促进等诸种主张,都只是就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的某一方面而言的,而且在同一哲学家的思想中是根据论时的具体情境而有所侧重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关于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关系的主流思想,是把道德修养就看作是道德认识,道德认识也就是道德修养,人们只需潜心于道德修养就可获得人生所需的智慧。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中国哲学简史》第14页)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的命题不仅是一个认识论命题,而且是一个德性修养的命题,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这本身就是一种德性而不仅仅是知。孔子的学生子夏更明确地把道德活动本身就看作是认识活动,他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张载认为在德行修养之外是不可能取得知识的。他说:“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神化》)认识之道在于崇德,德盛则自然能穷神知化,两者一而二、二而一,无需分别。陆九渊特别强调了做人的唯一重要和将做人作为为学的唯一内容,他豪迈地说:“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为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语录》)这是极重气节的中国哲学家们的一贯态度。
总之,哲学家们围绕道德认识与道德修养关系的论述,不论各自侧重于哪一个方面,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且共同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道德认识论极为弘宣和凸现道德认识的主体性:不论是把道德认识作为道德修养的前提或相反,还是把二者看作是交互为用或就是一事,其最终目的就在于把人提升到纯道德的理想境界,把人从“自然人”、或“经济人”、或“社会人”……纯化和抽象为“道德人”。此外,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学说也必须放在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践履)的关系中来加以审视才能探察其真正的底蕴,即“知”与“行”的内涵必须以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来加以诠释。
从上面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性论、伦理学和认识论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三者是互为圆环甚至三位一体的,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明确地把它们区分开来而各得独立的地位。
标签:认识论论文; 人性论文; 道德修养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人性论论文; 道德论文; 伦理学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论语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孟子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遗书论文; 荀子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