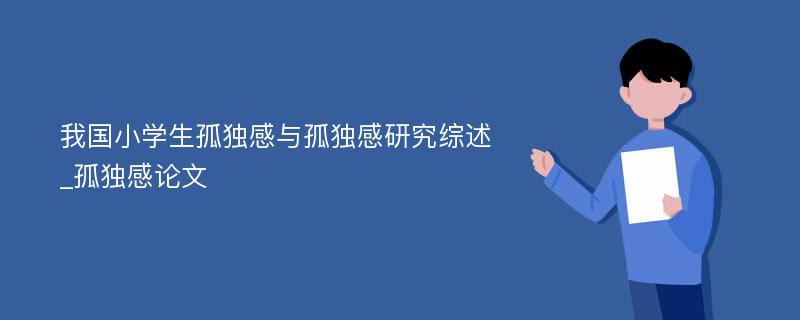
孤独感及我国小学儿童孤独感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独论文,儿童论文,我国论文,小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4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192X(2006)07·08-0105-06
国外对孤独的科学研究始于1970年代末。1973年,Robest-Weiss发表了《孤独,一种情绪及社会性孤立体验》一文。受该文的启发,Peplau和他的学生于1970年代末期开始了对孤独的系统探讨,创制了广为采用的UC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t Losangels)孤独量表,并对孤独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1979年,第一次国际孤独研讨会在美国召开。最近十几年来,国外对孤独的研究发展较快,至今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最近的研究表明,孤独与社会支持和精神健康有显著的相关。显然,孤独感方面的研究不仅是社会关系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人格心理及心理健康领域的重要课题。最近几年,有关孤独的咨询与治疗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Murphy和Kupshik(1992)曾用社交技能训练、角色扮演等技术帮助孤独的人提高交往水平,改善人际关系。由于孤独者往往存在社交技巧不到位及其它心理障碍,难以与他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因而大多数有关孤独的干预研究以社交技巧训练为主,综合运用其它技术,如认知调节、敏感性训练、情绪表达训练等现代人际关系的咨询与治疗技术。[1]
一、孤独感
1.内涵及特征
不同的学者对于孤独有不同的理解。Weiss认为(1973)孤独感是当个体感觉到缺乏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自己对交往的渴望与实际的交往水平产生差距时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或体验。Perlman & Peplau(1981)认为,孤独感是指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不足时的不快乐的体验,包括社会关系在数量上的不足和质量上的低下。Weiss(1987)指出,当人际关系网络出现某种质或量的重要缺陷时,人们所产生的不愉快感即为孤独感。关于孤独感的特征Peplau和Perlman(1982)提出,[2] 尽管人们的理解不一,提法各异,然而从这些定义中仍然可以看出孤独感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第一,孤独感源自于人际关系缺陷,它只有在人际关系中才会产生;第二,孤独感是一种主观体验或心理感受,而非客观的社交孤立状态,一个人可在漫长的独处中毫无孤独感,也可以在众人环绕中深感孤独;第三,孤独感体验是不愉快的,令人痛苦的。
2.分类
Weiss将孤独分为两类:情绪孤独感和社会孤独感。情绪孤独感是指人们依恋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孤独感,表现为缺乏亲密联系,如儿童失去父母,成人失去配偶等。社会孤独感是人们社会整合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或者缺乏社会感时产生的孤独感,如与周围的同事、朋友或邻居搞不好关系等。根据孤独感在时间方面的特征,即孤独感是一种状态还是一种特质,或兼而有之,有些心理学家将孤独感分为暂时和境遇性孤独感(任何人独自旅行或到一座新城市都会遇到)与慢性长期存在的素质性孤独感。
Young和Beck曾将孤独区分为长期性孤独、情境性孤独和暂时性孤独。Young认为,长期性孤独源自个体长期以来一直感到缺乏自己满意的人际关系或长期社交不足和存在社交缺陷;情境性孤独则产生于个体重要的人际关系破裂和瓦解及改变时,或人处在陌生、封闭、孤单的社交环境中;暂时性孤独则涉及的是我们的绝大多数人都时不时体验到的偶然的孤独感。长期孤独的人难以与他人发展和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经常感到孤独无援或与他人疏离,并为此而深感痛苦。情境性和暂时性孤独只是对环境变化的暂时性反应,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一定时期内仍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也可能转化为长期性孤独。Gerson和Perlman(1979)及Shaver(1985)也对孤独从时间上做了区分,他们认为孤独既可为短期的、可为一时性、境遇性的,也可以是长期性或特质性的。前者即Young所说的暂时性和情境性孤独,统称为状态孤独,后者称之为特质孤独。特质孤独可能是一种慢性和长期存在的慢性孤独,是个体长期人际关系不良或社交不足的反应,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特质。[3]
3.研究意义
孤独是一种消极的、弥漫性的心理状态,儿童长期处于此状态会导致适应不良。虽然一定的孤独体验对于人格成长的作用可能并不全是消极的,但孤独感造成儿童相当大的痛苦,孤独体验与抑郁和被遗弃感相联系,使儿童找不到社会归属感,导致自尊下降。Asher等研究表明,10%~16%的学龄儿童报告存在严重的孤独感,我国学者邹宏调查结果与此相近。[4]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儿童期是人生个性开始形成的时期,培养孩子健康的个性品质是目前教育一项重要的任务。人的个性品质包括许多方面,如自卑、自私和孤独、谦虚等,而这些品质又都不同形式地反映在孩子的身上。只要你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儿童的群体中有一些远离他人的孩子。从个性品质的角度分析,这是一些孤独的孩子,他们的外在表现很明显:不与他人主动交往,不参与群体的活动,言谈较少,像离群的小鸟。这些表现都与我们提倡的教育目标相背离,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害无益,是一种不良的个性品质。虽然在群体中孤独的孩子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从全面育人的宗旨出发,如何针对孤独的孩子进行教育是必须探讨的问题。
二、孤独感的产生及其影响因素
孤独感的产生很复杂,一般而言,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内在的安全需要促使人寻求情感保护,当这种寻求未能达到一定的期望值时,孤独感便产生。事实上,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中,更生活在精神世界中,人需要一种精神满足,这种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如果缺乏知心朋友,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可能产生孤独感。
孤独感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心理现象,它的产生、发展与个体所处的社交环境和个体的社会关系状况有关,与个体的人格因素、认知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5] 研究表明,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1.孤独感与同伴关系
儿童的孤独感与同伴关系状况密切相关,同伴关系差的儿童孤独感水平高。儿童的同伴关系是指相互关系的体验水平,一方面指同伴接纳,即在班级中与同伴的相互作用及在这些同伴中的社会地位。代表社会地位的是群体接纳水平或受欢迎程度(Bukowski & Hoza 1989),社会地位高,受欢迎的儿童同伴接纳水平普遍较高;另一方面是儿童的友谊。尽管对友谊概念各不相同,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友谊是一种主观的评定,是自愿的、两人之间的人际相互作用。已往有关同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在班级受欢迎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的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和情感困难与儿童经历的同伴拒绝有关(Asher、Coie,1990; Bukowski,Pattee,1993)。众多研究也表明,被同伴拒绝的儿童在将来可能有更多的社会心理问题,如犯罪、学业水平低、退学、财产滥用和其他心理不适应(Coie,Lochman,Terry,Hyman,1992)。另有研究发现,退缩拒绝的儿童导致更严重的同伴拒绝、最少的好朋友、最高水平的孤独感(Willams,Asher,1987; Boivin,Thomassin,Alainl,1988)。行为退缩、消极的同伴评价和消极的自我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可导致儿童的孤独感(Younger & Bouko)。
友谊在儿童的发展中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根据Asher和Parker的观点(1989),友谊能提供心理安全感、自我支持和自我认同、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爱好、指导和帮助、交往和相互激励,满足归属感和发展儿童的社会能力,友谊关系的良好发展可防止儿童将来的社会适应困难,减少孤独感。
2.孤独感与人格因素
在深入探讨孤独感的影响因素时,人们也注意到人格因素与孤独感的内在联系。人格因素影响到人们对其社交情境或社会关系状况的知觉与评价,影响人们对其自身处境的理解,进而影响到孤独感。Stokes(1985)探讨了孤独感与外向、神经质及自我袒露的相关,结果发现这三个变量都与UCLA孤独量表得分显示了显著的相关,其中神经质与孤独感的相关最为显著,他认为,神经质的人往往对人际关系过分敏感,害怕被拒绝,使用过当的自我防御机制,因而常有孤独感。Erlman和Peplau(1982)的研究结果发现,经常有孤独感的人往往较内向,人际角色被动,难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另有研究结果表明,有孤独感的人往往社交技巧、社交能力较差,有更多的社交焦虑,更抑郁和神经质(Jones,Etal,1981; Hojat,1982)。Jones(1985)的研究指出,孤独感与下列因素有关:其一,缺乏社会技能(缺乏自信心、内向、自我肯定程度低);其二,情绪的激发和冲突(沮丧、焦虑、神经质);其三,低自尊(低自尊,社会自我概念低);其四,消极的态度(敌意、生活和社会悲观的态度)。
可见,孤独感与人格因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样的环境,由于人格因素的差异,对环境的理解将会有很大的区别,如当个体的人际关系缺乏时,有的人将其视为一种挑战,试图改变,也有的人感到孤独。
3.孤独感与社会支持
有关社会支持与孤独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见。邹鸿(1998)在“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发展特点、功能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考察了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在社会支持网络中,获得同性朋友和教师的价值肯定、指导和情感支持越少,互选朋友越少,同伴接纳水平越低,其孤独感越强;在陪伴与亲密度维度中,感知到的同性朋友和父母的陪伴与亲密感越少,互选朋友越少,同伴接纳水平越低,其孤独感越强;与同性朋友、父母和教师的满意度越低,互选朋友越少,同伴接纳水平越低,其孤独感越强;来自母亲和同性朋友的惩罚越多,越可能体验到强烈的孤独感;与父亲和同性朋友的冲突越多,互选朋友越少,同伴接纳视频越低,孤独感越强。
Stokes(1985)考察了社交网络变量与孤独感的相关。他将个体的社交网络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网络大小,它反映的是个体社会关系的数量和经常交往的人数;第二是网络中与之关系密切的可以信赖的人数,他们能在个体需要帮助时给予全力支持;第三是网络中亲属的比例;第四是网络的密度,它涉及的是个体在网络中与其他人交往的频度。结果发现四个维度中,第二个维度与孤独感的相关最显著,其次是网络中的亲属比例。网络密度与孤独亦呈显著相关,孤独的人往往表现出社交回避行为,与其他成员的交往频率较少。Stokes还用社会支持行为问卷,考察了样本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与孤独的相关,结果也发现二者相关显著。
4.孤独感与归因方式
有心理学家研究指出,孤独感与退缩行为、归因方式有关。研究表明,具有孤独感的成人倾向于将社会行为的失败归因于内部稳定的因素(Anderson & Horowitz,French1983; Peplau,Miceli,Morasch1982),不受欢迎的儿童对社会行为的失败倾向于自我责备(Sobol&Earn,1985)。关于同伴接纳、归因方式与孤独感关系的研究表明,在同伴中不受欢迎并将社会责难做内部稳定归因的儿童有高孤独感和社会不满意感(Bukow&Ferber,1987)。美国心理学家(Asher,1990)归纳出了关于孤独感的模型,他指出,退缩的社会行为、同伴接纳水平低、少或没有朋友和内部稳定的归因风格可增加青少年的孤独感水平。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困难与孤独感的产生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此外,许多有关青少年抑郁、压抑与归因方式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对消极事件和积极事件的不正确归因会导致高水平的抑郁,进而引发高孤独感。
三、孤独感的干预与治疗
从有关文献看,孤独感的干预与治疗目前尚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实践模式,Rook和Pelpau(1982)[6] 认为孤独感的咨询与治疗之所以被心理学工作者和临床治疗者所忽视,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们一直没有把孤独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问题或症状加以对待,许多人仍将孤独视为是一种与其他心理痛苦形式相互重叠的成分,如有些人认为孤独从属于抑郁等。二是孤独与其他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问题相比,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人们尚存在不用专门的治疗和干预,孤独可以自我克服的偏见。三是受社会学家们的影响。社会学家们一般将孤独视为社会问题,认为孤独是由社会和文化背景所引发的。因此要防止或减缓孤独,需要改变社会环境而不是进行心理治疗。
Young(1979)曾以Beck的认知行为法为基础,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较早提出了一套针对长期孤独者进行个别治疗的模式。他认为人们的孤独情绪与行为改变和认知密切相关,通过改变孤独者不恰当的认知方式,帮助其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可以改善孤独情绪及社交行为障碍,并能预防复发。Young的疗程一般分六个阶段:(1)克服有关独自时的焦虑与悲哀;(2)尝试结交新的朋友;(3)与值得信赖的朋友进行自我袒露;(4)与伙伴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5)与伙伴发展成相互依恋的关系;(6)维持长期的友情关系。
Peplau和Perlman(1982)从其孤独的认知观出发,也探讨了孤独的应付与干预策略。他们认为孤独的干预应从三个方面进行:(1)改变个体的现实人际关系;(2)调整个体的社交期望水平;(3)让孤独者正视自己的孤独体验,改变不良应付方式。他们特别强调孤独的认知构成的改变,重视对孤独的人进行人际归因训练。而且他们认为,既然大多数人不能从专业人员那里获得帮助,那么建立孤独者的自我帮助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几年,有关孤独者的团体咨询迅速发展,如Murphy,Kupshik(1992)曾用社交技能训练、角色扮演等帮助其提高交往水平,改善人际关系,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关尝试。由于孤独者往往存在社交技巧拙劣及其它心理障碍,难以与他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因而大多数有关孤独的干预研究以社交技巧训练为主,并综合运用其他技术,如认知调节、敏感性训练、自信训练、情绪表达训练等现代人际关系的咨询与治疗技术。这些研究因其对孤独的涵义理解不一,其侧重点也不尽一致。
总的看来,近些年来孤独的研究在西方发展较快,许多心理学家的临床工作者对孤独的概念、测量与评定、影响因素及干预和治疗等方面做了深入系统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观念和实践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然而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加以注意,一是在孤独相关因素的研究中,人们多将视点放在诱发孤独的客观因素方面,较多关注影响孤独的环境变量和相应的情感表现,相对忽视与孤独有关的个体差异变量和认知因素;二是在许多研究中,孤独概念界定并不相同,测量方法、测量工具也有不同,以致出现一些不太确定甚至相互矛盾的结果。三是研究对象年龄阶段的不平衡,大多数研究针对的是社交孤立者如孤寡老人、丧偶或离异者的孤独问题,面向青少年的孤独感研究偏少;四是孤独的干预治疗不仅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已有的干预也缺乏特有的模式。[7]
四、我国小学儿童孤独感研究现状
我国孤独感研究最近十年发展比较迅速,各年龄段都有涉及,但是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研究明显偏少,这是现在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本文着重介绍我国小学儿童的孤独感研究情况。现在的研究涉及了儿童所处环境,师生关系和家庭环境对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儿童自身的特点,学业不良、同伴接纳、社交焦虑、社交自我知觉与儿童孤独感的关系,以及友谊这种特别的同伴交往对孤独感的影响。
1.师生关系与儿童的孤独感。学校背景下的孤独感是学生基于教师对自己的评价、情绪反映和行为表现及对自己在同伴群体中社交地位和学业水平的知觉而产生的孤单、寂寞、失落、无助和不满的主观情感体验。[8] 师生关系是学校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基本人际关系,[9] 是师生之间以情感、认知和行为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心理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促进学生愉快的学习和减少学生问题行为的关键因素,它有利于学生健康情绪和智能的培养,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而小学生的孤独感则会影响其与教师的交往,这对师生关系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杨雪梅[10] 的研究发现师生关系的亲密性与小学生的纯孤独感、社交需要未满足感、同伴地位评价和社交能力评价均显著相关;师生关系的支持性与小学生的孤独感显著相关;师生关系的冲突性与小学生的纯孤独感、社交需要未满足感和同伴地位评价显著相关。孤独感不同水平的小学生在师生关系支持性、合作性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高分组,而在冲突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高分组。
2.家庭环境与儿童孤独感。辛自强、池丽萍[11] 的研究将对儿童的孤独感研究从学校系统扩大到家庭系统,并综合考察了儿童孤独感、问题行为、同伴关系和家庭功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儿童孤独感与同伴群体和家庭功能的关系的概念模型,该模型认为家庭功能与孤独感的关系要通过社会能力和行为、同伴接受性等中介变量实现。研究结果发现,家庭功能与同伴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要以外部问题行为为中介;同伴接受性是儿童孤独感与外部问题行为的中介;家庭功能与孤独感的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依次通过外部问题行为和同伴接受性这两个中介变量实现,或者通过内部问题行为这一中介变量实现。
3.同伴关系与儿童孤独感。俞国良[12]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儿童的同伴接受性与孤独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儿童的孤独感是按“受欢迎儿童—一般型儿童—被忽视型儿童—被拒绝儿童”的顺序递增的,儿童的社交地位越不利,其孤独感就越强。
4.儿童孤独感的年级性别差异研究。在众多对儿童孤独感的研究中,一般都探讨了孤独感的年级和性别差异,而没有定论。例如,有的研究发现,儿童的孤独感有显著的年级和性别差异;有的研究表明,小学高年级儿童(4、5、6年级)的孤独感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年级差异;周宗奎[13] 等研究表明,3~6年级小学生的孤独感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孤独感显著高于女生。
5.认知因素与儿童孤独感。有研究发现,一些受欢迎儿童报告了极高水平的孤独感,而一些被拒绝型儿童却报告了极低水平的孤独感。这种现象一方面印证了孤独是一种主观体验,另一方面说明只从社交地位来考察孤独感,不能充分解释同一社交地位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因此,仅从同伴接受性这个非主观性的角度研究孤独感,使人们难以对它做出较为全面的认识。基于上述原因,一些研究者加入了认知的因素来研究儿童的孤独感。周宗奎的研究发现,儿童的社交情绪体验与其对社交后果的归因有一定的关系,[14] 于是将儿童在交往中的客观社交地位与主观自我知觉结合起来,[15] 考察二者对孤独感的影响,以期对孤独感的产生机制有更全面的了解。结果表明,社交自我知觉不同,儿童体验到的孤独感也不同,社交自我知觉消极的儿童其孤独感显著高于社交自我知觉一般组和积极组,社交自我知觉一般的儿童其孤独感显著高于社交自我知觉积极组;两两差异极其显著;对孤独感的回归分析表明与客观的社会喜好相比,主观的社交自我知觉对孤独感的预测力更大。
6.学业困难、友谊与儿童孤独感。刘在花、许燕[16] 等研究了学习困难儿童友谊质量、定向、孤独感的特点及其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与非学习困难儿童相比,学习困难儿童友谊质量、定向显著偏低,孤独感显著偏高;学习困难儿童友谊质量、定向受性别影响显著,孤独感受年龄影响显著;学习困难儿童友谊质量、定向对孤独感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五、孤独感研究展望
我国的孤独感研究比较少,且存在年龄不平衡的特点,对儿童的孤独感研究更少,这对儿童健康个性的形成和塑造是不利的,也是当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应当加大力度所在。
孤独感作为一种主观体验,原有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些认知因素与儿童孤独感关系的探讨,比如社交焦虑、儿童自我知觉。但是其他的认知因素对儿童孤独感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儿童自我意识与儿童孤独感的关系问题,自我意识不同的人孤独体验感是否会受到影响;儿童期的自我意识处于形成时期,那么孤独体验是否会影响到自我意识的形成呢?儿童自我意识反映了儿童对自己在环境和社会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也反映了评价自身的价值观念,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目标、完善人格特征的重要保证。儿童从婴儿期起自我意识就开始萌芽,至青春期渐趋成熟。如果在发育过程中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使儿童的自我意识出现不良倾向,则会对儿童的行为、学习和社会能力造成不良影响,使儿童的人格发生偏移。这种自我意识可以从科学的逻辑起点来分析。科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哪个范畴,不能靠主观而定,要看它是否在客观上符合科学的逻辑起点的基本要求。[17] 因而儿童的自我意识应当有一个科学的范畴作为起点与发展基础。
现在国内外的干预主要针对个体进行,重视认知改变、人格因素、归因方式、行为塑造,采用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的形式。原有研究表明同伴接纳水平低的儿童体验到更多孤独感,而且同伴地位一经确定是比较稳定的,不易改变,即使儿童有了认知和行为方面的改变,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得到同伴的正性强化,是不容易固定下来的,对于儿童孤独感的干预效果也不会明显,所以无论是作为影响儿童孤独感的重要因素还是作为儿童孤独感干预过程中的强化因素,都应该同时对孤独感儿童所在班级进行干预,增强班集体的接纳性,优化班集体氛围,这是原有干预的缺陷所在,而且对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和实际操作而言这也是可行的。
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除了对个别学生的辅导之外,对所有学生的人格辅导也是一部分内容,良好的接纳、宽容、关爱会成为学生良好人格特征的一部分。
2.原有的综合干预涉及家庭、社区,这会受到时间、次数、深度的限制,而在学校中进行小学生的班级干预可以在时间、内容、深度上进行控制。
3.团体干预促使儿童的行为、观念发生变化,班级干预促使班级同学的观念、行为发生变化,从而增强班级的关爱、支持、接纳水平,成为孤独感儿童改变的动力与强化力。
4.这种团体干预结合班级干预的干预模式不仅适用于孤独感的干预也适用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其他涉及到同伴接纳的内容,比如儿童攻击性、退缩行为的矫治等。
5.因为团体干预结合班级干预的方法具有时间经济性、可操作性、可控性、实效性等特点,所以这种干预模式可以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广泛推广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