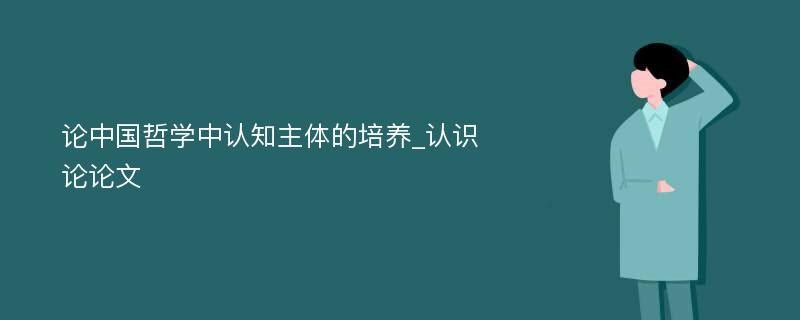
中国哲学的认识主体修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修养论文,主体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注重认识主体的修养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长期以来,受西方哲学认识论理论框架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这一特点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有鉴于此,发掘、阐释中国哲学的认识主体修养论,对于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有裨益的。
一、重视认识主体的修养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特点
哲学是研究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学问,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哲学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西方哲学认识论所研究的认识对象侧重于自然界,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心与物、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人认识世界的能力,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理性思维的工具、形式和方法,真理的标准等。中国古代认识论所研究的认识对象侧重于人道、人性,而不是天道、自然界。有的学者称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主流是道德认识论,而西方的主流则是自然认识论(参见夏乃儒;廖小平)。中国古代认识论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心与物的关系,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即所以知与所知、能与所)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学与思的关系,言与意的关系,体认、悟、直觉,真理的标准和主体修养等。
中国哲学重视认识主体的修养同它把认识论与价值论、求真与求善融为一体直接相关。求真与求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两者的关系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西方哲学推崇理性,认为理性高于德性。在德性与知识的关系上,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他的这一名言的旨意并不是说有了美德就有了知识,而是说知识是美德的前提条件,有了知识就有了美德。他认为人性是善的,无人有意作恶,作恶是出于无知;知识包括了一切善。所以他又说:“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转引自苗力田、李毓章,第54页)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德性与理性的关系上强调理性,认为理性是神圣的,符合理性的生活就是神圣的;哲学追求智慧的活动是被公认为所有追求美德的活动中最愉快的。伊壁鸠鲁主张,善就在于求知,他劝导人都要学哲学。斯多葛主义也认为,有智慧才能摆脱快乐的诱惑,把人们引向理性的道路、德行的生活。基督教虽然提倡盲从、信仰,但在《圣经》中有专门篇章论及智慧。《旧约·箴言》说:“智慧必入心,你的灵魂要以知识为美。”到了近现代,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理性主导德性。康德最为典型,他提出“理性为道德立法”。总之,西方哲学中理性高于德性。求善在于求真;认识论上力图排除价值对认识的影响,因此鲜有涉及认识主体的德性修养。
中国哲学则与此不同,认为智生于仁,德性高于理性,崇德以致知。在春秋时代,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尚未凸显,智、仁、勇被认为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三种品质,而三者中智为先。《国语·吴语》记载有申包胥对越王勾践讲的话:“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但作为教育家他对智也十分看重。他承袭同时代人的思想,仍把智放在仁、勇之前。他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他又说:“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智者利仁”(《论语·里仁》)。孔子之后,智与仁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孟子那里,仁、义、礼、智为人生来俱有的“四端”,智排在“四端”之末。“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智不是为了求真、辨真假,而是为了求善,分善恶吉凶之是非。因此,在孟子看来,仁高于智,德性高于理性。《管子·内业》则明确提出:“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得。”庄子的认识论虽与儒家相对立,但在德与智的关系上并没摆脱德高于智的传统。他提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求真知先得修炼做真人。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善生智慧。慧能说:“回一念善,智慧即生”(《坛经·忏悔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坛经·机缘品》)。宋明理学更是强调智出于德。张载提出“德性之智”、“崇德致知”、“仁智一体”,“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正蒙·神化篇》)。朱熹向他的学生反复说明,仁包义、礼、智。“学者须是求仁”(《朱子语类》卷六)。直到近代,谭嗣同仍说:“智慧生于仁。”又说:“仁之至,自无不知也。”“知不知之辨,于其仁不仁。故曰:天地间亦仁而矣,无智之可言也。”(《谭嗣同全集》,第292、297页)
总之,中国哲学认识论注重仁与智、善与真、德性与理性的内在联系,并主张智慧生于仁,崇德以致知,融认识论与价值论为一体。
中国古代少有哲人对人的认识能力提出质疑,因此,他们对西方哲学讨论的“人能否认识世界”的问题少有论述,而是径直提出人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与崇德致知相联,中国古代哲人主张,为了求得知,必须修养认识主体。老子主张通过“涤除玄览(鉴)”(《老子》十章)、“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来获得对道的体认。中国古人把心看成是思维的器官,思想行动的主宰者。孟子讲:“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只要“尽心”就能“知性”,进而“知天”,而“尽心”是个修养问题,“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
在中国哲学史上,《管子·心术》首先明确提出认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和主体修养的问题。《心术上》说:“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后又解释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管子》的这一论述言简而意丰、明晰而深刻,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哲人重视主客区分和重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遗憾的是它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近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界盛行这样一种说法:西方哲学主张“主客二分”,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中国哲学的实际。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曾以“所以知”、“所知”,“体”、“用”,“己”、“物”,“能”、“所”等不同方式表达了主客区分。① 《管子》从认识论上如此明确地讲主客区分,远远早于西方哲学。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尚未注意到认识论上主客体的对立,直至近代才明确讲主客二分。更为可贵的是,《管子》突出了主体能动性,提出认识论研究的重点应是主体如何求知的问题和主体如何修养的问题(即治心之术)。
先秦哲学集大成者荀子认识到,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的认识必然有蔽(片面性),“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荀子·解蔽》篇论述人如何去蔽,防止主观性、片面性,从而获得对道的正确认识。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虚、静的思想,阐述了“虚壹而静”的认识论。《解蔽》篇是中国哲学史上专门阐述认识论的重要文献。到了宋明时期,无论是理学、心学还是气学,都把认识论与道德论视为一体,从而把如何认识的问题归结为道德修养的问题。张载说:“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神化篇》)程颢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颐说:“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同上,卷三)又说“致知在乎所养,养知莫过于寡欲二字。”(《河南程氏外书》卷二)所谓“诚敬存之”、“养心寡欲”皆不过是内心的一种修养工夫。朱熹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德之事。”(《朱子语类》卷十四)王阳明认为,人心莫不有良知,良知即天理。人心之智、愚在于人心之善、恶,而人心之善、恶在于养。“养之以善”、“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心日以愚”(《王阳明全集·悟真录三·论人君之心唯在所养》)。王阳明把致良知看成是修养工夫,即所谓的“即工夫即本体”。宋明理学把认识论归结为道德修养论固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体讲是偏颇的,不利于认识的发展,尤其是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基于“智慧生于仁”的思想,谭嗣同同样把智看成是修养问题。他说:不以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触、乃至心思得智慧,而是“转业识而成智慧”(《谭嗣同全集》,第318页)。“转业识而成智慧”是佛教唯识宗的说教。唯识宗认为,万法唯心,通过人的感觉和思维获得的并不是真正的世界本体,只有经过宗教的修炼,才能去染归净,转识成智,获得智慧。谭嗣同接受了这一说教。受心学的影响,熊十力认为,人人皆有本心,皆有宇宙本体,但由于被习心、情见所蔽锢,妄执着物,因而不能见本体(本心);通过体认、修养,涤除情见,就能获见本体:“工夫诚至,即本体呈显”。他称赞心学的“即工夫即本体”是中国哲学之要旨、血脉,提出,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修养,未来的哲学应是“思辨与修养交尽之学”。(熊十力,第565、566、692页)
总之,把认识论与价值论融为一体,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显著特点之一,由此必然导致重视认识主体的修养。
二、中国古代认识主体修养的方法、途径
影响认识主体的因素甚多,其中主要有社会立场、道德情操、思维方法、知识构成、心理状态、身体和生理状况等。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哲人有关认识主体修养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
1.“公生明,偏生暗”
人的社会立场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一个人只有站在为公而不是为私的立场上才能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以中国古人提倡为公不为私。《尚书·周官》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孔子讲的“绝四”之一是“毋我”。《管子·心术下》说:“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黄帝四经》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经法·道法》)。荀子在《解蔽》中把欲、恶列为导致“蔽”的首要因素。他在前人基础上提出“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
到了宋明时期,“公生明,偏生暗”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邵雍反对“以我观物”,主张“以物观物”:“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观物外篇》)张载讲去“成心”,“成心(成心者,私意也)忘,然后可以进于道。”(《正蒙·大心篇》)程颢说:“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灭私欲则天理明矣。”(同上,卷二四)而“灭私欲”的办法就是所谓的“主敬”。朱熹说:“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极尽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学者先去人欲以致其知,则无不明矣。”(《朱子语类》卷十五)“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同上,卷十三)宋明理学把“人欲”等同于“私心”,把私欲看成绝对的恶,主张“灭人欲,存天理”,从而把“公生明”的思想推到了极端。
2.“诚则明”
在中国哲学中,“诚”历来是伦理学讨论的道德范畴,但也是十分重要的认识论范畴,它涉及的是认识主体的态度问题。中国古代哲人中讲诚较早且对后世影响大的是孟子。他提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如何做到诚?他说:“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朱熹认为,孟子所言是“思诚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为思诚之本”(《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离娄上注》)。明善是道德认识问题,即辨别善恶、是非,属于智的范畴。可见,在孟子那里,诚是客观世界的本质,追求诚是人的本性,明乎善是诚的前提。荀子主要是从道德修养讲诚,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他也认为,诚是天地所固有的,“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荀子·不苟》)。他在“公生明,偏生暗”后紧接着说:“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同上)《大学》在诚与知的关系上基本与孟子一致,但有所发挥:“欲正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很明显,这里致知是诚意的前提条件,强调的是智对诚的主导作用。
《中庸》用很大的篇幅解释孟子“诚”的思想,认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至诚者可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致诚为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对诚作了极度夸大和本体论化,以为有了诚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把诚神秘化了,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在诚与明的关系上,《中庸》的有些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是什么?朱熹解释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四书章句集注·中庸注》)从认识论和道德论讲,朱熹的解释是符合原意的。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必须持诚的态度,亦就是通常所说的老老实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求得真知,才能做到明。这就是“诚则明”。
宋明时期,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邵雍说:“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观物外篇》)张载说:“诚则实也。太虚者,天之实也。”“诚者,虚中求出实。”“人之事在行,不行则不诚,不诚则无物,故须行实事。”(《张子语录》中)程颢认为,万物只是一个天理,心是理,理是心,所以认识天理只是一个“诚”,“学在诚知诚养”(《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同样认为,心、性、天,同一理,“灭私欲,存天理”在于做到敬、诚,“闲邪则诚自存”(同上,卷十五)。程颐又说:“夫诚者,实而已矣”。他以“实有是物”、“实有是用”、“实有是理”、“实有是心”、“实有是事”来释诚(参见《河南程氏经说》卷八)。朱熹讲“诚”,突出“毋自欺”、“毋妄”。他多次说过:“诚,实也。”(《大学章句注》)“诚只是实”,“诚只是一个实”(《朱子语类》卷六)。王夫之对孟子的“诚者,天之道”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夫诚者,实有者也。前有所始,后有所终也。实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其闻也”(《尚书引义》卷三),把诚看成是客观存在,或客观物质世界和人固有的本性。他对“明诚相资”从认识论上做了说明:“明诚,相资者也,而或至于相离,非诚离明,而明之离诚也。诚者,心之独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灵而生者也。”
3.虚与壹则明
中国古代哲人不仅认识到在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的立场、态度起主导作用,而且认识到主体的思维方法也十分重要,提出要注意思维方法的修养,防止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
孔子讲“绝四”,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讲要客观地看问题,防止主观臆想、绝对化、固执成见和唯我为是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为了克服、避免认识上的主观主义,中国先哲提出“虚”的范畴。老子注重直觉,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十六章)。庄子也讲虚:“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老庄的“虚”是要认识主体尽量涤除一切主观因素(包括欲望、已有的认识),以静观直觉事物发展的规律。《管子·心术上》提出为了求知,必须“修此”(即修养认识主体)。怎样“修此”?“修之此,莫能(如)虚也。虚者,无藏也。”这里所说的“虚”亦是指去掉各种欲望杂念,属道德修养。荀子吸取了《管子·心术上》的合理思想,同时对“虚者无藏”的观点进行了改造。荀子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荀子·解蔽》)荀子对“虚”的这一解释,已不限于道德修养,而是包括思维方法的修养了。荀子认为,作为现实的认识主体的心并不是一块白板,即无臧,而是有其已知,即有臧。“虚”并不是无臧,而是不以其已知去害其所未知,从而妨碍获得新知。人的认识过程既是在实践基础上由不知到知的过程,也是以已知去认识未知从而获得新知的过程。人的认识离不开已知,已知是获得新知的必要条件,但它也可能成为获得新知的障碍。荀子的“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的话,表明他已认识到已知有可能妨碍获得新知。所以荀子的虚不仅是指认识主体要涤除物欲,也不仅是要求认识主体态度要虚心,而且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即正确处理已知与未知、新知的关系。
荀子对认识过程中的片面性弊病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荀子·解蔽》)客观事物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的统一体。人在认识事物时往往只见事物的一方面,并为这一方面所蒙蔽而不能认识事物的全体。为了防止“蔽于一曲”,做到全面地看问题、明于大理,荀子提出:“兼知”、“兼陈”、“兼权”,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还要看到事物的反面。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即在对立中把握同一。
中国古代哲人重视思维的作用,还提出“壹”的范畴。孟子讲“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提出专心致知。《管子·内业》进一步提出专一深思生知。它说:“思乃知”、“思索生知”。又说:“能抟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管子·心术下》也说:“专于意,一于心。”《管子》作者不了解在思之又思的基础上发生的飞跃(“通”),把这种飞跃视为精气专一到极点的结果,其实这正是思之又思之到极点的结果。荀子对《管子》的“壹”的思想进行了发挥和概括。他认为,认识时必须用心,否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不仅要用心,还要专心,“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壹于道以赞稽之,万物可兼知也”,“知者择一而壹焉”,“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荀子还提出要处理好两与壹的关系,既要“兼知”,又要“不以夫一害此一”(《荀子·解蔽》)。总之,认识某一事物,不可一心二用,而是要专心致志,思之又思之;用力既久,日积月累,便会豁然贯通,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专心深思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必要条件,是形成直觉(顿悟)的必要条件。对此宋明理学多有论述,在此从略。
4.静则明
人不仅有思维的理性的一面,还有欲望、意志、情感等非理性的一面。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两者都发生作用。西方哲学认识论主要讲理性的一面,中国哲学认识论则对认识活动中非理性因素多有论述。“虚壹而静”的“静”,主要是指人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对认识主体情感修养的要求。
孔子没有从认识论视角论及静,但他已提出人的情感对认识的影响问题。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亦即忿(愤怒)的情感导致惑,不能理智地认识和处理问题。《大学》大大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指出,身有“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者,则不得其正。“正其心”就是以心(理智)来调整好情感、情绪,防止过于激烈或过于低落的情感、情绪导致错误的认识和行动。
从认识论上讲静最早的是老子。老子讲虚,也讲静,虚静连讲而归结为静。他说:“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管子》的《内业》和《心术》认为:“修心静意,道乃可得”,“心静气理,道乃可止”,“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对道,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忧乐喜怒欲利则失道。因此,修心在于静心。庄子对静做了比老子进一步的解释。他说:“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万物无足以饶(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庄子·天道》)。庄子认为,心静则明,心静才能认识万物。如何静心?“斋以静心”(《庄子·达生》),即通过心斋、坐忘,忘掉一切利禄、名誉以至四肢形体。荀子综合了前人的思想,对静做了新的解释:“心未尚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荀子·解蔽》)。荀子的解释有比前人进步之处,即静不是绝对的不动、绝对的静,而是排除做梦和剧烈情感的干扰,保持一个正常的平静的心理状态。“虚壹而静”的提出是中国哲学对人类认识论的一大贡献。
佛教传入我国后,佛教的定止观与道家的虚静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定慧双修观。唐朝道家司马承祯则吸取佛教的思想提出:“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坐忘论》)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会通儒、佛、道三家讲静。程颢认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为不使心受内外之累,须定心,定心即定性。定者静也,“两忘则澄然无事。无事则定,定则明”(《答横渠先生定性书》)。朱熹说:“盖欲应事先须穷理,而欲穷理又须养得心地本原虚静明沏,方能察见几微,剖析烦乱,而无所差错。”(《答彭子寿》)这要求在思考时要有平静的心态、情绪,故他提倡静坐。他说:“始学工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定”,“精神不定,则道理无泊处”。为了做到静,“心要精一”(《朱子语类》卷十二)。当然,脱离实践、脱离生活,没有丰富、真实可靠的感性材料和经验,仅仅进行精心静思,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的,但在有了丰富、真实可靠的感性材料和经验的基础上,再反复精心静思、沉思,则确实是获得新知的一个必要条件。
注释:
① 王夫之在《尚书引义》卷五中批判佛教唯心主义时, 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客区分作了历史总结。WW罗传芳XXCK
标签:认识论论文; 儒家论文; 荀子·解蔽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老子论文; 孟子论文; 管子论文; 朱子语类论文; 荀子论文; 国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