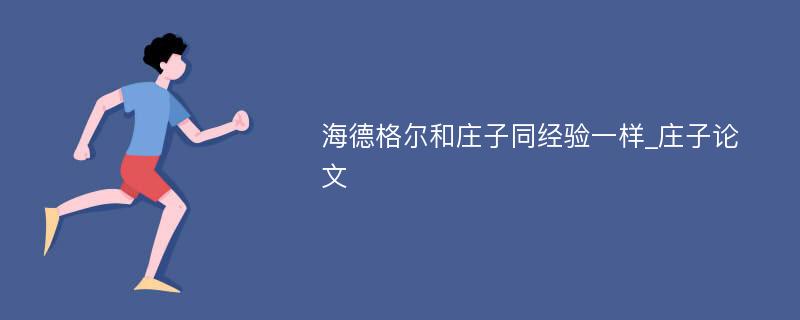
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同一在于体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庄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4)03-0028-04
一、海德格尔的融契于世界之中与庄子的游乎无何有之宫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时,指出“在之中”是此在的 存在状态,是一种生存论状态(existenzial)。不是说,此在作为精神和肉体之人,在 作为现成的存在者——天地万物之中存在;不是说一个物在另一个空间之中存在,而是 说,此在依寓于世界而存在,进一步的意思是此在“融契(aufgehen)于世界之中”[1] 。流传下来的存在论原则,无法把握此在原初地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结构,因为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在形而上学体系中是对于客体而言的主体活动,是去认识已经完成的给定的 东西。海氏后期,更注重作为澄明呼求着人的存在,人敞开其心胸让存在者契入,让存 在者在场而存在。心物交融的境域是原初的混浑,说是混沌,不是说在形而上学主宰下 万物的差别和界限浑然不清。海德格尔在《物》中用天地神人四化(Vierung)来描述四 重整体,他强调四化不是作为一个无限大的整体,不是作为无所不包的空间,附加到天 地神人四方身上,也不是说,四方作为现成存在着的东西相互并列,“四化作为世界的 世界化而存在。世界的相互映照的游戏(das Spiegel-Spiel)是成其自身的圈舞。这样 的圆舞并不是像环那样包围着四方。圆舞是一个环着的环,是作为相互映照的游戏。这 个圆舞成其自身地在它的纯一的光照下,澄明着四方。”[2]这样的圆舞,这样的天地 神人的纯粹统一是不能被说明和论证的,也不能归结为诸如原因(Ursache)和根据(
Grunde)。如果人们力图把存在和道理解为第一因、规律、依据,人的心就不可能贯通 到“世界化的纯粹性的质朴那里(Langen in das Einfache der Einfalt des Weltens) ”[2]。海氏这里在in后面用的是第四格,而不是一般的“在……之中”的第三格,其 用心在于:人心敞开的世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也不是用这个精神世界从上到下 地去笼罩现成的身外世界,而是参与进去、贯通进去、融契进去。如果人体验不到人与 物原初的相融相契的境域,如果人只停留在对物的现象和本质进行观察和思考的阶段, 如果人只满足于已经指派给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人还没有把握到人之为人、物之为物 的根基。
海德格尔认为,人能够感觉和表达的东西“预先(zuvor)从自身而来,已然澄明自己, 并且在它共同带来的澄明中向着人去显示自身”[2]。这预先的澄明境域是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产生的根基。不仅仅物只能在心物交融的澄明中才作为物显露出来,就连人, 也不首先具有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独特性质而成为人,而是说,人的突出之处在于,作为 思维动物,“他向存在敞开。在被摆进存在之前,他已然进入与存在的关联中,并且如 此这般地呼应存在。人原本就是这一呼应(Entsprechung)的关联……在人那里对存在的 隶属主宰着,因为人被转让给了存在。”[3]即使人和物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 说,人和物先于天地,本源地作为物自体而存在,而是说人和物首先源出于视之不见、 听之不到、搏之不得的道,用海氏的话说:“基于那种无用的东西(auf etwas
Nutzlosen),不论科学研究是听还是没听这种呼求,也不管它是否把听到的东西置之不 顾或者被所听到的东西震惊,对象同一性的要求仍然在言说。”[3]这里的同一性不是 抽象的同一,而是科学研究应该获得的坚实基础。科学家要体验人与外部世界天然的一 体,首先要摆脱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首先要从人是能感觉、善思维、 会说话的通行观念中跳出来。经历这种跳跃,在道家那里就是得道、体道。体道之人关 注的不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差别界限。庄子主张撇开这种认识事物的模式,而要“彷徨 乎冯闳,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知北游》),飞翔于寥廓的空间,无智的人与道契 合,而不知道它的终极。
尝试着用庄子的“彷徨乎冯闳”,去诠释海德格尔的返回到思索之路,兴许我们可以 体味海德格尔的初衷与庄子思想之间的相通之处。庄子在《知北游》中描述了心游于无 何有之宫的体验:
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尝相与无为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 调而闲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来焉而不知 其所终;彷徨乎冯闳,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 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 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4]
很多研究者把游于方外看做一种有别于形体活动的心理或者精神活动。所游的无何有 之乡是一无所有,空旷无边的地方。方外,浑然一体没有分界,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其他 的东西存在。游于方外,还被看做是主体之心与客体事物的关系,圣人通过修身养性, 就能够让自己去体悟纷纭变幻的天地万物背后的统一本质。这样的解释,仍然没有把庄 子的思想说透,还遗留着将心与物二者视为互相对立存在着的东西,用海氏的话说心物 二者仍然是存在者。因此圣人所体悟的道,还不是前形而上学、前逻辑的存在。圣人的 游心、游神从来不是在主体之我这里的心理活动,而是说我参与、融入到存在那里的体 验。关于存在的体悟,不是说把人塞到那个不可逾越的孤独的主体之中,而是说人重新 返回到我们隶属的天地万物的统一之中,我们作为此在之人从来就生存在天空下、大地 上,从来就与万物相融共处,我们从来就处在无何有之乡。天地万物之间有界限,有富 余、虚空、衰老、死亡的区别,有起始、结束、积聚、消散的变化,这些区别和变化人 们感觉得到,并且可以用概念、语言表达出来。但这些区别、变化在庄子那里,并不是 原初的,而是由道生成的。这里的道既不是存在于天地之前,产生天地万物的第一因, 也不是万物生存运动背后的逻辑根据,而是说所有的区别和界限都起始于天人合一、心 物一体那片无差别、无界限的混沌。这片混沌并不是无阴阳之分并产生阴阳二气的宇宙 初始阶段,而是说人先天就生存于与天地万物的一体之中。
二、女偊的学道和海德格尔的思存在
庄子书中有一个女偊学道的故事,女偊年纪虽大,但看起来却像孩子,肤色柔润光 洁,为什么呢?女偊说,因为我听闻了道。所谓“闻道”是运用了不同于感性认识和理 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方法。学道不是理智的理解,也不是实践的过程,学道产生于理论与 实践活动之前。学道既没有结果,也没有功效,关键在于持守。持守即破除人世的知故 成见,逾越传统观念的束缚,从习常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跳跃到体道守道的境地, 细心地全神贯注地倾听,把我们的心境敞开,使我们进入到这一新的境界中。这种跳跃 能够以不同以往的眼光去看世界,这种不同以往的视野来得突然,比起世俗的观念又显 得微不足道。持守了三天,达到了外天下的地步;还不够,需要继续持守。由于人们在 生活中总是固执地坚持着某种目标,总是与周围的人与物处于形形色色的关系之中,持 守了七天,才排除了事物对心灵的干扰。在所有的人生哲学中最难解答的、对个人又至 关重要的、最本己的、不可逾越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人从哪里来,又向哪里去,是人 不能不关切的问题。在庄子看来,生死问题不属于理智分析的范围,而是在冥默之中随 顺于生死变化而不加辨别的体悟,是因循于自然而无所执著的玩味。女偊说:“已外 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庄子·大宗师》)朝彻指的是不执著于天 下、外物、死生而获得的自由无碍的纯粹精神境界。
朝彻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有相似之处,澄明之境不是类似于供存在者表演的舞 台或空间,而是说存在者的存在在于此在对存在者的敞开。此在原本就生存地、出离地 进入到存在者之中,先天就把自己交托到存在者那里。不论此在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此 在都置身于存在的澄明之中,人总是把自己指引到由人敞开着的存在者那里。并不是说 人发明创造出了一道光明,而是说,人若能从沉迷中觉醒过来,才能获得这个朗照,重 新回到本源之处。海氏指出:“超越存在者,但并不脱离存在者。这是说在存在者之前 ,还有另外的事情在发生着。在存在者整体之中一个敞开的场所存在着(eine offene
Stelle),一个澄明存在着。从存在者那里来考虑,澄明比存在者更加存在着(seiender
als das Seiende)。这个敞开的中心(die offene Mitte)不是由存在者包围着,而是说 这个澄明着的中心本身就如同我们不认识的无一样包围着所有的存在者。”[5]超越并不 是从现象领域向精神领域的飞跃,不是从一种有形有名的现成的东西向另一种无形无名 的现成的东西的跳跃,而是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领域返回到主体与客体未曾分离剖判的 心物、天人混沦为一的境域。体悟澄明,重新获得澄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女偊经 过了九天,一步一步地接近这种境域。这个离我们很近的东西,在庄子那里就是人的本 性。女偊并没有去创造道,也不曾创造那片朝彻的光明,那个道,那片朝彻的光明是人 的天命,是人须臾不可离开的,女偊只是“见独”,“闻道”,去迎候道,呼应道。因 为道之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庄子·大宗师》),人与 物都在作为根基持存性的道那里获得存在的可能性。作为根基持存性的道不是一个客观 存在着的现成的东西,而是说人撇弃了机巧心智对身心的干扰,不再单轨地在表象的方 向上继续向前跑,才获得了宁静的心灵,进入深思之路。
道家和海德格尔引导人们改变思维方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论问题,不是在主观 与客观对立领域中发生的认识方法的转变,而是引导人们抛弃通常的认识途径,开辟另 外的视野。“损聪明,弃智虑”之后开启的另外的场所,是人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根基, 是把无家可归的人们引回到无何有之乡。海德格尔精辟透彻且通俗易懂地论述了人生存 的基础,他说:我们处于无思的状态,但思维的能力并没有消失,我们是在无思的时候 ,使我们思维的能力闲置起来,这个闲置的东西在人那里并未失去根基。从来没有根基 与失去根基的区别之大就像休耕地与高速路一样。在高速路上,从来不曾长出粮食来。 由于我们有听的能力,我们才会聋。正因为我们曾经青春年少过,我们才会老,“正因 为人在他的本质根基处拥有思维的能力,拥有精神和理智,并且被规定去思维,因而我 们才能够变得思维贫乏甚至无思。只有我们自觉与不自觉地拥有的东西,我们才能够失 去它或者说脱离它”。[5]外天下,外物,外生不是创造本来不属于人的东西,而是返 璞归真,在内心深处重新获得失去的根基的过程,找回原本属于人的世界。
三、化瞬间为永恒的体悟
庄子认为,当下存在着的东西会毫无障碍地、如其本然地显露在我的身心中,融化在 我毫无成见、不去区别分析的那片心境中。至人把心敞开到万物循环变化、没有开始和 结束的境地。在这种体验中,人已经不是有着特定形象声色的,在体验的当下,人自身 的一切欲望意志、形态特点、情感意向已经化解干净,人能够达到“造乎不形而止乎无 所化”的境界,即不露形迹而永恒存在。在这种体验中,至人以其虚无平静之心契入到 天之大、地之广、高山之宁静、流水之潺潺中。如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老子》16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 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老子》34章)。这种既可称 为小,又可称为大的道,不是至小无微、至大无极、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元气,而是说, 我返归到我与宇宙万物原初关联的境域。
海德格尔在谈到中世纪神学家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对物(Ding)的解释时说 :dinc这个词既表达上帝,也表达心灵(Seele)。上帝对于他来说,是最高最极端的物 ,而心灵是伟大的物。埃克哈特大师绝不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上帝和心灵是像大石头 那样的东西,是像质料那样的对象。他认为:爱具有这样的本性,它改变着人,使人进 入到他所爱之物中。[2]
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者、理论家马斯洛(A.H.Malow)的理想,是改善科学方法 和扩大科学权限,用以弥合当代十分严重的科学与信仰的分裂,使人类的终极追求、崇 高抱负能够在科学推动下获得人类的信仰。马斯洛在心理学治疗和研究过程中,接触了 很多第一手资料。他把人与物完全同一的体验,称之为高峰体验。他是这样描述这种感 受的:
当他达到更纯粹、更个别化的他自己时,他也就更能够同世界熔合在一起,同从前的 非自我熔合在一起。例如,相爱者亲密地构成一个单位而不是两个人,我——汝一元论 变得更有可能了,创作者与他正在创作的作品变成一个东西,母亲和孩子觉得是一个人 了,鉴赏家变成音乐、绘画和舞蹈,天文学家和星体一起出现在那里,而不是中间隔着 望远镜筒分别地出现。[6]
当然,马斯洛把我——汝一元的体验当做一种心理现象加以研究,海德格尔则把心物 一体看做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看待。但马斯洛的描述可以使心物一体更形象、更具体。
在现代小说中,在很多关于平平常常生活的描述中,也出现了人们怎样突然从动荡不 安进入虚极静笃之中的场景。诺贝尔奖获得者、丹麦作家塞兰派(F·E·Sillanpaeae) 在他的小说《生活的太阳》中写道:
在平静的心中,他仿佛感觉到嫩绿青草的香味。壁钟的嘀哒声,如同永不停歇地重复 敲打着他。这种永不停歇的重复,渐渐地使倾听者进入这样的状态:在这样的瞬间,他 意识到一种生命的大朴——存在。在这样的意识中,在这样的瞬间,包围着他的所有东 西都包含于其中,钟表的嘀哒声、发芽的青草的郁郁生命,这一天迷人的忧伤以及他自 己。他的内心仿佛在自言自语:我此刻就坐在这里,此在的所有之谜都已然解释了,并 且意味深长。[7]
这是一位农民儿子返回故乡探望母亲时的感受,他坐在父母房中的摇椅中,并且从窗 户望出去。这种体验是人与存在大朴相遇相契的感受。在这种体验中所有的欲望和意求 都平息了,充塞于心灵中的不再是个别事物,也不再是事物的某个方面,而是指向存在 之大朴。这个大朴对于我们日常的存在来说,是那样的陌生,以至于我们找不出适当的 语言去形容它。这个大朴展开着自身,并且像谜一样地漫延开来。这个大朴是那样的纯 粹,以至于与每一种特别的兴趣和每一种内心的不安宁相区别,这样的大朴是纯粹的皓 白。他在摇椅上坐着,他身体的摆动是那样自然,不为意识所知,仿佛是来自心灵与身 体内在的摆动。这样的摆动总是回到出发点。在这种状态下,后来变得清晰的关于存在 的意识状态是预先被料到的。那个事先知晓并且最终要达到的状态与那个尚未展开的大 朴的体验相呼应。在宁静中,已经存在着未展开的大朴的体验。这种体验是把生命的大 朴带入意识,大朴不是关于世界存在整体的概括,而是把人的生命、人的生存活动带入 到万物整体中。在大朴的体验中,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都被包括在其中。在大朴的体验 中,关于事物的所有疑问和不解都消失了,一切仿佛都只在这一片浑浑沌中显露出来, 变得清晰。
关于大朴的体验是当下的体验,当下不是与过去、未来联系中永恒时间长河上的一个 时间点,而是纯粹的当下。瞬间不是时间的概念,而是表述了人与宇宙万物契合为一的 处境。如果说瞬间是时间的话,也不是那种或长或短的时间,而是指人把自己展开、参 与到万物运化之中去的到时(zeitigen),是人把自己伸展到物之中的在场(wesen)。当 下,即这个体悟的瞬间和存在之整体是同一的。存在整体不能够脱离人当下瞬间而独立 存在,如果脱离人向着存在整体的敞开和在场去把握整体,那么这样的整体,就不是活 生生的万物整体的本然状态,而是从人的生存世界割裂下来的死板的抽象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