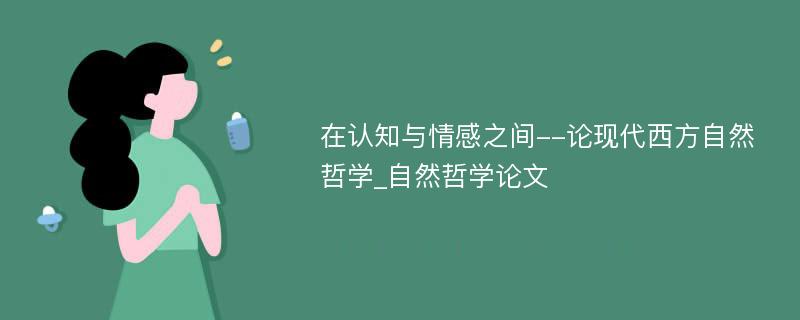
在认知与情感之间——略论西方近代自然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认知论文,哲学论文,自然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0)01-0008-06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哲学。在这种自然哲学中,精神作为自然的属性蕴含于自然整体之中。世界是精神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合一的实体性,它的本质是自然的合一。但“实体性”这一综合的概念孕含了个体性、主体性的思想种子,随着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发展,这颗种子终于在近代萌发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想幼芽,并塑造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特征。西方近代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是人与自然矛盾实质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历史的理论反映,也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所孕含的理论矛盾的进一步展开和延续。
一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经验派的哲学家,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培根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验传统。这个传统到了培根这里,终于引发了新的自然观出现的条件。培根主张人应该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归纳客观事实,从而获得知识,借助知识来真正认识自然。而认识自然的目的不只是寻求一种纯粹精神上、智慧上的满足(就像希腊人一样),既然自然是作为与人相对待的存在,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征服作为对象的自然,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在此,人第一次成为自觉的目的,从古代哲学所醉心的那种合一的“实在”中凸显出来。
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哲学为新自然观和近代科学的产生作了关键性的工作。笛卡儿承袭的是怀疑派的传统。他认为必须用怀疑的方法对一切存在的现象进行怀疑,然后从中找出最明晰、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来作为演绎的前提。而怀疑一切所得到的最终事实是:只有思维着的“我”和上帝是确定不移的存在。而“我在”是因为“我思”。物则是上帝的产物,同时也是“我思”的对象。这种“心物二元论”实际上完成了人与自然的二分。人不再隐于自然之中,而是站到自然的对立面,并且作为主动的存在与受动的自然相对待。而自然,作为受动存在,在笛卡儿哲学那儿逐渐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存在。心灵的属性是思维,而物质的属性是广延。广延性消灭了物的质的多样性,将它们统一在数学、力学的规律中。凡是具有广延性的物体,都是没有灵魂的机械存在,而人是灵魂与肉体机器的结合。在笛卡儿的哲学中初步形成了机械论的自然观。在这种自然观中“与凝固的自然相对的是人的心灵,心灵与其肉体和整个自然界面面相觑。在面面相觑中,僵化的自然当然无所作为,它只是遵循自身的机械规律而运转。而人却大有可为。既然自然只是一部凝固的机器,人就可以发现它的规律,任意地改造它。人可以征服这无言的机器,让它为人服务”(注:李章印:《自然的沉沦与拯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40页。)。这种自然观在牛顿那里完成了它的成熟形态,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近代科学的观念和进程。
启蒙思想家使笛卡儿和牛顿的世界观成为一种信念深入人心。这种信念即相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井然有序的、必然的规律和法则,人类的理性可以掌握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从而掌握人类自身的命运。在这个科学的时代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进一步发现了自然的客观结构,在征服自然的对象性活动中,人进一步地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力量和地位,并且上升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要的矛盾方面,在主体的框架内,人与自然似乎获得一种平衡。然而矛盾内在地持续着。
18世纪末19世纪初,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拉瓦锡的化学革命、布丰和拉马赫的进化论思想,就已经在完整、强大的机械自然观的图景上扯开了一道道缺口。进化、演化、发展的观念进入到自然科学理论之中。这种观念是一种辩证的自然观,它强调从自然界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中把握事物自身的规律。在这种新的自然观念的修正和引导下,古典科学在19世纪得到全面的发展,科学形成一种空前严密和可靠的自然知识体系,并积极地被普及。同时,理论科学的伟大创新很快转变为技术科学,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从机械的自然观到辩证的自然观,是自然观上的一次进步,尤其是在生命科学领域,以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统一过去生物学的各个独立的分支,乃至确立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人被确认为自然物种中进化得最好、最高级从而也是最高贵的生物。这个科学结论很快成为一种新的信念、新的世界观。它愈加强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已经矗立在自然之上的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形象。以人、主体为主要方面的矛盾以它特有的逻辑和方式存在并继续向前发展。
二
在人类的原始的精神结构中,人类作为主体,作为自然之子,它对自然母体除了有独立的、自由的倾向,还有依恋、认同的倾向,这两个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当对立的方面上升为主流时,同一的方面并没有消失,而是蜇伏着、潜流着,积聚着自己的力量,并以特定的方式顽强地展示自身。
当机械论的自然观在西欧大地萌发时,泛神论的自然哲学却在德国思想界开出一种奇异的思想花朵。与西欧思想界流行的严谨的、逻辑的语言相反,德国哲学家雅各布·波墨用一种类似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原始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自然观:“一切事物有自己的表现方式,这就是自然的语言,由此一切事物都清楚、响亮地表达自己的性质……每一事物都表现出给予它的形式以本质和意志的母亲的特性”(注:转引自桑迪拉纳:《冒险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波墨认为宇宙和人心相通,人通过一种内在的经验和神秘直觉进入宇宙内部,了解真正的自然。而真正的自然是在对立中展现出自己,自然万物在斗争中呈现出来,自然在斗争中发展了自己。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后来在黑格尔哲学大厦中发出来的光辉。但黑格尔思想无疑是新理性主义构筑起来的,而波墨则更多地带有类似古希腊、古东方思维的纯朴色彩,他强调的是人心对自然母体的一种神秘的体验。
18、19世纪先进的英法文化强烈地吸引着德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对自然的数学结构的信仰使得神秘主义越来越丧失其影响。但德国传统仍在顽强寻求自身与新思想的结合点。莱布尼茨以具有活力、灵魂(隐得来希)的单子来解释机械的自然的本质,据此来说明宇宙的生机勃勃的过程,试图调解机械论和有机论。莱布尼茨对自然的这种机械论和有机论折中调和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被称为主体性哲学家的康德。康德顺着这条路向走向主体自我意识,在这种主体意识中,那个原始的矛盾以主体分化和客体分化作为它自身的解释方式。康德在《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中,用事物内在的引力和斥力的矛盾解释宇宙的起源、演化和各种自然事件。这种内在的对立力量依然循机械律发生作用,但如此形成的自然是一个内在的有机体系。这样,机械论和有机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和。但康德在对自然作出这种解释之后,他的德国传统又让他继续反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认识就是正确的呢?我们的知识具有必然性吗?他发现,主体认识依据的是先验的范畴和知性概念,而进入概念框架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现象。因此,现象可以说是主体意识创造的客体或对象。但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可以给予知识以客观必然性,比如时间、空间这两种感性形式就具有客观必然性。而自然的本质却是神秘的物自体,它高于并远离经验和概念。这样,自然就分裂为物自体和现象界。物自体虽然不是知识的对象,但它依然可以成为主体的对象。因为人的精神结构除了知性力之外,还有理性力和判断力。理性是最高的自由,牵涉到意志这一物自体;而判断力则是情感的功能,情感处于认识和意志之间,判断力可以超越知性对自然进行审美判断,继而过渡到理性意志。这样,人就可以超出知性认识而对自然进行情感和意志的理解。由此,主体的精神结构也分化出三个层次:认知层次、审美层次和意志层次。认知层次限于科学认识;审美层次与科学认识对立并超越了科学认识,并过渡到意志的对象:道德原则的主体。
康德意图全面地融合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寻求出一种普遍性和统一性。但他的哲学的结果则进一步引向了科学与全面的人性的分裂、自然的分裂、主体的分裂。在他的哲学中,存在着认知的自然、审美的自然与意志的自然,这三者无法统一。人性中又存在着认知的主体、审美的主体和自由的主体,这三者也无法统一。于是科学与全面的人性进一步分裂了,科学与艺术、与道德似乎分道扬镳了。
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科学的发展继续坚守着对自然的必然性理解的信念,通过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道路,主体不断地改造征服了自然,也日益与自然对立,疏离了自然,从而也疏离了自身;而在艺术那里,人类却依然对自然抱着母性的情感关怀的期待。歌德是那种具有哲学家气质的诗人,他认为自然的秩序是“非测量秩序”,自然的奥秘只有靠对自然的直接观照来领略。“与其强迫自然进入我们精神的抽象之中,不如努力‘倾听’它的秘密”(注:Karl·J·Fink:《歌德的科学史》,剑桥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这种以贴近自然、倾听自然的把握自然方式,已经超出了认知的范畴而走向审美的范畴,歌德对康德的自然观的这种艺术性的发挥,终于使浪漫主义的自然哲学在德国开出绚丽的浪漫主义艺术的花朵。
三
浪漫主义是作为技术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叛逆出现的。他们认为工业、科学、文明的进步,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远。在他们心目中自然有自己的内在特性和语言,这就是自然的形态和表现,是自然各部分之间的特殊的和解能力。人首先应倾听这种语言,才能与自然交流和融通。而与自然交流和融通,是人内在的深切的精神需要,倾听自然就是追求人心中本然存在的、但被文明疏离了的“神性自然”。这一倾听是一种人类的自我拯救,它不再由上帝承担,而是由浪漫派的诗人的吟唱来对自然作“诗的观照”。因为诗人的语言保留了许多神圣的原始的精神之光,从而在诗的照射下,自然成为精神的图腾。
浪漫主义是从主观自我开始的,但它逐渐超越了个体的偶然的主体主义,趋向一种普遍的统一性。主体主观的极度扩张便走向它的反面,它觉悟到除非主体与自然、宇宙发生联系,否则主体的存在就孤立而失去意义。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无限的永恒的一种渴望。这样,浪漫主义就在人与无限的大自然、无限的空间的关系中看待人的存在,只有在这种关系中,生命才获得意义。自然就是启示,是人的体验的对象。启蒙时期的人们并没有把自我主体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他们欣赏的只是大自然的田园风味,而浪漫主义则是把主体浸没于大自然之中,神秘地、泛神地感觉自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实质上是一种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表现。作为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反动,它推动矛盾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发展。所以,浪漫主义思潮固然有着返归荒野(自然)的表达形式,但人、主体并不消隐于自然之中,而是在其中轰然着人性的迥响。
谢林作为浪漫派的哲学家,他的自然最初来源于无限的绝对。但绝对在自然中不能最终实现自身,而需借助艺术和宗教。因此,自然就成为艺术的直观的对象,艺术把自然和自由综合在一起,从而展示了自然的奥秘。“艺术好象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一道火焰”(注: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65页。)。艺术是已经分离的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和人内心的本然的全面需求通向永恒的原始统一的美丽彩虹。实质上,谢林在这里所指出的永恒的原始的统一只是一种表达的形式罢了。作为初始存在的统一,在经过了自身的分裂、差异、对立、斗争和渗透、融合之后,再返归的统一应是与初始统一具有不同内涵的统一。而谢林和浪漫主义的思想家、艺术家们并不正视这一点,不能忍受现实,尤其是混乱的现实,使这些浪漫英雄一心恢复在历史中、生活中被打碎了的抽象的统一。这种朴素天真的神秘主义倾向终于导引他们步入歧途,走进一种病态的境界。他们试图超越现实,但这种超越只在精神领域里,尤其是在音乐方面获得成功。而在实践的领域里,浪漫主义最后成了消极的逃避。谢林后来又用宗教的直观代替艺术的直观,而这种中世纪的幽灵已很难被近代社会接纳了。
黑格尔试图在理性的概念大厦中对自然作最后的拯救。思辩主义代替浪漫主义来向抽象的统一的目标复归。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自然界是作为终极实在的理念的外化而存在的。自然虽然是客观的,有生命的,但这种客观性和生命力却是来源于抽象普遍的理念。所以自然与理念的关系也象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的关系一样。康德还保留了现象界的独立性、而黑格尔则让自然经过思维再回到理念概念本身。回到了一种虚构的抽象的概念统一。自然在黑格尔那里完全成了一种派生的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在深入到概念自我运动的环节时,他的辩证思维帮助他提出了“实践”的概念。但他所“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页。)因而把人理解为绝对观念在历史领域中展现的理性的存在。这实际上是用纯粹抽象的“理性”代替了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主体被抽象化了,也被片面化了。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大厦的构架上看,有机论的自然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不仅没有得到拯救,反而更加沉沦于概念、思维的深渊之中。
费尔巴哈在试图从宗教和理性的“天国”回到“大地”上时,却又走到了另一个片面性,他把人理解为纯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即认识的感性对象。“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费尔巴哈看重的是在人的自然属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他理想化了的感性的爱和友情,而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真实关系则完全被感性化和理想化了。这样,他以“自然的人”取代了真实的、作为主体的人,在他的“自然的人”视野中,“实践”只是一些类似于本能的行为活动,失去了它作为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的革命性的意义。在费尔巴哈的思想中,人与自然的现实的、真实的关系被彻底取消了。缺乏科学实践观的哲学是“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这里只剩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至此,德国古典哲学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其终结也就势所难免了。
四
西方近代哲学确立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构架,是自然哲学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如果人不能在理论思维中将自身从混沌的自然中区分出来,不能确立自身作为主体的存在,则自然也就不能成为人的对象,不能成为为人的存在,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早就在历史地发生着。近代哲学只不过是在认识论上确认主客二分而已(当然,这种理论确认意义重大)。近代大多数哲学家都承认科学和理智的合理性、权威性,确信主客二分是自然观也是哲学的巨大进步。但是,应该说,这种进步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危险:即主体的确立促成了主观主义的倾向,塑造了近代哲学的主观气质,这种气质“往往把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看成仅仅是有待加工的材料”(注:伯特兰·罗素:《西文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在这种理念下,科学、理性很快具体化为人们按机械原则来形成的组织技巧和能力,而自然则完全成了一种被动的存在。由于自然的这种在主体视野中的被动性质,“物质的诗意的感性光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页。)消失了。物质成了被征服的对象,随着被征服的对象的增多,领域的增广,造成了一种主体辉煌胜利的景象。然而这个胜利,却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取得的。被征服的自然、物质失去了它自身对人而言的“诗意的感性光辉”。那么人呢?作为征服者的主体在失去了诗意的自然对象的同时,便也失去了其本身价值内含的“诗意的感性光辉”,失去了其全面发展的趋势。继而,片面的主体不断地被自身的片面性所吞噬。开始是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机械化,接着是人在社会机器中的机械化。理性原则变成了一种工具。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这种工具理性也不断膨胀,使得人在社会活动中不断丧失其主体性,引发了人的精神价值的不断失落并引起深刻的痛苦。
西方近代哲学在它的德国阶段显示了一种主体追求与自然统一的努力。这一方面是理性自身的要求,更多的是表达了主体对自然在情感上割舍不了的联系。这种情感意味,既有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悠长传统,又有对主体认识将存在对象化,使人类情感失去母性依赖而导致的恐惧、不适、拒绝和抗拒。这种情感的倾向深深地沉隐在形而上的思辩中。
在西方近代哲学家中,对自然的认知倾向和对自然的情感倾向的对立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他们更多地是想在主客体哲学的框架中对这两种关系作一种融合,一种平衡,试图达到一种新的统一。这种努力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归于失败。但矛盾并没有就此终结,在西方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思潮与非理性主义思潮是这一矛盾的新的表现形式。我们从它们的对立中依然可以听见人对自然的认知需求和情感需求渴望统一的邈远的回音。
收稿日期:1999-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