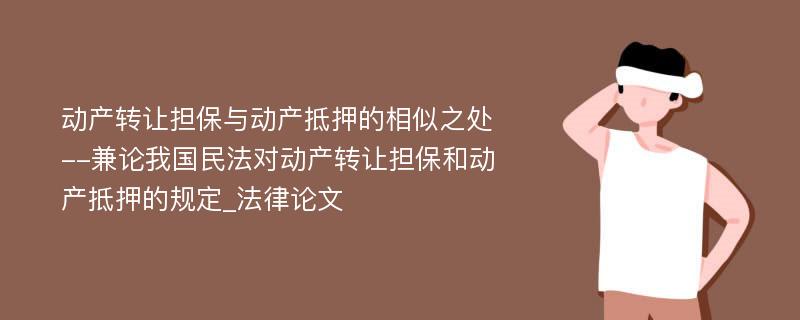
论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之雷同——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对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的规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产论文,让与论文,民法论文,草案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民法典制定进程的推进,让与担保这样一项类似“鸡肋”的舶来品是否应被纳入民法典已备受学界重视。在许多学者看来,让与担保是一项独立的私法制度,能够弥补民法典型担保制度僵化的缺陷并节约交易成本,因而应将之成文化。[1]从全国人大法工委2002年12月提交给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草案”)来看,显然采纳了通说:一方面继续沿用1995年《担保法》的做法,规定了动产抵押,另一方面又设专章规定了让与担保制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有无区别?如果两者雷同的话,可否仅规定动产抵押制度而不移植动产让与担保?(注:王泽鉴先生认为,“仅创设动产抵押制度,此在一方面可简化法律关系,在他方面亦不致影响债权人的担保利益。”他还认为,《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Act)》为简化及统一法律关系,将统一动产抵押法(Uniform Chattel Mortgage Act)、统一附条件买卖法(Uniform Conditional Sales Act)及统一信托收据 法(Uniform Trust Receipt Act)废除而仅规定一种担保方式即担保约定(Security Agreement)的立法例“颇值参考”。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8页。)上述问题牵涉甚广,须全面检讨动产 抵押、让与担保和质押等相关制度存在的价值及功能,分析其利弊得失,方能论断。笔 者不揣陋见,拟就上述问题结合各国立法例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各国立法对动产让与担保和动产抵押制度的不同态度
动产抵押是曾一度存在于古罗马法的重要担保制度,但滥觞于《法国民法典》的近代 大陆法系民法并未承认其合法地位。《法国民法典》第2119条规定“动产不得设定抵押 权”,《德国民法典》也维持占有质原则而排除了动产抵押。(注:《德国民法典》制 定者放弃动产抵押立法化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欠缺适当的公示方式,不利于维持安全 的信用经济;二是为了限制没有土地的非富裕阶层的人们对担保的利用。参见王闯:《 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这样,在近代大陆法系民 法传统中,抵押只能设定在不动产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质押以移转标的物的占有为成立要件,在满足债务人融通资金需求的同 时无法满足其使用收益的要求。(注:质押的另一个缺陷在于债权人占有标的物的同时 要承担相应的保管义务。其优点则表现为:质权人占有动产,一方面可避免债务人毁损 标的物,有助于保障债权;另一方面还具有公示作用,可促使债务人尽快清偿债务。) 因此,在克服质押缺陷的前提下创设新的动产担保制度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纵览大陆 法系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最终选择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安排可分为三类:
第一,动产抵押立法化。以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1804年《法国民法典》将抵押严格限定于不动产之上适应了当时农业社会的经济需求,但时代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迫使法国在不改变其民法典第2119条的情况下发展出较为发达的动产抵押制度。法国创设动产抵押制度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其一,通过特别立法规定动产抵押,如海商法 中规定的船舶抵押权;其二,将划分动产与不动产的标准弹性化,承认动产附着物、注 册动产等可以作为抵押物,[2]实现不动产抵押向动产抵押扩展的实际效果。法国动产 抵押的合法化是在民法典的范围内不得已采取的变通措施,没有突破既有的民法理论框 架,局限性较大。我国台湾地区在创设特殊动产抵押即“海商法”规定的船舶抵押和“ 民用航空法”规定的航空器抵押的基础上,全面继受美国法,在“动产担保交易法”中 创设了一般动产抵押制度,以登记、烙印或贴标签相结合代替占有作为公示方式,几乎 使全部动产均可成为抵押物。动产抵押在台湾发挥了巨大的经济功能,而同样规定在“ 动产担保交易法”中的信托占有(让与担保之一种)则很少为人们利用,名存实亡。[3]
第二,默认动产让与担保。以德国为代表。德国普通法时代所确立的占有质原则在事实上消灭了动产抵押,当事人为设定普通法所禁止的动产抵押权,不得不采取缔结附买回权的买卖契约的方式,即让与担保。对于这种权利移转型担保,德国法院经历了否定 、初步承认、认可“三部曲”式的艰辛发展历程。[4]德国判例最初认为,让与担保是 当事人为担保债权的目的,通过买卖的外观形式以规避普通法上禁止设定动产抵押的规 定,当事人并无转让所有权的意思,所以该法律行为无效。但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期即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主流观点认为,排除动产抵押是为了在本质上提高信用,维持安全 的信用经济,但由此处于中下阶层的商人或劳动者不能在融资的同时使用收益其动产, 显然不利于经济繁荣,因而默认动产让与担保。(注:作为佐证的是在民法典审议过程 中,当一名委员提出禁止“为担保而让渡所有权”的动议时,其他委员坚决反对该动议,致使该动议最后未被采纳。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制度之研究》,成文堂1989年版,第193页;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此外,依据德国民法典中关于“占有改定”的规定,让与担保也得成立。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与此相应,帝国法院也以一系列判例逐渐承认了让与担保的有效性。时至今日,让与担保因弥补了民法否认非占有移转型动产担保的欠缺而成为德国动产担保制度的中心。(注:数据统计显示:在以204件企业破产的裁判事例为对象的统计结果中,让与担保在全部事例中的比例为15.3% ,质权占3.2%;在动产作为银行融资担保标的物场合,让与担保占24.1%,而法定质权 仅占2.3%。参见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40页。)
第三,动产抵押和让与担保并存。以日本为代表,1898年《日本民法典》并不承认动产抵押,但随着动产价值的提高,以及作为担保物的动产在债务人的生活或营业上日益不可或缺的情形下,“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公示方式”的传统民法观念暴露出弊端而陷入困境。为此,日本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对策:其一,通过特别法将抵押制度扩大适用于特定类型的动产,具体包括《农业动产信用法》、《机动车抵押法》、《飞机抵押法》、《建设机械抵押法》和《日本商法典》中的船舶抵押;其二,在多数情况下,动产让与担保发挥了作用,“在日本,动产的让与担保也作为动产抵押化的方法而产生”,[5]“动产的让渡担保成为动产抵押的代替方法”。[6]
综观各国立法例,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其一,“抵押与动产的矛盾,仅仅是历史上的意外事故”。[7]由《法国民法典》将抵押严格限定于不动产到各国普遍承认动产抵押或作为动产抵押代替手段的让与担保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其二,动产让与担保作为动产抵押的替代手段而出现。法国建立了较为发达的动产抵押制度,因而不承认让与担保;在我国台湾地区,让与担保本为代替动产抵押之方法,[8]但在“动产担保交易法”创设了一般动产抵押制度之后,让与担保已渐趋消亡;德国因不存在动产抵押,让与担保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日本虽以特别立法的形式创设了动产抵押,但因可以成为抵押物的动产类型过于狭隘,在多数情况下,动产让与担保成为动产抵押的代替方法。综上可见,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发挥了相似的社会功能,其原因何在,不妨从两者的制度构成中去探寻。
二、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之比较
广义的让与担保包括买卖式担保及让与式担保,而狭义的让与担保即让与式担保又可分为附条件的让与担保和信托的让与担保。作为担保物权之一种的是信托的让与担保,本文所谓的动产让与担保即为信托的让与担保之一种。依民法草案物权编第311条的规定,动产让与担保是指为了担保债权的实现,将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动产转让债权人,债务履行后,债权人应当将该动产返还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一般认为,动产让与担保为非典型担保、权利移转型担保,而动产抵押是典型担保、非权利移转型担保,因而两者“具有不同的法律结构,满足不同的社会经济需要,各有其存在价值。”[3](308)民法草案将两者并列规定,可见采信了类似的观点。但是,让与担保在完全担保物权化之后,与动产抵押在法律结构上是否还存在差异?即使存在某些差异,是否能使两者各具独立的存在价值?对此,笔者拟在比较两者的性质、设定、公示等法律结构的三个重要方面的基础上做出解答。
(一)性质之比较
动产抵押权为一种担保物权并无疑问,至于动产让与担保权的性质,则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为所有权说,认为让与担保权不是一种新创设的与抵押权或质权相当的担保物权,而是基于让与担保合同设定的所有权;另一种是担保权说,认为让与担保只不过是担保权的设定,重视担保的实质。[9]所有权说过于偏重作为法律手段的所有权让与这种外观形式,而轻视当事人之间所欲达到的实质上的担保目的,几乎将设定人置于单纯出卖人的地位。根据所有权说,担保物的所有权完全移转到让与担保权人,但让与担保权人行使所有权不得超出担保债权的目的范围之外。让与担保权人对标的物的处分系有权处分,因而不论第三人出于善意或恶意均能有效地取得所有权,而设定人不能追及。极度弱化设定人的地位使所有权说渐趋式微,担保权说则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有力说。依据担保权说,在动产让与担保场合,设定人应将动产所有权移转于让与担保权人,但让与担保权人仅取得形式上的所有权,在让与担保期间,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双方均不得处分担保物。民法草案物权编将让与担保置于“担保物权”之下,显然采纳了担保物权说。因此,动产让与担保权与动产抵押权在性质上均系担保物权,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权利移转型担保,后者是非权利移转型担保。由于在动产让与担保中权利的移转仅仅是形式上的,因而,这一差异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进一步的比较将印证这一论断。
(二)设定之比较
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均以担保主债权的实现为目的,标的物的提供人均可以是债务人或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取得担保物权均以订立书面合同为必要;(注:参 见民法草案物权编第246条:“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第3 12条:“当事人订立让与担保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非移转占有型动产让与担 保(注:动产让与担保可以分为移转占有型和非移转占有型。移转占有型动产让与担保 将标的物移转于债权人占有,虽然解决了公示问题,但与质押一样存在须移转标的物的 占有从而不利于债务人继续使用收益的弊端,因而并非动产让与担保的常态。民法草案 物权编规定的即为非移转占有型让与担保(第315条:“让与担保期间,担保物的占有人 以及让与担保的权利人不得处分该担保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与动产抵 押一样不移转标的物的占有,而动产物权的公示以占有为通例,因而面临同样的公示问 题。(注:民法草案物权编对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规定了不同的公示方法:前者自 在动产上标志让与担保时设立;后者则沿袭了《担保法》登记生效主义与登记对抗主义 相结合的模式。对同样的动产担保物权公示问题采取不同的公示方法,似不利于法律体 系的严密完整。王闯先生的解决方案或许更有可取之处,详见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 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王闯:《动产抵押制度研究》,载梁慧星 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页。)可见两者的设定十分 相似。
一般认为,两者设定的最大区别在于标的物适用范围不同:具有可转让性的动产即得成为动产让与担保的标的物,而动产抵押物则限于特定的动产类型。[10]《担保法》规定的动产抵押物的范围如何,有不同理解:其一为严格限制型,认为应限于《担保法》第42条第4、5项规定的特殊动产和生产资料,[11]或者认为《担保法》没有规定的财产 可否抵押,应根据法律规定确定;[12]其二为宽松型,认为立法不可能穷尽所有可以用 作抵押物的财产,只要某项财产符合抵押物的条件,即抵押人有权处分、具有可转让性 、便于管理和实施,就应当承认其属于抵押物范围。[13]笔者赞同后者,理由有二:其 一,薛驹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草案修改稿)>修改意见的汇报》中的说 明:“有的委员提出,应当明确规定牲畜可以抵押,承包的荒山、荒滩等荒地使用权可 以抵押。因此,建议将草案修改稿第3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 输工具和其他设备可以抵押,修改为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可以 抵押。”[14]可见,将动产抵押物限于特殊动产和生产资料的观点并不妥当。其二,随 着动产抵押公示制度的完善,为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动产抵押物的范围也愈趋广 泛,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几乎所有的动产均可设立抵押。民法草案物权编对动产抵押 物的范围并没有做出限制;(注:我国民法草案第241条规定:“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二)抵押人所有的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四)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国有机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财产……”第250条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 ,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登记部门为抵押人所在地的公证部门。”)而且草案对抵 押标的使用了“财产”一词,从法理上讲,一切可让与的财产,从有体物到无体物,从 单一物到集合物,从特定物到流动物,从已形成物到形成过程中的物等,均被囊括其中 。由此可以认为,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中“动产”的外延是等同的。(注:即使对 动产抵押物的范围不作任何限制,动产抵押也并不一定是首选:当事人对担保物如果没 有使用收益的迫切需要,往往会选择更为迅捷和低成本的质押。因此,认为对动产抵押 物的范围不作限制将使登记机关不负重荷、当事人不胜其烦的担忧并无必要。参见王磊 :《论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现存缺陷及其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5期,第2 7—30页。)
(三)实行之比较
一般认为让与担保的实行是一种私的实行,让与担保权人在债务届期未获清偿时得直接取得所有权,而不需经过拍卖或变卖的程序,从而与抵押权和质权的实行相比可以节省一定的交易费用。[5][10](900)[15]在规定抵押权的实行须为公法程序时,(注:《德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债权人就土地和抵押权所及的其他标的物取得的清偿,以强制执行的方式来完成。”因此,在德国就抵押权的实现而言,债权人必须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令,由法院将抵押标的扣押,进而实施强制拍卖或强制监 管。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288页。)确实如此;但时至今日,各国物权立法对抵押权实行的规制已趋缓和。我国立法顺应了这一趋势,充分贯彻意思自治的理念:《担保法》及民法草案物权编均规定抵押权实行的方法有协议折价取得抵押物所有权或拍卖、变卖抵押物取偿三种;在协议不成时,抵押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民法草案物权编第318条对让与担保的实行规定了有约定的依约定,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时让与担保权人应合理行使优先受偿的权利。在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情形,让与担保的实行仍需诉诸法院或仲裁机构。鉴于此,两项制度的实行已无高下之分。
三、移植动产让与担保还是固守动产抵押——与贲寒教授商榷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已在功能、性质、设定、公示等诸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从学理上讲,动产让与担保是权利移转型担保,担保力最强;而动产抵押既非权利移转型担保,也非占有移转型担保,担保力最弱。但是,随着让与担保的法定化,所有权说为担保权说所取代,让与担保权人虽仍取得担保物的 所有权,但在让与担保期间,这一“所有权”已被虚化:担保物由设定人占有、使用、 收益;让与担保权人不得处分担保物;即使债务届期未获清偿,让与担保之实行也以双 方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让与担保权人须履行清算义务。为平衡设定人和让与担保权人 的地位,让与担保的担保力已被弱化。动产抵押则凭借立法技术的发展,担保力在法律 上获得补正:公示制度的完善,使动产抵押权的效力获得公开的承认,并使同一物上不 同抵押权人权利次序获得统一的标准,也使动产抵押物范围不再有所限制;物上代位制 度、抵押权物上追及力的赋予,均使抵押权人的利益获得更为周全的保护;抵押物受让 人的涤除权则很好地平衡了抵押人、受让人和抵押权人三方的利益。动产让与担保与动 产抵押相雷同已是在所难免,由此,民法草案将两者并列规定的不合理性也已凸显:
其一,两者在我国没有共存的必要性。如前所述,德、日等国让与担保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动产抵押制度的缺位,而我国1995年《担保法》即已规定动产抵押;民法草案将功能、性质、设定、公示等诸方面均十分相似的动产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并列,必将使法律关系复杂化,使担保物权竞合问题更加扑朔迷离,必将使实务界面临重重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同时,由于人们在交易实践中已经熟悉动产抵押,对完全陌生的让与担保极有可能弃之不用,导致让与担保制度的闲置,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其二,两者在我国没有共存的可行性。动产抵押和让与担保之所以在日本并行不悖,是因为其立法严格限制了动产抵押物的种类,除此之外以占有改定方式进行担保融资的动产,只能采取让与担保方式进行。这是让与担保与动产抵押共存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台湾地区,让与担保本为代替动产抵押之方法,但在“动产担保交易法”创设了一般动产抵押制度、对动产抵押物不作任何限制之后,让与担保已渐趋消亡,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上所述,民法草案所规定的动产抵押和动产让与担保中“动产”的范围是一致的,因而两者在我国没有共存的空间。
既然我国未来立法不应同时规定动产抵押和动产让与担保,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取舍的问题,即应仅规定动产抵押还是仅规定动产让与担保?贲寒先生在《动产抵押制度的再思考》一文(以下简称“贲文”)中认为应废除动产抵押制度,用让与担保制度取而代之。[16]但笔者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法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动产抵押制度,而不移植动产让与担保。理由如下:
首先,贲文认为动产抵押与动产让与担保“在功能、设立方法、公示方法和效力等方面,完全雷同”的同时,又认为动产抵押存在“公示方法、公示效力及适用范围”上的障碍,[16]前后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嫌。因为既然两者相雷同,那么动产抵押面临的公示问题动产让与担保也无法避免,所以废除动产抵押“有利于维护物权公示效力的统一性”[16]之说并不成立。同样地,既然两者“在功能、公示方法和效力等方面是完全相同 的”,那么废除动产抵押“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让与担保制度媒介融资的功能”[16]之说 也不能成立。(注:虽然从学理上分析,动产或不动产、其他物权、债权、无体财产权 或尚在形成中的权利均得为让与担保的标的,但在让与担保完全担保物权化之后,与不 动产抵押、权利质权相比也已无任何优势可言,所以从这个角度“更好地发挥让与担保 制度媒介融资功能”也无从说起。)
其次,贲文认为废除动产抵押“有利于维护物权法体系的完整性”,“避免民法典物权编的内容过分臃肿”,[16]笔者认为这同样不能成立。动产与不动产具有质的差别,两者的利用方法、交易的流通性等各方面均有极大的不同,大陆法系近代民法不承认动 产抵押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解决其公示问题,而不是因为其有损于物权法体系的完整性 。(注: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类比是,我们不能因为在不动产所有权之外还存在动产 所有权而认为动产所有权的存在破坏了物权法体系的完整性。事实上,不动产所有权与 动产所有权确实存在诸多差异,但这正是区分不动产与动产的意义所在。)动产抵押与 不动产抵押的最大区别在于公示方法的不同,除此之外,两者更多的是相似之处,因而 动产抵押可适用关于不动产抵押的规定,由此,对民法典内容过分臃肿的担忧似无必要 。
再次,中国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历史继承性的分析。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是根植于特定社会传统和民族习惯的一种社会现象;新法与旧法之间只有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才有利于交易规则的固化。传承意义上的革新较之于断裂意义上的革新总是更为可行,我国近二十年来的“变法”采取了一种渐进主义的模式,制定民法典也不应偏离这一路径。我国自1995年《担保法》规定动产抵押以来,动产抵押在我国存在已达八年之久,已成为人们担保债权的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已有相当程度的贡献, (注:法律的效用甚难估算,笔者亦未能收集到全国关于动产抵押的权威统计资料。但 所谓“叶落知秋”,据不完全统计,仅2002年1—9月大连市工商局共办理动产抵押登记 329份,抵押金额333 583万元,足见动产抵押已发挥了相当大的担保功能。参见武冬梅 :《大连市工商局把牢合同关》,http://www.cicn.com.cn/docroot/200209/17/kw01/ 17010205.htm.)而我国民事立法和实务本无所谓动产让与担保,(注:我国现行的按揭 制度并不是让与担保,两者在设立目的、生效要件、权利实现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异 。参见屈茂辉、戴谋富:《按揭与让与担保之比较》,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年 第2期,第125—128页。)两者相比较亦无明显的优劣之分,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继承 性出发,自应保留动产抵押而不移植动产让与担保。
最后,既然动产抵押和让与担保相雷同,因而动产抵押面临的问题让与担保也不能幸免,所以即使废除动产抵押移植让与担保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徒增制度变革的成本。因此,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如何完善动产抵押制度。对此,已有诸多重要学者的精辟论述,[17][18]也非本文的研究范围,于此不论。尚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既然我国不必移植动产让与担保,那么是否还有必要植入让与担保?纵览各国立法例,除日本承认不动产让与担保外,其他各国所谓的让与担保均指动产让与担保,并且日本的不动产让与担保可以说是被置之不用的,[4]可见,不动产让与担保并无太大的存在价值。由此观之,我国似无移植让与担保的必要。
四、结语
在进行法律移植时不仅应冷静地审视制度本身的价值和生命力,还应反思我国是否具备其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并权衡利弊得失,以免“水土不服”乃至形同虚设。物权制度本质上最具有固有法之色彩,各国物权法因为国家、民族、历史传统的差异而往往互不相同,在进行移植时更应小心求证。笔者在此并非想全盘否定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确立的价值和意义,只是想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为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提供一点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