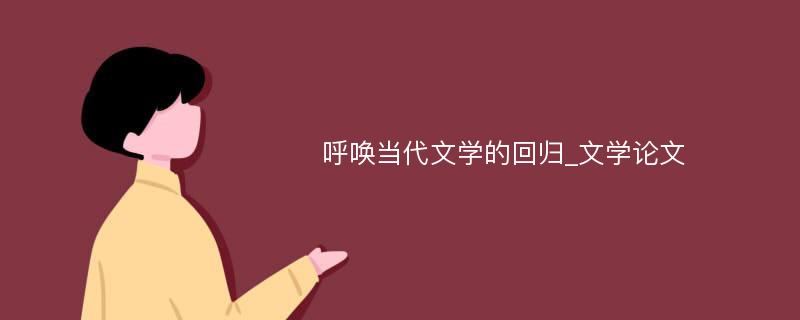
呼唤当代文学本真的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真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5-0204-03
一、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失真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大背景下产生的。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毁灭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让人类经历了梦魇般的岁月,世界秩序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进入20世纪下半叶,全球的发展出现奇迹,新技术革命、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各国,全球化、一体化更是势不可挡,世界秩序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诞生,国家体制和社会秩序发生根本变化,中华民族进入了全新的时代。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并开始了向现代化迈进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
20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巨大变动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一方面,物质的极大丰富让人们由来已久的夙愿和梦想变成了现实,譬如飞机的上天、卫星的巡天、人类登上其他星球、电的普及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改变等等,没有理由不让人们兴奋、亢奋甚至忘乎所以,于是乎人类俨然是世界甚或宇宙的上帝、主宰,世界的一切似乎都不在人类的话下,自然的、非自然的、物我皆要掌握在肱股之间,人类的自大达到了难以抑制的程度。另一方面,现实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物质的丰富让人们眼花缭乱,世界的变化让人们心神不定,原有的心理定势被打破,梦醒之后一片懵懂,甚至周围世界是否真实也难以界定,于是人们就很难走进理性世界。
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发生发展的。我们说文学是一个时代人类经历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背景造就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失真是不难理解的。
当然,我们说当代文学的失真是一种整体倾向、整体水平上的失真,不是指某一个体的失真。叩问已有50多年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却产生不了类似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世界上产生影响的作品,甚至不能取得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样的成就,除了本文不便言说的其他原因之外,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本真。
文学的失真首先是作家的失真。所谓作家,说到底就是专门从事文学营生的创作家。作家是一种职业,是一种从事精神生产的职业,创作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职业目的。文学作品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物质产品,完全听从于市场规律的摆布,但是,文学(包括其他艺术产品)毫无疑问也应该有自己的市场,有进入市场需要遵从的规则。对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完全可以进入市场听从于市场的选择,对于重要的有分量作品,如果市场选择机制失灵的话,国家可以采取购买等方式干预和调控,这样,文学自然会形成自己特有的市场秩序,作家的作品自然能够生成利润和价值。然而,新中国建立后,文学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党和国家纳入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之内,原本以文谋生的作家成为享有国家俸禄的公职人员,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重要作家,不少成了国家的官员,如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作家们有了职务和行政级别,当代文学的制度、体制、秩序完全建立起来。应该说,作家获得了应有的地位,有了稳定的收入,文学有了体制的保障,能更好地激发作家的自我能量和文学的创造力,更有利于文学的生产。但是,事情好像并没有按照应有的逻辑发展。文学和作家被制度收编之后似乎一下子找不到了自我。就作家而言,应有的身份是作家还是公职人员?创作是一种自在的行为还是一种完成职务的作为?在许多情况下,作家的这种身份和行为的确难以界定。
其次,作品内容的大面积失真。作家身份的改变意味着作家立场的改变。作家原本也是自由生产者,或者说是现代社会大生产的产业人员,生产的艰辛,市场的变幻,劳动的回报,在社会的精神领域和物质流通市场寻求生存空间,作家必然会有一种谋生者的压力和动力,当然更会有普通劳动者谋取生活资源过程中的全面感受,这种感受进入作品之后将难以出现半点虚假。而作家身份改变成为公职人员之后,立场必然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说作家们完全没有了普通劳动者的感受,但至少缺少了普通劳动者谋生的全真感受。缺少了普通劳动者的全真感受,就很难彻底地、设身处地地从普通劳动者的立场说话,或者说不可能完全进入普通劳动者的语境。尤其进入当前的环境,毋庸讳言的是许多当代作家已经贵族化,他们享受着国家的工薪衣食无忧,然后再操作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作品挣取额外收入。最重要的是作家身份的改变使他们的生活领域固定化。作家们形成了自己的生态链,从根本上丧失了进入社会丰富、复杂、多样生活的原始动力,对于社会的苦难、生存的艰辛、复杂纷繁的矛盾,他们很难生发出介入的勇气和斗志,即使介入进去,一旦利害关系显露,也可能会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患得患失,知难而退。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那么缺乏社会底层诸如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话语,那么缺乏无产阶级的深层表达。考察当下的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作品),充斥其中的大多是官场生活、高收入的准贵族个人图景、小资情调以及从历史中演绎出的宫廷斗争。毫无疑问,这不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真实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感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生活没有他们那么轻松,那么有滋有味,甚至不可能拥有他们那样的烦恼。无论是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由温饱向小康迈进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不乏苦难、不乏艰辛,甚至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更多要由广大民众承受,文学如果把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生活感受放在一边不予理睬,就很难让人们相信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感受。
再次,语言的失真。文学尤其是小说最早源于民间,源于大众。中国的小说最早称为话本,实际上就是说话、讲故事的脚本,也许可以理解为一种说话的方式或表达的方式。因此,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缺乏鲜活、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就难以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从语言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考察,最新鲜、最活泼、最有生命力的语言都在民间,在人民大众之中。文学作品的语言要富有感染力就必须从社会大众中吸收大量鲜活的语言,质言之,作家就必须沉到基层、沉到民间向广大民众学习说话、学习表达,真正掌握他们的思维,掌握他们的言语方式,掌握他们喜怒哀乐的表达途径。现实的情况是,当代大多数作家浮于上层,行走于都市,消遣于星级酒店、高级别墅、风景胜地,在作家文人圈应酬,在富人圈应酬,在官员圈应酬,哪里能够目睹到芸芸众生的世相,倾听到老百姓鸡毛蒜皮式的诉说,体味到基层民众的酸楚和艰辛。近墨则黑,近朱则赤,作家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作家的语言必然是圈子语言、富人语言、官场语言。这不能说不是当代文学界产生不了《红楼梦》、《水浒传》、鲁迅、茅盾、老舍、赵树理,甚至不能产生孙犁、沙汀的重要原因。不客气地说,当下的大多数文学作品筹措的语言不伦不类,更多的是知识分子语言,就如普通话,全国一个“腔调”,没有什么作品的个性特色;有些作家有点借用地方语言的意识,但由于缺乏对地方语言的深入研究和体味,往往是非驴非马。因此不但具体作家的作品缺乏自己的语言特色,而且作品中的人物也都一个腔调,没有个性特色。尤其是有些作家趋于追求和适应全球化、时尚化,刻意对语言进行包装,以讨取都市小资阶层的欢心,文学作品的语言几近成为世界语言。这些都不是老百姓表达思想、情感、述说生活的语言,更不是他们喜闻乐见的语言。语言是进入文学作品的路标和审美的基本元素符号,文学语言的贫乏和空洞是文学作品丧失审美价值和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二、呼唤当代文学本真的回归
中国当代文学的失真是一个客观事实,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中不可更改的历史。重要的是人们期待中国当代文学就像中国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一样,取得可以告慰民族、告慰历史、告慰未来、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当代文学就不能不从深层次发生改变。在笔者看来,真正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现状的改变,在于回归文学的本真。
第一,重构中国的文学体制。首要的是要矫正对文学的认识,不能把文学作为一个贵族阶层享用的专有物品供奉起来,不能用制度、用投入把它重重保护起来,要把文学真正作为一个产业,把作家作为有一定特殊性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让作家完全进入自由自在的创作环境和写作状态。以此为基本视点建立文学作品流通的市场,建立文学发展的内部和外部机制,让作家生产的产品主要由市场进行优劣选择,让更广大的基层民众参与进去,有发言权和评判权,而不是主要由官方和主流社会进行评判,进行选择。这里强调的建立文学的市场流通机制,并非要国家完全放任文学生产,而是要改变国家对文学的调控方式,通过政策法律管理、有选择有重点地投入、国家购买、奖励等手段,起到引导生产,引导流通和消费的作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建立这样的文学市场机制,作家的身份是否需要改变,是否依旧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享有国家俸禄值得认真研究。作家如果仍然作为国家公职人员,那么创作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是职务行为,就不能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因而就难以完全进入市场流通。
第二,文学进行自身清理。老实讲,文学一行杂芜丛生,其中非文学性的因素太多。这里我们并非要求清理文学门户,而是旨在清理文学界存在的非文学性的东西。毫无疑问,文学创作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事业,但这种崇高和神圣是由文学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是由文学本身的成就和作用塑造的,而不是凭空吹捧出来的,也不是靠那些非文学性的因素建立起来的。文学的生产当然也不完全是文学家的专利,任何人都应该有进行文学创作的权利,但任何人进行文学创作都应该尊重文学的本质属性,尊重文学承担的责任,遵循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如果说文学创作也存在功利性的话,那么这种功利性的体现就是生产了为人们和社会消费和享受的精神产品,以及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为创作者挣得的必要的生活资源,还有由此造就的文学家。因此,我们不否认文学的某些功利性要求存在,当然也不抹杀文学创作者对功利性的正当追求,我们强调的是,创作者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真正确立文学的崇高地位,完成文学承担的责任,达到文学的目的之后,实现自己的功利性追求。然而,当代文学界的现实情况与这种基本要求相距甚远,急功近利的风气弥漫整个文学界,雕虫小技、应景之作比比皆是。因此,整个社会都在发出文学没落了、文学衰败了的感叹,但深居业内的文学界却没有真正的深刻的自省,不少人仍然稳居于都市的显要地带,为了摇曳在眼前的名利炮制着平庸的应景的作品,还有些人为了维护文学界以及个人的既得利益在后面摇旗呐喊,热烈吹捧,以便制造不是文学现象的“文学现象”,为萧条的文学市场掀起些波澜。这种畸形的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当然仍然与现有的文学体制、与文学市场的畸形、与文学的评价机制不健全有关。因为文学的生产者属于国家公职人员,没有进入这个行列的人便在现有的文学制度下,创作出能够为现存的文学评价体系认可的作品,实现准入。进入到圈内的人基本上有了铁饭碗,至于能不能创作出有分量、有实绩、有市场的作品似乎无关紧要。于是,对于那些不能从自身的良心和灵魂深处自我产生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干脆在办公室、宾馆酒店、别墅雅室呆着,不可能下到社会底层关注民生,关注苦难,关注矛盾。因此,文学必须打倒社会贵族,必须清除世俗的功利性,必须让作家回到人民中来,回到社会底层来,从而让文学真正反映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关注民生,关注人性,关注自然,关注历史的足迹和民族的灵魂,有血,有泪,有哭,有笑,粗砺,质朴,进入人的灵魂能划出一道痕迹,一句话,让文学回到自己的本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