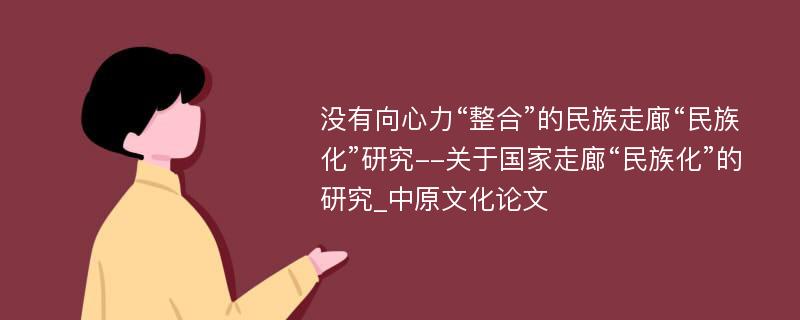
不被“整合”的向心力——民族走廊“国家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心力论文,不被论文,走廊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037-08
“民族走廊”学说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费孝通先生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宏大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都是关键。[1]围绕费先生的指导思想,我国民族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界迅速掀起了一场民族走廊的研究热潮,逐渐形成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等几大区域性的研究领地。继而,武陵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等新概念及论证亦开始进入公众视阈。综合十多年来民族走廊的研究成果,可发现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方面:民族走廊的地理、生态环境与交通研究;民族走廊的历史研究;民族间交往与融合研究;民族文化遗产与走廊经济开发研究;走廊民族政策与制度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特征研究,等等。在细部研究方面,民族走廊少数民族语言、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也受到一定的关注,试图解决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迁等方面的问题。
从研究模式上看,传统的研究多以族群为单位,以某个民族或村寨入手,缺乏区域研究的整体视角,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人员易受画地为牢的限制,无法相互启迪、形成研究合力。另一方面,人们对民族走廊的研究,往往沿着一种“预期”的模式:视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先验的、不言而喻的进程。譬如,人们通过关注民族走廊历史上的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认为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个地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2]
以“内地化”或“汉化”模式讨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边缘地区民族走廊的整合是否适当,值得商榷。本文希望沿着这一研究理路继续展开下去,相关的探讨包括:民族走廊如何与作为更高一层级的王朝国家产生关联,如何被王朝国家整合,其效果又如何?与之相对应,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群体为何长期游离于王朝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外,它们的政治向心力、国家认同感如何……在此基础上,找出民族走廊“成为中国”的进程与缘由,也即,中国建构在民族走廊的拼图,并重新检视已有民族走廊历史书写的“内地化”或“汉化”模式。当然,本文只是对上述问题一种粗浅的研究尝试,以期抛砖引玉,博学之士能将此类研究引向深入。
一、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结构
(一)“异域”的历史
民族走廊的历史其实就是与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在古代社会,交通阻隔、战争、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对民族走廊对外交往造成了重要限制,也直接影响到民族走廊历史的书写。由于文献缺载、简略或语焉不详,历史上走廊内的地方王国、部族群落发展缺乏清晰的脉络,很多族群的渊源充满悬疑。一些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蛮夷”及其建立的政权,史料记载莫衷一是,甚至出现名称混淆、史料篡乱的现象。以藏彝走廊为例,由于与汉族父系体系的巨大差异,汉文史籍记载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国,留给后人一系列悬疑:女国是否有东、西女国之分?东女国的具体位置何在?史料中几个女国风习类同又当如何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吕思勉[3]、任乃强[4]、王子今[5]、石硕[6]等多位专家学者相继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证。他们或驳斥,或补充,新的观点层出不断,然而,至今仍未能形成一种共识性的研究结论。历史上区域性的王国政权尚且如此,对于散杂群落历史的争议更是可想而知。三岩系蜚声藏族史学界的一个不大区域,历史上剽悍的民风及赵尔丰武力征讨使其“恶名”得到最大程度“彰显”。该部落位于川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历史上既不属藏,亦未附汉,直至清末改土归流前,仍是一个“化外野番”。从流传下来的遗风习俗看,三岩人明显不同于周边其他藏族群体,其族属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但研究结论同样充满了争议。①可见,厘清民族走廊的历史,注定要比其他空间区域复杂得多,亦困难得多。
某种程度上讲,民族走廊与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走廊内众多族群、部落自身无文字记载相传,它们的历史主要靠汉文记载和书写。因此,那些和中原王朝交往联系的部族、王国最有可能进入内地官修史志当中。相反,那些和外界联系较少的部族,则未能载入汉文历史中,它们或已“失去”历史,其兴衰败亡无从可知,早已湮没于历史的汪洋大海。可见,历史上中原王朝不同的经略方式,影响到民族走廊族群历史的“书写”。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民族走廊的经营策略大体归为两类。一是积极进取、锐意经略型,比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抚谕民众,招抚邛、笮、冉等部落,并置县,划归蜀郡统辖。另一类则对边远地区、民族采取消极策略,甚至置之不理。宋太祖玉斧划地图,以大渡河为界,“此外非吾所有”,以达到与大理国“和平相处”,致使北宋时期基本中断了与大渡河西南,乃至边疆地区政权或部族的交流,其实际疆域为我国历代王朝中最小的一个。因此,民族走廊中的王国、部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
当然,如果民族走廊的族群研究不倚重“客观标准”,族源问题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记载与留存的风俗去追溯、建构不同族群之间关系,把各少数民族当做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话,其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情境:当地民间传说、历史记忆、族群认同无疑也构成了民族走廊的历史拼图。在藏彝走廊彝族民间传说中,尊奉神农氏为鼻祖;武陵民族走廊苗族早期的记忆和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有关,保留着和黄帝部落争夺华夏的古老历史……民族走廊这类传说、记忆大都揭示了一个类似的历史“渊源”:多数族群的族源、祖先都一致性地指向了中原地区早期的炎黄部落。在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边远印象以及仿若荒诞的传说背后,存在某种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机理的扣连:民族走廊中的族群支系在华夏系谱中身处边缘,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沿用三皇五帝的传说故事定位,借此证实其久远的“历史”及华夏身份。
作为偏远的异域,民族走廊未能进入历史书写的主体,其“历史存在”可归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存在于汉文书写的历史当中,②主要指那些居住在走廊边缘,邻近汉文化的族群,或是那些历史上曾经与中原王朝交往、接触的族群,它们的历史出现在内地撰修的史志中——通常位于专门的“蛮夷传”之列。第二类无汉文历史记载,但其族群内部有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或口传故事,这类族群的存在延传着他们的历史或记忆。第三类为“消失”的族群,它们留给后世的历史仅仅是一些只言片语的传说或故事,而且这些传说、故事附着于第三方的“记忆”中。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戈基人即属此类,他们的故事为川西北羌族部落口口相传——在当地羌人的历史记忆中,其祖先曾经和一种叫做“戈基”的部落发生过战争。[7]三种类型的族群历史层次分明,犹如一个洋葱:表皮层系接近汉区的第一类族群;中间层相当于民族走廊中的第二类族群;最里面的一层则是那些隔绝于汉文化,“遗失”在历史中的第三类族群。
(二)走廊的结构
相对于走廊的历史而言,走廊的结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空间体系。民族走廊内部族际成分繁芜:有散杂的部落组织,有中原王朝的属国,也有独立的“王国”。以宋代的西南地区为例,藏彝走廊内外分立着宋和大理两个强大政权,为走廊内多样性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空间:有部分地区进一步官僚化,并发展成为地方王权;而有些则有若世外桃源,保持与既有国家或自立成国的距离。[8]
概括地讲,地处“蛮夷区”的民族走廊主要涵盖两类区域,羁縻区系主体,此外还有很多蛮夷游离于羁縻统治之外,与王朝之间甚至缺乏名义上的统属关系。[9]在羁縻区内,中原王朝的管辖大多是象征性的,并无实质性的统治。在藏彝走廊,表面上看它在西汉时期就纳入王朝秩序,但是汉朝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其实相当有限,走廊内大大小小的王国与部落林立,它们之间交错分布、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走廊深处地理位置偏僻,内地教化难以到达,彼此言语不通,形成隔阂。以至于在历史上,藏彝走廊一直未能建立“地域性的内部统一”。中原王朝对走廊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虽然历史上几个强大的中原政权,曾试图在走廊内设治,建立机构,进行治理。但其有效管辖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并不持久,常常伴随着王朝势力的盛衰而张弛,乃至失去控制。因此,历史上,民族走廊“国家化”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中原王朝无意或无力实施有效整合,将其纳入管辖范围之类。
从族群属性看,民族走廊似一个“非我族类”的聚合体。中原王朝对其治理、统治从未完全或彻底实现过,甚至对走廊的认识亦远未达到全面或准确的程度,从走廊内族群的名称、称谓足可窥见一斑。
民族走廊聚集着众多少数民族,历史上人们对其族类划分或认识粗略而模糊。“蛮”、“夷”、“戎”、“狄”等系中原地区统治民族对包括民族走廊在内周边族群的泛称。在汉文史籍中,先秦时期就有了族群区分的观念和称谓。[10]《竹书纪年》、《尚书》、《诗经》中即出现了“夷”、“西戎”、“蛮”、“狄”的记载。此类称谓表明,诸夏各国视蛮、夷异族为一个遥远的存在,而且在用语上明显有歧视之意。“戎,禽兽也”,[11]“狄,豺狼之德也”,[12]将戎、狄视为豺狼与禽兽,显然是对他们非华夏、非中原、非中心族别所贴的异类标签。稍后的史书中,对民族走廊、边疆地区蛮夷族群的笼统称谓加上了地理方位的词汇,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武陵蛮”等。《汉书》中陇西郡下还有秦时的狄道、氐道、羌道等针对夷狄的民族型政区设置。[13]从方向性分类到地理位置、民族型政区的族类划分,包含着中原王朝在行政建制与夷夏之分这两套体系下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分类。从羌到羌道、蛮到武陵蛮是王朝对民族走廊土著认知与分类的一个重大转变,与王朝增加和土著的接触,并在新的夷夏秩序中重新定位我者与他者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这些称谓也彰显统治者希图将蛮夷之族由遥远的“化外”之阈纳入“王化”的愿望。
西汉以后,我国史书开启了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专传的优良传统。《史记》开其端,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其后史书皆宗其例,整部二十四史除《陈书》、《北齐书》外,皆有少数民族专传,虽各书立传的范围不同,详略不同,划分的原则亦有异,但一些重要少数民族,尚大体能明其脉络。[14]《史记》较早对藏彝走廊进行了关注,开辟《西南夷列传》一栏,用一个“夷”字概称西南所有族群。而在“夷”的总框架内,记载了夜郎、靡莫、邛都、昆明、巂、筰都、徙、冉駹、白马等数十个族属的状况。
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古代从来没有壁垒森严的民族界限,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区分标准,都归结为一个“礼”字。[15]华夷秩序是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族群关系体系,所谓夷、戎、蛮、狄并非确指某一少数民族或族群,而是一个指代或泛称,一个“序”和“礼”的分类系统。诸夏、夷、狄、戎、蛮等概念的区分,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人们在文化生活、典章礼仪方面的差异而已。诸夏与夷狄是地域、血缘上的区别,更是文化生活、耕作方式、政治形态的区别,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意涵。具体言之,凡非中原大地、非农耕社会、非礼教教化,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该思想指导下,以夏变夷,将少数民族“内地化”或“汉化”便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圭臬。
礼仪的正统化是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礼仪、秩序视为王化、正统的标志,王朝国家正是一种用礼与法的语言来表达的秩序和规范。在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族属的评价,乃至排斥或歧视,与王朝所提倡的礼仪与制度密切相关。和行政体系“内”、“外”之别有内在联系的另一对概念,就是所谓“化内”与“化外”。“化”的本意是声教、教化,亦可引申为文化。因此,化内、化外之别显然是华夷之辨逻辑的延展,其含义更多是是否纳入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而言。[16]
通过对走廊历史与结构的梳理可知:当人们论及边缘地区的民族走廊时,基本都是在关注国家的整合与王权的建构与运作,其内在的脉络仍是作为中心区域的华夏、中原如何影响,乃至变周边的“蛮夷”为“我类”,视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先验的、不言而喻的进程。然而,事实未必尽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给出了一个“边缘”“不被国家化”的反面例证。在斯科特看来,生活在东南亚佐米亚(Zomia)崇山峻岭中的高山民族实际是国家政权高压统治的主动逃离者,他们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反文字倾向与族群建构的方式等,都是用以逃避国家的策略。③在国内,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结论与此可谓异曲同工,费先生认为:绝大多数不受融合的非汉民族只有走到汉族所不愿去居住的地方,大多是不宜耕种的草原和山区。有些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17]当然,此类问题换一种角度解读,或别有一番道理,即,封建王朝不一定怀有对边远地区实施统治的兴致。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无国家的山区地方”进入抑或逃离国家,而在于进入或逃离的动因、情境、机制及其运作进程。概而言之,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历史资料或历史事件的解读值得商榷。
二、“内地化”尝试:封建王朝的开发与经略
民族走廊的历史表明该区域为历代中原王朝所不熟悉、未完全纳入王化之地,民族走廊的结构显示走廊内曾经存在大大小小上百个王国、部落。虽说边缘族群可通过选择性策略,保留自身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以逃避中原政权“国家化”的影响。但毋庸置疑,拥有经济优势、地缘及地域优势的王朝帝国往往被证实有一种开拓疆域、王化四海、经略“蛮夷”的雄心。
早在战国时期,始皇嬴政就开启了拓展疆域,大规模征伐民族走廊“非我族类”的序幕。在南方,开凿灵渠,贯通南岭走廊,开发并设立南海郡、桂林郡,以及象郡,秦朝势力深入到岭南之地。西汉武帝沿袭了这一恢宏策略,开发西南夷,在藏彝走廊及周边区域设置郡县、开发经营。
汉代对藏彝走廊土著首领封以“王”、“侯”、“邑长”,是羁縻政策之雏形,但真正大规模的羁縻统治始于唐代。所谓羁縻制度就是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树其酋长,使自镇抚”的一种治理策略,它保留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的政治统治地位,羁縻机构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承担朝贡义务。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八百五十六个,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各民族地区的联系。[18]藏彝走廊所在的西南地区在初唐七八十年里,少数民族纷纷“内附”、“来降”,唐王朝对该地实施了积极的经略。[19]有唐一代,以羁縻府、州、县这样的民族型政区设置将边疆地区整合进王朝统治中,虽然其统治并不稳固,一些羁縻州府叛服无常,但是唐政府借助此类民族型政区进行社会政治整合的愿望显而易见。政治整合性管理行为强化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从而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互动。[20]
元代在汉唐羁縻政策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土司制度,广泛推行于西南、西北、中南民族走廊地区。明、清沿袭了这一制度,并促使其更加成熟和完善。土司制的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土司职官设置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以明代为例,它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再下一级还有千户、百户,等等。土司一经除授,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及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21]
如果说土司制是封建王朝受地理交通条件、自身经济军事实力所限,对民族走廊地区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其后进行的改土归流则是王朝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推进一统化、“国家化”政策的一个战略举措。改土归流表现为裁撤土官、土司,改派流官直接经营。它所体现的不仅是行政体系的变更,更是文化风习、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的革新,是中央王朝由间接治理向直接统治的全面过渡。
此外,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推行“国家化”、“一体化”进程中,为加强对边疆民族走廊地区的统治,还设有专职机构或人员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如,秦置典客和典属国,汉设大鸿胪和客曹尚书,隋唐的鸿胪寺卿及礼部之主客司,元朝的宣政院,以及清代为统治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而设置的理藩院。这些制度或政策的实施,对保持边疆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也极易受到王朝更迭、政局变动的冲击与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从羁縻统治到土司制度,再经历改土归流,封建王朝对民族走廊的经略、治理逐步强化。然而,王朝统治者处心积虑开疆拓土,推行“国家化”举措的同时,一种来自走廊内部逃避管理、反控制、反征服的张力亦在增强。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在推行过程中反反复复、时断时续即是一个例证。此外,历史上民族走廊地区,更有许多未被羁縻、管辖的部落、游民,它们也系封建王朝“国家化”策略的“盲点”。
综上,中原王朝统治者锐意进取,积极开发、经略民族走廊地区,对实现王朝统一化进程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统治者推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认为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华夏的“中国”。很显然,这类“国家化”模式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边缘地区进入国家是一种复杂的、缓慢的进程,中国是一个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个地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此外,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族群关系除具有“合”的倾向性外,还存在“分”的趋势——在民族关系中,由外在的生活处境造就一种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经历一种文化的过程而不断得到自我强化,形成一种族群间相互分离的向度。[22]正是这种“分”的向度构成了我国民族文化中异质化特征。
有学者把先秦时期中原周边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分为三种类型或模式——殖民模式、土著自动模式和浅层控制模式,这三种模式涉及的地区在国家化程度上是有差别的。[23]该结论亦证实,历史上中原王朝或中原国家素有控制、经略周边区域的雄心和意愿。然而,从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考察,这类雄心却往往难以遂愿。一方面由于走廊过于复杂,地理、气候、民情风俗足以让“征服者”望而却步;“羁縻”意味着边远族类在承认天子统辖权的前提下,保持着自身传统与较大的独立性,对王朝而言,这是一种控驭而非实际控制;[24]受册封土司的离心倾向也明显存在,虽说土司对封建王朝的政治向心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容否认,其社会文化基础—“宗族”和“庙宇”即暗含着对抗“国家”的因素。[25]加之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实力消长不定,缺乏经略民族走廊的长远规划,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王朝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别、以夏变夷思想使其开发策略自身存在先天不足。
三、“蛮地”的向心力:文化异质与文明“东向”
民族走廊作为民族交往的动脉和族际交流的主要通道,对生活在其中的历史民族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又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为迁徙、流动的交通要道,又可为退避、封锁的庇护地,以求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的自我保存。[26]因此,走廊板块与中原王朝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既接触交往,又有退避、保全自己的倾向。走廊族群内部关系复杂,其文化和社会组织变迁呈多样化向度,相互间的互动更是千姿百态,因此,“内地化”理论失之松懈。[27]“内地化”与“汉化”思维脉络不足以解释我国当前的民族格局,但过于强调历史上走廊内族群对中原王朝“反控制”、“反征服”,以及实施“不被统治的艺术”也非历史原委。作为“蛮夷”之地的民族走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并未导致民族间的离散与分裂,他们对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强烈的内聚力和认同感。
民族走廊不同于内地区域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其内部多元上。在藏彝走廊及其周边区域,从空间上看有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区四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从民族来源看主要有:汉藏语系的汉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民族,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的低、布朗、德昂等民族,这些民族的种类占中华56个民族一半以上。[28]特殊的空间地理环境与多元化的种族来源,造成了走廊内异质程度较高的民族文化图景。走廊地区的地貌通常表现为山川河谷的形式。山区的特点是落后闭塞、交通不便,使来自中原地区文明不同的各民族得以保留下来。在藏彝走廊内部,自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有利于物质文化的保存,许多被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称作古代文化的“活化石”。[29]同时,走廊中多条南北峡谷通道,自古以来即为西北、西南诸多民族迁徙、交流的要道,形成走廊两侧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迥异的自然生态基础。正因为有保存的条件,才能使民族走廊积淀民族文化,成为历史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沉积地带。各地形成了许多有趣的文化奇观: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甚至同一支系的人群内部所讲的语言也存在方言和土语的差异,[30]以及各地独特的“语言孤岛”现象。分布于边疆地区的民族走廊既是我国古代社会民族迁徙、交往的大舞台,同时也是一个保留了各自文化特质的民俗博物馆。
李亦园先生曾指出:“在中原区域中居住的中国民族文化基调中一直有一种容纳、吸收居住于边缘民族的‘主旋律’在发生作用。因此几千年来,整个中国境内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都是在这一‘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之中而作旋转。”[31]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在历史上并不是以血统、种族的形态去吸收或统合别族的,而是以发挥“文化”或“文明”影响的方式来起到这个核心和凝聚作用的。李先生所强调的中原民族与边缘民族“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不仅指历史上“夷人”接受汉文化、华夷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是指边缘族群对中原华夏文明的一种认同、仰慕与主动学习的心理。在中华民族从分散到一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凝聚作用的不是汉族族体,而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在当时国内各民族眼中属于先进水平的,且为大家所景仰的“汉文明”。[32]石硕教授在《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一书中提出:西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没有成为印度或是其他某个邻国的一部分,也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国家,而恰恰最终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西藏文明自吐蕃时代以来在地域空间上大体采取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轨迹,不断呈现向中原倾斜与靠拢的趋势,并最终被纳入中原文明体系之中。[33]此结论用在解释民族走廊中的文化现象,亦不无道理。走廊内部文化异质性强,积淀深厚,族群部落间不相统属,但他们对中原文明的仰慕、学习心理却异常强烈,甚至不远万里,长途跋涉表达慕义之情。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居住在藏彝走廊中部白玉、巴塘一带的白狼部落不远万里,到洛阳觐见,并在汉庭演唱颂歌三首:《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表达了偏安走廊一隅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慕义归化之情。
民族走廊的少数民族心系华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体现在“蛮夷”与中原族裔共祖同源情结上。藏彝走廊中的彝、白、拉祜等均认为自己先民从河湟地区迁入云南,与西北民族同源。所以,从种族、文化源流看,这类民族是适应固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结合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的。[34]民族走廊少数民族同根共祖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同胞兄弟观念包含在众多民族的创世史诗当中,是一种起源久远、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据笔者调查,在藏彝走廊东端的四川省石棉县蟹螺藏族乡,当地藏族群众认为火塘中三个锅庄分别代表着藏族大哥、汉族二哥,以及彝族三弟。藏、汉、彝分别为当地三大世居族群,它们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在云南,彝族创世史诗《查姐》中写道:“阿朴独姆兄妹成亲后,生下了三十六个小娃娃”,“从此各人为一族,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④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图》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洪水过后,只剩下从忍利恩,他与天神的女儿衬红褒白成婚,并生下三个儿子,“一母生出三种人,三弟兄说三种话,三个民族同祖先。”⑤《史记》华夷诸族共为“炎黄子孙”的记述,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离及其走向融合的依据与前提。民族走廊自然历史、文化心理的特点,反映在民族意识中,成为许多民族同源异流的观念,铸就了中华各民族源于炎黄、都是炎黄子孙的观念。⑥这类传说起源久远,在走廊内各民族中广为传扬,体现了民族精神深层中存在的、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各民族的相互认同,对于多元一体民族结构的建立起着促进和指引作用。因此,可以讲,中华民族的一体既表现为文化上的一体,也是基于想象的“种族”、“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于是,炎黄五帝就自然成为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共有始祖。
民族走廊与中原地区在制度化的交往中,亦增强了其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和内向力。历史上风行于西南、西北两地的茶马贸易,是沟通内地与边疆民族走廊重要的物物交换形式。“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古代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茶易马的商贸形式。宋明王朝还专门设立了管理茶马交易的官职,并一度将茶马交易作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35]因此,可以讲,茶马贸易既是中原王朝对民族走廊地区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的输出,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的基本国策。此外,朝贡体系、征调赋役等也是地方社会与封建王朝沟通、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朝贡表明一种通行的宗属关系,是中央对四方的一种统治、怀柔政策。我国历史上的朝贡关系是地处走廊深处的族群走出走廊、打破封闭,加强与中央王朝互动往来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土司时期,贡赋数量不多,却具有重要意义:朝贡象征着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36]
四、封而不闭:远播华夏文明的“国际”走廊
对外国际关系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表现在政治意义上是“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认同,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散亦是一系列重要的方面。[37]民族走廊一端连接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另一端连接着华夏广袤疆域之外的异邦诸国,沟通着同样灿烂辉煌的异域文明。民族走廊是一个历史通道,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空间体系,从秦汉起就是联通中原与边疆、中国与世界的国际通道。
在我国古代,南北东西文化以至于族群的交流互动,主要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在西南,藏彝走廊是一条重要的东西方国际走廊,它在沟通南北丝绸之路,推动中外文化互动、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38]藏彝走廊的四个方向都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其南北两端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是北方丝绸之路,其南方出口则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由横断山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半岛,并从横断山脉南端西经南亚印巴次大陆伸展到中亚、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这条丝绸之路形成于2000多年前,是西南各族系往返迁徙的重要通衢,古蜀文化对西南民族的整合,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同时它也是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早期联系的纽带。
西北走廊是我国古代沟通中亚、西亚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北方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地理路线上,它大体与西北民族走廊相当。在西汉,形成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中西交流的商品主要有金器、银器、镜子、稀有动物和皮货、植物、药材、香料、珠宝首饰等。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带动了区域社会的进步。罗马与汉朝两大文明相互吸引,造成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商路沿途,邦国林立,更有中介波斯,乘势而起。[39]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在我国南方,以南岭走廊为“底层”,存在一条跨越大洋,连接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起点为福建泉州。从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性来说,海上丝绸之路较陆上丝绸之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元时期,仅福建泉州港就与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着海外贸易。[40]以贺州为核心的桂、粤、湘连接带,历史上曾是中原与西南、岭南以及海外交通的走廊,秦代即已开辟,它北接潇水,出洞庭湖,南接番禺下南海,族群、货物、文化交流频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迄今仍留有大量古迹。[41]借助于岭南走廊的地理交通优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交织在一起,以中国为核心组成一个海上贸易网。[42]
结语:从边缘—国家到多元—一体
民族走廊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边缘—国家关系,蕴含着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多元”,表现为民族的多元,它不仅是民族来源的多元,更是文化、风俗、经济等多方面表现的多元,其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多元。[43]民族走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其运作,它们有着不易改变的风习,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体中多元化特征。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以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边缘地区进入国家实际表现为一种全方位、复杂的历史进程。在“内地化”或“汉化”模式下,通过经历一系列制度或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并非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中国”的一部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多元’与‘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紧张,正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点,简而言之,是中国社会既在客观上保持一定程度的文化多样性,又在主观上具有强大的国家认同的凝聚力。”[44]
民族走廊曾是一块块“化外”之地,有独立的王国和部落。其语言、习俗和中原地区差异甚大。强盛的中原王朝,尤其是汉唐之际,帝王将相雄才伟略,怀有开发与经略边疆“四夷”的谋略与雄心,于是就有了羁縻政策、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等一系列的制度与事件,有了客曹尚书、鸿胪寺卿及理藩院等相应的职官与机构,也有了臣服与纳贡的归属感与向心力。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相渗透,部分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特征。但是,这种政治整合仅发生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它也未能覆盖整个民族走廊,因为仍有一部分部落未与中原王朝发生接触,他们或是中原王朝无力或无意征服的一类,或是怀有“不被统治的艺术”,能够逃避控制,保持自己的族群属性,游离于中原王朝统治范围之外。
传统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整合性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地区组织与国家制度、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成为相互交织渗透的一体两面。[45]历史上的政治整合远未达到完全、彻底的程度——当代中国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但民族走廊内部族群之间、区域之间文化异质并不妨碍其心系中原的向心力、对华夏文明的认同感。中原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边远民族跨越万水千山阻隔表达慕义归化之情,学习与效仿中原文明;在对外关系中,民族走廊的“国际走廊”属性特征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少数民族意识中民族同源异流的观念,以及创世史诗中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的意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动力,使得民族走廊在历史发展中,保持着强大的向心力,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
收稿日期:2013-01-12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范河川:《山岩戈巴父系社会简介》,《西藏研究》,1999(1);许韶明:《三岩帕措族源考》,《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廖建新:《三岩“帕措”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4);岳小国:《三岩藏人族源探研》,《长江论坛》,2012(4)。
②这类族群中,一部分也有自己的文字,因而有本民族的文献资料流传下来。
③James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④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红河调查队搜集,施学生口译,李文、李志远记录,郭思九、陶学良整理:《查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74-75页。
⑤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创世纪(纳西族民间史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95页。
⑥在我国56个民族中,多数民族保留着炎黄始祖的历史记忆,但在部分少数民族中也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