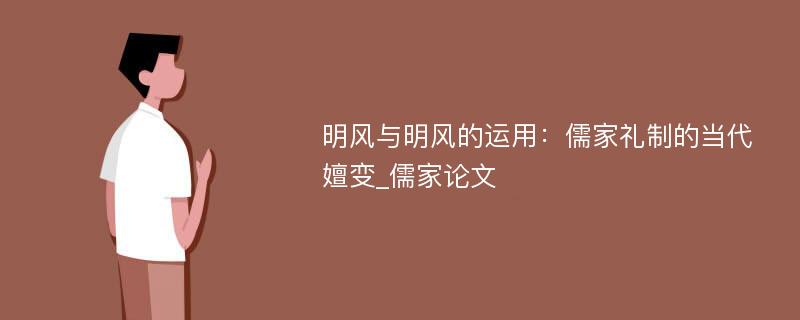
明体达用: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当代论文,明体达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儒家礼学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礼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备受推崇,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却饱受批评,在当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思潮中也黯然退避。那么,儒家礼学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它能否在经过转换后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一份资源?这是儒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儒家礼学的“体”与“用”
中国传统的礼涉及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礼教、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多种提法,但从存在形态上看,主要可分为行为、制度、观念三大层面,而儒家礼学就是对这种种礼的现实存在的理论表述和建构。
一般的观点是把儒家礼学看作“体”,而把依据儒家礼学制定的礼乐制度看作“用”,这种意义上的体用是一种理、事关系。但本文对于儒家礼学的体用还有一层特殊的理解,这就是体、用都是就儒家礼学内部而言的。礼义是一种与现实的礼仪等相对的道理,这个关于礼的道理可以分为事中之理和超越的天理。超越的天理是礼之体,而现实生活中的君臣、父子、夫妇、人物、华夷等具体的伦理关系、社会规范是礼之用。这种意义上的体用是一种普遍之理与特殊之理的关系;然而这个意义上的普遍并非经验层面上的抽象概括,而是超越的源头。上述两种体用关系的分析判别,揭示出儒家礼学所蕴涵的超越性与现实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两种不同的维度,构成了讨论儒家礼学内涵及其永恒性价值的关键。
遵循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存在论模式,儒家礼学的超越的礼之体就体现在现实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群、群与群的关系之中,这种体现兼含上述两种体用关系:(1)超越的天理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关系、社会规范之中,这是普遍之理体现在特殊之理中;(2)超越的天理体现在现实的人与人等关系之中,这是普遍之理体现在具体之事中。那么,儒家礼学的超越的礼之体的内涵是什么呢?本文的看法是,差异性是儒家礼学的本体,荀子就明确提出“礼别异”(《荀子·乐论》)。差异性本身构成礼之体,而人与人等之间的关系则构成各种不同的差异,两者是一种体用关系;各种差异要随时变易,但差异性本身却具有永恒性。传统儒学对礼之用的变易性与礼之体的不变性也有认识,只是它所理解的差异性仍然不自觉地停留在亲亲、尊尊等具体的差异上,缺乏纯粹的抽象表达。
作为儒家礼学基本精神的差异性究竟是何种程度上的差异?这在不同的礼中表现不同,在儒学发展史上各家各派的论述也不尽一致,但都维持在差异关系的范围之内。在儒家礼学看来,现实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群、群与群之间都是差异一体关系;这种差异关系介于绝对的同与不同、等与不等之间,它既不会走向完全的同等,也不会走向隔绝不通。并且,儒家倡导差异性的目的并不是要制造对立,而是要以差异性为依据制订出合理的礼仪、礼制、礼法、礼俗等,以保障诸存在者之间的和谐共存,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作为礼之体的差异性具有超越性,而作为礼之用的具体礼义、礼仪却需要随时变革,因此,“明体达用”就成为儒家礼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先秦时期,孔、孟、荀等大儒有感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着力彰显儒家礼学的差异精神,损益旧礼以制定新礼,成为汉唐时期作为治国根本的礼教、名教的直接源头;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有感于汉唐儒家礼教、名教的僵化与佛、道二教的冲击,重新彰显儒家礼学的差异精神,对后期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巨大。实践证明,儒家礼学具有维系社会正常发展的功能,其中蕴涵了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原则。
二、对近现代儒家礼学现实困境的反思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大转型中,儒家礼学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和困境,其原因在于传统礼教的僵化,使它成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内在发展,也无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因而把儒家礼学与封建礼教合为一体加以批判,是近现代以来批判思潮的基本理路。
早期从洋务派开始,如郑观应等人就认为中国不如西方不仅体现在军事、科技、经济上,同时更体现在伦理道德方面;认为西方伦理重视自由平等,而中国传统伦理重视等级服从。维新派对于儒家礼教的批判更为广泛深刻,其中以谭嗣同最为激烈。谭嗣同饱受旧式家庭虐待,个人的切身感受使他对儒家礼教压抑个人的一面极为反感,强烈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进入20世纪,西化派与马克思主义派都激烈批判了儒家礼教,如陈独秀指出:“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鲁迅、巴金等文学家对旧式大家庭的人伦关系黑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也在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近现代以来对儒家礼学、礼教的批判具有历史合理性,它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但今天看来,我们对儒家礼学所蕴含的丰富内涵需要给予新的关注,应该把它与封建礼教区别对待。儒家礼学有体有用:礼之用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表现为三纲、嘉、吉、军、兵、凶、冠、婚、丧、祭等,这些礼之用是具体的,体现了浓厚的封建宗法等级意识,必须加以批判,但礼之体所蕴涵的普遍的差异秩序本身,却具有永恒价值。具体的礼义、礼仪固然是礼体的呈现,但二者之间并非同一关系。这里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实质内容而言,近现代以来对儒家礼学的批判既涉及对作为儒家礼学本体的差异性的忽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回应西方近现代以来平等原则的挑战。
本文认为,儒家礼学的差异性与平等精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首先,差异与平等都是伦理、社会、政治规范的永恒原则,无所谓新旧好坏。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肯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群、群与群之间在先天、后天上的差异,尤其注重肯定人与人之间在感情、才智、能力、德行等方面的差异。这一原则来自于对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实际的概括,是一个现实性原则;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平等观念则是一个理想性原则,它奠基于自然人性论之上,把个体的人假设为抽象的平等、独立的原子;“自然人性是人类平等的唯一立脚点……讲平等除了自然人性之外,不依赖任何其他的条件,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是同一依据”(韦政通,第263页)。其次,从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出发,我们还可以对平等这一概念作出简单性与复杂性两个维度的解读。简单性平等意味着摈弃种种现实性因素和历史传统,从抽象的角度出发肯定关系主体之间的等同,而复杂性平等则以尊重关系主体各自本来的差异为基础,寻求一种包容差异的平等公正。儒家礼学追求的是一种包容差异的平等,所谓“维齐非齐”、“和而不同”,就是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公正、和谐。
三、近现代儒学“礼”、“仁”关系论检讨
近现代以来对儒家礼学的批判之所以倾向于基本否定,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分体、用,把礼学简单看作等级制度的代名词;二是对差异性的普遍价值认识不足,不理解公平、正义的复杂性、历史性。然而面对这种批判,近现代的儒学研究并没有作出积极回应,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礼、仁关系论中。
在近现代的儒学研究中,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全盘否定儒家学说,试图重新阐发儒学中的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内涵。他们在礼、仁关系上大多主张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即把仁看作是超越的、抽象的、普遍的道德意识,而把礼看作是仁的外在表现,是现实的、具体的、特殊的伦理关系。所以得出的结论是,礼是特殊的,“三纲”已过时,而仁是普遍的,“五常”具有永恒性。如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50、60年代提倡“抽象继承法”,他在论述孔子的仁与礼时,重点论述仁的抽象继承性,而把礼看作是封建性的糟粕。(参见冯友兰,第306页)
另有一派学者则坚持从儒家学说自身出发寻求其现代发展,这就是现代新儒家。但在礼、仁关系论上,现代新儒家同样是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其代表观点是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内圣开出新外王”说。牟宗三先生肯定儒学超越的仁、心性的永恒价值,同时又认为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走不通,需要有一个道德良知的自我坎陷,他说:“中国文化是理性之运用表现,非理性之架构表现。然中国要在现世界站得住立得起,必须由内圣开外王处有一转折,绕一个弯,使能显出架构表现,以开出科学与民主,完成新外王的事业。”(牟宗三,第97页)牟宗三先生的道德良知曲折之后所对接的不是传统儒家的外王之道,而是西方的民主、科学,是以仁为体,以民主、科学为用,礼在儒学中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
冯友兰、牟宗三的礼、仁关系论在当代的儒学研究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基本诠释模式,它们侧重肯定儒家仁学的超越性、普遍性,而对礼学所具有的超越性、普遍性相对来说重视不够。从理论逻辑上分析,儒学的礼与仁二者共同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实践,由此扩大到人与群、群与群、人与自然等现实关系。人伦道德实践是儒学最根本的源头,由此产生两个超越维度:一个是人伦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超越,即由现实的道德情感上升到超越的道德意识,这是仁的维度,其中超越的道德意识是仁之体,而现实的道德情感是仁之用;另一个是人伦道德实践的主体间性的超越,即由具体的伦理关系上升到抽象的差异秩序,这是礼的维度,其中抽象的差异秩序是礼之体,而具体的伦理关系是礼之用。礼与仁都有体与用、抽象与具体之两面;二者固然紧密相关,但礼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仁的外化,它同时也与现实功利、宗教传统、政治权力、社会习俗等相关联。儒学的礼与仁实际是一个互为体用、多向发展的关系。
四、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
人伦道德实践是儒家礼学的根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深化,儒家礼学及其相应的礼制、礼法、礼仪、礼俗等必然要因时损益,但其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秩序、和谐理念却具有普遍性,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既有利于儒学的发展,又有利于促进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探讨。首先,以差异性为根本原则的儒家礼学构成整个儒学的核心内容,是儒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方面,也是儒学走向社会生活层面的有效途径。其次,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源自宇宙、人生、社会之实际,与平等原则一样都是建立新人伦、新礼制的基本支撑点。社会公正不应当是简单的平等,而应当是包容差异的平等。从儒家礼学传统中发掘其公平、正义的内在蕴涵,积极与西方思想对话,参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答,是实现儒家礼学理论拓展的重要契机和途径。
从现实意义上讲,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需要经过合理转换的儒家礼学。针对现代社会伦理关系混乱、道德水平滑坡等现象,从维护政治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出发,提倡明礼诚信成为时代要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明什么样的礼的问题。如果始终停留在“谢谢”、“您好”等口号上,则现代社会的新礼建设就很难深入。在本文看来,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有助于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群、群与群之间建立合理的秩序,实现礼所应有的规范社会人生的作用。
本文肯定儒家礼学在当代社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不表明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是抽象不变的永恒真理,更不意味着以之为指导思想的儒家礼仪都是合理的。对于儒家礼学,我们需要下一番明体达用的工夫,转换其理论内涵与运用途径,使之真正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扎下根来。首先,从理论形态上讲,传统儒学往往将礼学差异性原则本体化,上升为永恒的天理,本文则主张所谓的天理不过是对千差万别的现实差异关系的概括;它来自于人类社会生活实际,也要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中不断更新其理论形态。其次,从概念内涵上讲,儒家礼学的差异性原则本应包含平等、等级两端,但在传统礼教中,大多是向等级性一端靠拢,而远离平等性一端,这种偏颇理应得到纠正。今天我们应当以平等观念补充、修正儒家礼学,抛弃等级性,改差异、等级互动为差异、平等互动。再次,从差异性自身的依据上讲,传统礼学主要依据亲亲、尊尊、年龄、性别等因素,而我们则应该根据今天的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扬弃,补充知识、能力等因素,提倡一种多元互动的合理差异性。第四,从应用范围上讲,传统礼学的差异性原则往往是“天人合一”式的,而我们今天则应该实行领域分离原则,在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方面建立以差异性为基础的合理新礼,而在公共权力、基本人权领域追求普遍平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中与西、古与今之礼相混杂的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这给儒家礼学的当代转换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儒家礼学主张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天、地、人、物之间的和谐共存,这样一种学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为现代社会生活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