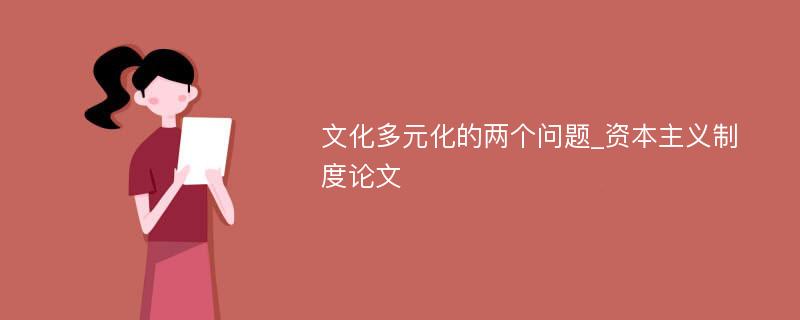
文化多元主义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在经济发达国家是一个热门的议题。不仅自由主义者忙于修补自己逻辑上的漏洞,提出更宽容的社会基本框架的理解来接纳各方的挑战;文化多元主义者也摆出咄咄逼人的攻势,致力于拆毁自由主义理论的墙脚,创出各种话语论证文化多元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性。(注:这里使用自由主义一词,意指一个立场相对宽泛的概念。举凡经济、法律、政治、哲学方面,注重阐释基本秩序及其原理的学说,均可以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而活跃于各个领域的当代“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 )可以归入文化多元主义的范畴。如若留心西方当代思想的发展,很容易看出这两者的分歧和争议。例如,约翰·罗尔斯的《万民法》明显是面对东欧阵营解体、民族主义崛起等新的世界格局而重构一个可以“共存”的世界秩序;而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则给予民族—国家内部的种族文化冲突宽泛的理解以维持既存的局面。而各种“批评理论”致力于指出既存秩序的不合理性和一厢情愿的空想。参阅汪晖、陈燕谷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edited by JulieRivkin and Michael Ryan.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后著将各种批评理论分门别类,节选重要的论著和文章,并附上简短的导论,是了解西方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读物。)理论的争议其实和事实背景深切相关,它指向经济发达国家文化政治生活屡起波澜的社会运动:反种族歧视、反文化殖民、女权主义、同性恋等。正是这些20世纪才全面崛起的社会运动创造了文化多元话语。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文化多元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前瞻性的话题,不仅没有一个自由主义式的基本秩序容纳上述社会运动的正常生长,文化多元主义的隐若现身也找不到它的自由主义老对手。这说明今天的中国基本不在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论争的语境中。但是,当下不在此种语境不等于问题不会在将来浮现,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更深程度地卷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我们或迟或早也要面临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的话语冲突,社会的文化政治生活也要面对可以被概括为文化多元主义的那种社会运动的困扰。就象这些问题在经济发达国家没有一致的答案一样,将来在中国也不会有包治百病的药方。学术的讨论比起饱受困扰的社会生活本身能提供的只是有限的理解。
一
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似乎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它创造了生活中空前的无差异倾向,无休无止的交易和消费形成了均一化的强大压力,人们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得尽量适应这架“疯狂运转”的机器创下的游戏规则,否则就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它又极大扩展了人们精神和生活的空间,使得人们有可能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生活,那么因血缘、种族、文化而有所不同的历史遗产有可能得到新的发展契机,因而资本主义又鼓励了生活的差异化倾向。我有理由相信文化多元问题的出现正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这种相互矛盾的社会现实。它不仅是差异化倾向的产物,这点或许容易理解;它更是无差异倾向的产物,无差异倾向的强大压力招致猛烈的反抗造就了文化多元的社会运动。正因为如此,那些极端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调视自由主义如敌人,它们痛恨那些“死去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n)。但客观地看问题,它们更象相互依赖的天敌。在民主法治的秩序下,文化多元所追求的各种集体权利才有充分落实的可能性;而各种形式的文化多元的社会运动使自由主义追求的民主法治秩序发展出更充实的内容。
早朝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曾经残酷摧残落后民族及其文化,可是脱离殖民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又为本身文化多元发展创出广阔的空间。举凡科技的高速发展、信息交流的频繁、贸易量的空前增长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等因素,在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增长的同时,至少在民族—国家的内部摧毁了因血缘、种族、文化造成的人为交流限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而从前视为不可逾越的交流屏障,在现代社会面前被大大地突破了。扩展了的生活空间意味着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信仰、趣味、爱好甚至性别倾向来定义什么是好的生活并将之付诸实施。好的生活不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现成答案,例如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部落住民对好的生活的答案除了他的传统赋予的答案之外还有什么;反过来,我们同样不能想象替一个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指定一种他必须过的好的生活除了招致反抗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好的生活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流动的定义,一个具有多项选择性的定义,根据趣味爱好的转移而有不同的答案。政府保证基本秩序和负责宏观经济增长而人民自己寻找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答案。社会发达程度是和好的生活的多样选择性成正比的,发达程度越高,多样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
促成人们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众多分歧答案源自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因素居多,例如一个信奉穆斯林的人和一个遵从儒家教诲的人关于好的生活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同,但他们不同的见解都是世代相传的结果。答案的分歧还源自趣味、爱好、习惯等个人性因素,例如同性恋者与非同性恋者的分歧肯定是产生于性别倾向这种纯粹个人因素。不过,不论什么因素造成人们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分歧见解,重要的是市场社会的发展才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的基础。正是在市场社会的环境里,人们才可能将潜在的关于好的生活的分歧发展为当下存在的真实生活。脱离了这个基础,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分歧见解都不可能转变成真实的生活,人们如果不是生活在韦伯所说的传统社会,就是生活在被指定的“好的生活”的社会。关于好的生活的定义尽管分歧,但它们之间决不至于兵戎相见。绝不如历史上不同民族争夺生存空间而形成的那种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分歧是存在于统一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基本秩序是这些分歧的底线。因此,它们是相互依赖前提下发展出来的分歧,而不是各自孤立状态下衍生的分歧。
社会发展提供了人们选择各自心目中好的生活的基础,于是各种传统的因素和非传统的因素都可能被发掘出来而成为答案之一。文化多元主义及其社会运动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那些人们熟知的因素,如种族、语言文化等自然成为反歧视斗争的有力旗号;压制已久的性别问题也爆发出来使女权主义成为望而生畏的力量;连以往隐存于社会阴影下的同性恋也终于浮出水面,对同志们来说,这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好的生活,诸如此类。可以想见,在今后的社会演变里,还不知道有什么趣味、爱好和习惯会被发展成为一种好的生活的答案,引起同道者奋起要求集体权利的斗争。因为好的生活的定义随着社会的转变而转变,当经过斗争赢得集体权利,它就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真实生活,而不再作为文化多元问题突现于社会面前。但是,目前不为人关注的趣味、爱好和习惯会自然生长,有一天当它强大到觉得自己被歧视了,就会转变成新的要求集体权利的旗帜。没有办法预见,下一个文化多元问题的凸现,是以什么样的文化因素作为形成想象共同体的号召。人们或许以为,文化多元问题引起的集体权利斗争,经过长久的文化融合,说不定终将出现一个大同的局面。这种一厢情愿的乐观主义其实是不了解文化多元问题在现代社会的真实成因。基于历史和传统因素而形成的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歧见或许在遥远的将来烟消云散,但基于趣味、爱好和习惯而形成的歧见与人类同在。每一新时代兴起的文化想象的具体内容可能不同,但却不会消失归于无有。反抗歧视,要求某种形式的集体权利的斗争,一定会长久困扰市场社会。(注: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容忍不同价值观和趣味的存在,由此造成文化上固有的矛盾和困扰。该著虽非讨论文化多元主义问题,但可以作为理解资本主义文化困扰的参考。)
文化多元问题除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创造的表现文化差异的巨大空间密切相关之外,还与它本身内在的无差异倾向相关。全球经济一体化充分表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市场自身的扩张性。所向披靡的市场扩张通过殖民、贸易、资本输出、人口迁移在过去数个世纪迅速将自己普及于全世界,并且一点一点蚕食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地盘。马克思曾经用“没有良心的自由贸易”形容市场令人可怕的扩张。(注:《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 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全球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不同程度卷入一体化的经济互动,日渐加深的全球一体化经济互动自然瓦解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社会,迫使它们新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社会纳入一体化的经济互动进程,而文化亦由此起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所造就的无差异普遍主义倾向,就其实质内容而言,决不是文化价值的无差异,而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互动。站在市场扩张的立场,如果要用一个词适当形容当今全球一体化经济互动背景下的文化,则未尝不可以说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当然,所谓“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只有在表示市场价值观普遍化的意思时才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用全球一体化经济互动或市场扩张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延续的经济史事实的时候就会发现,市场扩张运动使得原本不是处在这个主流漩涡的社群在不断被卷入主流漩涡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歧视压力,从而招致反抗。并非身处市场扩张运动的主流漩涡的社群所以被卷入其中,这正是市场扩张的结果;市场扩张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人们的生活上,将自外于这个漩涡的一切逐渐卷入它自身之中。而某些社群所以感受到强大的歧视压力,是因为它们原本并非身处市场扩张运动之中。一方面是不断被卷入市场扩张漩涡当中,另一方面是感受初来乍到的歧视压力。这就是今日身处市场扩张运动背景下的非主流社群的真正处境,也是文化多元主义运动的真实处境。我相信,文化多元主义运动是市场扩张背景下的运动,源源不断的歧视压力招致强大的反抗,而反抗的结果当然是融入市场扩张运动之中。因为引起反抗的那种歧视,它本身正是来源于市场扩张。
女权主义盛行于战后,也是本世纪文化多元主义运动有力的一翼。女性歧视、妇女权益如何突然成为困扰当今社会的问题呢?资产阶级当初向封建势力提出权利要求,反对封建势力的歧视,创造了平等权利的话题。而现在女权主义又如法炮制衍生出自己的平等权利要求。历史地看问题,普遍主义权利诉求是深深植根于市场扩张运动的,它反映了市场扩张可以达到的实际情形。那时普遍主义权利实际上仅及于卷入市场扩张活动的男性。说它普遍是在市场扩张范围内的普遍,就它那个时代的规模,它不可能遍及于女性。所以,一面是普遍主义的权利诉求,一面是并无女性歧视、妇女权益问题的发生,女性作为社群并无强烈的受歧视的压力。而社会则并没有感受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妥。罗马法把妇女儿童定义为家主的财产。(注:参阅Justinian,The Digest of Roman Law,Translated by C.F.Kolbert,Penguin Books,1979.)工业革命时代的习惯法也多少秉承了这个传统。财产占有在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分割,也没有必要在家庭范围内分割。以我们今人的眼光看,这很象是对女性的歧视。不过,与其说是歧视女性,不如说是法律权宜的形式,与歧视不歧视女性,根本牵扯不上关系。因为那个时代并无发生此类问题的余地。女性在传统上基本不介入市场活动,同契约文书的签署等交易活动无关,普遍主义权利诉求也就不包括她们在内。如果说到歧视,则是参与市场活动男性受到维护等级制的封建势力的歧视,而不是女性作为社群受到歧视。不过,市场扩张一旦形成,或迟或早它会将不在其中的社群卷入自身的活动中来。最明显的莫过于二战引起的社会变化,战争期间英国、美国等国家青壮年男子大部分上了战场,女性被迫投入制造业和社会服务。战争变成一个意外的机缘在极短的时间内加速妇女人口卷入经济和社会事务。事实上,这就是市场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深度扩张,将更多人口卷入职业化的过程。但是,歧视的问题随之而来。女性一走出家门就感受到歧视的压力,人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以往完全没有的妇女走出家门的现实,心理准备不够;法律也不能配合突如其来的转变,例如报酬、职业限制、女子教育、法律地位等问题都没有可以遵循的答案。既然市场扩张不可逆转,这些社会措手不及的方面自然就形成了歧视的具体内容。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女性要求一个与男性一样的平等的答案,掀起了反歧视的斗争。战后女权运动异常活跃,社会也作出许多相关的法律补充和修正,平等权利问题至少可以说有了一个法律形式的答案。这表明歧视的压力是与市场扩张同时发生的,没有市场的扩张就没有歧视问题的发生。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扩张会产生不同的歧视问题,而反歧视、要求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其最终结果都是加速完成市场的扩张。近年,有迹象显示女权运动衰落,这可以视作市场在性别人口方面的扩张运动已经有了一个大体认可的结果。
反殖民问题也可以作如此的理解,不过它发生的范围不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而是国家间的关系,因而也具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殖民扩张其实是市场扩张早期的比较残酷的形态,这种粗鲁野蛮的市场扩张终于因民族独立和解放而退出历史舞台。有意思的是市场扩张并未随殖民主义寿终正寝而停滞不前,它只不过采取另外的形式。(注:有的后殖民理论将殖民时代结束后的市场扩张称作“自由贸易帝国主义”(free tradeimperialism)。 语似夸张,但也意识到市场扩张会有不同形式。 见Patrick Brantlinger:The Rule of Darkness,文章收在 LiteraryTheory:An Anthology,edited by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Pp-856,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饱受了殖民扩张的困扰。这块地方本来是“朝廷自有制度主张”的地方,言下之意当然是自成一套不必等洋人来教训,它的制度模式确实和已经形成扩张能力的市场制度两不相干。无奈市场扩张到中国来。固有的宗族制度和朝廷典章在市场扩张面前分崩离析,而现代工业组织和法律秩序却在旧制度的分崩离析面前缓慢生长。中国是极不情愿地被卷入市场扩张的漩涡里来的。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殖民扩张到中国来,朝廷的模样当然可以延续更长一些日子,关起门来做皇帝的快活至少不会那么快就惊散了。可是,随着市场以殖民的形式扩张开始,中国随即觉醒到自己落入被歧视的处境,条约口岸甫成不久,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就此伏彼起。市场扩张同反歧视、争取民族独立斗争几乎一同到来。因为市场规则是要求独立和公平的,所有参与者都需要独立的法律地位,国家也不例外,而所有经济、政治活动都需要服从同样的规则。殖民式的市场扩张一面损害中国的独立地位,置中国于殖民和强权的困扰之下,但另一面也促使中国脱离孤立封闭的状态,卷入普遍化的“规则的世界”。收回主权,打例列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所构成的“国民革命”,是那个时代无数旗帜各异的革命者最具有一致性的目标,也是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最具有实质内容的部分。究其所以然,独立、平等、反抗强权等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不正是在殖民式市场扩张中学习和领悟到的吗?歧视不是本来就存在的现象,它是交往才发生的现象。市场扩张造成了民族歧视、国家被殖民化的问题,但市场扩张也激起反歧视,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而市场规则本身则一直在殖民和反殖民的民族独立斗争中扩张自身。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长久斗争,在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和悲壮的记忆。这场斗争落幕以后,民族主义者以简单的笔调涂抹这段历史,仅仅把它描绘成奴役和反抗奴役的英勇决斗。(注: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近代史著作,均是按反帝、反封建作为线索贯穿。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可作代表。现在看来,此类著作对近代史进程的理解,极其有限。)其实这恰恰掩盖了这段历史最具有实质性的地方:市场在世界规模的扩张。反殖民主义当然导致了民族独立和较为初步的现代国家的建立,但这场胜利并没有遏止也无须遏止市场的扩张,无论殖民主义还是反殖民主义都是市场扩张本身的自然结果。
二
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运动最核心的地方是反对歧视和要求集体权利。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遭受歧视所以不得不以集体权利对抗歧视的压力,因为没有集体权利的保护所以身处弱势社群而受歧视。在反歧视、要求集体权利旗帜下包裹着的则是社群意识本身。在现代社会里,血缘、肤色、种族、性别、风俗、趣味、爱好、习惯等,都可能成为社群意识觉醒汇聚的焦点,或者说都可能成为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运动的导火线。就象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种族是最敏感的触点,几乎一触即跳;其次可能就是性别了,虽未到动辄得罪的程度,但也要谨言慎行才好;另外某些趣味也是禁区。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运动对社会解放功不可没,它使人们认识到集体权利有它必要的地位,各种族文化是平等的。但是活动和社会政策在多大的程度上肯定集体权利的诉求,如何平衡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这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一致的意见。反歧视本身可能引出新的歧视——对个人权利的歧视,正如绝对的集体权利必然损害个人权利一样;文化多元主义的集体权利诉求如果走到极端,将集体权利绝对化,将文化的差异夸张到脱离实际的程度,很可能损害社会需要的平衡。在前所未有的困扰面前,澄清歧视、文化等概念,或许能推进我们的认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歧视现象的存在。歧视的历史非常古老,而且伴随人类始终。看看人类自相奴役的古老历史、想一想“夷夏之辨”类似的老问题,翻开史书满篇不乏“戎、狄、夷、蛮”等字眼,就可以知道歧视的历史有多长。可是,直到近代以前,并不曾发生以反抗歧视为号召的抗争运动。即使有强势种族与弱势种族的战争,但无论对哪一方来说,它都是“上帝和魔鬼”之间的战争。这种“你的神与我的神”之间根本不相容的争斗,当然不必要在反歧视的框架内解决,它只有你死我活唯一一条出路。反歧视运动的出现,说明了社会的进步,更引起我们对歧视现象本身的思考。我们可以将歧视划分成两类,一类称作“偏见歧视’;另一类称作“地位歧视”。当然地位歧视也与社会偏见有关,但与偏见歧视不属于完全同样的问题。歧视当然来源于偏见,人类不能根绝歧视是因为人类首先不能根绝偏见。每一个人都在有限的生命期内根据自己可能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形成思考判断,这些思考判断又不可避免受个人身处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影响,无法期望得到中立的立场。除非是关于事实的判断,还可以找到差强人意的客观标准,但澄清事实是何其的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关于规范问题的判断,则根本没有客观可言,它们合理性的程度,只能在漫长的历史中多少获得澄清。由此可见,生命的有限和信息不完备这两大限制,是人类无法摆脱偏见的根本原因;偏见有可能维护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和私人利益,也是它永远存在的重要原因。存在偏见的障碍不能除去,歧视也就如影伴形,挥之不去。源于偏见的歧视我们可以称之为偏见歧视。
自从个人权利的平等运动出现以来,歧视现象逐渐与法律地位问题牵涉上关系;更随着市场在世界范围的扩张,国际秩序内的民族国家地位平等也出现了。资产阶级个人权利的平等运动,是以普遍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事后被马克思主义批评为打着人类的旗号,争取的其实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普遍主义的个人权利理念至今还是被文化多元主义批评为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纵观历史,旗号与实际情况确实是不一样,不过我认为问题在于如何解释旗号与实际情况不能吻合的现象。市场力量的生长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市场扩张,而市场扩张是逐渐波及社会其他领域的,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蚕食封建等级社会,也逐渐将更多的人口、资源卷入到自己这架机器中来。与此相应,个人权利的落实自然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个人权利所以是普遍主义的,并不是出于事前的夸张,而是市场本性决定的,市场不容许特殊主义。这样,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个人权利理念,另一方面是普遍主义个人权利并不完全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两者共存于市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权利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就是地位歧视。个人权利的地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与生俱来的。但是,既然存在市场扩张,权利普遍化程度加深的正面推动力也必然存在。事实上,这正是文化多元主义所以存在的真正理由,它以集体权利诉求的形式落实普遍主义的个人权利。由此可见,地位歧视是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它的历史没有偏见歧视那么悠久。人们能够期望逐步消除的只是地位歧视,而不是偏见歧视。地位歧视可以透过争取权益的社会运动加以消除。回顾近数百年来,人类在这方面确实迈出了值得骄傲的步子,反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运动对半平分了这一人类文明化的成就。可是,偏见歧视却并不见得减少,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依然随处可见。我在这里断言人类不可能期望消除偏见歧视,并非暗示一个灰色的前景,相反这正是我们乐观处世的理由。没有偏见的社会是千篇一律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无比可怕和令人恐惧的“美丽的新世界”。
文化多元主义及其社会运动在将集体权利绝对化的时候就将反对地位歧视扩展到反对偏见歧视,在笼统的反歧视的旗号下把消除偏见歧视也当成社会运动的目标,这种越俎代疱的局面造成了新的困扰。我觉得,消除偏见歧视不应该是文化多元主义的目标,它只能以消除地位歧视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地位歧视是一个法律框架内的问题,它可以而且应该在法律范围内作出修正。但偏见歧视是一个远为复杂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地方是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客观和公正的判断尺度,因而无从知道某种价值观或意见到底算不算偏见。这里使用偏见一词,是针对各种价值观和意见的纷纭扰嚷现实状况假设而言的,相互冲突的意见碰到一起时自然就是互为偏见了。另外,偏见并非等于没有存在的价值,即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断定某种意见是不符合实际的偏见,但它仍然可以启人心智。所以,在正常社会,没有人可能有理由以消除偏见歧视作为社会运动的目标,但文化多元主义运动常常在反歧视的“正义理由”下跨越界限。他们不明白这实际上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把地位歧视和偏见歧视混为一谈,结果使社会舆论的神经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神经质;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托庇下,媚俗遂成不可避免。极端化的集体权利诉求如果落实为社会政策,那就必然是动辄得罪,“政治正确”遂相伴而生。
让我用一个假设的例子说明问题。中国古典小说写到和尚,大多不是善主。不是贪财好色,就是贪杯嗜酒,更兼形貌丑陋。《水浒传》里的鲁智深虽然最终修成正果,但他偏不是正经的和尚,只不过英雄末路,“不如就了这条路罢”,更何况他虽经剃度而不戒酒肉。这类带有对佛教歧视性的文学形象,未尝不可以说表达了对佛教的偏见。如果中国有强大的佛教压力团体提出反对这种歧视而最终落实为某种社会政策,古典文学课程的老师有义务澄清和尚的真实历史形象,情况会怎么样呢?为了消除这种偏见,代价是我们错过了欣赏这种偏见包含的智慧和幽默。《金瓶梅》里卖红丸给西门庆的人,如果是一位江湖郎中而不是一位流鼻涕的梵僧,那一定是索然寡味了。同样,古典小说里“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或“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之类的话头,当然是多少包含了对女性的偏见在内了,但如果都被女权主义痛斥为“死去的黄种男人”的性别歧视而要革除出古典之林,那么这种“政治正确”所遮蔽的是什么呢?那定然是错过了理解古人对男女深情的独特解会了。事实上,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没有类似托在“正义理由”名下的媚俗。历史教科书里,尽量赞赏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的英雄业绩,对其中的愚昧、盲目、非理性行径则避忌不言;在谴责传教士伪善的“文化侵略”的激烈声浪中,独独隐去了传教士对现代医学和教育的传播贡献。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民族主义话语的强大压力。史料是有心人皆知的,而历史面貌则被描绘成“政治正确”的样子。这样塑造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历史未尝没有几分道理,可是在这几分道理的曲解之中遮蔽了历史的真相,扭曲了追寻往迹的自由心灵。文化多元主义假如锁定偏见歧视为自己的敌人,我们的生活中注定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忌讳,这恐怕不是学术自由的福音,而是“一统江湖”的前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存在偏见歧视的现象,但是用历史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已经出现的偏见多少都会被后代的人抛弃,那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学习、试错的过程。试图用集体权利诉求的方式纠正偏见歧视,就是人为地设定一个事实上不合乎理性的假的“平等和公正”的标准,来判定社会生活的各种价值观和意见。我相信,文化多元主义在这点上是越出了自己应当谨守的边界了。
象歧视一样,文化这个概念也在当代世界引起很大困扰。笔者不是要在这里全面检讨文化这个概念,而是想借助一些分析看看文化多元主义所论证的文化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集体权利诉求运动背后一个强有力的根据是文化是有差异的,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道理是说得通的。在我们自己的经验里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差别很大,至少是有差别吧;就象个人权利平等一样,各个文化在权利上也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但是,尊重的边界在哪里?如果尊重是绝对的,在大多数民族—国家内部则非到分崩离析的分离主义程度不可。确如阿帕杜莱说的那样,民族—国家之间的那一横,表示的不再是联系而是断裂和分离,(注: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第539页,三联书店 1998年版。)由文化差异到“差异政治”的危险性正在这里。而且,文化差异背后假设了一个“压迫者的文化”的概念,它的言说常常是指向这位杜撰出来的压迫者。
现代以前,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遍的,因而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自我中心倾向。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形成以后,这种局面逐步被打破。每一种文化都落入了“地方性”的局面,普遍主义仅仅是自我中心的幻觉。因为资本主义市场扩张本质上并不是“文化的扩张”,尤其是站在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对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作文化扩张的理解更是没有穿透历史的视盲。当然,各种文化由普遍主义的意义走向地方性的意义,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日达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欧洲文化、美国文化还是笼而统之的“西方文化”,无论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还有大而化之的“东方文化”,在资本主义市场扩张面前只能具有地方性的意义。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与其说表达的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了解,还不如说是表达了对国家势力的焦虑。“文化冲突”无论如何不可能主导现代世界的冲突,因为通过一定文化阐述和肯定的价值观,在古代或许有但在现代则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寻求各文化的地方性意义,保留历史的传统,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形式,在各自认同的文化价值内发掘好的生活的意义,我想,这就是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尊重文化差异的可能目标。但是,文化差异话语常常暗示“文化的压迫者”,它们把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理解成“文化扩张”,并认为此危及弱势文化的生存地位,故而主张文化差异的说法,由文化的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契机进而为“差异政治”,走向了极端化。认同自己文化的人希望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这原是不错的。但为了肯定自己认同的文化,想象出有外来的“文化敌人”的威胁,由此把文化差异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这就走过了头。证诸史实,各文化的交流,无论是贸易、信息还是人口迁移,其规模均是在不断扩大,无论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间,都是如此。假如“差异政治”或“承认的斗争”引发分离主义运动,无论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就是它阻碍了文化之间的交流,剥夺了人民可能享受到的经济繁荣和增长带来的好处。即使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目标,共同体由想象变为现实,随着经济低落而来恐怕不是文化自豪感的满足而是文化的沮丧。在民族—国家内部促进至少是维持各民族文化在现有水平的交流,这恐怕是文化差异的底线;“差异政治”的结果,如果是阻碍各文化的交流,阻碍地区之间的贸易发展和信息交换,阻碍人民的自由迁移,真正能够从中受益的只有主导“差异政治”的少数人,而受损的却是广大平民老百姓。同样的道理,民族—国家的政府如果将主权绝对化,拒绝融入国际社会,人为制造贸易和交流的障碍,封闭自己的市场,由这种封闭政治虚构出来的文化自主性图像,可能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但是不能分享这种文化自主性荣耀的平民百性则一定有机会分尝由贫穷带来的痛苦。
认同是一个很好的字眼,可是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怎么能相互认同呢?在现代世界要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取得认同,至少和古代世界一样困难。古代有地理距离、知识水平的限制,现代有文化多元主义极端化的限制。不过,回顾历史,某种均衡的取得与其说来自认同,不如说来自妥协。认同的独木桥走不通,妥协仍不失为一线希望。在一个基本秩序的范围内,如何平衡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这是文化多元主义及其社会运动带来的最严重的挑战。其实这并不是文化多元主义挑战自由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向文化多元主义发难,而是各方都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可以预料,出路大概只有妥协了。个人权利原则和集体权利诉求之间在某种程度的均衡,将继续塑造当代社会。如果不能达成均衡的基本秩序,社会便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