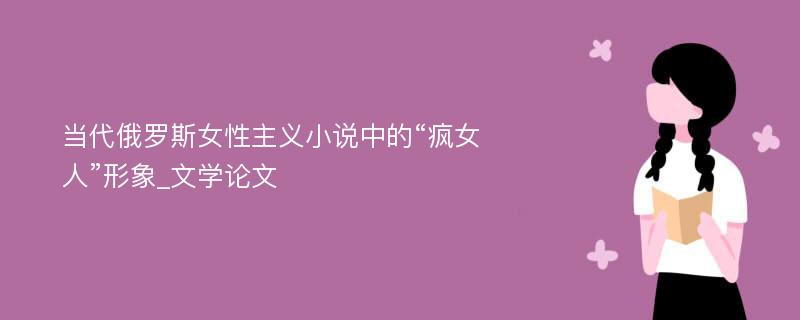
当代俄罗斯女性主义小说中的“疯女人”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当代论文,疯女人论文,形象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俄罗斯女性主义写作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界也正进一步展开对它的译介与研究。本论文主要通过细读文本,发掘当代俄罗斯女性写作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其传达的文化与性别政治的信息。
俄罗斯文学有一种“女性优越情结”(注:卡里尔·爱默生:转引自尼娜·斯特劳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宋庆文、温哲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在18、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是与“俄罗斯”、“大地母亲”、“妻子”等富有诗意和情感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女性形象都是爱的化身,是衡量男性主人公崇高或低俗的标尺。20世纪苏联官方文学文本中女性也往往以天使或地母的崇高形象出现:改造社会活动中的英雄、男性主人公的革命伴侣、家庭生活中的母亲,有时候她甚至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对女性形象的过分崇高化逐渐被当代女性主义者视为父权/男性文化对女性真实形象的伪饰和虚构。这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在 自己的文本中重新书写女性,借以剥去父权/男性文化通过伪饰与虚构对女性真实形象 的抹煞和去除。
以重新书写女性形象为写作中心的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已经形成群体。尽管她们的艺术观念各不相同,但是在传达女性被长久压抑的声音这一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这些女性作家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俄罗斯男人的病症”(注:尼娜?珀利琪?斯特劳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宋庆文、温哲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一样,注意到了“俄罗斯女人的病症”。她们对俄罗斯文学中女性生活本质未得到充分揭露的现象进行探索,表现了独特的洞察力以及鲜明的女性立场。
20世纪60年代末期纳塔丽娅·巴兰斯卡娅(1908—)发表中篇小说《一星期只有七天》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妇女的地位,包含着不动声色的社会谴责。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是当代俄罗斯女性主义作家中最早书写女性真实命运的,70年代她开始发表此类主题的短篇小说及剧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俄罗斯出版了一系列“女性小说”作品集。叶莲娜·塔拉索娃、斯维特兰娜·瓦西莲科、斯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娃、尼娜·萨杜尔、拉丽莎·瓦涅耶娃等公开打出女性写作的旗帜,书写女性被湮没的真实生活,还原女性的历史。
这些女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是悲凉的、险恶的,是苦难但不一定高尚的——她们怀 着对苦难的憎恨,有时候甚至是对他人的憎恨。她们不再是宽容慈爱的地母,而是疯狂 的复仇魔女。
这些“疯女人”形象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疯女人”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孤独女性,是生活在男性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她们身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压迫,是男性文化(父权制文化以及以国家意识形态面目出 现的男性话语)剥夺的对象。
当代俄罗斯女性写作文本中女性占据中心位置。男性要么被放逐到边缘地带,要么干脆被隐去,成为缺席的存在。这些居于文本中心的女性主人公往往是单亲家庭的母亲或者身兼母亲、女儿、妻子三重角色,被丈夫或情人抛弃,被狭窄的居所、窘迫的经济困 扰,在家庭生活中冷酷刻薄,常常做出疯狂的举动,不仅伤害别人,也伤害自身。在这 个暗昧扭曲的女性世界里,“母性不仅是建设的力量,也是破坏的力量,愚昧的力量。 ”(注:瓦莲京娜·绍欣娜:转引自谢尔盖·巴温,《平常故事(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 斯卡娅)》(俄文版),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1995年版,第34页。)
塔吉娅娜·托尔斯泰娅《诗人与缪斯》(注:塔吉娅娜·托尔斯泰娅:《奥克维尔河》(俄文版),莫斯科马蹄铁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262页,以下论文中出现的作品只注出版本及页码,凡引自作品的引文不再另注页码,以避免挤占篇幅。)中尼娜是一个被男性话语制造出的女性神话所戕害、患上了“伟大妄想症”的女性。她自认是未来伟大“诗人”的缪斯,肩负庇护并引导她的“诗人”的责任——而实质上这种庇护与引导不仅扼杀了诗人的生活,毁掉了他的才华,也扼杀了尼娜的生活。缪斯的神话被打破, 诗人的神话亦不复存在。
叶莲娜·塔拉索娃《不记恶的女人》(注:叶莲娜·塔拉索娃《不记恶的女人》(俄文版),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214页。)是一个隐喻性的女性书写文本。主人公“她”是受过高等教育、“33岁,与耶稣基督同龄”的女性。生日夜晚“她”独自在家,对自己被父权文化压抑、女性意识苏醒、反抗历程进行“超越禁区”的回忆。主人公“她”曾是美丽少女,但是身体深处早就埋下“疾病”(抗拒父权/男性文化抑制)根芽。这“疾病”根芽慢慢长大,“她”因与众不同的身体遭受来自他者的作弄嘲笑与虚伪的同情——“多可怜的女人啊”。“她”被男性文化误导,也仇恨自己的身份:读到过一段把人之诞生贬低为“野蛮原始”的动物性行为的文字之后,“试图从做动物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并“痛恨自己的身体”。她与周围人的关系也被破坏。
“她”的反抗就是尽做些被禁止的事情,为此,常遭受父母的毒打和痛骂。对母亲“听话些,会对你好的”的警告,“她”报以冷酷的反抗与无情的话语。反抗总是招来更强烈的暴力侵害,“她”被送进“过分正常:坚固的墙壁,坚固的栅栏。没完没了的墙……栏杆……栅栏”的“疯人院”,被指称为一个患有疾病、丑陋不堪的“非正常”女性。“她”拥有“巨大的心灵与驼背的小侏儒”——反抗而又绝望的女性自卑的真实自我——这一强烈的反差折磨着“她”。
“她”拒绝“听话”,不再相信“对她撒谎”的书籍,拒绝被父权文化收编。在“疯人院”里,“她”被高大强壮的女性视为“我的女神”。在父权/男性文化禁闭女性自由的“过分正常”之地,“她”学会了思考。“她”的血液里奔流着“任什么都压制不住的呼唤”,要“开始嗥叫吧”,认识到“一切都是谎言。连衣裙也是谎言”之后,渴望“扔掉它,跑吧”。疯女人、病女人这些父权/男性意在消解女性话语的虚假命名, 被女性变成获得自由意志的途径,贬抑女性的“医院”成为觉醒女性的“狂欢节广场” ——“她要讲笑话,她是病人,想怎样都可以”,连父母也被“她”无所顾忌的笑话引 得“笑出了眼泪”。而“疯人院”这一禁闭之地也成为她巨大心灵的“故乡”。
通过“疯女人”这一形象,女性“内心的不自由”被充分展现,女性被侮辱、被损害的实质也得以揭示。作为独立的个体,女性和男性一样,渴望自我实现,自我潜能的发 展。渴望“公平”地获得“我的”那一份(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有如天使》,《 姑娘屋》,莫斯科扁角鹿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对父权/男性文化社会中的“ 疯女人”而言,这样的“自我实现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女性不仅没有获得官方父权、 男性话语所宣称的“平等”与“自我发展”机会,而且还因为父权/男性社会对女性的 生育要求承担了更沉重的生活负荷。在私人领域即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责任(东正 教的文化传统要求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应该服从男性家长,承担料理家务、抚养孩子的任 务,而且,由于客观原因,多数女性因男性家长的缺席,不得不承担家庭经济的压力( 注:茅慧青,《苏联妇女地位之研究》,参见http://www.4thly.com/postrussia/ruswomen1-2.html,2003年9月1日。))和公共领域即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作为补充 劳动力参与社会生产)的责任,使俄罗斯女性承受沉重负担,失去“自由发展”的可能 。代表男性利益的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神圣”的诉求(除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大地母 亲,还有苏联时代现实的“母亲英雄”、“劳动英雄”称号)和“永恒”的生存(日常生 活的烦琐、家庭生活的紧张)给女性造成了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男性话语若干年来 对女性的欺骗(“连衣裙也是谎言!”)也侮辱和损害了女性,使其沦为“第二性”。
第二,“疯女人”是自觉或非自觉的彻悟女性。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她采取行动,表达对于压抑她们的男性群体与文化的愤怒,反抗父权/男性文化。因此,“疯女人”又是反抗的叛逆女性。
《不记恶的女人》的“她”、《有如天使》(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姑娘屋》(俄文版),莫斯科扁角鹿出版社,第31—37页、第217—224页、第12—25页。)的安格丽娜、《自己的圈子》中“绝顶聪明”的“我”、《美狄亚》(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姑娘屋》(俄文版),莫斯科扁角鹿出版社,第31—37页、第217—224页、第12—25页。)中的“妻子”,以及《午夜时分》中的祖母与母亲(女主人公诗人安娜·安德里阿诺夫 娜)都是“疯女人”。
认识到男性的欺骗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决定与其对抗。她们拒绝相信男性话语,拒绝被男性世界收编,阻碍年轻女性与男性世界的交往、防止她们被父权/男性话语欺骗。抵抗男性话语加诸女性的“职责”——拒绝成为“天使”、拒绝成为母亲,拒绝做男性的养护人、伴侣以及救助者。
“疯女人”形象表现子女性对男性世界“独特的愤怒”。女性被男人抛弃,却必须承担养育这些男人子女的重负。对女性而言,生育和抚养孩子带来的压迫感、屈辱感远大于幸福感。母性爱的本能与自由发展的渴望在女性身上发生激烈对抗,然而失去的总是 获得“内心自由”的可能。“疯女人”们认识到造成不幸的根源是父权/男性文化。她 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午夜时分》里的女性通过对所谓“母亲天性”的反 抗,宣泄自己对男性社会的不满,并把愤怒扩大到一切与男人有关的方面。安娜·安德 里阿诺夫娜嘲笑女儿对爱情的纯洁感受和对美满婚姻的希求,她把女婿称为“下流坯” ,从“女人的”家里赶走了他(男人);她嘲讽男人之间友好的表示,认为那是虚伪的、 “奇怪的东西”。她们憎恨生育:安娜·安德里阿诺夫娜不仅在女儿即将生育需要帮助 的时候冷淡地拒绝了她,还怒气冲冲地抱怨女儿为什么不去堕胎,说许多女人甚至在不 可能堕胎的时期以堕胎方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并“坚强”地挺了过来。
《美狄亚》中的“妻子”干脆杀死丈夫的女儿。一方面,这是对丈夫的报复,使他失 去年轻女性的爱,另一方面,也是阻断女儿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如果她成长为一个主 体意识觉醒的女性,她就会被指称为“疯女人”、“病女人”,被排斥到边缘地带;要 逃避这样的命运,她就只能做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第二性”,屈从于男性另一种形式 的贬抑。“疯女人”的“杀婴”与女作家以“缺席”、“婴孩化”、“残疾化”等方式 “驱除”男性具有同样的意义,表现的是同一种女性主义情绪。
但是这种愤怒情绪的宣泄往往不仅伤害男性,最主要的,还伤害了女性自己。对抗愈来愈激烈,女性被“愤怒”撕裂,或者走向冷漠,或者走向疯狂——总之,女人不再成其为女人。
第三,“疯女人”具有抽象化、类型化的特征。她们共同构成一个互相印证的女性世界,表现“疯女人”被一再强化的悲剧性生存状况。
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具有类型化特征。女作家常常用“她”、“一位妇女”、“我”、“母亲”、“两个小妇人”等来指称她的人物,有些人物甚至自始至终都没有名字。即使在小说一开头就说出了人物的名字,可后来的叙述却把名字淡化、淹没了。往往人物的名字和身份在叙述过程中被不经意地一带而过,名字变成了人物的代码。名字在于塑造人物个性方面的意义被取消。她可以叫安娜,也可以叫济娜,无 关紧要,总之她是一个女的,是“她”。小说中的情节因此不再专属某个具体的安娜或 者济娜,而是女人、母亲的普遍遭遇和命运,是“在残酷世界中女性的命运。”(注: 格奥尔吉·维林,转引自谢尔盖?巴温,《平常故事(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1995年版,第27页。)
“女人”是女性文本中女性形象共同的名字。《午夜时分》里的女诗人安娜·安德里阿诺夫娜的女儿阿廖娜是《姑娘屋》(注: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姑娘屋》,莫斯科扁角鹿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175页、第152页—157页。)里的纯洁女大学生,对生活充满了幻想,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逐渐教会了她失望、在爱中滋生出仇恨。随着阅历增加,到中年阿廖娜很可能就会变成和她母亲一样的人,正如她母亲到暮年 渐渐成了外婆希玛的,尽管她曾经意识到并尝试避免重蹈母亲的覆辙。分娩时的阿廖娜 就是《快乐湖故事》(注:尼娜·戈尔兰诺娃:《快乐湖故事》,《不记恶的女人》, 莫斯科个人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9页。)中的女主人公,独自一人,居住在“官 方文件中不存在的棚屋”,在“官方文件中不存在的产院”分娩——面临父权/男性话语中“不存在”的困境;她们其实也就是《女人十日谈》(注:尤里娅·沃兹涅先斯卡 娅:《女人十日谈》,电子文本。)里那十位来自不同阶层、具有不同身份的产妇;拖 儿带女的安娜·安德里阿诺夫娜与她女儿、同样拖儿带女的阿廖娜和《济娜的选择》( 注: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姑娘屋》,莫斯科扁角鹿出版社,1999年版,第 167—175页、第152页—157页。)中年轻的济娜其实是同一个人:无助,饥饿,独自承 担抚养孩子的重负,必要时候也不得不做出可怕的“选择”;一旦精神崩溃,失去理智 ,她们就是《美狄亚》中那个司机的妻子,因为仇恨丈夫的胡作非为而杀死他们共同的 孩子以报复男性。
尽管由于个别压抑经验的差异,以及身份、处境不同,颠覆或反叛的策略与形式亦有所不同,但在焦虑之下,歇斯底里的写照是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常用的方式。从美少女到悍妇、病女和疯女,不管女主人公出场时多么美丽动人,最后也成为面目凄楚、满布愤怒的丑陋女性和病态疯狂的女人。这些女性人物从美少女到女神的升华(在恋爱以及养育年幼子女的过程中),最后沦落为悍妇、病女、疯女。疯女人以及她们的叙述者, 以疯狂、精神分裂、自我毁灭的形式表达内心的愤懑和痛苦,表达了人物、叙述者和女 性作家的女性主义情绪:愤怒。而女性作家在各自文本中,通过不同的场景与情节叙述 ,制造文本间性,使女性的压抑与疯狂被一再强调,女性形象的悲剧性一再被加强。
传统文学经典中具有雕塑个性的外貌描写,在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笔下也成为一种类型化隐喻:安格丽娜、纽拉以及“她”的外貌特征都丑陋难堪——一方面,女性被毁损的外貌,正是与她们被父权/男性文化否定、贬低、毁损的内心一致(注:叶莲娜·塔拉索娃:《不记恶的女人》(俄文版),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而另一方面,女性自己也参与摧残自己的外表——“把脸弄脏”——拒绝成为男性话语要求的“美丽温顺”的天使形象,选择成为丑陋的疯女人、病女人,从而反抗男性话语,获得女性自由。
第四,“疯女人”是寻求出路的女性。她们东奔西突,寻求获得解放的途径,借助“ 男性的成长”、“女性的独立”以及通过童话模式“爱”与“自我牺牲”实现的两性“ 和解”。
《大团圆》(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姑娘屋》(俄文版),莫斯科扁角鹿出版社,第31—37页、第217—224页、第12—25页。)中波林娜业已退休,是一个被丈夫摧残、欺辱和压抑女性。偶然间从她久未联络的女性前辈那里获得遗产——“一间自己的屋子”,她获得了女性独立的物质基础(注: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得以摆脱丈夫的侮辱与损害,成为“自由独立”的女性。再次重返与丈夫同居的住处时,波林娜也能够以平和稳定的姿态应对丈夫的恶言恶语。丈夫迟到的成熟与宽容理解(不再像一个任性顽童对妻子强词夺理、横加污蔑,以恶作剧给妻子制造不愉快,而是对妻子的爱护表示感激、对妻子的辛苦表示同情:“你吃一点吧,你也饿了”)使得波林娜“嚎啕大哭”——两性间长久紧张 敌对的冲突得以“和解”,实现“大团圆结局”。
《祖父的画》(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五卷集》第4卷(俄文版),哈尔科夫菲里奥、莫斯科特克奥·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第291—299页、第139—144页、第276—284页。)是一个童话故事体的短篇小说。“人因为撒谎、嫉妒的罪恶”给人类自己带来了惩罚,“太阳将被永远遮住,无尽的冬天就要到来”。只有肯牺牲自己最宝贵东西的人才能从无尽之冬拯救人类。爷爷因养家之故,毕生照定制肖像的要求作画。最后时日他摆脱“订货”的束缚,画出自己唯一的天才之作。爷爷不肯献出自己宝贵的大作。 小姑娘决定“平静地献出唯一宝贵的东西——自己的生命,为了大家能够在太阳下生活 ”。爷爷最宝贵的画掉下来摔碎了(父权/男性绘制的美景被打破)。小姑娘躺在冰冷的 地上,大病一场。她醒来已是温暖的六月,认为是爷爷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画拯救了大 家。成年男性爷爷与天真年幼孙女成为两个互相对照的形象。自私的爷爷在宽容孙女的 召唤下学会奉献与牺牲,才使人类重获美好温暖的生活。
《大鼻子姑娘》(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五卷集》第4卷(俄文版),哈尔科夫菲里奥、莫斯科特克奥·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第291—299页、第139—144页、第276—284页。)、《魔镜》(注:彼得鲁舍夫斯卡娅:《作品五卷集》第4卷(俄文版),哈尔科夫菲里奥、莫斯科特克奥·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第291—299页、第139—144页、第276—284页。)都讲述奉献与宽容的故事。一个小姑娘卡佳买了一副便宜的太阳镜。这是一副魔镜,既可以望远又可以显微。她时时处处戴着,遥不可及的美景与近处的龌龊肮脏使现实生活成为难以忍受的折磨,使小姑娘失去生活愿望。借助魔镜她帮一位丢失孩子的妈妈找到了孩子。这使她学会接受并不完满但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想“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就只好和细菌微生物一起生活吧”。与生活现实的妥协、对缺陷的宽容正是“疯女人”与女作家们一起找寻到的摆脱困境出口,也是女作家书写“疯女人”形象的目的之一。
尽管有些女性作家运用虚拟的叙述方式,提出解决问题与摆脱困扰的方案,但是当代俄罗斯女性书写模式的主流特质,还在于大量书写女性自我的匮乏、焦虑与边陲化的真 实面貌。她们把反父权/男性文化和女性压抑主题双双纳入文本之中,不但讲述女性在 父权下的压抑现实,也试图通过把男性置于文本边缘的叙述策略和布局去颠覆父权体制 。她们试图把“女性自我”融入更大的集体意识之中。因此,在书写女性经验上,特别 强调女性身体与精神人格在社会文化中所能承受的重量,一再以女性的悲剧性面貌去强 调被男性文化扭曲、压抑女性的过程。
她们对女性身体的书写,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而言是一种叙述策略:兼具攻击与修订、解构与重构传统女性形象的功能。正是通过对这些女性历史的重写,女性作家向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典范提出质疑。而传统父权/男性文化社会里的疯女人形象,亦通过她们一再重写而获得新的隐喻。
“疯女人”形象是男性文化对女性意识觉醒的一种压抑策略与方式。男性通过对具有觉醒意识的女性意识借助男性文化具有的命名权力进行“妖魔化”,贴上“疯狂”的标签,从而取消女性主体意识存在的合法性。
《不记恶的女人》和《有如天使》都致力于揭露男性文化通过命名收编女性与借助“妖魔化”压制女性的真相。小女孩出生之初即被“命名为安格丽娜”,“天使”之意,被男性借助父权文化赋予的命名权力烙上男性文化的印记——成为“天使”,“家庭中的天使”,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相当惹人喜爱,有无穷的魅力,一点也不自私,在家庭生活这门难度极高的学科中出类拔萃,每天,她都在牺牲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愿望,别人的见解和意愿,她总是更愿意赞同。……必须迷住别人,博得他人的欢心,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要想成功,就得说谎。”(注: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第三卷·女人的职业》,王斌、王保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7—1368页。)
幼年的安格丽娜确实惹人喜爱,乐于与人分享自己的东西。而随着她的成长,安格丽娜意识到主张自己公平的权力,看到别人有了东西,就问“我的呢?我的呢?”她尝试讨那些已经获得、正在享受的人们喜欢,渴望分得一份,可是“结果都一无所获”。她试图装扮自己,她愿意走入群体,却被否定、嘲笑。安格丽娜因为没有完成男性文化对女性的要求,不再“奉献牺牲”,不再以“说谎”掩饰自己的要求,压制自己的渴望,而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被父权/男性话语指称为“可怜的傻瓜”、丑恶的“鳄鱼”。
疯女人这一形象成为与“天使”对立的隐喻。女性形象的复杂性与双重性被建构出来。男性文化给女性预设的“天使”角色是唯一符合男性文化机制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成为遏制女性主体意识的牢笼,是主体觉醒女性获得创造力所必须摆脱的“阴影”,必须扼杀的“妖魔”。“疯女人”是男性文化给那些试图反抗的女性强行贴上的驱逐标签,用以给那些脱离这一机制的女性施加压力。
俄罗斯女性作家文本中的“疯女人”形象还具有另外两重意义:其一,女性写作借助这一形象剥去传统文学文本中对女性形象的矫饰和伪崇高化,还原女性真实的内心状态,发出女性的声音,使得在男性话语之下被视为非法的女性身体及女性感受获得合法性,得以进入被驱逐与排斥的历史图景;其二,借助这一“疯女人”形象,觉醒的女性得以摆脱父权/男性文化强行加诸女性的“外衣”,抗拒父权/男性文化用以束缚女性的“ 天使”形象,实现女性的“解放”。“疯狂”不仅是女性对来自于男性文化压制的反应 ,也是对这种压制的绝望反抗。“疯狂”是女性反抗的方式与策略。
女性主义者主张女性必须书写自身的经验,以解放潜意识中巨大的源泉,使女性从“无”中回来、从荒野中回来、从“文化”的彼岸回来,……借助这种书写模式,女性作家亦将取回女性丧失在菲勒斯中心的“能力和资格”,以及她们所失去的欢乐、失落的喉舌。使女性挣脱罪人身份,让世界和历史“听得到女性的躯体”(注: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转引自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95页。)。在西苏“写你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的名言中,女性深层潜意识中的巨大源泉得以喷涌奔流。在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的书写中,女性亚文化群 体得以走出男性父权/社会的黑暗,走出各种规范女性欲望和身份的定义,走进历史文 本。她们的女性感受表露出她们被隐匿在历史中的焦虑原貌。这种焦虑,以不同的面貌 出现,也通过不同的女性角色得以阐释。除了以歇斯底里的疯女人形象出现之外,女性的焦虑亦在愤怒怂恿下,透过暴力的语言表现在对男性边缘化的文本构造中。
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并非依循俄罗斯传统文学文本中的典型女性形象,亦没有受到她们前辈苏联文学文本中革命型女性和其他理想型女性的诱惑。这使得她们既得以走出父 权的厌女的阴影,又摆脱了女性乌托邦的幻想,能够从女性的阴暗层面展现女性身体、 欲望等性别政治问题,更深刻地揭露了文化意义上的女性世界。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在访谈录中说:“(我的短篇小说)里提出了不少问题——为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不是‘谁之过?’,而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们明明白白,可还是这样生活?……我努力把这些故事讲到纸上,看来是试图从中得到安慰,也许吧。可能,在 我写出的作品里有某种拯救的根芽;你已经告诉了,你已经向人们求助了……”(注: 玛·佐尼娜:《不朽的爱》,见《文学报》(俄文版)1983年第47期,第6版。)女性通过 书写自己,发出被压抑已久的呼声。这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女性写作的共同目标。她 们确实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像那个“33岁,与耶稣基督同龄”的“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