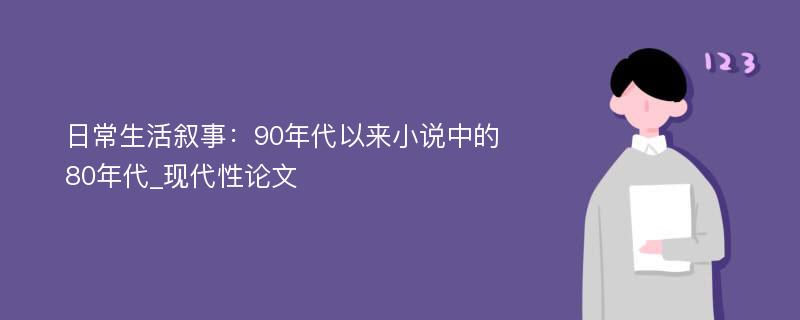
日常生活叙事: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80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日常生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9-0104-04
秉承着19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的余脉,1990年代以来小说对“日常生活”表现出超常的叙述兴趣。具体到90年代以来叙述“80年代”的小说文本,“日常生活”话语是我们透视90年代与80年代初、中期同类创作不同审美特征的一个饶有趣味的视角。对“80年代” “日常生活”精神表征意义的重视使得90年代以来关于“80年代”“日常生活”叙述的文本区别于那些关注日常生活世俗性、物质性与消费性特征,带有“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叙事姿态的嬗变是一种能够“映现”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①的“镜子”。因此,考察“日常生活”之内涵的时代变迁,不仅仅指向“日常生活”本身,同时指向特定时代整体的政治经济结构、情感结构与文化结构。
一、世俗化与同一化:“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的两个思想层面
“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扭结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日常生活受到社会基础、文化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具体形态又是一定价值观念与伦理体系的体现。具体到中国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日常生活”从政治化走向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同时,日常生活意识的觉醒也转化为追求现代化的动力。换言之,“日常生活”的发现既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与表现,同时这一发现也进一步促进了观念的变革与精神的解放。1990年代以来小说对“80年代”改革开放与现代性进程的重新认识是从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叙述开始的。魏微《大老郑的女人》以女人涂口红、掸眼影、穿超短裙等日常生活的改变作为1980年代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标志,其叙事意义不仅在于呈现这一社会现代性进程,更重要的是开掘与这种日常生活现代性相伴随的现代思想观念的萌生。
“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作为80年代启蒙文化的表征,指向80年代的现代性进程;另一方面,这种“日常生活”又是作为特定年代的文化风尚、社会习俗与时代精神的风向标加以呈现的,“日常生活世界本身的每一变化,同时也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应变革”②,因此,透过“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把握80年代的文化风貌与情感特征。王安忆曾在《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一文中说道:“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③也即是说,特定时代的历史风貌并非体现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上,而是体现在其时的衣食住行、伦理规范与习俗体系等日常生活层面。《长恨歌》中的“80年代”侧重在王琦瑶的衣着、爱情、死亡等日常琐屑的生活之流中,从而凸现“日常生活”的历史文化意义。
1990年代以来“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小说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呈现现代性进程中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觉醒的层面,还在于呈现现代性的理性规范性、同一性对差异性的忽视和对人性的压抑层面。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就以戏谑和反讽的笔法表现了80年代现代理性以及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控制:“在符驮村的男女们看来日日戳戳,吃吃喝喝,是人生在世的两大美事。”小说对80年代的叙述聚焦于直接与符驮村民的人生两大美事相对应的“分田到户”与“生育问题”两方面,而这两方面,恰恰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对符驮村“日常生活”的介入。作为现代性理性规划的计划生育与符驮村民的身体崇拜和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相背离,它通过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通过对身体快感的剥夺来达到对个体生命的控制与日常生活的改造。显然,小说并未一味肯定80年代的启蒙与现代性进程,而是从个人生活与体验的角度批判其对日常生活的改造与扭曲的一面。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干涉人们的生,还影响到人们的死。阿来《轻雷》中的藏民本来拥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攫取欲望最终烧毁了这座森林,破坏了生态平衡,同时导致藏民死后无处皈依。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的生老病死的被扭曲正标志着藏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没落与丧失。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技术—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直线型的,这是由于功利和效益原则为发明、淘汰和更新提供了明确规定”,“但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④。这表明,经济层面的现代性与文化层面的“日常生活”并非完全同步。“日常生活”的经验性、传承性和恒定性与凝滞性决定了其对于“现代性”的惰性与反动。如果说80年代初铁凝的《哦,香雪》通过一个文具盒表达了对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和现代性诉求的话,那么王安忆发表于90年代初的重述80年代的小说《妙妙》则通过对妙妙在日常生活中先锋实践的反讽表现其对80年代的现代化、进步的内涵的独特思考。正如火车给香雪带来了现代化的气息,妙妙对于现代化的体认,也是通过电影、电视以及来头铺街拍电影的剧组来实现的。在服饰问题上,妙妙遭遇到在现代与传统、先锋与保守之间无所适从的尴尬困境:“她只能在思想上抽象地行动,在思想上走到了人们的前列。而现实中,她的服装则因不甘随流却又技巧低劣而显出不伦不类,透露出一种绝望挣扎的表情。”正是出于对落伍和被时代遗弃的恐惧,妙妙在性观念上刻意表现自己的开放,其在爱情、性观念上价值的偏差与错位势必导致了最终孤独的命运。可以说,王安忆正是借妙妙在服饰、性行为等日常生活方面寻求现代性的悲剧命运,对80年代中国一味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进行了反思。保守的头铺街对现代性的盲目抗拒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坚守。
通过对1980年代日常生活与现代性错综复杂关系的多维叙述,1990年代的“80年代叙事”文本在对“80年代”的理解上更为多元透彻。尽管80年代在总体上是以现代化与启蒙作为时代标志,但却无法掩盖其内在思想观念的冲突与时代裂隙,“日常生活”是我们透视80年代转型时期复杂历史风貌的一个极佳视角。
二、冲突和调适:在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之间
一般说来,日常生活体现的是个体性、自主性与经验性的存在,而规范伦理则代表了社会化、强制化与理性化存在。可见,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既存在内在冲突,又有各自的活动领域与适用范围,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张力性的制衡状态。不过这种制衡也是以一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作为保障的,一旦社会关系出现异化,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可能被打破,导致个体日常生活的异化或社会规范伦理力量的削弱。因此,考察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的错综关系是透视特定时代社会关系与历史风貌的一个极佳视角。1990年代以来“80年代叙事”小说正是在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的冲突与调适中揭示了80年代新旧转型时期不同思想观念与文化理念的交锋。
1990年代以来“80年代叙事”小说对80年代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关系的考察是从对“文革”的回顾与反思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不理解“文革”期间个体日常生活的异化程度及其时社会规范伦理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改造与规训策略,就无法真正理解80年代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关系。因为在一定程度上,80年代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的冲突延续了“文革”的某些特征。郝东军《雁过留痕》尽管将叙事时间定位于1981年的一天,但其叙述的着眼点却是“文革”期间社会规范伦理对个体日常生活的监督与控制。这种监督与控制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在方式上,“文革”规范伦理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干涉更多是通过暴力、强制与镇压的形式存在,这与葛兰西霸权理论所强调的对意识形态的“赞同”与“认可”存在显著区别。《雁过留痕》中的村主任每次饭前都跑到别人窗户下监督人们是否吃了肉。吃肉这种个体日常生活行为被强制纳入“文革”规范伦理管辖的范畴内。二是在手段上,这种控制是通过将政治权力下放给特定的代理人,通过代理人的监督与管制加以施行。村主任正是这一社会规范伦理的化身。三是在程度上,这种代理人监督力量日积月累,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无意识层面,公开的外在的强制与暴力逐渐演变为人们潜在的内化的自我暴力。“文革”结束后几年人们还习惯性地将肉藏在饭下正是这种暴力强度的典型表现。由此可见,“文革”期间的个体日常生活受到极度压抑,吃穿等生活需要以及爱情、亲情等情感诉求一再遭受“文革”社会规范伦理的监控、挤压、遮蔽与抹煞。“文革”之所以选择不遗余力地监控与改造个体日常生活作为巩固其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手段,其原因植根于日常生活内在的文化规定性。而对个体日常生活的监督与控制也即是对个体自我人生意义与价值取向的控制。如果说“文革”期间是以社会规范伦理监控个体日常生活作为其统治手段,那么80年代的个性解放与人性启蒙也正是以个体日常生活突破社会规范伦理的监控为其发端、策略与表征的,而这正是1990年代以来“80年代叙事”小说的叙事着眼点。
“80年代叙事”小说中个体日常生活的突围是从摆脱社会规范伦理的制约,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念来独立安排自我的日常消费开始的。像牛仔裤、卷发、蛤蟆镜等已然成为个体彰显自身文化个性,叛离社会规范伦理的象征。池莉《所以》中“我”的父母平反后托人重金购买了“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剥夺的手表和自行车,这种自主性日常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尊严回归的象征。如果说这一日常生活消费行为的意义指向还不够鲜明的话,那么王蒙《青狐》写到主人公青狐买裸女画装饰房间而差点吓死僵尸式的继父这一叙事细节,则反映了个体自主性的日常生活向社会规范伦理的公然挑战。在“80年代叙事”小说中,个体总是“根据自我选定的价值体系自觉地安排自己生活”,也即是说,个体日常生活选择与安排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意味。然而“日常生活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的个性在其中活动的场所”⑤。个体借日常消费行为对社会规范伦理所进行的反抗只能作为起点,而不能成为其自身目的。因为这一日常消费行为一旦超过了自身的度,失去了必要的节制,则可能导致对个体自我的再度奴役。刘建东《全家福》中母亲因为一双皮鞋对父亲的背叛,象征着日常生活中物质力量与性的生命欲望战胜了伦理规范束缚和精神统治,父亲的中风正是这种束缚与统治崩溃与解体的标志。然而这一日常生活的反抗却有其自身限度,喷涌而出的无节制的日常生命欲望则可能造成新一轮的社会悲剧与人性悲剧。
“80年代叙事”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呈现个体日常生活挑战社会规范伦理,从而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80年代个性解放与人性启蒙进程,而且还能够由此进一步批判80年代社会规范伦理对个体日常生活的监控与压迫,并展现转型期的80年代新旧杂陈、举步维艰的历史风貌。毕飞宇《玉米》中有这样戏剧性的一幕:校长拿着大剪刀剪学生的喇叭裤脚。这一细节可以看作是对“文革”期间社会规范伦理监控个体日常生活的反讽性回应,同时也影射了80年代反对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某些侧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反映的“文革”式的社会监控在1990年代以来的“80年代叙事”小说中并不多见,更多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监控已经放弃“文革”式的暴力与强制形式,而采用更为隐蔽的软暴力形式加以实施。当然,这一叙事比例大体上也正符合80年代的社会监控方式比例。这种隐蔽的软暴力是借助社会规范伦理与政治权力的合谋达成的,这一合谋使得社会规范伦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而政治权力又被赋予强烈的伦理规范色彩。个体日常生活在社会规范伦理与政治权力的双向夹击与挤兑之下逐渐丧失其独立存在空间。王成祥《猪油飘香》中作为八岁的孩子的“我”与父亲关于偷吃猪油所引发的冲突,在本质上便是个体日常生活自主权利与社会规范伦理与政治权力执行者之间的冲突。较之《猪油飘香》侧重于叙述政治权力对个体日常生活的剥夺,艾伟《爱人同志》则将叙述重心移位至社会规范伦理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控制。张小影对截瘫英雄刘亚军的照顾,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与受刘亚军男性魅力的吸引,融合了特定的个体体验。然而其时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和军队需要这样典型的浪漫的美丽故事来安慰前线牺牲者的家属和负伤的官兵,于是张小影就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一美丽的政治谎言中,受其摆布。而且这种社会伦理规范逐渐内化,成为其自觉自愿的选择。
三、时代的错位与“日常生活叙事”的局限
1990年代以来“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小说,由于既有利于人们考察“日常生活”与现代性进程的多维关系,又可以藉以观照80年代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规范伦理之间的复杂联系,对我们重新认识与理解80年代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它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凸现了80年代的时代特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在凸现80年代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对80年代的遮蔽与扭曲。尽管《长恨歌》、《母鸡生活》等“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通过日常生活展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与文化风貌,但无节制的日常生活流的恣意流淌与泛滥却冲刷了时代非日常生活的精神性层面。如果说这种泛滥的日常生活叙事在叙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90年代时还具有相对的自足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将其运用到对具有相对精神至上倾向的80年代历史时,其偏执性是显而易见的。表面化的日常生活洪流、感觉化的叙述,挤压了人性、情感、心灵等精神性领域,进而遮蔽了80年代的时代文化意义。
比上述更常见的一种“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时代错位表现为剥离80年代“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意义,而以90年代欲望化的日常生活代替“80年代”的“日常生活”。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首先是部分作家的叙事惯性与避重就轻的惰性。对当下生活的叙述可以依凭一定的生活经验积累,而对历史的叙述则要求作家既要有对历史精神的把握与对历史细节的细致考察,又要求作家具有丰富的历史想象力。这两方面的匮乏往往导致一些作家以90年代的日常生活经验代替对80年代日常生活的叙述。其次,这种以90年代欲望化的日常生活代替80年代“日常生活”的“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文本的出现,也与90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背景不无关联。消费文化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具有平面性、具象性与感官至上性等特征,最大限度地剥离与抽空日常生活丰富性的精神内涵,最大限度地还原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与物质性是消费文化影响下“日常生活叙事”文本的典型特征。莫言《丰乳肥臀》中80年代叙述部分对80年代历史缺乏整体探究兴趣,只是津津乐道于上官金童对乳房的畸恋上。这种以欲望叙述代替丰富复杂的日常生活全部内容的叙述极有可能造成日常生活的异化和对精神层面的挤压。与《丰乳肥臀》对时代把握的乏力相似,余华《兄弟》对80年代的把握显示出一种有意淡化其时代特征、模糊时代背景的不自信。小说中支撑整个80年代叙述的仅仅是李光头、宋钢和林红的爱情纠葛以及李光头的残疾人工厂的兴盛,叙事流程很快就从“文革”叙述转移至90年代以后。应该说,小说的“文革”“暴力模式”和90年代“欲望模式”的简单化与抽象化叙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契合时代特征的,但是以“欲望模式”来完成对80年代时代精神的把握则明显远离“80年代”的精神实质。显然,这种对欲望化的日常生活无节制的展览,无疑是以牺牲与放弃对80年代社会现实的探索与深层人性的追问为代价的。
上述时代错位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创作竭力迎合读者的日常趣味,迎合市场的审美文化心理,其“日常生活”往往表现为一种被大众传媒与时尚所劫持的日常生活,既缺乏解构意识形态的文化功能,又丧失了其本体的自足的意义。
注释:
①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②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③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④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8-59页。
⑤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