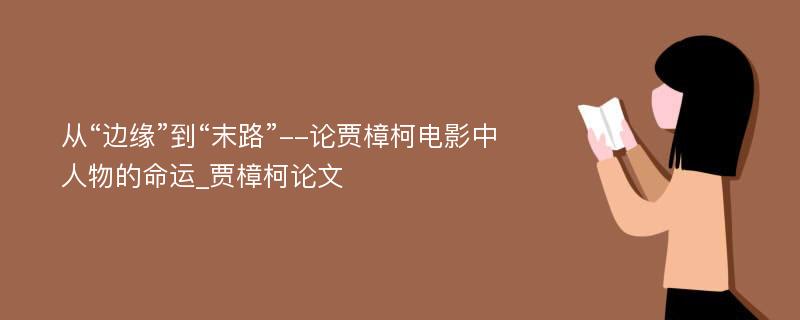
从“边缘”到“末路”——论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末路论文,边缘论文,命运论文,人物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09)01-016-06
从1995年开始独立电影工作起,贾樟柯已逐渐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评论界对其电影褒贬不一,但贾樟柯的电影却有着一如既往的个性追求与独立表达。他的电影镜头始终对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关照他们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态,并在颇具写实特征的叙事和影像中,展现出这些卑微的生命追求梦想、渴望自由的过程,以及个人微不足道的命运和惨淡的悲剧性。
作为二十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贾樟柯见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转型与变革。在时代的迁移与变化、以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底层世界的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世界”的“他者”,他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世界”,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与未来。
但是,这些被主流社会所遮蔽的卑微生命,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城市化的进程时,却表现出了对新生事物的极大热情,他们追随时代潮流,企图摆脱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渴望自由与成功;另一方面,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与变化,这些没有知识、没有资本而又追随潮流的小人物往往力不从心,无所适从,最终一无所获地回到现实面前。贾樟柯将自身的生命体验融入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边缘人物身上,通过这些被遮蔽的人群的生命状态和生活轨迹,来关注变革社会中这些卑微人物的生存际遇。
一、漂泊的青春与边缘的生存
贾樟柯电影中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另一类局外人,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艰难地生存着,在时代的变革中他们又迅速地被边缘化,“边缘化是当代中国很重要的社会现实,它是将大量的原来很主流的人群变得非常边缘,比如工人。”[1]贾樟柯见证并感受着这种变迁,同时也是出于对卑微若草芥的普通小人物的悲悯情怀,所以他的电影真诚地记录着这些边缘小人物的追求和迷惘、泪水和欢笑、梦想和绝望。他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2]
从“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到《世界》、《三峡好人》,贾樟柯影片的人物无一例外的都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被朋友、亲人抛弃的小偷,四处走穴的文工团演员,下岗待业的小混混,居无定所的野广告模特,来到大城市打工的乡下人……在被重构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居于社会的底层,既承担着现代性的代价,同时又对这个现代化的世界充满了渴望与梦想。在贾樟柯的每部影片中都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使偏远的小城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洗衣机和电视机进入普通百姓家,县城里到处林立的歌厅与录像厅,年轻人被裹卷进以流行歌曲为代表的流行文化中,曾经熟悉的建筑物正在被拆迁等等。面对变化着的周围的生活环境,他们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外面的世界几乎是自由与梦想的代名词,所以从小武到韩三明,这些社会边缘的漂泊者都在梦想着离开故乡,做着故乡以外的“世界”的梦,但是,他们试图挣脱现实的努力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要么无功而返,要么一败涂地。
作为与主流职业相对立的职业小偷,小武一直游荡在社会的边缘,寻找着自己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小武昔日的好友小勇从小偷转变为成功的商人,为了自己的颜面,结婚时拒绝小武的到来。而自己付出真情的女朋友为了更好的赚钱机会却不辞而别;回到家中又遭妹妹的嘲笑和父母的责骂,最终被家人赶出家门的小武无奈地回到县城继续流浪。不断地追求而又不断地被抛弃,小武渐渐丧失了所有的希望,最终暴露出了悲剧的真面目。小武在最后一次偷窃中,因传呼机响起而被捉住,被铐走的小武引来了周围观众的围观,成了另一种示众的对象,而此时小城上空的广播中在反复宣布着“严打”的消息,对于“二进宫”的小武来说,等待他的恐怕将是长期的服刑生活了。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在改写着社会阶层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小武来说,小勇、女朋友胡梅梅成了永远可望不可即的现代化的美梦,他的悲剧也是这个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
如果说《小武》还是一个人的悲剧的话,那么《站台》则是群体寻找梦想的失败了。贾樟柯在介绍《站台》时也称,这是一部非常悲观和宿命的电影。[3]131~134
在《站台》中,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等是县文工团的年轻演员,刚刚从“文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思想中走出来的他们,又在改革年代里因文工团的迅速衰落而被承包了出去。年轻的他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为了生存,他们便开始了闯荡江湖、四处走穴的漂泊生活。当他们带着青春的骚动和自由的梦想,高唱着《啊,朋友再见》,并向着外面的花花世界走出了汾阳古城的城门时,这帮边缘青年并没有追寻到自己向往已久的自由世界,而是来到了比汾阳更闭塞落后的农村或矿山演出,完全变成了观众面前的卖艺人。尽管他们努力适应时代的变化和满足观众的要求,但观众回报他们的只是扔到舞台上的垃圾与恶作剧,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最终只变成了对荒野外火车(现代化与外面世界的象征)的追逐,而快速奔驰的火车鸣着汽笛驶向了远方,把他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万般无奈下,他们只好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尽管他们多次反复通过汾阳狭窄的城门,但最终还是没能够摆脱这个地方,影片中的人物最后都不得不告别自己的幻想回到自己的家乡,过着循规蹈矩的庸常的生活。影片结尾处,尹瑞娟抱着孩子,水开后的水壶发出火车汽笛一样的尖啸声——这曾经是激起他们渴望远方世界的声音,也是丢弃他们继续向前奔跑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声音,而此时的崔明亮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在混合了压抑与梦想的追求中,这些文工团的年轻成员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除了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失望和打击,就是无奈地在“世界”的边缘上游移和飘荡。影片以这些年轻人的遭遇质疑了所谓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感召下,社会为每个人制造了很多现代化的美梦,可当现代化真的来临时,它似乎又总是在绝大多数人触及不到的地方。
《站台》在“期望”与“失望”之间描绘了时代历史的变化和无名小卒们追求而不得的悲哀和虚无,这种追求不得的悲剧命运在《任逍遥》中依然延续着,只是在《任逍遥》中,斌斌和小济以更加决绝的姿态来追求他们想要的梦想与自由时,他们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因而也续写了他们原本就已边缘化的悲剧命运。
斌斌和小济是大同这座破败工业城市街头的小混混,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要么骑摩托车在路上飞奔,要么去火车站的候车室茫然的消耗时间,尽管斌斌与小济既没文化又无资本,但他们却对外面的世界有着不可遏制的渴望与无限的向往。斌斌幻想着通过参军而远离故乡与母亲无休止的唠叨,但因被查出患有乙肝体检不合格而梦想破灭,他的女朋友也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而与其分手;小济一直梦想着去抢银行:“我要是生在美国,遍地是钱,我早抢劫了。”在发财梦的挑逗下和幼稚的冲动下,这俩贫穷无知的边缘少年上演了一出模仿黑社会“英雄”抢劫银行的可笑闹剧。带着手铐的斌斌站在警察局里接受审讯,此时的他面无表情的唱起了“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这是悲伤疲倦的现实与单薄卑琐的愿望之间遥远的间隙。他的同伙小济也因抢劫银行未遂而仓皇逃窜,他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与“逍遥”无关了。
“任逍遥”原本是斌斌、小济、赵巧巧等边缘青年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小济与赵巧巧甚至在自己的胳膊上刺了一只象征“逍遥”梦想的蝴蝶,但在他们的现实世界里,庄子的“逍遥游”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完全成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情境。因现实生活中不断被抛弃,加上内心无法释怀的茫然与精神的空虚,这些幻想逍遥自在的边缘青年不仅离主流、庄严与自由越来越远,而且最终连未来的希望甚至未来本身都已完全丧失了,这就是他们最终被抛弃、被断绝的悲剧宿命。斌斌与小济等人的悲剧是边缘小人物在这个时代茫然失路的绝望喊叫,也是对所谓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反驳。
二、外面的世界:无法企及的美梦
如果说,“故乡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只是在小县城中做着挣脱现实、追求自由的美梦,那么,《世界》中的赵小桃与成太生等人俨然已踏上了去大都市寻梦的旅途,但大城市完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自由天堂,在这里甚至比小城镇更加难以生存。在《世界》中,贾樟柯将主人公放在了世界公园这样一个表面繁华而内在封闭的虚拟的“世界”中。世界公园既是一种真实的场所存在,又是一种伪造的真实。世界公园中坐落着微缩版的世界名胜建筑,从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再到美国的“世贸大厦”等世界著名景观一应俱全,在世界公园里,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机械复制时代的诸多产物,但那只是虚拟的辉煌。虽然“不出北京,走遍世界”、“一天一个世界”等广告词充满了虚拟的自豪和对“世界”的渴望,但在世界公园表面的繁华背后,是赵小桃与成太生等“汾阳来的人”的艰难生存与卑贱人生。逼仄潮湿的地下室旅馆、肮脏破败的小餐馆,简陋拥挤的裁衣店,荒芜杂乱的建筑工地等场所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环境。舞台上的赵小桃们身着鲜艳的异国服装,在美仑美奂的灯光中翩翩起舞的场面,不过是他们给游客提供的繁华的享受,而他们本身却只是这种繁华的背景,或者是这种繁华的成本。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透出“世界”中的人们的无奈与茫然,正如影片中意大利斜塔前走过的那些背着铺盖卷一脸茫然的民工。相对于整个时代来说,来大都市寻梦的这些边缘人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因为在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的背后,真实地存在着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而且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是痛苦压抑、失落无根的边缘生存状态,以及被时代与历史放逐的宿命。他们的命运正如贾樟柯所说:“世界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假的,不存在世界,只存在角落。世界不过是一个想象,使我们把各种各样的生活状况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假想空间,而我们本身并不生活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只生活在角落里。”[4]186的确如此,赵小桃和成太生并没有生活在“世界”里,而是逐渐地被边缘化到了世界的角落里。彻底绝望的赵小桃与成太生在煤气中毒生还后,赵小桃问道:“我们是不是死了?”“没有,我们才刚刚开始。”痛苦漫长的人生路,他们才刚刚开始,虽然肉体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而内心的希望与自由抑或内心的“自我”已然死去。
在“故乡三部曲”与《世界》中,以小武们为代表的这些边缘小人物曾经对生活有过幻想与渴望,他们努力追逐过外面精彩的世界,尽管最后都一败涂地的回归原点,但至少他们曾经有过梦想。而到了《三峡好人》中,沈红与韩三明对生活似乎已经没有自由的幻想与追求了,他们要寻找的只是他们曾经丢掉的东西。从汾阳来到奉节的沈红和韩三明,一个是要寻找两年未归的丈夫,一个是寻找十六年前走掉的妻子和女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寻找的只是生存层面的感情与权利,因为家庭和情感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归属单位。跟随着他们两个人的寻找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和小武一样在黑道上谋生的小混混,可以看到和斌斌一样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也可以看到因拆迁而造成生活发生巨变的形形色色小城居民。这些边缘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因县城的拆迁而变得更加艰难,同时,影片也把一个和汾阳相隔万里的小城——奉节,同样融入了见证历史文化变迁的电影铭文之中。
沈红与韩三明最终的寻找结果虽不一样,但相同的是,在他们执著寻找的背后都透出了一种无言的痛感,都体现出了一种悲凉与无奈。沈红在得知自己丈夫有外遇的情况下,在江边与丈夫相拥之后宣布自己已有外遇,因此决定结束自己的婚姻,沈红用一个谎言挽回了自己最后的可怜的尊严,但也因此陷入了婚姻破裂的尴尬处境。韩三明的寻找结果看起来似乎是个圆满的结局,因为妻子麻幺妹决定和他复婚,但条件是他要替妻子还清三万元欠款,韩三明要用一年的时间到如走钢丝般危险的黑煤矿中赚钱以赎回妻子。去黑煤窑赚钱是以生命为注的赌博,用韩三明自己的话说:“早上下去不知晚上能不能上来。”但是他必须坦然地面对现实,显而易见,去黑煤窑是韩三明救赎妻子的唯一的有效方式,是一条为了生而接近死的生存之路。最后,韩三明带领奉节的其他工友一起去往了山西,更多的边缘人为了生存而加入了更为辛苦危险,并弥漫着死亡阴影的谋生之路。所以,尽管韩三明寻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妻子并决定复婚,但复婚的路程却充满着荆棘,在艰难、危险的筹钱路上,韩三明的命运我们无法预知。影片结尾处,韩三明抬头看到了远处高空中有人在表演走钢丝,与此同时,影片中响起了川剧《林冲夜奔》中的悲凉唱腔:“望家乡,山遥水遥;望家乡,山遥水遥……”这样的结尾也许正是对韩三明等人前途的一种暗示。
从小武到韩三明,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从开始追求理想与自由到最终的凄惨失败,每一个人的追求都因黯淡的现实看不到出路而失去了对生活的任何幻想,最后只剩下更加艰难的生存。他们难以逃脱的悲剧命运背后是源于转型期社会整体的结构性矛盾所致的某种必然,同时也解构了人们普遍认为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实现快速发展的神话,对于边缘小人物来说,是现代化的神话点燃了他们的所有渴望与梦想,但同时又是现代化的发展将他们更加无情的抛弃了,现代化的步伐带给个体的仅仅是高歌跃进的短暂狂欢,留给他们的则是长久的手足无措的阵痛,因此,小武们对梦想与自由的寻找最终成为一个无限延伸而又无从到达的旅程,从这一意义上说,贾樟柯的电影也通过这些边缘人物追求梦想的最后惨败对现代化救赎的可能表达了隐忍却有力的质询。
三、在逃脱现实中“落网”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在这种突然的、不期而至的剧烈变革中,都市变化与经济发展一跃成为整个国家生活的中心和重心,在这种情势下,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意义上都在被悄悄地逐出现代化的历史舞台,曾经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占据中心位置的“乡土中国”成为被现代化遗忘的空间。与此同时,文化消费的观念也正在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传统文明与现实秩序无法对接在一起。贾樟柯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这样表达过自己对当下中国的感受:“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5]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到因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兵荒马乱”的感觉。不管是在汾阳还是在奉节,在这些破败的小县城里都有着无数的舞厅、歌厅、发廊和台球等消费娱乐场所,狭窄的街道上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拖拉机一起在县城里横冲直撞,水果摊、台球桌在脏乱的街道上林立,临街老房子的墙上涂着大大的“拆”字,而空中的广播在不停地播放“祝您发财中大奖”的广告……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商品意识形态的介入与相对贫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透过这种张力,贾樟柯的电影在表现时代历史变化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在面对社会巨变时的精神痛苦与压抑。
在表现社会变化与时代变革时,贾樟柯将电影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以体现时代特色、营造一种“似真”的情景,同时,这样也使他的作品有着一种时代现场式的呈现,而主人公则充当着八九十年代时代现场的目击者或亲历者。首先,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会出现各种社会政治事件,并以此建立起小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如在《小武》中,空中到处传播着国家关于“严打”的消息。《站台》里刘少奇被平反的消息传遍汾阳荒凉的街头,建国35周年的天安门阅兵仪式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在《任逍遥》里也出现了法轮功、中美撞机事件、成功加入WTO、申奥成功等社会事件,《世界》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大城市的艰难生存,《三峡好人》中的移民工程等。另外,贾樟柯的电影镜头也凝视着在当代中国巨变背景下小县城的变化:破败不堪的小县城街头有了喧闹不止的录像厅和卡拉OK厅,街道上摆着台球桌,两边林立着温州人开的发廊,而小县城里的人们也开始哼起了流行歌曲,留起了新潮的发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却在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并必将对小县城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时代便是商品经济时代与传媒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迅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处于社会边缘或者底层的小人物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从而产生了一种社会情绪即“顿失感”,这种“顿失感”指的是在突然的、不期而至的变革中,人们心理上突然感受到一种失落、无奈、困惑、迷茫和无望,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所产生的感觉表现出的是一种眩晕感,这如同一个人从长期的黑暗中一下子走到阳光下,感受到的不会是光明和晴朗,而只能是痛苦的眩晕。这种痛苦的眩晕主要表现在主人公在遭受打击后的情绪上。小武当年共患难的“哥们”靳小勇如今转变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小勇在结婚时故意遗漏了小武,但小武却依然信守着当年的承诺,而小勇不仅早已忘记了所谓的承诺,还因为怀疑钱的来路不明而退回了小武的结婚贺礼,自尊心备受打击的小武只能在卡拉OK厅猛灌假喜酒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无奈与自卑,从而也渐渐地暴露出了他可怜的、悲剧的真相。在《站台》中,刚刚从悠长的革命隧道中走出来的崔明亮们,又面临着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商品社会,他们像被驱赶一样再次被卷进了新时期和新的价值标准中,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形势,他们又像被丢弃在路边的垃圾一样微不足道而又不知所措。小济和斌斌被“美元”激起了发财的欲望,最终成了一对极不像样的银行强盗,最后以抢劫犯的结局为自己的发财梦画上了句号。《三峡好人》中的小马哥为了哥们义气而命丧黄泉,这倒是应了他对韩三明说的那句话:“在奉节,现在哪还有什么好人哪!”奉节作为一个处于拆迁中或者说即将消失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城,与生活在这里无人关注的边缘人群之间建立起了某种隐喻性的关系,这也正如小武的朋友更胜在被迫搬家时不无抱怨地说道:“旧的是拆了,新的又在哪儿呢?”更胜无奈的问话反映出的正是商品经济社会到来时给小武们带来的无奈、尴尬与痛苦的眩晕。
如果说商品经济大潮的到来使小武们感到的是无奈、尴尬与痛苦,而且使他们更加边缘化了,那么传媒时代的到来似乎点燃了他们曾经失落的希望,但是,面对传媒给他们制造的幻想,他们不仅没有触及到自己想要的自由与幸福,反而从“边缘”走向了“末路”。
正是电视传媒的传播,把社会在剧烈变化中的各种信息、各种各样的声色光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人们的视野和生活中,使边缘化的小人物沉浸在“与世界接轨”的神话中,《站台》里的边缘青年追逐火车的场景正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微妙寓言,《世界》中微缩的世界公园更是全球化话语的变相表述。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被隔绝在“世界”的生活圈之外,而只活在当下的世界里,在这个当下的世界里,他们面临着生存的压力、生活的困惑和情感的纠葛等众多问题,即大众传媒所制造的现代化神话与边缘人物的实际生活方式之间发生了错位。现实生活不断地被电视传媒所虚构的现代化神话重构与解构、消费与消解,对他们而言,现代化所给予的进步许诺、发展前景如果不是苍白的谎言,至少是意义全无的空话。贾樟柯曾经说过:“比如说现在那里(汾阳——引者注)十七八岁的孩子,比咱那时候还痛苦。因为变化没多大,就多了几个宾馆,县城该多大还多大,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没有煤气,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自来水。但跟我们不同的是,传媒却已很发达,他在家能看Channel V,每天看卫视,全是特别时尚的东西。然后一出家门再看自己的环境,他收到的信息,收到的倡导的生活方式,描绘的理想世界和他眼睛里头的反差太大了。”[6]对于生活在县城的小武们来说,大众传媒所极力宣传的现代化非但不是一种有力而有效的救赎,非但不是一个将临未临、令人无限憧憬的共同梦,相反,它只作为他们遥远的梦想与理想的对象而悬置着,唤起的是名目更为繁多的欲望或欲望的代偿方式。他们努力挣脱现实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的道路,因为曾经的生活已割断,而新的生活又没有起点,没有衔接的断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失败的孤独的身影。正如《任逍遥》中,电视中传出了因高速公路的修通,大同离北京缩短到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但是我们又看到另一怪异的景象: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的高速公路,到了大同的外围就突然停在了一个泥堆面前,断开的公路四周是空旷的土堆和远处的荒山,而骑车走来的小济在断裂的公路处停止了前进的脚步,这正是对小武们命运的一种巧妙暗示:他们断裂的人生之路已无处连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正如赵巧巧走过来的那条被切断的柏油马路。这是小武们痛苦的根源,也是他们最终被抛弃、被断绝的宿命的原因。
贾樟柯的电影正是通过以小武为代表的边缘人物或者飘忽不定的游荡生活,或者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努力挣扎与抗争,最终却以凄惨的失败而告终的悲剧命运,表达了对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但又找不到未来出路的普通人群精神与生存状态的关心,以及对当下中国广泛的普通民众命运的喻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以小武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物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被淘汰、被抛弃的悲惨遭遇,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他们内心的茫然、痛楚与绝望。
四、结语
从“故乡三部曲”到《世界》,再到《三峡好人》,贾樟柯的电影以现实主义的审美观追求“现象还原”,追求真实的个人表达,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并述说了边缘人物在人类基本生存层面上艰难“活着”的生存状态,“让云层之下小人物的心酸与苦难得以普照阳光”[7](251),正是贾樟柯的这种美学追求与知识分子良心,使他的影片具有了一种强烈的平民精神。虽然我们不知道贾樟柯以后的创作道路和特点将有何变化,但通过他的“故乡三部曲”、《世界》以及《三峡好人》这几部作品,我们至少可以得知,对底层社会卑微生命的关注是前贾樟柯电影表达的核心与艺术灵感的来源,我们也期待着他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追求自己的艺术“世界”。
收稿日期:2008-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