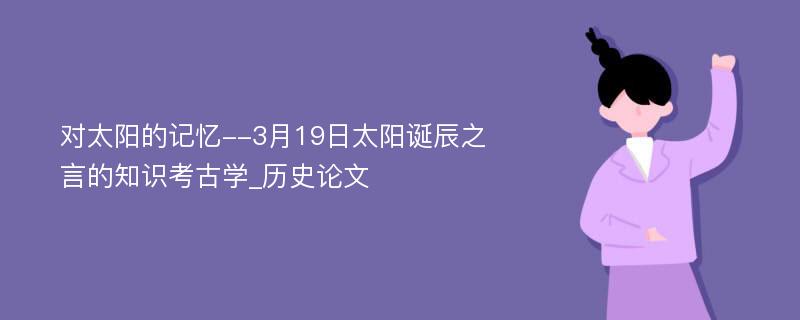
太阳的记忆——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的知识考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阳论文,诞辰论文,话语论文,记忆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楔子:甲申三月十九日
明崇祯甲申十七年(1644),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时代的序幕拉开了。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大军攻入北京城,包围了崇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十九日,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死。约一个月左右,崇祯帝死亡的噩耗在江南地区广泛传开,群情激动。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之职。而此时的北京正巧二度易主:满族皇帝成了紫禁城的新主人。在其后近20年的血雨腥风里,晚明虽然在南方先后建立了弘光政权、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等,但是在清王朝的武力征服下,这几个政权相继覆灭,其残余势力惨淡经营的“反清复明”斗争也云消雾散了。
一棵遭遇电击雷劈的老树即使时过千载,年轮上也会留下斑斑痕迹。在历经如此巨大的政治变动后,汉族社会是如何记忆前朝历史的?三月十九日作为崇祯帝忌日,是一个可资考察的象征符号。有关东南沿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台湾的历史学和民俗学研究表明,在明清交替之后,三月十九日被改篡为太阳诞辰,太阳诞辰的创造蕴含着纪念崇祯帝之死的意味。
较早关注三月十九日这个特殊日子所内涵的象征意义的是历史学者翁同文。翁同文在30年前撰写的天地会研究的论文里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基于“反清复明”的政治需要,天地会创造了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神话。第二,天地会之所以把崇祯帝的忌日说成太阳诞辰,乃是因为天地会有以“忌辰”为“诞辰”的传统[1]。翁同文的第二个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证实,而前一个观点则有商榷的余地。因为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话语的出现在先,天地会的出现在后,与其说天地会创造了这个象征符号,毋宁说天地会利用了这个象征符号。近年,历史民俗学学者赵世瑜与他的合作者依据地方史料,考察了浙江地区的太阳诞生神话和习俗。他们认为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神话与浙江抵抗满清征服的地方历史密切相关,是一个地方性的话语,其中凝聚着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2]。
多年来,笔者在研究民间秘密结社和浙江地区的民间信仰时,接触到不少关于“反清复明”和太阳诞辰话语的史料,一直试图解释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忘却。上述两项研究,特别是赵世瑜等的研究征引甚丰,笔者读后受益匪浅。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侧重面之不同,在对文本的诠释上,笔者与上述几位研究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自然,所得出的结论也颇多不同。本文作为笔者研究心得的一个初步报告,试图以公共记忆为中心讨论围绕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discourse)的几个问题。公共记忆(collective/publicmemory)有地域、文化、组织、阶层、年龄、少数族群和民族等之别,太阳诞辰三月十九日公共记忆的主体是谁?公共记忆是如何创造出来并被文本化的?太阳诞辰话语里凝聚着记忆主体怎样的历史记忆/忘却?一言以蔽之,本文意欲对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进行“知识考古学”(Lárchéologiedusavoir)式的研究。
二、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创造
崇祯帝之死使春夏之交的江南显得与往年大不一样。五月三日,监国福王发布丧事消息后,各地纷纷举行悼念活动。在苏州,大批士民自发地来到府学明伦堂,从五月九日到十一日,连续三天举行哭庙仪式(注:参见岸本美绪:《崇祯17年の江南社会と北京情报》,载《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164页。)。对江南的许多士民来说,三月十九日是一个痛失君父的日子。
很多迹象表明,在崇祯死后的第二年,三月十九日即成为纪念崇祯之死的日子。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就任帝位,建立了弘光政权。弘光政权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小朝廷,许多官僚很快就把为君父报仇的念头置诸脑后,“士大夫辈但以得官为荣,而不以失义为辱”[3](p.343)。弘光元年(1645),在崇祯周年祭即将来临时,部分不满现状的官僚和士人试图借助悼念崇祯来唤起弘光政权的危机意识。起先,翰林院编修张星“以寒食届期,请遥祭诸陵及先帝”[4](p.371)。正当礼部议而未决之时,南京城内外出现了许多揭帖,称:“端阳竞渡,吊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子推也;三月十九为先帝后衔愤宾天之日,攀髯莫及,吾辈各于郊外结社酹酒,以志哀恨。”[4](p.371)张星的上疏和民间的揭帖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二者共同营造了三月十九日祭奠崇祯先帝的舆论。接着,太常少卿张元始“感其言”,立刻上疏,建议弘光帝除允准在太平门外设坛祭奠崇祯帝,并且还应祭奠死难的东宫皇后和定王、永王二皇子,将三月十九日固定为一个国家性的纪念日。[4](p.371)
三月十九日过后不到两个月,刚满周岁的弘光政权便迎来了自己的末日:五月十五日,清军攻陷了南京城。弘光政权不再,但由这个政权开创的官方设坛祭奠和民间“结社酹酒”的仪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三月十九日作为一个记忆符号,从此,不仅为后继的晚明政权、特别是民间“忠义之士”所承袭,而且,在忍受和抵抗异族征服的岁月里,还被赋予了“反清复明”的内容。
那么,崇祯忌日何以能被改篡为太阳诞辰?《礼记·祭义》载:“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民族学学者何星亮称:“每个朝代都在一定日期在东郊日坛祭祀太阳”,“祭日的时间和牺牲,则历代不尽相同”[5](p.180)。明代的祭天礼仪继袭了唐宋的传统,在“大祀”、“中祀”和“小祀”中,日月和社稷的祭祀被置于昊天上帝和宗庙祭祀所在“大祀”之中,这与把对日月和社稷的祭祀放在“中祀”之中的唐宋和清朝相比,显示出明代更重视对日月和社稷的祭祀。在晚明的士人看来,崇祯皇帝之死乃是死于“社稷”和“宗庙”,日月同辉,自然对于他的祭祀应该沿用社稷/日月的礼仪。上述张元始的奏疏所言及的祭祀崇祯帝的礼仪就是祭日/社稷的礼仪:在南京城东郊的太平门外设坛祭祀。关于祭祀的情景,已经无法知悉。不过,还可以从1918年连横所撰《台湾通史》风俗志里捕捉到一些影子:“三月十九日,传为太阳诞辰,实则有明思宗殉国之日也。以面制豚羊,豚九头,羊十六头,犹有太牢之礼。往东祭之,帝出乎震也。家家点灯,欲其明也。亡国之思,悠然远矣。”[6](p.408)台湾民间在祭祀太阳诞辰时,以面粉制作猪羊代替牺牲,举行祭祀,看上去很像“太牢之礼”。按《礼记·王制》载:天子祭社稷时用牛、羊和豚三牲,谓之“太牢”。“祭日以太牢,祭月以少牢。”(《史记·封禅书·索隐》)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六记明朝祭日礼仪道:“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神向西。祭用大牢玉,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祭,祭服拜跪,饮福受胙。余年遣文大臣摄祭。”[5](p.181)
台湾的祭日习俗大概在晚明郑氏政权据守台湾的顺治年间即已形成,康熙年间郑氏政权覆灭后,该习俗由官方话语转化为民间话语,由含有哀悼崇祯之死的仪式转为暗喻崇祯之死的太阳诞辰节日,最后三月十九日的原初意味竟也从太阳诞辰节日里消失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民间祭祀太阳诞辰与祭祀其他神佛诞辰的仪式已经没有本质区别了。1919年,日本人丸井圭治郎在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中写道,台湾民间“不在乎不同神佛的区别,甚至只要是属意的神仙,都会给其设定一个生日,每年加以祭祀”。太阳星君是拥有生日并被祭祀的28个神佛之一,其生日在三月十九日。[7](p.28)
以虚拟的“太牢之礼”祭奠崇祯帝,在东南沿海地区似乎就是郊外“结社酹酒”。在晚明政权败亡和满清的政治压抑下,“结社酹酒”的集体祭祀已经很难实行了,对亡君故国的悼念呈现出个人化的倾向。光绪《鄞县志》记述了清初当地名叫纪历祚的文人的行状:“明亡,弃诸生作道人装,每年三月十九日,以麦饭泣奠思宗。或问:草莽臣而祭天子礼有之乎?答曰:此所谓野哭者也。”[8](p.9)这位不忘前朝的纪先生着道装、备饭食、在野外哭祭崇祯的形式,不同于“结社酹酒”或“太牢之礼”(“三献礼”),是另一种祭祀仪式。由于记忆主体和外在环境之不同,三月十九日的祭祀仪式不可能是单一性的,必然具有复数性的特征。据赵园对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明清易代之后,在“新朝”的统治下,有不少“遗民”保持着对“故国”祭祀习惯。钱谦益在《书南城徐府君行实》记徐氏:“南渡日,弘光改元,岁时家祭,称崇祯年如故。嗟乎!称弘光犹不忍,况忍改王氏腊耶?”[9](p.386)曾仕晚明隆武政权的黄见泰在明亡后,“家设襄帝位,朔望朝拜,以木板为笏,跪读表文,声琅琅彻于户外,人皆怪之”[9](p.386)。
至此,崇祯忌日如何转化为太阳诞辰节日的真相似乎就要揭开了。但是,问题还远远没有穷尽。如果进一步阅读东南沿海流传的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记载,我们很少看到上述亦儒亦道的祭祀内容,相反,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证明太阳诞辰话语依托于民间佛教语境。阅读有关文本,令人强烈地感到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话语乃是从民间佛教中创造出来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征引两个民国年间修订的地方志的记载。一个是浙江省定海县的例子,一个是江苏省嘉定县的例子。《定海县志》方俗志载:“三月十九日,各寺庙设醮诵经,相传为明朝国难日,讳之曰太阳生日。俗传《太阳经》,太阳明明朱光佛,三月十九午时生,家家户户点红灯等语,朱即明之国姓也。”[10]上述文字告诉人们,纪念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既不是“野哭”,更不是于东郊设坛“遥祭”,而是在定海“各寺庙”举行的,人们把崇祯之死的“国难日”称为太阳生日,而这个习俗来源于一个名曰《太阳经》的文本(后文将专门论述)。再看与浙江比邻的江苏省嘉定县(现属上海市)的例子。《嘉定县志》风俗志载:“三月十九、四月初八、九月十九等日,往往于社庙诵经,有焚纸扎之船者,谓之化莲船,又称做佛会。每年亦有醵资雇航赴杭州拜佛,谓之朝山进香,一日吃斋。此唯妇女有之,男子绝少。最虔者蔬谷纯为淡食,谓之吃淡斋。其次终身不食动物,专茹蔬谷之类,谓之吃常斋。”[11]与定海的例子不同,这段话只字未提三月十九日与崇祯之死的关系,呈现出来的是一幅善男信女(主要是妇女)按照既定的民间佛教时间去当地的社庙或者杭州灵隐寺上香诵经,“佛会”追忆的对象未必就有崇祯的影像。因此,在这里,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节所内涵的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记忆,不如说是对历史的忘却。
本来,在民间太阳神崇拜里存在许多关于太阳诞辰的神话。其中最为流行的太阳诞辰的说法是,太阳二月初一日生(北方)和冬月(十一月)十九日生(南方)。民俗学的研究证实,在太阳生日这天,北方和南方一些地区的民众都要设立香案,供上瓜果菜蔬和食物以祭祀太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崇祯十七年以前不见史书记载。该话语出现在民间例行的宗教节日中,说明在弘光元年(1645)南明政权按照儒家仪式举行官方祭祀的同时,士民中的善男信女也于同日在寺庙里举行祭祀活动。特别是,当清朝底定东南沿海后,面对满清残酷的压迫,一些不愿仕清的“忠义之士”怀念故国,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将三月十九日崇祯之死附会到宗教例行的活动中。民间奉之既久,习以为常,于是一个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生的神话便诞生了。徐时栋《烟屿楼文集》收录的《太阳赋》给这一推论提供了佐证。徐文道:
十一月十九日之说,盖出自道书,旧时吾乡未必不尔。诸先生欲愚僧道,想必有说以更正之,使舍汝而从我也(以上原文系小字——引者)。浸假而状其严,浸假而建之宫庙,由日及月,象形惟肖,惑众箕敛,奉事二曜故事,则会众而岁举,故国则无人而凭吊。后之君子,昧其本初,观其末节,叹斯礼之犯分,笑其期之区别。一知夫愚僧诈道之矫举,而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之碧血也。(注:徐时栋:《烟屿楼文集》卷38《太阳赋》,第12页。《太阳赋》一文亦收入戴枚修、张恕等纂《鄞县志》卷2,但徐文集中小字部分略而未收。)
撇开作者“欲愚僧道”之类不着边际的言词,结合《太阳赋》的前后文可知,鄞县原有太阳十一月十九日诞辰的传说,乃是明朝遗民为怀念崇祯帝而把太阳生日改纂为三月十九日。遗民们在创造太阳诞辰话语后,建立宫观,定期集会,使得三月十九日成为一个仪式化的地方宗教信仰。大约在顺治、康熙年间,这一宗教节日就已经成为该地的民间习俗了。对此,民间相习为常,从而忘却了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之事的本意:“故国则无人而凭吊”。因此,在一般人看来,该习俗荒诞不经,不过是“愚僧诈道之矫举”而已。
综上所述,晚明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了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创造,公共记忆凝聚着汉族社会对亡君和故国的怀念。他们在促使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宗教仪式化的过程中,动员了儒教和民间佛道祭祀文化的资源。太阳诞辰三月十九日之所以能被纳入民间宗教语境,无疑与东南沿海的民间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而《定海县志》称各寺庙祭祀太阳诞辰的习俗来源于一个名为《太阳经》的宗教文本,则促使我们必须考虑在太阳诞辰话语宗教化的过程中,除儒释道三教之外,是否还有民间宗教或民间教派介入其中?为此,有必要对有关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话语文本作一考察。
三、太阳诞辰话语的文本化
在浙江地区,流传着若干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太阳经》文本。这些文本大多经历了不断被创作的过程,有的不仅受到了清末排满革命历史的影响,甚至极可能是在民国年间才被创造出来的。笔者关心的是,不同版本的《太阳经》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让我们先看看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地区流传的《太阳经》的内容(以下简称杭本):
太阳明明珠光佛,四大神州照乾坤。太阳一出满天红,晓夜行来不住停。
行得快来催人老,行得迟来不留存。家家门前都行过,碰到后生叫小名。
恼了二神归山去,饿死黎民苦众生。天上无我无晓夜,地下非我没收成。
世间无我来行动,昼夜不分苦万分。太阳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红灯。
位上神明有人敬,无人敬我太阳星。有人传我太阳经,合家老小免灾星。
无人念我太阳经,眼前就是地狱门。太阳明明珠光佛,传与善男信女人。
每日清晨诵七遍,永世不走地狱门。临终之时生净土,九泉七夜尽超生。
务望虔心行到老,后世福禄寿康宁。[12](p.506)
为后文比较《太阳经》文本异同的方便,这里再把另一个在宁波慈溪流传的文本(以下简称甬本)抄录如下:
念念太阳经,太阳三月十九卯时生。太阳出来照四方,普照大地万物生。
一照东方太阳升,二照南海观世音。三照西方千重佛,四照北方地狱门。
东南西北都照到,风调雨顺国太平。有人念我太阳经,合家老小无灾星。
世上太阳最公平,穷不欺来富不捧。照在人间身上一样温。
世上若无太阳照,万物皆空化灰尘。善男信女来修行,修行先念太阳经。[12](p.507)
杭本和甬本只有一处内容一致:“有人传(念)我太阳经,合家老小免(无)灾星。”这两句话十分重要,是判断不同版本的《太阳经》是否存在内在联系的重要根据。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两个文本很容易发现,在两个文本中,太阳的形象完全不同:杭本太阳以第一人称劝说民众持诵《太阳经》,预言灾难即将来临;甬本则以第三人称感谢和赞颂太阳哺育之恩,呈现的是风调雨顺的景象。杭本对应的是一个非常态的时空,甬本则对应的是一个常态的时空。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杭本里的太阳孤寂而愤怒,象征着死;甬本里的太阳慈祥而公平,意味着生。因此,三月十九日这一符号在两个文本里隐喻的内容截然相反,杭本的三月十九日积淀了厚重的历史记忆,“太阳明明珠光佛”、“家家念佛点红灯”句中的“明”、“珠=朱”“红=洪”等提醒着人们,三月十九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但是,到了甬本,三月十九日所内涵的历史记忆早已淡漠,展示的是历史的忘却。就此,如果把两个文本置于清代历史的语境中来考虑的话,可以断定杭本早于甬本。
那么,杭本是如何形成的呢?前引《太阳经》都声称:“有人念我太阳经,合家老小无灾星。”这分明是在暗示末劫来临。有迹象表明,杭本和民间教派的宝卷不无关系。事情要追溯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乾隆三十八年(1773)初,清政府破获了一起横跨河南和湖北两省的白阳教案,在河南信阳州固始县教徒李元义家中起获一部《太阳经》抄本,河南巡抚何煟在呈报清廷的奏折中附录了该抄本,内容如下:
太阳经,太阳经,太阳出现满天红。家家门首都走到,道你众生叫小名。
天上少我无晓夜,地下无我少收成。个个神明有人敬,那个敬我太阳星。
太阳冬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天灯。朝朝每日念七遍,一家大小免灾星。[13]
令人惊叹的是,比较白阳教本《太阳经》和杭本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太阳诞辰不同之外,白阳教本《太阳经》共83字12句,几乎句句都能从杭本中找到影子!白阳教案横跨河南和湖北两省,传教者名叫朱洪(这一犯忌的名字,是否别有深意,容后再论)。河南巡抚何煟奏称,朱洪居住在湖北应山县广水地方,该地与河南信阳州接壤,信徒李元义等均为湖北人,“先后至信州地方佃种地亩为业”[14]。即是说,白阳教案发于河南,案头却在湖北。清廷追查到湖北后,时任湖北巡抚的陈辉祖奏称,朱洪的《太阳经》是其父口授的,其父朱子常“向诵太阳经咒,称可消灾致福,并贴诞异语句对联,以敬佛好善,可修来世”[15]。朱子常死于乾隆三十三年,所传习白阳教教派确切来源待考[16](p.348),在民间教派的传承谱系上,白阳教属于清茶门教系统。白阳教教主王忠顺直隶卢龙县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安徽天长县被捕,旋被处死,其信徒遍布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等地。白阳教既然可以从北向南由河北传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太阳经》也有可能随着白阳教教徒的足迹,辗转传至浙江。
但是,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嘉庆二十年(1815)八月,清政府在安徽和州破获的收元教方荣生案,让我们惊奇地看到了另一个与杭本更接近的《太阳经》文本。两江总督百龄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附录方荣生所藏经卷抄本,内里涉及《太阳经》的文字如下:
太阳出宫满山红,不紧不慢不省廷。走的紧了崔(催)人老,走的慢了不从容。
天上无我实难过,地下无我不收成。有我太阳来往转,有我太阳照乾坤。
不虔不净冲撞我,无称无呼叫小名。恼了二佛归山去,饿死黎民苦重生。
二月初一是我生,信心男女点明灯。有人传我太阳经,合家大小得安宁。
见了不传太阳经,眼前就是地狱门。[17]
在上述收元教文本里,太阳诞辰是二月初一,这既不同于白阳教《太阳经》的十一月十九日,也不同于杭本的三月十九日。但是,收元教本的内容既与40年前的白阳教本相似,更与流传至今的杭本雷同。方荣生是个野心勃勃的教主,曾派教徒在安徽、河南、江苏、江西和湖北等地散发反清匿名揭帖。八月案发后,方荣生被处死。从方生前的供词看,收元教信徒的足迹已经到达江苏江宁。如果收元教信徒顺江东下,不难辗转到达浙江。这是《太阳经》流入浙江的另一个可能的渠道。
至此,可以对三个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一小结了。其实,要比较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棘手的难题,即三个文本成书先后的问题。就三个文本发现的先后时序看,依次是白阳教本、收元教本和杭州本;从内容上看,也是越往后越详细,杭本可以说是白阳教本和收元教本的复合本。但是,民间教派的经卷不同于一般儒家经学著作,由于看不到原书全本,很难判断孰先孰后,对此暂且搁置不论。面对历史记载的局限所带来的无法穿越的障碍,作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笔者认为最迟在乾(隆)嘉(庆)年间,带有反叛内容的民间教派的《太阳经》已经出现在浙江地区了,在此前后,太阳诞辰三月十九日话语进入《太阳经》。反过来说,太阳诞辰由二月初一和十一月十九日被改篡为三月十九日一事,意味着民间教派参与了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再创造。《太阳经》中的太阳声称:如果看到《太阳经》,而不信太阳神的话,一家老小必会遭殃。面对汉族社会的历史忘却,太阳这一近乎恐吓的声音,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反清复明(汉)。
四、记忆/忘却的再生产
现在,本文面临一个尴尬的难题:清顺治二年,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了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及至顺康年间,该话语逐渐演化为地方民俗信仰,而隐喻反清复明的《太阳经》文本则是在乾嘉年间被发现的,其间竟相隔了100多年!这让人联想起围绕天地会(三合会)是否起源于“反清复明”的争论。但是,笔者不想把话题引入类似天地会起源的争论上,沿着本文设定的知识考古学的思路,笔者关心的是:在乾嘉之前的100多年间和之后的100多年间,三月十九日太阳诞辰所积淀的公共记忆/忘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经历了记忆/忘却的认识再生产呢?
当记忆的主体把对崇祯帝之死纳入太阳诞辰这一话语体系后,三月十九日即已在记忆历史的同时开始了其历史忘却的旅程。记忆主体——个人和组织的消亡,以及记忆在传承过程中的模糊是导致忘却的内在因素,而满清政治权力的介入则加速了历史忘却的进程。在满清统治稳固确立后,为了融合帝国内部的满汉关系,统治者不但对死难的前明官绅树碑立传,把记忆的对立双方纳入君臣之义的话语装置里而大加褒扬,还通过大修岳飞庙等举动淡化华夷/满汉之别,意欲在历史记忆上与汉族达成和解。于是,在200多年的漫长时空里,太阳诞辰话语展示的不是历史记忆,而是历史忘却。长生教徒陈众喜编辑的《众喜粗言宝卷》附录了一份年历,三月十九日,“太阳佛朝元,今讹传谓生日”。不止长生教这个异端教派在忘却三月十九日的历史含义,前引同治年间徐时栋作《太阳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大范围的乡土社会——鄞县历史忘却的光景[18](p.11)。鄞县位于浙江东部,清初曾对满清的武力征服进行过激烈的抵抗。但事过200年,对于三月十九日所负载的历史记忆,不仅谙熟乡里历史的老者不知道,地方史志中不见记载,而且在个体记忆中也逐渐流逝,以至“后世无传”。记忆的主体消失了。于是,当这个日子成为一群妇女信徒的宗教时间后,呈现出来的是形同实异的另一个三月十九日。
然而,三月十九日的历史记忆并非按照忘却的路径呈直线展开。满清帝国的强大和繁荣既非均匀地覆盖于整个疆土,亦非所有的个人和群体都能享受和认同帝国的繁荣所带来的恩惠。在三月十九日所凝结的历史记忆渐渐销蚀和淹没于帝国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也有极个别的个人与群体在进行记忆的抗争,三月十九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便成为支持政治抗争的“象征资本”(bienssymboliques)。持天地会创造太阳诞辰神话说的翁同文提到过康熙十六年蔡寅发动的起事。传说朱三太子是崇祯帝的第三子,在湖南进行抗清斗争,事败而死。清初发生过多起“朱三太子”案。据江日升《台湾外记》载:蔡寅在郑成功之了郑经从福建漳州败退至泉州时,假借“朱三太子”的名义,率领头裹白巾之众于三月十九日夜袭击清军驻扎的泉州城。不过,三月十九日在被作为记忆象征使用时,已经不再是原初追悼“亡君之痛”的含义,而含有了“反清复明”、恢复汉族江山的象征意义。这一变化说明三月十九日未必就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象征符号。事实上,明清易代后,在满族/清朝和汉族/明朝的对抗中,三月十九日早已为其他诸如宋、明、牛八(朱)、甚至十八子(李自成)等汉族历史符号所涵盖和替代。在前文论及的志在“反清”的白阳教里,传教人自称“朱洪”,是不是寓有“反清复明”之意?值得探究。因为在天地会内部流传着“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的口诀。“朱洪”一名还为不少反清复明秘密结社所使用。[19](p.104)因此,反清记忆主体的政治需要的变化也促使了三月十九日成为一个停留在过去时空上的“历史”,三月十九日之历史记忆不仅失去了记忆主体的支撑,同时也在失去其公共记忆的特性。
六十年一甲子。永历政权(1646—1661)的崩溃被一些人视为明朝的终结。在永历政权崩溃后整整四个甲子的公元1900年,中国历史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勤王”自立军起义被清王朝镇压后,大批亡命日本的激进知识分子转向“驱除鞑虏”的种族革命。240年前的历史记忆开始复苏,历史记忆的复苏伴随着霍布斯鲍姆(E.Hobsbawm)所说的“传统的创造”(inventionoftradition):通过一系列礼仪和象征来暗示自身与过去的连续性[20](Introduction)。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三月初,章太炎在东京发起成立“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意欲通过对甲申三月十九日的纪念来鼓动留学生进行排满。纪念大会预定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在东京上野的精养轩召开。章太炎的倡议得到了众多留日学生的响应,革命家孙中山也闻讯从横滨赶来参加。但是,在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的要求下,日本警察阻止了纪念会的召开。孙中山返回横滨后,与章太炎等在中华餐馆永乐楼里补开了一个“纪念式”。章在《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里写道:“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沉之祸,不远而复”。得知纪念会召开的消息后,香港的《中国日报》登载了宣言书全文,陈少白等还在香港永乐街举行了纪念会。据冯自由回忆,在东京纪念会受阻的前一日,有一个小插曲。章太炎接到日本警察署的传唤,在回答警察的询问时,章拒绝被称为“清国人”,自称是“遗民”(注:冯自由记录该事有若干文本,参阅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33—135页;秦孝仪:《国父年谱》(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增订本,第161—163页。)。
近代语境里的三月十九日记忆既不同于作为原初意义的“亡君之痛”的历史记忆,也不是“反清复明”里的“亡国之痛”的历史记忆,更不是作为民间宗教习俗的历史记忆/忘却,以往复数的、小写的历史记忆(historicalmemory)符号在被注入排满种族革命的内容后,被抽象为单数的、大写的历史记忆(HistoricalMemory)。因此,在精英知识分子看来,三月十九日固然是可利用的传统资源,却与流传200余年的太阳诞辰话语毫不相干。而且,正如悼念崇祯之死的三月十九日为反清复明(汉)所替代一样,三月十九日很快为种族革命的现实斗争需要所淹没。晚清革命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三月十九日这个日子,不如说三月十九日是否能唤醒作为历史记忆共同体的汉族的历史记忆。唯其如此,当复苏的历史记忆反照于现实之上时,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中获得了一席之地。笔者查阅过大量清代出版的江浙和台湾的地方文献,几乎所有的历史书写都对三月十九日讳莫如深。而在民国修纂的志书里,则大量出现有关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的记述。
五、缀语:甲申三百六十年
建构公共记忆的行为同时也伴随着忘却,忘却构成了记忆的一部分。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明朝皇帝崇祯自缢身亡后,东南沿海士民为了纪念这位生于忧患、死于战乱的君父,创造了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并假以儒家和佛道祭祀仪式表达哀痛。在满清铁骑席卷汉族社会和汉族士民奋力抵抗的过程中,甲申三月十九日的象征意义从为君父报仇逐渐转变为“反清复明”。当晚明士民将亡君亡国之痛的公共记忆附会为一个民间宗教节日后,三月十九日公共记忆便开始了其忘却的旅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记忆主体的一代代枯萎,三月十九日所凝聚的历史记忆从承载这个历史记忆的装置——太阳诞辰节日习俗中消失了。
历史虽然不可逆转,尘埃未必尽能落定。三月十九日记忆在丧失其公共性之后,仍然以个体记忆(individualmemory)的方式在民间社会存续。乾嘉年间,一些不满清统治的民间教派把三月十九日写入自己的《太阳经》中,试图以“太阳出现满天红”所象征的“末劫”来临,鼓动忘却太阳诞辰公共记忆的汉族社会起来反清。20世纪之初,这一公共记忆的再生产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反清排满的革命者通过纪念崇祯之死,把三月十九日置于民族—国家语境之中,并赋予其近代意义。而且,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中,三月十九日的历史记忆和太阳诞辰的宗教信仰在20世纪初久别重逢。
“甲申轮到他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1944年3月,正当抗日民族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剖明朝灭亡和李自成成败的原因。文末写道:“三百年了,民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民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21]《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被誉为“名震一时的文章”。何止“一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文被节选收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一代代学子耳熟能详的名篇。但是,无论是郭沫若的历史书写,还是我们对这一书写的阅读,所谓“民族的遗恨”——三月十九日公共记忆早已定格在遥远的历史时空,记忆/忘却的主体——相互对立的双方在被编入近代民族国家共同体(
nationalcommunity)后,通过想象和建构“我们”而拥有了共同的公共记忆(nationalmemory)。唯其如此,当“我们”即将结束寻觅太阳记忆的知识考古之旅时,蓦然回首,那刚刚聚合起来的太阳记忆重又化为碎片。
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六十周年,甲申轮到它的第六个周期了。
标签:历史论文; 弘光论文; 太阳论文; 崇祯论文; 崇祯帝论文; 古希腊论文; 历史故事论文; 历史学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