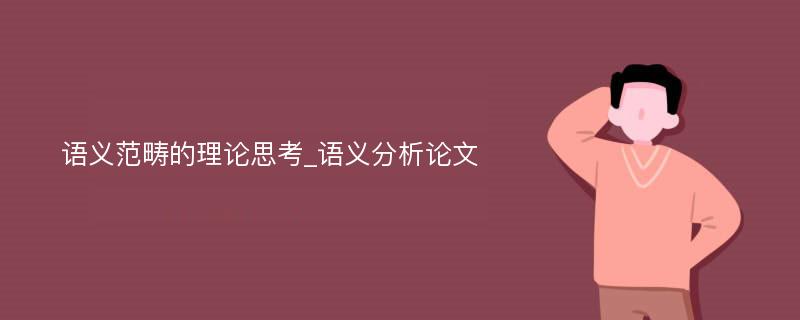
关于语义范畴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范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关于句法语义的研究方兴未艾,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和亮点。但是,具体的专题性的研究比较多,而有关的理论问题却还没有引起大家充分的重视。特别是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的关系、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以及语用意义的关系、语法范畴和语义范畴的关系,语义范畴的内涵以及内部到底有多少个类别,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的兴趣就是试图对这些重大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 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的关系
从汉语语法学一百多年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语法研究方法正好经历了从偏重意义,到偏重形式,再到形式与意义相互印证这一发展过程,而推动方法嬗变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引进的国外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跟汉语语言事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基本上是在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对汉语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照搬照抄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具体运用时就必然会产生不和谐的地方。矛盾是世界所有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创造性地修正、甚至改造国外新理论以试图解决理论与事实矛盾的过程中,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渐形成了几点共识:
(一)明确了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揭示语义的决定性、句法的强制性、语用的选择性以及认知的解释性,因此语法意义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陪衬,而是第一位重要,必须极大地强化。
(二)明确了语法研究的思路,既可以从语法形式入手,去寻找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也可以从语法意义入手,去探求语法形式的表现手法,这是个互为起点和终点的双通道。不存在哪一个优哪一个劣的差异。
(三)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相互验证。无论从哪一方入手,都应力求从另一方去得到证明或解释。否则,单向的研究都是缺乏科学价值的。
(四)由于汉语语法的特殊性,语法形式比较隐蔽,比较含蓄,比较特别,所以从语法意义入手去寻找形式的验证,似乎对汉语更加合适。句法语义应该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
什么是语法形式?什么是语法意义?可以说,对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过程是我国语法研究历史的一个缩影。
(一)对语法形式认识的深化
对语法形式的认识,从历史来讲经历了三个阶段:
1)20世纪初期,早期的汉语传统语法深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认为:语法形式就是词语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即从词形层面看到的“狭义形态”。这主要是指词形的各种变化、内部元音屈折和词头词尾。从印欧语看,这些都是不同词类的形态,而且与句法成分相对应,但汉语不是借助词形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的语言,如果固执地去寻找这类形态,最后必然发现,这类狭义形态,不但稀少,而且既没有普遍性、概括性,也没有强制性。这样的后果,就可能得出汉语没有词类、没有语法的错误结论。
2)20世纪30年代起,受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的影响,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促使语法学家们有意识地去寻找汉语语法的特点,方光焘(1939)和陈望道(1943)等认识到词语的结合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形态,并称之为“广义形态”。特别是50年代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语法形式的认识,把诸如虚词、语序、重叠以及语调、重音、停顿等这类汉语特有的形态也看作“广义形态”。
3)80年代以后,国外众多语言学理论陆续引入中国,在方法和思路上进一步打开了汉语研究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层次分析和变换分析方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广泛运用,特别是对歧义结构的分化,加深了人们对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关系的认识,很多学者(朱德熙,1985;邵敬敏,1988;胡明扬,1992)认识到语法形式不等于语法形态,形态只是形式的一部分,邵敬敏(1988)第一次在“显性语法形式”(包括狭义形态与广义形态)基础上,提出“隐性语法形式”概念(包括分布、组合、层次、变换等)。·
总之,对语法形式的认识经历了从“狭义形态”到“广义形态”的扩展阶段,再从“显性形式”到“隐性形式”的深化阶段。按照我们的理解,语法形式至少应该包括:
语音层面 词缀、元音交替、辅音交替、错根、停顿、
声调、语调、重音、轻声等
显性语法形式 词汇层面 虚词、重叠
句法层面 词类、词组、单句、复句、语序、重叠等
隐性语法形式 结构层面 分布、组合、层次、变换等
(二)对语法意义认识的深化
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表现某种特定语法意义的形式叫语法形式,通过语法形式才显示出来的意义叫做语法意义”(邵敬敏,1988),或者说:“只有语法形式表示的意义才是语法意义,只有表示一定语法意义的形式才是语法形式”(胡明扬,1992)。很明显,这是一种循环论证,但这种定义方式也显示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渗透关系、依附关系、相互验证关系和双向选择关系。关于语法意义的认识,目前主要是两种界定的方法:
1)从形式到意义的看法:由语法形式体现的意义就是语法意义,这是根据形式来界定意义。比如,早期传统语法认为由词形形态表现出来的“性、数、格、时、体、态”以及“有定、无定”等就是语法意义。随着对语法形式认识的扩大,语法意义的内涵也开始扩大,比如认为“施事、受事、工具、处所、时间、数量”等也都属于语法意义。
2)从意义到形式的看法:对词语的分布、语序、层次、组合等句法形式起决定作用的意义就是语法意义。这是根据意义对形式的决定作用来界定意义的。除了上述施事、受事、工具、处所、时间等之外,还包括动态性、自主性、可控性、有生性等。但由于语法意义内容复杂、种类繁多、主观性较强,因此目前学术界对其性质、特征、类别、层次等方面的认识还相当模糊,甚至连一些基本的概念,如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语用意义等都有不同的理解。
可见,这两种关于语法意义的界定方式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对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之间关系的两种不同角度的认识。从形式到意义,还是从意义到形式,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取向问题、难易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谁决定谁、谁是现象、谁是本质的要害问题。仅从研究问题的视角看,意义与形式之间似乎是平等关系;但从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无疑应该是意义决定形式,反过来形式也制约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意义是本质,形式是载体。例如“我看完书就睡觉”之所以合法,是因为时间顺序原则这一语法意义决定了“我看完书”应该先于“睡觉”;而“我睡觉就看完书”这种语序就违反了汉语的时间顺序,因此不合语法。在这里,语序这种语法形式,本质上是由顺序义来决定的。
(三)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关系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开始对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主要是:
1)语法应该包括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句法结构体,无论词语、词组,还是句子,都由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构成,二者不可缺一。
2)在研究方法上,由形式可知意义,由意义可知形式,属于对等关系,就好像是一张纸的两个面,不可分割;但作为研究对象,则可以而且应该具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
3)80年代以来,我们认识到,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复杂关系。即一种语法意义可以通过多种语法形式表现出来,而一种语法形式也可以表现多种语法意义。最典型的证明就是歧义结构,像“动词+名词”这种组合可以表现多种语法意义,如“学习英语”是述宾关系、“学习时间”是偏正关系;领属范畴作为一种语义关系范畴,可以通过短语(如“王冕父亲”)、句式(如“王冕死了父亲”)分别得到实现。但是如果我们对语法形式的认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说到底,语法意义的任何改变,一定会在语法形式上得到显现,而语法形式是从属于不同层次的,换言之,一定的语法意义跟一定的语法形式必然是一一对应的。
(四)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语用意义的区别
“语义”是个多义词,广义地说,它可以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
词汇意义,简称“词义”,严格地说,就是该词语的某个义项本身蕴涵的各种义素的总和,它不必考虑对分布、组合、变换等语法形式有没有决定作用,即可以脱离句法而独立存在。而语法意义,简称“语义”,就是从若干词语、若干结构、若干句式中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且是对词语、词组或句子的分布、组合、变换等起决定性作用的意义。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一,前者是具体的,只能够解释某一个词语;后者是抽象的,可以解释一组相同的语法现象;第二,前者跟句法的结构组合、结构变化基本无关,而后者则密切相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词汇意义,可以分化为若干个义素,其中有的义素是跟句法有着密切关系的,那就是“语义特征”。例如“他把小偷赶到门外”和“他把小偷押到门外”不同,前者是“他”没到门外,后者“他”和“小偷”都到了门外,关键就是动词“押”具有【+携带】义素,而“赶”却不具有这一义素,是【-携带】。关键还在于,这不是个别的词语现象,而是涉及到词的集合,形成“押、带、搀……”与“赶、推、踢……”两个集合的对立,从而具有句法上的价值。
语法意义跟语用意义的区别也是至关紧要的,两者的关系也常常纠缠在一起。语用意义是语言在交际过程中所获得的意义,所以它跟语气、句类、语境密切相关,而跟句子的结构基本无关。例如“别睡觉了!”可以说,“别地震了!”不能说,其原因是因为“睡觉”可以自控,“地震”不能自控,这是语法问题,但是,“房子在晃动,别地震了!”这是表示一种否定性的猜测,这说明“别地震了!”作为祈使句不能成立,而作为“猜测句”则可以成立。这样的区别是语用因素决定的。但是,现在这样的语用意义也常常被看作是语法意义的一部分。
总之,以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循环论证来定义它们自身,虽然定义本身无懈可击,但对语法研究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应该从意义的决定性和形式的反制约性这种对立统一的角度来重新界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内涵。它既反映了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之间的对应性、验证性和统一性,还容易确定形式与意义的验证标准。
二 语法范畴、形式范畴和语义范畴
语法范畴,通常是指“某种语法意义和表现这种意义的形式手段两者的统一体”(张涤华等,1988)。具体来说,又可以区分为“形式范畴”和“语义范畴”,或者称之为“形式语法范畴”和“语义语法范畴”。
“形式范畴”,这是从形式入手建立起来的一套范畴,例如名词的“性、数、格、位”,动词的“时、体、态”,形容词的比较级、最高级,等等。以往从西方语言学理论引进来的语法范畴,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形式范畴。形式范畴,通常包括词法范畴和句法范畴。早期的汉语语法学家借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定义汉语的语法范畴,而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的语法意义主要是通过词形的变化来体现的,所以研究思路自然是从词的不同的形态变化归纳出不同的语法意义,这就被称之为“词法范畴”;后来研究思路开阔了,开始从句子层面研究词类分布和句法成分的组合,认识到广义形态、语法功能的作用,从而建立了“句法范畴”的观念,但基本上还属于以形式标志为主的语法观念。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形式范畴,实际上也包含了语法意义的内涵,只是从它的出发点来命名而已。
“语义范畴”,这是在探求汉语特有的表现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或决定语法形式的语法意义的过程中,在不断明确语法研究目的和探求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在认识到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之间内在的决定与反制约关系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换言之,语义范畴从本质上讲,就是从语法意义角度归纳出来的语法范畴。语法意义主要有两类:一是从词类次范畴小类中概括出来的具有范畴性的语义特征;二是从词语或句式的组合中概括出的范畴化的语义关系。可见,语法意义包括了语义特征和语义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从语义特征或语义关系对语法形式起决定作用这个特定角度来重新界定语义范畴。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语义范畴,从本质上讲,也都需要形式的支撑和鉴定。
“形式范畴”和“语义范畴”应该是相通的,互有照应的,只是出发点不同,着重点不同,从而造成了差异。
(一)语义范畴和语法范畴
关于语义范畴及它跟语法范畴的关系,目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把语义范畴看作语法范畴或者直接叫语义语法范畴。
胡明扬(1958)认为“语法范畴是把语法意义归类得出来的类名”,他强调语法范畴是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结合体的归类。当然这主要还是指显性语法形式所体现的语法意义,因此,“由隐性语法形式和相应的语法意义构成的语法范畴不妨称之为语义语法范畴”(胡明扬,1992)。可见这里实际上是把语法范畴分为两类:一是显性形式语法范畴,一是隐性形式语法范畴。马庆株赞同这一观点,他特别注重两点:一点是“词汇意义——语义特征——语法分布”,从而打通了词汇和语法的关系,证明了“汉语语义范畴(语义特征)和语法范畴(分布特征)的对应性,例如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语法上对立的各种表现与语义上对立的相应关系说明自主非自主既是语义范畴,又是语法范畴,可以称作语义·语法范畴”(马庆株,1998a:233);一点是“词组——语义关系——语序”,研究不同词类的成员在组合中表现出的有序性,提出了绝对义/相对义对时间词和处所词的排列顺序的制约作用(马庆株,1998b)。但他们都把语义与语法、语义范畴与语法范畴的关系仍理解为对应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
第二,语义范畴独立于语法范畴(形式范畴)。
吕叔湘(1942)主张语法研究可以语法意义为纲,说明所赖以表达的语法形式,这样的语法意义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谓的语义,包括各种语义范畴和各种语义关系。邵敬敏继承了吕叔湘的语法思想,主张“语法研究应该根据汉语的特点,着重分析汉语的语法意义范畴及其表现形式……确切地说是研究语法意义如何通过各种语法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既有词汇及语用问题,而更主要的还是句法本身的问题”(邵敬敏,1992),他不仅明确提出了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独立性以及“语法意义范畴”这一概念,而且认识到词汇与句法的联系,这一点对认识实词的词汇意义也会对句法产生作用有重大意义。例如在“动词+名词”的组合中,为什么有的是动宾关系(如“学习英语”),有的却是偏正关系(如“学习园地”)?对此,邵敬敏(1995)解释为“动词和名词的语义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句法结构关系的不同”,后来邵敬敏(1997)又明确提出“语义决定性原则,即汉语语法的决定性因素是语义,而不是形式”。这里,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1)构成词组的动词语义特征与名词语义特征决定了词组的语义关系,是语义特征决定了语义关系;
2)以构成词组的动词语义特征与名词语义特征的双向选择关系为基础,提出了语义关系对句法关系的决定性;
3)语义关系一旦融进某个句法结构中,句法结构就成为一种语法形式载体,这时句法的强制性就会发挥作用。
总而言之,横向组合的语义基础是纵向聚合的语义特征,而纵向的聚合类的语义特征,则可以形成语义范畴。
第三,语法范畴产生了语义范畴。
陆俭明、沈阳认为:“语法意义通常是指不是由词语、语境、推理产生而是由语法形式产生的意义”,换言之,他们是从形式与意义的生成关系来定义语法意义的,显然这是受到生成语法理论的影响,认为是“语法形式产生了意义”。这里其实触及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即到底是意义决定形式,还是形式产生意义。他们还把“语义范畴”分为狭义的语义范畴(词法范畴)和广义的语义范畴(句法范畴),前者主要指有词形变化的语言所体现的体词属性范畴(性、数、格、有定和无定)和谓词属性范畴(时、体、态和人称),但是,“汉语的这些语法意义并非通过词形变化体现,因此应该就不属于词法范畴,而已经是一种句法范畴”;后者是指“由某种句法结构形式产生的语法意义”,他们称为“句法范畴”或“语义范畴”。(陆俭明、沈阳,2003:353-357)最后合而为一,认为“句法语义范畴,……是指跟句法相关的语义范畴,……这是对语法意义进行分类抽象概括而得到的,……一定的范畴意义对句法会起——定的制约作用。”(陆俭明,2003:161)这样,他们就把语法范畴跟语义范畴合而为一了。
(二)跟语义范畴有关的概念的共识
西方语法理论的“性、数、格、位、时、体、态”等语法范畴是根据一定的语法形态概括出来的,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研究汉语语法,已经证明很难走得通;而我们所说的语义范畴则跟语义特征、语义关系息息相关,并且是得到隐性语法形式验证的,我们坚信,从这样的语义范畴出发,才是适合汉语特点的新的语法研究思路。
如果大家对以上的分析基本认同,那么我们在给若干跟语法意义有关的概念下定义之前,就可以达成一些共识:
1)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语用意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决定语法形式,并且受到语法形式的制约,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2)所谓范畴,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对事物的特性及事物间关系的高度概括,包含三个要点:特征、关系、概括。
3)语法范畴包括形式范畴和语义范畴两个方面,根据语言的特性,既可以着重于形式范畴的研究,也可以着重于语义范畴的研究。两者只是出发点和重点不同而已。
句语法意义可以概括为语义范畴。按照语义特征的类别聚合决定了语义的特征范畴;按照语义的选择组合决定了语义关系范畴。其中,语义特征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
5)语法意义具有某些重要属性:内涵的抽象性、外延的概括性、形式的可证性、存在的客观性(邵敬敏,1988)和本质的决定性。
6)语法意义是一个交叉的网络系统,而且从语法内部关系来说,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具有对应性、交融性和相对性。
7)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结合为某个句法结构体,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作为研究对象来讲,语法意义以及语法形式应该而且必须分开来研究,即他们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三)有关语法范畴等重要术语的界定
据此,我们可以对一些跟语法意义、语义范畴密切相关的术语进行必要的定义:
1)语法范畴,指涉及语法形式、语法意义及其关系的范畴,可以分为形式范畴和语义范畴两大类。
2)形式范畴,是从语法形式角度界定语法意义的范畴,包括词法范畴和句法范畴。
3)词法范畴,指狭义语法形式,即词形变化所引起的语法意义变化的范畴,强调以词法的形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去寻找词法意义的区别。
4)句法范畴,指广义语法形式与隐性语法形式所引起的语法意义变化的范畴,强调以句法的形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去寻找句法意义的区别。
5)语义结构,是指隐藏在句法结构背后的由语义特征和语义关系建立起来的结构体,是从语义关系角度解释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结合体。
6)语义特征,就是体现语法意义的特征,是指跟句法结构成立与否、句法结构变化以及相互区别有关的语义要素。一个词语的义项往往由若干个语义成分(义素)构成,但只有对句法结构有决定性的语义成分才是语义特征。
7)语义关系,就是体现语法意义的语法成分之间的关系,它必须由两项语法成分才能形成。语义关系由语义特征的聚合和组合决定。
8)语义论元,语义关系的一种,特指围绕动词的各种名词性为主的成分在特定语义结构中所形成的语义关系。语义论元离不开句法结构,也离不开语义结构,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
9)语义角色,语义关系的一种,特指语义论元之外的语法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包括名词与名词、形容词与名词以及相关短语之间的语义关系。
10)语义指向,指语义结构内部予以成分之间所联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除了直接成分和间接成分之间存在着语义指向,在语素之间,在义素之间,在语义特征之间,都可能存在着语义指向。它可以存在于句法结构之内,也可以超越句法结构。
三 语义范畴的分类及其依据
语义范畴的分类及其确定的标准,一直是语法学界难题之一。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国际语言学界对语义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形式语法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语义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第二,即使以往有一些关于语义的研究,也只关注由形态变化决定的语法意义的类型,如上所述,实际上是“形式语法范畴”,几乎没有人关心语法意义本身的“语义语法范畴”。第三,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出于各自的需要,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方法、目的出发,在描述语义时,带有比较强的主观性和任意性。第四,有关语法意义、语义范畴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大多还停留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对有关的理论、方法还缺乏深入地思考,观点还不太成熟,理论也不系统。但是,如果能及时总结目前语义范畴研究的成果,梳理一下思路,提出一些问题,就有可能促进语义研究的深入发展,且有利于不同学派之间的沟通、讨论、交流。
我们认为,语义范畴,又叫语法意义范畴、语义语法范畴,指对语法意义进行抽象所得出的范畴,首先可以区分为“语义特征范畴”和“语义关系范畴”,前者可以再区分为“词义特征范畴”和“句义特征范畴”;后者可以区分为“语义论元范畴”、“语义角色范畴”和“语义关联范畴”。语义特征范畴是根据聚合的性质标准,而语义关系范畴则是根据组合的性质标准。
(一)语义特征范畴的内涵与类型
语义特征范畴,包括从词的次范畴小类抽象出来的“词义特征”和从句式抽象出来的“句义特征”,前者决定了其在句子里的分布特征,这种决定自身分布的词义特征在语法意义上可称为“分布语义”;后者决定了其在复句或语篇里的表达功能,这种决定自身表达功能的句义特征在语法意义上可称为“句式语义”。这两种语义特征的共同点是自身聚合类的独立性,尽管需要词组或句法结构来论证或检验。
1)词义特征范畴,即从一个词的集合中提取出来,并且对某些句法结构具有制约作用的重要义素。比如:自主、可控、有生、携带、持续、获得、消失、推移、顺序等。当然,这些范畴下面还可以进一步分出次范畴来。
目前开展比较好的是关于“词义特征范畴”的研究,在目的上主要是着眼于词类次范畴的分类,在方法上主要通过句式变换分析法来区别,寻找决定自身在句法中分布特征的词类语义特征,特别是实词的次范畴,“对每一个实词都可以进行义素分析,……作为语法研究,我们只关心同句法结构有密切关系的义素分析,即‘语义特征分析’,尤其是动词、形容词和名词的语义特征分析,只有进入句法结构以后,这些语义特征才能显现出来,并对句法结构有所制约”(邵敬敏,1992)。如果能抓住次范畴的语义特征,其解释力就非常强,不仅可以独立存在,并在不同的句式里起作用,甚至可以预测其“潜在的组合可能性或分布特征”(胡明扬,1992),使词汇分类与语法分类结合在一起。比如,马庆株提出的动问次范畴的“自主”语义特征,不仅可以解释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之间语法形式的差别,而且对“使动结构”和“动补结构”也有解释力(陆俭明、沈阳,2003:358)。当然,由于词类的语义特征是隐性的,有时候划分的小类解释面很窄,或者说概括力不强,划分的词类语义特征只有在典型的句式里才能表现得比较突出,或只有与语义特征相反或没有此类语义特征的词类对比时才能显现。
根据出发点的不同,实词语义特征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不同的路子得出的语义特征体现语法意义的程度不同,解释能力也有差别,但都属于从深层到表层、从意义到形式的路
A.解释分布型。以解释分布为主,着眼于词类语义特征与语法分布的对应性。例如朱德熙(1956)根据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对立,提出了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在现代汉语的形容词里,性质与状态两种概念的区别构成一个语法范畴——性状范畴”;马庆株(1991:59)考察了有顺序义的体词性成分(指人名词、时间词、处所词等),并指出相对/绝对顺序义的不同。
B.分化辨析型。以分化小类或辨析语义差异为主,着眼于词类次范畴语义特征的差异或分化歧义。例如,朱德熙(1979)根据由动词“给”组成的句式分化出部分动词词汇意义里所包含的“取得”和“给予”两个语义成分;陆俭明(1989)根据“V来了”把动词分为心理/位移/目的性动词并提取出动词的去除义等;邢福义(1984)提出“NP了”中NP的[+推移性]语义特征;邵敬敏(1988)确定了动词的“消除义/实现义”所造成的句式不同。
C.范畴表达型。以表达思想为主,着眼于提炼语义特征的表达方式。例如时间和空间范畴是所有语义范畴的元范畴,因为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存在和运动的。目前得到学术界认可的实词类语义特征范畴主要有:动词的自主范畴、体词的顺序范畴、形容词的性状范畴;量范畴(数量、动量、时量、模糊量等)、时间范畴、方所范畴、肯定范畴、否定范畴、指称范畴等。
2)句义特征范畴,即根据不同句式、句类所提取出来的、跟句子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句子的语义特征,句义特征范畴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句义特征范畴包括:
A.语气类型:根据句子的语气来进行区分,包括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句类语义特征。
B.表达类型:根据句子的表达效果划分,特别是特殊句式:处置、被动、肯定、否定、意愿、猜测、使成、判断、虚拟、评估等。
(二)语义关系范畴的内涵与类型
凡是两个句法成分构成一个句法结构,这两个成分,不管是词语、短语,还是句子,甚至于句群,就必定形成一定的语义关系,把这种语义关系抽象出来的组合义,就形成了范畴。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考虑到性质和特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语义关系范畴细化为三类:
1)语义论元范畴。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范畴,特指以动词为核心,跟其他名词性为主的句法成分建立起某种语义关系,这些跟动词发生联系的句法成分就是语义论元范畴,比如:施事、受事、工具、材料、凭借、方式、数量、方所、时间等。在本质上这不是词类语义特征的范畴化,其名称也不代表词类次范畴的语义特征,它反映的是结构成分与结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一旦离开这种句法结构,这种语义关系就不存在了,但是这种语义关系一般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各自的语义特征,其实它也受自身语义特征的支配。语义论元范畴的特点是组合双方的相互依赖性。
我国最早认识到句法结构中动名间语义关系的是吕叔湘(1942),该书分析了动词与名词间的12种语义关系,如受事补词(给予关系)、关切补词(服务关系)、交与补词(共事关系)、凭借补词(工具类、标准类等)、方所补词、方面补词、时间补词、原因补词、目的补词、比较补词、起事补词、止事补词。另外,他还提出形容词也有补词,多半是方面补词、比较补词。后来,朱德熙(1978)明确谈到动词“向”的观念,并提出了单向、双向和三向动词,这就是现在说的动词的“价”。
自“格”语法理论介绍到我国以后,众多学者开始研究汉语动名间的语义关系。孟琮等(1987)分了14个语义格,即受事、结果、对象、工具、方式、处所、时间、目的、原因、致使、施事、同源、等同、杂类。鲁川、林杏光(1989)提出:格关系是诸多语义关系中的一种,只反映体谓语义关系,不反映偏正关系,也不能安排话题和焦点以解决句子生成的排序问题,因此格语法应改为格关系,格标记是介词和语序。他们把格关系分为六层,每层包括三个格,每个格下边还各有几个“格标类”。邵敬敏(1996)根据语义双向选择性原则,认为语义格不是由动词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双方共同决定的,只要有一方发生变化,并超出了二者的语义范畴,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二者的语义关系是以人们对事物之间的种种联系的认知为基础的。他不仅看到了在语义关系研究中配价语法和格语法的以动词为核心的支配观念的不足,提出了确定语义关系的平等性原则,而且把小句宾语以及形容词性的句法成分也作为“格”或“价”来处理,扩大了格的范围。他建立了一个七大类二十四小类分层次的语义格框架。袁毓林(2003)设计了用于形式验证的8种语法指标,坚持了从意义出发必须能在形式上得到验证的原则,并结合原型理论给出不同论元角色的典型句法、语义特征,然后通过类比归类的办法来确定特征不明显的语义成分的论元角色,最后建立了一个由17个论元角色组成的层级体系(袁毓林,2002)。
由上可知,传统语法、配价语法、格语法、原则与参数语法都以动词为核心,借助动词的辐射能力建立语义关系范畴,根据语义格/论元的名称及与动词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语义关系范畴:一种是以动词为深层参照对象的对应性语义范畴:施事/受事、等事/系事、领事/属事、原因/结果;一种是直接参照动词或以动词为隐性参照对象的语义范畴:与事、工具、材料、方式、感事、自事、对象、数量、时间和空间。
如果要把建立在动词基础上的语义关系范畴搞清楚,应该理清动词的次范畴分类及其语义特征,这对命名价、格或论元以及确定其数量、性质是基础性的,另外把体词性的短语、小句也作为格/价/论元处理可能比较适合汉语的实际。根据对动词的参照方式和依存程度得出论元系统:相对元和依存元都属于语义论元范畴。
论
一级二级
元 相对元 NP/AP-V-NP/AP 施事/受事、等事/系事、领事/属事、原因/结果
系 依存元 V-NP/AP与事、工具、材料、方式、感事、自事
统 对象、范围、行为、属性、事件、状态、数量、时间、空间
2)语义角色范畴。指动名关系之外的其他的句法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主要是名词和名词,形容词和名词所构成的各种语义关系,例如“整体/部分、领有/属有、质料/本体、先行/后续、动作/结果、动作/程度”等。这样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格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并将成为语义研究一个新的亮点。
3)语义关联范畴。是以句子作为基本单位所形成的语义关系,它反映的是事件与事件的语义联系,其中特别注重分句与分句之间(即复句内部)的语义关系。可见,语义关联范畴的特点是相互依赖性。比如:比较、并列、连贯、递进、等同、转折、因果、目的、条件等。
“凡复句,都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邢福义,2001:24),分句与分句之间存在着各种语义关系,对这些关系进行分类并概括,形成语义关联范畴。黎锦熙(1924)最早提出复句概念,并且把复句分为包孕复句、等立复句(平列、选择、承接、转折)、主从复句(时间、原因、假设、范围、让步、比较)等。20世纪40年代,王力和吕叔湘的研究最有创见,王力(1943)的分类是:积累、离接、转折、按断、申说、时间、条件、容许、理由、原因、目的、结果(12类);吕叔湘(1942)的分类是:离合、向背、异同、高下、同时、先后、释因、纪效、假设、推论、擒纵、衬托(12类)。邢福义(2001)采取的是复句三分系统:因果(因果、推断、假设、条件、目的)、并列(并列、连贯、递进、选择)、转折(转折、假转、让步),共有12类。但这种种语义范畴之间的关系,至今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短语与短语之间也可以构成某种语义关系。这些语义关系,一部分跟词与词的语义关系相似,例如:时间范畴、空间范畴、指示范畴、称代范畴、数量范畴、比较范畴、领属范畴、顺序范畴等。另外一部分则跟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相似,例如递进范畴、选择范畴等。对每一种语义范畴,我们都需要进行重新审视,重新梳理,重新解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具有解释力的语义范畴系统网络。
四 结语
关于汉语语法语义范畴的研究,充满着太多的疑问,它的内涵、外延、类型以及内部的关系,都还不太清楚。以往汉语语法的研究偏重于形式,或者说,以形式为出发点和重点,大家还不习惯于从语义出发并把它作为研究的重点。也许你不同意我们的分析,或者不完全赞同我们的分析,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你不能不正视这一个课题。你可以坚持原有的研究思路,依然从形式出发,但是你不能反对别人从语义出发来进行新的探索,也不能无视这一思路给语法研究带来的冲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汉语语言学界有少数学者认为,汉语是跟英语这样的“形式型”语言相反的“语义型”语言,甚至于曲解王力先生的解释,说汉语就是“意合语法”。这样的观点可能意味着:汉语的语义不需要形式的载体,不受形式的束缚,也不需要形式的验证。我们认为,这样的误导是非常有害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形式的意义,也不存在没有意义的形式。把这两者割裂开来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且实际上也就是取消了汉语语法的客观存在。这种“伪语义语法”跟我们所提倡的语义语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在大声疾呼加强语义范畴研究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人为地割裂意义和形式的血肉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