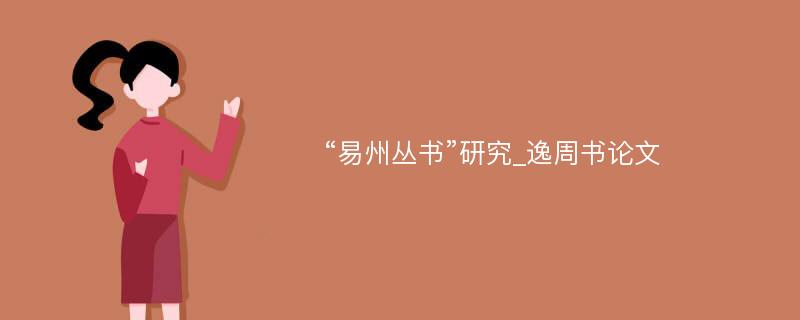
《逸周书》丛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3X(2002)01-0081-04
《逸周书》的史料价值颇高,但也存在不少脱佚与疑误,亟待澄清。
一、《逸周书》书名起始考
《逸周书》原名《周书》,目录书的最早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注云:“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史记”是先秦、秦汉时对史书的通称,周史记犹言周 代的一部史书,有的研究者认为《逸周书》原名《周史记》,那是不妥当的。先秦典籍 如《战国策》、《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称引是书时,都叫它《周书 》,今名的“逸”字是后人所加。
然而《逸周书》的名称究竟是从何时肇始的呢?清人潘振以为,《逸周书》的名称是从 晋代开始出现的。潘氏《周书解义自序》云:“《汉志》载《周书》七十一篇,即列于 《尚书》之后。而总系之以辞,时未有‘逸’之称也。逮郭氏注《尔雅》,李氏注《文 选》,俱引称《逸周书》。”所谓郭氏指晋人郭璞,故后人便据此认为:“逸周书”的 名称是从晋代开始的。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早在潘振以前,王谟就说“许叔重《说文》引 《逸周书》”(见《汲冢周书跋》)。比潘氏稍晚,陈逢衡作了一部《逸周书补注》,他 在《叙略》中解释说,书名之所以不恢复《周书》旧名,而“题《逸周书》者,从《说 文》引称《逸周书》以别于《尚书》”。后来,朱右曾作《逸周书集训校释》则更明确 地指出:“《周书》称‘逸’,昉《说文》。”[1](P1322)王谟、陈逢衡、 朱右曾等人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考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其中有多处称引这一名称的 。如示部“祘”下注云:“《逸周书》曰:士分民之祘,均分以祘之也。”羽部“翰”下注云:“《逸周书》曰:文翰若翚雉。”人部 “赒”下注云:“《逸周书》曰:朕实不明,以俒伯父。”豕部“豲”下注云:“ 《逸周书》曰:豲有爪而不敢以撅。”这些都足以说明,最迟到许慎著《说文》时, 就已经有“逸周书”这个名称了。
此书本名《周书》,为什么人们要称它《逸周书》呢?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 种名为《周书》的著作:一种有71篇,单独流传;另一种只有19篇,是《尚书》的一部 分(《尚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又相传71篇的《周 书》是用孔子编定《尚书》时所剩余下来的材料编成的;人们为了区别这两种《周书》 ,便称前者为《逸周书》,后者仍称《周书》。清人段玉裁解释道:“《艺文志》:《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也。刘向曰: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故许君谓之《逸周书》, 亦以别于《尚书》之《周书》,免学者之惑也。”[2](P8)许慎作《说文解字》时,两 种《周书》的材料都经常引用,所以必须严格区分,“逸周书”的名称亦因此而生。许 慎(公元30-124)是东汉中期人,比东晋初期的郭璞(公元276-324)早了200多年。如果说 《逸周书》之名始于晋代,那又如何解释《说文》中早已多次称引这个书名呢?或者因 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引用《说文》羽部翰和豕部豲中两条“逸周书”文字时没 有“逸”字,于是怀疑今本《说文》中的“逸”字为四库修书后人们所加。这也很难讲 通。因为第一,段玉裁写《说文解字注》几乎与修四库全书同时,(段于1780年始注《 说文》,四库全书于1773-1782年完成),为何段氏所见《说文》有“逸”字而四库馆臣 们见本没有呢?其次,早于四库修书的王谟亦云“许叔重《说文》引《逸周书》‘文翰 若翚雉’,又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1](P1286)这证明早于四库修书时 的《说文》亦有此“逸”字。看来《说文》这几处引文本作“《逸周书》曰”是不必怀 疑的了。综上所述,可知“逸周书”之名开始于东汉,而非晋代。
二、《逸周书》篇名原无“解”字考
今本《逸周书》71篇,除末篇《周书序》之外,其余各篇篇题都缀有一个“解”字, 如《度训解》、《命训解》、《谥法解》之类。这些“解”字非原书所有,而是后人所 加,学者不可不知。
这样的错误大概自宋代就开始出现了。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引宋人黄震《黄氏 日钞》云:“《周书》自《度训》至《小开解》凡二十三篇,皆载文王遇纣事……自《 周祝解》至《谥法解》,不知其所指;终之以《器服解》。”姚氏接着指出:“按篇名 系以‘解’字,盖晋孔晁所加。犹《淮南》高诱注本皆系以‘训’字。”[3](P1542- 1543)黄氏引《逸周书》篇名时,未曾留心这点,于是连孔晁所加的“解”字一起引来 了。像这样不经意地错引《逸周书》篇名的,还有不少大家,如顾炎武(见《日知录》) 、章学诚(见《文史通义》)、刘师培(见《逸周书补释自序》)、郭沫若(见《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附录)等,“皆所谓通人之蔽也,更无论世俗昏昏矣”。[4](P48)影响所及 ,直至解放以来所流行的一些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和《逸周书》校注本等,也有类似的毛 病。看来,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有的学者弄错《逸周书》的篇名,并非粗心所致,而是他们固执地认为篇名末的“解 ”字为《逸周书》所原有。如清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叙略》云:“是书命名,俱以‘解 ’名其篇。案《说文》:‘解,判也。’……又《古今乐歌》:‘伧歌以一句为一解, 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云:‘古曰章,今曰解。’据斯二说,古人原有以一篇 为一解者。”他认为《逸周书》篇名的“解”就相当于后世的篇。与陈逢衡同时稍后的 唐大沛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说《逸周书》的篇名都作“某某解第几,其中称‘解第’者 ,犹言‘篇第’也”,并说,《孔子家语》中“称‘解’者十篇,盖仍古书之旧目也, 与此同例”。[1](P1)清人吴承志在《横阳杂记》中则说:“《周书》七十篇,旧题俱 系以‘解’字,以《管子·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 明法解》例之,此书疑春秋、战国间人采《周志》及杂说以解百篇中之《周书》者。” 并以为《泰誓解》就是解释《尚书·泰誓》的,以此为证(参见顾颉刚先生《逸周书世 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按照他的意见,《逸周书》篇名的“解”字仍当作“解释” 讲,为原有,此书各篇都是为了解释《尚书》的《周书》部分的。
上述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陈、唐二氏皆以为《逸周书》的解相当于篇,他们的根据 是《古今乐歌》。其实这是乐府诗歌的体制,它与其他文献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 。而唐氏断取“解第”二字以等同于“篇第”,则尤为幼稚可笑。吴承志以为《逸周书 》各篇都是解释《尚书》的《周书》部分的,也很难讲通。顾颉刚先生指出:“《书序 》中所列《周书》目凡四十篇,取校《逸周书》目七十篇,固有相应者,……然不相应 者甚多,《周月》、《时训》、《谥法》、《职方》、《芮良夫》、《太子晋》等于四 十篇中俱无可附丽,与《管子》中《牧民解》之解《牧民》,《形势解》之解《形势》 大异,实不可取以并论。”[5](P228)顾先生还举出了一条重要的证据,就是今本《周 书序》中对诸篇的提要说明,从首篇《度训》到末篇《器服》,没有一篇的介绍是有“ 解”字的,如“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宏道以弼无道,作《度训》……武 以靖乱,非直不克,作《武纪》。积习生常,不可不慎,作《铨法》。车服制度,明不 苟逾,作《器服》”。这是重要的本证,足以说明《逸周书》的标题原是没有“解”字 的。清人朱右曾则从他证方面找根据。他在《逸周书集训校释序》中说,晋五经博士孔 晁在注释《逸周书》时,“每篇题云‘某某解第几’,此晁所目也。旧但云‘某某第几 ’,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可证也。 ”蔡邕是东汉晚期人,其时尚未有孔晁注,《周书》篇名仍保持原貌,自然无“解”字 。笔者早年读宋人高似孙《史略》,也找到了一个新的他证。高氏对《逸周书》存世诸 篇篇题都依原本名称进行迻录。大体说来,凡有孔晁注的,都有“解”字,凡无 孔晁注的,都无“解”字,而且有注篇数与无注篇数与今本相同。这又有力地证明,《 逸周书》篇名的“解”字当为孔晁作注时所加。
人们引用《逸周书》的篇名时之所以出错,大概是因为不熟悉古书注述体例所致。关 于这一点,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来了(参见先生《广校雠 略》卷二《援引古书标题论·称引篇目不可误连注述之名》)。十余年后,先生在《中 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古书篇题,有的字是后人作注时加 上去的,学者必须注意把它们分别一下。例如《逸周书》,开始题‘度训解第一’,这 ‘解’字是晋代孔晁作注解时加的。‘解’便是‘注’的意思。后人引用《周书》,断 不宜连‘解’字来作篇名,这是亟宜纠正的错误。”顾颉刚先生赞同并实施了这一做法 。他在20世纪60年AI写作《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一文时,就将“解”字削去, 并加注释说:“今以《周书序》中无有一‘解’字者,知出后人所增,故于写本中删去 。”[5](P228)我们今后引用《逸周书》的篇目时,应该记取张舜徽先生的告诫,效法 顾颉刚先生的做法,决不可误连“解”字作篇名。
三、卷四《大匡》当是《文匡》之误考
今本《逸周书》的某些篇名也遭俗儒妄改,变得奇特怪异,互相矛盾,难以索解。诚 如李宗邺先生所叹:“今本《逸周书》篇名费解,篇次错乱,两篇《大匡》又不编在一 卷,这一部古书,虽经历代学者注释校正,到现在仍很难理解。”[6](P101)今本《逸 周书》卷二有《大匡》(第11篇),而卷四又有《大匡》(第37篇)。在同一部书内有两篇 文章标题完全相同,又不是同名人物传记,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对于这个问题,清人谢墉已有怀疑。他在《刊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中指 出:《逸周书》卷二之《大匡》属荒政,讲救灾,“若第四卷《大匡》为监殷事,篇内 虽有‘大匡’、‘中匡’、‘小匡’之名,不应与前篇同其名目,二者必有一讹。”谢 氏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按推理哲学,在同一部流传久远的古籍中,如果有两篇文章的 标题完全相同而内容不同(同名人物传记除外),则其中必有一误,或两皆误。反之,我 们只要证明其中的一个篇题是正确的,就可排除“两皆误”的可能性,并进而确定错误 的篇题所在。而据《周书序》的介绍:“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 小明武》三篇。穆(当作“文”)王遭大荒,谋救患分灾,作《大匡》。”《小明武》是 第10篇,则上面序文依次介绍的是第11篇《大匡》。此外。该篇正文又说:“维周王宅 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上述《周书序》与卷 二《大匡》正文都有力地证明了第11篇《大匡》的标题是正确的。由此可知,第37篇《 大匡》的标题有误是毫无疑问的了。但究竟是因何而导致错误的呢?该篇序言今已亡佚 ,无从考证。在该篇标题下,“谢(墉)云:前已有《大匡》,此不应又名《大匡》。盖 篇内有‘大匡’字也。不能定其讹错之故。”[7](P95)谢墉的意思是,大概本篇正文内 有“大匡”二字,后人因而附会,便将标题改为“大匡”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 原标题究竟是什么呢?清人孙诒让采用他校的办法,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答案。他说,这 篇文章的标题,“《史略》作《文匡》,似较今本为长。”[1](P387)高似孙是宋代人 ,他见到的《逸周书》版本,该篇篇名作《文匡》,这应该是正确的。因为高氏距今70 0多年,其时《逸周书》自然更多地保存了原貌,此篇标题可能未被改动。其次,此篇 内容主要是讲周武王对东隅的诸侯进行文德训范,作三监以救其民,即“文匡”之意, 与下篇《文政》相类,说明标题与正文的意思是互相吻合的。第三,从字形上看,“文 ”字与“大”字形体相似,容易致误。由此看来,今本《逸周书》第37篇篇题《大匡》 是《文匡》之误,应该没有多少疑问了。
四、《逸周书》非出汲冢考
《逸周书》本是一部先秦古籍,而相传在晋武帝太康初年,汲郡人不准盗发古冢,得 竹书数十车。《隋书·经籍志》的作者遂以为《逸周书》就是汲冢所出的古书之一,于 是称它为《汲冢书》。到北宋初年修《太平御览》,又称它为《汲冢周书》。清人吴锡 麟说:“是书(指《逸周书》)自《隋书·经籍志》误为出于汲冢,遂至混淆者千数百年 ,几并孔注而晦。”[1](P1292)对这种错误的认识,宋人早已进行了批评,如李焘就指 出:《逸周书》既为司马迁、刘向、班固所见,那么,“系之汲冢,失其本矣。”[1]( P1277)稍后的丁黻与王应麟,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浦起龙、姜士昌及《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等,都反复论证,认为是书应称《逸周书》,而不能称作《汲冢周书》。这种观点 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符合客观事实真相。
然而自宋代以来,还有一种“两本”说,认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后稍隐,赖汲冢竹 简出乃得复显”。《四库全书总目摘要》批评说这是“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 [8](P446)清人朱右曾、近人朱希祖又发展了这种观点,谓晋代时《周书》有两种版本 ;一为汉代以来所传之今隶本,此本有孔注,但到唐时已残缺,只剩八卷;另一种为汲 冢所出之古文本,此本无注,但是全体,有10卷。朱希祖先生还说:“刘知几《史通· 六家篇》云‘又有《周书》者,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不云有阙,盖 所见为十卷本。”(参见朱希祖《汲冢书考》)今人编写历史文选教材时,遂谓刘知几所 见之《周书》“必指《汲冢周书》无疑”。[9](P14)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肯定了《隋书· 经籍志》的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似有澄清的必要。
把71篇的完整《周书》说成是汲冢所出,殆系臆测,并无根据。第一,晋人杜预曾亲 眼看到了汲冢所出之书,但他没说有《周书》。其《春秋左氏传集解后序》说:“太 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乃申杼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迄,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 十五卷。”[10](P2187-2188)接着,他历举汲冢所出各书,而未有半字谈及《周书》。 假如汲冢真的出了一部这样完整的《周书》,杜预怎能弃而不数呢?第二,东晋王隐曾 作《晋书》,亦载汲冢出书之事。其《束皙传》云,汲冢所出诸书中,“有《周易上下 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此四部差为整顿 ”。[10](P2188)王隐所说汲冢所出较为完整的书中也没有《周书》。第三,今本《晋 书》的《束皙传》虽然提到了《周书》的名称,但将它列为杂书。据该传传文记载,汲 冢所出书除了15种主要书籍之外,“又有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 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面18字可以有不同的标点法,上引文字标点 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如果此《周书》是完整无阙的,晋史作者怎么会把它看 作是杂书?既然它的篇幅多至71篇,又怎么可以包括在19篇杂书之内?近人刘汝霖说:“ 余考《汲冢周书》,在杂书十九篇之内,断无多至七十一篇之理。盖《汲冢周书》至隋 已亡,后人因书名相同,遂误以汉之《周书》当之也。”[11](P121)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第四,有些先生又说,《束皙传》中所说的“篇”实指“卷”,汲冢《周书》10卷, 《周食田法》盖为7卷,《论楚事》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各1卷,合为19卷(篇)。 这种推测似乎圆通,实则仍与事实不符。因为根据《晋书·武帝纪》与《卫恒传》的记 载,都说汲冢所出75篇简书总计只有10万言,是则每篇约合1300字。《逸周书》10卷, 也只有13000字左右。而今本《逸周书》正文约35000字,尚不包括已佚的11篇文字及存 世诸篇脱佚的文字。这充分说明汲冢所出“周书”绝对不是全本的《逸周书》。第五, 有的论者以为,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谈到的71章的《周书》就是汲冢所出之全 本《周书》。然而在《史通·申左》篇中,刘知几却明确指出:“汲冢所得书,寻亦亡 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12](P423)可见他并没有看到什么汲 冢“周书”,更不用说全本了。相反,刘知几在《史通》的《六家》、《书志》、《因 习》、《疑古》等篇中,多次引用《逸周书》的话,都称《周书》,而不叫“汲冢周书 ”。清人浦起龙也指出:“《史通》亦多引其书(指《逸周书》),皆不冠以‘汲冢’, 《隋、唐志》之误信矣。”[12](P6)我们应该记住浦氏的话,不要重犯《隋、唐志》的 错误。第六,论者既以汲冢《周书》为71章的全本,自然包括《周书序》一篇。但是此 序乃《周书》各篇的提要、序言,言其作意(包括周以后附益者),后人将其合为一篇, 这不可能由周人完成,不可能出自战国时的古墓。综上所述,可知汲冢是否出了“周书 ”,至今仍有疑问,即使有,也是一部与《逸周书》(本名《周书》)名称相同而内容不 同的杂书,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收稿日期:2001-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