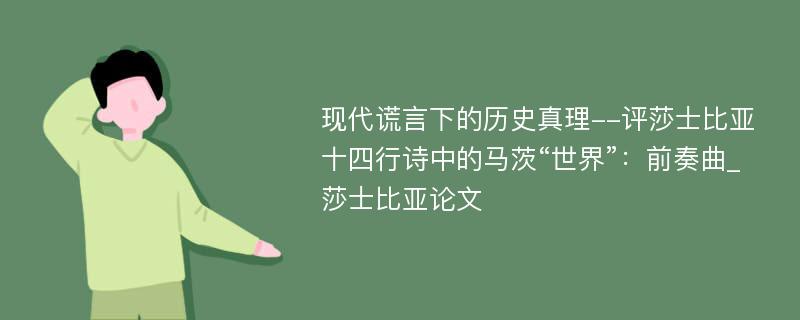
现代谎言下的历史真相——评麦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前奏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前奏曲论文,诗中论文,谎言论文,真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3-0138-09
[Matz,Robert.The World of Shakespeare's Sonnets:An Introduction.Jefferson:McFarland & Company,2008.]
对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在诗和莎士比亚本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个关键的问题。现当代学者大都从纯文学角度,把莎士比亚看作这组十四行诗的作者,而诗中的“我”和莎士比亚是两回事。1997年海伦·文德勒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艺术》,2007年丁普娜·凯勒耿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均按此处理。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前奏曲》中,作者罗伯特·麦茨声明,他无意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当作莎士比亚传记来研究,因为这些诗的创作动机或出发点,至今没有明确的历史文献可查。莎士比亚本人更未留下与此有关的只言片语。但不能否认的是,诗中的故事四百年来一直存在。虽然并非一定要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诗人的“传记”来研究,但却可以借助传记角度的独特优势来揭示出一些历史事实。麦茨决定从影响十四行诗、莎士比亚的生活和世界的文化背景出发,挖掘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隐含的故事。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它的立足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而非诗中亘古不灭的爱情。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般认为是写给两位不知名的爱人,一男一女。莎士比亚称这位无名男子为“朋友”、“年轻人”、“爱人”、“男孩”等。在这些称呼中,除了“年轻人”,其他称呼或多或少都会引起歧义。比如“朋友”在文艺复兴时期并非单纯指精神上的情谊,它包含了当时男性之间对忠诚和平等的理想追求。麦茨认为研究者在提到这名男子的时候,称其为“年轻人”较为客观。这位贵族“年轻人”是诗集的中心人物,他是名男性,绝非女性。对那位不知名女子,麦茨建议呼其为“黑情妇”(black mistress),而非当今大多数人口中的“褐女士”(dark lady)。麦茨认为,在有关这位女子的组诗中,“褐色”只出现了一次,“黑色”却出现了很多次。莎士比亚也从未把此女子呼作“女士”,反而多次直唤其为“情妇”。
具体到诗中“你”和“我”,研究者该怎样定位呢?传统观点认为诗中的“我”指诗人或者仅仅指讲话者本人,“你”指“年轻人”或“黑情妇”,两人也可能只是虚构人物。这显然是纯文学的角度。麦茨则更愿意把“我”作为“莎士比亚”,“你”也是活生生的人。16、17世纪的诗中确实充满了虚构人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麦茨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十四行组诗不同,它们大多是自传性的。他列举了两位著名诗人作为例证:一位是西德尼,他的十四行组诗中写的就是一位真实的女人,佩内洛普·德弗罗。诗集首次出版时,其中一首不得不被拿掉,因诗中泄露了这名女子婚后的姓名佩内洛普·瑞奇。另一位大诗人斯宾塞曾在十四行诗中赞扬了三位“伊丽莎白”,这三位女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分别是女王、他的母亲和爱人,三人的真名都叫伊丽莎白。麦茨也不同意诗中“你”是多个,而非一个,十四行诗的特性决定了诗中情人的单一性。重复出现的词语、意象和主题使十四行组诗中的人物形象前后一致,也使这些诗成为一个整体。对一个人的忠诚甚至过分的痴情恰是十四行诗的基本传统,虽然莎士比亚十四行组诗中的“你”指一男一女两个爱人,但绝非多个男人和女人。
对诗中人物的性别和身份进行明确定位之后,麦茨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这些诗产生的时代背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护”文化之下,和现代的“市场调控”文化截然不同。研究者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对这部诗集的理解很可能会产生偏差。麦茨从当时文化背景出发,尽力还原了莎士比亚创作十四行诗的动机,对诗中的同性爱、婚姻观、女性身份定位等久论不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提起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评论者和读者首先注意到的是爱情。莎士比亚创作十四行诗的动机是否为了讴歌爱情?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十四行诗为何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盛行?
麦茨从两个角度解释了十四行诗在16、17世纪英国风行的原因。首先十四行诗是一种展现“优雅”的手段,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朝臣最看重的是“优雅”风度。他们恪守礼仪规则,表现得有礼、时髦、机智,有时甚至化身诗人,用一种“优雅”风度捕获君王的恩宠。十四行诗的艺术与朝臣所寻求的手段不谋而合,它格律严谨,规则繁琐,形式工整。然而,经过精心策划,这种内敛、朴素的形式却能传达出热烈的情感,使诗人隐藏于内心的骄傲得到极大的张扬。十四行诗把形式上的谦卑和内在自我的宣扬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有文学才华的绅士如西德尼,就把创作十四行诗当作展现高雅风度的手段。正如西德尼在十四行诗中借歌颂斯特拉来歌颂自己一样,麦茨认为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组诗中同样借赞美“年轻人”来赞美自己,因为“年轻人”恰是诗人的另一个自我。在第62首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公开承认了这一点。“年轻人”在莎士比亚十四行组诗中充当了一面镜子,镜中映照出来的正是莎士比亚本人。
同时,麦茨研究发现,创作十四行诗还是一种提高社会身份的有效途径。西德尼名门出身,尚对十四行诗的这种社会功用十分青睐,更何况平民出身的莎士比亚。没有文学才能的贵族和绅士们,通过恩宠和庇护诗人来展示自己的慷慨和学识。莎士比亚这类身份低微的诗人则通过给贵族庇护人写诗、献诗来获得金钱的资助,更重要的是借此在宫廷或者豪门望族中谋求一席之地。
16世纪90年代初,莎士比亚确实在寻找文学庇护人。1593年,他出版《维纳斯和阿多尼斯》,把它献给南普顿伯爵。次年,他又出版《鲁克丽丝受辱记》,并敬献给同一人。南普顿伯爵本人是位难得的文学庇护人选,他出身名门,年轻(当时大约十九岁)、英俊、文雅,同时还富有。更难得的是,他在贵族文学圈很活跃,喜欢资助艺术,还将继承大笔财富,有能力实施资助。1592到1594年间,瘟疫暴发,伦敦剧院关闭将近两年,而且谁也不知何时会重新开门营业。莎士比亚此时只能另辟蹊径。麦茨推测莎士比亚试图借十四行诗创作转变成一名宫廷诗人,毕竟那时莎士比亚并未料到他将来会以伟大的剧作家身份名垂后世。虽然不能肯定南普顿伯爵就是莎士比亚组诗中的“年轻人”,但这些十四行诗中确实流露出寻求文学庇护的传统元素。
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强调秩序和稳定,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而且不鼓励逾矩,这和现代社会充满野心和抱负的氛围格格不入。然而,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商业中心,也正因如此,莎士比亚才能通过他的戏剧在伦敦赚钱谋生。在充满了买卖关系的社会,文学庇护人和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过去那般纯洁,一如彼此忠诚的主仆。莎士比亚在这种环境中是怎样对待他潜在的庇护人呢?
首先是恳求。在第37首十四行诗,“年轻人”就被描述成卑微作家苦苦恳求的庇护人。有时莎士比亚会反其道而行之,用嘲讽代替恳求的口吻。嘲讽的对象有与他竞争的诗人,也有“年轻人”本人。在第21首,莎士比亚狠狠地挖苦了“对手诗人”,认为他们使用矫饰的比喻、夸张的言辞,其实都是在言不由衷地歌颂“年轻人”。这些诗人就像兜售商品的小贩,向“年轻人”推销着他们的赞美。莎士比亚表示自己绝不那样做。他对“年轻人”的感情是真挚的,与任何花哨的语言无关,他要用最朴素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最真诚的爱。在第67、68首中,莎士比亚再次表示自己绝不和那些虚伪的诗人为伍,像他们一样哗众取宠,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同时,莎士比亚也在诗中讽刺挖苦“年轻人”。在第33—35、92—93等首诗中,他毫不留情地讥讽“年轻人”表面美丽,内心丑恶。在第95首,莎士比亚甚至把“年轻人”比作专吃玫瑰花心的“害虫”,而不是像以往一样赞“年轻人”是朵“玫瑰花”。莎士比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难道真如文学批评家阿瑟·莫若提所理解:这些十四行诗中的指控证明了莎士比亚的承诺——做“你最诚实的朋友”,不像对手诗人那样阿谀奉承?(Marotti:396—428)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艺术》一书中,文德勒谈到莎士比亚对“年轻人”的不恭敬时认为,莎士比亚这样做是对文艺复兴时期语言传统、庇护关系的一种质问和嘲讽,显示出莎士比亚自身的文学主张。(Vendler:2)
麦茨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认为文德勒等人的评论脱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背景,是在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衡量当时的文学现象。文艺复兴时期,在作品中与位高权重者相对抗的现象确实存在。莎士比亚并非个例,也非创新。他不是在借此宣称自己作为诗人的独立性,只不过表示自己不愿做单纯的赞美机器。他清醒地挑出“年轻人”的缺点和不足,想通过“最诚实的朋友”这种方式使自己区别于其他对手诗人,以增进他和“年轻人”之间的亲密。莎士比亚是在使用不奉承的方式来奉承“年轻人”,这种手段比对手诗人实实在在的奉承更具杀伤力。
有时候莎士比亚似乎在倾诉真情,麦茨选取第29首十四行诗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首诗中,莎士比亚宣称“年轻人”的爱对他来说超越一切,甚至连帝王的尊贵高崇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种真挚的情感就像“拂晓时分振翅高飞的云雀”,不沾染世俗的一切尘埃。其实,这也只是莎士比亚的一种手段,以对财富和地位最轻蔑的态度来表达他对这两样东西的热望。
麦茨认为莎士比亚不论是向“年轻人”表白真挚情感,还是挑他的错,都不过是创作十四行诗的技巧和手法。莎士比亚表面上一反彼得拉克传统中花哨的比喻,另辟蹊径,使用朴素真实的语言。其实,背弃文学传统本身正是十四行诗创作的传统。莎士比亚从来都没有离开十四行诗的传统,就像他的第130首诗,句句都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但这并不是一种艺术的勇气,只是一种艺术的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使他的献诗与众不同,以此博取潜在庇护人的注意和恩宠,从而获得资助和庇护。麦茨提醒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要被莎士比亚的语言所蒙蔽,认为他真的在挑战传统,还原彼得拉克俗套之下的真相,抨击文学庇护人和被庇护人之间浮躁、虚假的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并非像现代这般超脱,成为一种唯美的艺术形式。事实是,那个时代的诗歌往往以政治功用为第一,艺术总在为世俗利益服务。
阅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候,许多读者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诗人在前126首是向一名男子表达爱情。当代学界在解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候,也常常有意识地误导读者。麦茨明确指出前126首十四行诗确实是写给一名男子的,比如第63首诗中的“他的美”,清楚地表明这位爱人的性别——男性。这组写给男性爱人的诗赞美了浪漫真挚的爱情不随时间、金钱或者心情而改变,其中包含了几乎所有我们时常吟诵或引用的名篇,比如第18首、第55首、第116首等等。可是,后一组有关那位情妇的十四行诗却截然不同。我们不常引用其中的诗作,因为这组诗中的爱情充满了嘲讽、甚至厌恶,比如第129首和第138首。
诗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同性爱是怎么回事?莎士比亚究竟是不是一名同性恋?在著名的同性恋作家或历史人物名单上,莎士比亚常常名列其中。麦茨在此处承认,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当作莎士比亚的生平来解读,确实会产生很多问题和局限性,其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很可能把莎士比亚当作同性恋。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
“同性恋”这个名词代表的是现代性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无关。麦茨认为从性的角度来解读莎士比亚,无异于把莎士比亚当成了我们同时代的人,抹杀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和当代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首先要弄清的不是莎士比亚究竟是不是同性恋,而是莎士比亚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性观念的文化差异。“同性恋”是个现代术语,有很多局限性,如果把它运用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就不啻用现代观点来解读诗中的同性爱,同时又忽略了同性爱、尤其是男性之间的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庇护文化中和社会等级文化中的重要性。
同性爱在当今文化中常被看作对正统道德观念的颠覆,然而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情形恰恰相反。麦茨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不存在“同性恋”一说,当然也没有“异性恋”这个名词。这两个名词产生于19世纪末。为何这两个名词(或相似说法)之前没有出现呢?历史学家认为,过去不是这两个名词缺失,而是这两个名词描述的人不存在。当然,在“同性恋”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并非不存在。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违法的,将判处死刑。(Foucault:43)但麦茨发现宫廷记录显示当时为此被处罚或起诉的事件几乎不存在,道德和法律显然是两回事。和“同性恋”不同的是,同性性行为不代表一种身份定位,这一点和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概念非常不同。在文艺复兴时期,婚外性行为都是罪恶的,甚至婚内的性也不能完全免除罪恶感。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和通奸一样是罪恶的,实际上通奸在当时比同性性行为更为严重,因为当局担忧它会带来私生子。
通过麦茨,我们了解到一些有趣的历史真相:在莎士比亚时代,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根本不会去考虑他们是否是同性恋者,通常也不担心自己会被起诉。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化中,男性之间的爱非常普遍,还颇受推崇。这种爱不仅是一名男子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他和另一名男子在公共、社会、政治联盟方面的保证。当时的英国是男人的天下,君王与宠臣、贵族与仆从、朝臣与追随者、庇护人和被庇护人之间,都可以找到这种男性之间的同性爱,拥有这种爱的男性会很骄傲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热烈的情感。“朋友”这个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传达的就是这种既属于私人又属于政治的密切关系。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婚姻一样,“友谊”也是一种公共关系,它通过私人之间的情感把男人之间的社会或政治利益拴在一起。“朋友”在当时等同于“爱人”。当时,男人之间表达亲密情谊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在书信中。在交互往来的信中,他们极尽修辞之能事,如恋人一样向对方表白热烈的爱。献诗也属此列。还有一处是床上:关系亲密的男人会同床共枕,比如师生、主仆或者朋友。如果一名男子的“床友”地位崇高,他将会借助这种床笫间的亲密关系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同床”在文艺复兴时期,带有很强的社会和政治意味。麦茨一再提醒读者,读莎士比亚写给“年轻人”的十四行诗时,应该了解这些重要的文化背景。
传统观点认为,莎士比亚写给“年轻人”的诗表达了纯洁的精神之爱,写给“黑情妇”的诗则充满了赤裸裸的性。在介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众多著作中,这种观点至今还颇为流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把莎士比亚拉入“同性恋”的泥沼。比如在《河滨版莎士比亚》中,哈利特·史密斯介绍十四行诗的时候就声明:“诗人对朋友的态度中交织着爱和崇拜,谦卑心和占有欲,但绝不是性欲。”而对“黑情妇”的态度则是“赤裸裸的性欲”。(Smith:1840)在企鹅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介绍部分,道格拉斯·布什则小心翼翼地告诫读者,别把诗中的友情误读为同性间的性渴望:“男性间的完美友谊……我们要知道,常常可以超越对女性的爱……存在于现实生活……,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是有目共睹的。”(Bush:13)
麦茨不否认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确实表达了对“年轻人”肉体的渴望,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友情和性根本就撇不清干系。我们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承认这个事实,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十四行诗中的主角是名男子,而不要再对两名男性之间的情爱遮遮掩掩,那样只会欲盖弥彰。在莎士比亚写给“年轻人”的十四行诗中,许多地方都意味深长。第99首诗在麦茨看来色情味就非常浓厚:“年轻人”的呼吸、手、头发、脸颊等身体部位一处处都被细细描述,显示出诗人和被描述对象之间的极度亲密关系。在其他诗中,“年轻人”也一次次被作为恋人、性对象来刻画,比如第110、104等首诗中。这些描写都清晰地传达了莎士比亚对“年轻人”肉体的欲望。莎士比亚还特别擅长使用含有性暗示的双关语,比如第52首诗就充满了这类文字游戏。但是,即使莎士比亚在诗中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欲望,并不表示两人之间就有性关系。同样,在“黑情妇”系列,虽然诗中充满了有关性的言辞,也不表示有实际的行动。麦茨认为语言表达和实际行为从来都是两回事,尤其关乎性的时候。在整部诗集中,没有一首诗、一个单词明确表示诗人和两位爱人之间有实际意义上的肉体关系。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男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而非其他。麦茨建议在阅读莎士比亚写给“年轻人”的十四行诗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生活在所有男人都是‘同性恋’的文化中是怎样一种情形?”而非“莎士比亚是个‘同性恋’吗?”当然,前提是“同性恋”这个术语不是指身份定位,只是简单指男人之间的爱和性吸引。由此看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爱情其实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下的完美友情。
在文艺复兴时期,男人之间竟能如此亲密,那么婚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麦茨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婚姻的解读颇为新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前十七首是著名的劝婚诗,其核心问题就是婚姻和孩子。在这组诗中,莎士比亚对十四行诗的传统进行了改动。传统的十四行诗中,诗人经常恳求情人和自己同床。这种行为往往是婚外的,也就是通奸。在莎士比亚的劝婚诗中,这种传统被篡改了。诗人劝这位贵族“年轻人”结婚,与他合法的妻子同床。婚姻、甚至孩子,这些和传统十四行诗根本不搭界的元素被莎士比亚堂而皇之写进前十七首诗中,但这并不证明莎士比亚对婚姻或孩子有多么崇高的态度。劝婚诗中的妻子只是“一个女人”,她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轻人”可以通过她拥有一个合法的儿子。在莎士比亚的诗中,儿子往往被另一个词“继承人”代替。莎士比亚劝“年轻人”结婚的理由是不能置家族名号和男性责任于不顾,家族名号需要血统的延续。作为一名俊美的男性,“年轻人”也有责任让他的美通过后代留在这个世界,这两项都需要“继承人”来完成。合法的“继承人”则来自一名婚姻内的母亲,因此“年轻人”不应该拒绝婚姻。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中的婚姻就是这么现实,这也解释了为何宫廷情诗的传统是私通,浪漫的爱情往往产生在婚外而非婚内。那个时代的婚姻中当然也不乏真爱的存在,但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夫妇之间的爱并不是结婚的理由。
莎士比亚虽然劝婚,但他并不认为婚姻是唯一能使“年轻人”获得永生的方式,婚姻之外还有诗。麦茨在此向读者揭示了莎士比亚常常炫耀自己诗才的真正原因。在莎士比亚眼中,婚姻的地位还不如诗歌。他的诗比起“年轻人”的婚内儿子,似乎更有把握让“年轻人”的青春和美永留人间。在第15首诗中,莎士比亚第一次提到了他可以让“年轻人”生命长青。在第17首诗中,莎士比亚明确地把他的诗和“年轻人”未来的孩子并列,认为“年轻人”不仅能通过孩子、还能通过诗,获得永生。而且,“诗”的位置被放在这首十四行诗的末尾。在双行押韵的警言式结尾中,放在末尾的“诗”其实处于全诗中最显著的位置。紧接着,在第18首诗中,莎士比亚彻底把孩子抛开,开始全力赞美他的诗在延续“年轻人”青春和美方面的巨大作用,莎士比亚用他的诗偷偷取代了“年轻人”的妻子和孩子的双重位置。麦茨认为莎士比亚这一招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其实犯了忌讳。首先,剧作家在当时几乎不受重视,诗人的地位虽稍高一些,但写诗仍被看作一种游手好闲的嗜好。其次,莎士比亚和“年轻人”之间社会地位悬殊,这种用诗来侵犯家族血统传承的作法有些过于大胆。为了不再冒犯“年轻人”,更为了维持两人之间的友谊,莎士比亚开始回归十四行诗传统。事实上,传统的十四行诗是莎士比亚和“年轻人”之间进行沟通的绝佳手段。十四行诗常常有关宫廷爱情,里面的男女主角通常是一位身份高贵的贵族女性和一个地位低下的男性诗人、仰慕者或寻求庇护者。低下的地位决定了宫廷情诗的作者常常采用一种卑微的求爱姿态,因为之前的大胆冒失,莎士比亚发现这种传统的卑微姿态对他向地位高贵的“年轻人”致意非常有用。他所要做的,不过是把传统的贵族女性换成贵族男性即可。比如在第26首中,莎士比亚就把“年轻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比作君王和臣仆。诗人把自己姿态放得越低,他对高高在上的“年轻人”的欲求就越强烈——莎士比亚迫切需要“年轻人”在社会、政治上帮助他提高地位。莎士比亚暂时把婚姻放在了一边,直至第116首。在劝婚诗中,莎士比亚对婚姻的态度是非常实际的,那是传统的男女之间的婚姻,为了家族血统的合法延续。
那么莎士比亚心中理想的婚姻是什么呢?麦茨在著名的第116首诗找到了明确的答案:婚姻,应该是两颗真心的结合。只是此处的婚姻指的是两个真心相爱的朋友、两位男性之间的心灵结合。虽然第116首诗是莎士比亚最常被引用、被吟哦的爱情诗篇,我们必须承认,这首诗是写给一名男性,而非女性。这首诗歌颂的是同性之间的真爱,不随时间、岁月改变,直到世界末日。莎士比亚在此是有意提到婚姻的。英国国教信徒在举行结婚仪式时,神父例行询问:“若谁有任何阻碍你们合法结合的理由……请坦白。”这首诗开头即是:我绝不承认两颗真心的联姻会有阻碍。
莎士比亚对传统婚姻和理想婚姻的态度经过前后对比,至此一目了然,麦茨认为莎士比亚本人的婚姻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莎士比亚把妻子留在家乡,自己长期旅居伦敦。在他的诗中,两个男性的友谊远远压倒了异性婚姻之间的爱情。婚姻之外的传统宫廷爱情呢?在第116首诗中,宫廷爱情只剩下了“红唇和朱颜”等肉体的诱惑,显得那样肤浅而短暂。两个男性之间的爱却深及灵魂,地久天长。他们之间的唯一阻碍就是社会地位的悬殊,而这正是莎士比亚向“年轻人”献诗的重要目的:赢得庇护关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劝婚诗中,女性以一张模糊的面孔充当了“年轻人”的妻子、未来儿子的母亲。除此之外,“年轻人”和女性共同现身的还有六首诗:第40—42、133—134和144首。在这些诗中,“年轻人”背叛了莎士比亚,和诗人的情妇偷情。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情妇勾引“年轻人”,是因为情妇认为“年轻人”和莎士比亚是一个人。莎士比亚虽然失去了情妇,却再次确认了自己和“年轻人”的亲密关系。“年轻人”和诗人情妇上床,也不过是赞同诗人对女人的眼光。“友谊”和“年轻人”永远是第一位,情妇最终被冠以勾引的罪名。莎士比亚认为她用欲望引诱了“年轻人”的清白之身,想把这位高尚的圣徒变成同她一样的魔鬼。在这六首诗中,女人的面目虽然比劝婚诗中清晰,但在两个男人的情感世界中她仍是可有可无,只是两个男人得以验证彼此亲密情谊的媒介。即使在专门描写“黑情妇”的诗中,我们发现莎士比亚关注的主要是她的肉体,而非精神。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中,诗人在前后两组诗中的不同态度显示出他心中两位爱人的不同地位。麦茨把第57首和第128首诗进行了对比,两首诗都充满了性暗示,表达了诗人对肉体的欲望。但在前一首诗中,莎士比亚把自己放在仆从的位置,顺从、谦卑,心甘情愿痴等“年轻人”的垂青。而在后一首诗中,诗人的口吻却半戏谑半猥亵,把“黑情妇”当作调侃戏弄的对象。莎士比亚设想“黑情妇”在抚琴,嫉妒“琴键”比自己有艳福,可以亲吻情妇的手指。既然“琴键”能那么放肆,诗人也让“黑情妇”把嘴唇送过来让他一亲香泽。其中的“琴键”(jacks)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指粗鄙而声名狼藉的下等人,莎士比亚借这个词暗示“黑情妇”已与他人有染,不用在乎再多他一个情人。这种语气和态度在其他诗中也常出现。比如在第137首诗中,莎士比亚称“黑情妇”是“众人停泊的港湾”、“公共区域”,暗示她人尽可夫。这种侮辱性的口吻在前126首十四行诗中从未出现过。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把“黑情妇”当作一个性对象,其实是把她放在传统文化模式下来描写的,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对女性身份定位的主要方向吻合。
在16、17世纪的英国,麦茨发现女性基本分为两类:“已嫁人的”或“要嫁人的”。当时对女性贞洁的要求非常严格,通奸不仅是对丈夫权威的挑战,而且还会威胁到家族血统的传承。女性的主要角色定位就是妻子和母亲,为家族血统的合法继承服务。劝婚诗中的女性正是这种形象。“黑情妇”在莎士比亚的眼中比前十七首诗中那位面目模糊的女人地位还低,因为她不仅是女性,还不贞洁。在“黑情妇”组诗中,莎士比亚一再强调:爱与男人相关,与女人相关的只有性,“黑情妇”在莎士比亚眼中不过是性的代名词。不仅如此,“黑情妇”的性带给男人的还有懊恼、沮丧和不值,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观念,认为男人一旦和女人有了肉体关系,就会沾染上女人的缺陷,从而削弱自身,第129首诗就表达了对肉欲的爱恨交织。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世界:前奏曲》中,麦茨还分析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赏析的历史变迁,认为这些诗是具有历史性的。它们不仅受莎士比亚时代的历史制约,而且还涉及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版本、校订和阐释。我们应该结合文艺复兴时期文化背景来理解这些诗歌,不能把它们作为超越时空的艺术作品来阅读。
对于莎士比亚,读者往往会有一个疑问:他非凡的文学才华来自哪里?莎士比亚并未受过高等教育,只上过“文法学校”。难道他真是个天才?麦茨在此书中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文法学校”绝非现代意义所理解的“语法学校”。“文法学校”的学生都是八到十四岁的孩子,他们每天用十二个小时学习拉丁语法而非英语语法。这些孩子受到严格的拉丁文训练,学习用这种语言写作和翻译。在文法学校的第二个阶段,这些来自中等或上等人家的男孩子已能熟练进行拉丁文和英文互译,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是奥维德、维吉尔、贺拉斯等古典诗人或者是备受推崇的文体学家西塞罗等。为了训练拉丁文风,他们还要进行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相互改编,学会修辞技巧,用拉丁文写作。他们很可能还得学一点希腊文。
现代的大学毕业生也许只知道几个基本的修辞手段,但在16世纪的文法学校,学生要学习一百多种修辞术语。麦茨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文法学校”的教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莎士比亚文风的源头,在文法学校的常规教学内容中,丰富多变、华丽甚至有些矫饰的修辞技巧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是绅士教育的必修课。这就是为什么此类文风会充斥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以及英国宫廷中。奥维德的作品在莎士比亚时代不仅家喻户晓,也是学校的教材。比如莎士比亚第60首诗,不论从主体还是意象,都是对奥维德的模仿。这首诗可以看作在强调修辞的时代,这种技巧的教育和训练在莎士比亚身上的一个突出体现。莎士比亚的父亲还算有钱,他很可能把儿子送到了当地的“文法学校”。虽然莎士比亚没有继续上大学,但“文法学校”的教育已经足够。不可否认,莎士比亚确实有非凡的天才,但他的才华很大程度上还是首先来自于他那个时代和他所受的教育,这种教育规范并促进了莎士比亚的创作才能。对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来说,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在阅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候,麦茨建议读者可以把这些诗看作莎士比亚真挚情感的流露。同时,读者也不妨换一个角度,把它们看作一种圆熟的修辞技巧的展现、一种老套的献媚,目的不过是希望所吹捧的人能提携一下诗人自己。
标签:莎士比亚论文;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文艺复兴论文; 同性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