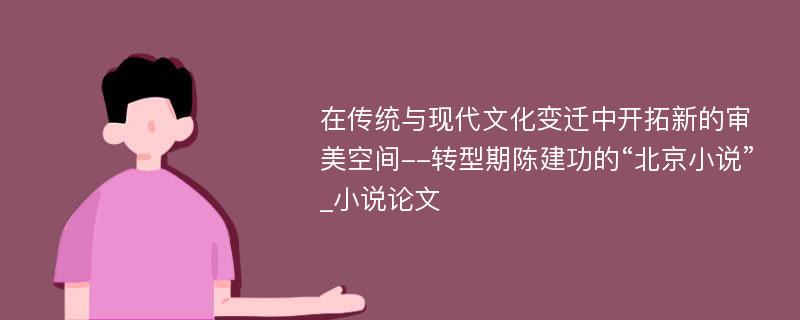
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变奏中开拓新的审美空间——转型期陈建功的京味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味论文,变奏论文,转型期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文化内涵与审美艺术形式都颇具稳定性的京味小说,80年代中期以前很以它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和传统的审美艺术范型在京城乃至全国红火了一阵子。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转型期,它的稳定性受到了挑战——虽说基本遵循着“有头有尾地讲述一个北京人的故事”模式的传统京味小说在一些报刊上还时有露面,然而拿问世于80年代初期、堪称京味小说经典的邓友梅的《那五》、《烟壶》、苏叔阳的《我是一个零》、韩少华的《红点颏》等作品与90年代的那些京味小说特别是陈建功的一些京味小说相比,或是就拿陈建功自己80年代与90年代的作品相比,无论是在文化内涵上还是在文体上都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不同。
与80年代新时期的京味小说相比,90年代转型期京味小说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其文化定位上。
新时期的京味小说是在80年代初期风靡于文学创作界的文化寻根思潮影响下发轫的。与某些作家从荒僻山野或旷远边地寻觅千古华夏的文明之根不同,京味作家们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从三千多年北京城市的文化历史积淀中去观照今日的北京,寻觅发掘着它与古老北京文化的渊源关系,洞幽烛微地捕捉着传统北京文化正负面因素在当代北京人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中遗传与变异的轨迹:或钟情于古老北京文化的现代价值,流露出浓郁的恋旧情怀;或着力于发掘传统北京文化的负面值,表现出深沉的文化批判色彩。概而言之,新时期的京味小说是以具有特定历史积淀和审美形态的传统北京文化为核心,为灵魂的。它的文化定位即在于此。
90年代转型期京味小说的文化定位则因改革开放所掀起的经济大潮和社会转型而发生了位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疾风暴雨般猛烈地冲击着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耸立如林的高楼大厦和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塞满各式汽车的高速公路打破了四合院的封闭与宁静;竞争激烈的商品大战打破了和睦有序的家庭亲情关系和重义崇礼的社会人际关系;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把北京人从容闲逸的生活常态撕成了碎片;物质诱惑刺激着享乐主义;传统道德观念被逼退到崩溃的边缘,北京文化的自足体系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全面挑战。然而,节节溃败的传统北京文化毕竟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故而有着很强的超稳定性和对他者的同化力。这样,与南方一些开放城市相比,北京城市现代化的步履就显得迟缓而阻力重重。传统的文化积习与生活方式在顽强地坚守着自己阵地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总是以极大的惯性对新生活方式进行着同化改造。因此,转型期的北京文化就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较量与兼容共存中形成为一种新的结构。在新老文化的变奏中回旋前进——这就是转型期京味小说的文化定位。这一时期北京文坛上涌现出的几位京味文学新秀,大抵都把自己的创作限定在这一文化定位之上。吕晓明的《简易楼》、《天利市场》,王愈奇的《房主》、《豆汁般的日子》等,或反映商品大潮冲击下旧思想、旧观念的沉渣泛起,或揭示转型期经济膨胀与世风日下的尖锐矛盾,在作品的精神内涵上都显示出了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变奏节律。
在京味小说创作中最准确地把握着这种文化定位的是陈建功。他不仅从80年代初期起就致力于京味小说创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对北京城市的历史变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文化性格投以特别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在他的随笔集《从实招来》中,大量记述了他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北京人接触交往中的感受体会,记载了不少他搜集整理的北京民风、民俗、民谣、民谚。陈建功不但把这些有关北京文化的丰厚积累融入了自己的“谈天说地”系列京味小说,而且进一步对京味文化与京味文学的发展走势等进行着理论思考。早在1991年他就在赴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四合院的悲戚与文学的可能性》中以犀利的目光敏锐地发现:作为传统北京文化形象喻体的“四合院”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瓦解和衰亡”。他一方面注意到在现代文明的挤压、吞蚀与包围下北京四合院文化“被挑战,被碰撞,被诱惑,被瓦解”的处境,一方面也注意到在这种处境下它的“惶恐、悲戚、愤怒,或许还有反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陈建功不仅敏锐地发现了转型期北京文化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变奏形态及其必然走势,而且进一步发掘到四合院文化“更内在的危机”在于“人们的心理空间所受到的驱赶和挤压”——在于这种文化变奏在北京人内心所激起的矛盾与冲突,喧闹与骚动,失衡与失序,怀疑与惶惑,痛苦与不安。这心灵的骚动就其本质而言是北京人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受到挑战之后一种权衡与抉择中的两难表现。比起生活方式在物质层面的诸多改变,心灵层面的痛苦与冲突自然更加沉重与深刻。陈建功从对文学本体论的认识出发指出,文学“更偏重于反映主观直觉”,“对记录人类文明某一发展时期林林总总的心路历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明晰地意识到,“这新与旧更迭的时代,这心灵骚动、寻觅的时代,或许恰恰是文学的机会。”就是说,京味文学面对着自己的对象——四合院生活方式走向崩溃的北京城和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北京人,除了应迅速调整自己的文化定位,在新老文化冲突中把握不断更迭变换的外在世界,更格外关注北京人在这种时代变革中“情感的生态平衡”状况,探究北京人在与四合院生活方式告别的过程中内在世界的心灵轨迹。他那些问世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如《找乐》、《放生》、《耍叉》等,其主要人物都是北京的老人。然而和写于80年代的《盖棺》中的魏石头和《轳辘把胡同9号》中的韩德来相比, 叙述方式上已经开始明显地“向内转。”陈建功在叙述观念上由侧重外在世界的再现转向侧重内在世界的表现,使他的京味小说创作进一步获得了文体上的启迪。他努力以文体的创新“颠覆陈旧的、令人乏味的审美定势,为读者开辟着新的审美天地”——富有深厚文化内涵和悠远历史渊源的京味小说,在世纪之交的90年代,在中国人跨入现代文明门槛的纷沓脚步中,在北京人告别四合院文化的心灵搏斗中,开始走向文体的自觉。
陈建功90年代京味小说在文体上的变革,首先表现在认知世界的基本态度——叙述立场的转变上。一般地说,在以往的京味小说中,作家们基本都采取着一种传统的知识份子叙述立场——或作为民众的启蒙导师,居高临下地解剖社会,传道解惑,开处药方;或作为民族的代言人,满怀激情地指点江山,臧否人物,评判历史。不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隐于叙述人身后的作家总是以一种教育者的姿态站在民众的对面给读者阐释一个故事。陈建功早期的京味小说,象“谈天说地”系列中的《丹凤眼》,讲述的是一个青年矿工的恋爱故事。叙述人尖锐激愤地讽刺批判了以职业、权势论人高低的腐朽观念与择偶标准,满腔热情地赞颂了男女主人公挑战世俗观念,终于获得了幸福美满爱情的勇敢乐观精神。在这里,作者即采取了一种全知全能的人生导师的叙述立场。其它如问世于80年代初的《盖棺》、《京西有个骚达子》、 《辘轳把胡同9号》等均属此类。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建功的叙述立场明显有所改变。他在中篇小说《放生》中向读者倾吐了这样一段隐衷:“或许你们还记得《盖棺》和《丹凤眼》,记得《找乐》和《鬈毛》,可我告诉你,我编得有点腻了。你是不是也有这感觉:听得有点腻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陈建功坦率地承认:作家把文学当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扮演着万能导师的社会角色,“把老百姓都给吓跑了”。陈建功经常爱说一句大白话:“别在老百姓面前装孙子”,比较文雅的说法还有“别把自己放在比蓬蒿之人高几分的位置上。”这种认知世界的态度决定了他叙述立场的“下移”——从知识分子传统的启蒙者、代言人的叙述立场转向了民间的叙述立场,以普通人的眼光去发掘普通人的心灵,用普通人的口吻去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前科》,通过作为作家身份的“我”叙述自己被派到基层派出所“体验生活”的过程,其中贯穿着跟随片警苏五一拘捕、审讯、办案,和市井小民坐在一条长凳上伪装“强奸嫌疑犯”让受害者辨认,和有“前科”的无业青年一起到小饭铺喝酒、唱歌等生活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这里并没有采取既往同类题材小说惯用的传统叙述立场——或突出知识分子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的谦恭,或突出知识分子轻视工农抵制改造的高傲,而是选取了混迹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之中,用他们的目光观察事物,用他们的逻辑思考问题,用他们的人生哲学待人处世的民间叙述立场。唯此,陈建功笔下的片警苏五一身上,威严凌厉、恪尽职守才能与温情宽囿、敷衍诡谲水乳交融于一体;寻衅伤人、捣乱滋事、犯有“前科”的胡同混混同时又是一个能讲出一大套人生哲学的、人情味十足的大孝子。这种叙述立场正可谓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叙述立场的民间化下移势必要求打破传统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为此,陈建功较多选取的是有限知情者的视角。人称上大多采用第一称“我”,把自己本人放进作品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以这种局部知情者的身分同时充当着叙述人。由于无论是作为作家的“我”,还是作为某些事件亲自参予者的“我”,抑或是作为人物行为与心灵旁观窥探者的“我”,以及由此所聚合成的作为叙述人的“我”,所能把握到的视域都要受到各自身分的限制,都不可能凌驾于人物与整个故事之上而达到全知全能,故此,由这种有限视角所开拓出的只能是有限的视域。《前科》中的片警苏五一和下放派出所体验生活的作家“我”一起摸爬滚打了一个多月,然而他对“你们这号知识分子”的认识却都只是作为人物的一种心理存在,也就只能在作为叙述人的“我”的视域之外。叙述人所感知到的只能是人物捉摸不透的有关的言行片断,于是,叙述过程便出现了“空白”,意义便带上了不确定的模糊性。比起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这种有限的视角所展现的视域自然不会那么一览无余,其意义更没有那么直露明晰。然而,空白却可以带来更多想象的空间,给叙述人,也给读者。对叙述人来说,摆脱了必须在时间与空间线索链上衔接连贯、情节结构上完整地展示生活因果逻辑的全知全能的编造之苦,叙述便因之获得了空灵、节奏和回旋的余地;对读者来说,想象使他们获得了参予艺术创造的审美自由,于是,一百个读者就有了一百个哈姆雷特。至于意义的模糊性,则更将对象置于一种叙述的半透明状态之中,造成解读时的“难以捉摸”,然而这种阅读障碍本身却形成了一个审美特区——朦胧流动,闪烁多姿,耐人寻味。
陈建功还经常在作品中利用不同人物的多重视角发掘转型期复杂多变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人物观念、心灵感受中的对话关系。《前科》就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以多重叙述视角的交叉构成有限视域多层组合的复杂叙述方式。其中主要的是作为作家的“我”的知识分子视角和片警苏五一所代表的民间视角。叙述过程中还间或插入一些其他视角,诸如社会下层失足青年的视角等,从而在不同的视角交叉中形成了不同的声音各自用自己的调子唱同一题目的多声部现象。在作品所涉及的基本人生态度上,作家“我”从自由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唱出的基调是仁爱,是博大的人文情怀;片警苏五一从最贴近平民百姓的基层执法人员的角度出发,唱出的调子是本份,是“我们就是工具,不是工具,国家花钱养你干嘛”,是出于天性的对下层百姓的同情;而无业青年秦友亮则是从自身既有疵点,又在生活地位上与社会有着深刻矛盾的无业游民的角度出发,唱出的调子是卑怯与狂放、认命与无视王法相混合的无主题变奏。这里无意说《前科》就是一部复调小说,然而陈建功多重叙述视角的运用确实在小说中造成了一种对话的关系,营造出一种复调式的氛围。它不但与变革时代社会观念及社会心态的多元多变特征相契合,而且也与作品文化内涵中传统与现代的交叉变奏形成了审美形式上的契合。
革新叙述视角的结果是引发了陈建功京味小说叙述观念的全面变革,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即在于改变了或曰深化了京味文学追求生活形态上的真实性这种传统观念。经典的京味文学作品,自老舍始,在表现北京文化的原汁原味方面极其考究,故而极力追求着状写北京城与北京人的原形原貌的真实。老舍作品中许多环境场所都采用真实的北京地名以加强真实感,单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作家对反映生活真实性追求的执着与严格。新时期的京味小说大都恪守着老舍所遵奉的依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把真实性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变革的时代给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在总体发展趋向上展示出众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已初露端倪,有的还带有“假定性”意味,似乎尚与“真实性”无缘。然而,它又总是无法超离生活的变奏所给定的“限定性”。如此,在这“假定性”与“限定性”之间,便敞开了一片神奇奥秘的尚无人涉足的空间。对于长期生活在北京城和徜徉于传统京味文学审美模式中的京味作家来说,这同样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从不同的视角对它进行观察探测,即会展现出不同的视域景观。现实生活中北京人,或许看到的是告别他们熟悉的四合院生活方式的“失乐园”的痛苦,或许看到的是在激烈文化冲突面前做出抉择的艰难,或许看到的是令人眼花缭乱、迷狂失衡的物质诱惑……而对京味小说家而言,他们看到的或许是具有丰厚积淀的传统北京文化秩序的崩溃使京味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或许是世风日下、人心浮躁对京味文学儒雅风格的冲击。而面对着京味文学世纪末衰落的陈建功却敏锐地看到了:“在这新与旧更迭的时代,这心灵骚动、寻觅的时代,或者恰恰是文学的机会”。他不但发现了这一机会,而且及时地把握住了这一机会——在北京人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与心路历程的多种可能性中,开辟着新的审美空间。
问世于1992年的《放生》可称得上是陈建功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在京味小说创作中自觉地进行文体实验的代表作。小说一开端作者就直言自己发现了一种“独具魅力的叙事角度”——将自己面对大量素材构思小说时的种种设想、推敲、筛选、加工的全过程写进小说奉献给读者。这大约可算是一种后设小说特有的视角吧!后设小说的专利并不属于陈建功,然而他利用这种形式从多重视角中展示了转型期新与旧交迭更替中北京人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及其走向的多种可能性,大大拓展了京味小说的文化空间与审美空间,同时引发了小说叙述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辟蹊径的文体创新。
展读《放生》,从作者对大量素材的斟酌、比较、推断与设想中,我们读到了沈天骢老爷子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组成的“丛林峡谷”间,在脚手架林立、搅拌机轰鸣的工地夹缝里,面对着再也找不到一枝树杈可以悬挂自己心爱的鸟笼的尴尬凄凉处境,如何选择处置爱鸟出路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无论是“放生”(包括从自家十六层楼窗放生、求小孙女带到公园去放生和自己打“的”去香山放生等多种可能方式),还是“留养”(包括求人买鸟虫、由儿子揹他下楼去遛鸟、 把鸟送人、 由热心的老伙伴用小三轮拉着或乘儿子客户的小汽车到龙潭湖去遛鸟等可能方式 ), 这种种出自作家想象却又符合着生活现实限定的可能性设想,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具有发展为现实的可能。故此,上述一切带有假设性的可能性都不是虚假的,而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这众多现实的可能性恰恰反映了变革时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且在其发展逻辑上也切合着变革时代的本质特征。这就把真实性的意义从“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反映生活”扩展为从更深更广的涵盖面上去展示生活的发展趋向,从而把对现象真实的关注提升到了对本质真实的把握。陈建功在《放生》中不但不讳言而且极力昭示沈天骢老爷子的故事都是自己编出来的,并且不断地以“编一篇小说,先让他放(生)了吧!”或“小说写到这,可以打住了,也可以接着写”而引出故事发展的许许多多假设的可能性。然而,在这每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后面,我们却都能看到一种真实的处境,一个真实的灵魂,一个真实的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无可奈何地走向衰亡和瓦解的北京四合院故事。
追求生活可能性的叙述方式不但深化了作品的真实性,而且还使陈建功作品打破了京味小说凝固的审美形式,使其不但在文化内涵上,而且在审美形式上也从传统向现代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从老舍到80年代的京味小说,一般都遵循着较为典型的情节模式,保持着较为完整规范的结构形态。即使有善用夹叙夹议的特点,也绝不打破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情节模式。加之对全知全能叙述视角的情有独钟,那文本基本上就等同于一个客观、完整的故事。陈建功《放生》为展示生活多种可能性需要而采取的后设小说叙述方式,把作家在构思小说时对生活多种可能性的比较、剖析、筛选、组合等艺术思维活动从幕后推向了前台——将它们纳入文本,展示于读者。小说的起始就并非故事的开端,而是用了三节共五千余字论述与故事本文不相关涉的小说创作中的文体问题,剖示《放生》的创作缘起,包括自己对北京老人的特殊兴趣,他们独特的文化性格并引民谣以证之。接着,再掉笔用一整节的篇幅写自己在美国参观老人院遭遇美国老人执拗地请求他唱歌的情景,并由此引出对中美两国老年人文化心理比较:一个是从容不迫,知足常乐;一个是孤独寂寞感缠身,心灵躁动不安。五千八百字过后,才收住话头,拉回到本题“讲一个北京老爷子的故事”。然而,又不马上进入故事,而是以十分怅憾的心情向读者揭示,北京的老爷子们也开始像美国老爷子那样惶惑焦躁起来了。至此,才开始回忆自己与要写的这位北京老爷子沈天骢的相识交往过程。这其间仍穿插着不少“闲笔”,如作为一个作家,对文学在社会上受冷落的感受;趋之若鹜的练气功人的各种心态等。待叙述定位在沈老爷子和他的百灵鸟们曲折的遭际之上,作者仍是围绕着忧心如焚、在放生与留养间难于定夺的沈老爷子心理与行为的多种可能性录述自己的思维轨迹。如此,《放生》的文本就不再仅只是一个“故事”而变成了一个“作家编《放生》故事的过程。”这“编故事的过程”与“故事”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在时态上,“故事”是完成体,而“过程”是现在进行时;二是“过程”把“故事”中呈隐性形态存在的被筛选或被改造了的许多原始素材和藏匿于黑暗中的作家主体艺术创造活动都还原为一种显性形态,成为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由于时态上和形态上的这些差异,“故事”显得更加完整,更加集中,更加有序,更加精致;而“编故事的过程”则显得庞杂丰富,自然随意,新鲜有趣,故而更能发人想象,揭示作家心灵深处的奥秘。总之,后设小说的叙述方式给文本带来的是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种陌生化一方面来自后设小说的文本形式,因为比较而言,人们对“小说即故事”的传统文本模式已经熟视无睹,而对“叙述作家编故事的过程”这种小说文本形式却所见甚少,当然更谈不上熟悉。因此,对其感到陌生新异就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后设小说因追求表现生活的可能性而衍生出的叙事上的不确定性,有如布满小说文本夜空的星星,每一颗都在眨动着眼睛,宛若一个个诱人的谜,吸引着读者去解读,去破译。这是其产生陌生化审美效果的第二重原因。
陌生化使读者的审美兴趣受到了全新的审美信息的刺激,并因其信息之新异而呈现出极强的“度”。这种新鲜强烈的审美刺激激发着读者的创造性审美想象,在解读文本的同时获得美感享受。利用陌生化效应开拓新的审美空间在《放生》中可谓比比皆是。小说在写“我”应沈天骢老爷子嘱托买回了蜘蛛和面包虫后,老爷子喜孜孜地喂了心爱的鸟,又得到了“我”今后继续帮助买鸟虫的许诺,心满意足地端起了酒盅。故事总该向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了吧?出人意料的是,作者旋即逆转一百八十度,设想出如下几种可能性:一、“我”当初爽了约,并没有去买鸟虫;二、老爷子托付买鸟虫的不是“我”而是他的儿子,而儿子又婉转拒绝了他的请求;三、儿子非但不买鸟虫,而且在下楼散步时又忘记了帮老父亲把困在楼上三天之久的百灵带下楼去遛一遛。这些关涉到沈老爷子和他的鸟的命运的南辕北辙的多种可能性本身就足以颠覆读者此前已经建立起的审美认知而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何况作者的叙述又改弦更张,沿着这些新的可能性发展了下去,又引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新情节——老爷子不再是喜孜孜地喂鸟、心满意足地喝酒了,而是忽而怨怼,忽而慨叹,忽而无奈,闪展腾挪,把故事引向一个凄凉的结局——把心爱的鸟放生。这一串串颠覆性叙述到这里忽然变成了小说的主旋律,陌生化效果便由此而生发繁衍出来了。
除上述叙述立场、叙述视角、叙述观点的变革外,陈建功小说叙述方式的变革更主要的表现在叙述结构上。一般地说,80年代京味小说的叙述结构往往呈现为情节模式,为组织与部署情节的发展服务。这种结构的特点是,必须构成并服从于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作者需依据经验从现象中辨别并捕捉住事物的前因后果关系链,然后依此将有关素材组合成一个头绪明晰、符合生活必然逻辑的故事。然而,文学发展到今天,情节化的小说结构越来越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事实上,现实世界中有大量现象无法纳入事物发展的因果必然关系而被排除在情节链之外,其中包括外在世界与人物内心世界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常常存在着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对于事物的发展常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故此,情节模式的单向发展常因遗弃因果链之外的这些因素而流于简单化。
京味小说由其对文化意蕴的特别看重和对笔墨情趣的执着追求,对情节模式叙事结构曾做过某些突破。自老舍始,打破情节的连贯性插入大段文化议论或闲笔点染的叙述方式已不属罕见。至新时期的京味小说就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以至出现了汪曾祺那样的叙述结构散文化的趋向。陈建功在京味小说叙述结构上的革新则是在自觉的文体意识下进行的。在他80年代的不少作品中,就显出了这种探索的痕迹。即使在他的情节模式小说中,也常常于某一情节的叙述过程中出其不意地驻笔,旁出斜逸地突然转入另一叙述单元。当然,这些尚属情节模式结构中的插入叙述,是情节自身的扩展。进入90年代,陈建功在叙述结构上的探索开始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首先,在叙述线索上,陈建功试图跳出情节模式小说结构中启承衔接紧密的故事发展线,而代之以更贴近现实生活自然形态的纷杂、无序、偶然性组合的叙述线索。其实,这些貌似自由无序的叙述线在超离了情节发展因果关系制约后,并非真正杂乱无章,而大都依照着叙述人的情感活动线索去建构和部署作品的叙述结构。这种叙述线索的选择,是因为它恰好符合了文学创作中主客体关系的规律——客观的生活逻辑必然要受作家主体审美情感的审视、筛选与规范。与情节线索链相比,情感线索链除了具有结构故事情节的功能,还可以串挂起大量为情节线所难于包容的非情节性因素,如此,就扩大了作品的生活涵纳量,拓宽了作品的审美视野,同时也就克服了情节模式在构筑形式体系时的单向性与单薄性,增强了对生活的审美概括力。《放生》的叙述结构从总体上几乎完全与作者的情感视野相迭合,是叙述人的情感投注牵动着整个事件的进展。作品最后为主人公选择了似乎是最“荒诞”、最不符合生活逻辑的放生方式——自己花钱打“的”到香山,放鸟归林。要问:为什么作家不安排沈老爷子在万般艰难的环境中克服各种困难把心爱的鸟儿继续喂养下去?那样不是能给小说带来更多曲折诱人的情节?为什么作家不让沈老爷子推开楼窗直接把鸟儿放到钢筋水泥铸就的大都市楼群中,那样不是更能突出主题,增强悲剧色彩?然而,作家的审美情感在对这剧烈动荡变革中的北京城和心灵躁动不宁的北京人进行观照时,那主客相撞击所生出的审美情感逻辑和对自己主人公的特别钟爱已经完全主宰了形象体系的发展走向——生活的客观逻辑经受着作家主观审美情感的规范与导引,汇入了主体审美情感逻辑的光辉之中。正是这贯穿始终的审美情感逻辑所形成的叙述线索,决定了形象体系的组建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于情节模式小说的叙述结构。
除了叙述线索上的变革,陈建功小说叙述结构在组合方式上也显示出了不同于情节模式的变化。他致力于恢复原本错综复杂、纷繁混沌而被情节模式淘汰得过于纯净、过于头绪明晰的现实世界本相,把被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排除在叙述结构之外的分散的、带偶然性的非情节因素拾撷回来,以便从被单纯的线性因果模式折射不到的角度去接近现实世界。那些为情节线所遗弃的生活现象便在作家审美情感视野中灿然展现出它们与情节主线的内在联系,整部作品的形式体系便因之出现了新质新变。陈建功还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手段组合他小说的叙述结构。整部作品不再仅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构体,而是形成了大小若干叙事构体的组合格局。当然,套于大故事中的小故事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却并不与主构体隔绝游离。 作者的目的也不在强调其独立的审美价值, 而在于与主构体在相互碰撞中形成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关系。
在非情节因素与非主构体故事加入后,陈建功小说的叙事结构就不再是一个情节闭合的自足世界,而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为广阔的开放的艺术世界。《放生》的叙事结构中不但涵纳了许多诸如叙述人独白(如自己在某一时期的文坛上为什么表现出沉默);散落于主情节线之外,与故事并无直接关系的生活现象(如在气功学习班里的所见所闻所感)和有关资料(如引录“耗子大爷”一整天生活作息的北京儿歌);人物心理(如沈老爷子围绕着家庭和睦的一系列心理活动)等非情节因素,而且还在总体大故事中套入了若干独立的小故事,如用第三节整整一节的篇幅讲述了自己在访问美国华盛顿某老人院时遭遇一老人执拗地要求他唱歌的故事;第六节中插入一位学识渊博却不懂人情事故的总工程师一生淡泊名利、耽于事业,而到了八十高龄却想去上海倒股票的故事。这些非情节因素和相对独立的故事或旁出斜逸,或浮游散在,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作为小说主体的情节并无关系或关系不大。依照传统结构观念属于当删除的杂枝芜蔓,然而在陈建功的小说中却成了叙述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主构体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现象世界的表层上,而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与情节主体构成了或对比、或衬托、或照应、或互补的关系。美国老人执拗地要求“我”唱歌的故事自然与沈天骢放生的故事毫不搭界,然而作者通过这种跨文化对比在揭示现代文明给老年人所带来的孤独、寂寞、心灵饥渴上,却产生了无比的艺术张力。作品因之变得丰富、深刻并带上了某种哲学色彩。作为主构体的情节部分所把握不到的某些生活意义在叙事结构的多重组合方式中被发掘了出来,作品的主题思想也便因之具有了多解性——传统北京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走向衰亡瓦解;生活方式受到挑战的北京人心灵的失落与躁动;转型期北京新老市民在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上的分化;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与发展中的污染问题;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人与自然疏远的矛盾的不可调和……可以说,《放生》通过自己独特的叙事结构方式,汇集起了性质与形态都各不相同的叙事成分。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挟带着不同的信息与意蕴投射于一个北京老人养鸟—放生的故事。牵动着作品艺术框架的组建,生活内容的圈定,社会关系的组合,人物命运的安排,文化意蕴的发掘,审美距离的调配以及文本解读玄机暗纽的设置等等,等等。
当然,随着叙事结构线索与叙事结构方式的变革,陈建功90年代京味小说的叙述结构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严整规范的风格明显地向散文化风格靠拢。情节主线索一统天下地位的打破和多种形态叙事成分的加入使小说叙事结构摆脱了许多限制而呈现出灵活多变的姿态——忽而由非情节因素的插入而显得舒缓,忽而由其它故事的插入而显得迂迴,忽而由承载多种可能性构体的集束切入而变得浓烈,忽而又由叙述人的独白而转为疏淡……忽此忽彼,忽擒忽纵,忽散忽聚,忽浓墨重彩,忽水色点染,活泼异常,形散而神不散。少了叙事结构组合中过于精雕细琢的匠气,多了不假修饰浑然天成的自然美。
陈建功小说在世纪之交所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在文化内涵上还是在文体上,都将京味小说从传统的文学领域向现代品格的建立大大推进了一步。新时期北京文坛上繁盛至极的京味小说在转型期90年代呈现出衰落景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很显然,固守旧有的文化定位与审美范型,将无法经得起时代的检验而进一步走向衰亡。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学,京味小说只有紧跟时代,开拓出展现时代风貌的审美新天地,才有可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缘。也就是说,文学在随着历史步入一个新的时空领域后,并不意味着它就自然地进入了一个新的精神空间,它要靠作家主体精神的开拓与导引。在今天,作家的现代意识,他作为创作主体的现代性精神立场、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将成为决定性因素。以80年代前期的陈建功与他的90年代相比,在精神世界中无疑是发生了一次现代性跨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许多作家一样,陈建功精神世界中的现代意识才刚刚从强权政治的重压下抬起头来。从他那一时期的作品看,尚处于恢复“五四”精神的水准上。而通过90年代的《前科》、《耍叉》、《放生》等透视陈建功的精神世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那其中清醒的理性精神立场,超离了绝对化的思维方式,重视个体生命体验的认知方式,非对应性、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以及对世界本体及人自身的深度关注——这一切,都是现代精神的基本特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确地回答为什么在京味文学走向衰落的情势下,只有陈建功能够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变奏中为其开拓出新的审美空间——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文学现代性的获得只有在作家精神世界现代意识的建立中才能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