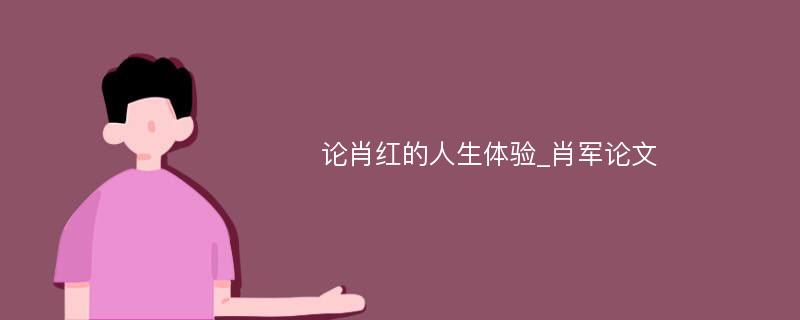
论肖红的生命体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命论文,肖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新时期的肖红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最初的“反帝爱国的女作家”的提出,到后来的“改造民族灵魂”的女作家的确认,人们的认识越来越逼近对象的实质。但遗憾的是这种探索没有继续下去,直到目前仍然停留在这一认识水平上。然而,不论是“反帝爱国”还是“改造民族灵魂”,都无法解释《马房之夜》和《后花园》这类优秀作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二者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呢?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肖红的创作中,与“反帝爱国”和“改造民族灵魂”同时存在的是她对生命的深刻体悟。
作为一个具有“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1]的女作家,肖红在致力于“反帝爱国”与“改造民族灵魂”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开始表达她对生命的体悟。从最初的《镀金的学说》到临近生命终点的《红玻璃的故事》(只有构思),她在很多作品中都或淡或浓,或片断或整体地表达了她的生命体验。她常常由某种生活情境联想到整个人生,体味并表达出人生的悲凉感。《镀金的学说》本来是通过伯父言行之间的矛盾揭露封建卫道者的虚伪的,但由他与昔日情人重遇而引发的人世感怀中,却传递出人生易老的苍凉之感。《王四的故事》的本意是表现一个不觉悟的被压迫者的悲剧的,但在他的可悲晚景与美好的青春怀想的巨大反差中,也渗透着人生的凄凉感。《小城三月》主要是揭示旧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摧残,但在主人公翠姨的悲剧命运中同样透露出人生的悲凉。“小城三月”这一题目无疑是个象征,它象征着美好生命的短暂易逝。作品在对“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的感叹中,在结尾处加上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年轻的姑娘们坐着马车去买衣料,“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的看似随意的一笔中,同样流露出生命的生生灭灭无法永驻的悲哀。而在《呼兰河传》中这一点更为明显。
如果说,上述对生命的体验还是在表达某种题旨时的偶然触发和顺手夹带,那么,在另一些作品中作家则通过完整的构思和整体形象的创造,“专事”表达了这种独特的感受。正如前文所说,肖红之所以感到人生如此悲凉,是因为她体味出“人生苦短”、“浮生若梦”,她的《马房之夜》就表达了这种感受。她在这里同样是在地主与长工之间展开情节,但她却放弃了《夜风》等作品曾经选用过的“阶级视角”,打破了阶级疆界,在生命的大视野中观照他们的关系。老长工冯山渴盼与少年时代的伙伴五东家重聚。当听说五东家不日就要到他寄身的少东家做客时,他极为兴奋,越是盼望这一刻的到来,越是担心此事是否有假,于是他逢人便问,以证虚实。他问马倌,问马夫,问厨子,问少东家,问倒脏水的老头,问丢着铜钱玩的小姑娘。这种反复的询问核实充分说明他渴见故人的心情的迫切。然而,这又绝非一种单纯的渴见故人的愿望,而是企图在这一重见中,在重见所引来的对“年青时的那一群伙伴”的回忆中,重温自己的人生旧梦,以找回失落的美好岁月。因此这种重会故友的欲望就成了生命在临近终点时对人世的苦苦挽留和死抓不放。它使人冷彻肺腑地感到了“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篇小说在肖红全部创作中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不但技巧圆熟,而且深刻地道出了人类对于生命的一种普遍感受。也许正因如此,它在发表的第二年(1937年)就被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四年后又被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成为肖红最早与外国读者见面的作品。
肖红之所以觉得人生悲凉,也在于她在原本就苦短的人生中发现竟有那样多无法回避的痛苦,而离合之悲就是其中之一;它仿佛一块极其粗砺的怪石,搓磨着人的肌肤,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痛楚啃噬着人的心灵。她在《后花园》中曾用色彩斑斓而又迷茫惆怅的笔触叙说了一幕离合的悲剧,在无限惆怅的气氛中诉说了人生的悲凉。中年光棍汉冯二成子整年孤独地踞守在昏暗的老磨屋里,与小驴老磨为伴。突然,在他心灵的荒原上燃起了一簇鲜红的爱的火苗,他爱上了邻家的少女赵姑娘。但因自惭形秽,他又不敢表露这种心迹。他把它深埋在心底,有如岩浆被埋进地心。这种感情使他欣慰也使他痛苦,他为之兴奋也为之羞愧。然而,赵姑娘出嫁了,他变得精神恍惚,惘然若失。他升起了无名的惆怅,同时也感到了某种解脱。但在为去女儿家的赵老太太送行归来的路上,他顿时被一种无以名状的落寞和伤感所包围,他向无极的虚无发出“人活着为什么要分别?既然永远分别,当初又何必认识”的追问,发出“这样广茫茫的人间,让他走到哪方面去呢?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就不管他了”的抗议!作家在这个普通长工的生命体验中,表现了离合之悲加给生命的苦痛,既有诗人的感怀,又有哲人的沉思!
在生命苦短和离合之悲外,肖红觉得人生的悲凉还在于人永远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命运总是左右着人们,把人牢牢地固定在一条苦难的人生小路上。在此弥留之际,在她无法把这种体验化成文字的情况下,她仍然把表达这种体验的完整构思口述给骆宾基,让他完成她的遗构,这就是《红玻璃的故事》。虽然骆宾基缺少肖红那种浑然圆整地表达这种体验的能力,在关键之处只能予以直露的说明,但它依旧留下了肖红的心灵印记。王大妈被前往黑河挖金子的丈夫扔在家里,在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过着“寡清”的日子,但她仍然那样乐天勤谨。即使是在大忙的秋季,也挂念着外孙女小达儿的生日。在前往女儿家为小达儿庆祝生日的路上,她与所见到的熟人说笑不止,无忧无虑。但当她愉快地吃完小达儿的生日面条后,突然发现小达儿正玩着一个红玻璃花筒,由此她受到极大的震惊。她突然顿悟到原来冥冥之中有一个命运之神在驱驶着她们祖孙三代人。“自己的童年时代,也曾玩儿过这红玻璃的花筒。那时她是真纯的一个愉快而幸福的孩子;想起小达儿她娘的孩子时代,同样曾玩儿过这红玻璃花筒,同样走上做母亲的寂寞而无欢乐的道路(她同样被去黑河挖金子的丈夫抛在家里)。现在小达儿是第三代了,又是玩儿着红玻璃花筒”。她预感到小达儿“还是逃不出这条可怕的命运的道路”。一旦“窥破了命运的奥秘”,她便感到了“生活的可怕”。她被这一顿悟震惊了,击倒了,她失去了生的欢乐。此后,人们再也“听不见她的话声”,“再也望不见她那充满生命力的眼睛和笑容了”,以致终于在这一顿悟的打击下死去了。这个红玻璃花筒也无疑是个象征,它象征了人生命运的无法逃避,苦难的无法解脱,它写尽了肖红悲凉的人生体验。
肖红之所以形成这种人生体验,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情绪状态息息相关。本来,人生是地球生命的不断衍续的存在形态,它不可能象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美好,也未必象另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可悲。在某种意义上,对它的乐观与悲观的体认都与体认者的生活遭际以及由此构成的特殊心境有关。肖红之所以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凉并不时表现它,是因为生活给了她太多的打击,她心灵的上空始终时隐时现着一片悲凉的阴云,她的这类作品无不是这片阴云出现时的投影。可以说,在肖红短暂的生命历程上,她的情绪世界一直包含着消沉与振作的双重因素,这两种因素交错着,递变着,构成她心境的特殊状态。少爱无欢的童年与坎坷多难的少年生活,使她的心灵遍布着伤疤。她象“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一只畸零的小鸟!”这种遭遇使她消沉,她真切地体味到了人生的悲凉;但同时这种苦难也养成了她倔强坚韧的反抗性格,在反抗周围的黑暗现实之际,她又充满了战斗者的乐观和振奋。走上社会以后,这两种因素仍然错杂在一起,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中,其中的某一因素就上升到主导地位,决定着彼时的心境,也影响着其时的创作。总体来说,1936年以前,她是乐观的,是振奋的。此时她在患难中与肖军结为伴侣,这个走出家庭的“娜拉”既未随落也未回来,而是开始了流浪生活。在她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2]因此尽管当时生活极为艰难,但她的情绪是乐观的,心境是开朗的。对此,肖军曾明确地说过:“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3]这种乐观奋发的精神成了她这时情绪的主旋律,为她的作品定下了昂扬振作的基调。虽然此时她心中也不乏对人生的悲凉体认,但她却很少(并非绝对没有)触及它。然而,从1936年夏季开始,肖红的情绪却出现了急剧的落潮,此前那种昂扬乐观逐渐消退下去,而几年来一直被掩抑着的消沉苦闷却主宰了她。尤其到1937年,她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她心灵中的苦水象迭起的海浪一样奔腾着向她压来。“她又陷在了深沉的,几乎是难于自拔的痛苦的泥沼中了!”[4]她痛不欲生地呻唤着:“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她说:“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5]之所以出现这种巨大的转折,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肖军在爱情上的“不忠实”深深地伤害了她。肖军后来也坦白地承认道:“我知道这一次痛苦主要是我给与她的”;“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深深地刺伤了她”。[6]这意外而巨大的打击有如一根导火索,引燃了她心中积压多年的身世之悲;有如一把利刃,揭开了她心灵上的旧伤,使她在痛苦中忆往思昔,重温早年的旧梦,而这充满着凄凄寒意的旧梦只能反转过来加剧她心灵的痛苦。这种现实与既往的双重苦痛构成无边无底的深渊,深深地吞陷着她,使她经受着折磨。这种折磨又使她本来就已多病的身体更加衰弱,而身体的垮掉又使她看到了死神的袭来,一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无限哀感彻底主宰了她。正是这多重打击所造成的心灵痛苦,令她情绪消沉,心境悲凉。因此,她心灵上空那片长期隐没着的阴云出现了,她的明亮心境隐退了,她的表现人生悲凉的一系列作品也就随之诞生了!虽然此后她的生活曾经出现过曲折,但她的心境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转变。
但是,她毕竟是现实主义者,她敢于直面现实。尽管她情绪低落,心境悲凉,但却并不悲观绝望。她个人没有因此走向颓废,没有皈依宗教,更没有自杀(象中外很多作家那样),而是支撑着面对人生,没有放弃一个作家对社会对人类的职责。她顶着生活中的各种苦难与折磨,战胜着自己病弱的身体,勤奋创作,继续用自己的笔去揭示人类的愚昧,履行着改造民族灵魂的使命,并以强烈的民族感情鼓动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甚至在即将告别人世之时,仍然对人讲述自己的创作计划,讲述着已经构思完毕而无力写出的作品。在临终前仍然挂念着没有写成的“半部红楼”,并深表“不甘”。正因如此,她在表达人生体验的作品中,也没有因为人生充满着无边的悲凉而主张逃避人生,走向佛家,走向道家,或者走向叔本华。虽然她对人生悲剧性的体认与上述诸家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对待这种悲剧的态度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肖红的表达生命体验的作品在她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它道出了生命的永恒悲凉,但又不把人引向悲观绝望,使人站在较高的阶梯上去俯视人生。即使是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艺术实践也显示着非同寻常的个性和价值。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政治革命,时代便要求文学也担负起同样的重任,而作为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也乐于自觉地充当完成社会重任的角色。因此,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社会视角,尤其是政治视角来观照和反映社会生活。但是,所有作家的这种极其合理的实践方向却无疑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项,在为数甚众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少能见到对生命现象进行哲理思索和艺术表现的作品,致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缺少“形而上”的高度和深沉。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上,我们才发现了肖红这类作品的可贵。她凭着那可贵的“叛逆之心”与“叛逆之胆”,坚执自己的信念,颇带几分任性地去从事自己的选择。在人们高喊“一切为了抗战”的情况下,她却偏偏认为“作家是属于人类的”,[7]主张以“人类意识”来观照生活。当然,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她没有忘记表现抗战斗争,从《黄河》到《旷野的呼唤》,一直注视着中国大地上的抗日斗争,鼓舞人们的抗日情绪,并以很多笔墨描写“人类的愚昧”。同时,又站在较高的基点上表现她的真实的生命体验,写出了人生的永恒悲凉,引动人们关于生命的无限遐思。它虽然缺乏政治意识,对社会革命没有直接助益,但却更富人类意识,触及了生命的奥秘,直接走入人类的心中。在她的《生死场》、《商市街》等作品风靡一时的情况下,不同国度的中国文学翻译者却共同选择没有引起中国读者充分重视的《马房之夜》加以翻译介绍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在今日的中国,一些读者喜爱肖红,除了悲悯她的身世、惋惜她的过早死去和喜爱她作品中那种如诗如画的艺术境界以外,恐怕也与她的生命体验与对这种体验的艺术表现不无关系。她的那种透骨的人生苍凉感对任何生命个体无疑都是一种强大的冲击力。也许,肖红作品的长久生命力就在这里? 注释:
注释:
[1]胡风:《生死场》读后记。
[2]肖红1937年5月9日给肖军的信。
[3]肖军:《肖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4]肖军:《肖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5]肖红1937年5月4日给肖军的信。
[6]肖军:《肖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7]肖红语,见《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载1938年6月《七月》三集三期。
标签:肖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