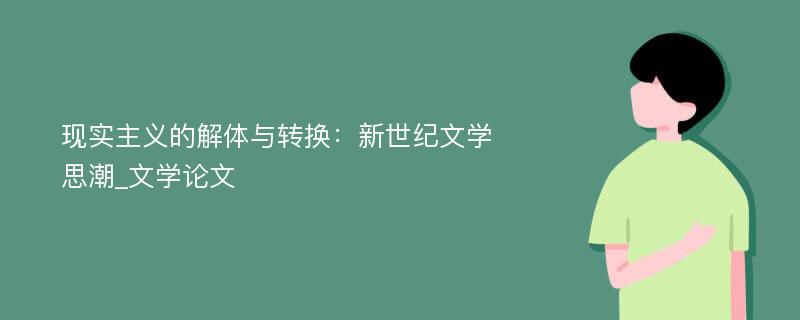
现实主义的拆解与转用——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动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长时间占据主流位置的现实主义写作,尽管在世纪末丧失了这样的位置,但作为创作方法,在新世纪仍然被很多写作者所运用或部分地运用,以至新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写作仍然举足轻重。然而,新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已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它表现为继上世纪后叶对现实主义冲击后进一步的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拆解与转用。
上世纪后叶,现实主义被冲击、被拆解,主要是对它的主流地位、权力话语地位的冲击与拆解,这种冲击与拆解在实践上体现为非现实主义的多元写作的展开。这样的实践集中见于80年代所谓先锋派文学的群体性崛起,以及90年代前几年由外部真实向内部真实的文学表现重心的转移。新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拆解,在极端政治化纠偏及认识论淡化中进行。它的理论冲动来于政治解束,来于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厌倦,以及对被过分强调的哲学认识论的逆反心理。这既是拆解现实主义的理论冲动的由来,也是对现实主义予以拆解的重点。不过,由于现实主义与主流文学的长时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文学意义的,更是政治意义的,这决定着在新世纪文坛现实主义尽管多受冲击与拆解,它的文坛地位仍具有不可忽视的象征性。现实主义对于主流文学的举足轻重的构成性,使得对于它的冲击与解构一直是很有限的。此外,由于现实主义的强大的实践根据,对现实主义中真正作为文学创作方法的那些理论内容,也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理论批判。这种情况使得现实主义被理论地拆解又被理论地保存。而在写作实践中,则出现现实主义解构中的现实主义转用问题。
一、此种真实与他种真实
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真实性。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关键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能做到真实地反映生活,则政治标准在其中实现,艺术标准也在其中实现,写作者作为艺术家的职业要求——深刻地认识生活、艺术地再现生活,也在作品的真实性中获证。因此,现实主义真实性是一个蕴涵着各种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要点的综合性标准,在其中,文学本质、文学属性、文学功用、文学构成、文学批评标准、文学创作方法、文学创作条件等理论问题均各就其位,并获得理论彰显。
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哲学根基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它以现实社会生活的物质存在性亦即客观物质性为第一性根据,文学写作实践是第一性根据的正确反映及艺术表述。在第一性命题中,确认现实生活有其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本质、规律、历史必然性,是这本质、规律、历史必然性决定着时代与历史的发展,而不是第二性的意识决定这一发展。因此所谓真实,就在于是否准确地把握并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规律及历史必然性。与之相应,就有了一套理论上系统化——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理论概括——的创作方法论。包括细节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生活具体的可视可见性,可实现性及得于生活的合理性;人物性格的客观合生活性与合自然性。这合生活性既要合于大环境生活又要合于小环境生活,还要合于人物切身关系生活,人物行为动机要从这样的多层次生活规定性中产生,人物性格也在这样的多层次规定中形成与展开。合自然性则指合于人物的生存规定性,包括神经类型规定、体质规定、性别规定、健康规定,以及这类规定在其生活经历中的心理留痕。人物性格是人物行为、人物关系展开、情节推演的动力学根据。由于性格的合生活性合自然性,因此它是一种客观规定性,写作者只能发掘它而不能随意地设置或改变。环境,如上所述,这是多层次、立体化的生活网络,它所包含的生活自身的网络信息越充分、越贴切于生活,则环境越真实。具有确定性格的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之相互作用,形成行动,演绎为人物命运及文学情节。人物与环境关系,这也是真实性的基本构成,它强调特定性格的人物与他生活其中的环境关系的互动与互构,在这样的互动与互构中,人物的性格活动越合于性格与环境关系规定,而这性格及环境关系又越合于现实生活的本质性,则人物刻画越成功。至于环境关系,它越直接地或潜在地合于现实生活的本质性与现实具体性,并且越与人物的性格活动具有内在的有机关联性,而且这内在的有机关联性也要合于生活的本质规定,则这样的环境设置与再现也就越成功。细节、人物、环境、人物与环境关系对历史发展所构成的纵深关系,这层关系是现实主义真实的深层关系,在这层关系中现实主义真实与历史必然性相遇并且相切合。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现实主义方法体系中,从细节到人物到环境再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及各方面与历史的关系,都是真实性的标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这一标准如何确认,以何种形态确认,由谁来确认。这是现实主义写作实践无法绕开的问题。这一方法体系的理论困境在于作为第一性的客观现实生活与作为第二性的文学,在其真实与否的标准上怎样建立起可供操作的依据,即是说,构成真实性的客观生活的本质、规律、历史必然性,指认其确是生活的本质、规律、历史必然性的指认权当然不是写作者,也不是阅读者。它只能是批评者在具体的文学作品批评中依据各方面材料所进行的个人指认——具体批评只能以个人形式发生,而当指认只能是个人指认时,真实性标准也就有主观设定之嫌。由此,现实主义所尽力守护的生活的客观性便在真实性批评中面临沦落为主观标准的危险。这是现实主义论的阿喀琉斯之踵。
与坚持多年的现实主义的此种真实相对,自上世纪后叶,中国文坛的一些勇于探索者在对现实主义主流话语的突围中,探索着不同于现实主义真实的他种真实。他种真实概括地说,便是与客观真实相对应的主观真实。此处说对应而不说对立,是因为他种真实亦即主观真实,并不截然排斥客观真实。说到底,客观真实的判断运作,其实也是主观运作,就像客观真理的主观运作一样。
追求主观真实,这在新世纪文学中已成为重要追求。主观真实的标准是写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主观理解、主观体验与主观感受。雷达在分析阎连科长篇小说《受活》时,引用阎连科的话说:‘他说,真实只存在于某种作家的内心,来自内心的、灵魂的一切,才是真实的,这就是写作中的现实,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① 雷达对这种现实主义的主观真实性的强调表示赞同,但对阎连科把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对立起来,甚至全盘否定客观真实的现实主义写作的说法则给予明确否定。雷达对于现实主义包括现实主义主观真实的态度,显然很正确。
主观真实性,与现实主义的客观真实性一样,也同样离不开细节、人物、环境、环境关系等要素,并且也同样是通过这些要素来表现。二者的不同,实质地说不在于表现的材料因素,而在于表现的材料因素的性质。现实主义的客观真实性,用于体现客观真实性的材料因素,力求使自己获得某种象征意义的客观性。尽管时常这客观性并不可靠,但写作者总有一种自我主观否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尽力使他的材料因素栖居于具有象征意义的客观性中。主观真实性,用于体现主观真实性的材料因素,则力求获得写作者的主观性,它们被写作者的主观理解、体验与感受所浸泡、所选择、所变形、所组合,从而成为写作者的主观性表现。而实际上,任何主观性表现,只要不是特别地强调与客观性表现的差异,则都是一种具有一定的客观普遍性的主观性,或者是一种主观的客观普遍性。见于主观的生存真实或生存的主观真实就是这样的一种真实。“体验就是生存构成。在体验中主体向对象敞开并收获对象,使对象成为主体构成部分;同样,在体验中对象也向主体敞开,邀请主体融入,使主体成为对象的构成部分;主体与对象在体验中隐没各自的界限和定性”。② 在这里,具有客观普遍性的主观真实、生存真实、体验真实,其实是一回事。
主观真实性真实,其写作者的理解、体验与感受,一般要合于写作者的个性心理活动,合于其个性心理与外部生活相互作用的一般心理规定,同时也合于这样的个性心理活动相对于同时代阅读及历史阅读可以求得的普遍的可理解可体验与可感受性。这便是主观真实性的三个层次——个性心理层次;个性心理外部接受的现实规定层次;个性心理的普遍接受层次。对作品的主观真实的判断根据,不是客观现实生活,而是接受者对于表现主观理解、体验及感受的作品所获得的合主观性。在这里,个体接受者对于所接受作品的理解、体验及感受的普遍性就是主观真实与否的标准。这里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新世纪文学所追求的主观真实中,接受的合主观性与接受的大众趣味性,之所以并不对立,甚至往往可以互相通融,其原因在于大众趣味的个人主观化,即大众趣味以其权力性作用于不同的接受个体,使之转化为接受者的具有普遍性的主观趣味,并且这主观趣味又充分渗透于个体接受的理解、体验及感受中。
如果说现实主义客观真实满足的是接受者认识生活的需求,则追求主观真实的作品所满足的便是接受者认识自我的需求。自我总是在生活中,是在生活的现实关系中行动着的自我,自我的任何行动都离不开自我的生活理解、体验及感受,因此认识生活及现实生活关系中行动的自我,便是认识自我的生活理解、体验及感受。主观真实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写作者的生活理解、体验及感受,接受者通过作品的主观真实,也就知道了主观真实的理解、体验及感受是怎么回事,从而认识主观真实的自我。而认识了主观真实的自我,也就认识了由众多主观真实的自我构成的人生现实与历史。由此说,追求主观真实的作品,与追求客观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也具有认识现实与历史的价值。
新世纪文学的主观真实表现还处于探索阶段,这一探索又正进行于新世纪市场经济在日渐有序中不断繁荣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各种社会生活情况,如利益直接化、生活图像化、系统性生活对于日常生活的威胁、交换价值对于使用价值的支配、大众趣味权力化等,以相当复杂的生活现实性构成主观真实,这足以使探索中的主观真实的文学表现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以至使所谓主观真实不同程度地不真实,这种情况见于追求主观真实的文学写作,便直接影响着新世纪初以来这类作品的质量。如绝望的写人,冷漠的写人,狗也不如的写人,当这类对于人的感受成为一种对于普遍性的人的感受时,它们就不同程度地失去了主观真实。
二、典型人物与人物典型
现实主义的数额巨大的不动产,便是一大批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典型人物,以及围绕典型人物展开的理论论述。关于典型人物,一个核心性标准便是普遍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标准中,个性的自然性及变化同一性自不必说,个性的社会性则决定着它必须在作品的具体情境中获得,这具体情境是个性人物形成并展示其个性的家庭、学校、社会群体、职业部门等。首先,作品人物的个性普遍性就产生于这类具体情境的社会普遍性及个性与这类具体情境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普遍性中——这类具体情境越集中地体现现实社会生活中同类具体情境的共性,则其普遍性越高;作品中个性人物与具体情境相互作用与生成的过程越能见出现实社会生活中同类情况下相互作用与生成的共性,其普遍性也越高。其次,作品人物的个性见于具体情境的普遍性,不可能是静止的或抽象的普遍性,它总是在变化发展着,这才有人物与环境的冲突、人物的个性活动、人物命运等。而具体情境与人物个性在相互作用中变化发展就有一个变化发展的前后限定问题。共时性地说,这属于现实社会关系限定;继时性地说,这就是历史限定。现实社会关系对作品的具体情境的限定同样有一个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实社会生活中同类限定的共性问题;历史限定也是一样,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个性人物与其具体情境的变化发展的相互作用,都有其潜在根据亦即历史根据,并都有其受这类根据作用的变化发展的取向,即向哪个方面变化发展。这里也有一个同类情况的共性体现问题。即是说,文学作品中具体情境及具体情况与个性人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展开,其展开的现实限定与历史限定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同类情况的共性,一般说,越是体现现实限定与历史限定的共性,其普遍性价值就越高。这种普遍性价值也称为现实普遍性价值与历史必然性价值。
概括地说,现实主义文学中,具体情境的普遍性,具体情境与个性人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具体情境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普遍性及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普遍性,共同体现在人物的个性生成与展现中,就有了普遍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人物标准。这是一个在写作与批评中均被长期坚持的标准。
上世纪后叶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初以来,普遍性叙事或宏大叙事,作为超越性地把握生活与阐释生活的生存姿态与生存方式,被置于解构境地。实际上,这是利益直接性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大众化,众人越来越要求切近于物、融于物的时潮在起作用。对于普遍性叙事的解构不仅是技术性的或叙事技巧、叙事视角性的,更足写作者的普遍的身份状态与身份感。超越才能发现并展示普遍,就像登高才能远眺。超越身份或超越位置的群体性失落,即失落在日常现实,沉落于琐事之中。对此,吴秀明分析说:“现实主义精神贫血其实正反映了作家创作主体的贫血。诚如大家所说,最近几年在滚滚商潮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夹击下,我们有些作家放弃了现实主义经典作家所惯有的改造社会的巨大热情,也缺乏现代主义先锋作家所独擅的抵抗平庸批判流俗的勇气,而是受‘新写实小说’的负面影响,过于粘着现实,对种种社会‘怪现状’则漠然处之,有的甚至回避价值判断,表现了浓重的虚无与媚俗倾向。”③ 现实主义与普遍性真实密切相关,普遍真实又相关着超越,超越的文学身份坚持着现实主义的普遍真实。当文学的超越身份消解时,现实主义普遍真实的解构便随之而来。普遍性叙事的理论解构不过是随顺了这一时潮而已。
普遍性解构,导致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标准的动摇、模糊、不再坚持。而文学写作,无论新生写作群体如何要挣脱脐带,独自标榜,他们都摆脱不掉自上AI写作作者的母体而来的宿命,因为他们不可能脱离语言与修辞的既定场域。这种与上AI写作作斩不断的关联,致使新世纪新生AI写作作,当然更不用说上AI写作作的转换性延续,不同程度地接受曾处于主流位置的现实主义典型人物标准的影响。而典型人物标准中普遍性的不同程度的解构,也就成为受现实主义影响的新世纪文学写作的一种新的现实规定。
这种规定普遍地体现为新世纪文学人物塑造中普遍性模糊或普遍性不再被作为标准而坚持,人物形象塑造出现了由典型人物向人物典型的转换。
个性在人物塑造中因失去了原有的普遍性追求与普遍性依托,成为写作者的主观设定。写作者进行人物的个性设定与个性展开,不再考虑或较少考虑个性的普遍性价值,接受者也越来越习惯于不再从普遍性方面去通过人物形象获得现实生活认识与启示。这是写作中人物个性设置的解束,写作者获得了巨大的个性写作自由。写作者的个性自由成为人物个性设置的自由。如温亚军的小说,擅长于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展示各种富于个性的人物,而这些人物的设置与展开,只是为了造成一定的阅读效果,追求特有的小说“意味”,而不再是什么普遍性。对此,盂繁华评论说:“读温亚军的小说就像走在洞穴中,在将要走出洞口的刹那间,迎面一缕阳光照亮了整个洞穴,那平淡无奇的过程突起波澜并惊心动魄,这就是绵里藏针不动声色。在敞开小说的瞬间,既出人意料又不可思议。我所说的温亚军小说的‘意味’,正是这个意思”④。为“意味”而写人物个性,“意味”是设置与展示的目的,人物个性写作的意义在于实现设置与展示的“意味”目的。
纵观新世纪文学的人物形象长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物个性设置与展示的自由性。写作者可以根据任何生活线索、史料线索,对人物个性进行夸张的、离奇的、跳跃的、偶然的、怪诞的、荒谬的设置与展示,而且,这种设置与展示并没有另外的目的,设置与展示本身就是目的。
个性设置与展示的价值取向,也由写作者根据不同的需要,如媚俗需要、评奖需要、改编需要、出版社编辑需要、亲朋好友需要、自我趣味需要等随意确定。在当下喧闹语境中,多数个性设置与展示需要又主要是指向随顺大众趣味与实现写作者个性自南这两个方面。而众多人物的个性设置与展示,不管其价值取向如何,又主要是为了吸引众人的阅读效果。这样,道德价值取向也好、正义价值取向也好、民族价值取向也好、法制价值取向也好、历史价值取向也好,其取向目的对于多数写作者其实就是一个——被众人所乐于接受。
写作者的个性,在人物个性设置与展示中也获得重要意义。此前在现实主义普遍性标准的要求下写作主体的个性自由,被限定为人物塑造中的倾向性,而且越隐蔽越好。在新世纪文学写作中这种限定被获准放开。众人给予这个获准,批评界也给予这个获准。写作主体在人物个性设置中的个性自由,越来越成为不言而喻的自由。人物个性及人物的个性命运,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写作主体个性所主宰。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体现普遍性深度的人物性格逻辑,已经沦为合成性逻辑,即人物性格的某种为阅读所需要的规定与写作主体所乐为的规定相合成,而且这种合成中,写作主体乐为的分量正不断增加。而直接以写作者个性为作品人物个性的人物塑造.即所谓表现自我与自我表现,在近几年的文学形象塑造中已成为重要景观。如钟晶的《我的左手》,作者着力要写的,绝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代表了怎样一种倾向或具有怎样一种共性的人物。在冬子这个主人公身上,作者所表达的是自己的内疚,并又通过冬子把这种内疚升华为悲悯,冬子因作者的内疚与悲悯而获得个性。姚鄂梅《穿铠甲的人》,是为了一种理念在写人物,并使人物成为理念的形象,杨疯子的痴情固然动人,也固然发人深思,但动人与深思的却不是典型性格的普遍性,而仅只是是否应“穿着铠甲”生存的理念,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标准便在新世纪文学中转换为个性人物标准。当然,个性人物也有个高低上下之分,除了手法与技巧的高低差异,在个性人物的塑造、接受与批评标准中,实际上是潜在着或潜用着前面说到的主观真实标准。主观真实的合主观性与合个性性规定着任何个性写作自由也都是有所限定的自由,它必然受在现实生活作用下一般主观活动程序及活动规定的限制,这是一种发之于内又见于社会普遍心理活动的限制。社会普遍的心理活动通过各种社会生活程序,内在地制约着个性主观心理活动,形成其民族制约、历史制约与时代制约,甚至更为细致,形成个性主观心理的社会群体性制约、职业制约、角色制约。建立在社会普遍心理之上的个性主观心理及建立在个性主观心理之上的个性写作自由,都在主观真实的标准下收束为另一种普遍性追求,即主观普遍性追求。主观普遍性的普遍意义,不仅在于人的普遍性理解的主观形态或对于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感知的普遍性,它更可以通过精神的光辉,使人进入超越之境。这样的超越之境,既不是日常的知,不是生活的善,又不是世俗的美,而是心灵在完满和谐之境的自由漂游。康德曾分析说:“它既然不是植根于主体的任何偏爱(也不是基于任何其它一种经过考虑的利害感),而是判断者在他对于这对象愉快时,感到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于是他就不能找到私人的只和他的主体有关的条件作为愉快的根据,因此必须认为这种愉快是根据他所设想人人共有的东西。结果他必须相信他有理由设想每个人都同感到此愉快。”⑤ 这里所谈的感受,显然是主观的感受,又是人人皆可获得的普遍性感受。对主观普遍性的至高之境,爱因斯坦描述说:“我们认识到有某种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的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的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⑥ 当然,这是主观普遍性的理想之维或超越之维,跨世纪前后文学写作中的主观普遍性,多数尚被日常的琐绪杂感所困囿,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维度。
由此说,新世纪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现实主义的客观普遍性束缚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代价便是它必须使自己进入主观普遍性的束缚之中。
在主观普遍性束缚中,主观心理程序的类分,就使人物个性设置与展示有了类分标准,如欲望性人物、智谋性人物、变态性人物、权势性人物、情感性人物、抑郁性人物、思想性人物、行动性人物等。这类分类的普遍性标准是主观性的,它从内部揭示人性及人的生存状况,并由此获得主观真实。在这样的类分标准中,越是体现类分的主观心理或主观世界共性的人物形象,便越是有文学价值的形象。更进一步,像现实主义的客观普遍性在更高层次上进入客观的历史普遍性一样,追求主观真实的主观普遍性,也有其更高的历史层次,也可进入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宗教感情”的境界。这是现实生活中主观活动的超越层次与历史层次,是体现在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社群的各种主观活动中的历史必然性。越是体现这样的历史必然性的个性人物形象,也就越是有文学价值的形象。
根据恩格斯就《城市姑娘》论及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可知依恩格斯的意思,没有体现出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相互作用的社会普遍性的作品人物,也同样可以是典型的。如果这种理解不错,那么,那些不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却合于主观类分普遍性的个性人物,也可以达到典型高度。对这类人物,可以相对于典型人物而称为人物典型。比如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写了一个女村长在选举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琐事,作者的写作意图如陈晓明在评论中所说:“不是语言对外部世界和事物反映,不是直接去还原生活现实,而是要再造一个语言的现实。在这里,他渴望通过语言本身来建构一个生活世界,并且以此来产生文学性⑦。”这样的主观追求体现在他对于繁花这个女村长的塑造上,一种忙碌且又游戏般的个性人物便产生出来。而繁花这一人物合于写作者主观意图的普遍意义,就在于她对于已成为近年来文学写作中农村干部政治工作与日常生活模式的戏谑化的解构。
此处须强调的是,这样谈论客观普遍性与主观普遍性,并不是指认新世纪写作或新世纪文学接受与批评,具有明显的主客分立的二元化倾向,这只是相对现实主义典型论的解构。把其实早已存在但却较少予以理论关注的他种真实即主观真实作进一步的理论确认,进行主客观对应性的阐释,这只是为了明理,而非为了对立。而且如前所述,时下是客观普遍性标准的模糊期与不再坚持期,主观普遍性标准也处于这样的时期。大家都在模糊地探索,又何谈确定的分立?有别但不分立,这应该是文学发展的常态。
三、系统性未定的细节生活
现实生活是由一系列细节构成,细节,无论是人的行为细节、穿着修饰细节、言谈细节、心理细节、人际交往细节,还是各种环境细节,都属于可以不断细化的具体生活形态。不过,现实生活的种种细节,总是不同生活系统的具体体现,受制于各自的系统性,如某人的生活细节,就受制于他的性格系统、具体生活关系系统、现实生活交往系统,以及促使他行动的具体环境系统等。正因为生活细节总是系统性细节,所以生活才既是个体的又是有序的,生活才在细节中井然有序地展开。
文学归根结底是生活的反映与表现,因此生活的细节构成也就规定着文学的细节构成。文学细节同样具有系统性,这系统性在现实主义写作中,体现为生活系统性的文学遵循。尽管文学中的生活系统性是虚拟的生活系统性,但两者之间保持着相似关系,这也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体现。非现实主义写作,如新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主观真实写作,细节的系统性则体现为主观活动的系统性,这主要是特定情境中的主观心理活动与行为的系统性。细节的这种系统性建立在写作者个性与所塑造人物个性的基础上。这样的系统性不受或较少受生活系统性的制约,不追求甚至否定与各种生活系统性的相似关系。如卡夫卡《城堡》中的不少细节,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理解、体验及感受的基础上,这是生活系统的变形或者变更。
新世纪文学,随着现实主义的不同程度的拆解,以及追求主观真实的写作尚在探索,致使此前相似于生活系统的作品细节系统在新世纪写作中不再作为系统而坚持,即是说,作品细节,不再坚持按照生活系统的相似性进行设置与组合;同时,这些失去了生活系统相似性的细节,在合于主观真实的系统性中,由于这一系统性在写作者与研究者中都尚处于探索与有待明晰的状况,因此也无所着落。于是,在具体文学写作中就不断出现文学细节在生活系统的相似性与主观活动系统的待构性之间忽此忽彼或亦此亦彼的情况。不少细节,能从生活系统的相似性中找到根据,同一部作品的另一些细节则游离于生活系统的相似性之外,接近于模糊的主观系统性。如罗伟章《狗的一九三二》,小说的总体视角及主要叙事线索是围绕着陈明德父子与狗的关系展开,众多精彩的细节可以找到对于生活细节的相似性。然而,作者表现其主观意图的狗的细节,如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导致幼狗小黄复归家园而被主人勒死的细节,即群狼望着月亮嚎叫,就明显地从生活系统的相似性中游离出去。
由于文学中的细节承载着文学诸因素得以展开的任务,因此,细节系统性的游移不定,就使细节承载的文学诸因素,也在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之间游移不定,或者忽此忽彼。
不过应该说,现实主义这个庞然大物,这个曾居主流的文学实践与文学批评,尽管它在新世纪被进一步拆解,甚至原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实践已不多见,但现实主义的细节真实的追求及细节真实的实践经验,则仍在新世纪写作中发挥作用。很多作品虽然在细节的生活系统相似性方面不再坚持,但在具体细节的设置与描写上,仍认真坚持与生活细节的对应关系,并由此制造一种逼真效果。即便在追求主观真实的写作中,也不乏与生活细节相对应的逼真的细节描写。这可以看做是被拆解的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种转用。王瑞芸的《姑父》,是一部用细节说话的小说,用来刻画姑父的一系列细节,逼真到令人屏住呼吸的程度。姑父出场时的细节,“下巴上有一颗黑痣,嘴里缺了两颗牙”,“两只肩膀高低不平,一颗头往高的那一边微侧过去,像在费劲扛住一个东西”,尤其是姑父的那双眼睛:“姑父的眼睛是呆定定的,看着是像假的,要生得小一点也罢,偏还生得大,眼白那么多,更像假的了”。姑父的肖像细节,特别是那对眼睛,在此后几次提到,从不同角度勾画着姑父的丑陋、怪异、胆怯,甚至卑琐。姑父的吃相细节,更是精深细微,传神摄魄——“姑父还是不说话,只见他用鹰隼般的速度,只一口就把鸭块全放嘴里了,鼓着腮嚼,脖子上的老皮跟着一抽一抽地动,动了好一阵,见他两根手指头伸进嘴里,抽出一截腿骨来,送到眼前看一看,复又放到嘴里吮一吮。吮的时候,腮帮瘪了下去,一边一个大坑。”吃相细节随后又不断出现,如偷吃金丝枣等。这类细节告诉人们的便是姑父曾怎样地饥饿,怎样为了吃而不顾一切。肖像细节、吃的细节、恐惧细节等,构成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传达的信息,是姑父在二十多年时间里,被无辜地迫害与折磨到何等令人恐惧的程度。这样的细节运用,不仅在于刻画性格,不仅在于揭示人物关系,也不仅在于表现人与环境的冲突。这些曾是现实主义细节描写的要点所在,它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强化写作者对于一段人生命运的感慨与体悟。这是写作者的主观真实的细节转译:“其耐人寻味的人性内容、历史内涵,不禁使人感叹。”⑧ 这样的细节运用,在新世纪小说写作中成为现实主义转用的常见手法。
注释:
① 雷达:《我眼中的〈受活〉》,白烨主编:《文学新书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② 高楠:《别一种真实——艺术的生存体验》,《思想战线》,2005年第2期,第91页。
③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第103~104页。
④ 孟繁华:《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张炯、白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⑤【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8页。
⑥ 许良英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5页。
⑦ 陈晓明:《戏谑化的乡村权力——评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白烨主编:《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15页。
⑧ 江水:“丰满的细节总是充满力量——读《姑父》”中国小说学会、齐鲁晚报社主编:《2005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