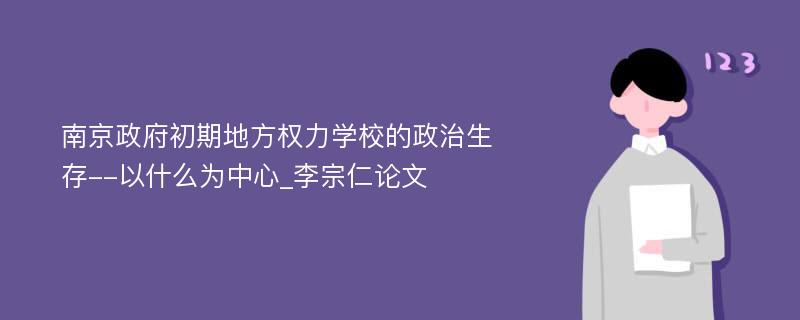
南京政府前期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生存——以何键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力派论文,南京论文,政治论文,地方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最初十年即1927—1937年,国内政治舞台的焦点之一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与其他军阀的联盟相对立”,①但具体情形之复杂远非这个“两极对立”模式所能概括。不仅蒋与反蒋两个阵营内部不断分化,而且两极之外还存在大片模糊中间地带,湖南地方实力派何键即属后者。他利用1929年蒋桂之争上台后,由于长期处在蒋桂及宁粤对立的夹缝之中,不得不极力在其间骑墙投机。以往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多忽略蒋与反蒋之间的中间地带,对何键的研究则或坚信何键始终坚定拥蒋,或对其骑墙投机一笔带过。②考察何键在统治湖南时期与中央、与西南③的应对及由此体现之政治态度与生存策略,可在一定程度消解上述研究之不足,并从地缘政治角度为解读南京政府前期各地方实力派不同的生存样态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和思路。 一、因蒋桂之争上台 何键是以1929年桂系驱鲁(涤平)之“湘案”为契机、“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而取得湖南政权的”。④1927年唐生智东征讨蒋失败后,作为唐部主力,何键第三十五军退回湖南,接受桂系改编,这是何、桂发生直接关系之始。1928年5月鲁涤平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后,何、鲁之间围绕湖南统治权的争夺日益激烈。控制两湖的桂系亦视鲁为蒋介石打入其领地的棋子,随着蒋桂矛盾凸显,开始密谋驱鲁。1929年2月13日,何键与桂系将领叶琪在岳阳密商倒鲁。19日,桂系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突然下令免去鲁涤平职务,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派兵南下驱鲁。何键上位心切,所部在鲁涤平部“尚未出城”时“已佩带桂系新发之臂章”,⑤并在湘赣边境构筑工事,对中央军“备战工作很积极”。⑥后来,桂系有人干脆说,“湘案”“差不多是由何键个人搅出来的”。⑦ 对于“湘案”,蒋介石最初反应强烈,时在中央军校读书的唐纵在日记中记述蒋说及此事,“怒形于色”。⑧蒋在“湘案”意见中指出:“湖南事变之性质……此种行为相习为风,则中央威信堕地,地方割据形成,全国更无统一之希望。”又说武汉政治分会“擅自任免湖南省主席及全部委员”,“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⑨出人意料的是,2月27日,南京政府宣布由何键“暂行代理”湘省主席。在蒋看来,何、桂虽已沆瀣一气,但何毕竟并非桂系一员,承认何键之新地位有利于拆散何、桂之间并不牢靠的合作。美国学者谢里登(一译薛立敦)分析:“可以想象,在击败努力把势力伸进湖南的桂系的1929年,如果蒋试图以自己的人来主持湖南,他将面临各地方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而他此时正准备对付冯玉祥和阎锡山。”⑩ 此时,何键已初步显示其应对蒋桂夹缝的“本事”。武汉方面任命他为湘省主席后,他以“剿匪,,任务未了为由拖延,直到几天后收到南京“暂行代理”任命始宣誓就职。蒋桂战争在鄂东等地展开后,蒋介石对何键亦不抱太大希望,仅希望其不“积极助桂”而已。3月26日,蒋致电拟由江西出兵攻击桂军的朱培德,称“如其(指何键——引者注,以下引文之括注凡未注明者均为引者注)能中立,则为助已多矣”。面对蒋委任的湖南编遣特派员一职,何同样选择拖延。为逼其就职,蒋电何指出:“湖南无中央,决无存在之理;亦即兄与桂系亦无两存之道。”希望何“当机立断,毅然就职,明白反桂”。(11) 蒋桂战争很快有了分晓,何键也一改此前的目暧昧。3月底,何键设法向桂系解释自己不再支持广西,同时派代表到南京表达对国民政府的拥护。(12)4月4日,何连夜通电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并谎称他一直没有收到中央上月24日给他的任命电,以示并未拖延。(13)4月24日,蒋介石入湘出席何之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就职礼。当着蒋的面,何键信誓旦旦:“务使我湖南成为中央的湖南,并成为中央有力量的湖南。”(14)还当场发出“讨桂宣言”,谴责桂系“滥用政分会的权力,擅发政令”,“今春迫走前主席鲁涤平”。(15)何键随即出兵入桂讨伐。 本来,1927年后何键即受桂系所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管辖,在湖南取代鲁涤平也得益于桂系“驱鲁”,桂系无异于何之保护人。何键所部又有不少广西人,如叶琪即历任何键部师长、副军长,“与何共事甚久,私交甚笃”,(16)后始脱离何键返桂。桂系两巨头白崇禧、黄绍竑与何键还是保定军校步科的同期同学。桂系在决定以何代鲁时,即考虑何虽非“理想中人”,却是“保定军校同学,较之亲南京政府的鲁涤平毕竟要好一点”。(17)“湘案”发生后,蔡元培等曾向桂系提出四项调停条件,因李宗仁拒绝后两项而未成;这两项条件就是“各军退回原防,鲁涤平回湖南”及“改组鄂、湘两省政府”,(18)可见桂系对何键之维护。因此,何键投蒋后,黄绍竑在广西省政府纪念周上指责“何键本与我们联合倒蒋,现在却被他收买了”。(19)叶琪在蒋桂战争失利后经湘回桂,曾与何匆会一面,也面斥其“背信弃义,卖友求荣”。(20) 齐锡生在分析军阀的“个人行为准则”时,认为存在“个人忠诚与政治忠诚的分离”,“政治利益会造成暂时的结合或敌对,但决不会允许它们伤害紧密的个人关系”。(21)在1928年的四川,当杨森的师长范绍增决定脱离杨森、转投刘湘时,范提出的条件是刘湘不能强迫他去打他从前的上级。(22)何、桂此时之关系也有类似之处。何键虽然借着讨桂战争的胜利,完成了从桂系作为其保护人到蒋介石作为保护人的转变,(23)更有出兵讨桂之举,但并不欲真正置桂系于死地。面对叶琪的斥责,何键辩解自己是“暂时忍痛,保存实力,以为后图”,发誓“皎皎此心,可矢天日!”5月底湘军占领桂林后,据说何键捏造入桂士兵来信,信中希望调回湖南,不愿继续在广西打仗。何乘机下令湘军从桂北后撤,以免“李、白覆灭,不符合他养寇自重的意图”。(24)蒋对此极不满。6月20日,蒋严令何固守桂林;如桂林已失,必须负责恢复。26日,蒋指“芸樵(即何键)退湘,殊为可恶”,除电令何刻日恢复桂林外,还托人警告何务必“刻日恢复桂林,否则不奉命令,擅自进退,是否革命军为党牺牲者所应如是?!”(25)7、8月间,一个名为“反小组织”的组织接连冲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及湖南省党部,另行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临时省党部”。蒋相信这“是何键捣的鬼”,一度决定彻查何键。(26)9月,受汪精卫“护党救国”主张影响的张发奎在湖北宜昌宣布反蒋,并经湖南回粤。蒋没有下令湖北军队入湘追击,引起何键怀疑,为此蒋托人转告何:“湘军对党国忠诚不渝,故付其击贼之责,不应疑鄂军不能奉命追击或另有他意也。”(27)可见此时蒋、何之间互信仍极有限。 1930年上半年,反蒋声浪再次高涨,桂系亦从广西直扑湖南,何键的态度再次暧昧起来。刘建绪师作为何键嫡系,一直退到衡阳还没有放一枪,长沙、岳阳旋被桂军占领,刘本人也想“靠拢桂系”,“根本不想同桂系打”。(28)蒋大怒,在何键代表张慕先面前怒骂何与桂系勾结。(29)事后,何键以所部参谋长刘晴初下过对桂不战之令为由,免去其职,改由蒋派来的刘膺古接任,既推卸了放弃长沙之责任,也借以表明对蒋的忠诚。 二、从“与西南为敌”到“挟西南自重” 1931年4月底,广东陈济棠等因胡汉民被蒋软禁之“胡案”,与桂系携手反蒋。由于地缘和历史关系,何键不可能对这场宁粤之争置身事外,而陷入新的政争夹缝。 “粤变”期间,何键并未动摇拥蒋的立场,甚至比以前更鲜明。5月3日,何键对部属说:“目下共匪披猖,当注全力于铲共,(粤变)若不获已而牵及于湖南,则惟有秉承中央之命令与民众之真贞心理,竭力以赴之。”(30)6月22日,何主动向蒋提出“湘军各师旅长愿就行辕觐见”。30日,蒋接见湘军各师旅长。(31)8月,当石友三受“粤变”影响在南京附近起兵反蒋时,何又表示:“南北纷扰,非一时所能安定,然结果中央胜利,蒋总司令刻下决无危险也。湘当要冲,艰苦异常,拥护中央,不计利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建议蒋“先行通电自责,如唐德宗之罪己”,剖白对蒋“至诚报效”。(32)宁粤和平会议在沪召开后,何还致电蒋之亲信刘峙,提出宁方不应与粤方召开“对等形势之会议,至损中央立场”,蒋也“不可消极,反使群龙无首”。(33) 与此相应,何键极力做出仇视广东政权的姿态,指责他们既缺乏反蒋之合法性,又破坏和平统一。5月11日,何键等致电陈济棠,劝其“取消前言、停止一切行动”,“勿为破坏和平统一之罪人”。(34)27日,在长沙市党部讲话时何键说:“凡发难必有其正确之主张,足以号召天下。若集平日绝不相侔之各派系而为一时之利害结合,谁复相信?结果亦不过同床异梦,终不免互相火并耳。”6月13日,何对衡阳各公法团体训话说:“广东政府内容复杂,精神不能一致,且无救国救民之根本办法,料其难以成功。”9月14日,何在纪念周演讲,称粤方为“逆”,强调“顺逆是非之辨不得不严”,“逆为匪之制造者,逆不消灭,则匪终无肃清之期”。(35)“粤变”初起时蒋决“取放任态度”。(36)何却致电蒋,声称“粤变”后湖南“反动分子”异常活跃,然因“我中央尚无讨逆之明令”,就算缉获亦无法“加以附逆之名”;中央若再不对“粤逆”声罪致讨,势将“影响观听,有淆顺逆之辨”。何键拥宁反粤之鲜明,连其民政厅长曹伯闻亦有所不安,提醒其对两广仍应“以种种方法应付,和缓其兵,免湘地受其蹂躏”。(37) 何键如此鲜明地“与西南为敌”,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正统意识之影响、对广州反蒋阵营邀唐生智加盟的忌恨等。当然,绝对的拥护或反对也不存在。何键这样的政治人物,无论拥宁反粤,公开表态往往言不由衷,更何况此期间他与两广仍信使往来不绝。(38) 1931年底,宁粤从决裂走向和解。次年元旦,西南方面取消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而这只是宁粤之间另一种对抗形式的发端。同日,广州成立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就“把广东的富饶经济资源和广西的军事专家与战斗素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反对南京政府的地区联合体的基础”。(39)此后数年,宁粤之间陷入类似“不战不和”之状态,是为“宁粤对立”。 何键当然明白湖南不能始终与南方强邻为敌,随着宁粤关系转变,他也表现出从“与西南为敌”到“挟西南自重”的剧变。1932年5月,何拟乘南巡郴州、衡阳之机,与陈济棠会于粤北韶关,后因故未往。(40)作为替代,“何氏日前已派有航空处长黄飞代表来粤,与当局会商剿匪计划”。(41)同年10月,何会见西南特使但衡今,大谈“非西南团结不可”,而“西南团结”又“必须如何归到事实团结,方有着落”,但衡今据此认为何与西南“利害正同”。(42)何键在日记中也记录了与西南的频繁互动。1932年5月9日,何在长沙寓所会见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前湘军将领陈嘉佑。8月6日,曾在桂军任职的湖南人郭方瑞“由粤来谈西南各省对外协会事”,郭称此会“系西南各省之学者及军人政治上之有力者所组成”,第二天又谈到“湘、粤、桂三省如能精诚团结,可为抗日、剿赤之最有力者”。9月,又有人来跟何谈“湘、桂关系密切及西南种种设施”。(43)这些来人极力鼓动何与西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到1933年上半年,甚至在蒋介石面前何键也没有掩饰对西南的好感。2月,何向蒋请示是否应赴粤,并认为“伯南(即陈济棠)、德邻(即李宗仁)二兄倾向钧座之心甚为诚恳,较之非实力派所见为高”。(44)蒋认为何对粤事之曲折“未详悉”,(45)此行会被人利用:“兄或派一头脑清晰之人前往试觇,便知内情。据报纸道路传言,南中正从事组织西南国防委员会,或欲兄出席以增声势,亦未可知。”(46)何改派秘书长凌璋赴粤。根据凌之报告,何又认为陈济棠对“剿匪”“极具决心”,(47)4月25日,何再次电蒋:“伯南兄等允任剿匪重任,为钧座分忧劳,闻之欣幸无似。”(48)蒋批示:“拟覆,并告以李、陈、蔡等敬午电内容。”(49)李宗仁、陈济棠、蔡廷锴的“敬午电”是向蒋索要“剿匪”临时费的;在蒋看来,在“剿共”经费上斤斤计较,很难说得上是为他“分忧劳”。 何键频频与西南交往并对其示好,被蒋称为“挟西南自重”。蒋这样说:“湖南则始终介于西南与中央之间,而欲挟以自重者也。”(50)广西也说湖南“大抵只藉广西这副面孔好对付中央以谋自固而已”。(51)何键的用意是通过与西南之交往显示双方关系密切,增强与南京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减轻西南对湖南的压力,化解其夹缝不利地位。 此时,何键一面“挟西南自重”,一面仍维持与蒋及南京中央的较好关系。1932年10月,蒋入湘巡视,驻节何府,何对之“礼敬勤恳”。蒋对同行的宋美龄说:“余此来一旬之久,精神颇佳,感想亦好,对于湖南之社会与教育,或有相当效力也。”(52)次年3月,蒋同时承受江西“剿共”失利、日军猛攻热河等压力,特致电何,要他“赴赣督剿,代我职权,以分忧劳”;当何谦辞不就时蒋又强调“无论如何,何之责任终须加重”。4月17日,蒋何商定双方“剿匪”责任,蒋决“以全权付之”。(53)1934年6月,何键还不顾身边“主自保者”反对,(54)就任西路“剿匪”军总司令,还花了500多万元补贴其中一些配属指挥而不属第四路军的部队。(55)这在独立性很强的地方实力派中实不多见。 如果说上述蒋、何两人的相互支持及欣赏不免含有政客间虚与委蛇的成分,那么,何在处理与中央关系上往往俯从后者,则是明显事实。以地方财税权为例,1930年1月15日,蒋在同意何扩编军队的同时,声明“在湘中央税收仍当解归中央,勿作新编之军费也”。(56)1932年2月,何以财政困难为由,拟于卷烟税附加“军事特捐”30%,煤油税附加10%,蒋立即电何声称“卷烟、煤油等税关系国际信用,望勿加税为要”。(57)1933年1月,何以筑路为由征收进出口棉纱每包2元,亦被财政部“叫停”。(58)相比何键之顺从,1933年9月,陈济棠在广东抢在中央之前变相开征洋米进口税,中央在此后数年屡次交涉,蒋亦多次出面,都无法使广东停征该税或转交中央。(59)麦科德指出,辛亥革命后历届湖南政府多截留国税,何键却被迫向南京政府上交这些收入,这使其处在比其前任军阀们更弱的位置。(60) 当然,此时蒋、何关系也并非没有不和谐音调——这也是何键“挟西南自重”的动机之一。1932年1月,何之亲信、湖南宁乡县保安大队长朱鼎三等突然逮捕国民党宁乡县党部萧学泰等十数人,指控萧为“共党”,以此打击与何作对的党部势力。接到湖南省党部的报告后,国民党中常会派方觉慧、洪陆东两位中委赴湘彻查此案。经过调查核实,方、洪认为此案疑点众多,要求将嫌犯萧学泰等解赴中央审讯;何键则坚持萧学泰并非仅有“共党”嫌疑,他根本就是“共党”,此案已完全查明,不必解赴中央。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南京方面只好搬出蒋介石。蒋并不顾及何的面子,立即下令将萧学泰一案嫌犯解赴汉口审理。何一面遵令解送,一面还是“复蒋总座一函,言萧学泰为共党之要犯,证据多起”。(61)经过重新审理,萧学泰等人均无罪释放,萧还留在中央党部任职,这无异打了何一记耳光。 在补助地方“剿匪”经费问题上,尽管蒋一再夸奖何为“剿共”出钱出力,何键仍然有所不满。1933年5月,蒋向何指出中央补助广东而不补贴湖南,仅允许湖南筹募“救国借款”,“原属万不得已之办法,固非中央对粤独厚,而对兄故有所悭吝也”。(62)8月5日,何以西路军总部月需经费50万元,“特电请蒋委员长补助”。(63)蒋又叮嘱行将入湘的张群再向何解释,希望何对中央“特加谅解”,因“芸樵与中央关系尤深”。但不久何仍以经费补贴为请。(64)一方面湖南没有像两广那样获得中央“剿共”经费补助,自行“开源”时又一再被中央制止,另一方面蒋却要何主动加强与两广的联系,坚定其倾向中央之心,何很难不感到不平和怨愤。 此外,中央上收湖南的财税亦使何键无力维持部队。何自掏腰包补助西路军其他部队时,本以为蒋最终会核销这笔款项,不料后来“蒋竟不核销他这笔钱,他只好停发全军(第四路军)薪饷数月”。(65) 在蒋、何之间隔阂渐增之际,蒋决定派张群入湘,了解何“与彼方(指西南)接洽及运用情形如何”。(66)据张群入湘后报告,何键原本希望“发行公债五百万,以资活动”,遭到“省外湘人借以抨击,省内群情怨怼”,何因此“不嗛于中央”;此时陈济棠等又“向渠极力拉拢,近又派但衡今到湘征询意见,希望一致行动”,何即派张其雄赴粤,“聊示其本怀,固不免挟西南自重”。(67)蒋对此很不满。9月底,蒋致电何之参谋长刘膺古,间接提醒何键:“西南方面之实情并非事事笼统,湘中所得报告每不相符,非观察者隔靴搔痒,即代表人别有成见,应格外注意。”(68)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公开反蒋。由于“闽变”被认为“毁党灭国”,何键当然不予支持。不仅如此,他还分别会晤陈济棠和李宗仁,帮助蒋稳住两广。何、李会晤时,李最初提出“请钧座下野及财政公开、军队待遇平等、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全国为若干国防区及绥靖区、缩短训政时期等项意见”,经何劝说,李同意“不将首项意见列入通电中”。(69)这又显示湖南在沟通宁粤方面的特殊作用。 然而,几乎同时,何键与西南的关系也在酝酿突破。1933年11月7日,胡汉民在致其妻舅陈融的密函中指出,何键派来的张其雄对西南要人“力言何确同意于反○,粤宜放心一切,与(之)缔结合作进行之约”。(70)这里“○”指蒋介石。陈融、萧佛成在何键与李宗仁会晤前也提到“湘何必欢迎桂军,则湘何与李当有默契”。(71)由于缺乏更多可靠资料,而西南元老派或会夸大何之反蒋意愿,故还难以断言何已准备放弃拥蒋,也许他仍是操其“挟西南自重”故伎。但无论如何,何键靠拢西南之举都显示蒋何之间、中央与湖南之间裂痕加大和争夺加剧。 三、扑朔迷离的1934年赴粤 1934年6月,何键亲赴广州,与西南要人多方接洽,更与两广实力派结成以反蒋为前提的三省同盟。何键此次赴粤是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首先是西南的拉拢。1934年2月11日,陈济棠对黄旭初说西南应“用某种方式使滇、黔、川一致团结”,未及于湘,似指湘已不成问题,因黄随即提到面对蒋之军事威胁,广西“只好团结粤湘,准备自卫”。(72)4月,据戴笠得到的情报,李宗仁曾提到“粤陈对联合西南各省组府虽已答允,仍迟疑,须再看何键之态度如何,方下决心”。(73)4月12日,胡汉民致函何键,表示“湘粤桂三省势如辅车……使此数省不能彻底团结共同为救亡而奋斗,恐西南不亡于军阀,将亡于外患,唇亡则齿寒”。(74)5月,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议决“粤、桂即共同派人入湘”。(75)5月16日,李宗仁致函胡汉民,表示将与陈济棠一道“对何表示决为其后盾”。(76) 其次,何键身边反中央、主自保的“旧派”也支持其入粤,何之副官熊道乾说1934年何键赴粤,“乃旧派(所谓旧者,即随芸樵最久之人也——原注)中人怂恿之”。(77) 当然,何键赴粤也体现了蒋的意志。“闽变”中西南最终保持中立,甚至谴责闽方“毁党灭国”,使蒋意识到宁粤之间仍有相通的政治基础。1934年上半年,蒋连派蒋鼎文、薛岳、蒋伯诚等入粤。5月底,何键应召赴南昌,蒋、何两人多次面谈,达成何代表蒋赴粤的决定。何即声称“此行半由其本人发起,半系奉蒋委员长之命令”。(78)但有论者仅指出“蒋派何键赴粤,既有解释误会,更有挟粤就范的意味,实为向粤宣明湖南已站在中央一方”,(79)忽略了粤方、何键等内部因素。 6月18日,何键起程赴粤。学术界对何键此行是否与两广实力派结成三省反蒋同盟,仍无明晰可信的认识。杨学东仅提及何与两广“秘密确定‘剿共’、‘防蒋’并重方针”,并未提及结盟与否。(80)陈红民则认为何“始终都未与两广结盟,关系并不密切”。(81)甚至理应知情的黄旭初也指出何此次入粤,对“改造时局”议题——这是反蒋的委婉说词,“未闻谈出何种结论”。(82) 事实上,通过《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等相对可信的第一手资料,结合《香港中兴报》的相关报道,已可断定何键在粤期间确实与粤桂实力派结成反蒋同盟。6月22日,何键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在陈私宅密谈,“结果颇佳,反门问题已趋一致”。(83)26日,何、陈、李、白等再次会谈。李起草了一个三省结盟的协议初稿,交何过目及修改。而何键“所修改(者)较原案更彻底,如关于军事之组织,以三省攻守为基础,而以推倒独裁为目的”。至此,在西南阵营看来,三省结盟问题已圆满解决。29日,萧佛成作为参与最高机密的西南元老,第一时间向在香港的胡汉民通报会谈结果:“史姑娘结合事,已得美满解决。”(84)几个月后,萧在致陈济棠密函中又提到“现在云樵已与我同盟”。(85) 随后,西南方面即有意高调“反何”,以掩饰何此行与两广有反蒋勾结。先是李宗仁提议“宣传方面对于史之莅粤不妨略加以反对字眼,为她作掩护,使门不疑其(与)我方发生密切恋爱也”。萧佛成即刊文抨击何键,“为史姑娘作掩护”,“冀门不疑其有别恋”。(86)而透过对胡汉民在香港所主办的《香港中兴报》之观察,也反映出三省结盟之事实及西南对此的欲盖弥彰。 6月23日,《香港中兴报》提到何键到粤,暗示何与西南有特殊关系:“关于应付时局,则西南各省一致实行团结,第一步对抗恶势力之侵逼,第二步则作进一步之行动,在各省团结之下,积极拥护西南政府。”又说“湘粤桂三省因区域及环境关系,尤有特殊之结合”。(87)24日,该报又称“何键来粤,外表虽云会商剿共军事,实则到来与西南当局磋商三省团结问题,盖何鉴于环境恶劣,敌人图我日亟,苟不一致团结,则湘粤桂三省必难幸免”。(88)所谓共同对抗“恶势力”及“敌人”,即暗示反蒋。而当三省结盟达成后,为配合以“反何”为何键作掩护之意图,《香港中兴报》一反前态,也开始指责何键。30日,即萧佛成向胡汉民通报三方结合事已“美满解决”的第二天,《香港中兴报》发表社论,表示以湖南之重要地位,“苟湘何能顾应国人公意以铲除独裁政治为己任”,“军阀政治不难推翻”;“彼苟忠于党国,则当唐李白(指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诸人一再讨伐独裁之际,兴兵响应,则独裁势力或早已削平”;进而抨击何键此行既是“为独裁领袖文过饰非,以减轻西南对宁府之指摘”,也是“为独裁领袖作说客,以‘合作’‘团结’一类术语缓和西南之反独裁心理”。(89)该报当天还出现“白健生(即白崇禧)先生总不会跟着蒋家人走的”、“代宁方作说客之何键”等字眼,(90)唯恐读者不清楚何键的身份和立场。 6月28日,何键和陈济棠专门商量双方如何向蒋介石交代,“以免露出马脚”。(91)何最初向蒋报告时只说其到粤“未有结果”。7月6日,何亲赴南京向蒋详报,“事略稿本”这样描述:“何键自粤来报告,公知粤已绝望,当速进行,乃预定对粤计划。”(92)几乎同时,陈济棠也向蒋通报了何在粤怂恿两广反蒋的“逆行”。12日,陈通过蒋伯诚向蒋透露: 此次何芸樵来粤所商,对钧座极不满,何谓蒋决不能共事,我们要救国救己,非三省连合防蒋制蒋不可,请伯南从速准备,并量力助湘桂,使蒋不敢先发。何又谓蒋将特税完全夺归中央,是无异缴职枪枝,我主席、总司令可不当,气不能忍。(93)这段话现场感极强,所述何对特税被夺之不满及不惜辞职以示抗议等亦为事实所证实。更重要的是,它说明当《香港中兴报》及萧佛成忠实履行以“反何”掩盖真相,从而暗示何键仍忠于蒋时,陈济棠没有这样做。14日晚,何键又与杨永泰(时任蒋之行营秘书长)、熊式辉详谈其赴粤问题。第二天,杨永泰将三人谈话要点签呈于蒋,主要内容包括“粤桂湘三省合作之七条办法”原稿是由陈济棠提供的,原有“三省合力打倒独裁”一条,已被删去;三方之间没有任何“军事协定”,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协商;何键还告诉两广领导人他曾当面问蒋,“万一(对西南)有军事时,则湘决不参加”,因此陈济棠等人听了颇为安心。(94) 至此,出现了一个刚刚结盟反蒋的何、陈两人竞相向蒋坦白甚至告密的诡异现象。由于两人事前有过商量,故其无论如何诡异仍应在“苦肉计”或“双簧”的范围内来理解;双方虽然都“揭发”了对方,但均明确否认或不提与对方有反蒋之结盟(即何键所否认的“军事协定”)。另外,蒋对西南有其基本判断,且早有征粤之意,故何键报告“粤已绝望”亦不会使西南处境更坏。反之,如果说何键和陈济棠在彼此结盟后即不约而同“毁约”并向蒋“告密”,甚至因此种诡异行为而推断三省从未结盟,不仅有违上文之种种证据,亦为湘粤稍后之反应所不支持。1934年7月,何键在庐山与湖北将领徐源泉密会。何首先表示如“西南对付蒋有通电时,彼即首先列名”,徐则回应“我们即署第二”,并“催芸樵决心”。(95)与此同时,陈济棠也在内部会议说在国内各实力派中,“现时我认为跟我走者惟一湖南,此是可决的”。(96)12月5日,胡汉民在密函中声称为对付蒋,“粤桂湘须先有军事之统筹办法,融成整个的力量”,并“宜具体的确定对滇黔方略”。(97)对比胡在1932年初所拟的西南对周边省份发展蓝图,还是“联络湖南、福建、四川,团结滇、黔”,(98)亦可见何键入粤后湘与粤桂关系的微妙变化。 不过,三省结盟确有“事实”,却可能从无“文本”,即三方一直没有在反蒋协议上签字。1934年8月初,西南要人开会,有人提议派人入湘催促何键在协议上签字,李宗仁说“今日之事,在我不在人,我有决心,人之不干者亦干,固不必乞灵于白纸黑字也”,最后决定暂缓派人。(99)8月28日,陈融致胡汉民函指出,何键曾派人来粤,询问“究竟两粤如何准备”,表示“万不能就此件一署名了事,因此件一签,无论若何秘密,门神总有所闻也”。(100)可见何并不怕结盟事为蒋所知,只是不愿光签字反蒋而无实际行动。 四、统一大潮中的迎拒 从广东回来后,何键在处理与蒋的关系上亦有可疑之处。他开始固执于不与西南开战的原则,甚至不惜为此与蒋论战。何在内部释放与西南睦邻亲善的空气,声称反对一切内战。而蒋得知“粤已绝望”后,开始作征粤“军事准备”。(101)由于湖南横在宁粤之间,蒋立即派酆悌入湘告诫何“两粤是乱党窟宅”,“不平内乱不能统一,不能统一即不能救国”。何也不服,写了数千言长函给蒋,声称湖南不能对邻省“妄启衅端”,“苟不见信任,则惟有将本兼各职一律辞去”;要不就“将我主席一职先行辞去,而(湖南)军队则照中央军饷发给,亦未尝不可”。(102) 在蒋、何之间信任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国内政局亦出现重大变化。1934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势力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向湘黔川滇等省挺进,并着手消除这些省的割据状态。是年11月,由于改组中央及收服两广一时均无从下手,何键已不可信,而湖南在此政治统一浪潮中又位置重要,蒋决定:“决先解决湘事,而对中央与西南各方,皆取和协态度。”(103) 1934年下半年,蒋针对何及湖南的强硬手段开始增多。7月,在汉口,蒋的特务以贩烟为名逮捕了湖南航空处长黄飞。10月,蒋下令湖南航空处全部人员赴南昌编并,飞机也由中央接收;年底,将黄飞处死。据黄的父亲的说法,“宋美龄知道振雄(即黄飞字)所做的事是替何老总买军火,怕何老总势力大了反蒋”,执意要蒋杀黄。(104)同年,南京的特务还暗杀了何键派去联络桂系的侄子何犹夫及桂系代表王某,以警告何。(105)此外,中央军还以“追剿”红军名义陆续入湘。蒋在11月25日致电何键时提到,“近日中央各部队陆续入湘,湘省部队亦调动频繁”。(106)一年后即“一九三五年底,中央军调入湖南者计十八师,人数约十二万”。(107) 何对此至少在表面上反应并不强烈,甚至有主动迎合之处。黄飞被捕后,何没有向蒋求情,反而致电蒋提到湖南有一架学生捐资购买的飞机,请其派员接收。(108)10月,何又自告奋勇去忠告西南,对蒋说:“当此匪患未清,外侮日甚,如伯南、健生亦效济琛、铭枢之所为,职是否先行进言忠告,以副钧座精诚团结救亡图存之期望?”(109)蒋回复:“兄处去人如有确实闻见,当盼随时电告,此时进言忠告未免过早也。”(110)当然,也有人回忆说黄飞被枪决后,“何键有苦难言,内心颇为不满”。(111)1935年3月,蒋在十日内连续致电何,何“复电甚少”,对所部“如何部署,无论事前事后,皆不详报”,使蒋“悬虑之至”。(112) 1935年6月初,由于何键态度暧昧可疑,在“解决湘事”的心理预期下,蒋一度以为粤桂湘即将联合出兵反蒋,紧急通报顾祝同等将官做好应战准备。14日,蒋电顾祝同,声称对粤桂逆谋“何亦预闻,而彼已派凌某来川密告”,似乎何已供认“预闻”“逆谋”。15日,蒋考虑湘何处置,指责“粤桂湘罪魁之卑劣成性”。17日,蒋决定“对湘何之要求当照准,以安其心”。(113)而何之要求似乎只是改组省政府及改委军师长而已。 1935年下半年,何键的权力进一步削弱。7月7日,刘建绪奉命代理何键的第四路军总指挥职务。(114)7月底,湖南省政府改组,有学者以新任财政厅长何浩若“与很多力行社员交往甚密”为由,判断“何键主湘之半独立形势”已被打破。(115)8月18日,南京批准何键的致蒋呈文,“将所有湘省税收交还财部,四路军饷粮由中央统筹支配”。(116)随后何键正式请辞第四路军总指挥。9月1日,刘建绪宣誓就职,“何键军事指挥权逐步转移到刘建绪手中”。(117)湖南军权之转移反映了何、刘之间的权力斗争被蒋成功利用,但刘仍属何键集团之“地方派”,与该集团之“中央嫡系”刘膺古、王东原等仍有很大矛盾,(118)蒋仍未完全控制这支地方部队。但总的来说,以上举动仍体现了中央对湖南的控制显著增强。而何键的反应同样不明显,只是对某些中央要员发过牢骚。如1935年12月8日,何对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说:“担任总司令,不能指挥兵队”,“总司令之下不能指挥队伍,介公北去,行营有人自为”。(119)次年2月12日,何又对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说:“湖南军队往往受行营直接命令,总司令毫不接洽。”(120)显然,何是在发泄军权旁落及对蒋撇开自己指挥湘军的不满。蒋在1936年再次莅湘时,亦感觉“于湘之何键亦似有所不安”。(121) 蒋既然已不信任何,当然要撤免其湘省主席职务,彻底“解决湘事”。1935年11月24日,蒋已“预定”“湘何内调”。次年2月8日,蒋又考虑“对何键宜派何人往说”及“湘事人选”。(122)但考虑到何在宁粤对立之中仍有“策动”、“结合”、“连络”两广之特殊作用,仍可供“运用”,(123)蒋始终未下最后决心。 五、两广事变时的投机与地方统治终结 1936年6月1日,两广突然以“抗日”为名出兵北上,震惊一时的两广事变爆发了。(124)何键不仅卷入了事变,而且在与西南的“勾结”上走得比以往都要远。 两广还在酝酿出兵时,即不断派人入湘策动。1936年5月6日,因事赴湘的熊式辉亲见正在当地活动的粤桂代表,当即向何指陈利弊,但“何键为人,利害之急,重于是非之心,口唯唯终未作斩钉截铁之答语”。(125)陈济棠之兄陈维周和桂系代表刘斐也入湘拉拢。何键在两人面前“满口答应”,还说“只要两广出兵,他马上就拥护,但要求补助军费,同时要绝对保守秘密”。(126)5月末,桂系又派李品仙、唐希抃入湘。何同样许诺:广西反蒋“我不反对,但要他们的行动达到一定的时期,湖南才能表态”。(127)何键这种态度对两广事变爆发也有助推之力。蒋后来获悉,何键与广西使者达成了多项秘密条件,包括“西南军”可入湘,但“不能攻陷长沙省会……以免舆论指责”,(128)显然,何既想联桂又不希望重演1930年桂军攻陷长沙的狼狈一幕。6月7日,李品仙、唐希抃再次入湘。这次何键没有刻意隐瞒,反而让广西来人在长沙街头“招摇过市”,据说这是让蒋知道广西已来湘策动,显示自己面临压力,而仍未动摇。(129) 衡阳向来是宁粤军事斗争的战略要点。据唐希抃回忆,他们6月7日一到长沙,何键即献计两广应抢占衡阳。蒋介石在同一天也致电何,令其“立饬罗霖师星夜运往衡阳预防,万勿延缓”;蒋也直接对师长罗霖下令其所部“主力速运衡州(衡阳之旧称)驻防”,并令罗本人“星夜亲往衡阳布防”。当天深夜,蒋再电何,称应毅然派兵固守衡阳。8日,蒋得报何不愿下令罗霖部进占衡阳,感慨“其奸诈险恶,一至于此”。(130)当天何确曾向蒋提出“罗霖邹洪各部队先在株(州)布防”,因“逆军昨已到永(州)郴(州),恐我军不能先占衡州”,蒋指其“殊为可笑”。(131)此时罗霖等部已随时可能因争夺衡阳与粤桂军冲突,然而8日晚,何键还安排罗与李品仙会面(罗曾为李部下),希望他们可以达成罗部“缓开”衡阳的交易。当李劝罗“缓开”并弃蒋投桂时,罗不为所动,坚持部队要开往衡阳。(132) 6月9日,何键仍试图阻止中央军进占衡阳。当天陈诚赶到长沙,何对陈说:“两广出兵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不应加以阻止。如两广部队通过湘境,自应准其假道。”(133)陈诚后来说:“佳未飞湘,申抵长沙,时桂逆代表李品仙尚在长沙,何键态度亦颇目暧昧,且声言中央不可占领衡州,更断言其绝对不能占领衡州。”(134)在陈诚已到长沙的情况下何键仍敢说“中央不可占领衡州”,并拒绝向罗霖下令出兵。罗霖在开往衡阳的过程中也得不到湖南的帮助,湖南公路局、铁路局不是说没有车,就是说路基不能行车。(135)同一天,蒋先是感慨何键必使衡阳“让逆”,“痛心之至”;后又感叹昨今两日夜因何键阻挡军令,恐衡阳不保,不胜悲愤,几不成寐。(136) 但如果说何键已经把赌注尽押于西南,又不尽然。在此期间,何键还一再派人进京与蒋沟通,留下与中央继续打交道的后路。两广出现异动后,何于6月4日转报中央,但未得复。(137)6日,何派秘书长易书竹入京谒蒋。(138)第二天,蒋致电何,称“易秘书长已晤见”,并“详悉种切”。(139)何复电称:“敬续派朱厅长经农、刘处长廷芳飞京报告一切,请示机宜,乞赐面训为祷。”(140)8日,翁文灏在日记中记曰:“朱经农、刘廷芳自长沙来,同见蒋。”(141)朱经农、刘廷芳进京见蒋的目的,两位当事人都说是担保何键之忠实并说服蒋尽快出兵入湘。1965年,朱经农之子朱长文说:“先父偕何之使者刘廷芳先生专机飞南京,谒今总统蒋公,痛陈情势,请其火速调军入湘,蒋公从之,局势乃稳定。”(142)这应该就是朱经农的意思。1986年,刘廷芳也说“蒋先生之所以果断出兵,正是听了我的报告才作出的决策”,“这是历史上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143)此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很大,虽有个别学者提出质疑,但刘廷芳、唐德刚坚持此事“千真万确”。(144)其实,罗霖师抢占衡阳虽然确在朱、刘两人谒蒋之后,但前者绝非后者行为之结果——蒋在6月8日会见朱、刘两人前已于前一天命令罗霖向衡阳进兵。当然,朱、刘两人未必清楚这一细节,也不排除他们在南京确实是这样说的。由此可见,何键一面配合西南的进兵,一面仍迭派要人入京以维持与中央的关系,仍是两边同时下注的投机惯伎。 6月9日深夜,罗霖率一营兵力首先赶到衡阳。粤桂军见无法抢占衡阳,开始南撤,这是两广事变的分水岭。据陈诚回忆,“至翌日(10日)清晨,何之态度始自行转变,不复以前之依维两可矣”。(145)又经过一段时间博弈,两广事变最终结束。由于存在多年的“西南”及“宁粤对立”局面不复存在,湖南的地缘政治结构也发生重大改变。虽然何键的地方统治仍维持了一段时间,但《中华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仍这样说:“两广联盟作为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被清除后,何键不再处于一个可同时跟国民政府和两广领导人讨价还价的位置,他也就失去了权力。”(146) 中央军占领衡阳及两广部队南撤后,何键的心情颇为复杂。6月13日,蒋称“湘何心犹未定”。(147)15日,何在扩大纪念周讲话,强调“这件事关系极为重大,故本人极其慎重;当事变发生之始,不仅湖南感觉得非常困难,即中央亦很慎重考虑的”,并提到1930年桂军“入驻长沙一次”,“国内人心,甚为惶惧”,(148)委婉地为自己先前态度不够鲜明辩护。21日,何对熊式辉表示愿任征讨粤逆前锋;7月14日,何在前一天谒蒋后主动致电陈济棠,敦劝其入京,这些举动颇值得玩味。 而蒋对何已彻底失去信任。6月15日,蒋明确提到“对湘何之调动时间”。(149)10月1日,蒋作九月份“反省录”时,指两广事变爆发后“川湘几乎皆已响应,其态度与两粤完全一致”。(150)从6月15日到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一直在考虑撤何之事,又始终未下决心。蒋主要担心会牵动国内政局、刺激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影响“剿共”大局。(151)因此,哪怕8月3日何派人到庐山向蒋主动请辞,(152)蒋仍未乘此免去其职。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蒋之被扣,对各地方实力派又是一个考验。何键的地方统治权力本已岌岌可危,此时想乘机重掌军权。他试图把旧部第四路军从浙江调回,但蒋很快被释回京,何急止原议。(153)期间蒋之特务还上门威胁何键,若有异动,全家将有生命危险。(154)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与日本的战争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才促使蒋介石任命一个可信任的下属(即张治中)来担任湖南领导人”。(155)11月,何被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内调为内政部长,结束了其作为地方实力派统治湖南的历史。 何键主湘时期的政治态度与生存策略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多变性及不确定性。作为主流说法,时人曹伯闻及不少学者均认为1930年中原大战后何键始终坚定拥蒋,(156)揆诸前文,当不确切。诚然,何键没有从“亲粤远蒋”最终发展到“联粤反蒋”,亦未公开放弃“拥蒋”,但他一步步靠拢西南甚至露骨地阻止中央军抢占衡阳也是事实。不妨作个假设:6月9日深夜如果是粤桂军而不是中央军抢先一步占领衡阳,(157)两广事变将如何发展?何键的态度又会怎样?就此而言,柯文提醒我们要尽量避免得出“事情的结果是前定的,不可改变的”之结论,(158)不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柯文所强调的“反事实”假设亦有陷入夸大历史发展偶然性之危险。就何键而言,其政治正统意识一向强烈,在反共、反俄仇苏、安内攘外等方面与蒋颇有共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21日,何即向蒋提出“宜先清内乱,再用兵御外”,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一种说法。一年后,1932年9月18日,何再次声称其对东北的主张包括“先安内而后攘外”。(159)因此,如蒋介石一样,把何键视同已“叛变”之“反蒋者”,“与两粤完全一致”,亦有夸张不实的一面。从根本上说,以“拥蒋”或“反蒋”的固化概念来界定何键,并不合适。 何键始终摇摆于宁粤之间,除了与其政治品性有关,主要还是由湖南的地缘政治所决定的。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仍存在大小数十个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对中央的态度及各自的生存策略往往有较大差异。两广在1931年后始终高调反蒋,云南鲜明拥蒋,四川闭省自守,何键则始终投机于宁粤之间。这种差异不能不考虑各自的地缘政治处境。粤桂滇川等省均位于中国边陲,远离当时国民党统治中心,既可较自由而鲜明地表达政见,也可不表态而置身事外。如云南之龙云,其与蒋的个人关系未必比蒋何关系更密切,对南京的政治认同也未必比何键更强烈,却以鲜明拥蒋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最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地方首领之一”,(160)其地处边远、相对湖南“安全”便是重要原因。萧佛成即曾抱怨龙云因“无压迫之虞”,故“决不愿意与西南立于同一战线”。(161)而湖南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更易受到中央军的压制。正如熊式辉所说,湖南“为中央各省与粤桂必经之通衢,一有军事,湘首当冲,其本身力量不够举足为轻重”。(162)这种地缘政治状况使何键应付维艰,不得不采取模糊而投机的生存策略。 附识:本文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台北张力、香港郑会欣、贺江枫、长沙刘利民诸位先生的帮助,承蒙三位匿名审稿人惠赐意见,一并致谢。 注释: ①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②有关何键之研究,较重要的有陈志凌:《略论何键对湖南的统治》,《近代中国人物》第2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549—578页;李炳圭:《何键》,谢本书主编:《西南十军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6—317页;杨学东:《何键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Edward A.Mccord,Residual Warlordism in the Nanjing Decade:He Jian in Hunan (draft),“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暨第二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184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杭州,2012年6月9日。 ③本文中的“西南”是流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政治术语,多指两广或两广用以自称,除两广实力派外,还包括胡汉民、萧佛成、邹鲁、陈融等所谓“元老派”,湘黔等地方实力派有时也自认为“西南”一分子。 ④刘岳厚:《国民党湖南甲乙派的斗争》,《湖南文史资料》第3辑,1962年,第8页。 ⑤《旅京湘同乡会呈请惩办何键文》,《中央日报》1930年8月18日,第2张第3版。 ⑥《万耀煌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 ⑦杨国材:《1929年蒋桂战争前桂系的舆论准备》,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⑧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⑨雷啸岑:《三十年动乱中国》,香港:亚洲出版社,1955年,第138页。 ⑩James E.Sheridan,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pp.197-198. (11)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270、267—268页。 (12)"Ho Chien," in Howard L.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2,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62. (13)参见张慕先:《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1963年,第153页。 (14)《湖南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1期,转引自李炳圭:《何键》,谢本书主编:《西南十军阀》,第297页。 (15)《何键之讨桂宣言(续)》,《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5月11日,第4版。 (16)张慕先:《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44页。 (17)唐希抃:《何键与桂系互相勾结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75页。 (18)陈进金:《“两湖事变”中蒋介石态度之探讨(1929)》,《国史馆学术集刊》2006年第8期。 (19)杨国材:《1929年蒋桂战争前桂系的舆论准备》,广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第35页。 (20)魏镇:《关于〈何键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的补充订正》,《湖南文史资料》第9辑,1965年,第205页。 (21)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154页。 (22)参见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23)Edward A.McCord,Residual Warlordism in the Nanjing Decade:He Jian in Hunan(draft),pp.22-23. (24)魏镇:《关于〈何键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的补充订正》,《湖南文史资料》第9辑,第205、207—208页。 (25)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61、78、77页。 (26)参见文任武:《何键统治湖南初期的一次党潮》,《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1963年,第206—209页。 (27)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第496页。 (28)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湖南文史资料》第7辑,1964年,第9页。 (29)参见张慕先:《何键利用蒋、桂矛盾取得湖南政权》,《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58页。 (30)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31)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317、333页。 (32)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第85、107页。 (33)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248页。 (34)田伏隆主编:《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35)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第44、54、102页。 (36)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第164页。 (37)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第47、81页。 (38)参见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第53、56、83、100、101页;唐希抃:《何键与桂系互相勾结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76页。 (39)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40)参见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第114—116页;《西南执行部政务会昨晨召开临时联席会议》,《香港华字日报》1932年5月20日,第2张第1页。 (41)《何键无来粤消息》,《香港华字日报》1932年5月23日,第2张第1页。 (42)《附:但衡今电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85页。 (43)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第113、145、155页。 (44)《何键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6日),全宗名:蒋中正总统文物(以下径称“蒋档”),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一年(十五)。 (45)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8),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99页。 (46)《蒋介石致何键电》(1933年2月7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一年(十五)。 (47)《何键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18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一年(十七)。 (48)《何键致蒋介石电》(1933年4月25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二年(九)。 (49)《蒋介石批示》(1933年4月),蒋档,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二年(九)。 (50)周美华编注:《蒋介石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5),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167页。 (51)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第21节)——我被推晋京参加四中全会经过》,《春秋》(香港)第124期,1962年9月,第4页。 (52)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31、318页。 (53)高明芳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31、237、432页。 (54)参见《张群致蒋介石电》(1933年9月8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二年(四十九)。 (55)参见杨学东:《何键传》,第556—557页。 (56)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394—395页。 (57)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216—217页。 (58)参见《何键请征收棉纱附加财部已复咨取销》,《中央日报》1933年1月14日,第1张第3版。 (59)参见姜抮亚:《1935年的汕头事件——1930年代广东地方关税(专税)和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6—327页。 (60)Edward A.McCord,Residual Warlordism in the Nanjing Decade:He Jian in Hunan(draft),p.37. (61)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第139、142—144、146页。 (62)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29页。 (63)《何键电蒋请补助剿匪经费》,《中央日报》1933年8月7日,第1张第2版。 (64)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2),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03、340—341页。 (65)杨学东:《何键传》,第556—557页。 (66)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2),第204页。 (67)《张群致蒋介石电》(1933年9月8日),蒋档。 (68)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2),第597页。 (69)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108—109页。 (70)《胡汉民致陈融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6册,第407页。 (71)《陈融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431页。 (72)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第21节)——我被推晋京参加四中全会经过》,《春秋》(香港)第124期,1962年9月,第7页。 (73)《江汉清致蒋介石电》(1934年4月17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三年(十八)。(“江汉清”是戴笠化名) (74)《胡汉民致何健(键)函稿》,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429页。 (75)《陈融致胡汉民电》,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8册,第469页。 (76)《李宗仁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8册,第528页。 (77)《杨熙绩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472页。 (78)《四总司令发联名通电西南已接受中央方针》,《湖南民国日报》1934年6月28日,第2版。 (79)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80)杨学东:《何键传》,第425页。 (81)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6页,脚注1。本书还将何键此次赴粤误系于1933年6月间(第33—35页),由此造成《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一文的以下误判:福建事变前,何键曾与西南走得很近,甚至亲抵广州,筹商粤、桂、闽、湘四省联合反蒋。 (82)黄旭初:《广西与中央廿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第21节)——我被推晋京参加四中全会经过》,《春秋》(香港)第124期,1962年9月,第7页。 (83)《萧佛成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463页。此处及下段之“门”均指蒋介石。 (84)《萧佛成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422页。胡汉民、萧佛成等人之间的秘密通信,常以“史姑娘”、“史大姑娘”、“史湘云”等指代何键,因其乃湘人,字芸樵,暗合《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下一引文中萧佛成所说的“云樵”及下段李宗仁所说的“史”均指何键。 (85)《附:萧佛成致陈济棠函稿》,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489页。 (86)《萧佛成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465、466页。 (87)《粤湘桂三省尤有特殊关系》,《香港中兴报》1934年6月23日,第1张第3页。 (88)《何芸樵昨发表谈话》,《香港中兴报》1934年6月24日,第1张第3页。 (89)《何键返奉化复命(社论)》,《香港中兴报》1934年6月30日,第1张第3页。 (90)参见《香港中兴报》1934年6月30日,第1张第3页。《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一文将《香港中兴报》此期间此类指责何的报道和评论,作为何在粤期间与西南“误会”“深化”之表现,并称何此时已“择善而从”,意为何已选择倒向蒋方(《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91)《萧佛成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465页。 (92)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417、498页。 (93)《蒋伯诚致蒋介石电》(1934年7月12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一呈表汇集(九)。 (94)《杨永泰致蒋介石签呈》(1934年7月15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一呈表汇集(九)。 (95)《张英宾镇远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476页。 (96)《陈融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466页。 (97)《胡汉民致陈融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6册,第469页。 (98)《胡汉民拟电稿》,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521页。 (99)《杨熙绩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474页。 (100)《陈融致胡汉民电》,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468页。 (101)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6),第498页。 (102)《陈融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463—464页。 (103)《困勉记初稿》(1934年11月27日),蒋档,卷名:困勉记初稿(四)。 (104)杨学东:《何键传》,第511页。 (105)参见黄德曾:《湖南的特务机构湘站的发展和活动》,《湖南文史资料》第32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2—73页。 (106)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8),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489页。 (107)威达:《西南异动始末之回想》,广州:国民印务有限公司,1936年,第7页。 (108)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7),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536—537页。 (109)《何键致蒋介石电》(1934年10月17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三年(四十五)。 (110)《蒋介石致何键电》(1934年10月19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民国二十三年(四十五)。 (111)程藩斌:《黄飞贩毒被捕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1964年,第151—152页。 (112)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0),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273页。 (113)详见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1),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345—349、361、36 7、376页。 (114)刘建绪是从1918年即追随何键的老部下,也是何之保定军校同学和醴陵同乡,此时与何产生了权力争夺。 (115)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400页。何键的副官熊道乾则把何浩若称为湖南内部较亲蒋的“新派”。(《杨熙绩致胡汉民函》(1935年2月22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472页) (116)《湘军饷粮将由中央统筹》,《大公报》(天津)1935年8月19日,第1张第3版。 (117)田伏隆主编:《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1840—1990)》,第164页。 (118)参见彭松龄、黄维汉、胡达:《何键军事集团的形成和瓦解》,《湖南文史资料》第7辑,第42—45页。 (1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52、657页。 (120)《翁文灏日记》,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页。 (121)《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洪朝辉编校,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122)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4),台北:“国史馆”,2009年,第473页;蔡盛琦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5),台北:“国史馆”,2009年,第555—556页。 (123)参见蔡盛琦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5),第558、563、569页;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台北:“国史馆”,2009年,第20页。 (124)有关两广事变,较重要的研究主要有陈存恭:《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探讨“安内攘外”政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1984年;罗敏:《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25)《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190页。 (126)刘斐:《两广“六一”事变》,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3—464页。 (127)李觉:《“两广事变”见闻》,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6页。 (128)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第321—322页。 (129)唐希抃:《何键与桂系互相勾结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77页。 (130)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第187—188、191、193页。 (131)陈诚:《两广事件之军事经过》,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全宗名:陈诚副总统文物(以下径称“陈档”),卷名:两广事件之军事经过。 (132)唐希抃:《何键与桂系互相勾结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77页。 (133)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135页。 (134)陈诚:《两广事件之军事经过》,陈档。 (135)参见罗子雯:《两广“六一”事变中何键玩弄两面手法》,《湖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83页。(罗霖,字子雯) (136)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第197页。 (137)何键:《关于两广出师抗日的传说——六月八日在扩大纪念周中报告》,《中山周报》第87期,1936年6月,第6页。 (138)翁文灏:《翁文灏日记》,第50页。 (139)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第187页。刘廷芳说易书竹入京后一连7天都见不到蒋,何键才派他和朱经农紧急赴京(见刘廷芳:《记两广“六一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的经过》,《传记文学》(台北)第50卷第2期,1987年2月,第24页,此文最早发表于1986年)。 (140)《何键致蒋介石电》(1936年6月7日),蒋档,卷名:一般资料—呈表汇集(四十五)。 (141)《翁文灏日记》。第51页。 (142)朱经农:《爱山庐诗钞》,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60页。 (143)刘廷芳:《记两广“六一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的经过》,《传记文学》(台北)第50卷第2期,1987年2月,第24页。 (144)唐德刚:《代刘廷芳先生说几句话(书简)》,《传记文学》(台北)第50卷第5期,1987年5月,第78页。 (145)陈诚:《两广事件之军事经过》,陈档。 (146)"Ho Chien," in Howard L.Boorman,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2 p.63. (147)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第223页。 (148)《望大家镇静维持常态》,《湖南民国日报》1936年6月16日,第6版。 (149)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第263、277、468—469、240页。 (150)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8),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545页。 (151)参见叶健青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7),第311、324、372页;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8),第60页;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9),2009年,第147页。 (152))《翁文灏日记》,第66页。 (153)彭松龄、黄维汉、胡达:《何键军事集团的形成和瓦解》,《湖南文史资料》第7辑,第46页。刘建绪担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后,为摆脱何键的影响,先率军远赴黔滇“追剿”红军,后率部开入浙江驻防。 (154)黄德曾:《湖南的特务机构湘站的发展和活动》,《湖南文史资料》第32辑,第73页。 (155)James E.Sheridan,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p.198. (156)以下诸人均持此种观点,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湖南文史资料》第7辑,第23页;陈志凌:《略论何键对湖南的统治》,《近代中国人物》第2辑,第559页;李炳圭、张经国、魏汝珍:《一九三○年军阀何键两次失守长沙述评》,《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3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5页。 (157)这并非不可能。据陈诚回忆,当中央军进入衡阳时,粤桂军离此亦只有30里。(参见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136页) (158)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59)高原、陈永芳主编:《何键·王东原日记》,第105、161页。 (160)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当然作为地方实力派。龙云与中央及蒋同样有冲突,宁粤对峙期间他同样在宁粤之间搞平衡,这里只是相对来说,且主要是指抗战以前。 (161)《萧佛成致胡汉民函》,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1册,第468页。 (162)《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第190页。标签:李宗仁论文; 胡汉民论文; 何键论文; 两广事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陈济棠论文; 剿匪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