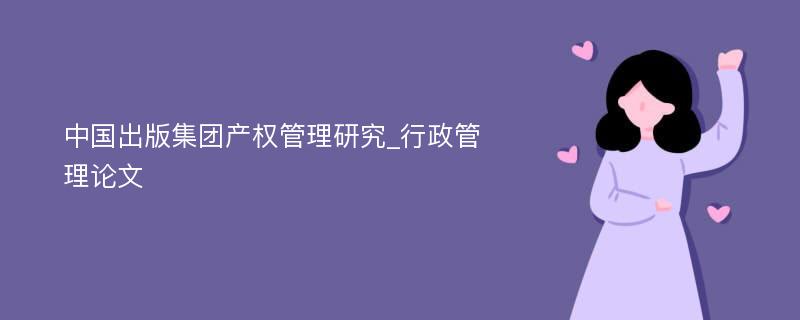
我国出版集团产权管理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权论文,出版集团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出版集团产权规制的现状
自从1992年我国出版企业集团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出版集团的产权改革逐步深入,大致说来,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集团公司成立为标志的国有出版资产产权与行政权分离的起始阶段;二是以国有文化资产管理部门成立以及授权经营为标志的产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发展阶段;三是以股份制改造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成熟阶段。可以说,我国出版集团的产权制度建设初步实现了从“两权分离”到“三级代理”的转变,特别是各地设立类似国有文化资产委员会的管理机构,标志着国有资产产权“三级代理”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目前,国有出版集团的产权管理基本采用了“三级代理”模式:第一级是政府主导组成国有文化资产委员会,多数地方政府都将国有文化资产委员会设置在宣传部之下,身兼国有产权委托代理和意识形态监管的双重责任;第二级是出版集团公司,多数是在原有出版企业资产的基础上行政重组而成,它们接受授权负责经营国有出版资产;第三级是集团内的子(分)公司,它们受集团的委托负责公司的经营。
从全国各地的做法来看,三级代理模式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文化国资委的机构设置与制度安排上。大致说来,主要有这样两种制度安排方式:第一种是设在宣传部门,如上海、重庆等地的市委宣传部联合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单位组成的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第二种是设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如辽宁、北京等地则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接手国有文化资产,实施对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并接受宣传部门的导向监督以及出版部门的业务指导。
从各地实施的情况来看,这两种方式的差异只在于其机构的归属和制度的重心有所不同,而其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一方面采取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出版集团资产国有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另一方面管理机构吸收宣传、财政、发改委以及新闻出版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广泛参与,在保障国有资产管理增值保值的同时,确保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下面我们以上海的做法为例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我国出版领域国有资产产权由出版行政部门管理,行政权与产权高度统一,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产权虚位、经营自主权受限以及产权流动性受阻等诸多问题,严重束缚了国有出版资产效能的发挥。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愈来愈意识到国有出版资产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出版体制改革能否深入的关键,上海可以说是以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出版体制改革的先行者。2004年4月8日,上海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决定,在上海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之下,成立由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共同参与的上海市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小组,并在市委宣传部下设上海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直接负责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等具体工作。
上海模式的最大突破在于把国有出版资产的产权管理职能,如投资、资产处置、人事、财务等管理职能,从分散于各行政部门行使,统一到产权专职管理部门行使,实现了行政权与产权的适度分离,解决了国有出版资产产权虚位的问题。与此同时,上海模式通过建立出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巩固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一方面通过“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方式,来规范国有资产监管主体、经营性国有资产营运主体和公益性国有资产营运主体的行为,达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统计工作,强化国有资产的财务审计评估制度①。
但是从上海模式最初的制度设计来看,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小组作为国家委托的“出资人代表”,掌握着出版集团的人事、财务等经营与决策权,加之出版集团和政府之间没有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这样的产权组织作为隔离带,最终导致出版集团的经营与决策权还掌握在政府手中,为政府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也就是说,设立文化国资委只是解决了国有出版资产产权虚位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国有产权的代理制度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的产权流动问题,这也是上海模式产权改革突破的关键点。换言之,就是要使文化国资委成为真正意义的“出资人代表”,通过合理的产权代理制度设计,实现从出版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方式向持股经营的转变。
在出版国有资产的行政管理方式向持股经营的转变过程中,上海模式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签订“国有资本委托经营和保值增值责任制”等方式明确“委托——代理”的产权关系,委托出版集团作为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营运主体,并通过出版集团实施对出版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行政权与产权分离;第二步是通过重组、改制等手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通过设立董事会等产权组织实现对出版国有资产的间接管理;第三步是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等手段,实现出版集团产权的多元化,最终以市场的力量推动国有出版资产产权管理的行政管理向持股经营的改变。
通过这些改革,上海模式初步实现了从行政管理向持股经营的转变,而其制度保障就是国有出版集团独特的法人治理结构,特别是董事会制度成为政府持股经营的重要制度安排。按照国有产权委托——代理的要求,国有产权的代理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应该保持在既能约束企业的经营,又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状态。这就要求国有出版资产的产权管理部门不能做行政的上级,而只能做股东。这也就意味着,国有出版资产的产权管理部门要放弃传统管理国有出版企业的行政管理模式,把经营权交给企业,而只保留在董事会中的投票权,并通过投票权实施对企业经营者选任、重大决策的监督与管理。从目前的各地的做法来看,主要是通过董事会的人事任命来实现的,即通过委派董事长和董事实现对国有出版资产的实际控制。
但是,从目前的改革效果来看,尚不理想。即便像新华传媒这样的上市公司,虽然有着十分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但从其董事会的人员构成来看,9名董事会成员除了3名独立董事来自集团外部,其他都来自集团内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合理的董事任命制度安排,这些内部董事都是由政府部门任命的代理人,而有些非上市国有出版集团甚至连高层管理人员也由政府任命。这些客观上造成了“董事会虚置”现象:一方面,国资委代行出版集团董事会的权利,董事会的独立性得不到保障,董事会的功能虚置;另一方面,董事会和经理层高度重叠,交叉任职,造成内部人控制。
二、政府产权管理的问题与出路
从上文对我国政府国有出版资产产权管理的分析来看,从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到“两权分离”,再到“三级代理”模式,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应当承认,政府国有出版资产产权管理方式还存在不少问题,而问题的症结就集中在下面这两个矛盾上面。
第一,意识形态外部性管理与产业管理之间的矛盾②。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出版产品是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好的出版物能够传承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而坏的出版物则可能有损于社会公众和国家利益。因此,各国都通过制度法律对出版进行相当严格约束,但是,这些约束更多的是社会性规制,而一般不采用经济性规制。而我国将出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政府直接管理。也就是说,我国的出版部门作为法律授权的规制行政机构,也是事业单位体制下对各出版单位实施专业行政管理的机构,同时又参与出版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法律规制权、行政管理权与企业经营权“三权合一”的管理模式,保障了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导向性,但是,在出版分类管理的前提下,这种模式对出版产业经营与管理的僭越与影响毋庸置疑。如今,随着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不少地方通过设立国有文化资产委员会来协调这个矛盾,但是,就现状而言这个新机构仍然存在于旧的管理体制中,文化国资委作为宣传部门下设的机构它应该专司意识形态导向职能,这就意味着其产权管理的职能只能附属于其意识形态管理功能,于是出现意识形态外部性管理与产业管理之间的矛盾就在所难免。这种矛盾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外部性管理方式与现有产业管理之间的矛盾所致,不解决这个矛盾,现有的出版体制改革的成果无法巩固,出版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很难实现。
第二,行政管理与产权管理之间的矛盾③。由于我国对出版产业的管理长期沿用意识形态外部性管理的行政方式,对于如何发展出版产业缺乏知识与经验,这种知识与经验的不足,致使政府不敢轻易放弃行政管理方式。现在各地成立的文化国资委就存在这种“渐进式改革”的先天不足:首先,文化国资委作为宣传部下设机构所具有的法律规制权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产权代理权存在矛盾;其次,法律规制权的行政管理方式与产权监督管理权的经济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
我们认为,目前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整体推进我国出版集团产权改革的进程。
第一,在现有出版资产分类管理的基础上,推进出版产业规制的法制化进程。目前,我国的出版行政管理实施分类管理的方式,即根据外部性的不同将出版资产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对于非经营性出版资产沿用传统的事业管理模式,对于经营性出版资产则采用产业管理模式。这种分类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克服政府管理的“越位”和“缺位”问题,但是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这些问题由于渐进式改革的不彻底性仍然存在,特别是经营性出版资产的管理中仍然浸透着传统行政管理的色彩。我们认为,一方面要通过设立文化国资委这样的机构,分离规制机构的非规制职能,使规制机构独立化;另一方面要推进规制行为的法制化,避免由于政府规制中法律短缺、政策泛滥,而导致政府规制行为的失范。规制政策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规制法律要经过法定程序,向社会公示,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总而言之,要使出版产业的规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第二,在合理定位文化国资委的前提下,实现公共管理职能与出资人职能的分开,从而推动政企、政资分开。目前,各地文化国资委普遍存在定位不清的问题,即文化国资委既是监管者又是出资人,既执行公共监管职能又执行产权监管职能。但是,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让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共管理相对分开,是提高国有资产的经济效益的重要前提。所以国内的学者普遍认为,目前文化国资委的这种双重身份是和“渐进式改革”的过渡性有关,文化国资委的最终定位应该是产权管理部门。我们认为,应该推动文化国资委向出资人方向转变:首先,宣传部门应该放弃将文化国资委作为国有文化企业的归口管理部门的做法,让文化国资委专司国有文化资产的经济管理;其次,文化国资委应该在明确界定国资委与监管企业各自职权和行为边界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和法律等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实现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开,最终推动政企、政资分开。
第三,完善产权管理制度,通过合理的产权管理制度安排实现政府导向的引导与规制。文化国资委需进一步完善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制度,特别是建立市场化的委托代理管理,将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制建立在市场经济契约的基础上,而不是用组织法规和行政干预的方式构建产权代理制。文化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可通过委托或委任特定自然人作为出资人代表来行使股东的权利,通过特定自然人对企业的内部参与,使出资人的权利影响企业经营者之特定的经营、管理行为。在目前国有出版集团中国有股份占绝对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董事的委任、派出、监管和制衡等相关制度安排以及具体权利与义务的配置,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比如说,考虑到出版集团国有资产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可以在管理中引入“金股份”制度,将国家对意识形态管理的特殊职责,化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金股份”,并派驻“金股份”代表——董事,这种董事可以由宣传或者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作为董事,这些董事应该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负董事责任,同时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没有特殊或特定权力,只是在涉及到国家出版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时可以行使一票否决权。这样就可以通过合理的产权代理制度安排实现政府导向的引导与规制,而无须组织法规或者行政干预等非正式手段。
注释:
①尹良富,上海宣传系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问题探讨,王文英、蒯大申主编,《上海文化发展蓝皮书:文化体制改革与上海文化建设(200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②姚德权,新闻出版业规制及规制变革思路,《财经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6期。
③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标签:行政管理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产权论文; 国有资产管理论文;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企业资产论文; 资产经营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董事会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