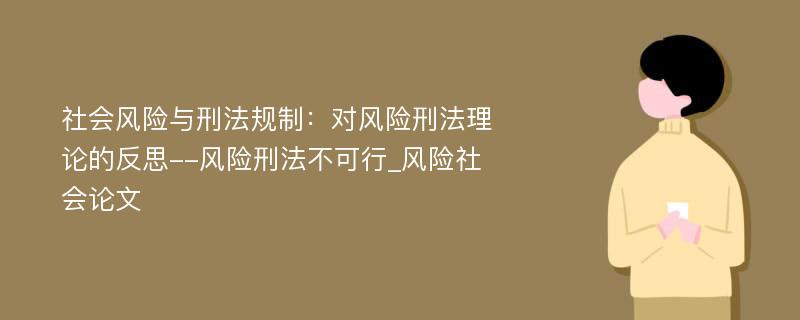
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风险刑法”不可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论文,风险论文,规制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化时代,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开始取代火山、地震、洪水和飓风等自然风险,成为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危险源,也就是说,风险源已由社会的外部转变为社会的自身。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对全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于对社会风险的细致观察以及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深忧虑,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构建了“风险社会”理论。受该理论的启示,德国刑法学者逐渐构建了“风险刑法”① 理论并被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所接受。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客观上给刑法规制社会生活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在这种背景之下,西方国家的“风险刑法”理论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西方国家的“风险刑法”理论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则值得反思。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优势
“风险刑法”理论的主张者认为,在风险全球化的社会里,刑法作为法秩序共同体安全的最有力保护者,应当对“风险社会”作出回应。“风险社会”是责任刑法向“风险刑法”转向的前提,在“风险社会”里,刑法的规制必须前置。同时,刑法对于“风险社会”的反应也具有不同以往的特征,即刑法反应的目的从矫正转向预防,反应的依据从客体实害转向个体危险。② 考察我国刑法学者对“风险刑法”理论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脱离上述范畴,“风险刑法”理论能够在我国形成比较有影响的刑法思潮并不是偶然的,从外部看,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不断深化、刑事立法活动持续活跃的背景下,“风险刑法”理论的某些主张无论是对立法者还是对司法者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内部看,“风险刑法”理论作为一种规范体系也基本能实现逻辑的自洽。笔者认为,“风险刑法”理论的优势至少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提出了刑法规制社会的新课题
“风险社会”理论是“风险刑法”理论的基本依据,而“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乌尔里希·贝克对于风险的界定是:“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副作用”。③ “风险”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对“风险”的演绎最终形成了完整的“风险社会”理论。关于“风险社会”的成因,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1)知识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进步;(2)风险的无责任主体性;(3)现代社会管理失败的产物。由于现代社会仍然在沿用工业社会的管理手段来控制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因此,“风险社会”是“集体的不负责任”(有组织的不负责)。④ 由于“风险社会”理论非常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对既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制度等的冲击,因此,其给现代社会关于公共治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而法律一向是现代国家行使公共治理职能的优先选项,因为法律体系内含的强烈的规范性以及制定程序的严格性无疑保证了法律在国家的众多社会管制手段中是最具正当性的制度体系,刑法自然也不例外。我国当前正处于现代化、民主化齐头并进的时期,社会关系的快速变动无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的社会因素,这就给刑法规制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带来了新的课题。
(二)反映了现代社会的集体焦虑
风险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一直处于“风险社会”之中。但是,前工业化时代的风险与工业化时代的风险不同。前工业化时代的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界,也就是说,自然风险是人类文明的最大破坏源。古罗马时代著名的庞培古城就因一次火山喷发而被彻底摧毁,而现代社会人类的认知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类似的悲剧已经不大可能重演。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理性得到了完全的释放,甚至一度出现“理性万能”的思潮,但人类在逐步摆脱自然主宰时又惊恐地发现自己被新的力量所束缚。技术应用的风险、制度崩溃的风险开始威胁人类社会,而这些风险的危险源竟是人类自己。科技力量的充分释放将人类的生活体验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令人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集体焦虑。因此,以制度来控制风险,以制度来重建社会信任,不但是人类面对风险的当然回应,而且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回顾刑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刑法规模的快速膨胀正是工业文明开始之后的事情,而诸如推定、拟制等设罪技术同样是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发扬光大的结果。人类对于风险的反应是要求更多的安全,而保障安全的任务最终又落到了刑法的身上。“风险刑法”理论的主张者声称:“如果刑法是一个社会感受的表述,那么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就会成为安全的中继站”。⑤ 在“风险刑法”理论的主张者看来,刑法正在成为治疗人类社会焦虑症的良药。
(三)契合了客观存在的立法现象
“风险刑法”理论的主张者提出,面对“风险社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挑战,刑法干涉应当普遍化,法益保护应当提前化。虽然笔者现在还难以断定“风险社会”理论与“风险刑法”理论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难以断定“风险刑法”理论是否应当成为立法者遵从和接受的理论,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自工业化时代以来,各国的刑法立法基本上都是沿着“风险刑法”理论预设的轨迹在前进。我国自1997年以来的刑法立法同样如此。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9条规定,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中增加两款作为第2款、第3款:“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该条第3款的罪名为“提供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该罪在性质上属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其他计算机犯罪的帮助行为或者预备行为,但立法者考虑到在网络空间中“一对多”的犯罪帮助形式的普遍化存在,且此类行为的危害性已经普遍地大于正犯行为,需要刑法予以单独评价,因而通过采用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方式来达到法益保护前置的目的。⑥ 再如,2011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飙车行为、醉酒驾车行为犯罪化,将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同样也体现了“风险刑法”理论的主张。显然,刑事立法透露出的新动向客观上起到了为“风险刑法”理论提供实践依据的效果,这也是“风险刑法”理论目前在我国支持者甚众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风险刑法”理论的劣势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承认“风险刑法”理论的优势并不意味着笔者否认“风险刑法”理论的劣势,其实,在人权保障日趋张扬的今天,“风险刑法”理论的劣势更应该令我们警醒。
(一)从“风险社会”理论到“风险刑法”理论是一次危险的跳跃
“风险社会”理论是“风险刑法”理论的基本依据,“风险刑法”理论的倡导者基本上都是根据前者来标定自身理论的合理性。姑且不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风险刑法”中的风险是否同一个概念,这里要问的是:从“风险社会”理论能否当然地推导出“风险刑法”理论,两者之间的某些关键因素是否被有意或无意忽略了?
1.刑法的正当性需求限制了“风险刑法”理论的存在空间
刑法天生具有的暴力性特点使得它一直是和平时期君主和帝王的最爱,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掌权之后,限制刑法功能的发挥和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才成为资产阶级首要的政治需求之一。反映在刑事立法领域就是自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开始,西方各国纷纷在刑法典中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与此同时,个人责任原则、刑法谦抑原则、刑罚的报应性以及严格的立法程序限制等在给刑法提供充分的法理依据的同时,也为预防国家刑事立法权的恣意行使提供了保障。权利是现代刑法的基石,是刑法正当性的原点,它决定了刑法已经不可能被单纯地作为工具使用。当然,在现代社会中刑法被越来越多地赋予了管制社会、控制风险的功能,社会关系紧张的态势频繁地触动着统治者脆弱的神经。民众对安全的期盼以及国家对秩序的焦虑共同推动了刑法的扩张。在民众看来,只要国家在刑法中作出了某项制度安排,自己所期望的某种理想生活目标就有可能得到实现或者至少指日可待;在决策者看来,只要在刑法中创设新罪就足以表明某些问题被慎重对待,罪名的宣示意义大于实际功能。但是,创设新罪的民意基础不等于正当性基础,“风险社会”理论也不能满足“风险刑法”理论的全部说理性要求,它只是“风险刑法”理论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和动因,满足刑罚权发动的首要条件应当是刑法的正当性,即使“风险刑法”理论背后的政策动因强大到足以让其成为刑法基本原则的例外,对于此类“原则的例外”也应当进行规范体系内的证成,而这无疑是一项繁重的说理性任务。可见,从“风险社会”理论的此岸到达“风险刑法”理论的彼岸还需要众多的中继站,两者之间不是直线传播的关系。
2.刑法所具有的最后法特点淡化了“风险刑法”理论的机能发挥
风险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风险原因的复杂性、风险后果的难控性使得风险控制成为极大的难题。“在全球化时代,局部的、暂时的风险如果处理不及时或不妥当,很可能迅速演变成影响力持久而广泛的危机。因此,寻求及时、有效的危险反应机制是现代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⑦ 但是,刑法的“最后法”、“保障法”的特点决定其不应当站在危险反应制度体系的第一线,不应当是风险控制政策的优先选择。控制现代风险首先应当是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职责,在法律体系中,它首先是侵权法规制的范畴,其次是行政管理法规制的范畴,最后才能上升到刑法的层面。以日本福岛核危机为例,加大安全的民用核技术的研发力度,建立严格的操作流程和规范以及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才是防范风险最有效的手段,而严刑峻法的防范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现代交通的高效与便捷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同样,只有完善交通设施、培育良好的驾驶习惯等措施才是降低交通事故率的最佳手段。如果有现成的行政法规不用,而将治理酒驾的希望寄托在刑法立法上,多少都有舍本逐末之嫌疑。由于发动刑罚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受刑者个体而言都是代价巨大的事情,因此,只有在采用其他法律措施无效时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指出:“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⑧ 刑罚的特性使得它更易受到决策者的迷恋,但仅依靠刑法来控制风险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风险,风险是危险中隐含着机遇,它既是对既有生活秩序的挑战,也是人类自我升级的契机。“风险刑法”理论的具体主张其实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就提出了,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风险刑法”作为一种口号的煽动性意义可能要大于其作为一种理论的借鉴意义。“风险刑法”理论的引入给我国传统刑法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即它使我国刑法具有恣意发动的可能性。
(二)“风险刑法”理论是解释性的理论而非建构性的理论
在笔者看来,理论的实践功能无非两种:理论指导实践和理论解释实践。就前者而言,理论的作用在于为实践提出一整套原则、方法、策略乃至具体的路线图。此时,具体的理论诞生于具体的实践之前,实践的意义在于践行理论、验证理论,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归入这一类;就后者而言,具体的实践产生于具体的理论之前,当某种新的生活事实出现之后,需要一套学术术语去诠释它,这种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特定的实践寻找某种合理性依据。虽然多数理论既有指导实践的一面又有解释实践的一面,但具体的理论总有自己的侧重点。“风险刑法”理论的优势在于解释而非构建,或者说它的理论指导意义是比较弱的,尤其是对刑事立法没有直接的指导性。考察我国近几年来刑法修正的过程可以发现,每一个罪刑规范存废的背后都有很多复杂的个性化的考量因素,甚至某些罪名的改动直接源于偶发的社会重大事件,“风险刑法”理论主张者提倡的某些宏大叙事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难见踪迹,但是,也不能否认“风险刑法”理论对某些立法现象具有一定的诠释力。此外,“风险刑法”理论主要作用于刑事立法环节,而在刑事司法环节则没有存在的余地。过于看重“风险刑法”理论容易造成对司法者的“挤压”效应进而形成某种理论压力。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还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注重人权保障、不奢谈风险控制仍然是司法者的重大使命之一。
三、选择风险还是“风险刑法”
“风险刑法”理论之所以能在当今刑法学界风行一时,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刑法在现代社会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在刑法立法中是更多地采用“风险刑法”理论的主张还是坚守传统刑法权利保障、谦抑之本色,可能是立法者今后不得不面临的一项政治抉择。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对于与“风险刑法”理论一同到来的刑法风险应该如何防范?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是否会在危机管控方面将刑法引入更加弱势的地位?迈向现代化的我国目前正处于与西方工业国家不完全相同的发展阶段,同时我国的刑法结构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在社会转型持续深入的背景下,自然犯的刑罚调整以及行政犯的入罪化应当是今后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向,即调整对自然犯的刑法反应强度以及将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由此看来,“风险刑法”理论的某些主张仍具有借鉴意义。但是,风险离我们较近,并不意味着“风险刑法”就应该离我们较近。刑法背后蕴含的正义、文明、谦抑、保守等精神价值是人类社会几百年探索之结晶,不应当在现代社会中被轻易抛弃,每一次犯罪圈的扩张都应当经受得起更多的正当性诘难。客观地讲,我国刑法学界既没有必要绝对地排斥“风险刑法”理论,视其为洪水猛兽,也没有必要盲目地信奉、崇拜该理论,让其在我国刑法领域横冲直撞、无所顾忌,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将“风险刑法”理论主张者的若干思考、结论纳入我国传统刑法的理论框架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以传统刑法理论的基本价值观念限制其不当功能的发挥。
注释:
① 与此类似的提法还包括“安全刑法”等。
② 参见赵书鸿:《风险社会的刑法保护》,《人民检察》2008年第1期。
③ [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④ 参见程新英、柴淑芹:《风险社会及现代发展中的风险——乌尔利希·贝克风险社会思想述评》,《学术论坛》2006年第2期。
⑤ [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刘国良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⑥ 关于正犯行为共犯化的具体理由,可参见于志刚:《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⑦ 张旭:《风险社会的刑事政策方向选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⑧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