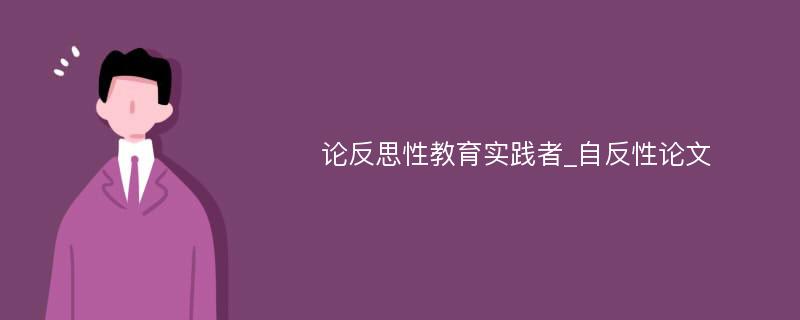
论反思的教育实践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06)11-0001-04
一 反思与实践
按照吉登斯的分析,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具有反思性的特征。[1] 也就是说,人的所有认知与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自身的监控,这种监控反过来又对正在进行的活动发生影响。但是,人类不是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反思的这一特点的。
在英文中,反思(reflec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动词“reflectare”,本义为回转、返回。在西方,反思最初的含义是指人的自我意识,就是返回自身,认识自己。在古希腊时代,这种意识和智慧相关,与思想相随。柏拉图就曾把智慧看作是“关于自身的学问”;亚里士多德也曾将对自身的思想奉为最高的思想,并将如此这般的思想活动视为至高无上的快乐。[2] 希腊人认为,认识自己是智慧的象征,也是快乐无比的事情,反思具有令人眩晕的美妙。
欧洲人迈向现代门槛之际,传统生活世界的世界观被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所取代,主体与客体也随之分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表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也使理性反思和批判有了合理性。从近代开始,反思被套上了理性的光环。康德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西方这种反思哲学的基础。随后黑格尔又提出了“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3] 反思由此指向了人的理性,指向了人的思想,指向了理论。反思成了理论自身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表现为一种于自身之中找到一切知识的最终基础的意向”[4]。这种认识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实践的自身意识放在了理论自身意识之后,反思是为了清除罩在理性身上的面具,还理性以本来的面目,然后用纯真的理性指导实践。在近代西方哲学家眼里,反思是理论的自身意识,实践自身意识只不过是理性自身意识的陪伴,反思与实践的关系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关系。
进入19世纪,哲学研究出现了重大变化,马克思提出了生活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过程。此后,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前反思的日常生活,维特根斯坦在日常的语言交往中解释生活世界。哲学的这种实践转向实际上都是要从人的生活实践中寻找人生存的价值,实现人的发展的丰富性和超越性。① 反思与理论、反思与实践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实践的自身意识不再只是伴随理论的自身意识出现,而且常常开始超前。对实践的反思不再意味着对意识自身的觉知,而是指对自身实践行为的知晓、评判,甚至承担责任——一种道德的自身意识。[4]
反思再一次回到了人的生活世界,成为人自身意识的一部分。与古希腊人不同的是,现代哲学家认为,反思的意识和行为只有在自身意识存在的条件下才会产生,而自身意识又是以群体的在先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反思不仅指向个体,也指向群体和社会,看似个体的反思,实际上透视着主体间的理解。反思既是私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现代人的反思是自为的、积极的、自主的和整体性的反思,它不再局限于智慧一隅,也不再停留于思想本身,它涉及到了人的整个生活世界和人的自身发展。
纵观人类对反思认识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反思是人类对自身的反观,是人的精神以人的思想和人的实践为对象的思考。反思是人类的自我监控,它总是在变动中建构自身,在不断的映射中认识自身,它始终代表着人类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努力,但是在现代社会,彻底化的反思方法也恰恰会证明自身是不可靠的,从而形成“自反性”,[5],自反性(reflexive)提示的不仅是反思,而首先是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否定着人的思想和人的生活本身。我们由此进入了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或“自反性社会”,教育在“风险”中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
二 反思与教育实践
反思意味着人要对自己参与其中的实践活动进行监控,包括对实践活动的意向性、实践中的行为以及实践的意义进行思考。在布迪厄看来,“在这种反思性的引导下,人们会注意任何‘实践性’的事物,它们被日常行动者调动,用来以最小的成本对日常存在和实践的紧迫性作出反应。”[6]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有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般性特点,即目的性、伦理性和生成性。② 反思对实践的积极关注,以及所具有的自我监控和自我批判的特点则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自足性,③ 恰恰是这种自足性,才使教育实践的上述特点从可能变为现实。
1 教育实践活动的目的性与反思
人类的教育实践活动从来都是充满着目的性的。从远古的庠、序、校,古代的官学,近代的私塾,到现代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教育形式日趋多样,教育活动也日渐复杂,但是教育始终就是一种充满着意向性、目的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知识的传承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无论是宏观的教育实践——教育制度的建立还是微观的教育实践——教室中的一堂课,都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和意向性。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反思既包括对目的合理性的评判,对意向性的审视,也包括对活动合理性的省思。它是人对参与其中的教育实践活动的自我审察,一方面,以目的性评判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用活动的合理性修改目的的不完善性和不合理性,纠正意向性的偏离。笔者的一段经历可以解释这一过程。我们观察了一节小学科技课,科技老师在指导学生动手制作风筝,希望孩子通过制作并放飞风筝来了解一些科技知识时,其基本的意向性可能是孩子们会对这种玩具感兴趣,因此会积极参与,他们会因喜爱风筝而去制作,去获得相关的知识。这只是老师的意向,而不是孩子的意向。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表现得不合作。他们对此表现出的冷漠,甚至是厌烦让人困惑不解。老师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设计,也开始了解那部分学生的想法,其中一个男孩子嗫嚅地表达出自己因为“老也做不好”才对做风筝不感兴趣。孩子因无法获得成功的体验,讨厌上科技课,着实让老师吃惊。老师们由此会想到,在教学过程中,儿童兴趣的形成、知识的掌握和成功性学习体验的获得同样重要,缺一不可,那么在反思中所了解到的这一切,特别是对儿童学习活动的意向性的理解,无疑将成为今后教学活动设计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反思以教育实践为基础,但恰恰是因为意向性和反思性,教育实践才具有了自足性的特点,教育实践活动也才得以在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审视中追求卓越与崇高。
2 教育实践活动的伦理性与反思
教育活动总是包含着实践者的伦理④ 追求,它表现为实践者对教育生活本身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关注。它不是从理性的、主体的、知识的路径寻求对教育世界的控制和主宰,而是在一种民主的、包容的、对话的、参与的理路中探寻实践者在教育世界中的相遇和相知,以及他们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教育实践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决定了教育活动是一种理解性的存在,它所关注的不是教育实践“是”的问题,而是“应该是”的问题,关注的是人类的教育活动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人类的价值如何在教育活动中实现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人类对教育活动的终极追求的问题。
反思是行动者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表现,但是谈及反思与责任问题,我们需要明确“反思我做得怎样”和“我怎样去反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种指向个人领域的反思,它所涉及的责任是有条件的责任,它是从“我在”,而不是“共在”的视角去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很必要,但是通过这种反思不能解决教育实践的终极问题。后者给我们提示了一种反思的视角,一个以“我们的在——教育活动参与者的在”去审视教育活动。这是一种“设身处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反思。这种反思要求实践者“无条件”地对自己行为负责任。鲍曼指出:“道德责任是无条件的和无限的,它在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不断痛苦中证明自己。道德责任从来不为其存在寻找保证,也从来不为其不存在寻找借口。道德责任存在于任何保证和证据之前,存在于任何借口或赦免之后。”[7]
教育实践所具有的以伦理追求为基础的反思性特点,保证了教育活动中人的在场,也避免了“自反性”对教育实践的破坏和颠覆。对于活动的参与者——教师而言,要学会对每一个学生负责任,他(或她)便不得以任何理由制造活动参与者的缺席。一位小学老师曾写下了这样的反思日志:“走进孩子眼中的教育世界,使我对学生和孩子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是孩子,我们要呵护;他们是学生,我们要理解;他们是有思想的人,我们要尊重与信任。我坚信,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教师不发展,学生的发展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只有通过反思,教师才能更好地承担责任,才能形成一种关于人的——“我”与“他”共同发展的使命感。
3 教育实践活动的生成性与反思
教育实践具有生成性。雅斯贝尔斯认为,“生成的静态形式即习惯,生成的动态形式即超越生成就是习惯的不断形成与不断更新。”[8] 教育实践的生成性具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教育活动本身是在教育实践中建构和发展的;其二,教育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在教育实践中获得发展的,教育实践不仅建构了教育的生活世界,也促成了人在教育生活世界中自我发展的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其三,教育的意义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实践的生成性源于人类教育活动历史的积淀和人自身不间断的努力。习惯与超越是人类在实践中、在意向性的活动中通过自识与反思,日积月累形成的结果。一方面,习惯保证了教育活动的有序进行,但是习惯的确定性也会规限人的发展的不确定性,造成对人自身生成性的羁绊,所以通过教育活动者的自识与反思使教育活动历久弥新,是教育实践活动的生成性使然。
如果说,反思不但以思维为自己的对象,而且以实践为自己的对象,那么对于教育实践的参与者教师而言,让“反思性回归自身”[6],就是要保证教师在实践中通过反思获得成长的同时,使教育活动本身呈现出教育的意义和追求。
三 反思的教育实践者的精神气质
教师是教育实践者的主要代表。对于教师群体而言,反思应该是一项集体性的自我监控,我们将从精神气质的角度,解读教育实践者对自身及自身参与其中的教育生活实践进行反思的品格。气质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但是在本文中我们谈及反思的教育实践者的精神气质,却不是从心理学角度展开讨论。给概念下定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特别是下一个规定性的定义,总有一种挂一漏万的感觉。我们只好从描述的角度来分析反思的教育实践者的精神气质。对于教师群体而言,教育实践者的精神气质是对教师共同体文化特质的描述和总结,是教师群体文化的反映,是教师群体行为模式及价值取向的展示。
反思的教育实践者的精神气质隐蔽于教师职业规范的背后,对教师职业规范起支撑作用,当职业规范正常运行时,它并不显现出来,当职业规范被违背时,它才以一种道德力量主持正义。
1 视育人为己任
对于教师群体而言,教书育人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它理应成为每位教师的职业信仰。但在实际的教育生活实践中,教书不育人,既教不好书,也育不好人的现象并不少见,这并非危言耸听。就拿我们的个人成长来讲,在我们受教育的经历中,能够真正视育人为己任的教师又有多少呢。原因何在?育人工作的复杂性,职业规范的模糊性,从业需求的多样性,评价体制难以操作性可能都是其中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教师能够承担起育人责任的保障。外部的各种规范和机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教师群体的职业信念如何能够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中,通过立言、立德和立行而刻骨铭心呢?我们认为,坚持“视育人为己任”的信念是形成反思的教育实践者的精神气质的内部保障。
对于教师而言,在教育实践中,坚持“视育人为己任”的信念,意味着教师的教育活动应该围绕着开启学生的心智,陶冶学生的品格,使学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展开,这既是目的,也是过程,当然更是结果。这是为人之师的一种职业“天职”,也是一种职业自律。这种精神气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通过千百次的反思性的实践获得的,是在教育实践中反复历炼的结果。
2 秉持独立的人格
对于教师群体而言,秉持独立的人格,首先是要求他们在精神上独立,同时也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判断能力,获得专业自信心,形成充分的专业自主性。
成为反思性的教育实践者之所以要秉持独立的人格,是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和教育活动的不确定性造成的。1927年,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我们所观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暴露到我们追问方法面前的自然。通过这种方式,量子力学使我们想起了古老的智慧:在戏剧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9] 不确定性表达了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复杂性、解释实践活动话语多样性的理解。在复杂的教育实践中,对于教师而言,任何脱离教育情境的模仿行为,以及从众行为对于他的职业生活来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一些教师在书店抢购特级教师的教案,希望可通过模仿使自己课堂教学旧貌换新颜,结果往往是徒劳的。其实失败的道理很简单,蕴含在特级教师教案中的实践智慧,是他们在教育实践中长期探索的结果,这里面既有独特的情境性,又有教师独特的精神意蕴,所有这一切,对于其他教师来讲,有借鉴的意义,可以通过解读去获得启示,但是任何照抄照搬的行为都是劳而无功的。
秉持独立的人格,要求教师保持一种探究精神;要求教师对教育问题保持一种专业敏感,具有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要求教师有足够的判断力,能够对现有的教育理念提出实践性的质疑;要求教师崇尚真理,不迷信权威,学会摆脱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束缚,并对建立新的制度提出有效的实践性建议;要求教师能够对自己第一手的教育经验进行反思和评判,寻找有效的经验进行总结和运用;“要求教师发现并解决课堂实践中的问题,有意识地质疑自己对教学的假设和价值观,在教学中注意联系制度化和文化情景,参与学校的课程开发,对自己的专业发展负责;要求教师成为学习环境的创造者、学习的促进者、批判性的思考者”。[10]
3 合作的品质
人的反思性实践活动在指向自身行为的同时,也在指向行为的背景和行为的意义。对于教育实践活动而言,教师的反思是关于师生互动与合作的反思,同时也是关于教师之间的合作的反思,它是在关系中展开的。教学过程从来就不是一个教与学的分离过程。它是一个交往过程,也是一个互动过程,所展现的是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主体间的关系。“每个主体都是关系中的主体,主体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关系。所以,主体间性超越了主体性的自我异化,又保留了个人作为主体的根本特征,同时强调主体间的相关性、和谐性和整体性。”[11] 教学过程是一个理解性的存在,理解的达成取决于主体间的相互沟通、意义的共识和视域的融合,取决于活动者自身意识、对象意识和反思意识的整合。我们可以在一个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去了解这种整合。上课时,教师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是一种自身意识的表现,意识到学生正在做什么,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象性意识。当教师了解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为学生接受,或者被学生拒绝,仍然是一种对象性意识,但是当教师扪心自问,所授知识为何遭受冷遇,自己的一番善举为何被拒绝,反思意识便开始登场,这是一种指向活动者自身,指向活动情境,指向活动意义,指向活动改善,自然也昭示着活动未来的意识。反思意识将自身意识与对象意识融为一个关于实践的整体意识,其意义在于把“教师的在”与“学生的在”联系在一起,把“此在”与“彼在”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在”。由此可见,反思是在合作中展开的,是形成理解的教和学的前提和保障。对于教师群体而言,合作品质既是在反思中形成的,也是教师共同体专业成长的基本条件。
注释:
①康丽颖:《教育理论工作者回归实践的自识与反思》,《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第62-67页
②在教师发展学校建设过程中,我的同事宁虹教授提出的对实践内涵的意向、伦理、整体和践行的理解对于我有一定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③实践哲学区别于理论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承认理论理性的有限性,承认实践活动对于理论活动具有一种奠基作用,承认实践活动具有其自足性,而理论活动则只能奠基于实践活动之上,不具有自足性。”见王南湜:《实践观的变迁与哲学的实践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1期,第43-48页
④据海德格尔的考证,“伦理”(ethic)这个词可追溯到古希腊文的ethos,其意义是“居住”“栖所”。这即是说,古老的伦理思维所思考的是人的居所,这样的思考关注的是人在世界中的栖居,亦即“相与之道”。见田海平:《从“本体思维”到“伦理思维”——对哲学思维路向之当代性的审查》,《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第7-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