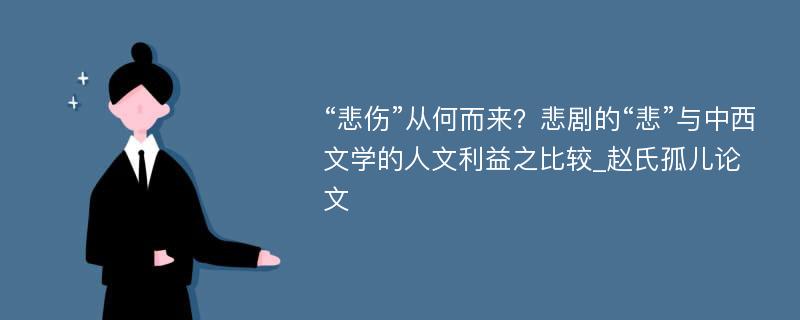
“悲”从何来?——就悲剧之“悲”对中、西文学人文趣向的一个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文论文,对中论文,悲剧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古希腊悲剧“悲”在哪里?
在“悲剧”借着酒神的运动会风靡于古希腊时,中国的戏剧尚不曾结胎于诗的母腹。诚然,我们不必为此而妄自菲薄,这正像我们没有理由沾沾自喜于书法艺术对汉文字的情有独钟一样。一个真正自尊的民族当有更从容的胸襟,它足以引为自豪的不只在于自己创获的种种成就,也还在于它对他人的值得赞誉的业绩总能够送上一份由衷的敬意。
无论是王国维所谓《窦娥冤》、《赵氏孤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页。)的断语,还是朱光潜所谓中国艺术的“神庙里没有悲剧之神的祭坛”(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的论说,皆可以聊备一格。不过,重要的也许是再度返回“悲剧”的源头,去领略那初始意味上的“悲剧”究竟“悲”在哪里,由此或会改变一种提问方式——比如,不必急于争辩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有无悲剧,却不妨先作这样的发问:古希腊式的悲剧是否有缘产生于中国?
然而,怎样的悲剧才可称作“古希腊式”的“悲剧”呢?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所作的界说,其中最切要者乃所谓被摹仿着的严肃、完整而又有相当长度的“行动”,而这“行动”又必得是能引发“怜悯与恐惧”之情的那一类。有“行动”才会有“情节”,而“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有学者认为“古希腊悲剧着意在‘严肃’,而不着意在‘悲’”(注:罗念生:《论古希腊悲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其实“怜悯与恐惧”固然是“严肃”的,却也还是一种“悲”——一种有着别一番滋味的“悲”。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突转”、“发现”和“受难”被认为是悲剧“情节”的三个最堪注意的要素,其中“突转”和“发现”显然更重要些,是它们把悲剧所谓的“受难”和一般受难从根源处区别开来。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地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更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1页。)所谓“突转”(意外的、突然的转折)和“发现”(因意外的披露而窥见真相),原是出现在“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的“一桩桩事件”中的,所以悲剧的契机最终便在于作为“情节”的“事件的安排”是否合于“意外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这一要求。事实上,“意外发生”的诸多事件环环相扣的必然的“因果”之链,最能示人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命运感,而希腊悲剧所演述的“行动”恰好大都隐贯着“命运”的消息。“命运”以不容规避的方式把“苦难”加于挣扎中的主人公,这并非由主人公自己招致却又终究无法摆脱的“苦难”所唤起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是古希腊悲剧特有的“悲”情。
不过,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就悲剧主人公可能的人格品位所说的话是颇成问题的。在他看来,悲剧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8页。)。说悲剧主人公“陷于厄运”并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这当然是近于中肯的,然而把“陷于厄运”归结为“他犯了错误”便有欠斟酌。至于他以“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品题悲剧人物,则可以说是一种失误,这失误在相当的程度上显露出品题者以苏格拉底之后的某种人文理致评断前苏格拉底时代人的心境的迂阔来。至少,把《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划归所谓“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之列是不相应的。难道这个在儿时被钉穿双脚而弃于荒野的人再“善良”、“公正”些就能逃脱命定了的杀父娶母之罪么?至于像《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这样的人,她又有什么不善良、不公正而该当承受那自杀身亡的厄运呢?把悲剧的酿成最终归于“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主人公的某种“错误”,这是多少执著于“对”与“错”的分辨而对悲剧的、人文蕴含的简单化。真正说来,悲剧之“悲”并不在于主人公“犯了错误”,而是在于“命运”或命运般的必然性所注定的毁灭主人公的那种无从消解的冲突。而且,即使是剧中的主人公确实“犯了错误”,那悲剧所以成为悲剧也只在于那主人公不能不犯“错误”。古希腊悲剧“悲”就“悲”在不能不犯“错误”或根本没有错误的人遭逢祸患,他的罹难或者无从找到肇祸的对手,或者即使有对手,那对手也不就是与所酿灾难相称的邪恶之人。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属于那种找不到肇祸者或没有肇祸对手可言的悲剧。剧中,没有一个人包藏祸心,也没有一个人预谋过什么,但这些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把主人公推向令人“恐惧”而又令人“怜悯”的自毁之途。俄狄浦斯挣脱定命的努力只是构成了命运之网张示于尘缘的必要环节,他终究弄瞎自己的双眼并放逐了自己。主人公不能原谅的只是落入命运的圈套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罪眚,并就此承担了他原可以推诿于命运的责任。悲剧把显现于事件的不幸冲突最终移置到俄狄浦斯的内心,那无可告慰的内心的痛楚永远无底止地发散着古希腊人的“悲”情。
悲剧《安提戈涅》中的祸首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主人公安提戈涅的死往往使人们记恨于这事件的直接相关者克瑞翁。但细细推敲起来,安提戈涅的自杀与其说是因着她的舅舅、忒拜城的新国王克瑞翁的威迫,不如说是各有正义依据的两种律令的冲突对善良而正直的主人公的灵魂的追逼。她生而为忒拜臣民,因此不能不遵从国王既经颁布的禁葬令;她生而为波吕涅刻斯的胞妹,却又有义务按照神律掩埋已死的亲人以使死者的魂灵得以安栖冥境。生而为臣民和生而为胞妹的命运把主人公带到非死而不足以自解的两难境地,这死遂化为一种高尚的震撼而透出那悲剧的、净化人心胸的“悲”郁。
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特》中,仇杀的血腥更多地露出被卷入事件漩涡的人的邪恶的圭角,然而,几乎所有的可在一定分际上被视为邪恶的行为都可以找到并不勉强的辩护理由。阿伽门农当然是一个悲剧角色,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身上也未始没有悲剧的色调,但悲剧的中心人物是俄瑞斯特,他生而为阿伽门农之子,不能不为他横死的父亲报仇,而报仇的对象却又正是生养了他的母亲。这对于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说来终是一种最不堪的两难,当他把剑指向告饶的母亲时他突然犹豫起来,他只是在再度把自己的行为系于神谕(命运的声音)后,才终于刺出了那集聚了悲剧的全部痛点的一剑。往后,复仇女神的追杀和阿波罗对主人公的呵护或正可看作俄瑞斯特的内心冲突的外在象征,这冲突的难以调和使这个在自我折磨中时而变得狂易的人苦苦寻求解脱。由复仇女神和阿波罗分别象征着的伦理意味上的两种价值都是神圣不可亵渎的,俄瑞斯特被命运送到两种神圣价值的夹缝中乃是悲剧之“悲”的真正閟机。
如果说悲剧《俄瑞斯特》的“悲”的痛点落在俄瑞斯特刺向他母亲的那一剑的话,那么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的全部“悲”情正可说是凝聚在美狄亚被杀机鼓动的双手伸向自己儿子的那一刻。撕裂了的都是天性自然的亲情,前者是儿子对母亲,后者是母亲对儿子。被报复的烈焰烧去最后一份温情的美狄亚是忠贞而残忍的;她原是要让负心的丈夫伊阿宋为失去子嗣而痛彻肺腑的,但她为伊阿宋生养的儿子终究也是她自己的儿子。这是母亲在对无辜的儿子痛下杀手,然而怜子之心毕竟也在颤抖。她完成了自己的杀人计划,只是带血的剑决然斩不断母亲同儿子的心的那种牵连。这似乎是悲剧的一种收场,却又正是悲剧的真正开始。主人公乘着龙车飞走了,但无论飞到哪里,那从此沉没在窒息一切告慰的“悲”中的灵魂,再也不能指望它有飞升之日。
在希腊悲剧的主人公中,美狄亚也许是最酷烈的一位。不过,她身上毕竟留着悲剧人物的那种“悲”的通性,此即,把所有的外在冲突最终都引向自身而致使心灵在反观自诘中难以自容。的确,不像俄狄浦斯、安提戈涅、俄瑞斯特的“悲”的遭际那样更多的在于外在“命运”的注定,美狄亚是自己谋划并策动了一切,但一任意志之激情的戾烈性格主宰着那谋划,这驱使着谋划者主体的性格在悲剧中所履行的依然是“命运”的使命。
二、中国戏剧中的另一种悲
中国戏剧中常有一些演唱某一凄楚故事或若干惨烈情节的苦戏。倘把这类苦戏中的凄楚、惨烈之情也称作悲,那当是与古希腊悲剧之“悲”非可一概而论的另一类型的悲。以“悲剧”称这类苦戏可能并不相宜,它会因着源于希腊文,τραγωδìα的“悲剧”内涵的扩展而模糊了两种剧艺中所隐含的人文意趣的微妙差异。中国苦戏中没有俄狄浦斯、安提戈涅、俄瑞斯特、美狄亚那样的自我撕裂式的主人公,也没有酒神——个在执著的传说中曾遭受肢解痛苦的神——作为悲剧之神的背景。
古希腊悲剧中的所有情节几乎都在于陷悲剧人物于两难而无以自拔的境地,中国苦戏中最悲凄、痛楚的情节却总是被公认的伦理或纪纲所扬弃。前者大都只是在最后才由无以排解的“悲”情荡起心灵的巨大震撼,后者则不酬以申冤、雪耻、赴义乃至于团圆而不达终场。两者或皆有不尽如此的剧情安排,但其底蕴或指归大体各从其类,并无大端处的扞格。
戏剧在中国的萌朕或可追溯到西汉的“角觝之戏”,乃至战国时演自屈原《九歌》的祭祀歌舞。然而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的诞生并不能早于宋元之际。明人徐渭《南词叙录》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其为《赵贞女》作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所谓“戏文之首”也许不必全然以时序为断,但以《赵贞女》、《王魁》等为中国戏剧中第一批代表性剧作,则当不会与史实相去太远。二剧皆引婚变为题材,又皆以谴责负心男子为归趣。今有学者因女主人公被背弃之苦情而判说两戏为悲剧,其实此所谓悲与真正的悲剧之“悲”并不相及。因为这苦情并不像希腊悲剧中主人公之衷悲的无可告慰,上苍作为公正的仲裁者终究还是以对恶行的分毫不爽的惩罚酬答了滚滚红尘中渴望呵护和眷顾的人们。蔡伯喈负赵贞女终被暴雷所震,王魁负敫桂英被阴神所助的敫氏之魂索去性命,蔡、王的不得善终无宁是人们对负情背义者的诅咒的应验。其固可以一平愤懑而大快人心,却不足以引发希腊悲剧带给观剧者的那种默然而至深的心灵震撼。
元代是中国戏剧一朝成熟便迅速走向巅峰的时代,被王国维誉为“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窦娥冤》、《赵氏孤儿》即是这时代诸多经典之作中的两部剧作。不过,单从悲苦或悲怆处说悲剧,至少已经对悲剧在它的最早出生地所获得的元始意义有所乖离。《窦娥冤》、《赵氏孤儿》等自有其价值,它原不必依“悲剧”的绳墨校雠于古希腊人。“冤”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的主题辞,它的全部戏路纠结在主人公的那份令人凄绝、痛绝的“冤”情上。悲苦由“冤”而来,这剧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冤”剧。“冤”可以“感天动地”,窦娥临刑前所发三桩誓愿——血溅悬练、六月降雪、楚州亢旱三年——竟一一应验,但这“感天动地”本身已大异于希腊悲剧中那种于天地无可寄语的“悲”。与希腊悲剧的主人公相比,窦娥虽冤却心有存主、正气凛然,并无精神重心被摇夺而产生的那种内在心灵的自我驳诘。同样,俄狄浦斯、安提戈涅、俄瑞斯特、美狄亚等悲剧人物,虽最终把所有外在冲突都收摄到他们内心世界的自我分裂,却从不曾有一人像窦娥那样满腹冤情而呼天告地。悲剧人物的内心冲突是不能指望某种外部力量去仲裁或调解的,“冤”剧则必得借助一个足以剪除邪恶势力的外在权威来申张公义。窦娥之冤的昭雪是因着父亲窦天章的秉公察案,而其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却是因为他那握有“先斩后奏”之权的提刑肃政廉访使的身份。悲剧之“悲”则悲在悲剧人物的无从摒除的内在冲突,它几乎除了主人公无望的毁灭(如俄狄浦斯)或神灵为之拔除(如俄瑞斯特)而不可消解;“冤”剧之“冤”则冤在冤案的酿造者的存心为之,在冤狱平反后负冤者即可解脱出来。“冤”剧不会没有期待贯穿其中的,并且那期待总会如期而至;至于悲剧,却并不唤起期待,它的至悲往往在于叵测的命运对主人公的所期的无情的沉没。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仍是一部“冤”剧。沉冤二十年一朝得以申雪,固然不能没有君王的一纸诏令,但诏令的下达却非下令者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靠了诸多带着正义信念和期待的人的生命换取。“义”被救孤的牺牲者看作是高于一己生命的价值,这价值就是剧中词云“那期间颇多仗义,岂可谓天道微茫”的所谓“天道”。关联着人间善恶的“天道”与古希腊人心目中的“命运”迥然不同,“冤”剧和悲剧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最终分道扬镳。冤剧有冤必有悲,但那连着冤情的悲因着“天道”的价值之光的照耀反倒能使蒙冤者或站在蒙冤者一方的人化悲切为一种义愤,并把这义愤投向某一确定的邪恶的目标;而悲剧有悲却未必有冤,由“命运”带给人的非可以“冤”喊出来的悲往往紧收在悲剧人物的心头,并不能借着一种转化或投射而有所减缓。当肇冤者屠岸贾就戮时,《赵氏孤儿》中由冤而生发的悲也由冤的申雪而消去。然而,在希腊悲剧中,即使是一任主人公恣意报复的《美狄亚》,那悲剧人物的悲情也只是因着发泄性的仇杀愈益攫住了近于疯狂的心灵,却没有因此使那逼向心灵深处悲的窒息感稍稍放松。
明人李梅实、冯梦龙以抗金名将岳飞的遭际为题材写成的《精忠旗》一剧,也被某些戏剧或戏剧史专家认作“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其实,措意于忠君爱国的忠、奸之辨的该剧,却仍在“冤”剧的窠臼中。剧中“阴府讯奸”一折,把善恶有报的人间期冀延伸到拟想中的阴曹地府,“冤”剧之苦情遂转为遗恨的宣泄和阴福的补偿。岳飞是得了上天“玉旨”与皇帝诏书的双重平反的,全剧在“恩光诏旨优,把愁收,都城喜气连童叟”、“长夜幽,今作了明如昼,但从前怨德都酬”的颂唱中结幕。
元人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白朴的《梧桐雨》是最早由王国维列入中国“悲剧”剧谱的又两部剧作,其序次仅在《窦娥冤》、《赵氏孤儿》之后。如果说《窦娥冤》、《赵氏孤儿》属于典型的“冤”剧,那么,《汉宫秋》、《梧桐雨》则正可谓为典型的“怨”剧。“冤”可生悲,“怨”亦可生悲,但此悲殊非古希腊悲剧所示范的那种悲剧之“悲”。“怨”是《汉宫秋》全剧的底调所在,“汉宫秋”说到底亦可谓“汉宫怨”。这怨也许是由衷的,但同撼人肺腑的那种悲剧之“悲”毕竟是可辨之于灵府的两种情愫。《梧桐雨》乃《汉宫秋》的姐妹篇,就取材而论,《雨》剧所凭藉的唐玄宗与杨玉环的遗事正是《秋》剧虚构汉元帝与王昭君之情缘的原型。《雨》中的唱词有时显得比《秋》中的同类唱词更痛切些,但两剧在由“怨”生悲、悲为“怨”囿这一点上却并无二致。
在诸多被执著为“悲剧”的中国古典剧作中,明人孟称舜的《娇红记》别具—格,其“悲”情非“冤”剧或“怨”剧之“苦”情所可比拟。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所吟述的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故事也许对于《娇红记》的创意有过不小的启迪,而在民间流播既久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中显然也找得到这剧的初孕的胎痕。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几乎构成婚嫁的强制律令的时代,两情相许的男女为了爱而结合往往须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梁山伯与祝英台殉情而亡,是死后化蝶才得以结合的。《娇红记》中的王娇娘与申纯有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焦仲卿,只是在双双毕命后化作鸳鸯才得到爱的自由。中国古典戏剧中的这一类剧或勉强可以悲剧相称,然而即使如此,《娇红记》一类剧毕竟还是以“化蝶”或“化鸳鸯”的方式为人们安排了一种聊以慰藉的“圆盈”的结局——它允诺男女主人公在另一个世界如愿以偿。
三、两种不同的神话叙事、“命运”观与审美意识
古希腊悲剧的端倪初露于富有戏剧性的史诗,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曾这样把戏剧——喜剧和悲剧——的发萌追溯到荷马的诗:“荷马从他的严肃的诗来说,是个真正的诗人,因为惟有他的摹仿既尽善尽美,又有戏剧性,并且因为他最先勾勒出喜剧的形式,写出戏剧化的滑稽诗,不是讽刺诗;他的《马耳癸忒斯》跟我们的喜剧的关系,有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跟我们的悲剧的关系。”(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13页。)荷马的诗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有了相当确定的底本,这之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述说的故事可能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已经流布了不短的岁月。英雄传说和神话在史诗中的浑然不分同神话中神与人的同形同性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古希腊神话在“英雄时代”已经有了人们普遍认可的谱系。赫西俄德的《神谱》虽然不过一篇千行左右的诗,却表征着古希腊人在这之前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就开始了他们独特的神话叙事。神话叙事也许与史诗的发轫同时,也许比最早的史诗更早些。但无论如何,当悲剧降生于公元前6世纪时,谱系化了的神话叙事和规模宏阔的史诗,为这一新形态的文学作品的问世至少已经作了两个多世纪的准备。
依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注: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然而,即便从埃斯库罗斯——他把演员的数目由一个增加到两个,并由此削减了合唱成分而使韵文的对话成为可能——算起,古希腊悲剧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以它无与伦比的成就写进人类历史了。悲剧的诞生不能没有抒情诗和音乐的参与,但表演在剧中的故事却大都在先前的史诗或神话叙事中述说过了。史诗与悲剧是古希腊两个时代的主导文学形态,就后一个时代往往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扬弃而言,悲剧也可看作是对史诗的扬弃。扬弃不是摈绝,它意味着一种内在的汲取和更新。尼采是把史诗归结为“阿波罗艺术”的,而他认为“我们可以把希腊悲剧解释为从阿波罗的影子中所不断产生的狄俄倪索斯合唱队”,“悲剧乃是狄俄倪索斯识见和力量的阿波罗化身”(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刘崎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页。)。从这见地中固然看得出论者的狄俄倪索斯(酒神)情结,但在把悲剧主要地归结为狄俄倪索斯精神时,他毕竟不曾忽略这艺术的新生儿与生俱来的史诗的胎记。
校雠于古希腊,中国汉文学史的一个明显的异质性状在于它的源头处没有史诗的踪迹。与史诗的阙如相应,见于汉语古籍的神话叙事则零散而无统绪。汉语神话大多辑于《山海经》、《庄子》、《列子》、《离骚》、《九歌》、《淮南子》诸典籍,而最能从中窥见其原始风貌的当属《山海经》。诸籍所载的神话人物多为女娲、伏羲、西王母、黄帝、炎帝、颛顼、帝俊、禹、羿等,但此一神话人物与彼一神话人物之间、同一神话人物的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之间并没有哪怕是可供局部统观的因果线索相贯。在究心于中国神话的学者中,有人推测汉语神话所以零散无序,乃因着神话图籍的亡佚,但也终于悟识到这零散无序正是汉语神话的本来面目;也有人以希腊神话为参照,试图从中国汉语神话中找出“诸神世系”。然而,在对伏羲、黄帝、帝俊等最具“主神”资格的神话人物乃至半神半人的羿、禹等“英雄”人物的神迹一一作了考辨后,结论却并不能支持寻觅诸神世系者的期待。成谱系的古希腊神话的叙事是网络型的,中国汉语神话的叙事是散点式的,两种相异的神话叙事表达着两种文明发祥的初始人们获得的不同生命视界。如何对古希腊神话叙事与中国汉语神话叙事的异致作出解释,这固然尚须探询中西文化殊途演进的真正契机,不过,可以大体确认的一个事实是,散点式的中国汉语神话叙事使史诗无由发萌,而史诗的无由发萌又势必会造成悲剧这一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延误。
谱系化的神话叙事寓托着叙事者寻根究底的心灵执著,支持这一份执著的是对人或可窥探其消息却决然对其无可施为的某种世事最后原由的信从。与此异趣,散点式神话叙事中涵贯的精神,虽不属意于对世事的某种最后原由的否弃,也不意味着对这最后原由的不置可否,却并不执著于由这最后原由生发的宇宙秩序的穷究。在这里,切身的践履是松开了理智的推求的,散点式神话的叙事者只是带着人间的诸多疑窦与关切向拟想中的神界的对应处寻找慰藉、解惑或救助。相应于两种不同的神话叙事方式和两种不同的关于世界最后原因或理由的态度,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和前孔子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发人深省的两种不同的“命运”观。“命运”的未可逆违在古希腊人那里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必然”的定则的信从使他们把多神的神界谱系化为一统之域。神话叙事原是叙事者心灵眷注的写照,古希腊人对必然的“命运”的敬畏既使他们的神话叙事就此获得了某种一以贯之的纲维,也使以这种神话叙事和由之生发的史诗为先导的“悲剧”自始就定下了“命运”冲突的底调。以古汉语作神话叙事的中国人也有其“命运”意识,不过,“命运”在先秦汉语著述中常被称作“命”。“命”不像古希腊人所说的“命运”那样予人以强制的必然性,少了几分命定执著的“命”,使中古时代的中国人有可能从别一种向度赋予其意义。“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注:《诗·周颂·敬之》。),其“命”固可领会为“善则予之吉,恶则加之凶”的天道,而“天难谌,命靡常”(注:《书·商书·咸有一德》。)之“命”,却是更多地在叹说兴亡无常以告诫人主惟有“常厥德”才能“保厥位”。对“命”的一定的公正性的期待和对其非前定性的申说,同时即是对那种外在地强加于人的必然性的荡开;这种“命”(亦可谓为“命运”)意识投向神话叙事,必致叙事非趋于线性因果关联而仅成一散点的格局,而散点式神话叙事又必致史诗的无由创生和戏剧的姗姗来迟。至于中国戏剧中终于少了悲剧的性状,却也未尝不可以从这非强制的必然性的“命”意识中得到相当的理解。
与两种不同的“命运”(“命”)观念相依互证,古希腊谱系化的神话叙事与古代中国散点式神话叙事尚各有其审美意识的隐喻,这默然的隐喻着的审美意识或多或少地促成了中西戏剧命意趣向的泾渭之判。通常人们总习惯于把希腊神话视为神话所当有的范型,并因此以之评判其他民族神话的所长与所欠。在人们的意想中,与人同形同性的希腊诸神似乎是神的理所当然的最高形态,而人兽同体之类的神则表明其所属神话尚处在神话演历的较低阶段。这是一种很少被反省的执著,它暗含着可能的西方中心论的偏颇和与之互为因果的人对自然一味征服的意欲。希腊神话中的神也有半人半兽乃至全然兽形的,但在神界终于赢得正宗地位的以宙斯为神魁的奥林匹斯诸神已全然与人同形同性。以与人同形同性的神衡之于神中的半人半兽,人兽同体者——例如斯芬克斯等——遂被称之为“怪”。其实,从神和“怪”的出身看,二者的“血缘”都可上溯到地母该亚,所不同者只在于“怪”更多地凭附于动物,神更多地与人同形同性。在神中,宙斯的父辈、母辈及同辈中的非同胞兄妹们构成神的较早的一族,这身形巨大——与人同形同性尚有一定的距离——的神族被称为“泰坦”。“泰坦”神族的神力在于自然,而宙斯神系的奥林匹斯诸神——真正堪称与人同形同性的神——的神力却更大程度地在于对自然之力的征服与支配。至于“怪”,则多是引致祸患或灾变的自然力的化身,它同“泰坦”神族所象征的自然力有着微妙的差异。希腊神话中,神与“怪”及两大神系的较量默蕴了以人对自然的权力取代自然对人的权力的期待,宙斯神系对“泰坦”神系的胜利隐示着人对自然之力的可能驯服。神话中所隐喻的人与巨大的自然力的对抗乃至人对自然的试图驾驭,倘渗透到审美意识,必致引发人的“崇高”感,而这种“崇高”感——它在戏剧中产生于敢于功过自承的人直面非可测度的“命运”时——则正构成悲剧所必要和当有的氛围。与希腊神话略不相类,中国汉语神话中的神的模样多为变形的动物或奇异的半人半兽。《山海经》称得上中国汉语神话的渊薮,而传达在这部文献中的神祇——凡形象被描绘者——无一例外属兽形或人兽同体,诸如龙首马身、龙首鸟身、鸟首龙身、龙首人身、人首马身、人首牛身、人首猪身、人首羊身、人首鸟身、人首蛇身等。在汉语神话未被史家着意作一种历史处置或被小说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所说的那种“小说家”)演述为“仙话”之前,诸神一直以人兽同体为形象隐喻着中国初民朦胧而耐人寻味的精神性状,兽(禽、虫)是自然的表征,人兽同体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喻示了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问题也许不在于汉语神话(而非“仙话”)中的神比起古希腊的与人同形同性的神更原始,而是在于人兽同体之神在纯粹“神话”的限度内何以终于不曾演变为与人同形同性之神。其实,人兽同体之神的持续创设和认同,本身即蕴含了创设者(初民们)与自然相亲比而非相对立的心灵状态。这情境在足够长的时间延续中,默默孕育了中国人以“和谐”而非“崇高”为主导祈向的审美意识的原始根荄。
谱系化的神话叙事和与之相表里的以强制的必然为内涵的“命运”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发于人与自然力的对立的那种“崇高”感,构成古希腊悲剧得以诞生的背景与依据,酒神——狄俄倪索斯——只是凭了这些才始终守护着悲剧的每一代新生儿的摇篮。与此殊异,散点式的神话叙事和与之相依互证的“天难谌,命靡常”的“命”意识,以及同这“命”意识和人兽同体神话相配称的人与自然的亲比乃至“和谐”趣向,则延迟了戏剧在中国的发生,也消解着古希腊式悲剧在汉语世界出现的可能。
四、后“轴心时代”的戏剧:西方和中国
希腊悲剧在欧里庇得斯那里再次攀上它的巅峰后,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这富于悲剧性的结局,乃是悲剧隐衷的一种真切的自我诉说。对希腊悲剧颓败的缘由,歌德有过这样的解释:“三大悲剧家每人都写过一百种或接近一百种的剧本。荷马史诗中的题材和希腊英雄传说大部分都已用过三、四次了。当时存在的作品既然这样丰富,我认为人们不难理解,内容材料都要逐渐用完了,继三大悲剧家之后,任何诗人都看不到出路了。”(注:爱克曼辑《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比起这个颇为公允而毕竟囿于题材资源的说法来,尼采的一个略嫌偏至的断论却要透彻得多。在把悲剧的凋敝归咎于欧里庇得斯后,他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欧里庇得斯只是一个化身,而透过欧里庇得斯所表现的神灵,既不是狄俄倪索斯,也不是阿波罗,而是一位叫做苏格拉底的崭新的魔鬼。从那个时候以后,真正的对立是狄俄倪索斯和苏格拉底精神之间的对立,悲剧就在这种冲突之间消灭了。”(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刘崎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悲剧的萎谢被关联于苏格拉底的出现也许是不错的,只是终生以“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自命的尼采并不能真正悟识他指责为“魔鬼”的那个人对于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意义。
苏格拉底带给人们的是一个被雅斯贝斯以“轴心“相喻的时代,从此,希腊人文眷注的焦点由“命运”转向“境界”(注:参看拙作《从“命运”到“境界”》,见《哲学研究》1996年第2期。)。“境界”意味着人生价值或意义的厘定,苏格拉底可谓从元始或终极处厘定人生价值或意义的第一位西方哲人。新的人文眷注的慧眼在于对人的心灵的确信,这能够亲切体证美、善、大等价值的心灵在苏格拉底那里正通着所谓世界目的或宇宙心灵。当世界的最后理由和最后目的被美、善、大的价值之光所照明,沉重而诡谲的“命运”(它在哲学上曾通过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所寻究的宇宙“始基”而被古希腊人所反省)便不再能掀起袭击人的心灵风暴。英雄乃至神的非凡力量和智慧与“命运”间的那种剥离不去的紧张感,一旦因着“命运”羽翼的收敛而松驰,悲剧也就难以在舞台上展露它那引生恐惧和怜悯的酷烈的美了。苏格拉底所确立的“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注:柏拉图:《斐多篇》,100B。)对“命运”的驱赶同时即是对希腊式悲剧的灵根的摇夺,就此而论,尼采称苏格拉底为勾去悲剧灵魂的“魔鬼”,也当然未可责作诬枉之辞。但苏格拉底以“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诱导人们趋“美”、向“善”、尚“大”而提升—种人生境界,却又何尝不是对价值祈求中的人的灵性的点化。希腊式的悲剧也许仅仅相应于以“命运”为终极关切之惟一维度的时代,我们尽可不必因着悲剧的执著而执著于寡头的“命运”。悲剧在苏格拉底之后的西方亦曾再生,不过,无论如何,那再生的悲剧已不单单是古希腊悲剧的翻版或复制。
与苏格拉底哲学对于希腊人乃至西方人的意义略相当,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论语·述而》。),立儒家成德之教于中国。无论贯穿在神话叙事、诗歌吟唱和哲学运思中的“命运”意识如何不同,前“轴心时代”——在中国亦即前孔子时代——的中国人终是与前“轴心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其由衷的忧患或惊异总会带着几分难以言喻的“命运”感。“命运”的诡秘诱使古希腊的哲人们取认知的路径以理性询问宇宙的“始基”,与“命运”(“命”)相关的利害抉择则驱策着中国古昔的作《易》者凭借卦爻以“人谋鬼谋”的占筮贞问人事的“吉凶休咎”。苏格拉底把哲学问题由宇宙“始基”的寻索转换为世界目的与人生意义的认取,以“美本身”、“善本身”、“大本身”的设定启示人的“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孔子则“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在为《易》指出一个全新的诠释向度时所经心的乃是对“仁”性内在的人“道(导)之以德”(注:《论语·为政》。)。前“轴心时代”的中国,汉语言文学中原本就缺了结构性叙事的性状,孔子的成德之教因淡泊“死生”、“富贵”而松开了人对外境的利益求取的执著,这便使那种寄兴于对待性关系的结构性叙事愈益不被看重。中国的人文教化在“轴心时代”之后虽有儒、释、道三教的格局,儒家的价值取向却一直占有主导的地位,而释、道两家施教也都以人的内在心灵境界为指归——佛家一向自谓为“内学”,道家的“不言之教”所引导人们的则多在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注:《老子》十九章。)。这样的人文取舍既是对人在对待性关系中才可能赢得的功利价值的一定程度的消解,也必致与之相系的结构性叙事方式受到可能大的制约。文学叙事或起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者流”(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这在儒者看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然而“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注:《论语·子张》。)。“君子不为”可能是滋生于街巷俚俗的文学叙事作品——叙事诗、传奇等——延宕不进的缘由所在,而这延宕又正可用来说明中国的戏剧何以姗姗来迟以至晚出于宋元之际。
在中国戏剧艰难孕育的漫长时间里,西方的悲剧一直赓续着它的一线脉息。欧里庇得斯之后,希腊悲剧再也没有重温过它既有的辉煌,但结局并不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横死于一旦。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悲剧还在阿斯堤达马斯、开瑞蒙、卡尔喀诺斯、忒俄得克忒斯等诗人那里苟延残喘;公元前3至2世纪,希腊也还产生过六十多位悲剧诗人。希腊哲学的主题命意从“命运”到“境界”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命运”问题不再被人们提起,但“轴心时代”后的“命运”眷注已经是在自觉了的人生“境界”意识的笼罩下。古希腊人在把“境界”自觉这份遗产——它同犹太教的交融互摄产生了基督教——留给它的文化后裔时,也把曾经从“命运”的渊默处引出灵感的悲剧的种子撒在了西方。无论悲剧在此后的成就如何,它的传承者总是代有人出。从罗马时代的塞涅卡到17世纪的法国剧作家高乃依、拉辛,乃至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诗人、剧作家歌德、席勒,悲剧的幽灵一直时隐时显。这期间,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尤其引人瞩目。这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是奇迹时代出现的奇迹,在悲剧失去其巅峰期一千多年后,它在这里一度找到了重现绚烂的灵韵。
朱光潜曾指出:“至少在悲剧里,莎士比亚几乎完全活动在一个异教的世界里。他通过塞涅卡和英国本国的前辈作家,间接地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悲剧的形式;又从他那些条顿民族的祖先那里继承了悲剧的精神。”(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235页。)这见解真切而传神。不过,他也说:“他的悲剧中的人物往往显得比基督化的欧洲人更原始。”(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5页。)对此,这里愿借克里斯托弗·道森的一个说法稍作矫正——在道森看来,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履行人文主义使命的人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是“基督教化了的人”(注: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事实上,无论是哈姆雷特、奥赛罗,还是李尔王、麦克白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无一不是多少被“基督教化”了的人,这同莎士比亚本人乃“基督教化了的人”大致相应。新的悲剧没有失去希腊悲剧的“命运”记忆,不过,宗教和道德向着人的生命的内化已使先前纯然外在的“命运”在进入“境界”化了的心灵时有所变易。同是复仇悲剧的主人公,希腊悲剧中的俄瑞斯特的内心世界是贫乏的,他只是被“命运”注定了的一个不能没有的角色。莎氏悲剧中的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则要丰赡得多,他让人透过由性格牵带出的冲突看到了一个自作仲裁的人的生命“境界”。元始悲剧中的“命运”线索在莎士比亚悲剧中延伸为“性格”所必致的某种必然性,这必然性在展示中所显现的悲剧人物的心灵“境界”向人们报告着后“轴心时代”的悲剧的别一种精神。
相形之下,中国的戏剧正可全然谓其为后“轴心时代”——亦可谓后孔子时代——的产儿。它没有可资追忆的前“轴心时代”的胎痕,因此自始便少了只是在前“轴心时代”才最有可能萌发的悲剧的性状。悲剧契接于后“轴心时代”的机缘是绝少的,但在西方,它毕竟有幸与莎士比亚相遇。在中国,却是因着不曾产生自己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竟至终于未能产生自己的塞涅卡、高乃依、拉辛,更不用说自己的莎士比亚了。
在西方作了史诗源头因而同史诗一起酝酿了悲剧的神话,在中国只是嬗变为“仙话”之后才成为名符其实的叙事文学。这类“仙话”出现在“轴心时代”之后,它最早传述于战国后期的方士,汉魏以降则更多地附丽于道教。神话的“仙话”化,也是神话的喜剧化。喜剧化了的神话虽已是结构性的叙事,却因其喜剧格调而从此与悲剧绝缘。诚然,有些汉语神话并未在后“轴心时代”流衍为“仙话”,但即使如此,这些未被“仙话”化的神话也往往在儒家或道家学说的辐射下消解于无形。这消解与“命运”感在一种致“道”的教化——儒家的“道德”教化或道家的“自然”教化——中的消解或变形是一致的,它使前“轴心时代”不曾生发史诗与悲剧的神话在后“轴心时代”愈益不可能生发史诗与悲剧。
在绝去神话的记忆后,中国戏剧的取材或为史迹,或为两汉以还的民间传说,或为唐宋的传奇小说。其人物、剧情的原型或受祸福报应观念的匡束更大些,或有着若隐若显的伦理宣诫的印痕。个中也多有不为乡愿、常俗所范的情爱或义举,但痛达生命本体的人生悲情——非世俗善恶所酿成的那种悲苦——尚告阙如。悲剧的创制当然不可能不受制于题材的选择,但重要的还在于悲剧的体式。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斯》取材于霍林舍德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其主人公的原型——历史人物麦克白斯——是11世纪苏格兰的王室贵胄和疆场名将,他以阴谋手段篡夺了王位,又在十多年后被讨伐者索去了性命。这一历史素材完全是可以纳入忠奸之辨的模式而成就一部正义战胜邪恶的正剧的,莎士比亚却把它写成了让主人公自我撕裂其心灵的“罪行的悲剧”。试设想,元明时代的中国剧作家会怎样处理同类的题材呢?取材于先秦史迹的《赵氏孤儿》是一向被王国维以来的诸多学人称作悲剧的,但与《麦克白斯》相比,其虽多冤苦之悲,却仍不过是把忠奸、正邪判然两分给两类人的衬着喜剧光晕的正剧。关汉卿的《窦娥冤》似乎更是既成定论的悲剧,然而细品其味,也正同《赵氏孤儿》相类,只是它在给予人们的感动中又多了一分“天意”的慰藉。
悲剧在文艺复兴以至近代西方借着莎士比亚、拉辛等的灵感再度还魂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悲剧的根蔓在后“轴心时代”的西方从不曾全然枯萎,一旦与相宜的风雨、土壤相遇便会发芽抽枝重现风采。尽管新一代的悲剧不只是单纯的返本复始,而它对钟爱于它的诗人的倾情回眸也分外罕见。文艺复兴是西方人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化寻根,希腊罗马幽灵的被唤醒表明了受基督教千年熏染的欧洲依然铭记着它古老的人文血缘。中国的汉语戏剧没有前“轴心时代”——悲剧萌朕的最佳时期——的遗传基因,当它在宋元之际获得它的典型形态时,日臻完备的“神道设教”已足以把可能生发的悲剧感消释于人对至公至正的“天理”的崇仰与信从。悲剧情怀是指向一种终极关切的,这终极关切在宗教或道德教化之外的另一维度上。中国人的审美心灵因着独特的人文教化的陶冶而自有其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趣向,于悲剧的情缘有所薄,必于他处的造诣有所厚。我们尽可以秉持这一分自信和诚挚如此评量艺术对东西方的泽被:悲剧是动人心魂的,但动人心魂的艺术不必只是悲剧。
标签:赵氏孤儿论文; 文化论文; 古希腊论文; 窦娥冤论文; 趣向论文; 神话论文; 汉宫秋论文; 诗学论文; 山海经论文; 梧桐雨论文; 娇红记论文; 戏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