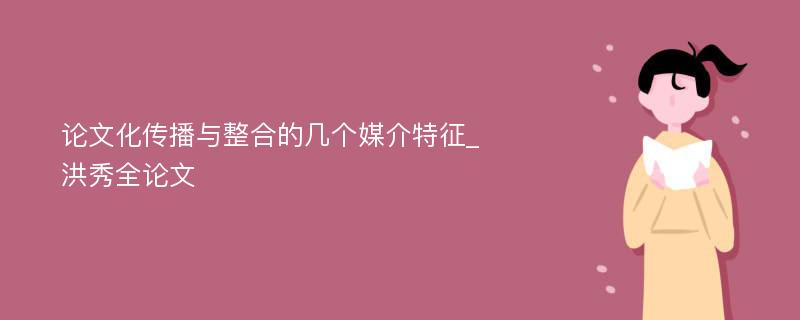
评文化传习与融通的几个媒介人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媒介论文,人物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化传习与融通是以人为媒介的人际交往活动,其媒介人的身份、地位、观点、立场的不同,使人类社会之间的文化传习与融通出现种种复杂情况,其中包括媒介人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矛盾。本文主要是对利玛窦、严复、洪秀全、曾国藩、章太炎、鲁迅作些分析,并结合这些具体人物谈一谈对文化传习与融通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利玛窦(1552—1610)是明末来华的一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居留近28年,不论是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还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从文化传习的角度看,利玛窦是以传教士身份出现的,他不属于时代先进思想的代表,但他在中国的实际所作所为,以及他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无人可替代的,是历史阴错阳差地把他推上了中西文化传习和融通的媒介地位,从而承担了别人没有承担的历史任务。
利玛窦来中国传教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利玛窦很识时务,他一到中国就刻苦学习汉语,研读中国儒家文化经典,了解中国国情、民情,在感情上尽快去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使自己能在中国立住脚。较高的文化素质,比较谦和的个性以及对自身宗教信仰自信而不自恃,宗教行为的检点及个人表现的宽容大度,都逐渐地打消了与其接触的中国人的怀疑和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也赢得当时中国官方的认可。
利玛窦在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方面值得肯定之处是:他着重寻找共同点和结合点,回避不同点。他对儒家思想也并不完全赞成,但是他注意缓和而不去激化儒学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力图从两者的融通上去诠释、说明。他自己就这样表白过:“在本人撰写的著作中,我始终都以对他们(儒生)的赞扬开始,以便能使我利用他们挫败其他人(佛教徒和道教徒),而不直接驳斥他们,仅仅是诠释他们与我们的教义相违悖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要同时反对三教,那么我们要作的事就太多了”(转引自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第79页)。他的这种抓主要矛盾的文化策略,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融通有了可能,利玛窦的传教功过也由此而生。对他加以肯定与否定都应注意到这一客观事实。
利玛窦身为传教士,他在中国的文化活动却不止于传教,而是同时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带进中国,使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有机会较早地接触到中国当时尚不存在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几何方面的新知识,从而激发了他们赶超西方学术的决心,立志在“会通”的基础上去“超胜”,这无疑是和利玛窦来华后传播西方文化分不开的。我们有理由这样说: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成绩是有限的,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使者的利玛窦,其作用却不可忽视。西方人是借助利玛窦,才真正知道中国确切的地理位置及名称的,至于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介绍,无疑是对西方人的中国文化知识启蒙。中国人则通过利玛窦,接触和了解到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呼吸到西方近化文明的空气。
利玛窦来华的初衷和来华后所作所为明显有别,其客观效果与他的主观动机并不完全一致。他把科学知识作为宗教传播的手段,也不是什么秘密,其实际情况则为:接受者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效果是两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在对利玛窦作历史评价时不能不记住马克思这样一段话:“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按着这一观点来分析利玛窦的活动、愿望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我们显然应当肯定他,尊重他的贡献。尽管他与伟大思想家相比,不过是“隔世风流”,但他作的仍不失是开拓性的工作。
严复(1853—1921)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前期思想进步,后期保守、倒退,他所起的最伟大的作用是把进化论思想引进中国。他翻译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论点,号召中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许多志士仁人在它的感召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鲁迅称赞严复是“十九世纪末一个感觉敏锐的人”。“一部译作,竟然能够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效应,实在是文化史上的奇观”(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1005页)。
严复是从救亡出发进行思想启蒙的,他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对抗宋代理学和心学的唯心论,用进化论的历史观对抗封建主义的保守历史观,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主张通过融合西方文化来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严复在政治上落伍了。他不能与时共进是因为他只能接受进化论,不能接受革命论,只同意渐变,不同意激变。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需要作多层次的分析,但他明确提出了:“民之可化,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原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大规模激进主义群众运动的态度。
严复面对的历史机遇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随之而前进,如果说他的前一时期,能够把进化论加以领会、运用,并溶进自己的血液中,出色地对中西文化加以融合贯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么后一时期,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当激进革命成为当时变革的主要目标之时,他自己的思想连同他所传播的西学思想也就难以成为主要的接受对象,从中可看到媒介人思想对文化传播的制约。
二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孙中山称之为“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他推崇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孙中山对洪秀全及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充分肯定,显示了他作为革命的政治家、思想家的立场观点,无疑是从打击和破坏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方面着眼的。
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相敌对的并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则是曾国藩及他领导下的湘军。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同狭义的文化斗争不能完全等同,但也不完全对立、割裂。分析洪秀全和曾国藩的文化思想,有的论者把洪秀全称作基督教文化的代表,曾国藩是程朱理学文化的代表,认为“曾国藩和洪秀全、杨秀清之间的斗争从文化方面说正是程朱理学武装的湘军和以基督教为有机内容的太平军之间的斗争”,“文化上的荒谬注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失败”。这种看法显然是陷入了一个理论上的误区,其根源在于把文化思想斗争与阶级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相割裂,这不能不让人们提出这样一连串的疑问:如果洪秀全不是用上帝的招牌,太平天国运动也打出程朱理学的旗帜,就能最终取得胜利吗?而洪秀全用洋上帝作招牌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
洪秀全的思想是否是传统的基督教思想,他创建的“拜上帝会”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组织,弄清这两个问题,就把洪秀全是否真正是基督教的代表搞清楚了。
洪秀全是一位出身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几次科举落弟、前途无望情况下,便将宗教作为他的精神寄托,体现了“无情世界的感情”。洪秀全信仰基督教不是为了使自己变成上帝的信徒,对其顶礼膜拜,也是利用它,另一方面以之去改变现实社会,其用意是为了现世,而不是来世。
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知识,也只是从中国牧师梁发根据《圣经》编写的通俗布道小册《劝世良言》中获得的,他的基督教理论修养是相当有限的,说他是基督教的代表也言过其实,外国来华的基督教神父曾与洪秀全论过道,双方都发现在对“上帝真理”理解上很不相同。而且洪秀全的上帝观明显夹杂着中国的宗亲观念,他把上帝看成人类的始祖,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帝原来是老亲”。此外,洪秀全的上帝观中又混杂着伦理、政治意图,上帝是为他的思想服务的,而不是他为上帝思想服务。相信上帝的人则应当同他一起“男将女将同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总起来看,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折射,是农民群众功利主义思想的表现。洪秀全心中的上帝是人神同型,把他自己标榜为代表上帝的“天子”,这就与中国传统的“天子”思想结为同道。
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农民理想,它也是洪秀全思想的集中表现,这说明洪秀全的主体思想仍然是属于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范畴,而不是外国基督教文化体系。洪秀全的实际思想水平,并未脱离“打倒皇帝坐皇帝”的农民革命窠臼。
曾国藩的传统文化功底要比洪秀全深厚多了,他在与太平天国进行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没有忘记使用自己的传统思想武器——祖宗的遗产,去反击太平天国的“叛逆”们。他声讨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诗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讨粤匪檄》)。两军对垒,各利其器,曾国藩利用传统文化这一思想武器去号召群众反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确实占据了思想阵地的有利地形,投合了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心理。
然而另一方面,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曾国藩不可能代表历史的进步方向,他的军事策略,政治手腕,文化宣传舆论都是受这一根本的行为左右和决定的,我们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把某一因素、策略抽出来,孤立地去强调、解释。
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把《资政新篇》作为一份空想计划留给后人;曾国藩的胜利,给他提供了开办洋务的机会。但是,曾国藩办洋务,只吸收西方的一些物质文明,目的是给封建制度打强心剂,曾国藩所倡导和吸收的西方文化,最终是为了改良中国封建社会机制,而不是推翻这一机制。
不论是洪秀全,还是曾国藩,都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文化,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方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值得肯定之处,但又都有主次不同的背景之分。
三
章太炎(1868—1936),被鲁迅称作“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是著名的“国学界之泰斗”,他的学术成就,梁启超用“至巨”来形容,不仅如此,他“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的还要大”(《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页)。
他一生横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几个不同的历史变革时期,新旧社会矛盾和斗争在他思想中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反映,给人留下一种光怪陆离的感觉。本文不是具体分析、研究他的思想变化历程,只是从文化传习与融通的角度,介绍一下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章太炎认为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承认人的活动是自然界整个运动的一部分,人的善恶源于物欲。对于进化论思想,也不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同意并接受自然规律方面的进化,但认为不属于人类社会的原理。他在《俱分进化论》中提出“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因此而提出“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
他的文化思想并不封闭,敢于吸收新知识,新思想,对西方文化并不完全抱着一概排斥的态度,他对西方哲学、社会学等都广有涉猎,对于印度的哲学、宗教思想也很熟悉。他不认为中外思想是绝对对立的,主张学习外国知识,并明确表示:“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国学讲习会序》)。但章太炎对西学并不象对国学那么看重,他对严复有些看不起,其中的原因包括严复的学问多在西学,国学根底不厚。他以为应当用西学辅助和巩固国学,把“新知附益旧学”,他对西学有保留、有戒心,后期又出现了对西学的敌对情绪,害怕传播多了会“灭我圣文”(《俞先生传》)。在他看来,“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与国学不相符的,就不是真新学,就要限制、排斥。
如果我们不是把章太炎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分析、评价,抽象地就思想论思想,并作出价值判断,可能得出五花八门的看法。反之,我们根据他所处的时代特点,采取历史的判断,那么就会发现,章太炎主观上是想与时共进,只是他的立场、世界观、历史观限制和束缚了自己。宗教和国粹是他手中的两件武器,有时他用这一件,有时又用那一件,有时又把两件变成一件使用。当他的思想符合、适应历史的发展时,他的武器就起了积极作用,不适应历史发展时就起了消极作用,章太炎自身的矛盾及复杂性在于:使用武器的主人左右了武器自身的价值。但他最为看重的仍是“国粹”这个重武器,而进化论、唯识论这些洋武器,则只是把它们作为“国粹”的配件看待,又有安装是否得体的问题,结果便使章太炎由前期的革命转到后期的保守、复古,由“原来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变成“拉还拉,而是拉车屁股向后”(《鲁迅全集》第5卷,第536页)。
鲁迅在学习、传播、融通外来文化方面与章太炎最大的不同,是他相信进化论,用进化论思想去批判国学中的因循守旧、僵化教条的说教,以及种种唯心主义内容,而不是象章太炎那样“以新知附益旧学”。鲁迅始终与时代同步,他不脱离社会斗争,认真学习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这又使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进化论”水平上。即使存在着一些思想障碍,但总是相信未来,这种“向前看”的思维方式与章太炎向后看的思维方式就有质的不同。
鲁迅对“国粹”抱着一种扬弃的态度,他能运用自己学来的西方文化知识来反思传统文化,不象章太炎那样总是在传统中徘徊,在“国粹”圈子中淘金,因而鲁迅的视野更宽阔。对外来文化,鲁迅则采用一种开放型态度,敢于大胆吸收,大胆取舍,本着营养自己的“拿来主义”去摄取新知,结果使自己的思想更为根深叶茂。而章太炎在排满目的达到后,一心复旧“国性”,由批孔批儒一变而为带头尊孔、复古,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其结果就出现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自己的思想也就枝干叶枯了。
从章太炎的倒退到鲁迅的前进,我们看到接受和融通外来文化方面两种不同的类型。鲁迅最终能高出历史上的一些先贤,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与他勇于、善于接受和融通外来文化,学习中外先进科学理论有着直接关系。
标签:洪秀全论文; 章太炎论文; 基督教论文; 利玛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曾国藩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进化论论文; 鲁迅论文; 严复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