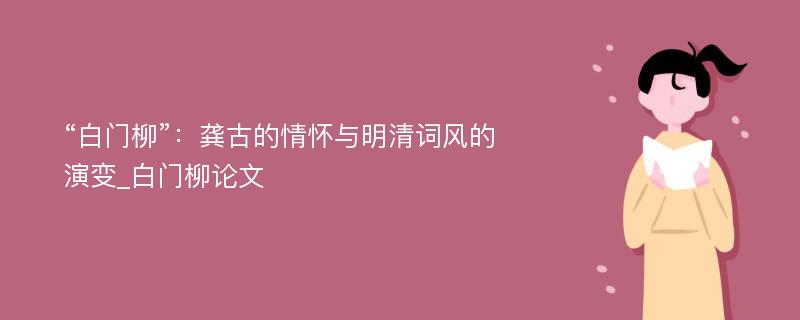
《白门柳》:龚顾情缘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情缘论文,白门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龚鼎孳和钱谦益、吴伟业在清初齐名,号为“江左三大家”,但其文学成就却一直为论者所忽视。有学者拈出龚氏23首“茧”字韵《金缕曲》,指出清初以龚氏等人为首发起的“秋水轩”唱和,用或悲慨苍凉、或郁懑哽咽、或自怨自艾的声音,合奏出易代乱离的一曲悲歌,为鼎革之际人们疏泄胸中块垒提供了一次机会,因而对清代初年的词风演进有着重要作用(注:参看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122页。),堪为有见之言。但前人评龚鼎孳词的价值,或谓“芊绵温丽”(注:彭孙遹:《金粟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5页。),或谓“词采精善”(注: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词话丛编》,第4038页。),均与“秋水轩唱和”诸作风格不侔,必然另有所指。
龚鼎孳有《白门柳》、《绮忏》二词集,皆为早年之作。二集虽然都为艳词,但前者情调统一,脉络齐整,后者内容庞杂,唱酬尤多。可见龚氏析之为二,有其特定考虑。其中尤以《白门柳》的感情、体式和结构,在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中,有着独特的意义。
一、《白门柳》的感情轨迹
《白门柳》有龚鼎孳自撰《题辞》,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靡曼相倾,恣心极态,江南奉为艳宗。吾所云然,不耑斯谓。要之,‘发乎情,止乎礼义’,其大略可得而观焉。”(注:《全清词》第2册“顺康卷”,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0页。)龚氏所引艳诗《杨叛儿》,载于《玉台新咏》的“近代西曲歌词”。虽然龚氏自言“不耑斯谓”,或者是感情的抒发方式不同,其作品本身当然也是艳词,而“江南”二字,则隐然点出了作品的背景。综合考察,这应是一卷记载与顾媚情史的专集(注:《白门柳》中多次出现“桃叶”、“薛涛才”、“画眉”、“长干”等词,也可证与秦淮妓即顾媚有关。)。余怀《板桥杂记》“丽品”条有云:“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通文史,善书画。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未几,归合肥龚尚书芝麓。尚书雄豪盖世,视金玉如泥沙粪土。得媚娘佐之,益轻财,好怜才下士,名誉胜于往时。……嗣后还京师,以病死,殓时现老僧相,吊者车数百乘,备极哀荣。改姓徐氏,世又称徐夫人。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注:余怀:《板桥杂记》,《香艳丛书》第7册,上海书店1991 年影印本,第189—191页。)顾媚既出自秦淮旧院,龚之初访眉楼,也是为了狎游,是则以《白门柳》名集,正得其体。史学家孟森先生曾撰《横波夫人考》一文,旁征博引,对龚顾情史考证甚密,惜未及《白门柳》,可谓百密一疏(注:载《心史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而所谓“《白门柳》传奇”,公私藏书均无著录,疑即此集。“传奇”云云,或为当时文风的某种体现,说见后。
《白门柳》展现了龚顾情缘的一道完整的轨迹,试为之勾稽如下。
1.初上眉楼。崇祯十四年大计,龚鼎孳考绩为全楚第一,冬,铨选入京。次年春,途次金陵,入眉楼访顾媚(注:关于龚顾会面时间,另有崇祯十三年年初一说。见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6页。)。《白门柳》起首四阕, 题为《楼晤》,应是纪实,参以同时之诗,无不一一对应。如[东风第一枝](《楼晤,用史邦卿韵》之一):“团扇第、书生觌面。……爱紫兰、报放双头,恰好阮郎初见。”[鹊桥仙](《楼晤之三,用向芗林七夕韵》之三):“红笺记注,香糜匀染,生受绿蛾初画。”龚《登楼曲》四首之一亦云:“晓窗染研注花名,淡扫胭脂玉案清。画黛练裙都不屑,绣帘开处一书生。”又[杏花天](《楼晤之四》)云:“搓花瓣、做成清昼。度一刻、翻愁不又。今生誓作当门柳,睡软妆台左右。”《江南忆》四首之四亦云:“手剪香兰簇鬓鸦,亭亭春瘦倚栏斜。寄声窗外玲珑玉,好护庭中并蒂花。”(注:《登楼曲》和《江南忆》二作,见龚鼎孳《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以上是初见情形。但当时龚鼎孳赴京考选,不能久留南都,因而二人乍见旋别,两情缱绻。[惜奴娇](《离情,用史邦卿韵》):“阑干外,愁潮恨岭。一步妆台,受不起、加餐信。……说谎高唐,可好托,春衾性。”[蓦山溪](《送别出关,已复同返,用周美成韵》):“清波桃叶,幻出刘郎路。两桨载鸳鸯,透金锁、重城几处。”也即《登楼曲》四首之四所云:“未见先愁恨别深,那堪帆影度春阴。湖中细雨楼中笛,吹入孤衾梦里心。”(注:《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
2.别后情愫。龚鼎孳入眉楼与顾媚定情后,旋即北上,两地睽隔,南北相望,相思之情也尽皆表现在《白门柳》中。其《长安寄怀》诗为其初至京师时所作,诗云:“才解春衫浣客尘,柳花如雪扑纶巾。闲情愿趁双飞蝶,一报朱楼梦里人。”(注:《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这种离思难遣、寤寐思之的情感在词中亦有表露。有时以神话作比,如[浪淘沙](《长安七夕》):“鹊楂一夕锦云收。我做牛郎他织女,夜夜桥头。”[风流子](《春明寄忆》之三):“销魂别,泪如巫峡雨,心逐广陵舟。乳燕幕开,锦笺难托,蜜蜂房闭,香粉都收。……七夕看看过了,梦见还羞。”由于相思难遣,反羡牛郎织女每年一会。有时托古事自喻,如[小重山](《邸怀》七首之五):“送眼落霞边。只愁深阁里、误芳年。载花那得木兰船。桃叶路,风雨接幽燕。”晋人王献之有《桃叶歌》云:“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注:《玉台新咏》卷一○。)王献之能以舟楫迎接其妾桃叶,龚氏遂感慨自己无处可觅木兰船,不能将恋人接到身边。有时则直抒胸臆,如[眼儿媚](《邸怀》七首之一):“柔肠憔悴无人见,见即恐花羞。试抛脑后,陡来衾底,又嵌心头。”[浪淘沙](《邸怀》七首之六):“翠幰报花来。春恨重栽。西风吹梦上妆台。旧梦不留新梦远,影里徘徊。”不过,有情人终能好梦成真。顾媚于崇祯十五年中秋北上,甫至沧州,因兵燹纵横,道路阻绝,遂流寓淮河沿岸的清江浦,次年春复渡江返泊于京口。入秋,复北上,辗转徙倚,直到崇祯十六年中秋始达都门。龚鼎孳曾赋[玉女摇仙珮]一词志喜,中有“怪年年碧海,成双非易。尽畴昔、罗裙画簟,无数销魂,见面都已”数句,感慨浊世滔滔,士女遇合,真自不易。
3.濡沫深情。龚鼎孳任兵科给事中期间颇以清流自命,屡屡上疏言事,弹劾权臣,虽或不免感情用事,其踔厉风发之气仍可嘉许。顾媚入京后,龚鼎孳作[念奴娇]一词,题为《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内有“翦豹天关,搏鲸地轴,只字飞霜雪。焚膏相助,壮哉儿女人杰”数句,自矜之余,也言及顾媚之力。但不久龚鼎孳便因此次劾论触怒明思宗而遭逮系入狱,时距顾媚入京仅五十余日。明代诏狱极其黑暗恐怖,龚鼎孳能够承受,和顾媚的精神慰藉当不无关系,因而有关作品也较多,如[菩萨蛮](《初冬以言事系狱,对月寄怀》):“婵娟千种意,莫照伤时字。此夜绣床前,清光圆未圆?”[临江仙](《除夕狱中寄忆》):“料是红闺初掩,清眸不耐罗巾。长斋甘伴鹔鹴贫。忍将双鬓事,轻报可怜人。”这也就是《内子初度,时余在狱中》诗其六一诗所云:“萧条四壁不堪愁,酒债琴心自唱酬。近识文君操作苦,侍臣无复鹔鹴裘。”(注:《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另有[玉烛新](《上元狱中寄忆》):“依稀烛下屏前,有翠靥绡衣,月明安否。小眉应斗。恨咫尺、不见痛灯人瘦。香柔粉秀。猛伴得、英雄搔首。千古意,谁许冰丝,平原对绣。”龚氏《上元词》二首则与此相通:“紫雾晴开凤阙初,五侯弦管碧油车。芳闺此夕残灯火,犹照孤臣谏猎书。”其二:“珠斗春浓接玉京,千门万户月华生。五陵游冶青丝骑,谁爱荆卿击筑声。”(注:《龚芝麓先生集》卷三四。)均是自感寂寞而许顾媚为闺阁知己。所以,当龚鼎孳于崇祯十七年获释,与顾媚复得相见时,就作有[万年欢](《春初系释,用史邦卿春思韵》)一词,内有“铁石销磨未尽,算只有、风情痴绝。生抛撇,瘴戟蛮装,更央珊枕埋骨。……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的动情之语,那就不仅是名士佳人的一般情怀,而是患难夫妻的生死深恩。此后,世事变幻,白云苍狗。龚鼎孳先降李自成大顺,后降清,不仅本人成为复杂人物,顾媚也不能不被牵涉其中(注:龚鼎孳降顺后,盛传其自我辩解云:“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说见冯梦龙《绅志略》(清钞本)、计六奇《明季北略》(大通书局《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等。但龚氏在明亡后所填的[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词有云:“弱羽填潮,愁鹃带血,凝望宫槐烟暮。并命鸳鸯,谁倩藕丝留住。搴杜药,正则怀湘;珥瑶碧,宓妃横浦。误承受、司命多情,一双唤转断肠路。”《题画赠道公》文中亦曰:“国破之日携手以从巫咸,誓化井泥,招魂复出。”则或者龚、顾确有身殉明社之举,但为人所救,得不死。)。但不管怎么说,其后期词中仍多有顾媚的影子,如[菩萨蛮](《题画兰云扇》):“春风宛转朱栏曲,吹花直上烟鬟绿。芳韵一枝斜,镜中人是花。纤云摇更曳,衬出鞭蓉雪。生爱靠香肩,倒言花可怜。”顾媚善画兰,龚鼎孳《定山堂古文小品》卷下《题画与曹秋岳》云:“甲申夏与秋岳留燕邸,郁郁寡欢。偶出此卷命予属闺人作兰。时则流离惨悴,笔砚颓唐,神虽王不善也。”又《题画兰》云:“舟过燕子矶头,江风殊劲,闺人遂拈弄笔墨以敌其势。于钦视此,当念我蓬窗相对,客心悲未央时也。”这样看来,龚顾二人的文艺活动就不仅是一般的流连光景,而是他们相伴度过亡国后艰难岁月的一种独特体验,或有复杂的心理活动在内。
综上所述,《白门柳》五十九首词,确为龚顾情史。今按时间先后略加诠次,其叙事稍晦者则从略:[东风第一枝](《楼晤,用史邦卿韵》),[蓦山溪](《送别出关,已复同返,用周美成韵》),[惜奴娇](《离情,用史邦卿韵》),[十二时](《浦口寄忆,用柳耆卿秋夜韵》),[西江月](《广陵寄忆,用史邦卿闺思韵》),[减字木兰花](《途中寄忆》),[薄倖](《春明寄忆》),[浪淘沙](《长安七夕》),[眼儿媚](《邸怀》),[念奴娇](《中秋得南鸿喜赋,用东坡中秋韵》),[兰陵王](《冬仲奉使出都,南辕已至沧州,道梗复返,用周美成赋柳韵》),[祝英台近](《闻暂寓清江浦,用辛稼轩春晚韵》),[风中柳](《复闻渡江泊京口,用孙夫人闺情韵》),[贺新郎](《得京口北发信,用史邦卿韵》),[玉女摇仙珮](《中秋至都门,距南鸿初来适周岁矣,用柳耆卿佳人韵志喜》),[念奴娇](《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菩萨蛮](《初冬以言事系狱,对月寄怀》),[临江仙](《除夕狱中寄忆》),[玉烛新](《上元狱中寄忆》),[万年欢](《春初系释,用史邦卿春思韵》),[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用史邦卿春雨韵》),[石州慢](《感春》),[小重山](《重至金陵》),[西江月](《春日湖上,用秋岳韵》),[桃源忆故人](《同善持君湖舫送春,用少游春闺韵》)。
二、《白门柳》与明末社会风习
《白门柳》中所表现的明末党社胜流对青楼名姝的感慕、推引之情并非偶然,它是明清之际社会风习的产物。相对于波诡云谲、险恶多端的政治环境,明末社会风气放纵奢靡,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这或如顾炎武所云(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南北风化之失”条云:“江南之士轻薄奢淫,陈梁诸帝之遗风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76页。),有江南风流蕴藉的历史积淀在内,但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或许关系更深。明朝自嘉靖、隆庆以来,从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分离出来的阳明心学,以其简便易习风靡一时,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上崇尚个性、纵情憎礼的风气。尽管其后东林学派提倡简朴,鼓吹实行,复社也以兴复经术,敦崇道学相标榜,但东林之学亦主斥乡愿,近狂狷,复社兴起之际,王学左派之泰州学派所掀起的个性解放思潮余波尚存,所以身当其流的江南士子,罕有固守礼法者。
与此相应,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声妓繁盛,南都及苏、松、常、杭诸州郡更为突出。据《板桥杂记》载:“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宾游,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呼传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注:余怀:《板桥杂记》,《香艳丛书》第7册,第179页。)声妓繁盛既是社会风气奢靡的征象,又因其推波助澜而使后者往而不返。极富意味的是,明代选拔官吏的场所南都贡院与声妓之渊薮秦淮旧院仅有一河之隔。于是,“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注:余怀:《板桥杂记》,《香艳丛书》第7册,第182页。)当时声妓之盛和士人留恋声色、纵情诗酒的状况可以想见。
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南中党社胜流与旧院名媛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的甚至逾越了男女之间的社会界限和性别界限,如柳如是之与汪汝谦,顾媚之与陈梁(注:见冒襄编《同人集》(康熙水绘园刻本)卷四,陈梁诸书中称顾媚“媚兄”、“眉兄”。)。即以顾媚而言,与她相交往的明末党社中人就有张明弼(字公亮)、吕兆龙(字霖生)、陈梁(字则梁)、刘履丁(字渔仲)、冒襄(字辟疆)、吴绮(字园次)、邓汉仪(字孝威)、张岱(字宗子)、吴伟业(字骏公)、方以智(字密之)、阎尔梅(字古古)、余怀(字淡心)等。尽管这种关系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与名妓之间,但后者放弃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以被男性群体接纳为荣,却可以视为晚明女性意识萌蘖之一端,也显示出晚明社会风气的独特开放性。陈寅恪曾分析其中原因云:“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王姿明慧,虚心向学所然,然亦因其废闺房之闲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南中名姝的乐籍身份迥异于闭处闺房的普通女性,使之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封建礼法的羁缚,得以自由地与社会名流相往还。她们兼善才艺,雅有情趣,又识大体,知善恶,故名士也往往将其当做精神寄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相互推引,相互依存的关系带有几分超越时代的人文色彩,他们之间相敬相慕的感情也有类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除了龚鼎孳和顾媚,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等,也都是如此。张潮《虞初新志》卷五载徐芳《柳夫人小传》:“(钱柳)相得甚欢,题花咏月,殆无虚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击钵之顷,蛮笺已就,风追电蹑,未尝肯地步让。或柳句先就,亦遣鬟报赐。……于时旗鼓各建,闺阁之间,隐若敌国焉。”又卷三载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冒、董)日坐画苑书圃中,抚桐瑟,赏茗香,评品人物山水,鉴别金石鼎彝,闲吟得句与采辑诗史,必捧研席为书之。意所欲得与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相得之乐,两人恒云天壤间未之有也。”这样,就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所指出的:“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以及恩格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表述:“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注:傅立叶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8页注释;恩格斯语见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同上书,第411—412页。另参看陶慕宁《青楼文化与中国文学》第5 章《明末清初江南文酒声妓之会与青楼文学的政治色彩》,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名妓的爱情婚姻状况当然不能完全用来衡量当时妇女解放的程度,但也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系。龚鼎孳在《白门柳》中所表现的和顾媚之间的感情,也可视为这一参照系中的一个参数。
三、《白门柳》的传奇特质
余怀《板桥杂记》言及龚顾情史时说:“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今查公私书目,龚并无传奇题为《白门柳》者,可知所谓“传奇”,即指词集《白门柳》。但是,余怀为何将这一词集称为“传奇”?
“传奇”一语原是对唐人文言小说的称呼,其后相沿,宋元戏文、诸宫调、元人杂剧以及明代以唱南曲为主的长篇戏曲都可以称为传奇,可见它兼有内容和形式两种功能。从内容上说,它必须奇异,即不同一般;从形式上说,它必须叙事,即要求长篇。南中胜流与旧院名妓之间的交往,以至谈婚论嫁,两情相契,当然都是传奇的好素材,正如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都谏娶娼”条所云:“云间许都谏誉卿娶王修微,常熟钱侍郎谦益娶柳如是,并落籍章台,礼同正嫡。先进家范,未之或闻。”(注:谈迁:《枣林杂俎》,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年版,第251页。)而这种奇事,往往错综复杂,跌宕起伏, 非大篇无以敷演。龚鼎孳将自己与顾媚从相识相知到同甘共苦的过程都表现在《白门柳》中,已如前述,至于体式,由于词的篇幅短小,将若干篇联缀起来,形成联章,加以编排,体现出一定的叙事过程,也就具有了大篇的性质。
文学史一般认为,词是一种抒情艺术,其审美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抒写人们心中的隐约幽微之情。但现代词学家吴世昌先生却敏锐地抉出词写故事的功能。早在1936年,他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就指出:“小令初起时也是有故事骨干的,《花间集》中短调如[浣溪沙],有不少都包含完全的故事结构,北宋短调如清真[少年游]、[长相思],小山的[清平乐]、[诉衷情],也都有故事结构。”又于同年评周邦彦[瑞龙吟]云:“近代短篇小说的作法,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述过去,求与现在上下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尔后发展。欧美大家作品殆无不守此义例。清真当九百年前已能运用自如。第一段叙目前景况,次段追叙过去,三段再回到本题。杂叙情景故事,又能整篇浑成,毫无堆砌痕迹。又,后人填长调,往往但写情景,而无故事结构贯穿其间,不失之堆砌,即流为空洞。《花间》小令多具故事,后世擅长调者,柳、周皆有故事,故语语真切实在。”(注:吴世昌:《词学论丛》,《罗音室学术论著》第2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00、 890—891页。)按照吴先生的这一思路,单篇词能够写“故事”, 联章词当然更能。而且,联章词中所写的故事互相关联,最适合表现故事的全过程,因而就往往具有“传奇”的特色。
以词为传奇的观念到了明清之际更为突出,同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可以作为参照。王士祯《花草蒙拾》评论道:“娄东驱使南北史,澜翻泉涌,妥贴流丽,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独绝。”(注:王士祯:《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685页。)所谓“歌行”, 指吴伟业以七言长篇写时事的“梅村体”。在词的方面,吴伟业曾被清人称为“本朝词家之领袖”(注:张德瀛:《词征》卷六,民国三十年刻阇楼丛书本。),或有过誉,但其词确有创造性,诗词相通即其体现之一。如十三首[满江红],以史事、时事入词,正可称为词中的“梅村体”。如[满江红](《蒜山怀古》):“沽酒南徐,听夜雨、江声千尺。记当年、阿童东下,佛貍深入。白面书生成底用,萧郎裙屐偏轻敌。笑风流北府好谭兵,参军客。人事改,寒云白。旧垒废,神鸦集。尽沙沉浪洗,断戈残戟。落日楼船鸣铁锁,西风吹尽王侯宅。任黄芦苦竹打荒潮,渔樵笛。”此词名为怀古,实咏杨文骢抗清事。据《明史·杨文骢传》:“文骢善书,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缘以进。其为人豪侠自喜,颇推奖名士,士亦以此附之。明年迁兵备副使,分巡常、镇二府,监大将郑鸿逵、郑彩军。及大清兵临江,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朔,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其地,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炮石,以为克敌也,日奏捷。初九日,大清兵乘雾潜济,迫岸,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冲之,悉溃。”以史衡词,若合符契。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伟业以歌行体入词,也是一种传奇式的写法,唐人传奇的产生正和长庆体的产生大体同时,彼此互有影响。如果说从长庆体发展而来的梅村体影响了词,使得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传奇的特征,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提出的是,龚鼎孳对梅村体并不陌生,集中不乏仿作。著名的有《金阊行为辟疆赋》,写名士佳人的乱世遭遇,寄寓家国之悲,流离之感,风格神似吴伟业《圆圆曲》诸作,可见当时文人之间创作的关系。吴伟业能够以歌行之法入词,是对文学史的一种创造,流风所及,对同时诸人不可能全无影响。龚鼎孳接过来加以发展,可谓后出转精。因此,余怀将《白门柳》称为传奇,也不是没有缘故的。
当然,《白门柳》之被称为传奇,和它的内容仍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明清之际,士女遇合与家国之思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一时胜流从不同方面表现这一内容,争奇斗艳,各有千秋。诗歌已如上述,散文如冒襄《影梅庵忆语》、侯方域《李姬传》等,分别记述作者和董小宛、李香君的情事,也都可称之为传奇,在这种背景中,龚鼎孳将自己的词作编纂成集,也含有珍视这一段感情的意思。事实上,龚鼎孳对传奇体情有独钟,他曾仿传奇体作《圣后艰贞记》,记述明熹宗张皇后的遭际,其书虽然今已不存,但可由此见出他的创作意向,而《白门柳》正可视为这一思路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词中所记录的情感如初遇之热恋,相思之苦痛,亡国失路之憔悴,相濡以沫之深情,跌宕起伏,哀感顽艳,正是易代乱离中士女遇合的一出传奇。明代传奇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对情的重视,如《牡丹亭题词》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注: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白门柳》的传奇性在这一点上也能体现得非常明确。
这里,我们想把龚鼎孳的《白门柳》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略作比较。《影梅庵忆语》写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情真意挚,深沉婉转,是晚明散文小品的代表作之一。从二人交往的过程看,由相识进而相知相伴,也经历了一段坎坷。如冒襄牵于家事科场,与董小宛几经离合:“姬曰:‘我装已戒,随路祖送。’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浒关至梁溪、毗陵、阳羡、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辞。姬惟坚以身从。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东下,断不复返吴门!’余变色拒绝,告以期逼科试,年来以大人滞危疆,家事委弃,老母定省俱违,今始归经理一切。且姬吴门责逋甚众,金陵落籍,亦费商量。仍归吴门,俟季夏应试,相约同赴金陵。秋试毕,第与否,始暇及此。此时缠绵,两妨无碍。姬仍踌躇不肯行。时五木在几,一友戏云:‘卿果终如愿,当一掷得巧。’姬肃拜于船窗,祝毕,一掷得‘全六’,时同舟称异。余谓果属天成,仓促不臧,反偾乃事。不如暂去,徐图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声而别。余虽怜姬,然得轻身归,如释重负。……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闱,姬猝到桃叶寓馆。盖望余耗不至,孤身挈一妪,买舟自吴门,江行遇盗,舟匿芦苇中,柁损不可行,炊烟遂断三日。初八抵三山门,恐扰余首场文思,复迟二日始入。姬见余虽甚喜,细述别后百日,茹素杜门,与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则声色俱凄,求归逾固。……七日乃榜发,余中副车,穷日夜力归里门,而姬痛哭相随,不肯返。且悉姬吴门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责逋者见其远来,益多奢望,众口狺狺。且严亲甫归,余复下第意阻,万难即诣。舟抵郭外朴巢,遂冷面铁心,与姬决别。仍令姬归吴门,以厌责逋者之意,而后事可为也。”(注:冒襄:《影梅庵忆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宣统元年至三年上海国学扶轮社《香艳丛书》本,第581—583页。)这段记载让我们认识到,冒、董终能好合,其间有着不少的曲折。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段话从字面上看,冒、董之关系是董主动,冒被动;董热烈,冒矜持。但我们认为,这毋宁说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尽管冒襄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言行有放荡不羁之处,礼法的观念仍然为其内心所谨守。所以,他的记载明白不过地是想让读者认识他本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动机。值得提出的是,龚鼎孳在《白门柳》的题词中也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相标榜,考其动机,或者因乐府《白门柳》太过香艳,因而提醒读者注意二者的差别。就这一点而言,龚、冒二人或有不同,但相同的创作取向却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一致性。所以,如果说冒的《影梅庵忆语》是明清之际士女遇合的一出传奇的话,龚的《白门柳》当然也是。
四、《白门柳》与明清之际词体的演进
以陈子龙等人代表的云间词派,在清初高举变革的旗帜,倡言“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注:沈亿年述《支机集》凡例,施蛰存编《词学》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推崇晚唐五代、尤其是《花间》词风,以幽远深微之美,初步扫除了明代以来的浅俗之习,为清词的发展创设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云间词人矫枉过甚,独重小令,也有局限。因为小令方幅狭小,难以反映复杂多端的社会生活,而且风格也比较单一,无法体现作家多方面的创造性。明清之际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弊端,也尝试予以反拨,龚鼎孳就是其中较早的一个。正如王士祯所评:“云间数公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坐此。合肥乃备极才情,变化不测。”(注:王士祯:《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685页。)
龚鼎孳作词开始也从云间入,善写小令。如[鹊桥仙](《楼晤之三,用向芗林七夕韵》):“红笺记注,香糜匀染,生受绿蛾初画。挑琴擘阮太多能,自写影、养花风下。风低金管,带飘珠席,两好心情难罢。芳时不惯是乌啼,愿一世、小年为夜。”[小重山](《重至金陵》):“长板桥头碧浪柔。几年江表梦、恰同游。双兰又放小帘钩。流莺熟,嗔唤一低头。花落后庭秋。蒋陵烟树下、有人愁。玉箫凭倚胜风流。乌衣燕,飞入旧红楼。”王士祯评前首云:“词至此,是追魂夺魄手段。公擅诗柄,又欲抽秦、柳五花簟耶?”评后首云:“令与陈、宋旗亭画壁,未知谁当擅场。”(注:邹祗谟、王士祯:《倚声初集》卷一○。转引自张宏生《倚声初集集评》,《清代词学的建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但龚不久就显示出更为开阔的气局:“古人蕴藉生动,一唱三叹,以不尽为嘉。清真以短调行长调,滔滔莽莽,如唐初四杰作七古,嫌其不能尽变。至姜、史、蒋、吴炼字句,法无不备。兼擅其胜者,唯芝麓尚书矣。”(注:沈雄《古今词话》引徐釚语,《词话丛编》,第1036页。)他最为人称道的是长调,如彭孙遹《金粟词话》所云:“长调之难于小调者,难于语气贯串,不冗不复,徘徊宛转,自然成文。今人作词,中、小调独多,长调寥寥不概见,当由兴寄所成,非专诣耳。唯龚中丞芊绵温丽,无美不臻,直夺宋人之席。”(注:彭孙遹:《金粟词话》,《词话丛编》,第725页。)但今人论及龚鼎孳的长调,每举其后期之作,如“秋水轩唱和”的23首[金缕曲],以为具有扭转风气之功,其实他对调式的探索在早期词中即见端倪。在《白门柳》的59首词中,共有20首长调,显示了龚鼎孳对这一体裁的重视以及驾驭这一体裁的才情。与云间词派远绍《花间》,“不欲涉南宋一笔”不同,龚鼎孳则有意识地取法宋人。据我们统计,《白门柳》有24首为和宋韵之作,虽多取径《草堂诗余》,如明人一般之所为,但由于时代风会和个人际遇,却避免了明人常有的陋俗,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如[鹊桥仙](《楼晤之三,用向芗林七夕韵》)之缱绻深至,逼似小晏;[西江月](《渡江作》)之清丽峻洁,大类稼轩;[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用史邦卿春雨韵》)之凄婉蕴藉,韵如淮海;[念奴娇](《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之豪放沉雄,格同东坡。值得进一步提出的是,《白门柳》中有6首和韵词,专门追和史达祖,设色浓丽,意象绵密,神似史氏。如[贺新郎](《得京口北发信,用史邦卿韵》):“莺馆安排静。待珠轮、逐程屯劄,柳旗花令。预遣探香乌鹊去,露洒星桥玉冷。可曾见、卢家官艇。金字虎头青鸟印,押红泥、遮抹春愁影。骑凤月,破烟暝。
瑶箱泪叠朱丝胜,试芙蓉、两行宫烛,对摊芳信。薇雨细揉弹事笔,温熟低心软性。料锦鲤、今番情定。雾幔晴衫深打叠,怕秋棠、不耐商飙劲。因早雁,嘱君听。”这是闻知顾媚北上喜极而作,通过安排住所,遣人相迎,摊信沉思,叠理秋裳等琐细举动,表达出浓烈的感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词中罗列了许多装饰性的名词,如莺馆、珠轮、柳旗、花令、星桥、金字、虎头、青鸟、红泥、瑶箱、朱丝、芙蓉、宫烛、芳信、薇雨、锦鲤、雾幔、晴衫、秋棠、商飙、早雁等,显得绵密繁缛,但由于全篇采用了叙事性的连续结构,意脉贯通,而非简单堆砌,所以并未造成词旨的阻滞不通。这正是学习史达祖词风而得其精华。众所周知,龚鼎孳喜欢提携后进,清初词坛上的风云人物陈维崧、朱彝尊等都得到过他的揄扬。揄扬朱彝尊事见于戴延年《秋灯丛话》,云:“国初宏奖风流,不特名公巨卿为然,即闺中好尚亦尔。龚尚书芝麓、顾夫人眉生,见朱竹垞词‘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倾奁以千金赠之。”所引词句见于朱彝尊[酷相思](《阻风湖口》)词,朱彝尊《龚尚书挽词八首》其六“江南断肠句,回首向谁夸”句自注曰:“公最赏予《阻风湖口》词”,可见戴延年所言非虚。朱彝尊推崇姜夔、张炎,提倡醇雅清空,开创浙西词派,而姜夔、张炎和史达祖正好词风类似,路数相同。所以,如果说龚鼎孳对朱彝尊开启浙西一派有所影响,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之言。文学史上谈到浙西词派,一般都仅仅考虑了曹溶对朱彝尊的影响,现在看来,似乎可以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
其实,仅仅从词的形式上也能看出龚鼎孳对朱彝尊的影响。龚鼎孳的这一卷《白门柳》,记述作者与顾媚相识相知相伴的一段情史,可视为独特的联章之体。无独有偶,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一集也是如此。朱彝尊和妻妹暗生情愫,却又无法公开,只能把种种隐微的感情表现在词中。从结构上来说,也是描写了双方交往的全过程,构成了联章的叙事方式。当然,比较而言,在感情的指向上,龚更明确,朱则较隐晦;在感情的体验上,龚略轻倩,朱则更为凝重。这或者是由于顾媚是青楼女子,而寿常是良家闺秀,因而笔致有所不同,取向出现二致,但二人都运用了这一同样的表现方式,却值得注意。我们曾经借陈廷焯的话评价《静志居琴趣》的有关作品是“情词俱臻绝顶,摆脱绮罗香泽之态,独饶仙艳,自非仙才不能。凄艳独绝,是从《风》、《骚》、乐府来,非晏、欧、周、柳一派也”,认为他的词开辟了艳词发展的新局面(注:陈廷焯语见其《词则》之《闲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稿本;参看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3章《艳词的发展和新变》。)。现在需要加以补充的是,正是龚鼎孳的《白门柳》为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五、青楼文学传统与明清之际的词学复兴
词兴起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振起于清。明词衰微的原因,清人曾做过总结。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九云:“盖明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师传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填词,故焦弱侯《经籍志》备采百家,下及二氏,而倚声一道缺焉,盖以鄙事视词久矣。”(注: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词话丛编》,第3433页。)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云:“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阆仙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视国初诸老,已难同日而语,更何论唐、宋哉!”(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词话丛编》,第3823页。)或谓混词于曲,或谓格调浅俗,都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有进一步论述清词的复兴者,如文廷式《云起轩词钞自序》:“有清以来,此道复振。国初诸家,颇能宏雅。迩来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而照天腾渊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极之志,甄综百代之怀,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语也。”(注: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光绪三十三年南陵徐氏刻怀豳杂俎本。)又沈增植《qiáng彊村校词图序》:“及我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钱塘厉氏,先后以博奥淡雅之才,舒窈之思,倚于声以恢其坛宇。浙派流风,泱泱大矣。其后乃有毗陵派起……。”(注:龙榆生辑录《彊村校词图题咏》,朱孝臧:《彊村丛书附遗书》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8728页。)但尽管人们对清词发展的脉络能够勾勒得非常清晰,可是涉及清词复兴的最初机缘,却往往语焉不详。1991年,孙康宜教授出版了有关陈子龙和柳如是诗词情缘的英文论著,指出在晚明南中胜流与旧院歌妓交往的背景中,陈、柳的唱酬影响了清词的发展方向,是明清之际词坛变革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注:孙康宜教授的英文著作题为:The Late—Ming Poet Ch'en T zu—Lung: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李奭学中译题为《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词本是在“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素手,按拍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注:欧阳炯:《花间集序》。)的环境背景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先天地和歌妓有着密切的关系。晚唐五代的不少文学家倾全力于小词创作,先后开创了西蜀和南唐两个繁荣的局面,其中尤以西蜀花间词人更有代表性。我们曾从爱情意识的苏醒和高扬、对女性的尊重、真挚的感情等三个方面说明了《花间集》的价值(注: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3 章《艳词的发展和新变》。),现在看来,这其实也就是《花间集》能够成为后世典范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明清之际的词学建设和这一传统又并不完全一样。在花间词中,全部是男性作家的代言之体,女性的声音只是曲折地传递出来;而在明清之际,名士与歌妓之间已经成为互动的关系。晚唐五代的歌妓只是以体态情愫参与词学建构,而明清之际则在此之外,直接贡献了带有美学追求的作品。陈子龙和柳如是有不少同调同题之作,如[浣溪沙](《五更》),陈:“半枕轻寒泪暗流,愁时如梦梦时愁。角声初到小红楼。风动残灯摇绣幕,花笼微月淡帘钩。陡然旧恨上心头。”柳:“金猊春守帘儿暗,一点旧魂飞不起(返?)。几分影梦难飘断。醒时恼见小红楼,朦胧更怕青青岸。薇风涨满花阶院。”又[踏莎行](《寄书》),陈:“无限心苗,莺笺半截。写成亲衬胸前折。临行简点泪痕多,重题小字三声咽。两地魂销,一分难说。也须暗里思清切。归来认取断肠人,开缄应见红文灭。”柳:“花痕月片,愁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水(里?)。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眎(味?)。”(注:转引自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2—243页。)如果说,诸作都能以其情真意切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这一成就应是两个人共同的成果。值得提出的是,陈子龙论词有着明确的追溯晚唐五代的意识,在《幽兰草序》中,他说:“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究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斯为最盛也。”不废北宋,是其晚年进境,而紧紧扣住晚唐五代,则说明他复兴词学的明显动机和做法。
在词史的发展中,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人前后开疆拓宇,引进豪放疏朗的格调,但婉约之风一直是主流。而且,“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在某种意义上,词更善于表现人们心中的隐约幽微的感情。这是词的最初传统,也是词的基本特质。因此,在明清之际,面对波诡云谲的风云变幻,不少人仍对艳词情有独钟。如顺治末年,邹祗谟和王士祯在扬州同操选政,以艳词为主,汇集明末清初作品若干篇,成《倚声初集》二十卷,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个部分。其中小令十卷,录词一千一百十六首;中调四卷,录词三百六十四首;长调六卷,录词四百三十四首。合计选词四百六十余家,一千九百十四首。如此繁富的卷帙,据选者云,是要恢复《花间》传统,但易代之际,人们的心理显然不会那么简单。元好问当金亡后,编《中州集》,以保存故国文献,应该是类似活动的一个注脚。另外,对于邹祗谟和王士祯这样的独具手眼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他们将这些作品汇集在一起,也未始没有文学批评的考虑。文风的变化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在人们心目中,传统题材原已构成某种定势,即使非常细微的变革所引起的结果也往往不可预期。如果说当年秦观“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使得艳词呈现出另一种风貌的话,那么,到了明清之际,这一现象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已与前代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艳词发展的新气象,也是词史发展的新动向。明清之际的词坛在青楼文化的背景中,重又注入了新鲜的生命力。它是《花间》传统的复归,更是《花间》传统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认识陈子龙和柳如是、龚鼎孳和顾媚的诗词情缘,对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当能看得更为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