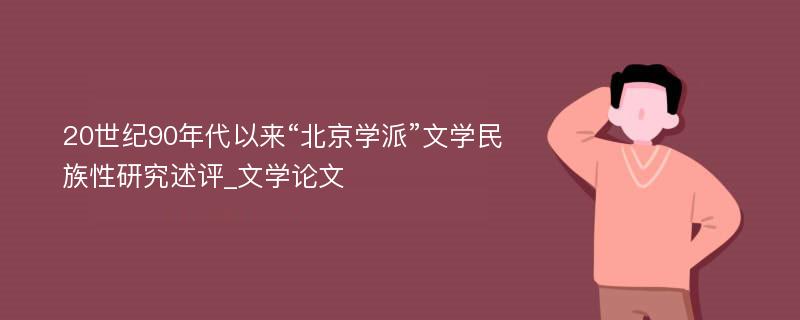
90年代以来“京派”文学民族性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民族性论文,述评论文,年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4)01-0075-06
京派文学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只劲旅,但是建国后对它的研究却是从80年代后期才开始勃兴的。80年代,曾是京派支柱作家之一的沈从文出版了他的学术性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从记忆中唤回有关沈从文、进而有关当年京派文学的一些陈年往事。进入90年代,随着沈从文、周作人、废名、朱光潜、萧乾等作家的作品、论著结集再版,学术界也开始发表或出版关于京派文学的专论或专著。杨义、查振科、韩立群、许道明、高恒文等学人都曾把京派文学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虽然这些研究论著选取的角度不同,观点有异,但是关于京派文学的特色和风格,研究者们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如杨义所言,“(京派)发现了在自然怀抱和宗法制维系中人的心境的和谐,‘一念之本初’的童心未泯,原始人性在与神性的交融中洋溢着顺乎自然的恒定感”,“以质朴而雅致、绵密而潇洒的笔触,点画出古老的中国城乡儿女、尤其是带原始静穆感的乡村灵魂的神采,神与物游,物我无间,创造出具有东方情调的和谐浑融的抒情境界”[1](P364~365)。简言之,对这一流派的文学风格,研究者多是从中国古典传统美学的视角着眼加以分析的。90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京派文学的美学风格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虽然京派文人身处学院之中,兼容中西方文学思想,并对现代思潮持开放、包容态度,但他们最终的精神指归都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杨义更是专门对比研究京、海两派,将京派作为古中国文化心态的代表,而将海派作为受现代风潮影响的近现代中国文化心态的缩影。[1]所以,90年代以来关于京派文学的研究论文、论著虽比80年代更丰富、更系统,但仍多是从传统文化的视角介入的。
一、地域文化:植根的母体
作家,无论是大家、名家还是普通作家,其创作特色和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地域的社会环境、文化内涵和文化氛围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京派作家里,说到地域文化的影响,研究者自然会想到沈从文和废名。同时,又由于对这两位著名作家的研究,黄梅文化、湘西文化、吴楚文化被一次次提到。向柏松的《沈从文与巫风》[2]是一篇专门讨论楚地巫风对沈从文创作影响的文章,作者认为,“沈从文迷恋的是与巫风共存的具有原始美德的社会环境”,他提倡“鬼神崇拜情绪,执著、庄严和痴迷”,并且“特别赞赏祭神活动的艺术气质及浪漫精神”。文章还对小说《神巫之爱》等进行了分析,提出神巫对爱的追求正是“作者艺术追求的象征”,“神巫所追求的只不过是浪漫的宗教情绪所笼罩的美丽的幻影罢了”,但是“神巫在追求幻影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了疯子般的迷狂和执著”,而这正是“抒发了作者对人生艺术化的迷恋”。向柏松对楚地巫风之于沈从文创作的影响,理解得颇为到位,既分析了沈从文对其所处地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作家对巫鬼文化的艺术精神心领神会后移植于自己的创作而获得的奇异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移植增强了小说的气氛,表现了人物命运的不可知性。彭晓勇的《民族生命元气的执着追求——沈从文小说论》[3]一文虽然不是从严格意义的湘西文化、吴楚文化着眼,但作者却明显地从“地域”角度楔入,以带有地域特色、地域内涵的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为视角,分析沈从文笔下“找不到民族自身位置”的湘西人的心灵世界,和作为现代文明的参照物的湘西“通体透溢出的一种生命的元气”。作者认为,沈从文“总是以一个湘西‘乡下人’的心理去发现、控诉推进文明的暴力行为怎样伤害着一个民族的心灵”,而“当这种对暴力的批判与湘西少数民族被武力‘同化’的遭遇相联系时,它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同情,而表现出对民族压迫的愤怒,寄寓着民族平等的要求”[3]。同时,作家着力描写了隐藏在这个少数民族人民体内的生命强力和生命元气,“这种生命强力与民族责任感的交融,就使其人性内容有了深刻的意蕴。这种充溢生命力的人生是美的、健康的人生”。彭晓勇认为沈从文是以湘西苗族作家的立场进行创作的,所以他的创作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抗争色彩。这种观点确实是看到了沈从文作为从湘西走出的作家自身的独特性,但是说法有些过分拘泥于湘西历史上少数民族曾有的心理感受。沈从文有着苗族血缘,但他从未以“苗族作家”自居,他在作品中所对抗的,是“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的伤害和异化,他似乎更愿意在塑造完美人性方面下功夫。另外,李同德《沈从文文学批评风格及其成因浅探》[4]一文指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风格受楚文化影响很深,“巫文化氛围,使楚人部分地摆脱了宗法制的严重束缚,表现一种自发的自由精神,用直观想像的方式去把握周围世界,因此楚地的巫风带有较多的艺术气质,对作家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楚文化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小说创作体现出的是其对沈从文的构思背景的直接影响;而正如李文所言,文学批评风格体现出的则是其对作家思维方式的浸染。
90年代以来关于废名与地域文化影响的研究,主要有冯健男《废名与家乡的文学因缘》[5]一文。研究者从自然环境、人事习俗、佛教和禅宗、民间文艺等方面,分析说明了家乡的传统风土人情、文化气息对废名创作的影响。自幼在黄梅长大的冯健男很了解黄梅文化特色,“首先,在佛教和哲学方面,黄梅占有独特的地位。——禅宗初祖是印度人达摩,二祖至六祖都是中国人。五祖弘忍为黄梅人,六祖慧能在黄梅接受五祖所传衣钵,四祖道信亦可能在黄梅传佛法于五祖,是以黄梅有四祖寺、五祖寺,黄梅人自古至今,引以为荣。”“其次,黄梅与匡庐一江之隔,据传说和县志所载,诗人陶潜、慧远、李白、裴度、苏轼等曾到过黄梅,留有诗作;而鲍照则居于此,死于此,葬于此。”“再次,黄梅是山歌、渔歌和采茶戏之乡。”冯健男认为废名自幼受佛学、禅宗影响很深,在其名作《桥》里,更是“形成了一种空气,弥漫于其中的是诗的意境与禅的意趣的结合,清凉的人生与静默的哲学的交融。”而且,“有意味的是,在黄梅,艺术总是带有禅味。哪怕是滑稽和幽默,也往往看破了尘世,点穿了戏中戏。”[5]在佛教和哲学方面,黄梅占有特殊地位,五祖和六祖的故事至今在那里都家喻户晓。废名小说意境与禅趣相结合,与黄梅禅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此外,黄梅的民间艺术也启发了废名,如木头戏、灯会等,都被他引入小说创作中,展现了独特的地方特色。冯健男先生是废名的晚辈亲属,对废名、对黄梅文化的双重熟稔和了解,使他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也更为贴切,令人信服。
杨义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中开列专章比较研究废名与沈从文。他指出,“按诸历史地理,废名小说所描写的湖北黄梅县和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沅水流域,皆属楚地,不过沅水流域位居蛮荒的湘楚,黄梅位居风气略为开通的吴楚,有‘儿童尽楚语吴歌’之说。因而,他们的作品尽管都有南方的清柔之美,但沈从文笔下更多奇特神秘的色彩,废名笔下更多平易和谐色彩。”[1](P334)这种比较颇有新意。两位作家虽都出身楚地,但风格颇为不同。正如沈从文在《沫沫集论冯文炳》中的自评,“《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1](P338),杨义形容沈从文的小说“有棱有角,有血性,有哲学,擒纵随心,驱遣自如”[1](P338),的确是看到了沈从文与废名的不同以及沈的优势所在。用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杨义点出了两位京派重镇作家创作风格上的差异,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地域文化渊源。他也将同样的比较方法用于分析京海两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指出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不同及其分别对京派、海派的影响,这方面本文将在下面详细谈到。
二、中国古典文化:血脉的传承
几乎没有一个“京派”研究者在其研究论著中不谈及中国古典文化的。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化渗入到了历代文人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现代作家多数深谙中西方两种文化,既精通国学又对西学有过系统的学习。京派作家也是如此。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朱光潜留学英法数年;沈从文虽无留学经历,但他曾在大学任教,与许多著名学者都有交往;废名毕业于北大外文系;林徽因则在美国宾州大学选修建筑系课程,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他们在对西方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之后,都重新选择了亲近传统文化。可以说,长期以来,对京派文学的研究,立足于此的最多。
杨义曾著文论述了道家文化对京派文学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京派作家在动荡时世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些隐逸味道,徘徊于《庄子》所谓的‘游方之外者’和‘游方之内者’之间,体现了某种淡泊宁静、渐近自然的人生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流派的作家大多喜欢陶渊明,这与他们某种潜在的道家情趣不无关系”[1](P62)。接着论述了周作人、朱光潜等作家对淘渊明的推崇和理解。其观点的独特之处在于,看到了京派作家是通过陶渊明而从诗学趣味的角度间接地接近道家文化的。同时,杨义又认识到了屈、庄对沈从文的影响,“在沈从文的文字中往往喜欢屈、庄并提,这说明他有意在屈原式的幽丽沉郁中,调剂以庄子的自然超逸”[1](P629)。杨义把沈从文作品中特有的原始美与道家的尚古思想联系起来,这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道家文化是从原始的自然和原始的人性中生发而来的。庄子和道家哲学很强调“自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的理想人格(“至人”、“真人”、“神人”)不是知识的人、事功的人、伦理的人,而是与天地宇宙相同一的自然的人。所以,沈从文作品中渗透出的对原始淳朴民风的依恋确与道家思想的浸润有关。
90年代,关于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研究,也主要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角度入手。主要的论文有温儒敏《沈从文怎样写鉴赏性评论》、陈剑文《沈从文文学评论的印象主义特色》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沈从文文学批评继承了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温儒敏以下的见解应该说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沈从文的风格批评显然继承和借鉴了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当他要把捉和传达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作家的整体风格时,所依赖的主要是直观感性的印象并常用鲜活的印象或色调,去造成带通感性质的评析,重在唤发读者的体味与感知”[6]。
刘洪涛的《〈边城〉与牧歌情调》[7]是近年对《边城》的研究论文中较有分量的一篇。作者认为,《边城》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儒道相济所构成的人物性格上。论文指出,“边城人”的诗性品格有着明显的道家风范,“如渡船老人的迂阔,顺顺的放达和洒脱,二老的浪漫等,都承继了道家思想的衣钵”。同时,论文结合作家沈从文自身的经历,分析了儒家思想在《边城》美学特色上的体现,从而得出结论:“《边城》处理的是爱情,不是情欲,一切深合传统道德,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7]。研究者看到了《边城》所体现的古风、爱情、意象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暗合,不过,这也仅仅是“暗合”而已。沈从文小说有意宣扬的是一种古朴、洒脱、率性、勇敢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而不是合乎传统规范、儒家元典的人生轨迹。
90年代以来对废名的研究集中于禅宗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作家很多,但像废名一样真正研究掸宗、参禅悟道的却很少。废名对禅宗的理解,深入体现在其创作中。王泽龙在《废名的诗与禅》[8]一文中分析了废名诗歌的风格,指出“在具有现代主义诗风的诗人中,废名诗歌的宇宙观不像其他诗人主要来源于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他更多得益于东方古老哲学与禅宗及美学。尽管他说他曾读过波特莱尔,推崇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但真正化入他诗中的精髓还是东方文化中的佛道释精义,中国的诗禅、画禅的传统以及他所崇尚的晚唐诗人李商隐与温庭筠的诗词意境与六朝文章风致。”其他研究者的研究也多从类似的角度入手,如胡绍华《废名的小说与禅道投影》[9],不仅分析了废名小说对禅道心理的借鉴,而且指出,受禅道思维的启发,其创作采用了一种包容着情感体验和理性判断的“悟性思维”。禅的修养使废名以虚静的心灵体悟自然,于活泼的万象天机之中追求一念净心。正如《桥》所展现的小林、琴子、细竹的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的世界,河边浣衣,田间散步,雨中打伞,日里观花——这种“静观”的心态是禅宗的追求,也是艺术和审美的起点,它在很大程度上玉成了废名的文学创作。
此外,徐文谋《废名小说的意境结构分析》[10]等文还对废名作品所营造的意境、涉及的意象作了研究,较一致的观点是,废名的作品具有“诗体化”特征,他有意营造一个充满古典诗情画意之美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世界,以静写动,以乐写哀,独具情趣。
90年代对废名作品风格的研究,视角比较集中、狭窄,这与废名自身的创作风格有关,但也与研究者的思路不够开阔有关。废名创作风格颇为独特,有平淡优美的一面,也有晦涩深奥的一面,这都有待研究者选取新的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在这方面,吴晓东的《背着“语言的筏子”——废名小说〈桥〉的诗学解读》[11]一文颇值得重视。研究者认为,“《桥》之所以晦涩恐怕与废名在小说中试图处理的是意念和心象有更直接的关系”。吴文指出,废名采用了大量濡染着作家自己个人化色彩的意念,其目的是为了使古典词语在新的意指中复活。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使自己私人化的心象与更多的读者理解的公共性相沟通的途径”。吴文在试图破解长期以来废名小说难以解读的原因,研究者提到的“意念的个人性与经验的公共性的关系问题”恰恰是废名小说中存在的要害性难题,这一崭新的切入视角使废名研究迈出了新的一步。
9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专著胜于论文,钱理群、舒芜等学者都出版了系统研究周作人思想、人格及创作风格的专著。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评述。就论文而言,我认为,顾琅川的《周作人与公安三袁》[12]一文是90年代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论文中较有分量的一篇。有关周作人受公安派、竟陵派影响的研究并不少见,顾文的可贵之处在于,详细分析了周作人与公安派的异同。他指出,周作人偏爱公安三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周作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与“明季”有着相似之处;二是他的中庸主义的处世哲学;三是他们之间心理结构的相通。而其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审美情趣上——“三袁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整一的审美情趣”,而周作人追求的“则是一种杂多归一、变动不居的审美情趣”;与社会人生的不同关系上——“公安三袁‘自我’的特征是其封闭性。在他们看来,创作的源泉不在其他,而在诗人自身的心灵”,而“周作人的‘自我’则以开放为特征。‘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此外,“公安派对礼法的抗议主要表现在对世俗世情的追求及其合理性的肯定,那么周作人着重表现为对于正常的人生情欲横遭压制的声讨,闪耀着犀利的批判锋芒”。通过两方面的深入分析,顾文不仅对周作人为文风格形成的渊源作了详尽阐述,而且也指出了周作人在为人上走入悲剧道路的原因。另外,丁亚平的《自己的园地:无声潜思与独立探询——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个性》分析了周作人印象感悟式的批评方式。郑世平《周作人后期思想管窥》指出,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并且这一历程也成为其命运三部曲。
三、两种文明:比较中的探寻
为了建立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理想和人生理想,京派作家在描绘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的乡村图景的同时,也写了一定数量的城市小说。他们对于乡村的依恋和对于城市的厌倦,通过对比强烈地凸现出来。研究京派文学的民族性特色,就不能绕过对京派作家创作的城市小说的研究。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城市小说体现了京派文学民族性的局限。正如刘淑玲的《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13]一文论题所示:京派作家的城市批判,是在他们建造的乡村“梦影”中进行的,或者说这部分小说,是为了成全他们关于乡村的“梦影”而创作的。刘淑玲指出,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它只是“以文学的方式在认识城市的同时,完成了一种文化描述,小说中的无数主人公们强化了他们的乡村情结,也了结了他们的城市梦想。这里,城市不是以‘题材’而是以‘意象’的形式呈现。他们无意于具体的城市生活特色,只关注这种生活中的人性变异,进而展示其生存困境”。京派作家对城市的观照的确缺少了动态的历史审视,而他们所描写的乡村,也并非写实的中国乡村,而是理想化了的、牧歌式的田园图景。城市作为乡村的陪衬物出现,已经失去了真正的、作为“城市意象”本身的意义,而只是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的符号。现代文明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阶段。它改变了落后的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表现出科学的求实精神。它虽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危机,却表现了历史的进步性和蓬勃生机。京派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片面认识和对传统文化的主观想像就造成了京派文学民族性的局限:文学的民族性应是动态的民族历史主义,而不应是静态的保守主义。这类研究论文还有张鸿声《与乡村对照中的都市——论京派都市题材小说》、丁帆《静态传统文化与动态现代文化之冲突》、秦志希《关于都市文化批判与乡村牧歌的质疑》等,它们一致认为,京派作家对乡村、城市这两种文明,还没有上升到一种现代理性去认识。乡村和城市,在京派作家营造的小说世界里,不是一种真实的客观性存在,而是主观性叙事。乡村人生是传统文化的价值隐喻,是现代人孤独、焦虑的灵魂的栖息之所,也是激发他们不断前进的精神源泉。这样,乡村文明/传统文化就成为京派作家批判现代文明的尺度,现代文明是为了衬托乡村文明/传统文化而存在。作家们并没有客观、全面地诠释这两种文明的优劣,而是借着双方的对比,苦心孤诣地营建理想的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精神没能较好地吸收现代文明的精髓,所以,对城市和乡村的片面理解和主观叙事使京派文学的民族性具有了明显的局限性。
这里必须提到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14]一文。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沈从文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优美健全,刘文却反弹琵琶,标新立异地指出,沈从文作品表现出的不是人性的优美健全,而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刘永泰认为,沈从文不具备深远的历史眼光,而是“简单地将社会发展和人性发展对立起来,将‘人性的丧失净尽’归因于日益复杂的社会”。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个体人性的扭曲变形,但人的社会性是人实现自己使其成为现实的人和有个性的个人的根据和必然形式,社会无论如何都是个体人性生成、发展、完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湘西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性的诸多要素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现代文明中人性的某些要素片面扩张造成了个体人性的扭曲变形,但作为类的人的人性却因此而发展丰富起来,对象化为更合理的社会结构,为个体人性的完善准备了更好的条件”。研究者独具只眼地看到了沈从文对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方面的欠缺。沈从文从湘西边城走出,在经过艰难的奋斗成为都市人后,就开始从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寻找乡村文明的遗留,以作为个人文化寻求和民族精神再造之源泉。他对乡村的描写本土色彩极强,具有独特个性。但他贫于“后视”,无法客观理解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因此造成了他思想和创作上的局限。
杨义则是直接从京海两派的对比,即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比的角度着眼展开研究的。这种对比使研究对象的特点鲜明显现,“在京派中坚作家笔下,我们领悟到大陆性原始人生的和谐;在上海现代派作家笔下,我们感受到沿海性异化人生的裂变,前者静谧得有若群山间一泓深潭,后者喧闹得有若海岸边一束飞沫。前者如竹篁清溪,翠色可餐;后者如霓虹灯广告牌,斑驳眩目。京派中坚作家是兼融北方的旷远、南方的明秀、西方的深邃的,上海现代派则撷取东方的活跃和南方的灵巧,——一方是山水的灵感,一方是性色的肉感;一方是生命的信仰,一方是自我的危机;一方是处女地的气息,一方是摩托车的速率;一方是渺若云烟的美神的梦,一方是光怪陆离的酒神的梦。它们展示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生方式,不同的文化心态。”诸如此类对比性的语言用得十分贴切而巧妙,在与现代化大都市文学的比较中,突出了京派作家的文学理想和文化风格,即民族化特色。可以说,想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两大流派——京派和海派——的最明显的特点,看杨义有关京海两派的比较研究是较为合适的。
综观90年代以来有关京派文学民族性的研究,涵盖的方面比较多,从内容到形式,从小说、诗歌创作到文学批评,从流派对比到作家比较等各方面都有所涉及,但是有一点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今天探讨文学的民族性,必须以“现代化”、“全球化”为背景。一种文学要在“现代化”、“全球化”境遇中健康发展,应该着眼于本土文化独特个性的当下建构。优秀的文学是代表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和心理取向的、具有合理性、现代性和前瞻性的文学。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方面,它不仅应将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参照系,而且还应把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研究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品格,以现代的哲学观念和美学观念来关照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时代性和超时代性,寻找文学在中国传统中永恒的、而又在时代进程中不断更新的意味,揭示它内在的民族传统和集体无意识积淀,发掘它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的崭新的美学内涵。对于京派文学民族性的研究正应如此,将其“民族性”放入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背景中,发现新的角度,进行宏观意义上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
标签:文学论文; 沈从文论文; 边城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读书论文; 周作人论文; 人性论文; 废名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