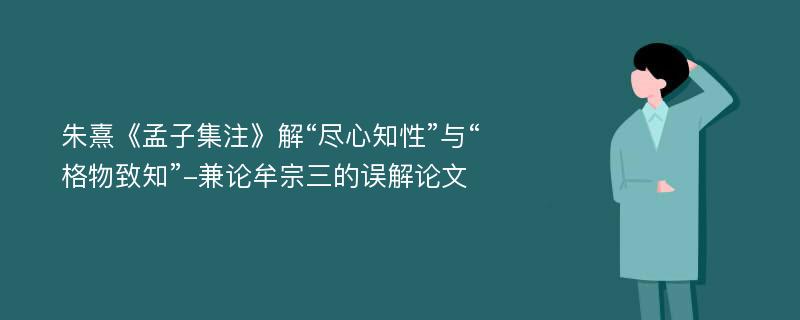
朱熹 《孟子集注 》解 “尽心知性 ”与 “格物致知 ”
——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乐爱国
[提要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关键词 ]朱熹;尽心知性;格物致知;牟宗三;主客二分;德性之知;心之为物
朱熹在《大学章句》作了“格物致知补传”,又担心受到误解,而在《大学或问》中做了进一步解释。其实,朱熹《孟子集注》对“尽心知性”的诠释,也可看作是“格物致知”的重要内涵。现代学者对于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解,多据“补传”所谓“即物而穷其理”而望文生义为现代主客二分意义上的认知论,或牟宗三所谓“泛认知主义”。至于朱熹《孟子集注》对“尽心知性”的诠释,则往往被看作是朱熹以《大学》为中心的对《孟子》的解读,是“认知地尽”“不合孟子原意”[1](P.403)。笔者以为,理解朱熹的“格物致知”,不仅要以《大学章句》“补传”为依据,还应当参照朱熹的其他文本,尤其要参照《孟子集注》;只有通过《大学章句》与《孟子集注》的相互参照,才能既把握《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之要义,又能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有正确的认识。
一 、“格物致知 ”的认知论解读及其问题
《大学章句》把“格物”界定为“即物而穷其理”,把“致知”界定为“致吾之知”,认为“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2](P.7)。在这里,“格物”之“物”是“天下之物”。朱熹《大学或问》对此作了解释:“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3](P.526-527)也就是说,所谓“天下之物”,首先是“心之为物”,然后依次向外:“身之所具”“身之所接”“外而至于人”“远而至于物”。这里所谓“天下之物”,分为“心之为物”和“心外之物”,但实际上是以心之为物为中心不断扩展的天下之物。事实上,朱熹《大学或问》的解释,就是为了避免“不求诸心,而求诸迹,不求之内,而求之外”,把“格物”只是理解为格心外之物。他还说:“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然或不知此心之灵,而无以存之,则昏昧杂扰,而无以穷众理之妙。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则偏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此其理势之相须,盖亦有必然者。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3](P.528)认为格心之为物是“即物而穷其理”之根本。
关于“致知”之“知”,朱熹称之为“吾之知”。他还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3](P.7)显然,“致知”是人根据自己心中的“已知之理”,“即物而穷其理”,进而将“吾之知”推至乎其极。《大学或问》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昔者圣人……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3](P.527)由此可见,朱熹所谓“已知之理”是“德性之知”,“致知”是“德性之知”的推而究之,不是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和知识。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虽然讲格天下之物,既格心之为物又格心外之物,但对格心外之物,抱以谨慎态度。首先,格心外之物,“须当察之于心”。他说:“天下之理,偪塞满前,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非物也,若之何而穷之哉!须当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后于物之所在从而察之,则不至于泛滥矣。”[4](P.400)可见,格物,首先是格心之为物,并根据此心之理而格心外之物。其次,格心外之物,须要切己:“若只泛穷天下万物之理,不务切己,即是《遗书》所谓‘游骑无所归’矣。”[4](P.400)朱熹还说:“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后渐渐推去,这便是能格物。”[4](P.248)再次,格心外之物应当与格心之为物互相发。据《朱子语类》载,问“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曰:“前既说当察物理,不可专在性情,此又言莫若得之于身为尤切,皆是互相发处。”[4](P.401)由此可见,朱熹的“格物”主要是格心之为物,而格心外之物必须以格心之为物为基础,格心外之物必须统一于格心之为物。
课程每个教学模块的载体都是日常生活中熟悉、并且十分关心的食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通用性。作为教学情境中载体的分析检验工作,覆盖了食品企业生产中的典型岗位。因此,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但能够掌握关键岗位技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还为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将“功能性食品”课程进行重组。
明代王阳明把朱熹“格物”中的格心外之物与格心之为物分割开来,从而把朱熹的“格物”仅限于或误读为格心外之物,因而有“庭前格竹”之说。明末的科学家也把朱熹的“格物”仅限定于格心外之物,而与西方科学接轨,对中国明清时期的科学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胡适推崇朱熹的“格物”对于现代科学的价值:“程氏兄弟及朱熹给‘格物’一语的解释十分接近归纳方法:即从寻求事物的理开始,旨在借着综合而得最后的启迪。”[5](P.8)后来又认为,朱熹言“即物而穷其理”“这便是归纳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6](P.366)显然,胡适也属于误读。
应当说,在朱熹那里,《孟子》“知性”只是知得人的心性,《大学》“格物”“物格”则是要格得“天下之物”之理,并非只是格得心之为物之理,而且还要格得心外之物之理,就这一意义上说,“知性”不完全等同于“格物”、“物格”;但是,格心外之物之理,是以格心之为物之理为中心,是以“知性”为中心,就这一意义上说,不仅《孟子》“知性”即是《大学》“格物”、“物格”,而且《大学》“格物”、“物格”也即是《孟子》“知性”。最为关键的是,朱熹所谓“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中的“知”,不应当理解为主客二分的主体对客体的“知”。
牟宗三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他说:“盖朱子所谓‘物’本极广泛,一切事事物物皆包在内。不徒外物是物,即吾人身心上所发之事亦是物。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等即是心上所发之事,故亦是物。‘穷,是穷在物之理’。就心上所发之事以穷其理,亦是‘穷在物之理’。此是泛认知主义,把一切平置而为认知之所对。”[1](P.324)其结果是“只剩下心知之明与在物之理间之摄取关系,而真正的道德主体即泯失”[1](P.354)。
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答张敬夫问目》引述《孟子》“尽心知性”,并指出:“心体廓然,初无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尽。人能克己之私,以穷天理,至于一旦脱然,私意剥落,则廓然之体无复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远近精粗,随所扩充,无不通达。性之所以为性,天之所以为天,盖不离此而一以贯之,无次序之可言矣。”[11](P.1397-1398)这里把“尽心知性”解释为“穷天理”。次年,朱熹作《尽心说》,认为《孟子》“尽心知性”是指“人能尽其心,则是知其性”,还说:“人之本心,其体廓然,亦无限量,惟其梏于形器之私,滞于闻见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尽。人能即事即物,穷究其理,至于一日会贯通彻而无所遗焉,则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而吾之所以为性与天之所以为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贯之矣。”[11](P.3273)这里把“尽心知性”解释为“即事即物穷究其理”。同年,朱熹又作《胡子知言疑义》,其中说道:“孟子尽心之意,正谓私意脱落,众理贯通,尽得此心无尽之体,而自其扩充,则可以即事即物,而无不尽其全体之用焉尔。……《大学》之序言之,则尽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11](P.3555)这里把“尽心知性”与《大学》“致知在格物”联系在一起。
骆塞夫先生《向阳与背阴》由树讲到人,背阴者生活艰辛,然,不甘平庸者以百倍于他人的努力,最终成材、成才;向阳者生活条件好,若借此机会养尊处优不肯努力,最终也难成栋梁之才。揭示的就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的辩证关系。
显然,胡适和冯友兰对于“格物”的诠释根本不合乎朱熹的本意。牟宗三认为,在朱熹那里,就心上所发之事以穷其理,与就外物以穷其理,“一切平置而为认知之所对”。事实上,朱熹强调“格物”以格心之为物为主,格心外之物必须统一于格心之为物,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所以,格心之为物与格心外之物,并不是“一切平置而为认知之所对”。牟宗三又认为,在朱熹的“格物”中,“真正的道德主体即泯失”。事实上,朱熹的“格物”既是认知主体对于物的认知,又是道德主体自我认知的道德修养过程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过程。因此,牟宗三把朱熹的“格物致知”看作是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泛认知主义,这与朱熹的本意相距甚远。
二 、《孟子集注 》对 “尽心知性 ”的解读
《孟子·尽心》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汉代的赵歧注曰:“性有仁义礼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为正,人能尽极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知其性则知天道之贵善者也。”[9](P.2764)以为能尽其心,则知其性。程颐结合《易传》说:“尽其心者,我自尽其心;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实,只能穷理,便尽性至命也。”[10](P.292)
现代所谓认知,是人作为认知主体对于客观对象的认知。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二分,人的知识来源于客体。与此不同,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人对于以心之为物为中心的天下之物的认知,虽然包含了对心外之物的认知,但还是要统一到对心之为物的认知。而且,“即物而穷其理”之“理”,既是物之理又是心之理而统一为性理。朱熹在比较“智”与“知”之不同时说:“‘智’字自与知识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知识便是察识得这个物事好恶。”[4](P.2421-2422)也就是说,知识不仅要知得事物,还要知得该事物在人的心目中之好坏。因此,人既是认知主体,又是认知客体,人的知识来源于自身所谓“吾之知”,“致知”是“致吾之知”,这就是“德性之知”。重要的是,现代知识与道德相互分离,而与之不同,朱熹通过“格物”而“致知”,以使“德性之知”至乎其极,既是认知过程,又是道德修养过程,知识与道德并非截然分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既是认知主体,又是道德主体,并且能够使道德主体的境界得以提升,正如每个人面对自己,认知自我的过程,也是道德修养提升自我的过程;谁也不会认为曾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仅仅只是主客二分的认知过程。
牟宗三特别不赞同朱熹对于《孟子》“尽心知性”的解读。他批评朱熹《孟子集注》所谓“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认为朱熹讲“尽心”是由于“知性”,是“因果颠倒,不合孟子原句之语意,而历来亦无如此之读解者,此所谓异解也”,还说:“‘知性’是格物穷理,由‘穷夫理而无不知’以明‘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是则‘尽心’之尽乃是认知地尽,此非孟子义。”[14](P.368)又说:“依孟子,‘尽心’之尽,是道德地尽,非认知地尽,是充分实现或体现之意,扩充之意,非格物穷理之意也。是则‘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句意是能充分实现或体现人之本心者便能明白人之性,犹言‘能尽其心者就知其性了’。‘知’是明白洞晓之意,非格物穷理之‘知’也。‘知’即在尽中知。……除朱子外,无作颠倒因果之异解者,亦无以格物穷理之知性说明心之尽者。朱子如此说‘尽心’,正是认知地尽,此显非孟子意。”[14](P.371)
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写成《孟子集注》,在诠释《孟子》“尽心知性”时指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2](P.356)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大学章句》完稿。
“穷理”一词,出于《易传》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郑玄注曰:“穷其义理,尽其人之情性,以至于命,吉凶所定。”[13](P.55)程颐以此与《孟子》“尽心知性”相对应。应当说,无论是朱熹《答张敬夫问目》将《孟子》“尽心知性”诠释为“穷天理”、《尽心说》诠释为“即事即物穷究其理”,还是朱熹将《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其中的“穷理”都是来自《易传》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1.2.4 妊娠结局随访 打电话对所有孕妇妊娠结局追踪随访或查阅本院电子病历,包括孕期超声筛查结果、妊娠结局、新生儿体检的外貌、结构、智力发育等。
显然,牟宗三对于朱熹解读《孟子》“尽心知性”的研判,除了不赞同朱熹所谓“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还把朱熹所谓“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解为“‘知性’是格物穷理,由‘穷夫理而无不知’以明‘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如前所述,朱熹讲“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主要是按照《大学》中“物格而后知至”的语言结构次序,对应于《孟子》“尽其心,则知其性”,并不意味着“知性”就是格物穷理,“尽心”就是“知至”。
对于《孟子》“尽心知性”的解读,朱熹从语言结构的次序上,强调“知性”在先,“尽心”在后,《朱子语类》中对此多有讨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细看。人能尽其心者,只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能尽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则知天矣。知性知天,则能尽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尽其心。‘物格而后知至。’”[4](P.1422)朱熹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的语言结构次序,应当是先知得性,后尽得心,正如《大学》所谓“物格而后知至”。他还认为,《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的语言结构,与所谓“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孟子原话:“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相似。由此可见,朱熹《胡子知言疑义》讲“《大学》之序言之,则尽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以及《孟子集注》讲“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其中所谓“以《大学》之序言之”,特别强调“序”,就是要按照《大学》中“物格而后知至”的语言结构次序,对应于《孟子》“尽其心,则知其性”,以“物格”对应于“知性”而为先,以“知至”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物格”诠释“知性”,用“知至”诠释“尽心”。
在朱熹那里,无论是对《孟子》“尽心知性”的解读还是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读,都是依据于《易传》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中的“知”都是“德性之知”,并不是主客二分的“见闻之知”或科学之知,所以,朱熹除了从语言结构的次序上讲“知性”“物格”在先,“尽心”“知至”在后,也偶尔以“物格”诠释“知性”、以“知至”诠释“尽心”。他在《大学或问》中说:“《孟子》之所谓知性者,物格也;尽心者,知至也。”[3](P.514)《朱子语类》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比如,朱熹说:“知性也,物格也;尽心者,知至也。‘物’字对‘性’字,‘知’字对‘心’字。”[4](P.1422)
当然,朱熹本人偶尔也有貌似以“物格”诠释“知性”、以“知至”诠释“尽心”的言论,后世有学者以此为据,解读朱熹对于《孟子》“尽心知性”的诠释。明代王夫之认为,朱熹《孟子集注》讲“知性而后能尽心”不及说“尽心然后能知性”为长,“若必要依《注》,亦只可云能察识吾性实有之理,则自能尽其心以穷天下之理;必不可以知性为格物也”[15](P.359)。显然,王夫之以为朱熹是以“物格”诠释“知性”。清代毛奇龄《四书改错》也认为,朱熹所谓“尽心则知至之谓”是以“尽心”之“尽”训“知至”之“知”。对此,戴大昌《驳四书改错》指出:“朱《注》云:‘性即心所具之理,……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故曰‘尽心即知至之谓’,并未以‘尽’训‘知’,毛氏何得訾其以尽心为知心乎。”[16](P.237)牟宗三则明确反对朱熹讲“尽心”是由于“知性”,而认为“历来亦无如此之读解者”,同样也不赞同把“知性”诠释为“物格”。
高校不同于一般的组织机构,其大部分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在课堂上或实验室围绕知识的学习、共享、传播、创新而展开。所以,高校内知识的活动过程,除了遵循隐性知识社会化、显性化、组合化、内部化这一运动规律外,还有其自身的组织与运动特征。
重要的是,朱熹与其门人在讨论《大学》“格物致知”时论及《孟子》“扩而充之”。据《朱子语类》载,任道弟问:“‘致知’章,前说穷理处云:‘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且经文‘物格,而后知至’,却是知至在后。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穷之’,则又在格物前。”曰:“知先自有。才要去理会,便是这些知萌露。……只是如今须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头万绪,无有些不知,无有毫发窒碍。孟子所谓:‘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扩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4](P.324)应当说,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所谓“致知”为“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是“知”的扩充,而孟子所谓“扩而充之”是“心”的扩充;朱熹以孟子的“扩而充之”解说《大学》的“致知”,可以表明“致知”之“知”即是“心”的“德性之知”,而不能误解为,在朱熹那里,孟子的“扩而充之”是主客二分的知识的扩充。由此亦可见得,无论是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还是《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其中的“知”,都不可能是主客二分的认知和知识。
三 、牟宗三对 《孟子集注 》的误解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四部,专门阐述朱熹思想。按照朱熹学术历程,先阐述朱熹三十七岁前,接着阐述“中和旧说”“中和新说”,然后是朱熹撰《仁说》,又有朱熹对《大学》的诠释,对《孟子》的诠释,对心性的讨论,对天地理气的讨论,等等。但事实上,朱熹的学术在“中和旧说”“中和新说”之后,经历了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先是接着“中和旧说”“中和新说”继续向内探究心性,然后以内为中心,逐渐向外。所以,朱熹在“中和新说”稍后,就先有《答张敬夫问目》《尽心说》《胡子知言疑义》对《孟子》以及心性的讨论,以至于撰《仁说》,然后才有对《大学》的诠释。问题是,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朱熹《答张敬夫问目》《尽心说》被安排在对《大学》的诠释之后,而在对《孟子》的诠释中加以阐述。牟宗三还认为,朱熹《答张敬夫问目》《尽心说》对于《孟子》“尽心知性”的诠释,“已涵《大学补传》之义,并自此即以格物穷理致知解孟子之尽心知性知天”,其中所谓“扩充”,“却是认知地扩充”。[1](P.396-398)按照牟宗三所言,在朱熹那里,《大学》“格物致知”的“知”如同现代主客二分的知识,同时,朱熹又以《大学》“格物致知”的“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中的“知”,使之也如同主客二分的认知,因而《孟子》“扩而充之”不是“心”的扩充,而是“认知地扩充”。然而,笔者则认为,在朱熹那里,先是《孟子》“尽心知性”中的“知”被诠释为“德性之知”,“扩而充之”是“德性之知”的扩充,然后才是《大学》“格物致知”,格天下之物;由于“天下之物”是以心之为物为中心的天下之物,格天下之物是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的格物,《大学》“格物致知”与《孟子》“尽心知性”,既有相同的一面,其中的“知”都不是主客二分的知识,而是“德性之知”,是“德性之知”的扩充,但又有不完全相同的一面,《孟子》“尽心知性”之“知”只是“知性”,而《大学》“格物致知”之“知”则不仅要知得心之为物,还要从心之为物为中心,推广到心外之物。当然,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虽然包括格心外之物,但都是“德性之知”的扩充,最终又都归属于“德性之知”。这就是所谓“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
一般认为,朱熹《大学章句》最初草定于淳熙初年(1174年前后)。[12](P.66)据推断,当时,《大学章句》“补传”亦基本完成。此外,朱熹还在《答江德功》中赞同程颐把“格物”解读为“格,至也,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并指出:“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者,形也。则者,理也。形者,所谓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无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则无以顺性命之正,而处事物之当,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极,则物之理有未穷,而吾之知亦未尽,故必至其极而后已。此所谓‘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也。”[11](P.2037-2038)这里已经把“格物”解读为“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当是朱熹所谓“即物而穷其理”的雏形。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在撰《答张敬夫问目》、《尽心说》之前所作《杂学辨·吕氏大学解》,对于《大学》“格物”是否包含格心外之物,已经抱谨慎态度,一方面认为“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另一方面又认为“格物”并非“直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11](P.3493)以至于无法确定《答张敬夫问目》《尽心说》在讲《孟子》“尽心知性”时所谓的“穷理”是否就是后来《大学章句》“补传”即天下之物的“穷理”。若是就先后而言,朱熹是先把《孟子》“尽心知性”诠释为“穷理”,尔后才有淳熙初年《大学章句》“补传”即天下之物的“穷理”。
除此之外,朱熹还用《孟子》所谓“扩而充之”解读“格物致知”之“致”。《孟子·公孙丑》载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对此,程颐说:“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而用之者,皆自弃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与不充,皆在我而已。”[11](P.321)如上所述,朱熹《答张敬夫问目》在解读《孟子》“尽心知性”时不仅讲“穷理”,而且讲“扩充”。朱熹《孟子集注》注“扩而充之”曰:“四端在我,随处发见。知皆即此推广,而充满其本然之量,则其日新又新,将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则四海虽远,亦吾度内,无难保者;不能充之,则虽事之至近而不能矣。”[2](P.240)还说:“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2](P.297)
所幸,江苏新华作为国企和党企并未从一时兴衰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而是当机立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巩固主营业务的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增强企业市场能力,让其印刷业务得以重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道德及修养之方”来阐述朱熹的“格物致知”是穷理;“致知”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他还说:“用此修养方法,果否能达到此目的,乃另一问题。”[7](P.920)冯友兰晚年说:“朱熹的这篇《补传》实际上分为两段。在‘豁然贯通焉’以前为前段,以后为后段。前段的要点是‘即物而穷理’,说的是增进知识,后段的要点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说的是提高精神境界。这本来是两回事,分开来说本来是可以的。朱熹全篇文章是把‘即物而穷理’作为‘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的方法,这就成为问题了。这就是把两回事混为一回事,把‘为学’和‘为道’混为一谈,这就讲不通了。”[8](P.178)显然,在冯友兰看来,朱熹“格物”所获得的知识与“精神境界”无关,是现代主客二分意义上的知识。
由于在朱熹那里,认知与道德则是不可分的,所以牟宗三认为朱熹的“尽心”之尽乃是认知地尽,其中的“认知”应当是与道德是不可分的,而不是与道德截然相分的现代所谓认知。从表面上看,与那种将道德与认知分离开来而只是强调道德优先相比,朱熹讲道德与认知不可分,其道德力量有所减杀,但是,朱熹强调认知对于道德的支撑,相较于将道德与认知分离开来讲没有支撑的“悬空”道德,实际上是增强了道德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朱熹那里,“尽心”之尽,不可能只是“认知地尽”,而应当是以认知为支撑的道德地尽;同样,“格物致知”也不可能只是认知论或泛认知主义,而应当是以认知为支撑的或者内涵认知的道德工夫论,可以引申出认知论,但不等于认知论。
对照组、乳腺良性肿瘤组、乳腺癌组血清IL-6、IL-8、IL-10及TNF-α水平均依次呈递增趋势,且乳腺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乳腺良性肿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与乳腺良性肿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1、1.34、0.57、1.05,均P>0.05)。
结语
笔者认为,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的“物”是“天下之物”,既不只是心之为物,也不只是心外之物,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心之为物与心外之物的并列相加,而是以心之为物为中心的既向外又向内而构成的整体。因此,“格物”既不只是格心之为物,即向内的“格心”,也不只是格心外之物,而是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的格天下之物。由这样的格物所获得的知识,并非现代主客二分的客观知识,而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把朱熹的“物”理解为心外之物,把“格物致知”理解为主客二分的认知,这是对于朱熹“格物致知”的误解。
在朱熹的“四书”中,《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同样重要,互为补充。朱熹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4](P.249)朱熹讲“先读《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大学》为中心,以《大学》去诠释《论语》《孟子》《中庸》。然而,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把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解为主客二分的认知,而与西方哲学接轨,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受到重视,其在朱熹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性被过度夸大。牟宗三说:“宋明儒之大宗实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中心,只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是故《大学》在伊川朱子之系统中,其比重比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主者为重,对于其系统有本质上之作用,而在其他则只是假托以寄意耳。”[17](P.20-21)在牟宗三看来,朱熹哲学以《大学》为中心,是以《大学》诠释《论语》《孟子》《中庸》。但事实上,在朱熹那里,《大学》只是“初学入德之门”[2](P.37)。朱熹说:“学须先以求放心为本。致知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格,正心是他去正,无忿懥等事。诚意是他自省悟,勿夹带虚伪,修身是他为之主,不使好恶有偏。”[4](P.1409)可见,在一定意义上,朱熹更为强调《孟子》的心性之学。
不可否认,在朱熹那里,《大学》“格物致知”与《孟子》“尽心知性”是不同的,但又有相同之处。牟宗三认为朱熹以《大学》为中心,所以不仅把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看作泛认知主义,而且进一步认为朱熹是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是“认知地尽”。然而笔者以为,朱熹以“四书”为中心,在朱熹那里,《大学》与《孟子》没有主次之分,只有读书的先后之分,《大学》“格物致知”与《孟子》“尽心知性”可以相互诠释,既可以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也可以《孟子》“尽心知性”诠释《大学》“格物致知”。以“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则“尽心知性”中的“尽”和“知”,是“格物致知”地“尽”和“知”,而不能是认知地“尽”和“知”,因为“格物致知”不只是主客二分的认知;以“尽心知性”诠释“格物致知”,则“格物致知”中的“知”是“尽心知性”地“知”,既是“即物而穷其理”,又是“尽心知性”。正如唐君毅所说:“朱子所说格物穷理之事,虽似为致知以求理于外,亦同时是尽心以知性于内。”[18](P.206)这就是以《孟子》“尽心知性”诠释《大学》“格物致知”,把格物穷理诠释为“尽心以知性于内”。
在进行同步电机零功率因数试验时,静止变频电源由于存在输出滤波器,因此,一般情况下只能够进行简单的电压/频率控制。矢量计算能力减弱,其有功分量和无功分量在纯正弦波输出模式下很难单独调节。因此,实现等效负载下同步电机零功率因数有一定困难,强行实现,需要对电源及其输出变压器特殊设计,并大幅度增加逆变器以及输出铁磁元件输出功率,使静止逆变器(方案)失去原有相当的成本优势。
重要的是,无论是《孟子》“尽心知性”还是《大学》“格物致知”,其中的“知”都不能是主客二分的认知和知识,而是与之不同的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避免把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误解为泛认知主义,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误解为“认知地尽”。
2.2.3 我国农村医疗救助资金总量不足,不能完全解决受助群众的困难。由于我国农村地区需要救助的人群比较多,而我国农村医疗救助资金总量不足,所以往往只有患大病的困难群众才能享受医疗救助,其他困难群众则得不到救助,受助群体范围较小。而且救助资金最高限额较低,对患大病的农民家庭来说是杯水车薪。
参考文献 :
[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宋)朱熹.四书或问[A]//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4](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胡适.先秦名学史[A]//胡适全集(第5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6]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A]//胡适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汉)赵歧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A]//(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A]//二程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A]//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2]乐爱国.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0.
[13](宋)朱熹.郑氏周易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
[15](明)王夫之.四书笺解[A]//船山全书(第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1.
[16](清)戴大昌.驳四书改错(卷十六)[A]//续修四库全书(169·经部·四书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7]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
[18]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1—0070—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乐爱国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朱子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收稿日期 2018-11-10
责任编辑尹邦志
标签:朱熹论文; 尽心知性论文; 格物致知论文; 牟宗三论文; 主客二分论文; 德性之知论文; 心之为物论文; 厦门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