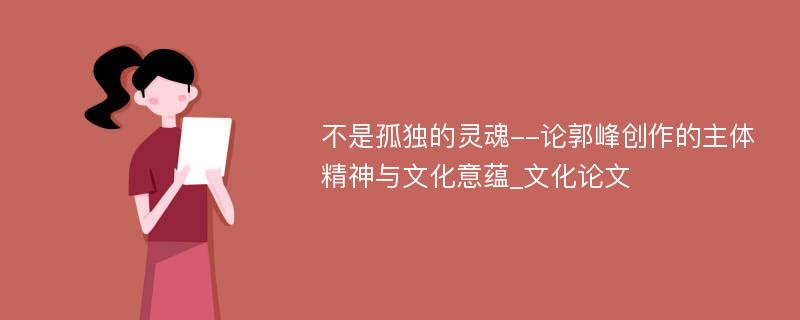
并不孤独的灵魂——论郭枫创作的主体精神与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主体论文,灵魂论文,孤独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文章较全面论述了台湾当代作家郭枫的创作成就,客观地分析了郭枫创作的思想情感,审美表现,探讨了郭枫的人生观与宇宙观;郭枫散文创作的主体精神和文化意蕴;郭枫的艺术追求与审美风格等。认为郭枫作品充满了批判意识、自然意识、生命感悟、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的思辨色彩;其内蕴的质美和激情,其浓郁的个性色彩,其独特的审美选择,来自于作家对人生的真见、真知、真性与真情。其审美视角表现出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和谐,其审美风格是传统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郭枫虽耽于独行的寂寞,但他心灵世界决不孤独。
关键词:颠踬人生 时政批判 生命真悟 静穆痴稚 甘美人性
环视台湾文坛,郭枫犹如一座沉默而崔嵬的嵩岳,浑厚、坚强、坦荡、俊逸、孤立于流俗之上,醉然于生命之灿然。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其步履虽然颠踬,却绝不踉跄,绝不卑屈。他以一种极为严峻与近乎冷酷的鹰鹫之眼去审识周遭现实,以一种理想的情感与尊严去热情地追求对生命本真的超越及对永恒、无限和自由的真善美的体验,因此,在文学的世界里,郭枫表现极为特殊,从不参加任何组织,不与官方的文学组织往返,不申请各种补贴,不接受一切报刊的奖金,疏离于正统作家之外,决不媚世媚俗,或凭临高山大海,或恋故乡花草明月,让灵魂沉于超世的光辉之中,显示出一种高贵的单纯与痴稚,静穆的伟大与质朴。他这种嶙峋的个性与风骨,使他在喧嚣忙碌的台湾文坛上虽没掀起象“三毛热”、“席慕蓉热”、“柏杨热”似的“郭枫热”,但他与他的同代诗人及作家如余光中、王鼎钧、杨牧、张晓风、许达然、陈之藩、张拓芜那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敬仰。
郭枫一个人趄趄独行,孤孤单单,但他挺得起脊梁,耐得住寂寞,决不凄凄惨惨。走进郭枫的诗文世界,其浓郁的个性色彩,其内蕴的质美和激情,其对人生追求的率真与诚挚,令人欣喜,令人感奋。郭枫诗文世界是自然的、心灵的、社会的、时代的世界,又是以真诚与大爱拥抱土地与人民的世界。其魅力来自于作家的真见、真知、真性、真情、既有一缕缕清新幽香,又有深邃的情思,既有开阔磅礴的崇高之美,又有细腻温婉的平民之美。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索郭枫创作的思想情感,审美表现,将对郭枫创作道路及成就进行全面地、客观地考察,让事实证明郭枫创作在台湾文坛上有着一定位置。
一、郭枫的人生宇宙观与审美观
郭枫的人生观并不复杂,是一种醇直的表现。他的思想犹如一条清澈透明的河流,没有被各种纷乱的思潮所浸染玷污,正直、豪爽、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热爱人民,参与社会批判是他的人生信仰,在其创作中并没合流于台湾其它一些作家所呈现出的旁杂的思想体系。尽管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各种思潮早已在台湾文坛蔓延,郭枫却避开这种横向干涉,将思维凝聚于纵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精神与民族优秀文化的审美内涵之中,淡泊、高雅、蔑视权贵、重义轻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传统文化仍然是他的思想基础;同时,在面对现实政治对人性的扭曲,权力与金钱对人的灵魂的腐蚀,郭枫表现出强烈的嫉恶如仇精神和积极的人道主义精神。
郭枫的人生观与他曲折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联,他出身于徐州,在黄淮平原的乡野长大,幼时丧父(其父郭剑鸣是黄埔军校第一届毕业生),其母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从此,他中辍学业,飘泊四方,甚至在马路旁摆摊卖烟维生,直至进入南京“遗族学校”,1949年在战火中随校南迁至台。在其成长过程中,目睹了家业的衰败,日寇的凶残,百姓的遭殃,亲友的薄情,一种憎恶黑暗,渴望光明,关怀人民,热爱人生,追求人格独立与尊严的个性日渐形成。在台湾他鄙视那些趋炎附势,急功近利的政治诱惑,保持着傲然瞿醒的姿态,因此,在郭枫创作时,以人道主义信念为核心,突破那种感性,以政治行动导向型表层次的浅吟低唱,追求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真正的人生价值。
文学是人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注视着现实的人生,现实的人性,从而在对人性的表现中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意义的作品。郭枫在其作品中关心人的命运,呼唤人性,表现人性,高扬人性,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幡然举起反对扭曲人性的旗帜,从政治上,文化上对人性异化进行大胆揭示和批判,表现出一种深入反省意义的美学风范。
此外,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对自然进行哲理思考是郭枫追求审美理想的又一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可寄托深厚的情感,或离愁,或闺怨,或相思,或欢悦。郭枫将其对人生独特的经验化作具有生命的自然意象,让自己和自然相互交心,个体生命成为宇宙中的一个音响,在这种人和自然间亲昵与优美的诗意中,唱出了一曲曲生命的赞歌。
郭枫创作的审美旨趣是民族的与乡土的,他的根深深地扎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在《独醉集》专栏中对台湾社会那些背离民族传统的现象进行了抨击。其创办的台湾“新地”出版社宗旨是“拥抱中国土地,开拓民族文学”,并把以下三条作为该社的出版范围:“1:文学要关怀乡土放眼世界,新地只印文学作品其他的书不印。2:文学要为民族发展而服务,新地只印写实作品虚幻的书不印。3:文学要树立风骨抗拒庸俗,新地只印纯正作品淫盗之书不印”,表现了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与民族事业的态度与决心。在其创作中一直融贯着传统的文化性格,其文化价值的选择和取向贯穿于郭枫毕生的文学事业。
二、勘乱时期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
四十多年来,台湾,大陆两岸文学在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下,虽然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但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精髓凝聚于每位作家思想之中。入世参与的儒家思想使古今正直知识分子负载着严肃的使命感和重大的社会任务,他们用自己生命进行创作,把时代和社会融于自己心灵生活。在勘乱时期郭枫十分注重对现实的关注,批判时政,反讽权势,同情百姓,追求真理,没有一丝放逐、悲观、绝望、颓丧的色彩,充满了昂扬、激荡的抒情和哲理交织批判精神。
在《五十自画像》一诗中他形象地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孤零零地在人间打滚/从小就不懂什麽叫做家/沉甸甸压在头顶的/是浸透了悲哀的云/生命像无花的树/挣扎着,向天空要颜色/……,让岁月那炽热的钢印/在心中烙下伤痕累累/让恶魔那恐怖的阴影/在前路散布恶梦无穷无尽/绝不用泪水冲洗屈辱/绝不向黑暗投降/风霜满面,依然仰向天空/等待早阳,等待春汛……”这首诗中表现出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决心,对胜利充满了信心。郭枫作品中有许多充满了呐喊、变革、创造、奋斗、自励的诗句,如“让生命化为一枚曳光的炮弹/散碎的肢体散落如花雨”(《飞升》),“等待,那爆发的日子到来/每个字句都化为迅疾的雷庭/鞭笞虎狼!并清扫隐匿的魑魅/吹响号角!迎接土地的春天”(《笔誓》),这些诗中表现了郭枫精神世界中“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
郭枫一部分诗对台湾统治者进行了讽刺批判,对传统文化熏陶下副人格特征进行了强烈地抨击,如《路过蒋介石庙》一诗中,是对现代“皇帝”陵墓的嘲讽,“蒋介石统治台湾,混过四十年/这庙是四十年唯一伟大的建筑/庙堂巍魏峨峨,气势吓人/像一头怪兽盘踞台北心脏地带/宏大的陵园,幽雅而辽阔/造出当代陵墓的世界记录/……。却很少人知道:庙的底层镇暴部队总是从这里出发”。在《植物园今昔》、《谁家的故宫博物院》同样直接地对台湾当权者破坏生态环境,掠夺国宝给予了揭露。郭枫极为关心台湾教育及知识分子的问题,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生灵涂炭进行讨伐,《台大变貌》一诗中写道“崇高而庄严的台湾大学/再也挡不住恶鬼叩门/成群魔鬼挤进来”,他对军事接管学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首诗是作者经过台湾大学大门广场前,面对热衷政治改革的师生绝食抗议却遭到围观者的冷漠而发出的强烈的愤慨与叹息。作者以沉重悲愤的心情欲把那些昏昧的人们唤醒,对执政者暴虐专制完全曝光,表达了摧毁专制的决心。
郭枫一向痛恨伪善、丑恶、阴险、畸形、变态的社会生活,在其诗歌中予以痛砭。《黄昏的番鸭仔》、《花斑豹》、《热带鱼》、《蛇》、《蜥蜴》、《饲料鸡》、《多面猫》、《衰老而饥饿的狼》、《疯狗》、《孽龙》、《狐》、《麻雀们》……等一系列勾画动物形象的诗中,象卡通或寓言般地展示了鸭的聒噪,鱼的沉浮,蛇的诡媚,蜥蜴之龌龊,饥狼之凶恶,癞狗之摇怜,孽龙之荒唐。批判层面上,郭枫的散文充满着时代性、战斗性、探索性,与柏杨、龙应台的杂文、小品文一样或抨击、或嘲讽、或规劝,充满了思辨色彩。郭枫的政论散文对青年一代理想的虚无,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新闻传播的平庸低趣,社会的蝇争蚁逐等众多方面予以了展示和批评,如《平凡而不庸俗》在《博士和青蛙》、《给文化驼鸟们》、《知识分子的觉醒》等文章中,郭枫对台湾教育体制的保守却又夜郎自大进行了批评,认为“在发扬‘中华文化’的呼声高唱入云之际,最使人痛心的是‘文化鸵鸟’们的愚昧。他们根本不懂‘文化’的意义,却比谁都叫嚷,他们慷慨激昂的想做一个过河卒子,实际上却是文化的罪人;他们闭着眼睛往死胡同里钻,就象驼鸟钻进沙堆里,只要把头藏好,露在外面的屁股是没功夫管的。”《高尔夫高尔夫》、《噪音世界》、《报纸趣味化》、《书刊市场拾荒》、《在荧光屏上》都是对台湾社会文化被异化的真实写照。
忧患、批判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知识分子面对艰难时世的一种使命感,忧国、忧民、忧君是它的不同层面。郭枫即使是在六、七十年代那种十分窒息的环境中,面对“党禁”、“报禁”、“陆禁”紧张时局,也没放弃对现实阴暗的揭露和批判,突破了文学的政治禁区,他与王拓、陈映真、宋泽莱、李昂、廖辉英等向政治主题延伸的小说家一样,郭枫以诗和散文作为解剖社会的利刃。我们可以看到郭枫:“他一路踢开阻挡/踢开那些残余的阴霾/踢开一个破落的时代/踢开满身的屈辱和创伤/缓缓地上升,渐渐地蜕变”,争取一个光亮的世界。
三、“坐对一山青”的自然意识与生命感悟
郭枫的诗文除了“言志”的充满了忧患意识与批判意识的篇章外,一部分还体现了对大自然的“缘情”与“道悟”,真正达到“入乎其内,令神与物冥”的崭新层次。古人强调心物交融,潜气内转,主客观达到完善的统一。郭枫总是从古典文学精华中与大自然的山水间找到诗的灵感,常常“坐对一山青,把心灵开放,向着一个绝俗的世界”去识得生命的永恒与超越,“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则可以参矣”(《中庸》),让思绪在茫茫宇宙,无限时空中自省反思,犹如云破月出,似淡烟轻笼,浑然于心,神思飞扬的“妙悟”达到内在的、深层的、本质的“真悟”。
首先,通过对傲岸峻拔的“山”之意象系列的顿悟,赞美生命崇高与庄严。《山》、《坐对一山青》、《高山流水》、《山与谷》、《噢,阿里山啊》、《山的哲学》等精美的篇章,寄寓了诗人特殊情感,没有一种“用心若镜,应而不藏”的感知方式,没有一种仰视真理,志气高远的旷达胸襟,没有一种热爱自然,崇拜生命的人生追求,诗人又怎能与山水达到如此偕境?怎能在山岳面前陶然暝然、诗意缱绻?怎能由衷地感的到生命的壮美与庄严?“山”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在郭枫作品中有着突出的地位,是一种理想的象征,是诗人自身审美情感倾向与自然的契合,即诗人的崇高美的思想、品格和审美修养的表现。山的挺拔、坚强、庄严、超人的意志、傲岸的品格令诗人钦赞不已,山所特有的那种雄伟豪迈气概是诗人精神意蕴的诗化。
作者由对山岳的敬仰到与山岳的融入,由宇宙生命意识的探索到对现实的忧愤,整个情感过程没有一点虚无与消沉,而是把生命投入到时代洪流,将历史与现实相契,昂然执着地追求人生真谛,因此,“山”作为一种特殊意象,显示了作者把握人生价值的态度,具有深厚的价值感和深层的主体性追求精神,也是自然意识与生命意识熔铸于民族意识后的升华。
其次,郭枫除以山作为抒情对象赞美生命崇高之外,还“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诗品》)以花草树木之品性来歌咏生命之坚韧。春柳的哀怨美丽,榆树的挺拔憨厚,白杨的潇洒脱俗,松柏的傲寒凌雪,作者都尽情赞美,用它们来象征质朴坚强的北方人民。榆树“既能耐干旱,又不怕风雨;它的根扎在地下,扎得深,扎得广;所以无论怎样摧残和摇撼,也休想让它屈服”,“老家的庄稼人,就是这么憨厚!想起老家的庄稼人,可不就象老家的榆树?根扎在泥土中,绝不动摇,枝叶伸向天空,吸取光热,拼命地要在痛苦和摧残中茁长。然后,从里到外,整个生命是无尽奉献”(《老家的树》)。作者用白杨来象征北方原野上抗日游击队英雄;用青松来象征能承受千古寂寞而孤傲挺立显示出生命风范的知识分子。透过这些对自然景致的抒情描写与展示附丽其间的种种品格,我们可看到民族的伟岸风姿及作者真诚而执着追求人生意义在内的生命价值观。
再次,郭枫还直接面对心灵对生命进行更高层次地领悟。这部分篇章所蕴含的深邃的智慧与哲理,赤诚与圣洁,具有震撼灵魂的力量。《独行者》、《且饮一杯寂寞》、《寻》、《我和哭泣》、《蝉声》、《台南思想起》、《异乡人》、《我走过长夜》、《悟》、《飘然过往》这些直抒胸臆的诗文,其价值在于作者用哲理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一般道出永恒,从存在道出本质。譬如面对孤独,郭枫确是一个“影子拉得好长好长”的独行者,然而,他并不会失眠于夜的黝黑,彷徨于寂寞的胁迫,他相信自己的跫音,相信自己心中永远燃烧着热情。对于郭枫寂寞不再是痛苦,不再是感伤,寂寞是成熟生命的一种姿态。“寂寞是一炉千年的温火,把人的灵魂细煎慢熬,能熬炼出一些支撑天地的铁骨”。他把寂寞化为一片芳香的天地,劝说世人大胆地啜饮寂寞,因寂寞本身就是人的本质之一。《寻》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启迪心扉。作者告诫人们不要让心灵沉迷于梦中的云朵,让生命贴近大地,生命的花不是为空虚的人开放的,美好的果实,不在云中,而在地上。全篇在情感的抒写中赋予哲理的思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只有在现实中去努力追求才能获得人生的真正的价值。
郭枫关于山川自然的吟咏,是他对人生艺术思考的表征,在哲学深层意义上使生命本质得到了升华。它们仿佛一缕缕合成的琴弦,奏出悦耳神奇、多姿多彩的无声旋律,令读者感到生命的激情、湛醇和美妙。
四、爱心的呼唤与人道主义的追求
与台湾不少作家一样,郭枫一直提倡发扬爱心,创作中对人性的主题十分关注,乡情、亲情、爱情、友情、童趣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展示。对乡土故人的追寻的乡愁意识——乡愁母题,是漂泊异土的作家所表现的永恒主题。乡愁及人性的表现描写,是儒家文化的人伦道德美学体现,是精神心灵的需要,体现了积极的思想意蕴。
郭枫的乡愁是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恋,对黄淮平原上的乡亲的真挚热爱。《老家的树》对故乡的眷恋痴迷使人感到诗人纵然离别故乡三十多年,但他的生命已与它无法分开,他的根仍然扎在那儿。郭枫的乡愁情绪不只是一种寻根意识,恋土情结,其最深刻最有价值的是在乡愁中燃烧着爱国主义激情,是他对我们中华民族坚强的生命力的歌颂。对祖国与人民的爱是人性表现的最高层次,唯有如此,人性才能得到升华与崇高。《我想念你北方》勃发出浓郁的赤子之情,长年盘结在作者心头的乡愁,像春蚕吐出万缕千丝紧紧缠绕着他,一声声“北方,我想念你”的热烈呼唤,情真意切,摧人肺腑。从思念北方的土地到朴质的乡亲,从对历史的缜思到现实的关照,无不显示出作者的一颗扑腾跳荡的爱国之心,特别是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显示了一种忧愤之情。《爱咱们应该爱的——写给萍飘美国的孩子》的系列书信中,作者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告诫远在异国他乡的孩子,“爱咱们应该爱的,爱亲人,爱乡土,爱咱们古老而又多难的中国!”并且自始至终坚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会站起来,我们绵长而优秀的文化将会再度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道主流”,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作为人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亲情、友情、爱情、同情、童情,郭枫率真而热烈地赞颂了这些美好的情感,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寻觅着,呼唤着,发现着人类天性中的仁爱、纯真、理解和同情。
郭枫善于从下层人们身上发掘他们内心的美质,歌颂那些灵魂单纯、明净、无私无畏、勇于奉献、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普通百姓。《可亲的人》描写了一位司机的可敬与心灵的美好,《集影》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和谐,心灵的勾通、相互的关心和人性的甘美。《九月的眸光》是一篇童话一般美丽的恋情散文,充满了浓郁爱意的抒情氛围。《三张小圆脸》抒写了童心的纯真与好奇,三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快乐地逗弄小蚱蜢时的童趣世界,让作者十分羡慕感动,“生活中要是永远能和纯真的心灵为侣,就是叫我做一只蚱蜢也好!让我和纯真的心灵为侣,互相欣赏,互相满足。我想,那时我眼中的世界,将美丽如一篇童话了”,作者一片天真烂漫,从童心中得到了生命的真悟。童趣使作者在俗化的世界显得纯稚,那么,友谊使他的生活更充满了温馨。郭枫非常珍视至真至诚的友情,其诗《明月》、《乡山之歌》、《连体婴》等抒发了对友谊的赞美之情。
从上例举,可观出郭枫对人性的追求是孜孜不倦,热情盈怀的。他不是抽象的人性论者,而是将弘扬爱心,提倡人道主义作为自我完善的生命准则,在生命与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展现这种精神。他曾说:“我们需要天性浑厚的作家,我们更需要发扬人性的文学”(《人的文学与文学的人》),他将文学看成是作家人格的载现,“作家要成为时代的证人和社会的良心,不是仅靠着写作手法,不是靠着朦胧的心愿就能得到的,主要的要看作家所具有的人格。人格是本性与学养的总和”(《人的文学与文学的人》),“我崇拜美,人和人本应该打破一切藩篱,铲除掉阶级、种族、地域的差别,彼此以纯真的感情温暖着的。”“发扬人性的美和艺术的美,才能匡救世界的堕落。”(《生命崇拜》),因此,可以说,郭风是爱神与美神双重追求者。
总之,郭枫作为一个诗人和散文家,其作品融进了他倔强而正义的个性,融进了他的满腔赤诚与热情,用一颗真心去领悟生命的真谛,去咀嚼人生的甘苦,去感受寂寞生存的伟大。他的作品充满了批判意识、生命意识、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的思辩色彩;其审美视角表现出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和谐,人生追求与艺术追求的统一;其审美风格是传统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呈现出悲壮、激越、崇高的时代旋律。
郭枫,虽耽于独行的寂寞,其敞开的心灵世界却决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