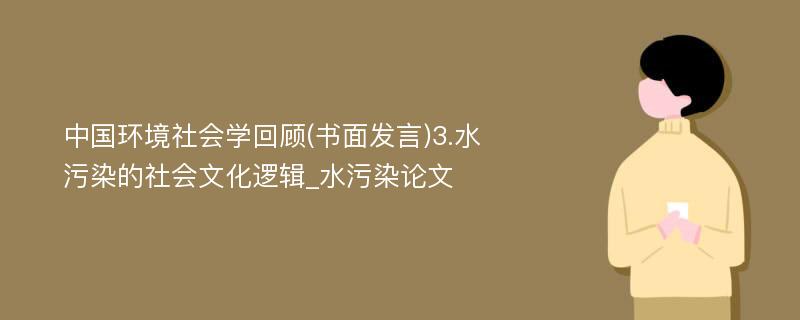
检视当下中国环境社会学(笔谈)——3.水污染的社会文化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水污染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水污染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级政府认识到保护水环境的重要性,加大了水污染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也加大了水污染处理和水环境保护的科研投入力度,一大批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另外,通过媒体等途径的宣传,民众对水污染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保护水环境的意识也有所加强。
但是目前水污染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虽然局部水域的水质有所改善,但总体水况仍然堪忧。城市水源地及景观地水质得到控制、改善,但乡村河网仍然呈恶化趋势。有的河浜淤塞、河道人为截断,水体污染严重。从区域关系看,大都市及经济先发展地区的水污染有所遏制、有所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污染却在恶化。因为大都市及经济先发展地区加紧了对污染排放的管制,使大量的污染源从城市和经济先发展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
水污染按其来源可以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一般把工业污染称为点源污染,比较分散的农业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称为面源污染。国外市场经济发达的法治国家,作为点源污染的工业污染基本上可以控制,面源污染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中国由于是后发国家,在最近的30年中工业快速增长,所以因工业而造成的水污染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面源污染问题也在日益突显。
工业污染仍然是水体污染最主要的危害源。首先是工业污染的总量很大。虽然处理设施有较快的增长,但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仍然十分可观。大量的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污染水体。大企业一般有相对严格的污染处理设施,但由于总量大,仍然对水体构成很大的环境压力。其次,工业、特别是化工等行业排放的污染物,毒性比较大,对水环境影响比较大。一个小化工厂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一条河流污染,但要让被污染了的水体自净,则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反复向河流排污,水体就很难自然恢复了。
依笔者观察,工业污染具有物质污染与“精神污染”的双重污染特征。即它不仅污染了水域,也对人的行为和观念产生了毒害作用。水的功能从“高级”到“低级”可粗略地分为饮用、渔业生产、农业灌溉……纳污,等等。当工厂把河流污染以后,河流就失去“饮用水”的功能;河里的鱼虾不能吃时,河就失去了养育鱼虾的功能……污染的最终结果,河流只能用于纳污了。一旦水体只剩下“纳污”功能,人们就不再尝试去保护水体,而只会做加剧水体恶化的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演变。传统时期的水乡居民,对河里可以扔什么、不可以扔什么,比较严格地遵守着当地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但河流被污染以后,公众保护水域的动力消退,无意识中,以前自觉保护水体的大众成为水污染的主体①。
农业生产对水体的污染影响也在加剧。农业生产越来越倾向于“懒人”作业,而以化肥替代传统的农家肥是“懒人”作业的选择之一。农村中农家肥使用的减少、秸秆利用的减少,使得包含在这些物料中本来利用而分散到耕地上营养物,更可能集中抛弃到水体中,从而增加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物。传统的养殖业是散户养殖,而随着养殖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养殖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规模养殖的比例不断增加。只要环保措施不能及时跟上,就有更多机会集中向水体排污。另外,为了保证农田的高产、稳产,农田水利的灌溉、排水系统的完善,使水在农地上停留的时间缩短,更有可能把庄稼没有吸收利用的营养物流入河流湖泊。
生活污水向水体的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城镇居民以及那些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村人口的总量在不断增加中,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最近一些年份,村民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抽水马桶普遍使用,但没有相应的污水处理系统,从而影响水环境。
水污染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说,它是一个“多因多果”问题。水体污染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同作用、演化的结果。
如何来看待水污染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关注点。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物质形态的水污染问题,关心污染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水污染问题,则主要关注污染背后的非物质因素。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则主要从人的行动、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方面,去研究水污染的问题。笔者以为,社会学可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进行基础研究,从学理层面上认识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理;二是为企业、政府或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社会行动”被经典社会学家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的出发点。如果用“社会行动”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去透视水污染问题,就很容易地透过并抛开形形色色的污染现象,直接地观察人的问题。事实上,水污染就是人们行动不当的后果。试以频频出现的水污染事件为例,水污染之所以会发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是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相关各方行动的结果。工业污染中最直接、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是企业主。作为经济理性人的企业主,追逐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只是简单地追逐眼前的经济利益,这样的企业行为不仅影响环境、影响其他群体的利益,最终也将影响企业自身的长久利益。但在社会转型期,大量的企业只是考虑自己眼前的收入。据推算,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约为3.5岁②。中国企业的如此“短寿”,与此不无关联。作为污染的直接害者,普通百姓为了基本的生存,在面对反污染的专业壁垒,在企业、政府的等强势组织面前,只是沉默,仅有少量的“傻子”、“疯子”作抗争。作为第三方的技术专家往往缺乏独立立场,而一些职能部门则利用掌控的环境容量之“稀缺资源”作为致富资源。所以,污染难以避免③。
当然,无论是个体的行动,还是群体的作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之中发生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目前中国与水污染相关的法律,虽然不能说十全十美,但基本的法律规范是有的。就是说,水污染问题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不按规范行事。比如,按照法律不该降生的企业“准生”了。本该达标排放的企业,却可以不达标排放而长期生产。污染发生后,因为取证困难等原因,污染企业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被污染方的损害则难以得到应有的赔偿。这样的后果,给企业主和大众以“污染有理,被污染活该”的法律印象④。
事实上,不仅社会行动嵌于社会制度之中,法律体系也是深嵌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假定,往往对人们的行动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往往是“来无影去无踪”,很难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在讨论生态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时,怀特最早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生态危机是与基督教有关联的。⑤中国的环境问题自然也有中国自身的历史根源,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问题,此处不再赘述。这里仅举中西方对人性认识的差异与假定作一说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与假定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人性是善是恶,本没有定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西方社会中对人性的假定可以归结为两种理想类型。中国传统社会对人性的假定,可以表述为“人性是善的,即使恶,也可以通过教化使之从善”。这是一个不易论证、也不可能在此短文中论证的话题,仅举《三字经》予以说明。《三字经》首句“人之初,性本善”,说人性是善的;随后,它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家庭与教师。所以,在中国社会中,社会控制中对伦理道德及其教化的重视高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理想类型中的西方社会,假定人性为恶。《旧约》“创世纪”第三章,说夏娃因为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从此种下了罪的后果。《旧约》“诗篇”第五十一篇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就是一种“罪性(Sin)”的人类“原罪”。从“人性恶”这个假定出发,社会控制强调从制度、规则上去约束个人,控制个人。西方世俗社会中,如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普遍建立的相互制衡的机制,像美国建立了“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圣人执政”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政治领域里的制衡机制、市场体制里的监管机制等等,都是从“人性恶”的假定出发建构制度的。中国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把“市场经济”作为工具(手段)来使用的。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让建立起来的。所以,如何来建立一个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污染的社会控制体系,需要长期探索。
水污染是一个“多因多果”问题,所以解决水污染问题的策略也需要多方入手、系统地解决。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看,治理污染的问题,主要不是解决污染物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与水污染相关的人的问题。我们平常看到的水体污染,只是一种物质表现形态,物质形态污染背后其实是人的问题——是因为人的行动不当造成的。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污染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点源的治理控制手段基本上是成熟的。因此,治理水污染要从调节人的行动着手,结合考虑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1)监管好污染者。目前,政府在污水处理和水环境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而政府的监管力度则相对滞后。笔者认为,无论是工业企业污染物的处理还是城市污水的处理,市场能够解决的都应该让“市场”来解决。政府最根本的任务是监管。中央、省级政府应加大对水污染技术监控网的建设。可以在主要河流、重点企业下游设置水质监测仪器,这样,政府部门可以直接掌握环境变化动态。从笔者调查了解的实际案例看,无论江浙界河上监测装置,还是在淮河流域上一些重点污染企业污染在线监控仪,对地方及企业的污染的遏制起很大作用。时机成熟后,扩大水质监测仪器布点密度。同时,建立“水质透明”制度:先可以在一些跨省的界河上建立水质透明制度;条件成熟时,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布实时监测到的水质信息。
(2)河长制。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⑥。水体污染很显然也是“公水悲剧”的表现。在当下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下,水资源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影响下,清晰产权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所以,有不少学者、政府官员,鼓吹学习某些西方国家,实行“排污权交易”。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很难通过实施“排污权交易”来解决污染控制问题。
清晰产权可以解决问题,但清晰“公水”的产权非常困难。如果一定要划清,成本也会非常的高。但如果避开公水产权不清晰问题,直接从管理入手解决问题,也未尝不可。从管理的角度看,如果责任清晰,即使产权不清,同样也可以解决问题。大例子是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早期的实践中,农村土地的产权是不清晰的(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农民的土地产权是清晰的),但因为责任是清晰的,所以生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生产问题。小的案例如我们在太湖流域的实地调查中,发现“河段责任人”可以有效地管住其对应河段的卫生与污染问题。所以,实行、推广“河长”和“河段责任人”的河流管理责任制,给责任人予相应的责任、权限和奖惩措施,可以解决河流“放任自流”而致的“公水悲剧”问题。
(3)管好干部。环保方针与政策制定之后,地方干部能否执行以及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就成了关键因素。然而,目前的干部考核制度不利于环境保护,也难以遏制环境破坏。科学发展观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考核地方行政官员仍然主要用经济指标。因此,在干部考核中应弱化对经济指标的考核。此外,干部异地任职和频繁的流动机制,也不利于地方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是一项见效比较慢的工作,短任期的外地干部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政绩,忽视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工作。相对而言,任用本地干部更有利于环境保护,他们比较在乎自己的名节,包括退休后的声誉。因此,干部的流动机制也需因地制宜。
(4)重视民间环保力量的作用。企业污染已经引发了大量的冲突。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实际上是污染受害者与诸如企业主一类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在这样的冲突中,政府应该恪守中立,做好裁判员的工作。在以往的水污染纠纷中,政府往往偏向企业主和地方干部这一边。老百姓不仅怨恨企业主,也怨恨政府官员,最后可能会演变成政府失信于民的局面。因此,在水污染纠纷中,政府应客观公正地处理污染冲突。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可以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起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因为没有利益动机和较少的功利色彩,对环境保护这样需要长远的、整体考虑的问题,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学海》2007年第1期。
②参见“中国企业的五大差距” http://www.psyexpert.com.cn/Articlel/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4
③陈阿江:《水污染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浙江学刊》2008年第4期。
④陈阿江:《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太湖流域工业污染的一个解释框架》,《学海》2008年第4期。
⑤White,Lyn,Jr,1967,"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Science,Vol.155,No.3767:pp.1203-1207.
⑥Hardin,Garrett,1968,"The Tragedy of Commons",Science,Vol.162,No.3859:1243-12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