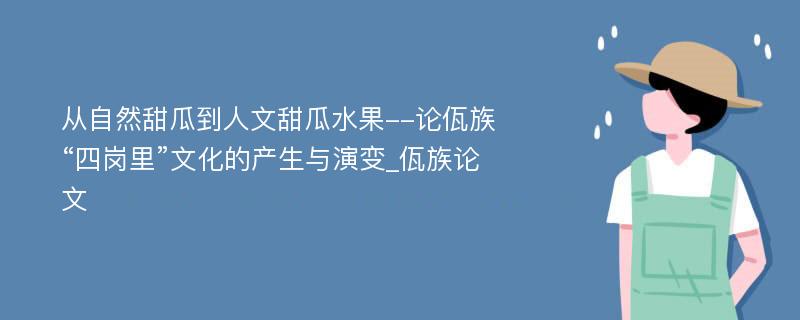
从自然瓜果到人文瓜果——论佤族“司岗里”文化的产生及其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瓜果论文,佤族论文,人文论文,自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岗里”文化无疑是佤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这不仅是多数文化、民族研究学者的认识,而且也是佤族地区各级政府多数文化工作部门所认同的。弘扬佤族文化,打造以“司岗里”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品牌,既是佤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佤族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借用我国民俗学界大师钟敬文的一句话,即:葫芦“是一种人文瓜果,而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瓜果”拟题,将笔者多年对佤族“司岗里”文化研究的一些粗浅认识整理成文,以求教于民族文化研究学者和民族文化工作者。
一、佤族“司岗里”文化产生的背景
一个民族文化无不受它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或者社会历史条件的多重影响,佤族“司岗里”文化自然也不例外。
(一)自然环境
权且不说远古时期,从有零星文献记载的历史来看,佤族的生存环境一直是内陆,是山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佤族的生存环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不固定的,出现由宽变窄、由大变小的变化趋势。
根据我国民族学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先秦时期各类文献中的“濮人”、“百濮”等族群,是近代以来我国境内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的先民。他们分布极其广泛,有“江汉之濮”、“楚之濮”、“葛濮”、“滇濮”、“句町之濮”、“永昌之濮”、“闽濮”等,因分布区域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名称,这些古代族群分布在今天长江以南的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广大地区。
到秦汉时期,云南青铜文化崛起,这就是滇文化。这一文化是以“百濮”文化即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民族古代文化为基础,融合了百越、氐羌等族群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秦汉时期的滇文化是以孟高棉文化为基础,并吸收了中原文化、百越文化乃至印度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1]另外,根据桑耀华先生近期的研究成果,秦汉时期,分布于曲靖市陆良,玉溪市江川、通海等县的“莫”人,又叫“休腊人”,其实他们是“孟人”、“莽人”、“蒲人”,即佤族等南亚语系民族的先民。[2]这就充分说明,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的先民在秦汉时期确实是分布到云南的中部、东部的广大地区。
从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佤族先民开始由云南中部向西部迁移。关于这一历史痕迹,有考古资料和古地名为证。说前者,在云南西部和四川西南部的大姚、姚安、祥云、景东、雅安等地,有“大石板”古墓群的重大考古发掘,这种古墓群是属于“濮人”留下的,也就是南亚语系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各民族的先民的古墓;[3](p74)说后者,此时,云南西部出现了“哀牢”[4](p25)、“永寿”[5]等佤族先民建立的古王国,范围包括了今天大理、保山、德宏、临沧和普洱等几个州市。
但到了唐宋时期,由于今大理州内先后出现了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民族政权,这就导致了“濮人”的大规模迁徙。唐朝樊绰《蛮书》卷4称:“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按:“望苴子蛮”即为今佤族之先民),说明在唐朝时期已经有大量的佤德语支各族西渡澜沧江而迁移,澜沧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成为他们的主要聚居地。正因为如此,元朝到明朝初期,临沧境内如顺宁(今天风庆县)、镇康、孟定的土司、土官都是“濮人”担任。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顺宁土知府被剿灭,政府在此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顺宁境内的大部分“濮人”被迫向镇康(含永德)、耿马及今天中(中国)缅(缅甸)边界一带往外迁移。到了明朝末期,汉族、彝族等其他民族不断往凤庆、云县迁移,当地的“濮人”有的也被这些民族同化了。
此时,也就是明朝末期以后,近现代佤族的分布区域就基本相对固定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阿佤山”。从空间来看,它指的是,横断山脉南端以南,怒江以东、澜沧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包着今天的临沧和普洱两市交接地的耿马、双江、沧源、澜沧、西盟、孟连几个自治县和缅甸北部的佤族聚居地区。这里崇山峻岭,平坝极少,山区面积在90%以上。
总之,从以上佤族历史脉络来看,他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都是在内陆山区,这一历史至少也有3000年以上。由此可以说,佤族文化是依山而生、依山而存,山是孕育它的母体。
(二)人文环境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佤族从有历史的记载来看,一直生活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省全部和四川、贵州以及缅甸北部的广大地区。佤族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云南古代灿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这里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有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猿人等古人类遗址,是最早栽培人工稻的地区之一。根据云南考古学者李昆声研究,云南新石器文化有八大类型,[6](P275~282)也就是说,这里不仅有堪称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而且还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辉煌的青铜文化。显然,这里有着人类古老的远古文明,有过辉煌的历史。
这样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地区,为佤族“司岗里”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人文环境。从考古发掘看,在云南昭通鲁马厂新石器遗址中有葫芦形的陶器的发现,[7](P23)江川李家山青铜器中也有葫芦笙的出土。[7]从历史文献看,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有“沙壶”、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有“沙壹”等记载。刘尧汉先生认为,“沙壶”和“沙壹”其实为同一物,“就是成熟的葫芦”。[8](P64)这就充分说明,几千以前云南就有了葫芦的种植。
当然,我们无法找到佤族种植葫芦历史的直接资料,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既然佤族在云南这块历史舞台上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云南悠久的葫芦种植历史,自然是佤族“司岗里”文化得以产生和形成的人文环境。
(三)内部因素
显然,佤族“司岗里”文化产生和形成的内部因素必然是佤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本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由生殖崇拜又衍生出生殖崇拜文化,它是当今世界人类多方面灿烂文化的萌芽”。[9](P389),而“司岗里”隐喻的是人类是由“洞”出来的,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司岗里”文化无疑是女性生殖崇拜文化的范畴,这已经是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看法。由此,可以肯定地说,佤族“司岗里”文化的产生,是佤族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质决定的,也就是以佤族古老的生殖崇拜文化为基础而产生。
二、佤族“司岗里”文化产生的时代分析
佤族“司岗里”文化何时产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但却饶有意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对于进一步认识佤族“司岗里”文化是有帮助的。
我们认为,既然佤族“司岗里”文化是从佤族女性生殖崇拜文化发展演变产生的,就一定有非常古老的历史。
前已提到,东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就已经有葫芦的记载,摘文如下:“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靠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前已提到,“沙壶”,指的是“成熟了的葫芦”。把人类之母称为“沙壶”,说明“哀牢”是一个有着葫芦崇拜的古族群,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女性生殖崇拜文化的先民。
关于“司岗里”即“葫芦(器)生人”的说法。尽管近现代佤族的说法因地方不同而稍有不同,但一些基本的内容是相同的,那就是先有一对特殊的夫妻,即人和牛的夫妻关系,母牛产下葫芦籽,然后有了葫芦的果实,各民族就从葫芦的果实出来……。另外,佤语中的“司岗”,指的是葫芦制作而成的器皿,也可以理解为“成熟了的葫芦”。
由此不难看出,《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与近现代佤族流行的葫芦(器)出人的说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许它原本就是佤族民间流行的人类起源在汉文献中的最早记载。
云南沧源崖画是佤族先民的杰作,距今3000多年。根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它的许多画面中,“葫芦(器)生人”这一内容非常丰富。[10](P212~214)这也可以作为佤族“司岗里”文化历史十分久远的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其实,佤族有历史悠久、极其浓厚的石崇拜。[11]而沧源崖画就是它的最早、最生动的体现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沧源崖画也就是佤族石崇拜和葫芦崇拜有机结合的一部绘画杰作。
佤族称谓在汉文献中的记载也值得注意。在唐朝人樊绰《蛮书》卷四中有:“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是盛罗皮所讨定也。……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等等。文中的“望”其实就是“佤”的同音异写而已。很明显,搞清楚“佤”的含义对于进一步认识佤族“司岗里”文化产生的时代也是有帮助的。
“佤”在佤语中,其实指的是“门”。之所以有如此自称,是因为在“司岗里”史诗中,佤族自称是第一个从“人类之门”走出来的民族,他们是“司岗”的“果艾”,即长子。
应当说,“望”或者“佤”不但是佤族的古老自称,而且也是与佤族同一个语支的布朗族、德昂族的古老自称。佤族“本人”支系,自称“日佤”,佤族“巴饶”支系有时则自称“果佤”,意为“佤的后代”。布朗族、德昂族,有的也自称“依佤”、“阿卧”等。“日佤”、“依佤”、“阿卧”都是一个含义,即“佤”是核心词。非常明显,“佤”应当是佤德语支各民族最早的自称之一,与这一古老的族群关于人类从“司岗”出来的说法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然,关于佤族与葫芦直接联系起来的最早记载,根据所看到的是清朝时期的《东华全录》乾隆“葫芦酋长”卷23这一文献资料。该文献记载:“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壬辰,裕亲王广录等议复;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永顺东南徼外,卡佤葫芦酋长蚌筑禀称,其地有茂隆山厂,矿砂大旺,内地民人吴尚贤赴厂开采,议给山水租银,不敢收受,情愿纳课作贡等语。”[12](P82)之后很多汉文资料就不断出现“葫芦王”、“葫芦国”、“葫芦酋长”、“葫芦王地”等记载。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完稿的《清朝文献通考》卷296“四裔考”就进一步明确记载:“葫芦国,一名卡瓦,界接永昌府东南徼外。”从这些所谓的“葫芦王地”或者“葫芦国”指的就是阿佤山区。
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一带的佤族“胡”氏,因在近现代时期反抗英国殖民帝国主义入侵的“班洪抗英”事件等斗争中,始终表现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侵略者而闻名天下。其实,班洪的“胡”氏,其远祖叫“卡拉芒卷”,原住在公明山附近的炯奴寨,所以以“炯奴”为氏。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炯奴”氏头人达本因参与地方政府调解勐省和勐懂傣族土司(都位于今沧源佤族自治县内)之间的纠纷有功,被清政府封为“土都司”,并赐姓“胡”。而“胡”者,其实就是“葫”也,是从佤族“葫芦(器)生人”这一说法而取的。[13](P15)之后,才有了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一带的佤族“胡氏”。
这时,佤族的葫芦崇拜就不仅只是作为民间口碑传说的形式流传,而且,也成了地方的名称(葫芦国、葫芦王地)、头人的称号(“葫芦王”、“葫芦酋长”)、家族的族徽(“胡”氏)。这样,佤族“司岗里”文化就更加大白于天下了。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佤族“司岗里”文化确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文化,它应当上承佤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生殖崇拜文化,下连云南各民族悠久的、栽培种植葫芦的历史文化。这一文化最早应该是氏族宗教的范畴,是人类宗教意识的产物。而人类宗教意识,按照学者们一般的说法,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阶段就产生了。而新石器时代则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代,所以佤族“司岗里”文化至少可以说是在新石器时代就产生了。但从有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可稽的历史来看,它应当是在我国的先秦时期萌芽,到秦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之后成为贯穿佤族民族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其他的文化缘它产生、兴起和发展。
佤族“司岗里”文化之所以流传得如此遥远漫长,是因为佤族历史上长期受到封建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双重统治,他们被迫过着漂泊不定、不断遁入山林的生活。那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相对完整保留的空间,然而也是一个民族发展极其缓慢的壁垒和温室。正因为这样,“司岗里”文化基本上没有重大的或者根本性的变化,犹如老态龙钟的老人伴随着佤族从远古的历史蹒跚走来,成为维系佤族民族凝聚力和不断推动佤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三、佤族“司岗里”文化的演变
佤族“司岗里”文化历经漫长的历史沧桑,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之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多元文化特征。
(一)从“司捏”到“司岗”
如前所说,在佤族生活的西南地区葫芦栽培种植的历史非常悠久,这是佤族“司岗里”文化产生的重要前提。从部分近现代佤族来看,他们是比较喜欢栽培种葫芦的,一般与南瓜等瓜类植物一起种在房前屋后,并且精心搭建攀缘的架子,以保证瓜果长得圆满匀称,便于食用。
在佤语中,自然的或者泛称的葫芦都叫“司捏”。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佤语词汇。
我们经过研究,在佤语中“si”(一般译为“司”或者“西”)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语素,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有不同的作用、意义。有一个意义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si”与佤族敬畏、崇拜的东西、神灵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太阳“司艾”,龙“司用”,老虎“司尾”,鬼“司儿”等等,都用“si”(“司”)字。但是,“si”(“司”)为何意义?目前尚未搞清楚。
从佤语葫芦的叫法中可以看出,远古时期的佤族先民存在着“司捏”崇拜即葫芦崇拜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应当是先有佤族对自然瓜果的葫芦崇拜,然后以此为基础才有对人文瓜果的葫芦崇拜。在这里,这一人文化的葫芦就是“司岗”。所以佤族的“司岗”崇拜是以他们对自然葫芦的崇拜为基础而产生的。
当然,佤族从对自然瓜果的葫芦崇拜,到对人文瓜果的葫芦崇拜,必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由于这方面的资料阙如,这里也就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从“司岗”到“司岗里”
在近现代佤族生产生活中,葫芦的使用仍然是非常广泛的。比如有些村寨的佤族,使用的碗都是清一色的葫芦器“垛儿”。除此之外,有盛水的葫芦器“司捏(若)”(si nie),保存种子的葫芦器“司库”(si ku),沥水酒的葫芦器“楣儿”(mei),装火药的葫芦器“司吉”(si je)作瓢的葫芦器“棚”(pou),乐器葫芦笙等等。
在佤语中“司岗”有几种解释,西盟佤族说,是石洞;沧源佤族说是葫芦。这两种解释比较普遍,依此佤族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支系,前者称“勒佤”,后者称“巴饶”或“巴饶克”,前者保留佤族的传统文化多一点浓一些,如砍人祭谷,祭木鼓,而后则已没有这种习俗,但他们并不讳言他们有过这种习俗,同样有过那样的时代。
另外,根据有的佤语研究专家所说,“司岗”也有子宫的含义。佤族称寨桩为“司岗”桩;称铐镣和防止猪践踏园圃使用的木枷为“岗”,等等。所以,有的佤族学者把“司岗”的意义引申为“团结”[14](P2)不是没有道理的。
语言素称“风俗化石”。在佤族支系“巴饶”俗语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石容器,出人类的葫芦。把石器与葫芦器并列,并且石器容居首,说明他们也有过人类是从石洞出来的说法。根据专家田野调查,西盟佤族自治县翁嘎科至今还保留了“石洞葫芦”的说法。[15](P12)另外,如前已提到的,在佤族民间石崇拜的习俗极其浓厚。足见佤族认为人从石洞出来的民间神话也是源远流长和广泛传播的。佤族与其他民族的先民一样,显然也经历过远古时期的穴居生活,这一生活应当与阿佤山区洞穴多有关,云南沧源崖画,耿马石佛洞新石器文化遗址等就充分体现了佤族的这种穴居生活。也就是说,人类从石洞出来这一说法应当也是佤族洞穴生活时代一个生动的反映。
总之,佤族不存在上帝造人或者某一个万能的神仙造人的说法,而坚信人类是由“洞”而产生的,这可以说是佤族人类起源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它不会改变的“母题”。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一系列佤族关于人类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洞”的多种说法。根据以上分析,对佤族人类起源的说法可以进行以下图示:
女性生殖器→石洞→石器→自然瓜果的葫芦(司捏)→司岗(人文瓜果的葫芦)。
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母体。人类从人文瓜果的葫芦即“司岗”出来,这已经是比较日趋成熟、相对稳定的说法,也因为如此,它才广泛分布在佤族的广大地区,也才有了汉文献的客位记录,从而形成了无所不包的佤族“司岗里”文化系统。
(三)“司岗里”文化衍生木鼓文化
由于佤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佤族文学属于民间文学,而不是作家文学。这样,“司岗里”之所以在佤族中从远古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其载体就是民间文学。
当然,由于民间文学在流传的过程中具有变异性,所以,“司岗里”就必然因为区域不同,受外来文化不同等因素而出现不同的“异文”,有着不同的说法和版本。
在佤族民间,“司岗里”即有口头传承的散文体神话作品,又有以韵文体传承唱的创世古歌。它成了佤族民间文学的总母题,在其之下产生了许多的子题,包括开天辟地,洪水滔天,万物起源,民族形成,性别区分,语言文字的来历,物种的培育和驯化,火的发现,以及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的起因,各民族相互关系,姓氏的产生等等,内容极为丰富,它反映了佤族远古时期的社会生活,原始先民的思想感情,奇异的思维方式,人生追求,价值观念等等,可谓佤族的“百科全书”,是最系统、最全面的佤族文化“巨著”。
木鼓文化是从“司岗里”文化当中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它与“司岗里”文化共同构成了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征文化。认识佤族文化,必须从认识这两个文化开始。
有学者指出,“木鼓,历史上云南有景颇、哈尼、基诺、佤、布朗等民族都曾使用过木鼓,但直到今天仍然保持使用木鼓的仅仅有佤族一个民族”。[16](P320)这就充分说明,木鼓文化之于佤族的重要地位和关系。
关于木鼓的发明,在佤族民间口碑传说中主要流行两种说法,其一,远古时,是一个名叫安木拐的女祖先发现并开始使用木鼓的。当时在她居住的洞口倒下了一棵空心的千年古树。白天,她敲响这棵古树,聚众上山打猎采集;夜间她敲响古树,领着大家围着火塘唱歌跳舞。敲响古树还可以抵御猛兽的袭击。这棵空心古树就是佤族最早的木鼓;其二,传说距今三十代人(约750年)以前,一个名叫牙懂的女祖先,叫她丈夫达业按她的生殖器制作木鼓。这样,佤族木鼓音槽就制成了女性生殖器的形状。这应当是佤族最早的人工木鼓。
口碑传说不足信,但却能折射一定的事实。以上两种传说都把木鼓的发明、使用与女人相联系,归功于女人,说明木鼓是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的产物。换一句话说,木鼓也就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木鼓文化与“司岗里”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佤族生殖崇拜文化的范畴。
佤族有三大支系,“巴饶克”(又译“巴饶”)、“勒佤”和即“佤”(又称“本人”)。“勒佤”主要分布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内,人口约占中国佤族总人口的20%,1949年以前他们还保留着猎人头、祭木鼓活动等习俗。“巴饶克”(又译“巴饶”)主要分布在沧源、耿马、双江等几个自治县内,人口约占中国佤族总人口的30%,虽然他们已不存在猎人头、祭木鼓活动这样的习俗,但却有比较普遍、十分浓厚的狗崇拜,最典型者当是他们当中的“永茸”家族,流行用狗头代替人头祭谷的习俗。魏晋南北朝时期,临沧境内有个佤语古地名“永寿”,意为“狗寨”。它是佤族氏族图腾名称演变而来的。[5]砍人头祭木鼓是紧密联系的,“巴饶”用狗头代替人头祭谷这一习俗,说明他们也有过那样的时代。总之,木鼓文化应该一度是佤族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它已经渗透到了佤族的宗教、艺术、观念等各个领域,木鼓成为“通天之鼓”、“通鬼之鼓”,构成为佤族的民族精神,成为维系佤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在西盟佤族当中,“氏族酋长的象征,就是克洛克,即木鼓。……每个古老和强大的氏族都有自己的克洛克。窝郎或芒那克饶便是克洛克的管理者,氏族成员围绕本氏族的克洛克居住。一些后迁来而又小的氏族没有自己的克洛克,他们则隶属于有克洛克的氏族”。[17](P102)木鼓起到强化血缘关系和家族甚至地域观念的作用。木鼓俨然“是佤族民族精神的象征”。[18]佤族民谚“生命靠水,兴旺靠木鼓”,通俗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深邃的思想,它淋漓尽致地道出了木鼓之于佤族的关系。
由上所述,对什么是佤族文化进行这样的叙述,即:佤族文化是以“司岗里”文化和木鼓文化为主要载体的一种多元民族文化。这就是佤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和主要内涵,它与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特征”此一理论也是相一致的。
四“司岗里”文化与其他民族葫芦文化的关系问题
纵观我国南方民族,许多民族都有“葫芦生人”、葫芦崇拜这样的民族文化。首先,这一应当与这些民族相同的生存环境是有关系的,是民族文化上一些常见的巧合现象。其次,因为葫芦“鼓腹的形象,多籽的特性,很像是妊娠女性的身体。原始先民便根据同构的原理产生出联想,认为葫芦具有繁盛的生殖力。于是,在其信仰中,就赋予葫芦以人类孕育和出生的母体的象征意义。”
然而,佤族与此不同,他们紧紧抓住了人类是由“洞”出来这一核心内容,并将葫芦加以抽象化。当然,随着各个民族相互交往的进一步密切和加强,出现完全相同的一些内容也是必然的现象。这种相同的文化不正是我国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吗?
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彝族、布朗族、德昂族与佤族葫芦崇拜的关系问题。
根据许多资料显示,彝族与佤族历史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19](P207)至于彝族与佤族在葫芦崇拜这一文化上非常有趣的方面,主要充分体现在“哀牢”人这一古族群的种种说法之上。
“哀牢”人作为云南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族群,出现于两汉时期,他们主要分布在滇西的保山、大理、德宏、临沧等几个州市的广大地区。关于其族属,历来有着争论,概括起来有3种说法,即:氐羌、百越和百濮族群。持氐羌族群说法的人,他们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在许多文献资料中南诏国的“乌蛮”彝族自称为“哀牢后裔”。事实上,如果孤立地看,必然坠入历史的迷雾当中,但要把它纳入到历史上各民族相互吸收、相互同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宏观的民族发展大趋势当中来分析,那么问题就清楚了。
从南诏历史的整个过程来看,它与佤族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如唐文献载:“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蛮书》卷4)“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蛮书》卷6)等等。“望苴子”即佤族兵,“永昌”今保山、临沧、德宏等地州,说明佤族兵在南诏政府的军队中占有很大数量,他们作战勇敢,在南诏的政权巩固和开拓疆土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上事实证明,佤族与南诏的统治者必然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根据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马曜先生说,白族老一代学者张旭曾经做过分析,指出:“南诏王室的族属可能和今天孟高棉语族布朗族等有渊源关系、“今天布朗族亦称‘乌’,与蒙舍诏同时称‘乌’,也不无关系。”[20](P444~445)经过分析,马先生进而指出:“南诏王族先为哀牢人,唐代初中期为乌蛮别种,唐代后期融合于白蛮之中”。[20](P445)这一观点是十分准确的。
近现代佤族与彝族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父子连名,尚黑崇石、崇拜葫芦老虎,过火把节等等,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与历史上他们的密切交往、相互影响是相关的。大量的历史事表明,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双向的。但从种种资料分析,佤族与彝族在葫芦崇拜这一文化问题上,可能是前者影响后者。关于“乌蛮”彝族自称为“哀牢后裔”,有学者进行这样的分析:“其一,蒙氏贵族接受了哀牢濮人中祖先来源传说的影响;其二,蒙氏贵族原本就是哀牢濮人,后来加入或是融合到社会经济、文化更为先进一些的‘昆明’族群中;其三,借助祖先是哀牢人的传说赢得世居在这里的哀牢濮人的支持,借以扩大影响,壮大势力,为征服洱海四周各诏作准备。从后来的发展势态看,蒙舍诏之所以最终能统一其他5诏,建立南诏地方政权,其中依靠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泛的哀牢濮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21](P6)这一分析非常正确,它充分说出了古代的彝族与佤族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因为这样,与彝族同语族的拉祜族也有着非常浓厚的葫芦崇拜。
布朗族、德昂族与佤族为同一个语支,这是众所皆知的。过去,人们对他们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留意不够。其实,不管是布朗族,还是德昂族,他们与佤族一样,都有“葫芦(器)生人”这样的说法。这就进一步说明“司岗里”文化不仅仅是佤族一个民族的,而且也是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同时,这一情况也进一步说明佤族的“司岗里”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