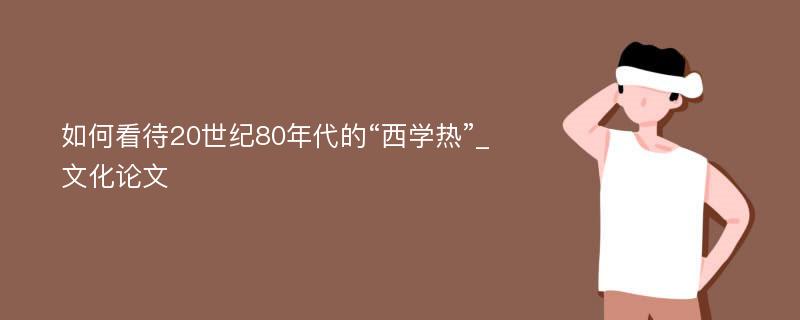
怎样看待八十年代的“西学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论文,怎样看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问题,近年来似乎又一次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若冷静客观地审视一下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状况,那么,应当承认,这种对话并非十分对等(注意:是“对等”,而不是“平等”),即从总体上来讲,从西方引进、输入得多,而向西方传播、输出得少。面对这种中西文化对话中的“不对等”现状,知识、文化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文人对此进行了反思,认为80年代我国大量译介、引进西方学术文化,一则使中西文化对话出现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不对等”),使“全盘西化”论得以卷土重来,严重地干扰和冲击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建设;二则在引进西方学术文化时多停留于盲目地照抄,机械地模仿、生搬硬套地“移植”的低水平上,因而这种“中西对话”的结果主要是消极的,失败的。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单向侵入的消极影响,他们中一些人打出了倡导新国学(或新儒学)、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旗帜。这样,80年代开始的中西文化活跃地对话、交流的态势似乎有终结、中断的危险。在此意义上,对80年代中西文化对话的得失功过进行恰当的评价,就成为这种对话能否继续健康地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
首先,80年代中西文化的对话究竟是“不平等”还是“不对等”?
笔者认为,主要还是不对等,而不是不平等。理由是:
第一,不对等主要涉及对话、交流的客观态势;而不平等则侧重于一种主观的态度,如对对话的另一方采取尊重还是歧视,居高临下还是低三下四,傲慢还是谦虚,热情还是冷淡,真心诚意还是虚情假意,如此等等。以此尺度来审视80年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状况,那么,只要不抱偏见,就应当肯定,那段时期,在中国大量译介、引进西方学术文化之时,西方学术文化界总的说来并未抱有歧视、居傲、称霸的态度,更未趁机进行文化侵略或掠夺。换言之,中西方在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时,双方并未在主观上采取不平等的态度。虽然事实上无论从数量、质量、范围、影响等方面双方的交流都处于非常不对等的状态。
第二,这种不对等状况的存在,不是由对话双方中任何一方主观上故意要造成的,而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众所周知,我国在“文革”前17年,已采取了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学术文化限制和封锁的策略,这种闭关自守的文化态度在10年“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一种不亚于本世纪初义和团运动那种极端保守、落后的文化上的排外倾向;与此同时,随着政治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达于顶峰和中国自封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自大狂热,文化上的华夏中心主义又死灰复燃。这样一种落后乃至反动的文化态度造成了对西方学术文化(除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外)的全面敌视、恐惧与仇恨,以为西方一切学术文化都是“反华”的,都是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与“和平演变”制造舆论的,因而应当一律加以排斥,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渠道完全被阻塞、隔断了。不仅我们对西方的文化、学术状况一无所知,而且,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也极为隔膜。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一结束,三中全会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以及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行,激发起一股极为强劲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学术文化中的好东西的愿望乃至渴望。这与经济文化相对处于优势的西方人民和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的要求(有时带有某种神秘、猎奇的成分)相比,显然是不对等的。西方人了解、学习中国的心情相对不那么紧迫这恐怕是一个铁的事实。这正是造成对话事实上不对等的社会基础。因为这种不对等,是一种文化需要的不对等。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同样,在中西文化对话、交流中,对与对方交流的文化需要及其迫切程度,直接产生对话的内在动机和实际行为的迫切程度。正因80年代初,中西方文化对话处于需要的不同状态、水平和程度,最终导致对话中事实上的不对等。这是由中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情势决定的,而不是哪一方的主观意愿决定的,因此不能说“不平等”。
第三,经过长达30年的隔绝,中西文化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应当承认,在70年代后期,由于“文革”的浩劫,中国文化学术同经济一样,处在一个极度萎缩、破败、倒退的状态,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前就已日益猖獗的“左”的路线,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狠抓“阶级斗争”,把学术文化完全政治化、工具化,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受到重重禁锢;“文革”中这种情况更为恶性发展,“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把中国文化学术推向绝境,什么“批林批孔”,什么“评法批儒”,什么“三突出”,统统成为“四人帮”摧残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学术的手段。而西方文化学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来,总体上是向上发展的,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我国文化学术在“文革”中急剧走向“荒漠化”之际,西方文化学术反而在走向后现代过程中显得异常活跃,新的思潮不断涌动,有不少新的创造与发展。这与当时中国濒临危机与崩溃的文化学术相比,呈现出极大的反差。
平心而论,这种反差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也是质量上的。诚然,文化学术的一部分具有意识形态性,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共通的,超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文革”结束时,中国真正的文化学术几乎不存在了,仅剩的一点也是经过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扭曲和变形的;而当时西方的文化学术,即使撇去其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那部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蓬勃发展的,就其可与我们沟通的那些部分而论,显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其中不少方面(如经济文化、管理文化等)具有很大的先进性。换言之,70年代末,当我们准备开始同西方文化学术对话时,我们虽然处在相对落后的低位上。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这样一个对话的起点,决定了对话在质上是不可能对等的,决定了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对当时较为先进、发达的西方文化学术的基本态度和任务应是广泛深入地了解、学习和吸收,而主要不是向西方输出与传播,因为那时可借以输出和传播的,比西方先进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就此而言,那个特定时期中西文化对话只能是不对等的,但不能说是不平等的。
二
80年代这种不对等的中西文化对话,其过程和结果倒底如何?应当怎样给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当今学界另一个分歧颇大的问题。而这一分歧,实际上直接关系到整个90年代乃至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战略与对策问题,因此,不可不搞清楚,不可没有明确的态度与见解。
依笔者愚见,这种“不对等”的中西对话,其过程与结果也是“不对等”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复苏与发展来说,这是一种总体上利大于弊、收获大于损失、积极成果大于消极影响的“不对等”。
事实上,80年代确实是西方文化输入、引进得多,而中国文化输出相对要少得多;其结果自然也是我们从西方文化中学习、吸收得多,而西方从我们这儿学到的则少得多。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是如此。这种“不对等”是从中西文化80年代对话的结果而言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种收获,文化学术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一部分人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80年代我国大量翻译、介绍、引进、传播西方文化学术,特别是西方观、当代(近百年来)的文化学术所形成的“西学热”,一是在价值观念上造成了盲目崇尚西方(特别是现当代西方)文化学术的崇洋心理,为现代的“全盘西化”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文化温床,有可能使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迷失方向;二是客观上干扰、冲击、削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使本土文化有断“根”的危险。
应当说,上述两点看法,虽不能说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但总体来说,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是把问题看得太重了。实际上,“全盘西化”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占有过主流地位,“五四”与30年代虽有人两度提出,但都未被主流文化所接受,更不必说付诸实施了。至于80年代,确实又一次出现了译介、了解、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学术的热潮,但这是“文革”之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特殊条件和情境下的产物,既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有其内在需求,并非外部强加于中国的。而且,这种引进与借鉴,是以中国改革开放、求得经济文化的全面振兴为大背景的,其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达到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宏伟目标,所以,从根本上说,这里不存在“全盘西化”的问题与可能性,一切对西方的学习、借鉴与对话都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下进行并决定取舍的,个别人即使真有“全盘西化”的思想与言论,也不可能整体上改变这一大的对话框架和影响;而且“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中有与国际、与先于我们现代化的西方的某些通则、尺度接轨的问题,有学习西方的内容,但并非一切都要“西化”。现代化还有民族特色这一面,而中国正以鲜明的目标与口号寻求着这种民族特色,这就抽去了“全盘西化”论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因此,可以说,80年代,“全盘西化”论在中国并无市场,并未因为引进、借鉴西方文化学术的“热”而形成有影响的“全盘西化”思潮与价值倾向。把那时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学术的“不对等”对话说成滋长了“全盘西化”的倾向至少是一种缺乏根据的夸大。
至于说80年代的西学“热”冲击和削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恐怕更有点杞人忧天。向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超稳定结构而著称于世的,它几千年来绵延至今,渗入中国人的骨髓、血液,根深蒂固而任何外部力量难以动摇。魏晋时期佛学的传入与吸收,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大开放,明代与世界文化的广泛交流,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制输入与自觉引进同时并存,都不仅没有使中国文化学术被“西化”,或被削弱以至失去根基,相反,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开放,每一次对外来文化的较大吸收,都极大地丰富、深化,加强了本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增添了新的活力,强固了它的根基。80年代的西学热亦不例外。诚然,那一段时期从表面上看,似乎从书刊杂志到学术机构,从精神文化生活到日常生活中,西方文化、学术的影响随处可见,而传统文化一个时期则有被冷落之感。但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实际上,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与研究同样也出现了新局面,在“文革”中被作为“封建主义”货色而打入冷宫的传统文化在整理、出版、研究、传播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成就,10年的成果恐怕远远超出建国27年来的总和;传统文化的复苏同样也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旅游文化),时时能为人们所感受到。尤为重要的是,现当代西学的引进与借鉴,极大地拓宽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使他们获取了学术、文化研究的种种新思路、新观念、新方法,这对包括传统文化学术在内的人文科学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借鉴西学下,我国80年代后期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美学等各个学科或跨学科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或进展;同时知识结构较为合理、中西文化均有一定素养的新一代人文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西学热”背景下健康地成长起来。因此,把80年代的“西学热”同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进而视为洪水猛兽,视为会切断中国文化之根的一把刀子,这实在是一种迂腐之见,一种文化短视,一种当代“恐‘西’症”。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只要看一看近百年来一些国学大师的情况就可明白了。从梁启超到王国维,从陈寅恪到熊十力,从汤用彤到钱钟书,他们总可以说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坚了吧,但他们哪一位没有坚实的西学根底?!而且,他们哪一位治国学的成就,不是同他们借鉴西学的眼光与方法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王国维如果不借鉴、吸收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思想,会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古典文学研究的传世名作吗?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的研究,几乎找不到西学的引文,但字里行间,却又处处透露出西学的眼光、思路、方法的影子,中西文化之融合达到糖溶于水的不露痕迹的境界。钱钟书先生一部《管锥编》,若无西学作为参照系,其国学研究的成就也必得大为逊色。可见,我们对西学的引进和借鉴,只要立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不但不会冲击、削弱,反而会促进、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因此,从长远来看,80年代的“西学热”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是利大于弊的。
三
在如何评价80年代中西文化对话中“西学热”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学界存在不同意见。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不断有人批评“西学热”中出现的囫囵吞枣、机械模仿、生搬硬套、做表面文章等不良现象,诸如“西方一百年的现代主义思潮、流派,我们十年就匆匆全部模仿、演示了一遍”,“满足于做‘二道贩子’,间接贩卖西方文化学术的‘二手货’,”“新名词大换班,新术语狂轰烂炸”之类说法,就是对这些现象的尖刻讥讽与挖苦。进入90年代后,更有学者从反思角度认为80年代的“西学热”是走了弯路,应当基本否定,并从中引出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对于这种看法,笔者同样持有异议。
首先,80年代的“西学热”是我国对外开放(包括文化学术开放)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出现上述种种现象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横加指责。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文革”闭关锁国10年之后才起步的。为了追回失去的岁月,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了解、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学术的愿望与要求极为强烈,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这种内在需求一旦释放,便成为“西学热”得以兴起的强劲的内在动力,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春风,更是成倍地激发和强化了这种动力。于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学术便从各个方向如潮水般涌入我国,更确切地说,是我们方方面面的内在需求打开了闸门,主动地迎接这股西学潮流的进入。这就难免泥沙混杂,良莠不清,一古脑儿全盘接纳下来。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文化开放的初始阶段都是普遍存在,难以避免的。
而且,由于中西文化对话的长期中断和阻隔,存在着引进与借鉴的时间差。也许在西方早已过时的东西,在中国还从未听说过,或者在西方已不流行而在中国正有借鉴的迫切、现实的需要,这样,从不同需要、不同渠道以“共时”形式引进的西方文化学术,实际涉及的时间跨度却长达一个多世纪,即呈现一种历时排列的形态。这正象接受美学创始人所作的一个比喻:夜空中灿烂的群星以共时形式呈现于人类眼前,但实际上各星球与地球的时距都是以多少万光年计的,它们在时间轴上是以历时态排列的。以美学为例,80年代我们几乎同时译介、引进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美学论著与最晚近的法国德卫达的解构主义论著和伊格尔顿·杰姆逊的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论著(后边几位都还健在并继续着他们的学术活动)。这就是短短10年引进西方一百年文化学术思潮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文化学术界能在10年把西方走了百年的途程压缩匆匆走一遍的客观根据。
“西学热”的中坚力量自然是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兴趣与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他们从各自的所长、所专入手,引进、译介的东西自然也是极为多样、丰富的,时间跨度上也往往各各不一,这也是80年代“西学热”中似乎缺乏重点、有点无序甚至乱套的重要原因。更应指出的是,当时中国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并不合理,长期与外部隔绝使多数人的外语水平很差,无法直接阅读、更不必说翻译国外文化、学术著作了,而且当时国内外文图书资料状况也不佳,新书甚少。这就给“西学热”带来了许多客观上的困难与局限,其中之一就是译介队伍弱、翻译水平不高,虽然从绝对数字上说,80年代译介西学论文著作不算少了,但质量上相对差一些,而就我国现代化的新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来看,则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还是远远不够的。正是中西对话中这种主体方面的相对落弱和局限,造成整体上满足不了学习、借鉴西方的巨大、紧迫的需求,于是“西学热”中的“二道贩子”、“间接引进”、东转西抄、以意为之甚至想当然地误读错解等现象纷纷出现了。
至于向西方学习、借鉴过程初始阶段的机械模仿和生搬硬套,更是难以避免的。模仿是人类的天性,求知与实践活动都是从模仿开始的。80年代“西学热”中,引进了不少东西,开始不会应用,就只能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只有通过不断地模仿、尝试、失败、成功,才有可能逐渐超越模仿,把人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80年代出现的种种机械模仿、新名词术语层出不穷等现象不但不奇怪,实乃出于必然,是借鉴西学初期的必经阶段、幼稚阶段,不经过这一阶段,是不可能走向成熟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反思自己过去走过的历程时,当然应当正视那时的不足,但对初学阶段的幼稚,不应横加指责、冷嘲热讽。
其次,80年代的“西学热”中,上述这些负面现象毕竟还不是主流,主流应当说还是功大于过,收获大于失误的。80年代翻译、介绍进来的西方文化学术,在数量上恐怕远远超出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这使得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大开了眼界,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学术视野和创造性思维的空间,使他们在观念、理论、方法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或发生着由传统向现代的重大转折,许多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作出了前人未做出、自己过去也不可能做出的成就。每个过来人恐怕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有这方面的切身体验。80年代“西学热”的文化氛围对于造就新一代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人文知识分子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90年代一些青年学者对80年代的“西学热”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打出“后现代主义”的旗号来反对“现代主义”,而且提倡新国学与本土文化,然而他们忘了支撑他们主张的理论基础还是西学,甚至他们频繁使用一套话语、术语,也来自西学,没有受到当初西学的直接、间接的影响,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成了一个难解的“悖论”。总起来讲,80年代文化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是建国以来文化学术最繁荣、成果最卓著的时期。这当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中西文化对话的展开、“西学热”的兴起,乃是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因素。
再次,面对现实,面向21世纪,在新旧世纪之交,在中国快步走向四个现代化、中国文化加速与世界文化汇合之际,中西文化的对话不仅不能削弱,还要大大加强。
在我看来,80年代的“西学热”虽然引进了不少东西,但面向未来,这种引进实在还是太不够了。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量上,我们过去引进的东西数量还不大,引进的范围还较窄,很多东西甚至还未触及,而且西方文化还在不断发展变化,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研究;二是质上,80年代不但译介方面存在不少质量问题,而且总体上说是译介、引进得多,研究、消化得少,不少东西引进了,热了一阵很快就过去了,未经细细地咀嚼、分析、批判、吸收,不少东西仍然外在于我们。要说80年代“西学热”的不足,这恐怕是最主要的不足。
我们作为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不但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而要借鉴西方文化、学术中一切好东西,而且有义务和责任研究、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以,过去译介、引进、研究、借鉴、吸收西方文化学术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今后不但要继续进行下去,还要大大地加强译介与引进;同时不能满足于译介与引进,要把更多的力气花在梳理、研究、消化、吸收上。这样,中西文化的对话,才能有效地进行下去,并逐渐提高一个层次,从“不对等”走向“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