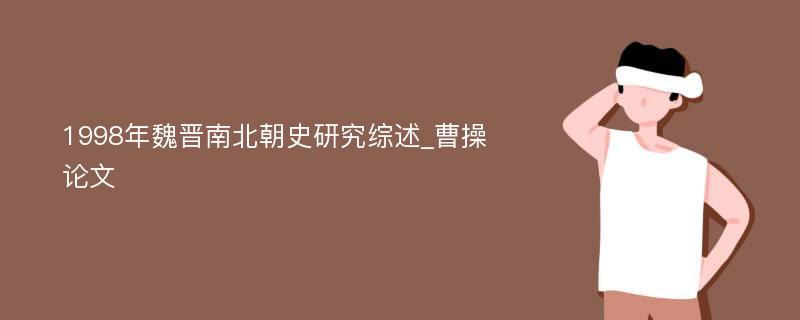
199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有关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中不乏一些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该年度出版的学术专著主要有:高敏的《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朱大渭的《六朝史论》(中华书局)、陈长琦的《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和朱大渭、刘驰、梁满仓、陈勇合著的《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据统计,1997年11月到1998年10月这一年来的学术论文,除考古方面约40篇文章外,大体有180 余篇论文探讨了本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现分以下支目择要作概略介绍。
一 政治史·制度史
对本时期制度史的研究,学术界颇为关注,成果颇丰。在军镇制度研究方面,高敏《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史学月刊》1998 年第1期)论述了十六国时期军镇制度的特征、形成过程、发展阶段、表现形式和实行原因等问题。认为军镇制度是当时州郡制和单于制统治形式之外统治居民的一种制度,特点是合军政于一体,并以军事统治形式代替地方行政系统。此制萌芽于十六国前期。十六国时期,由于以部落形式存在的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为了实行胡汉分治和加强军事制度等需要,大都同时实行州郡制、单于部落制和军镇制三种统治形式。但是,同后来的军镇制度相比还有明显的不同:这时的军镇,多与州郡并列;其所统居民,多为兵户;军镇多是临时性的,并未固定化;从本质上说是维护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利益的工具。因此,这时的军镇制度,充其量只能说是带有后来军镇制度的某些因素,或者说是军镇制度的萌芽期。到十六国后期,军镇制度已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盛行于后秦、西凉、北凉、南凉、夏等国。以军镇统民方式还有另一种形式即护军制,此制始于曹魏,到十六国时期已正式制度化和普遍化。前凉、前秦、后秦、西凉、北凉、南凉、夏等国均施行。护军机构一般分为与郡平行和与县平行两个等级,其所统大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有军镇与戍所的作用。梁伟基《北魏军镇制度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 年第2期)具体考察了北魏的军镇制度,认为北魏军镇建置原因包括强化占领区之军事控制、安置归附之少数民族、国防治安之考虑等。军镇皆非地方民政单位,而是地方军政单位。镇民由军府统帅,其成员有鲜卑拓拔部成员、各地之移民、罪犯、少数民族等构成,可以说是良贱混杂、胡汉混杂。军镇之性质,具有军事性与羁縻性之二重性格。北魏末年虽改镇为州,但是军镇仍然存在,即使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亦复如此。
在北朝军制研究方面,阎步克《周齐军阶散官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 期)对北朝军阶散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变化进行了系统的爬梳整理,对比了北周、北齐军阶散官制度的异同优劣后指出西魏末年以《周礼》改制,颁“九命”而建“六官”,与北魏相比,西魏“九命”中军号和散官排列整齐均匀,其中包含了两个进步:一是军号序列与散官一致起来,每“命”两个军号,分别构成上阶和下阶;二是散官也形成了首尾完整的序列,且与军号呈一一对应之势,这个发展,构成隋唐文武散阶制度的先声。在实践上,北魏末年“皆以将军而授散职”的军号和散官同时加授的现象比较普遍,东魏、北齐对这种“双授”现象着手整饬,成绩卓著,使泛滥于时的“双授”骤减。北齐河清官品中的军号序列也呈现均匀而整齐的分布,这样东西政权都出现了军号序列化与官阶一致化的进步,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来自北齐对西魏、北周军号序列的启示与借鉴,表现出见贤思齐的风格。这一点对讨论隋唐制度的渊源问题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考。
在南朝军制研究方面,张文强《南朝军制述略》(《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1 期)指出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为都督与州郡两个系统。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为军、幢、队、什、伍等。兵种主要分水、步、骑。中军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训练一般由各方镇都督刺史主持。当时的兵器是传统的弓、弩、刀、剑、矛,其制造由少府所属的尚方负责,保存管理的机构有南、北二武库。
在职官研究方面,张金龙《北魏御史台政治职能考论》(《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 北魏御史台的主要政治职能表现为五个方面:弹纠禁内(殿中)的非违行为;弹纠官吏贪污受贿、残酷刻剥的行为;弹纠官吏以良从贱、抑(掠)良为婢的行为;弹纠官吏淫秽不道;弹纠窃阶盗官、贪昧苟进之徒等。列举其辅助政治职能为五个方面:出使纠劾、行刑;讨伐叛逆;出任它职;监(营)护丧事;谏诤等。影响御史台发挥政治职能的因素有:君权;御史台长官所享有的特殊礼仪;宰相机构尚书省和京师行政长官洛阳令;御史台长官的品行与素质等。张旭华《南朝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及其作用》(《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南朝的九品中正制沿袭晋制而有变化, 中正的组织机构不断扩大,州郡中正的选任标准与吏部是一致的。南朝的清议虽然上承魏晋,但也有显著的变化。清议的性质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惩罚,而是逐渐具有法律效率的科条;清议的范围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清议的威力与作用大为增强。南朝中正品第与吏部铨选的关系更加密切,中正品第仍是吏部铨选的重要依据;在选官过程中,中正品第与所授官职相一致,是吏部官员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维护和巩固门阀制度的重要支柱,尤其在梁、陈时期,九品中正制与官班制密切配合,它不仅确立了以上品和下品为区分标界的流内与流外两大任官体系,而且依照门阀序列和等级高卑,严格区分出不同的任官次序,使尊卑有序,等级分明。同时,中正品第与官职清浊的结合也更加紧密,在维护门阀世族的特权地位和确保清浊分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论题。王永平《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 期)指出,汉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革的时期,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统治阶级上层不同利益集团升降浮沉的变迁。汉末大乱,乘隙而起的曹魏王朝中断了具有深厚历史积蕴的儒学世族正常的发展进程。不过这只是暂时现象,经过大约四十年的准备,儒学大族的复起之势已明,并向曹魏皇权提出了挑战,其标志便是景初二年末围绕魏明帝顾命大臣人选所展开的斗争。据考,曹睿病危之际本欲“以亲属广据权势”,并付诸实施,但短短四天之后便废了宗室顾命集团,代之以宗室曹爽和大族领袖司马懿共同辅政。明帝改易顾命人选,并非自愿,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族代表。此事虽微,然意义重大,它预示着未来儒学世族之全面得势和魏晋更替的历史走向。张承宗《三国“吴四姓”考释》(《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对“吴四姓”进行个案研究, 指出“吴四姓”与“吴郡四姓”,并不是一个概念。“吴”是指孙吴统治全境,“吴郡”只是其中一个区域。史书除了“吴四姓”、“吴郡四姓”之外,还有“吴旧姓”的提法。“四姓”指张、朱、陆、顾,特点分别是文、武、忠、厚。从时代来看,“吴四姓”形成于三国东吴黄武之时或者略后。在排列顺序上,张、朱在前,陆、顾在后。东吴末年孙皓对陆凯上书陈事说到“顾、陆、朱、张”,其排列之变化反映了顾、陆诸人的地位之上升。杨洪传《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指出,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个特殊阶层, 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辩”,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张琳《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认为,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 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极盛——式微的发展过程。这即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体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二 经济史·民族史
对本时期经济史的研究,本年度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农业方面,杨际平《从东海郡〈集簿〉看汉代的亩制、亩产与汉魏田租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根据新近出土、 刊布的汉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前后、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以前的东海郡某年《集簿》,推算出汉武以后采用240 步为亩的亩制是当时民间通用的亩制。推算出汉代平均田租额是3升上下。 当时的亩租都是以升计,而非以斗计。曹魏时期的田租,有的学者认为是“亩四升”,有的学者认为是“亩四斗”,此所谓“升斗之争”,由此可得到解决,即曹魏时期的田租应以“亩四升”为是,西晋时期的田租,亦为“收租四斛”。此外,作者推测汉代平均亩产,大体上是平均亩产1石上下, 也就是亩产70斤左右(市制),约为唐朝的一半。李宝通《北魏太和十二年李彪屯田史实略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 期)考察了北魏初至太和年间屯田设置的渊源流变,认为北魏前期屯效最著者当数薄骨律镇刁雍所修之水田。李彪屯田的史料,《李彪传》资料当较《食货志》原始,《传》载彪所上封事七款,很可能即源于李彪本人或“有司”之实录。李彪屯田兴置于西北,时间是太和十二年和次年八月。屯田经济对发展西北农业有巨大作用。屯田的生产者来源有迁移民户、国家编户亦即州郡户,此后,屯民实已构成诸镇“镇民”的主体。屯田最终难以逃脱受地主土地所有制侵蚀私有化的命运,不过直至魏末,屯田收获的大部分仍为封建政权所夺,边镇屯民的私营经济十分薄弱。在中原地区广泛推行均田制、均田农民对封建政权的人身依附关系较私家佃农已有所减轻的历史条件下,遭受强制束缚的西北边镇屯田农民反抗情绪空前激烈。中原地区与西北边镇均田与屯田的异轨,应可视为北魏末年“六镇起义”的基本原因。
商业史研究方面,张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7期)认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迭遭战乱,社会动荡,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在北方地区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逐步好转的曹魏、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秦以及北魏孝文帝改制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北方商业曾出现过三次发展与兴盛时期;而在晋末永嘉之乱、淝水战后前秦政权瓦解以及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和北齐、北周相争的年代里,北方商业也出现过三次破坏与衰落时期。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社会经济并未被破坏到难以恢复的程度,商业复苏的生机亦未被斫丧殆尽,它在重重阻碍下艰难发展,并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张旭华、王海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都会的兴衰》(《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具体考察了北方五个著名商业都会即洛阳、 长安、邺、平城、晋阳的兴衰史,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黄河流域屡遭战乱,人口丧亡,生产废弛,城邑萧条,致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因社会的激烈动荡而陷入极度的困境,北方的商业都会也因战乱的影响时盛时衰,兴废无常,经历了极为曲折的发展道路。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但同时也孕育着统一的因素,在北方重新统一和社会比较安定的各个历史时期,一些惨遭破坏的商业都会又会神奇般的迅速恢复,并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重新发展而又趋兴盛。因此,综观魏晋南北朝经济与商业发展史,尽管有种种困难与阻力,但生产力的发展冲破重重障碍,曲折向前,呈现出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的循环规律。
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刘汉东《水陆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魏晋南北朝时期水路交通比较发达,长江作为水陆交通的主干,贯通上下万里,上游的成都和下游的扬州为主要商业中心。黄河是北方水路交通的主要动脉,河面宽阔,水量充足,大部分河段水流缓急适宜航行。珠江水系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和北方地区的商业贸易相联接,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和外洋商品的进口。水路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比较突出的有西晋的连舡,方百二十步。水上运输工具和航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型内河与海洋船的使用,使商品货物运输量大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路交通的功能基本上为行旅来往、商贩贸易、漕运租粮、军事行运等项。水路交通比较发达,航程远,运输量大,到达的商业城镇多,因而对于与交通运输相关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商贩贸易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社会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北方,水路交通是重要因素。 汪波《东魏北齐时期的晋阳交通贸易》 (《晋阳学刊》1998年第4期)认为,东魏、北齐时期,晋阳的对外交通非常发达, 晋阳通往邺都、洛阳、长安、平城等地的路线繁忙异常,因其交通发达和特殊的地位,晋阳的贸易也很繁荣。交通发达、贸易繁荣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晋阳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本时期民族史的研究,也有一些文章涉及。孔毅《北魏前期北方世族“以夏变夷”的历程》(《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 期)首先指出了北方世族在“华夷之别”面前的痛苦与抗争。北方世族在经历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之后,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以夏变夷”的道路:在文化上,让拓拔鲜卑“知书”,使拓拔鲜卑开始踏上汉化道路;在政治上,将拓拔鲜卑的国家政权汉族模式化,并改造其政权的种族构成;在生活习俗上,以汉族的礼乐文明去替代鲜卑族的夷礼胡乐。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北方民族大融合进程的推进主要依赖于北方世族“以夏变夷”的信念和他们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们以巨大的代价为孝文帝改革铺垫了路基,为以后国家统一时代的到来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秦永洲《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文史哲》1998年第1 期)阐述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新”,正统与僭伪之争成为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华正统之争,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六国前期,“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第二阶段十六国后期,自建年号,自为帝统;第三阶段,南北朝时期,南北同为邻国,平等对话和北方系统地再造正统阶段。正统之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华夷君长,谁应为帝;南北君主,谁得天命;南北政权,谁是华夏文化中心。入主中原的夷族“假中国礼乐文章”,接过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汉族地主的导引下,再造中华正统,使中国文化以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形式发展下来。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的积极意义在于:首先,使国家统一自始至终成为统治者的历史责任和心理压力;其次,该时期的正统之争是在奉行同一种文化的前提下,在华夷之间进行的,它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夷族文化的吸收和自身的更新、延续,使其在经过了几百年多民族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之后,又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登上一个更新的台阶。再次,它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原正统的存在,召唤着周边各族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中原王朝可以灭亡,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却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在世界历史上消逝或者间断。张雄《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与汉化趋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具体考察了魏晋以来历成汉、前赵、 后赵、魏、前秦、北魏、西魏诸朝,巴人在巴西、汉中、关陇、河东、河北的迁徙及其在北方民族大融合中的汉化趋势。从西汉末期开始出现汉化趋势的巴人,三国时多见于巴西、汉中,并北迁关陇与氐人相杂居。西晋后期,以李氏为首的巴人,与汉、氐诸族从关陇南迁巴蜀,建立成汉政权,后来与梁、益二州的獠人相杂居。在北方,巴人从刘聪实行胡、汉分治起,成为“六夷”之一。前赵、后赵、魏分别徙诸族人口以实京师,巴人与诸族被频繁迁徙于关中、河东、河北之间,或参与反抗而受残酷镇压。在相同的境遇中,与汉、匈奴、羯、氐、羌、鲜卑一起,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在这个过程中自身也逐渐趋于汉化。北魏后期,巴人仍见于渭水左右及丹江上游,商洛则是巴人的聚居区,并表现了明显的汉化趋势。
三 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历史人物
社会生活研究方面,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对饮食生活专门研究, 指出食肆行业是指将各种主副食原料为经加工、烹饪成为饭食、菜肴以向顾客售卖的各种店肆,是融生产、流通与服务于一体的饮食行业的核心和主体,在汉唐时期包括各种饼肆、饭店和熟食店铺等。战国秦汉以来的饮食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第一层次的饮食市场——饮食原料市场虽然也有过一定的波动和曲折,但基本上是一直在向前发展着,即使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政治动荡、战乱频繁、经济破坏的时代,饮食原料市场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而第二层次的饮食市场——饮食成品市场却经历了比较大的起伏和波折,在汉代已经比较兴盛的饮食成品市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显著下降,呈现严重的萎缩和萧条景象,与其时饮食原料市场的发展状况不相一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饮食成品市场的盛衰荣枯不仅是一个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政治和经济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可以看出,在汉、唐时期这两个层次的饮食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市场则呈现两个层次盛衰不衡的情形。在婚姻研究方面,谢宝富《北朝魏、齐、周宗室女性的通婚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 北朝魏、齐、周各代宗室女性的通婚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北魏太武以前,宗室女性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通婚频繁。太武以后,北魏宗室女性与南北士族的通婚逐渐频繁。东、西魏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和亲政策,同时将相子弟亦是东、西魏公主重要的通婚对象。北齐、北周宗室女性的婚姻主要是与北镇军功集团、武川系军功集团之间进行的,与汉姓高门通婚的很少。
思想文化研究方面,牛润珍、杜英《十六国史官制度述论》(《齐鲁学刊》1998年第4期)认为, 十六国时期由于五胡君主的“正统观”和“汉化”意识,使汉晋以来史官制度得以传承。因各国民族、政治、地域情况不同,史官制度出现异变,形成三种类型:复汉型,以刘汉为代表,史官制度与两汉相似;魏晋型即著作官制,置著作官者有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燕、赫连夏、后凉等;诸侯国型,史官及记事制度类似春秋列国,但又带有地方割据政权的色彩如前凉、成汉、西凉、南凉、北凉、南燕、北燕等。魏晋型居主导地位,其兴替盛衰构成了十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主线。官方史学仍是十六国史学的主流,所撰国书主要是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内容很注意反映本民族的情况,这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亦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意识,这是十六国官方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在法制史研究方面,张建荣《试论〈晋律〉的刑制特点与理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 期)分析晋朝《泰始律》的刑制特点是:法律渊源不承魏制,而承汉制;法律体例愈趋精细、完善;法律编纂力求去苛秽、存清约;法律形式采取律令结合;刑罚制度上坚持不复肉刑;刑法理论上独特创见。张斐在刑法理论探讨上的杰出贡献是:阐述新律体例及其立法精神;划分新律中有关概念与界限;强调用律须慎变审理;阐述新律的刑罚制度及量刑原则;区分“事状相似、罪名相涉”的界限;强调“断狱应察情”;强调善于区分情节,合法适用判例;强调执法的原则和要求。
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度的论文,对三国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仍为史家所关注,张作耀《曹操军事思想十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6期)和《论曹操的无令弱民兼赋思想》(《文史哲》1998 年第4期)分别论述了曹操的军事思想和经济理论。 前文概括曹操的军事思想包括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先计而后动;将贤则国安;重赏明罚;礼不可治兵;兵无常形,尚奇而贵诈;力避多方面作战;重地势而不以险固为资;用间重密,利用矛盾;固粮于敌等十个方面。后文论述了曹操的“无令弱民兼赋”思想,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建安九年曹操控制河北之后,发出抑兼并令,着力抑制豪强兼并土地;减轻农民赋役负担,恤民疾苦;改革推广新的税制,以租调制代替两汉时期的租赋制等,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曹操抑制兼并的理论来自儒家思想。重兼并之法的现实意义在于抑制豪强、争取民心,但曹操的所谓抑兼并,并没有治本的措施。曹操颁行规定性的租调制,即“田租亩四升,户调绢二斤、绵二斤”,是从建安九年九月“公令”(即《抑兼并令》)开始的。曹操租调制减轻了河北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河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它对后代赋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蓝本。柳春新《曹操立嗣问题考辨》(《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 期)则考证了曹操立嗣问题,得出结论是:曹丕、曹植争嗣起于建安十七至十九年间,原因是曹植的文才引起了曹操注意;同时,曹操在立嗣观念上重视政治才能,颇为轻视“立子以长”的宗法制传统和原则。在此之前,曹丕的世子身份和实际政治地位,曹植无法比拟。曹操有立曹植为嗣的想法,却对其政治抱负和才能不敢自信。就才能而言,曹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一种文才和论说之才,能否转化为实际政治能力尚属疑问,为此,曹操对曹植及曹丕进行了考察,结果曹植的政治抱负和才能终究不能令曹操放心,于是曹操转而征求各下属机构中僚属的意见。崔琰、贾诩等人支持曹丕的意见影响了曹操的判断,尤其是舍长立幼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迫使他放弃了立曹植为嗣的想法。另一方面,曹植的支持者丁仪的政治表现、杨修的复杂背景对曹植争嗣造成了不利影响。立嗣是一件最重要的“家事”,其中充满了感情因素。曹植本来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经过曹丕的种种努力,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文史哲》1998年第6期)认为, 司马懿青少年时代曾经学习儒术,但已于建安后期完成了向黄老形名派官僚的转化。他与曹魏王朝的关系,经历了由消极回避,到积极效忠,而最终反叛夺权的变化过程。曹魏政变,是生存逼迫下的被动造反。高平陵政变虽然结束了曹氏的政治统治,但是作为建安名士的政治代表,司马懿上台后所改变的,仅是正始名士早熟的玄学“改制”;所恢复和发展的,是曹丕、曹睿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黄老名法与儒术的结合,使魏晋之际的官方意识形态打上了明显的“礼法”烙印。郑欣《何晏生年考辨》(《文史哲》1998年第3期)指出,关于玄学创始人何晏的生年,学术界已有四说,即190年、207年、193年、195年,但均有难圆之处。文章考证出他应生于194—199年之间,而最大的可能是生于196年。 方诗铭《何晏在曹魏高平陵政变前后》(《史林》1998年第3 期)从高平陵政变前后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探讨何晏的政治动态以及与曹爽和司马父子的关系。认为何晏被杀不是由于他是曹爽的死党,而是出于司马师的忌恨。何晏博览群书、才华卓绝,所崇奉的是儒家经典,其思想的主流也属于儒家。所谓参与政治上的“浮华”活动,被魏明帝“抑黜”,应是出于司马氏方面的诬蔑。何晏对曹爽执政是不满的,他所主持的选举也基本上是公正的。因此,何晏既没有完全站在曹爽一边,更不是曹爽的“腹心”。另外一面,何晏又与司马懿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思想上他们之间更具有共通之处。洪涛《尔朱荣述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2 期)就有些学者认为尔朱荣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提出异议,主张应该分析当时的农民起义军的具体情况。有些学者认为“河阴之变”摧毁了北魏中央政权力量,是导致中国北部重新分裂的重要因素,并由此认为尔朱荣是分裂的罪魁祸首。作者认为这样评价“河阴之变”是不恰当的。尔朱荣在“河阴之变”中杀了许多王公和官员,但这些王公和官员属北魏朝廷中的腐朽力量,他们是农民起义军攻击的对象,尔朱荣铲除北魏王朝这一腐败势力,客观上是为农民起义者完成历史任务。在革除胡太后、元雍这一批人之后,尔朱荣组织一个新的班子,这便是以他为首的尔朱氏集团,在中央政权较为稳定之后,尔朱荣军队东征西战,捷报频传,一改太后胡氏军队再战再败的局面。因此,认为“河阴之变”是导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的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综观尔朱荣的一生,他的长处有以下几点:善于用人;善于指挥作战;有治国安邦能力;处理问题果断神速。他的短处主要是自恃威强,骄傲大意以及崇奉占卜等。
标签:曹操论文; 南北朝论文; 东晋十六国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三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五胡十六国论文; 文史哲论文; 曹植论文; 尔朱荣论文; 北魏论文; 曹魏论文; 东汉论文; 鲜卑族论文; 淝水之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