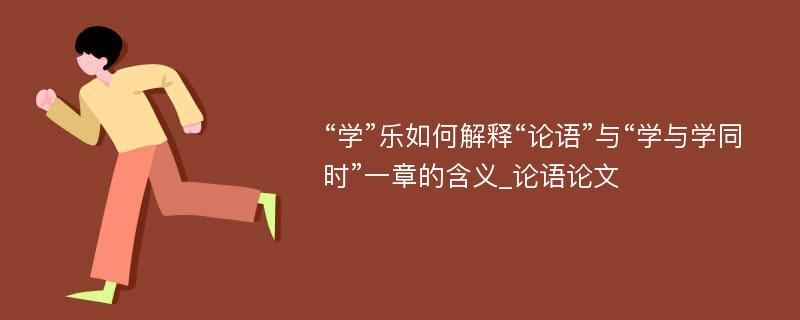
“学”何以能“乐”——《论语》“学而时习”章解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学而论文,章解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论语·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章言学而成德之义。
“时”有二义,一为适时(何晏《集解》引马融),一为时时[1] (《论语集注》)。后者义胜。
“习”,既有温习义,又有演习、践行义。
“朋”,《集解》引包咸:“同门曰朋。”朱熹解作“同类也”。其《集注》又引程子:“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1] 后者可从。此即《里仁》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之义。
读此章,有两个问题需要先提出来进行讨论:
第一,此“学”为何义?第二,“学”和“习”与“有朋而乐”、“不知不愠”有何关系?
如把“学”、“习”仅理解为知识性的学习,此“学”和“习”与“有朋而乐”、“不知不愠”便没有内在的关联性。但此章三句实一气呵成,意义连贯,不是无关的三句话。
这里关键是对“学”的理解。
孔子所言“学”,其核心是人的修养,其目的是立身成德,由此而成就人生的智慧。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 (《学而》)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2] (《学而》)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2] (《雍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2] (《子张》)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 (《述而》)
上引五章所论,既表明了这“学”的内容,同时也指出了“学”的目的所在。
“学”的内容,大体有二方面:一是“文”;一是在行为上所达成的德性修养。
“文”的内容,概括讲,即“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或礼、乐、射、御、书、数),包括现代人所说的知识、技能、技艺、文学、艺术、学术等方面。而“不迁怒,不贰过”和孝、悌、忠、信之属,则为“学”的主要内容,而“文”则只是“行有余力”才做的事情。
今人的态度,是把“学”单纯作知识技能义的理解;而这知识技能,又单纯是做功利之用的。这样理解的“学”,其实只能是“苦”,不能是“说”,不能是“乐”。
所以,这“学”,要达到悦、乐,一定要不断超越知识自身。或者说,要超越对知识技能的单纯功利性的态度。这超越的第一步,可以是对知识技能本身发生兴趣。比如,古希腊人很重视知识、技艺,它由知识技艺产生对世界的好奇、惊异,因而发展出对“真理”本身的兴趣,故有其知识论的建构,有其作为“爱智”的哲学传统。孔子亦有类似的观点。比如《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 知而好之,这类似于西方人的“爱智”。但孔子并不到此为止。“好之”,有一个对象;而“乐”则是中心之“乐”,是超越了对象性意义的“乐”。《孟子·离娄上》所谓“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也,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所说即此“乐”之义。
西方人的传统,是把这技艺知识的超越指向一知识论的系统。这其实又是一种分化。按孔子的意思,是不要抽离出一个单纯的知识系统。因为单纯从知识不能真正达到真实。但他也不是不要知识、技能。他对知识、技能的态度,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游”: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 (《述而》)
这“游”字很有意思。《礼记·学记》说:
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3]
这“游”字所标示出的为学路径是:为学既要涵泳于“艺”,又不偏执于“艺”。因为这里的“学”它不是单纯的学技术,不是单纯的学知识。由此路径,知识技艺被艺术化了。知识技艺是可以普及、可以重复进行作业的东西,而艺术则是充分个性化的产物。个性化,是使普遍而平均化的东西与个体的内在心灵生活相关联。在这里,才会有兴趣、趣味发生。《庄子·养生主》篇讲庖丁解牛,庖丁的解牛,一举一动,“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其技艺转变为完全个性化和艺术化的表现。为什么能如此?是因为他已由技而进于“道”。所以文惠君可以从庖丁的解牛而“得养生焉”——即超越技艺而进生命之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学”与生命存在的相关性。生命的开始是整体性的。我们教小孩子,讲究“寓教于乐”。小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在游戏中学会知识、技艺,他很有兴趣。小孩的学习,代表着生命的自然。大人的学习,可以说代表的是一种文明的方式。大人的学习采取的是分化的形式。知识技艺就是知识技艺,它被从生命的整体的“游戏”和“玩儿”中分离出来,成为专业,成为“正经事”。当然,大人也不能总干“正经事”,所以,我们现代人又讲究“休闲”,发明很多游戏和“玩儿”的方式。这是一种补充。还有一种补充的方式,就是上面说的“艺术”。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补充是分化了的产物,而不是生命整体意义上的“游戏”。因为,现代人已经不再能搞得清楚:究竟工作学习是为了游戏和休闲,还是游戏休闲是为了工作和学习。过多投身于休闲和玩儿的人,我们会说他是不务正业;而工作惯了的人,退休后则总会感到无所适从。同时,现代的各种艺术、游戏方式,也已经完全成了“专业”。“玩儿”的好的人可以成为富翁(但风险也很大,如从事艺术工作)。
这一切,乃是生命整体分化为对峙而互不相关的各个部分的结果。怎么办?现在的很多发明,讲究“仿生学”。孔子所揭橥的“游于艺”为学路径,就是一种真正生命存在实现意义上的“仿生学”。那就是回到类似小孩子那样的“游戏”态度中的学习方式。《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小时候的实践,为他以后的这种态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所以,表现整体生命的“学”,离不开“艺”,但又不能停留在“艺”上。人不能直接地由知识技能这条路来达到“真实”。生命要由“道”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但道不是抽象的东西,它的具体的表现,就是“德”和“仁”。故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德、仁的作用是教养。具体说,就是通过推己及人的“忠恕”工夫而达到人我的一体相通。“道”也就是“通”。“不迁怒”,是教养;“人不知而不愠”,是教养;“有朋自远方来”而“不亦乐乎”,亦属教养之事。这里所体现的,就是一个“通”的精神。喜怒哀乐一当于理,才能与人、与物相通。通而与人、与物无隔,生命乃有安顿的基础。这才有悦、有乐。孟子与子思的两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此点: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1] (《孟子·尽心上》)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3] (《礼记·中庸》)
这里的“诚”,标志着“性”的完成(“性之德”)。诚训“实”,即真实无妄。这个真实,是实现义,或实有诸己意义上的真实,而非知识意义上的真。这实有诸己的真实,是经历修养的功夫历程而达到的人己内外的一体相通。可见,通过道德修养的路,才能达到真实。经由这个安顿了生命的“道”的点化作用,那“休闲”和知识技艺(“艺”),方可转为人的真实存在的内容,从而获得其真实的存在价值。“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
《学而》首章三句话,在义理上是一体贯通的。
一个有了生命安顿基础或真实信仰的人,他的现实生活才是具有立体性、累积性(相对于消费性和平面性)和成就感的生活。
“君子学以致其道”,并不是一句空洞的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