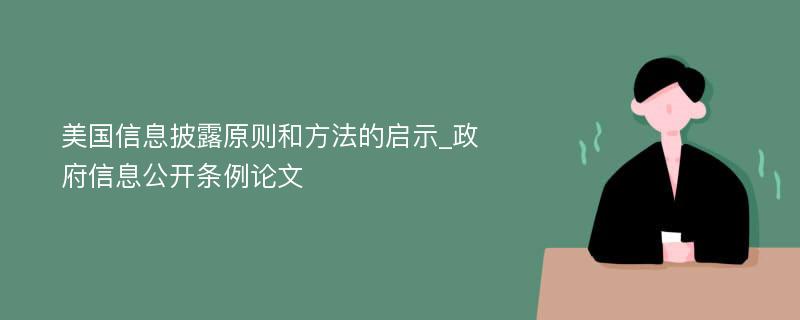
美国信息公开推定原则及方法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启示论文,原则论文,方法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作为民意的执行者,将其所掌握的信息公之于众,是法治的要素之一。诸多法治国家均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政府信息公开予以规范,如美国制定了《信息自由法》、我国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等。政府信息公开对于建设透明政府、公开政府、民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关法律规范的存在,并非就可以当然地使得规范所蕴含的价值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信息公开如欲达到建设透明政府、防止权力腐败等目的,必须具有完备的方法论体系,使得信息公开规范的价值能够在司法实践的层面得以实现,否则仍然无济于事。可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方法论,即使国务院及地方已经颁布施行了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规范,仍将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从当初制定《信息自由法》,到数次修改和其他法律的制定等,美国也经历了从规范适用的困境,到逐步摆脱,而逐渐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其民主、宪政、人权制度相适应,走出了一条方法论逐步完善之路。近来,以奥巴马为首的美国政府重新对以往政府信息公开的解释方法进行了方法论上的变革,从以往的限制性解释方法转变为推定方法(Presumption of Disclosure),这更是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推向了一个新时期,并将带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范式更新。
所谓公开推定,意指在执行《信息自由法》时,“对相关信息是否公开存有疑虑时,应优先适用公开原则。政府不应仅仅因为一旦信息披露将令政府官员尴尬,或可能会暴露政府的错误和疏失,或因为一些假设或抽象的顾虑,而不公开信息。各行政部门不得出于保护政府官员利益的考虑,而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不公开信息。”信息公开的推定应适用于涉及《信息自由法》的所有决定。而在布什当政时期,政府却被要求捍卫隐瞒政府信息的任何决定,除非这种决定缺乏有效的法律基础。①规范的适用离不开实践性的方法,因此,对属于“原则”(principle)层面的公开推定原则进行方法论上的梳理和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把握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在新范式下的方法精髓,同时对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在方法上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美国历史脉络下的方法演进
虽然在理念上,麦迪逊指出,“一个民治政府必须是一个民享信息的政府,否则毋宁只是一幕喜剧的序言,或直接就是悲剧,或两者皆是。知识将永远压倒无知。人民作为自己的统治者,必须利用知识所给予的权力去武装他们自己。”②政府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其公开、透明、有效是任何社会追求的目标,然而具体到信息公开制度,美国是一个具有相对漫长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典型国家。从美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脉络来看,其并非始终完美无缺,而毋宁是面临不断的挑战而一直处于完善的过程之中。从信息公开制度发达的美国的历史脉络,可以窥见信息公开制度发展中始终面临的规范难题。
虽然美国信息公开制度规范的体系化是以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为主体,迄今已经过1974、1976、1978、1984、1986、1996年等多次修改,但从信息公开制度的起源来看,最早的规范表现形式为美国的《管家法》(Housekeeping Act),该法授权行政机关长官控制其所主管机关的文件的散布。行政文件是否公开,在没有其他法律规定时,由行政机关长官自由决定。行政机关长官可以主张行政特权拒绝提供大量的行政文件。这种信息公开的模式,完全是一种行政权主导,明显与民治政府的理念不相吻合,因为民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应将其所掌握的人民的信息公之于众。随着民主的进步发展,美国于1946年制定了《行政程序法》,规定公众可以得到政府文件,但同时规定了广泛的限制,例如规定了因“公共利益”、有“正当理由”等都可以拒绝提供。③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从《管家法》到《行政程序法》的转变,信息公开制度在规范上实现了理念上的突破。因为《管家法》完全是由行政权控制的一种非民主的理念模式,而《行政程序法》则是一种信息排除模式,即公众有权得到政府文件,这是原则,而政府同时可以采取诸如“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等理由拒绝公开文件。从理念的层面来看,《行政程序法》的模式已经采取信息应该公开的原则,与现代民主、法治的理念相互吻合。但是从规范的角度来看,《行政程序法》的规范并不具有规范向度,因缺乏方法论而不具有可操作性与适用性,因为对于“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等概念从法教义学的角度来说,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宏大叙事。对于何为“公共利益”等涉及信息公开制度操作的环节,最终仍然操控在政府手中。这些模糊的概念反而有助于行政机关为其掌握信息在方法论上提供理由,而与当初制定该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④由于信息公开与否的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理念性的信息公开原则,并不能发挥应有的法律效果。从本质上说,从《管家法》到《行政程序法》,很大程度上是从完全的行政权管制模式到理念上公开但效果上由行政权管制的模式,只是两者规范形式上存在差别而已。
由于规范上的不可操作性,公开政府理念在《行政程序法》下也是徒有公开之“名”,而1966年制定的《信息自由法》则在规范上有了质的突破。它明确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取消了《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的诸如“公共利益”、“正当理由”等模糊概念;规定除了国防和外交政策信息等九项明确列举的不公开情形之外⑤,其他的均应当公开。这九项的明确列举,给公开原则带了操作性。因为这九项明确列举的排除情形,自身也进行了规范上的细化,如对于第(3)项“其他法律明文规定不予公开的事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是对于免于公开的事项规定得十分具体,不留任何自由裁量余地;第二是规定了不予公开的明确标准或列举不予公开事项的具体种类。然而虽然从规范的结构形式上看,《信息自由法》规定的九项免除公开事项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可操作性,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规范难题,因为法律规范不可能对诸如“国家安全”、“国家外交政策”等概念进行客观化、标准化的“数学式”界定。法律规范虽然具有操作性,但永远无法达到科学意义上的标准化,因为由法律规范自身所决定,其在操作中必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局限性和模糊性。而这些留下的“模糊地带”仍然可能成为行政机关操控的“黑色地带”,尽管《信息自由法》与《行政程序法》相比取得了进步,使得这块“黑色地带”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减了。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是现代信息公开制度普遍的理念,也即信息公开的范围是所有的信息,除非那些免除公开的例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一理念的落实,必须解决好“不公开为例外”。如果作为例外的不公开信息的范围“模糊不清”,则“公开为原则”很大程度上将受制于飘忽不定的“不公开为例外”,而无法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不公开为例外”的范围界定,由于法律规范自身的局限性等,不可能完全地客观化、标准化。因此,即使对于不公开为例外这一范围界定,仍然要通过指导性的“原则”和操作性的“规则”这一对基本方法范畴来进行架构。由公开推定原则可知,在无法知晓信息是否应当公开时,推定其应当公开,便属于解决“不公开为例外”这一规范难题时所采用的方法。
二、公开推定原则的方法层次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信息公开的司法操作,必定离不开体系化的方法论。美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变迁,也是方法论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过程。从当下我国信息公开的方法论来看,仍缺少体系化的方法论,对于公开推定原则仍缺少方法论上的认识。如有学者指出,我国信息公开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并针对“敏感信息”等概念在方法论上也认识到,“对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敏感信息的界定,具有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特征。除客观信息外,还有一定的主观特征,它是一种预先的人为判断。比如对‘可能危及’,不是必然危及,更不是已经危及。因此,行政机关对敏感信息的判断实际上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余地。”进而指出,“行政机关根据什么样或然程度作出的判断才是合理适度的”并没有作出规定。⑥以上的论述只是对问题进行了描述,却也体现了目前对信息公开在方法论认识上的贫乏。因为从美国信息公开方法论的演进可见,“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并非是方法论上的原则,毋宁是一种公开政府的理念,而作为信息公开制度的理念在方法论上并不具有规范向度和可操作性。同样,对于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并不能通过制定具体的规范来进行客观化、标准化的约束,也就是说对“行政机关根据什么样或然程度作出的判断才是合理适度的”没有作出规定,其本身并不是一个规范“问题”,也无法在规范上得到彻底的解决。其最终解决之道得寻求方法论。而公开推定则是解决这种由规范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
法治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规范作为载体。信息公开制度的实现也需要通过规范来落实,其中最核心的规范环节便是信息公开范围的确定。而根据“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所有的政府信息,并没有任何原则性的限制。在这个“所有信息”的范围前提下,才在其中存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例外。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可知,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的确定,便取决于对于信息免除公开情形的确定。这些免除信息的排除必须通过明确列举的方式来进行,而不能采取概括的方式,否则便会与“所有信息都公开”这一前提性原则产生规范逻辑上的冲突,因为在规范逻辑上,原则中的排除必须是明确具体的。如果免除信息没有方法论的约束,则完全可能出现政府通过免除事项来无限扩大不公开信息的范围,如在布什政府时期,布什政府备忘录便是通过利用《信息自由法》的免除事项来扩大免除信息的范围,而鼓励对敏感信息等进行保护。⑦
当然从规范语义的角度来看,规范语义包括两种可能:明确规范、模糊规范。免除性规范也存在着两种可能,即明确性和模糊性,虽然在规范向度上要求免除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可直接操作。但明确性规范的可操作性也是相对的,而对于不可避免的部分模糊性规范,则操作具有一定合理的弹性。这种规范上客观存在的弹性,则必定要寻求方法上的解决之道。公开推定原则,便是这一层面的方法,即在界定是否属于免除公开的信息时,出现规范等方面的困难而无法确定时,推定这些信息都属于必须公开的范围。这样,借助公开推定方法,便可在方法上完全确定例外信息的范围,进而可以使得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得以确定,而可以在司法层面予以操作。由此可知,公开推定原则在方法层次上是针对例外信息确定出现“模糊”困难时的一种方法。因而,“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操作可能性,其只是作为信息公开的一种理念。
三、举证责任分配:由公众到政府
从《行政程序法》到《信息自由法》,举证责任已经发生了理念上的转变。《行政程序法》在举证责任上,公众有责任承担举证证明他享有信息公开的权利,否则政府则可以不公开该信息;而《信息自由法》的举证理念则不同,它在明确授予公众有知情权的前提下,要求政府机关必须举证证明他有拒绝公开政府信息的理由,而与《行政程序法》的举证逻辑截然相反。⑧《信息自由法》对于举证责任分配作出了明确的原则性规定,即一切人都享有获得行政信息的权利。政府的各种文件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没有申请人资格的限制。个人申请得到文件,不需要任何说明理由,只要能指明辨别文件的标志以便行政机关查找,并且按行政机关规定履行一定的手续、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得到所要求的文件。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文件要说明理由,负有举证责任,例如,行政机关证明该文件属于免除公开的情形。如果行政机关不能证明存在拒绝提供文件的法律根据时,必须按申请人的要求提供文件。⑨
虽然《信息自由法》为信息公开提供了方法论的框架,但是在不同的方法之下,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效果。在里根政府时期,对于规范无法解决的自由裁量性公开(discretionary disclosure),其采取了“实质性法律基础”(substantial legal basis)作为方法。在实质性法律基础的标准下,只要政府能够为自己不公开信息找到实质性的依据、理由,便可以不公开政府信息。而如果要公开这些无法确定的信息,除非公众能够举证证明行政机关的“实质性”法律基础不成立。这种由公众举证反驳的举证逻辑,在本质上是对政府不公开信息的一种保护。从规范的角度看,由于对“实质性”进行判断的最终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行政机关,而由公众承担了举证的重负,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使得无法确定是否公开的裁量性政府信息被排除于公开的范围之外,而大大缩小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也使得透明政府大打折扣。
1993年克林顿总统签发的信息公开备忘录,重申了自由和开放社会的价值。⑨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便始终坚守公开推定原则作为解决裁量性政府信息的方法,而此时举证责任则由政府机关来承担,即由政府机关来证明其不公开的信息是完全属于例外排除情形。如果政府不能证明,则必须公开这些裁量性的政府信息。司法部长Reno进一步通过备忘录发展了具体的实现政府公开的原则方法,而改变了之前里根政府为行政机关设定的“实质性法律依据”(substantial legal basis)标准,而采用了“合理预见”(reasonably foresees)的标准。(11)所谓合理预见,是要求政府如果不公开政府信息,必须是属于能够完全合理预见公开信息之后将会对排除事项(exemption)保护的政府和私人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一个信息仅仅是技术上的,或者仅仅有理由在排除的事项范围内,则不能作为信息不公开的理由。(12)这样,在举证责任上,政府必须举证证明它对于信息的不公开,必须基于信息公开会可预见地对免除事项所保护的政府或个人利益造成损害。如果属于信息公开仅仅可能对政府或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则也不能成为不公开的理由而必须公开信息。
但是,在布什政府时期,经历了9·11事件之后,其对于信息公开所采取的方法则转变为“合理说明”的方法,而与公开推定的方法又截然不同。司法部长Ashcroft授权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只要发现了“合理性基础”,便可以证明行政机关行为的合理性。(13)这样的“合理说明”方法便赋予了行政机关极大的自由空间,进而扩大了排除事项的范围。
司法部长Ashcroft强调,司法部只要发现了行政机关推理中的合理性法律基础(sound legal basis),便可以维护其行为的合理性。依这样的逻辑,如果公众认为存在不充足的行政救济,则联邦法院面对行政机关的“合理性”也将无能为力。司法部的官员认为,司法部长Reno的备忘录提高了政府拒绝信息公开的门槛,而Ashcroft的备忘录采取的则是与之前克林顿政府截然相反的标准。(14)由此可见,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在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上,又重新将举证责任重担分配给了公众而使得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在信息公开案件的举证中处于支配地位。因为,对于何谓“合理性基础”,行政机关具有信息上的支配权,而公众必须反驳政府所提出的“合理性基础”,证明其不具有合理性,才能够获得政府公开的信息。而从方法论的角度可知,对于双方都无法举证完成的裁量性政府信息,则将不被公开,因为对于裁量性的信息,行政机关的“合理说明”明显优势于承担举证负担的公众的“反驳”。这样的举证分配逻辑在方法论上,其本质是一种对于裁量性政府信息的不公开推定。同样,对于合理性基础,行政机关是可以轻易地通过借助“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等理由来进行辩护的,这些理由往往由于公众缺少信息来源渠道而在客观上无法反驳,因为相关信息资料均由政府机关主导和掌控。
由上可知,在“合理说明”方法之下,政府可以通过“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概念来作出“合理说明”,而由于政府在信息掌控上居于主导地位,这在逻辑上便推定了这些“国家安全”等理由的合理性,除非公众可以举证反驳之。因此,“合理说明”方法本质上就是借助于“国家安全”等概念来推定政府信息不公开,除非公众可以反驳这种不公开推定。这样,“合理说明”方法就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和责任,实质上是与“所有政府信息都应该公开”的公开政府理念相悖的。
进入奥巴马政府时期,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命令美国司法部长颁布了《信息自由法》新的解释方法,即公开推定方法。其包含有三个核心要素:(15)(1)如果基于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的排除而不予以公开,则必须有明确的排除(exemption)规定;(2)存在可能的时候,不能将整个文件不公开,而是要对信息进行编辑;(3)不能声称一项排除事项仅仅是为了隐藏错误或者因为抽象性考虑。这样,对于裁量性政府信息,原则上对于公众都要公开。如果政府不公开信息,必须负举证责任来证明公开信息将会产生危害,而不能仅仅因为公共官员可能由于公开而陷入尴尬等而不公开政府信息。
在2009年新备忘录发布后,美国一些州的法律也进行了修改而采纳了公开推定原则,如南达科他州。(16)华盛顿州的法律也启用了公开推定原则,其通过《公共记录法案》中的两个条款对推定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一条RCW 42.56.550(1)规定,举证责任应该由行政机关来承担,证明他拒绝允许公众进行检查和复制是与法律关于禁止或者免除部分或全部信息公开的规定相一致的。另一条RCW 42.56.030则提高了政府机关持有记录的举证责任,从而在解释方法上采取对法案可以自由解释,而对于免除事项则要进行限缩解释,从而实现法案允许公众知情政府的目的。(17)这两个条款表明,政府必须公开任何公共记录,除非他能够证明,通过限缩解释方法之后,记录仍然可以免于公开。
由此可见,在公开推定方法下,对于免除事项的解释是信息公开制度实践中的关键。其应该采取一种限缩解释方法来进行,即对政府机关不公开信息进行严格的限制,从而将举证负担都分配给政府机关,由其说明不公开的理由。公开推定原则所要求的对于《信息自由法》中免除事项的解释应该采取限缩解释方法。如果政府机关在限缩解释方法下无法举证证明所不公开的信息会预见性地产生危害,则根据公开推定方法,必须公开信息。
当然,9·11之后,布什政府之所以采取“合理说明”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方法,其初衷是基于保护国家安全、敏感性商业信息及个人隐私,而在逻辑上认为保护国家安全、打击恐怖活动等必须采取“合理说明”这种实质上推定信息不公开的方法,从而达到保护国家秘密,保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但是这种逻辑方法明显是将保护国家安全与政府信息公开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不具有合理性。首先,《信息自由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基于保护国家安全和打击恐怖活动等公开政府信息可能产生危险的情形,因此,对于确实属于国家安全的信息,政府完全可以举证而将其纳入不公开的免除情形。但是如果将所有裁量性政府信息,都借助于所谓的“国家安全”等作为合理基础而不公开,从而将举证负担置于公众,则此方法将与“所有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当公开”的理念相悖。同时,对于保护国家安全,打击恐怖活动,并非仅仅通过保护所有的政府信息才可以达到目的。对于保护国家安全的任务,需要通过外交、国家政治等多种手段来完成。(18)因此,如果对政府信息采取不公开推定,一方面明显与公开政府的理念相悖,另一方面也并不能有效阻止危害国家安全的可能性。如果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信息自由法》的排除情形已经在规范上完成了任务,即由政府举证证明属于国家安全即可。而如果极端地对于所有的政府信息在方法上采取“合理说明”这种不公开推定的方法,则将过犹不及。(19)
四、司法方法:消极中的积极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对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实践,如果最终没有法院进行司法性的审查,则最终仍然无法发挥公开推定原则的方法价值。美国《信息自由法》最初并没有明确可以对信息分类提出挑战的主体,不管是行政主体还是司法主体。此时,免除事项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了政府机关不公开信息的“正当”理由,而使得政府信息处于完全由行政机关掌控的“任意不公开”状态之中。1966年的修改法案则首次包含了私人主体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方法来对行政机关对于文件分类的决定提出审查要求。诉讼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检查行政权在文件分类上的裁量范围是否恰当,而希冀法院能够扩大他们对于分类决定(classification decisions)的审查。当然法院往往让他们失望。(20)而当法院来对行政机关的分类决定进行审查,信息公开制度进入司法实践之时,那么司法权在对信息分类是否恰当进行审查,则要面临司法审查的基准与限度问题,即处理司法权与其他公权力之间的关系。美国的Epstein v.Resor案(21)便是第一起涉及在《信息自由法》排除规范下对于行政机关所掌握信息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恰当范围的问题。该案中,一位历史教授要求公开二战后强制遣返那些反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人的相关文件。但是这部分文件被分类为“最高机密”,但是原告认为这种分类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法院应当对于文件的内容进行审查,从而对于分类的适当性进行判断而做出自己的决定。而法院却拒绝去审查对于这些文件进行分类的决定。法院认为,如果行政机关即使在免除条款(exemptions)下也要负担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恰当的,那么将导致这些免除条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法院重新对陆军司令部的分类决定进行判断是恰当的,而将举证负担分配给部长大臣去证成他的行为,那么法院在对待由机关掌握的信息是否属于免除条款情形时,将给予同样的处理。通过这种推理可以看出,法院实际上已经使得《信息自由法》赋予法院对于机关决定的重新审查权失去了意义。这样简短概括就使得九种法定的免除情形的任何一种都会解除机关所负的举证责任。也有学者认为,法院应该积极地进行审查。1974年美国信息自由法修正案授权法院可以对分类的秘密文件依照行政命令进行审查。法院也被允许对于被要求的机关的决定进行重新审查。修正案的历史背景表明国会的目的确定无疑的是鼓励法院去积极地审查各项分类的决定。(22)
法院的司法审查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保障,那么法院应该采取积极还是消极的方法来进行审查呢?笔者认为,法院毋宁采取一种消极中积极的方法来进行审查。法院如果一味地采取消极的态度进行司法审查,则将会出现使得政府轻易将信息分类为免除事项的情形,从而使诸多本来应该公开的信息无法予以公开,公开推定也将无法发挥功效。而如果法院一味采取积极的姿态,则也会出现司法权侵涉行政权力的可能。从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已经认识到行政机关在外交领域具有一种特殊的专业职能,因而倾向于尊重这些较为敏感的行政决定。而行政机关对一个文件进行分类则倾向于在国防或全面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宽广的语境下理解。(23)这样,法院在诉讼中只能利用极少数的数据。然而这样一味地依赖行政机关的决定也是不科学的。
由此可见,法院在审查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基于对行政权专业性的考量,而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行政权机关对于文件的分类。但是这种尊重的前提必定是属于行政机关自己专业职能领域内的事项。对此,行政机关必须举证证明其属于免除事项的范围,法院才会予以尊重。同样,“被授权能够对文件进行分类的行政机关的数量是不可计算的。据估计联邦雇员中有55000人有权将一个文件标贴为‘机密’(confidential);18000人有权使用‘秘密’(secret)这一标签;有近3000个机关可以将一个文件分类为‘头等秘密’(top secret)。数以千万计的政府雇员,虽然只熟悉其中一小部分范围的国家安全或政策,但都有权对文件进行分类,从而免除公众的监督。联邦法官虽然不能像政府雇员那样对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专门性的分类工作,但至少法官可以要求政府提交其对于分类决定的解释。”(24)如果政府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则公开推定原则仍将适用,而将这些无法确定公开标准的信息予以公开。另一方面,对于政府的裁量性信息,法院则应该积极地运用公开推定原则进行审查,如果政府不能充分举证,则可裁定将裁量性信息予以公开。
因此,法院的消极审查和积极审查,在公开推定原则之下,通过举证责任倒置于政府机关,两者相通相容,并不冲突。
五、结语:方法论之启示
从美国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信息公开经历了由政府主导控制而排除司法审查模式到有限司法审查模式的转变,而每种模式下的方法论体系也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容,尽管规范的目的具有一致性,都是致力于构建民主、透明政府。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虽然已经构建了以建设透明政府为目标的相关法律规范,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仍有许多未尽的课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从以上的美国经验可以看出,未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司法化”,必须探求符合我国本土的方法论体系。借鉴美国的发达经验,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必须着力以下两点:
首先,必须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规范上的分类、界定,且对每一类免除信息进行详细的规范界定。目前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整体上仍然是司法操作性不强、方法论欠缺。这很大程度上和规范的规范性弱具有直接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定法规范来看,无论是《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等地方政府行政规章,还是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的信息公开规定都还比较粗疏,特别是对免除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仍停留在已经被学术界公认为落后于国家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早在1988年9月制定的《国家保密法》层面。(2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强调“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和“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这些规定偏于笼统,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容易使行政机关作出扩张解释从而在事实上大大扩张不公开的范围,与政府信息公开法制追求的信息公开的基本价值目标不相吻合。因此,必须在规范上细化各类排除不得公开的信息,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这样才能使得“以公开为原则”具有规范效能。
其次,在规范分类的前提下,须形成以“原则”为指导的司法方法体系。虽然规范上的分类,对于免除事项的详细规定,可以在规范层面解决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问题。但是当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进入司法实践的时候,必须具备体系化的方法论体系。从美国的经验可以看出,缺乏方法论的信息公开制度,最终仍然会在本质上演变成一种行政主导的非公开信息制度。而这种方法论的建构,应该以“公开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等与公开政府理念相一致的方法为主线,而不能仅仅采取形式性的“合理说明”、“实质性基础”等本质效果上与公开政府相悖的方法。
从美国相对成熟的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所有的总统都会宣誓致力于建设一个自由和开放的政府。但是这些宣誓从来都没有绝对化。每位总统也都理解他们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有保卫信息的义务。(26)虽然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制定了全国性的信息公开法,(27)但是这些公开信息法律对于政府信息的公开都存在基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考量而排除公开的情形。恰如戴维斯(Davis)教授深刻指出的,应该恰当地去寻求信息需求方与受信息公开影响的利益方之间的平衡。(28)而这种平衡的寻求,必须有章可循。从美国的经验分析可知,公开推定应该成为一种原则性的方法,适用于信息公开制度之中,这与公开政府的理念相一致。“判断一部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的一个方法就是,良法的逻辑起点是推定所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然后才存在排除情况。而恶法恰恰作相反的推定,然后去界定哪些是应当公开的。”(29)公开推定原则应该成为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践过程中的原则性方法!
注释:
①参见Memorandum from John Ashcrofi,Attorney General,to Heads of all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re: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ct.12,2001).
②参见"The Letter from James Madison to W.T.Barry," Aug.4,1822,in K.Padover (ed.),The Complete Madison,1953,p.337.
③参见刘杰:《知情权与信息公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④参见"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A Critical Review," 38 Geo.Wash.L.Rev.,1969,p150.
⑤这九项分别为:(1)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某些信息;(2)纯属于行政机关内部人事规则和习惯的文件;(3)其他法律明文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事项;(4)贸易秘密以及由个人提供并且具有特许性或机密性的商业或金融信息;(5)在行政机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中,法律规定不得向非机关当事人公开的机关内部的或机关之间的备忘录或信件;(6)人事和医疗档案,以及其他公开会侵犯隐私权的档案;(7)执行法律的记录和信息;(8)关于金融机构的信息;(9)地质和地球物理信息、资料、包括有关矿井的地图。
⑥参见杨小军:《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若干法律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⑦参见Memorandum from Laura L.S.Kimberly,Acting Director,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to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re:Safeguar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Other Sensitive Records Related to Homeland Security (Mar.19,2002).
⑧参见Kristen Elizabeth Uhl,"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Post-9/11:Balancing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and Homeland Security," 53 Am.U.L.Rev.,261,2003.
⑨参见刘杰:《知情权与信息公开》,第95页。
⑩Memorandum from William J.Clinton,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to Heads of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re: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ct.4,1993).
(11)Memorandum from Janet Reno,Attorney General,to Heads of All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re: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ct.4,1993).
(12)Memorandum from Janet Reno,Attorney General,to Heads of All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re: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ct.4,1993).
(13)参见Memorandum from John Ashcroft,Attorney General,to Heads of all Federal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re: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Oct.12,2001).
(14)参见Kristen Elizabeth Uhl,"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Post-9/11:Balancing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and Homeland Security," 53 Am.U.L.Rev.,261,2003.
(15)参见Ramsey Ramerman,The Presumption of Openness,Posted on May 31,2009,www.localopengovernment.com.
(16)参见Chet Brokaw,"Governor Signs Open Records Law," The Seattle Times,March 19,2009.
(17)参见RCW 42.56.550(1) and RCW 42.56.030,Public Records Act,Washington State.
(18)参见"Obama's Speech o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Times,May 21,2009.
(19)参见Kristen Elizabeth Uhl,"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Post-9/11:Balancing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Critie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and Homeland Security," 53 Am.U.L.Rev.,261,2003.
(20)参见"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a New Role for the Courts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23 U.Pa.L.Rev.,1975.
(21)参见Epstein v.Resor,421 F2d 930 (1970).
(22)参见"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a New Role for the Courts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23 U.Pa.L.Rev.,1439,1975.
(23)参见U.S.v.Marchetti,466 F.2d 1309,1318 (4th Cir.),cert.denied,409 U.S.1063 (1972).
(24)参见"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Public's Right to Know:a New Role for the Courts Under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23 U.Pa.L.Rev.,1439,1975.
(25)赵正群、崔丽颖:《判例对免除公开条款的适用——对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判例的初步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26)参见Elias Clarkt,"Holding Government Accountable:The Amende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84 Yale L.J.,745(1975).
(27)参见莫于川、肖竹:《公开法制的巨大力量》,《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8)Davis,"The Information Act:A Preliminary Analysis," 34 U.Cnt.L.Ray.,761,765-66(1967).
(29)参见Ramsey Bamerman,The Presumption of Openness,Posted on May 31,2009,www.localopengovernment.com.
标签: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论文; 信息公开论文; 行政合理性原则论文; 法律论文; 时政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举证责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