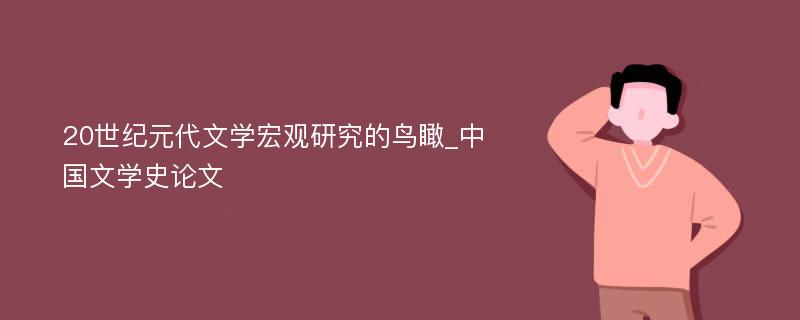
20世纪元代文学宏观研究鸟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元代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关于元代文学宏观认识与宏观把握的论著有相当的数量,本文涉及的,只限于以元代文学整体研究为对象的论著。本文要谈的,是20世纪百年中,关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元代文学与元代社会文化等问题的认识。
一、关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传统偏重诗文,且有种族之见横亘胸中,元代文学研究颇受轻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正统文人开始注意戏曲小说的价值,想利用戏曲小说的教化功能,以挽颓风,正人心,自然也不再无视元代戏曲小说的存在了。林传甲编写《中国文学史》时,元代诗人既不被肯定,而小说戏曲又被视为“无学不识者流”的“淫亵之词”。在这样一些学者的观念中,元代文学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什么地位。但随后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大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来认识这一转变。王国维从1908年起研究戏曲,陆续写成了《曲录》、《唐宋大曲考》、《戏曲考原》、《古剧脚色考》、《优语录》等,至1912年,完成了他的传世名著《宋元戏曲史》。他不仅认为元之曲可与楚之骚、唐之诗、宋之词等并称,各为“一代之文学”,而且认为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自然”、“最有意境”之文学。其代表作,即使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从此,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告别了“暗淡无光”的评价,转而认为元代创造了文学史上一代之辉煌。到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潮流中,1916年,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这时,元代几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了。1923年至1927年,陈垣发表了《元代西域人华化考》的后四卷,在卷八的《总论元文化》中说:“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则汉唐清学术,岂过元时!”
三四十年代,情况却又有所改变。人们在文学革命和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之后,这时又冷静下来,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作较全面的思考。元代诗文的研究也在这时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在对元代文学进行宏观评价时,自然也考虑到诗文的成就。1934年,以研究戏曲著称的吴梅出版了《辽金元文学史》其中诗文占了很大比重。到40年代初,钱基博的《中国元代文学史》更是只谈诗文。1932年北平朴社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反映了这一时期一般学者对元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他除了肯定元代的戏曲小说的辉煌外,还认为元代的诗词也不是很寥落的,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元代诗词的风格,也颇不同于以前。他认为元代散文是唐宋散文的继续。还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虽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出现了一些有系统的著作。他还特别注意了元代的白话碑和白话写成的《蒙古秘史》。和许多文学史家一样,他是把《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为元代作品来讲的。在他看来,有一代辉煌的元曲,有具有一定成就的诗文词及文论,加上长篇小说,元代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4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却主要是依据元曲评价元代文学的,元曲以外的各体文学都不占什么位置。这种看法对建国后的文学史界影响很大。
50年代,元曲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因此特别受重视。元代的诗文词差不多是被忽视了。于是元代文学的成就几乎等于元曲的成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
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都提出来重新认识和讨论。除了杂剧、散曲、元南戏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外,元代的诗文、文论以及元词、元赋等都有人进行研究和重新评价。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也是这一时期古代文学论争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元代的作品,更多的学者认为起码形成于元代。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的《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发表了周惠泉的《元诗浅谈》,说元诗常常为文学史家所忽略,这是不正常的。作者从内容和艺术两个方面肯定了元诗的成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到1985年,隋树森在《文史知识》第3期发表了《元代文学说略》,说元代各体文学也颇有发展,今天的元代文学研究,是应该对各种体裁都加以注意的。他指出,研究者多把精力放在戏曲方面,而对诗文等注意不够,应该加强对元代文学各方面的研究,使人们能够了解到元代文学的光辉灿烂。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还开始从史的角度或理论的角度重新评价元代文学。1986年,刘知渐在《重庆师院学报》第4期发表《编写〈元代大文学史〉的指导思想》,他设想的元代文学史从蒙古成吉思汗元年(1206)起,下限一直延伸到明洪武末年,大约两个世纪,也可称作十三、十四世纪文学史。按照他的设想写出来的元代文学史,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全面辉煌的时期。1987年,李修生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说:“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新的转折期。戏曲、散曲、小说在元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们逐渐取代诗、词、散文而占据文坛的重要位置。同时诗、词、散文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自己的特点。”
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出现了此前无可比拟的成果,而且观念的更新,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使得元代文学的研究展示出新的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1991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发起召开了全国元代文学学术讨论会;12月,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元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就元代的诗歌、散文、词赋、杂剧、戏文、散曲、文论、小说展开了专题讨论,强调要加强以往被忽视的领域。会议论文集收录李修生的《元代文学研究刍议》一文说:“从文学产生到先秦两汉为上古阶段,这阶段文史哲不分的特点,表示出了文化的包容性,和文学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前期是中古阶段,这时期的文学样式以诗歌为主。是雅文化占主导位置的时期。从宋光宗元年也即金章宗元年到鸦片战争以前为近古时期。这一时期,俗文学在文学史上占重要位置。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划时代的作品。而“元曲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跻身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殿堂,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他的这些观点在1998年第9期《文史知识》上发表的《元代文学的再认识》中又有进一步阐述。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则将元代文学的完整面貌展示给读者。关于它的创新意义,学术界已有充分肯定,1992年5月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专家就本书的出版召开专题座谈会,李修生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以前的元代文学史著,“不足以反映元代文学的真实面貌。这部《元代文学史》内容丰富、全面,举凡杂剧、散曲、南戏、诗、词、文、小说,无所不包,弥补了以前文学史有点无面的不足,内中诗文的七章,涉及数十位作家,不仅为历来文学史所未有,甚至已经超出当前学术界的研究范围……总之,此书是一部比较符合元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全面反映各种文学样式及其发展过程的文学史”(《总结·深入·开拓——〈元代文学史〉座谈会纪要》,《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元代文学作总体评价,自然与以往不同。
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元诗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元文、元赋、元代文论、元代小说、元词的研究都取得了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元代各体文学的价值也在逐步被肯定。李修生《元代文学的再认识》再次呼吁对元代文学的总体成就作重新评价:“我们提出‘再认识’,不仅是要恢复某些史实的真实面貌,而是因为对元代文学的总体面貌、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明清乃至近代文学的重大影响等,都尚未给予充分的注意。”他历数元代各方面文学的成就,又提出了元代俗文学作者与以往诗文作者的文人心态的差异问题。90年代后半期,不少人都认为元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如乔光辉在《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东岳论丛》1996年第3期)中说:“中国文学史应以元为界,前期应是所谓正统文学史,主要以诗词为主,后期则应是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史,与诗词相比,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篇幅较长,蕴含量极深,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更广泛,对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为真正的人学的文学是从元开始的。”并认为元代发生的文学嬗变,一直影响了元明清直至当代的文学创作。
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走向:长期不被重视的诗文词赋以及文学批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学者的评价也逐渐由否定走向肯定,研究出现新的局面。元曲研究也拓展其研究思路,进行新的思考。可以说,到90年代末,人们对元代文学的总体评价,正在走向全面、客观。
二、元代文学与元代社会文化
对于元代文学社会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就已开始。20年代初,胡适就在他的《国语文学史》的第七章中说:元统一全国,“文化上的分裂依旧存在。南方仍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种族上没有起什么大变化,所以文化上也没有大变化。北方就不同了……民族的迁徙和人种的混合又发生了无数的变化。若从中国旧文明的上面看起来,北方自然不如南方了:中国哲学的中心和旧文学的中心,从此以后,永不在长江流域以北了。但从大处着想,北方中国的语言渐渐成为一种大同小异的语言,使中国的国语有很伟大的基础……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扬眉吐气,渐渐的长大成人了”。这是对元代文学转型的社会背景分析,涉及到了政治、文化、民族、哲学以及语言方面的问题。1927年,陈垣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第八卷,则从另一角度论述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他说:“且元时并不轻视儒学……又并不轻视文学。延祐五年七月,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后至元三年四月,且谥杜甫为文贞。其崇尚文儒若此。”他是持元代文化全面繁荣说的,故所论与胡适不同。
三四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加上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文学史家在讲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时,多强调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当日蒙古统治者压迫书生,以及书生在当日地位的低微,是非常明显的事。在这一种情状下,中国的学术思想,遭遇到最黑暗时期。”刘大杰进而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政局下,城市经济发达,外来文化影响,促使社会环境发生激烈变化,“在这个旧精神旧信仰的崩溃下,文学得到了新的发展的机遇和自由,它可以从旧的思想和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前人所视为卑不足道的市民文学,大大地发展起来,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而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60年代出版的两部代表性的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也都是运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分析法来论述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的,只是较之刘大杰论述得更为充分。以游国恩本为例:作者首先肯定了元朝的统一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藏。因为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文作家,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以下则依次谈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文人的备受歧视和思想苦闷,崇尚儒学,提倡理学以进行思想统治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利用宗教麻痹人民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后则谈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海运漕运和中西交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由此为戏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成为代表性的也几乎是惟一的说法。1978年,台湾出版了包根弟的《元诗研究》(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41页),该书第一章《元诗发展之背景》,在政治环境中讲了蒙人之汉化政策,北方汉军将领之重视文教,道教之庇护士子,和学术思想之自由。在社会及学术风气中讲了书院制度之普及,理学之兴盛及对诗坛的影响,以及书业之发达等。90年代初,元代文学宏观背景研究和作家心灵分析则取得了一批成果。1990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张宏生的《感情的多元选择——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作者历数了宋元之际的诗人:忠于南宋的爱国志士,痛悼前朝的遗民诗人,逃避现实的山林隐士,失去了进身之阶的文士,出仕新朝而心存尤悔的仕元文人,和“不降则走”的变节者。作者用忠爱、悲愤、反省、控诉、逃避、苦闷、尤悔、沉沦八个题目,分析他们的感情活动和内心世界。作者在书的《结论》中说:“宋元之际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民族压迫性质的改朝换代的现实,既给人们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烙印,也给人们全新的生活体验,反映在文学史,就显示了以往任何时期所没有的特色”。本书给人印象较深的,是对一批内心充满矛盾者的心理分析,展示了他们苦闷的心灵历程。1991年,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出版,作者首先认为,由元王朝成为封建国家的性质决定,中国文化是继续沿着原有的传统发展的。而元王朝作为多民族国家同时具有东西交通空前发达的特点,使元代文学具有自己的特点。其次,关于儒士问题。作者认为:
元王朝对待儒士的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笼统地说元代儒士受压迫或笼统地说他们受到重用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又由于民族歧视政策和选官制度的弊端,元代儒士问题始终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唐、宋的时代相比较,元代儒士的地位、价值观念在实际上有所变化……
但是,“元代儒士社会地位的下降引出的儒士危机感,对文化、文学的影响是复杂的”。作者认为以往的分析有些简单化。其三,作者分析了理学对元代诗歌、散文、文论、杂剧等的不同影响。其四,又分析全真教对文学的影响。1992年5月8日《文学遗产》就该书出版召开的座谈会,对该书关于文化背景的研究给以高度评价,说这“较之过去的文学史从社会经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的一般性论述,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抓住了时代的特点”。“没有泛泛介绍元代社会各方面情况,而是抓住影响元代文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加以比较深入的阐述,这样比较解决问题,对读者理解后面要论及的一些重要文学特征很有帮助”。
1993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该书对耶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许衡、郝经、刘因、赵孟頫、戴表元、顾阿瑛、危素、杨维桢以及从事杂剧创作的一些书会才人进行评述,重点分析元代文人在这一特殊时代的内心痛苦和人格分裂:分析辽、金、元易代之际的社会状况对文人的影响,认为他们的行动、观念、心理的常态与变态,都难以摆脱这一社会情状的拘囿,在这些心灵敏感的文人中,产生了一些带共同性的倾向。认为当时文人对宋金都已失望,对有能力收拾残局的蒙古君主带有若干盲目的信任,民族情绪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激烈和普遍;战乱使人产生了与太平时期不同的生命体验,因而导致了对功名利禄的新的认识,对于亦隐亦俗生活方式的普遍认同,甚至对于耳目声色和口腹之乐的狂热追求;统治者与文人间的矛盾,大多未超出传统的君臣矛盾范围;由于不开科举,怀有入世理想的文人的心灵受到伤害;生计问题造成人心散乱,不思进取造成人格的丧失,地位改变迫使文人对生活作多角度的观察思考以及对儒家传统的突破。作者又分析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在动乱年代和异族统治下的危机。么著的出版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发表钟宜写的书评《元代文人心态研究的新收获》,文章认为,作者“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关照元代社会生活,尤其是文人的内心生活,提出了一个群体命运的问题,总体上去把握元代知识分子的心理脉搏,注意到政治文化的外显层,也洞察到民族文化的深隐层。特别注意因社会剧变而牵动着的文人知识分子和政治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化的动律”。1996年第2期《博览群书》也发表了王星琦写的书评。
1996年出版的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分析元代文学的历史背景时,除了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影响外,特别关注经济尤其是商业经济的冲击对人文环境的变化。对于长期以来学界强调的元代的民族压迫与政治黑暗,作者也要求客观看待,说:“尽管元朝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考虑的政策,从而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作者还说: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作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这一时期元代文学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论文,有《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左东岭的《元代文化与元代文学》、《东岳论丛》1996年第3期乔光辉的《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另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郭预衡的《文变染乎世情——研究元代文章的一些想法》也讨论了元代文化问题。左东岭认为,谈元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不应只留意民族歧视,“因为形成元代文人心理状态的决非民族歧视一端,而是两种文化撞击的结果”。他认为在元朝建立以前,蒙古已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四大汗国,“故其吸收的文化因子乃是中国、印度、大食及欧洲的杂糅,因而元蒙定鼎中原之后,始终未能完全纳入中原汉文化体系”。由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文人对朝廷的离心力,使得他们“或闭门读书讲学以保持节操,或混迹于市井勾栏创制杂剧等俗文艺以滑稽混世,或退隐于山林岩穴以啸傲江湖,由此也孕育出有元一代文人的变态心理结构”。文章分别分析了元代诗文、杂剧、散曲作家的心理状态,并特别分析了元末东南诗文作家的心态。应该说,这在当时是颇具新意的。乔光辉的观点与左东岭有某些近似,他认为:“元统治者对汉民族传统思想非常生疏且接受尽缓,元蒙在入主中原前就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他所吸收的是波斯、印度及欧洲文化的杂糅。元统治者对于汉民族心理及汉民族长期形成的一套封建政治制度颇为隔膜,不但未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相反地却欲把中原文化纳入欧亚杂糅的文化体系,因而采用了他们习惯采用的措施来统治中原。这是中原儒生产生共同心态的背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部分文人被迫放弃传统文人的清高傲气而遁入市民中,与妓为伍,探索出实现自身价值的新道路,元杂剧因而兴起;用世思想的不可能实现,文人便转向超现实的追求,“内道”片面发展促使神仙道化剧的大量涌现;上层贵族对元政府的盲从与闲逸,导致元诗宗唐得古之风的形成及孝子节妇题材作品的出现;少数民族作家群心态的汉化及其作品的激增。作者认为,这几点决定了元代文学的总体概况。
此外,李修生《元代文学研究刍议》提出,对宋金元文学应放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进行横向考查;元世祖忽必烈的影响,是研究元代文学必须重视的问题。李佩伦《元代文学研究观念新探》(《中国语言文学》第一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则说:明清以来,在日益严重的“华夷大防”偏见的观照下,评价元人的出处选择,涉及到了人的气节、品格,影响到了其作品的社会与美学的评价。对于研究现状,他认为目前“横向考察,元代文学研究尚未广开门径,未与哲学、史学交流沟通;纵向考察……元代文学研究领域内部,多是单项开掘,封闭一隅。虽是钩深入胜,总觉格局局促”。所论也是要求重视元代社会文化研究。
90年代的元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的研究,似乎是不约而同地寻求元代文化中与以往中国文化不同的特质,进而分析由此造成的元代文人不同于以往中国文人的心态,最终探索中国文学史在元代发生嬗变的表层和深层的原因,并对这一嬗变作本质的把握。
元代文学与元代社会文化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元代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一课题的艰巨性。这一研究在90年代有了大的突破。研究还在进行,我们期待着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