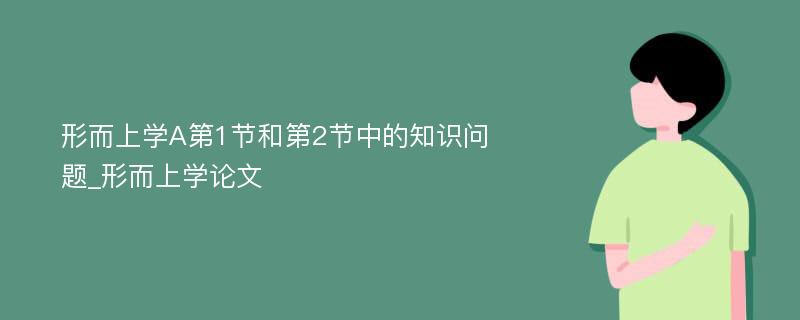
《形而上学》卷A第1、2两节中的知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两节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502.23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5420(1999)05—0042—0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A第1、2 两节探讨的主题是什么是哲学(philosophia),通过对感觉(aisthesis)、经验(empeiria)、技术(tekhnee)、科学(episteemee)以及智慧(sophia )等特定认识阶段的认识特征的分析与比较,他认为哲学就是“有关最初本原和原因的思辨科学(theooreetikee)”(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9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它是智慧的,最神圣的,也是最自由的。 显然,这里面隐含着重要的认识问题,只有通过对认识本性的深入思考,才可能对上述结论有清楚的理解。本文愿就此作一尝试。
一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A第1节中开宗明义就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980a22),并以我们对诸感觉的喜爱为证,说“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980a23、24),从而表明纯粹求知的倾向在感觉中就已经存在了。
这一观点非常值得讨论。因为,感觉并不必然地与认知相联系,人也为了实用目的和享乐目的而喜爱、运用感觉。在日常的经验生活中,人们触摸、谛听、观看,只是为了考察清楚自己的处境,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取得实际的效果;在低等动物的本能反应活动中,甚至感觉的这种感知外物的功能都被简化了,对外界刺激的感受立刻就转化成肌体的某种运动,以完全无知无觉的方式达成趋利避害的直接实用目的。另外,感觉也能给人带来官能上的享受,耳目给人声色之娱,口鼻给人肥甘之享,体肤给人轻暖之乐。因此,就感觉自然的目的趋向而言,我们也可以说谋生是我们的本性,享乐是我们的本性。
这样一些事实再加上现实生活的沉重,使得人们不能想象除了实用目的和享乐目的外感觉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从而,纯粹认识对于我们似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倾向于把感觉的单纯认识功能还原为生存功能的表现。
这不仅是一个眼界的问题,也是一个境界问题。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喜爱视觉尤胜于其他,不仅是在实际活动中,就在并不打算做什么的时候,正如人们所说,和其他相比,我们也更愿意观看。”(980a23—26)显然,这里向我们所展示的正是体现在感觉中的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纯粹认识的本性。亚里士多德以视觉为例来证明这种本性的存在,指出我们不仅在实际活动中乐于使用视觉,而且就在并不打算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乐于观看。这显然是一种纯粹的观看,因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实用目的。但是,在此我们却必须追问,我们拥有这样一种纯粹观看的能力吗?这是问题的关键,由此我们就能确证“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一命题的真实性。
而这显然是一个事实。我们虽然常常利用视觉来观察周围的环境,以求在行动中迅速作出相应的反应,来保全我们自己,并取得实际的益处;但是也确实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把视线从实际的事务中抽出来,纵目远眺或游目四观,在这时候,很难说我们有什么实际的目的和动机,我们仅仅是在观看而已。正是在这里显露了我们纯粹认识的本性,表明我们在认识上拥有从实际事务中摆脱出来的天然的倾向。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用“欲求”(oregontai)、 用“喜爱”(agapoontai)这样的词来表达我们在“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单纯的本性。而奥古斯丁则直接把这称作“目欲”。在《忏悔录》中,他在忏悔了眼睛所带给我们的官能享受之后,进而说:“除了上述之外另有一种诱惑具有更复杂危险的形式。肉体之欲在于一切官感的享受,谁服从肉欲,便远离你而自趋灭亡,但我们的心灵中尚有另一种挂着知识学问的美名而实为玄虚的好奇欲,这种欲望虽则通过肉体的感觉,但以肉体为工具,目的不在肉体的快感。这种欲望本质上是追求知识,而求知的工具在器官中主要是眼睛,因此圣经上称之为‘目欲’。”(注: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19.)“目欲”一词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我们天生所具有的纯粹认识的本性,而且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它在本质上是追求知识。
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的角度对视觉的这种纯粹观看的本性作了论述。他这样说:“在世首先是混迹于烦忙所及的世界,烦忙是由寻视引导的。寻视揭示这来到手头的东西并把它保持在揭示状态中。寻视为一切操持办理工作提供着推进的轨道、执行的手段、正确的机会、适当的片刻。在暂停工作进行休整的意义上,或作为工作的完成,烦忙可能得到休息。在休息之际,烦忙并未消失;但这时寻视变为自由的,它不再来束缚于工件世界。在暂停休息之际,烦置身于自由了的寻视之中。对工件世界的寻视揭示具有去远的存在性质。烦忙要让来到手头的东西接近,而自由了的寻视不再有来到了手头的东西。但寻视本质上是有所去远的寻视,这时它就为自己创造出新的去远活动的可能性。这就等于说:它离开切近来到手头的东西趋向于遥远陌生的世界。烦变成了对这类可能性的烦忙:休息着、逗留着,只就其外观看‘世界’。此在寻找远方的事物,只是为了在其外观中把它带近前来。此在一任自己由世界的外观所收攫;它在这种存在样式中烦忙着摆脱它自身,摆脱在世,摆脱对日常切近来到手头的东西的依存。”(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M].北京:三联书店,1987.209.)
在这段话中,海德格尔从烦忙和休息两种不同的状态对“寻视”这一视觉活动作了描述,指出“寻视”既有为生存而筹划、操持的功能,又有离开手头之物而作自由观看的功能。后一点是他尤其强调的,他指出“自由了的寻视不再有来到了手头的东西”,“它在这种存在样式中烦忙着摆脱它自身,摆脱在世,摆脱对日常切近来到手头的东西的依存”。尽管海德格尔是以一种否定性的语调来谈论这种“自由了的寻视”的,但是,撇开这一层不谈,我们看到,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一种纯粹的观看,它摆脱了一切实用目的的束缚,而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自由的境域。海德格尔还进一步指出,它是此在的一种本己的存在方式,是我们的本性。
这样看来,我们天生地就具有一种纯粹观看的能力,正是从这种现实存在着的单纯的“看”中,显露出了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纯粹认识的本性。
“看”与认识的这种内在关联实际上已经在语言中反映出来了。在古希腊文中“知”一词eidenai其词根就是idein(看),eidenai是idein的完成式oida的不定式形式。oida通常就解作“知”,因为在希腊人看来,“已见”表现在意识上就是“有所知”。可见,“知”在其原发处就是“看”,它是“看”的一种完成状态。此外,像通常被译作“思”的动词noein也与“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我们日常的说话中, “看”也经常被用作认识的同义词使用,以指代所有基于感觉的认识活动。奥古斯丁就曾说过:“‘看’,本是眼睛的专职,但对于其他器官,如我们要认识什么,也同样用‘看’字。我们不说:‘听听这东西怎样发光’,‘嗅嗅这东西多么光亮’,‘尝尝这东西多么漂亮’,‘摸摸这东西多么耀眼’。但对这一切都能通用‘看’字。我们不仅能说:‘看看什么在发光’,这仅有眼睛能看到;但也能说:‘去看看什么在响’,‘看看什么在发出香味’,‘看看这有什么滋味’,‘看看这东西硬不硬’。”(注: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19—220.)可见,较之于其他感觉功能, “看”与认识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才把视觉摆在了优先的地位,认为它突出地反映了我们存在于感觉之中的纯粹认知的本性。
应当指出的是,视觉较之其他感觉在纯粹认知方面的优越性,是古希腊人的共识。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到了这一点。他说:“眼睛是比耳朵更可靠的见证。”(注:汪子嵩.古希腊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89.)恩培多克勤似乎否认这一点, 但是从他的否定中也间接透露了这一共识。他说:“别以为视觉比听觉更为可信,也不要认为响亮的听觉就比分明的味觉更加高级。其他器官也是一条认知的途径,可千万不要将此贬低!”(注: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28、308—309.)柏拉图也以不同的方式提到了这一共识。例如在《国家篇》中他这样说:“我们不是用听力听,用其他感官感知所有可感对象吗?……但你注意到没有,创造者在制造见和被见的功能中花费了最大的气力?……在所有的感觉器官中,眼睛最像太阳。”(注: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28、308—309.)在《斐多篇》中他专门针对视觉和听觉又说:“……如果这两种感觉都不清晰和真切,其他感觉就更谈不上清晰和真切了,因为和前两种相比,其他感觉都是更低级的。”(注: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M].北京:三联书店, 1996.125.)
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亚里士多德才在指明了我们具有纯粹观看的功能之后紧接着说:“这是由于,它最能使我们识别事物,并揭示各种各样的区别。”(980a24—28)这就表明了“看”与认识的内在关联。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看”中显露出了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纯粹认识的本性。
二
视觉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纯粹认知的倾向给“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动物生来自然具有感觉”(980a28),如果人类求知的本性仅仅停留在感觉的层次上,那么就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了。因此,在感觉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就进而谈到了经验,谈到了技术中的认识能力。
经验是比一般感觉更为高级的一个认识阶段。但经验并不首先表现为认识,而是表现为实践。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从记忆得到经验,对同一件事的多次记忆形成一种经验的潜能(dunamis)。”(980b28 —981a2)在这里,“同一件事”to auto pragma中的“事”pragma, 是动词prassein“实践”的名词形式,它不是指认识活动中的客体对象、物体,而是指人们实际从事的活动、事情。因此,经验首先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同一件事的反复实践所形成的熟练的技能。“经验”一词的古希腊文empeiria就反映了这一点。empeiria由em和peiria合成,em是前缀,有“深入”、“进入”的意思,peiria其词根为peira, 指“尝试”、“试验”、“实践”,从而“经验”empeiria就指深入实践所获得的一种技能。在此基础上,才会逐渐积累起对事物本身的一种认识。正因为如此, 亚里士多德在上面所引的段落中才用“潜能”(dunamis)来限定经验认识经由记忆从实践中的生成。
那么,经验认识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说,它已经摆脱了对事物的感觉式的、直接而单纯的、基于表象的同一,而表现为一种认识上的综合。这就是说,它对事物之所是已经能够有所判断。亚里士多德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经验知道事物其“然”(hoti)(981a29)。在这里,hoti正是指事物的一般状况和属性,经验不仅认识到了事物的单纯存在,而且还把它和存在的其他方面联结在一起,形成了针对事物本身的某种认识。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才说它“看起来大致类似科学(episteemee)和技术(tekhnee)”(981a2、3),并强调说“科学(episteemee)和技术(tekhnee)通过经验而来”(981a3、4)。
在此我们却必须指出,经验在认识上的这种综合是通过习惯获得的,它只是借助习惯无意识的接受能力,把事物各方面的存在状态或者事件的各个环节外在地、偶然地联结在一起,它并不能够发现事物之间真正普遍而一般的联系,不知道事物或事件何以存在这样的联系,从而它在根本上仍旧是一种个别认识,它不可能把事物各方面的存在真正综合到一起,更不可能对事物的本质作出真正肯定的判断。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肯定了经验类似于科学和技术,它知道事物其然后,却立即指出经验不知道事物之所以然(dioti)(981a29),而技术却不仅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dioti)(981a28—30)。这里的dioti正是指事物的原因,经验只凭习惯知道事物如何如何,却不知道事物为什么如此,而技术却知道。“知和理解更多地属于技术而非经验,我们断定有技术的人比起有经验的人更为智慧”(981a24—26)。但是,技术又是如何知道事物的原因的呢?
我们说,其关键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于有技术的人知道普遍(981a17)。 亚里士多德这样说:“一当从对经验的多次深思(ennoeema)中一个关于同类事物的普遍判断生成,技术也就生成了。 ”(981a6—8)可见,技术是普遍判断的产物,它是对经验作理智(nous)思考的结果。但普遍为什么就构成了个别事件或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呢?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没有讲明,但是在其他地方,他却给出了许多理由。这不仅是由于普遍即是种,而唯有种能够准确地解释和述说个别(注:参考《范畴篇》第五节.Aristotle,Kateegoriai (《范畴篇》).Oxford classical texts.),而且是由于普遍是形式因,是事物的本质,而唯有形式因和本质能够使我们最为清楚地认识事物(注:参考《形而上学》第三卷第二节以及第七卷第一节关于形式因和实体在认识中的首要地位的论述。),因为,它是对事物或事件中存在的普遍而一般的联系的认识,它为具体事物或事件提供了逻辑上在先的理由。
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形式逻辑给我们提供了证据。根据形式逻辑,一个有效的推理,除了必然遵循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外,前提和结论之间还必须具有必然的逻辑蕴涵关系,也就是说,还要遵循充足理由律。那么,对于具体个别的经验事实来说,什么东西才能充当它的充足理由,才能解释它何以要如此发生呢?我们说,只有对它具有逻辑上必然蕴涵关系的普遍判断才能够。对此,亚里士多德作了精辟的说明。在《后分析篇》中当谈到普遍证明优越于特殊证明时,他这样说:“可以最清楚地见到普遍证明更优越的是在一前一后两个前提中,当我们把握了前者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知道了后者,在潜在意义上把握了它。例如,如果某人知道每个三角形都是两直角,那么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知道了等腰三角形是两直角,即在潜在的意义上,即使他并不知道等腰三角形是一个三角形。”(《后分析篇》86a22—27 )(注:Aristotle,Analutikoon usteron (《后分析篇》) .Oxford classical texts.)这里就谈到了普遍判断对于具体判断的逻辑蕴涵关系,指出了具体判断是潜在地蕴涵在普遍判断之中的。而在《形而上学》第十三卷中当谈到普遍和个别在认识中的意义时,他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元素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它不是普遍的,而认识是关于普遍的。从如下这些证明和定义就可看出:如果并非所有的三角形都是两直角,就不会产生这个三角形是两直角的推论,如果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动物,也就不会产生这个人是动物的推论。”(1086b32 —36)这就是说,对一个正确的三段论推理来说,仅当我们肯定了全体具有某一属性时,我们才能必然地断定全体中的个别也一定具有该属性。由此可见,唯有一个普遍判断才为一个具体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逻辑上充足的理由,使之成为必然的。如我们前面所说,普遍判断的普遍性是对事物内在本质联系的挑明,它把在经验看来只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是无法理解的个别事件纳入到了一个普遍必然的关系之中,使它摆脱了个别性和偶然性,从原因上得到了说明。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技术相较于经验在认识上才更为深刻。因为如上所说,技术是普遍判断的产物,它深入到了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层面,是对它们内在必然联系的把握。
三
在澄清了经验和技术在认识上各自的特征之后,亚里士多德就进而谈到了智慧。根据前面的讨论,既然只有对普遍的认识才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原因,从而在认识上才更为深刻和清楚,同时只有摆脱了实用目的束缚的认识才是纯粹的认识,从而才最能体现认识的本性,那么,智慧也就必然地要与认识上的普遍性和纯粹性相关,要与事物存在的原因相关,因为智慧是一种理智德性。亚里士多德正是由此来讨论智慧的。他这样说:“正如前面所说,有经验的人比起具有某种感觉的人看起来更为智慧,而有技术的人相比有经验的人,技师相比工匠,以及思辨科学相比创制科学都更为智慧。所以很清楚,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981b30—982a3)在这里, 他就明确地把智慧和本原、原因联系在一起了,认为对它们的洞悉是判断智慧与否的根本标准。而在下面他又从普遍性和纯粹性出发对智慧作了更为清楚的界定。我们认为,其中关键性的有以下几点:
1.“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尽可能地通晓一切,但并非拥有关于它们每一个的知识。”
2.“能够认识那些困难的、不易为人所知事情的人是智慧的(因为感觉是人皆尽有的,因此是容易的,算不得智慧)。”
3.“对每门科学中的诸原因更清楚、更会教授的人是更智慧的。”
4.“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982a8—16)
我们认为前三点正是就认识的普遍性而言的,因为只有具有最普遍知识的人才必然通晓一切,只有最普遍的知识对于感觉来说才是最难知的,同时唯有普遍才是事物的原因,唯有普遍才可作为知识被传授。而第四点所关涉的则是认识的纯粹性,因为纯粹认识正是那为知而知的认识,它以认识本身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由这几个判断标准来看,对于什么是智慧,我们就有了明确的认识。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理智德性,智慧应当是对事物最普遍的原因和本原的认识,同时它应当是最为纯粹的认识,在它之中不能掺杂任何认识之外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指明了这一点。他在阐明了智慧所应当具备的条件之后这样说:“由上述可知,那所寻求的名称(按:指智慧)就落到了这样一门科学身上:因为它必定是这样一门有关最初本原和原因的思辨科学。”(982b7—10)那么,这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呢?
这就是哲学。这不仅是由于“哲学”philosophia 从其词源上考证,天然地与“智慧”sophia相亲近,它是对智慧的思慕与渴念,从而它分享了智慧的荣耀和奥秘;而且是由于,唯有哲学才是对事物最为根本和普遍的原因和本原的思考,同时也唯有哲学才是最为纯粹的认识。亚里士多德通过惊奇阐述了这一点。他说:“它不是创制科学,这在第一批进行哲学思考的人那里就是显然的。因为,无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象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关于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可惊之物构成)。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任何实用为目的。当前的事情自身就可作证,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和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11—28)
在这段话中,他通过对哲学思考所必然伴随的惊奇现象的分析,就证实了哲学正是一种最为纯粹的认识。这是因为,惊奇是一种特殊的情绪和欲望,它没有实际的、基于功利的需求,却是对事物本身的“想知”,从而它是纯粹的,它内在具有思想的品质。显然,由这样一种纯粹的情绪和欲望所唤起的求知活动必然是纯粹的,它把认识本身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它当然不属于创制科学。
哲学就是这样的一种纯粹认识活动,它为了摆脱无知而思考,它使思想深入到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本原之处,由此它洞悉了事物存在的最初原因。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就进而谈到了哲学活动的自由特性。他这样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这就是说,哲学活动在认识上的纯粹性,在实践上却恰恰构成了一种自由的品质,因为,目的在其自身的活动不是别的,就是自由活动。亚里士多德以我们进行哲学活动的一些基本条件为证来说明这一点,指出我们并不是为了谋生才从事哲学思考,恰恰相反,只是在我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哲学活动才真正开始。这就表明哲学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它以认识本身作为自己的目的,它是思想对思想的思想(1074b36),在它身上体现了人类最高的价值目标。
但正因为这种活动的理想性以及超尘脱俗性,亚里士多德才认为,它是属神的,对于人来说是不易获得的。他这样说:“……诸科学中唯有它是自由的:因为只有它是为了它自己。因此认为对它的拥有非人所能就可能是公正的;因为在许多方面人性是奴性的,这样如西蒙尼德所言,可能唯有神才拥有这一特权,而人则不配去寻求这种就其自身而言的知识。”(982b27—33)在这里,所谓“在许多方面人性是奴性的”,正是就人类的物质需要而言。当我们过多地沉湎在物欲之中时,我们就忘却了在我们身上还存在着自由的本性,我们还拥有着从事一种远为高尚的自由活动的能力。这正是人类的可悲之处。因此亚里士多德才说人“不配去寻求这种就其自身而言的知识”。但是出于对智慧的热爱,他立刻又以一种更为积极的论调否定了上述过于悲观的说法。他指出,正如俗谚所云,“诗人多谎”,从而这种活动虽然神圣,但是我们人依旧能够分享。如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在我们身上存在着“理智”(nous)这一属神的部分。他这样说道:“如若理智(nous)对于人来说是属神的,那么这种合于理智的生活对于人的生活来说也就是属神的。不要相信这样的话,作为人就要想人的事,作为有死的东西就要想有死的事情,而是要尽可能地去追求不朽,并且向着生活凭自身中最高贵的部分去作一切事情;因为即使它体积很小,却较一切具有更多的能量和价值。它看起来就是每一个人,假如它是最主要和较好的部分的话。”(《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b30—1178a3)(注:Aristotle,Eethikoon
Nikomakheioon (《尼各马科伦理学》),Oxford classical Texts.)从而,哲学作为理智的最高活动, 它是最神圣、最高尚的,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要求我们以百倍的热情去追求它,以此来努力成全一种真正属人的生活。因为,不能否认,它也内在于我们人之中,是人性中最为高贵的部分。
如此,亚里士多德就最终阐明了哲学活动的本性和特征。概括起来说,哲学就是一门对最初本原和原因思辨的科学,它是最纯粹的认识活动,同时也是最自由、最神圣、最高尚的生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A第1、2两节中所要说明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更多地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表现了理智最高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活动。愿我们这篇论文能够对此有所阐明。
[收稿日期]1999—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