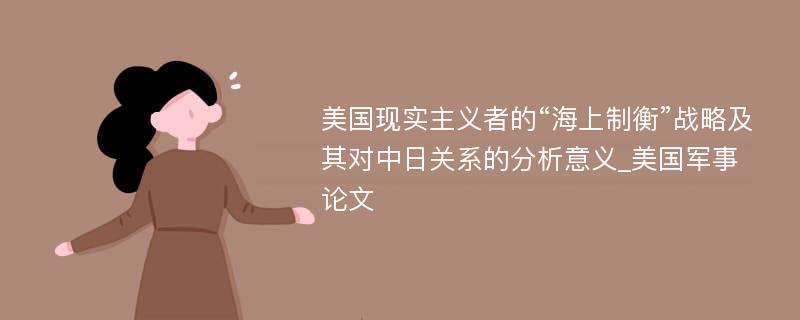
美国现实主义者的“离岸制衡”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分析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意义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现实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07-03-27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4-0018-22
200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以民主党的大获全胜告终,这无异于宣告了布什政府以军事化为典型特征的强硬对外战略理念的实质性失败。伊拉克作为这种对外战略理念的牺牲品,反过来也成了布什政府最大的政治、经济、道义和战略负担。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发展动向再次引起了美国社会和学术界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思想辩论,以厉行克制为核心的“离岸制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主张是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之一。美国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在其最终政策建议报告中提出撤军主张便是对该战略理念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证据,尽管该报告反对“仓促撤军”,但强调一种“负责任的撤军”政策,建议美国加强在伊拉克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外交与政治努力”,“转变在伊美军的首要使命,使美国可以开始负责任地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① 不仅如此,2006年12月12日,美国著名媒体《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美军离岸,恰逢其时》的文章,该文大力主张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军,仅在国际水域保留离岸的海军力量,以有效削弱“基地”组织或其他极端宗教组织招募成员的“反美”借口,切断它们的人力资源来源,并强调这是“维护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的最佳方式”。②
中国学者对“离岸制衡”也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并曾在国际性研讨会上提出了中国对美国的期望角色是“终极离岸制衡者”的观点。③ 鉴于“离岸制衡”战略在学界所受到的关注,本文拟从理论含义和政策导向两个层面加以探究,并分析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的影响,解释美国“乐见中日不和”的流行观点。
一、离岸制衡战略设计的理论与现实背景
冷战结束和“9·11”事件发生至今,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们一直都在反思美国现有大战略的利弊,积极建言献策。新孤立主义、选择性接触、合作安全和霸权优势被认为是主要的四种分析取向。然而,无论其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言表面上如何歧异,他们的终极关切都是如何降低美国霸权的风险,确保美国的优势经久长存。
二战后的美国国际战略往往被称为“优势战略”,其要点包括:以美国卓越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和美国价值观为基础塑造世界秩序;阻止在欧洲和东亚出现敌对性大国,实现美国对国际体系控制的最大化;将维护经济相互依赖作为美国的关键安全利益。④ 正是在优势战略的推动下,美国展开了与苏联的全面争夺。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尊的实力地位为其霸权战略提供了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但随着大国间实力分配的发展变化,单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单极幻想”,⑤ 美国相对衰落、新兴大国相应崛起、实力优势支撑下的扩展性威慑战略⑥ 的活力迅速销蚀都使优势战略难以为继。因此,根据对美国所处战略环境的现实特点和未来趋势的务实分析,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颇有影响的现实主义者如克里斯托弗·雷因等都力主美国用“离岸制衡”战略取代优势战略。“9·11”事件,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更加充分地凸显了优势战略的失败和离岸制衡战略的成熟。⑦
离岸制衡战略的核心在于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在世界其他地区通过与域内大国结盟以防止一个地区霸权的出现,仅当出现敌对霸权大国时美国再直接插手以重塑地区均势,从而降低美国卷入大国冲突的风险,将更多的政府力量集中于解决国内挑战。很显然,这种战略的本质是主张“节制优先于干涉、本国优先于帝国、国内需要优先于海外野心”。⑧
离岸制衡战略的提出和论证有着深刻的理论考虑和现实反思。首先,世界多极化是离岸制衡战略适用的现实因素。根据雷因的观点,在1648-1918年的欧洲国际关系史中,1660-1714年的法国霸权时期和1860-1910年的英国霸权时期具有单极体系的特征。但这两段历史表明,单极体系会因为新兴大国的崛起而转化为两极或多极体系,同时伴随着大国争夺的巨大风险。⑨ 从理论上看,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国家间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必然现象。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是自助的行为体,对安全的追求必然导致对实力的追求,够格的国家会为自己的大国地位而不懈努力。⑩ 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既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也是吉尔平分析国际体系变革的关键工具。(11) 保罗·肯尼迪1987年的《大国的兴衰》也是对各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不平衡发展造成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兴衰的经典研究成果,他当时便明确指出世界格局具有“五头政治”的特征。(12) 同理,冷战后的单极体系也必然会走向多极世界。不过,在雷因看来,多极体系并非美国的战略性威胁,虽然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依然难以摆脱竞争性,但它为美国铺垫了离岸制衡战略的体系基础,有利于促进美国与各主要大国的协调和合作。(13)
其次,国际政治的均势规律是离岸制衡战略的根本理论前提。肯尼斯·华尔兹指出,国际政治的核心规律是均势。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哪个大国希望任何别的大国成为领导者,“我们预期强者不会与强者联合以增大其实力优于别国的程度;相反,它们会摆好架势,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盟友。”(14) 于是,在国际均势遭到威胁的情况下,国家必然会出于安全的需要而倾向于“自动地”构筑制衡联盟,防止体系被等级化。(15) 基于对均势规律的推崇,离岸制衡战略反对美国追求霸权,认为美国的超强实力容易使决策者耽于傲慢,在战略上过多伸手,这必然刺激其他国家择机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而离岸制衡战略厉行克制的理念有助于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帮助美国避免陷入历任霸权国的兴衰曲线的“大战略逃逸仓”。(16)
再次,美国的全面优势是离岸制衡战略的实力基础。当今美国“头号现实主义者”(17)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在于霸权地位的维护,力量相当的竞争者的崛起是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水域的巨大阻遏力量和两栖战争的困难使美国没有征服异域大国而称霸全球的可能,其主要战略考虑应是避免某一大陆被一个本地霸权支配,从而间接地威胁自己的安全。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离岸制衡战略的运作要素包括:不存在全球霸主,只存在一个地区性霸权;现有地区霸权是现状维护者;现有霸权国拥有强大的能力实施军力的跨海投送;其他地区性大国都有各自的域内对手,相互竞争;同域的地区大国间的实力分配大致平衡,可以有效地相互遏制。(18) 从现实来看,美国独特的两洋国家地位、超强的实力优势和投送能力塑造了其实施离岸制衡战略的地缘政治条件和现实基础,美国具备作为“离岸制衡者”的条件。“离岸制衡”战略可以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阻止力量相当的竞争者的出现,永葆优势地位。
二、离岸制衡战略的政策含义
离岸制衡战略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第一,美国要尊重其他主要大国的重大安全利益,避免过多插手和干涉。兰德公司发表的《1996年战略评估报告》指出,离岸制衡战略要求美国在原苏联版图之内承认俄罗斯的主导作用;在欧洲弱化北约,支持德国取得更大的军事能力,或鼓励欧盟具有军事功能,以防止任何大国支配欧洲。(19) 在雷因看来,对其他大国在特定地区的重大安全利益表示理解、尊重和不干涉,有助于促进美国承认其他大国的大国地位,减少可能导致冲突的误解。离岸制衡要求美国克制霸权野心,收敛军事态势,使美国与新兴大国公开冲突的风险最小化。(20)
第二,对于国际义务,美国用负担转嫁理念取代负担分享理念。离岸制衡战略主张美国将维持欧洲、东亚和波斯湾—中东的稳定任务转交给其他国家,以减少美国在中东—波斯湾与东南欧等麻烦地区的安全负担,有助于美国实现两大关键战略目标:卷入未来大国(核)战争的风险最小化;提升相对实力。(21) 这是包括保罗·肯尼迪在内的战略历史学家都再三强调的美国大战略目标。(22) 在雷因看来,鉴于其海权国家地位,美国应义无反顾地扮演离岸制衡者,从现有的东亚和欧洲义务中抽身,通过限制海外义务来追求一个更安全、更强大的美国。(23) 实际上,保罗·肯尼迪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明确地警告美国注意自己的“帝国扩张过头”问题,要设法在军事或者战略领域使自己保持防务需要和可用手段之间的明智平衡,同时巩固国家实力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力避由于过多的海外义务而像当年的西班牙帝国和爱德华七世的英国那样陷入顾此失彼的战略被动,最终加速帝国的衰落。(24) 此外,在伊朗核问题上,离岸制衡战略主张通过威慑解决问题,认为伊朗不会冒民族自杀的风险去挑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使命,应该主要依靠远离波斯湾的导弹和海空军力加以解决,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介入。(25)
第三,美国要借助结盟关系实现非前沿部署。这项政策要求美国放弃在欧亚大陆的前沿军事存在,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一直存在一种“回家吧,美国”(26) 的新孤立主义战略思维。从历史上看,美国并非欧亚大陆的“和平缔造者”或“和平维护者”,美国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缔造欧亚和平,而是为了阻止一个危险的敌手赢得欧洲或东亚霸权。(27) 因此,米尔斯海默认为,在未来的中长期时间里,如果没有任何潜在的大国控制足够成为地区霸主实力的可能性,美国就应该从欧洲和东北亚撤出驻军。因为前沿驻军会带来极大的战略风险,会将美国一开始就拖入欧亚大陆的地区霸权战争,这“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不卷入是美国的最佳选择,晚卷入是次优选择,这将使美国付出的代价最小化,有利于它塑造于己有利的战后秩序。(28)
尽管非前沿部署的主张遭到了强烈的批判,(29) 美国目前保持欧亚驻军政策延续性的做法也削弱了离岸制衡战略的现实解释力,(30) 但种种迹象表明,离岸制衡思维对美国的国际战略还是不乏影响力的。布什总统曾于2004年8月16日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上宣布,将会把美国驻欧洲和东北亚的军事力量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从欧洲与亚洲地区撤出约6万名到7万名美军部队。(31) 2006年8月,美国国防部证实美计划将驻韩美军规模减至2.5万人以下。(32) 最近频频见诸媒体的报道还指出,美国可能降低与韩国的军事同盟水平,或者将驻韩美军并入驻日美军。至于在伊拉克的美国驻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07年1月的国情讲话中批评升级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33) 并针对布什的增兵计划旗帜鲜明地提出向伊拉克移交更多的安全责任、在未来四到六个月里分阶段重新部署部队、强化外交努力以稳定伊拉克局势等三点建议。(34) 这些都是离岸制衡战略思维在政策层面的反映和体现。
三、离岸制衡战略对中日关系的分析意义
离岸制衡理念在美国战略思想界颇有影响,但也受到了较多的批评。譬如,上文提到过的兰德公司的《1996年战略评估报告》就认为,虽然离岸制衡战略的短期代价并不明显,但是从长远看,它将导致美国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美国将面临来自其它大国的更强有力的竞争,甚至出现类似一战前那种不稳定的国际多极化局势。同时,美国有时还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政治原则,支持非民主国家反对民主国家,以便维持大国的平衡。罗伯特·阿特也对“离岸制衡”战略有过专业的理论分析和批评,将其归结为以孤立主义为核心的危险战略。(35)
尽管离岸制衡战略受到了诸多的批评,但完全漠视它对美国东亚政策的解释和预测价值也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当这种价值事关中国对外战略利益的时候。譬如,对中日关系的冷淡和紧张,有美国学者就曾指出,布什政府似乎实际上颇有些“沾沾自喜”。(36) 这反映了“离岸制衡”战略视角对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的中日双边关系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根据离岸制衡战略的设计,美国将利用日美同盟机制,支持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安全作用来防止任何一个东亚国家成为地区霸主。在美国看来,由于日本的安全完全仰仗美国的保护伞,因此它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在政治、战略和军事领域的“正常国家”,美国关注的主要对象是综合国力迅速发展的中国。因此,加强美日同盟以节制中国是离岸制衡战略思维的应有之意。实际上,伴随中国持续强劲的发展势头,美国正在将制约中国的战略责任更多地转移给日本,帮助日本的国家身份实现“正常化”,推动其成长为东北亚的真正大国,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不仅如此,美国还鼓励日本加强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尖端常规军事力量建设,甚至不排除允许日本研发先进核力量的可能,以强化日本在地区力量平衡中的战略地位;美国还不断鼓励日本提升对外安全义务,敦促日本积极参与维护地区均势现状的国际行动,纵容日本通过防卫厅升格、自卫队军队化等走向“正常国家”的政策努力。
美国对两国实施离岸制衡战略将极大地影响中日关系,中日战略关系的竞争性将增加,合作性前景不容乐观,这也是日本日益采取对华强硬政策、导致中日关系从“政冷经热”转向“政冷经温”的深层根源。(37) 美国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实力相当的竞争者,与日本的战略关切完全合拍。因此,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之一便是塑造一个以日本为支柱的联盟体系,允许日本在政治上和战略上更有作为。为了实现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美国默认了日本历届政府对侵略历史避重就轻的态度,这是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小泉时代,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日益勃兴,构成了影响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对中国来说,日本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它对军事实力与日俱增的显性追求和倚重无疑将给中国带来日益严重的安全忧虑,近年来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其国家安全观念的嬗变和安全能力的急速发展、防卫厅顺利升格为防卫省等安全政策、对和平宪法和无核原则的修正冲动已多少印证了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对于中日军力的现实对比,我们也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布热津斯基在其近著《大抉择》中写道,“日本计划再建造几艘1.35万吨级的直升机驱逐舰,这将使日本拥有比意大利‘加里波第’号航母还要大的舰只,能搭载16架鹞式喷气飞机。有远程加油战斗机(官方竟不可思议地说,日本的远程加油能力旨在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以及现代化潜艇舰队的支持,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相比虽然仍不很强大——早已是亚洲国家中最先进和最强大的了。”(38)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前所未有地加速了其追求更为现代化的军事实力的行动,美国对日本发展军事能力也主要采取了默认乃至纵容的立场,布热津斯基便直言“美国应该鼓励日本谨慎而稳步的增强军事力量”。(39) 实际上,早在1996年4月美日最高安全会议上,华盛顿和东京就通过了一个联合行动计划,要求日本在整个亚洲的联合防御行动中承担更大的军事责任,这种提法还是第一次。这表明,美国可能是要“促进,而不是抑制日本防务的加强。”(40)
面对美国离岸制衡战略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我们的对策必须要具有战略远见。从地缘政治意义上看,基于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对发展势头正劲的中国心存戒备是必然的。我们要加大军事威慑能力的建设力度,力求在中美安全关系中实现一种“非对称核威慑”(41) 的态势,同时也要注意克制,避免陷入恶性军备竞赛。我们要尽力寻求缓解美国离岸制衡带来的中日战略疏离乃至对抗,与日本的战略对话机制有必要在条件成熟时升格为更高级别,甚至可以建立双边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晤谈机制。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地区大国的有利地位,(42) 在地区安全对话和互信机制的建立方面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维护中日间安全态势及其它地区安全关系的良性发展。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实践表明,创设地区安全体制有助于建立有效、透明的信息交流机制,尽量缓解国家间的安全疑惧,引导安全领域的有序合作和协调。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努力推动甚至主导地区安全机制的构筑,为本国的安全利益和地区的和平稳定服务。从东北亚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倾力主导、并初见成效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模式大概可以提供东北亚安全体制的基础和雏形,尽管困难重重,但对此可以保持审慎的乐观,为塑造“东亚不战共同体”铺垫机制基础。
四、结论
离岸制衡是美国学界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学者探究冷战后美国霸权护持问题的一种战略新思维,它主张通过美国顺应多极化趋势、尊重别国的重大安全利益以避免与其他大国的直接冲突,并通过转嫁海外负担、减少前沿部署以避免过度耗费美国实力,实现美国优势的长期维护。同时,它也提醒美国承认全球霸权是个神话,主张利用美国惟一地区霸权国和两洋大国的实力和地缘优势,维持欧洲和东北亚“平衡多极”的现实实力分配结构,避免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挑战美国优势的“相当竞争者”。离岸制衡战略颇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乐见中日“不和”的流行观点,以及为什么美国要纵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该战略还具有提示我们在中日、中美交往中坚持战略理性原则、灵活机智地处理敏感议题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p.1,http://www.usip.org/isg/iraq_group_report/report/1206/iraq_study_group_report.pdf.
②Eugene Gholz,Daryl G.Press and Benjamin Valentino," Time to Offshore Our Troops" ,New York Times,Dec.12,2006.
③Richard P.Cronin," Prepared Notes for Summary Remarks on the Final Panel of the Vietnam-China-United States Trilateral Dialogue" ,http://www.stimson.org/southeastasia/? SN=SE20051129928.
④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America' 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22:1,1997,p.88.
⑤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17:41,1993,p.8.
⑥在美国的战略研究中,“扩展性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指A国承诺保护盟国B和C,一般的做法是明确对B和C的攻击就是对A的攻击,从而引发对那些进攻B和C的国家的报复。美国的扩展性威慑战略在亚洲的安排是将日本和韩国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Michael G.Roskin,Nicholas O.Berry,IR:the New Wor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Engl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3,p.212.
⑦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 Fall 2006,pp.7-41.
⑧(23)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22:1,1997) ,p.124,p.87.
⑨(13)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17:4,1993,pp.5-51.
⑩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chapter 6.
(11)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ters 2,3,5.
(12)(24)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538,pp.514-515.
(14)(15)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26,Chapter 6.
(16)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5:2,2002,p.233,pp.245-247.
(17)Lawrence F.Kaplan," Washington' s New Worldview:Springtime for Realism" ,The New Republic,June 21,2004,pp.20-23.
(18)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1,chapter 7.
(19)王缉思:《从美国外交新特点看中美关系》〔J〕,《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3—4期,第7页。
(20)(21)Christopher Layne," 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5:2,2002,p.246,pp.245-246.
(22)[美]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M〕,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章。
(25)Christopher Layn," Iran:The Logic of Deterrence"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April 10,2006 Issue,http://www.amconmag.com/2006/2006_04_10/cover.html.
(26)Eugen Gholz,Daryl G.Press and Harvey M.Sapolsky," Come Home,America: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21:4,1997,pp.5-48.
(27)(28)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265,p.389.
(29)(35)[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M〕,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第五章。
(30)2005年2月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在双方安全同盟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重申“维持驻日美军的规模与作战能力”,http://news.sinhuanet.com/world/2005-02/22/content_2602343.htm。
(31)韩榕华:《美计划将驻韩美军规模减至2.5万人以下》,http://news.xinuannet.com/world/2006-08/08/content_4932541.htm。
(32)徐宝康:《美防长要降低合作级别 韩美军事同盟快破裂了》〔N〕,《环球时报》2006年7月27日。
(33)Nancy Pelosi," Address on the State of Our Union" ,http://speaker.house.gov/newsroom/speeches? id=0008.
(34)Nancy Pelosi," Escalating Our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Iraq Sends Precisely the Wrong Message" ,http://www.speaker.gov/newsroom/pressreleases? id=0027.
(36)Richard P.Cronin," Prepared Notes for Summary Remarks on the Final Panel of the Vietnam-China-United States Trilateral Dialogue" ,http://www.stimson.org/southeastasi/? SN=SE20051129928.
(37)刘江永等:《中日关系现状与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28—43页。
(38)(39)[美]布热津斯基著:《大抉择》〔M〕,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20页,第133页。
(40)[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M〕,柯雄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1)关于非对称核威慑的分析,参见阎学通:《东亚和平的基础》〔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1—10页。
(42)关于中国国际地位定位的系统性理论论证和思考,可参阅陈岳:《中国国际地位分析》〔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