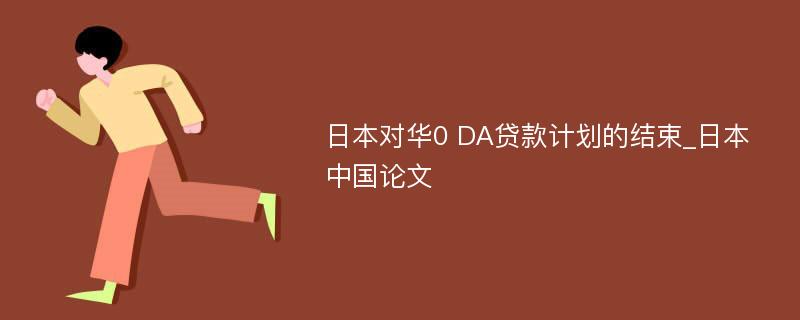
日本对华0DA贷款计划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贷款论文,计划论文,D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官方发展援助(ODA)是日本战后外交最重要的工具,中国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后,它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中尤为明显。日本向邻国提供的ODA数目惊人:1979-2005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3.13万亿日元的贷款援助、1457亿日元的赠款援助、1446亿日元的技术合作,它是多年内对华双边ODA的最大捐助国。①日本的贷款援助不仅是到目前为止对华援助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反映了日ODA的普遍特点。
过去,ODA计划使日本对中国拥有相当可观的政治优势,有助于将争端维持在更可控的层面(例如,1996年围绕尖阁/钓鱼群岛的领土争端)、就中国的军事政策向其施加压力。②在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日本向中国发出了负面信号,通过暂停ODA加入西方的对华制裁。其后,日本早于其他大多数西方捐助国恢复援助,向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正面信号。
成功的ODA计划顺理成章自有终止的一天,各国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依据受援国的发展水平制定了逐步停止援助的标准。不过,日本政府于2005年决定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终止对华贷款援助时,却没有遵循通常的步骤。鉴于日元贷款计划对日中关系的重大影响以及伴随这项决定而来的激烈互动,本文将分析相关的原因和背景。
经济援助还是赔偿?
日本对华ODA计划始于1979年12月,当时日本向中国提供了2亿美元的第一笔贷款,用于六个建设项目,而且还为中日友好医院的建设提供了6100万美元的赠款援助。1978年,中国政府重新定位对外经济政策,打开了接受国外援助的大门。③同大多数政策一样,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ODA是政策支持者和政治定向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下文将对此予以论述。
日本大平政府的想法是,将经济援助作为协助中国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期望以这种方式让中国成为爱好和平的参与者、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④这是日本参与政策的一部分,包括向中国提供政治和经济奖励,同时以政治军事力量制衡作为防范(例如,自卫队和日美安全同盟)。⑤就此而论,向中国提供ODA是一项高度政治化的决定,得到战前经历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政治家的支持。而且,这是日本到当时为止对共产党国家最大的ODA计划,开始于日本面临相当大的经济困难的时代。⑥
日本的高额外汇储备和贸易盈余有助于提供ODA。这种方式也符合日本的偏好,即运用经济力量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淡化其政策体现于日美政治军事同盟中的现实主义色彩。这种经济手段所基于的前提是,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将带来一个爱好和平、面向西方的中国。这将减少中国政府不受约束地资助军事目标的危险和中国(此后)出于非和平目的运用经济实力的可能。⑦就日本国内的气氛而言,对华经济援助得到全力支持,因为公众舆论对中国充满好感、乐于接受相关的政治经济解释,尽管1972年的“熊猫热”到1979年已有所消退。
日本对ODA计划的公开支持也受到道德规范方面因素的重大影响。其中之一是日本对中国于1972年放弃战争赔偿的谢意,中方这样做的动机在于争取日本公众,避免与日本执政党内仍旧非常强大的亲台势力对抗,通过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加强自身与苏联对抗的战略地位,等等。不过,放弃赔偿的原因也在于双方心照不宣地认为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于1978年开放经济后,这种未曾公开表达的默契转变为中国对获取日本经济援助的期望。不过,在1972年中日建立外交关系时,ODA与中国放弃赔偿没有明显的联系,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甚至都不在中国的考虑范围内,更不用说接受外国援助。
直到1970年代末,放弃赔偿才和ODA发生联系,两国为数众多的声明和文件显示了这一点。有人认为,抛开其他对日本自身更有利的考虑(例如,地缘战略考虑、日本设备出口商的直接经济利益、ODA作为日本的参与政策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有义务通过向中国提供ODA来反省自己的过去。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指出,双方都没有在以文件形式正式提及或确认的时间内宣称存在这种联系,因此只能推测这种联系乃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在心理上所构建。⑧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称ODA是“准赔偿”。⑨这种联系也被作为论据说服对华经济援助的反对者。⑩日本商界代表积极利用中国放弃赔偿敦促政府给予中国特殊贷款待遇。1978年4月,日本受到中国取消许多设备订单的打击,当时兼任日中经济合作协会会长的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表示:“由于中国没有从日本获取赔偿,日本政府应该在诸如贷款利率等方面做出特殊的例外安排。”(11)
日本政府本身也利用赔偿与ODA之间的联系为该计划争取支持。1983年,正值日本讨论第二次日元贷款计划时,外相安倍晋太郎提醒国会预算委员会成员:中国放弃赔偿使双边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日本出于对过去的反省,要与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合作。(12)
因此可以推断,到1970年代末,日方将ODA计划与中国放弃赔偿相联系,既有道德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在1978年经济开放后,期望日本表示自己的谢意和慷慨。此时中国也对中日经济关系有所失望,由于需要取消许多设备订单,一些中国人对日本加以指责。然而,将赔偿转变为ODA既让日方也让中方在政治上付出了代价。在随后的年头里,这大大削弱了中国对东京慷慨行为的感激,因为1945年以前中国深受日本侵略之害,援助被视作对中国此后之慷慨大度理所当然的补偿。就日方而言,由于日本也向其他许多国家提供ODA,通过提供ODA消除过去的伤害可能无助于许多日本人客观面对过去,至少不能达到令中方满意的程度。东京大学教授藤原归一指出,东南亚国家接受了日本的赔偿,如今日本的战争责任被认为是过去的事情。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人将日本的ODA视为赔偿,但ODA并未被正式称为赔偿。因此,他认为日本为中国的放弃赔偿付出了高昂代价。(13)最后,当日本于2005年决定终结ODA贷款计划时,这种联系在中方的言辞中占据重要分量。倘若中国人如今开始认为,由于自己过去受难和放弃赔偿,ODA是日本的义务,那么如何才能就结束这种义务达成一致?即使在结束贷款的问题进入议程之前,每当中方为获取更多援助及更优惠条件向日本人提及这种联系时,后者往往也感到不悦或难堪。
“出于日本的利益考虑”
中国人觉得这项计划是“出于日本的利益考虑”,也就是说,这项计划令日本自身在经济上受益。这种较晚的引述对中国认可与感激日本的ODA计划产生了消极影响。然而,ODA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施舍。上文已经提到,这项计划的启动和持续涉及商业利益(还有政治利益)。从现实主义视角看国际关系,一般认为ODA对捐助国和受援国双方都有益,并非是前者给予后者的恩惠。撰文论述ODA的中国学者显然清楚这一点。(14)尽管如此,中国人的态度仍旧过于强调日本的经济收益,加之含蓄地将ODA与放弃赔偿相联系,淡化了日本ODA计划的其他动机含义,从而使中国人感到没有太大必要对ODA计划表示感激和认可。
“日本自身获益”的这种批评某种程度上源于将ODA与捐助国的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虽然日本经常因这种联系受到批评,但如今ODA贷款的相当部分并无附加条件,ODA给日本公司带来的订单所占比例已由1980年代后半期的50%左右降至1998年的15%。(15)不过,赠款的附加条件是向日本公司采购。但大多数批评的原因在于,ODA贷款必须还本付息(尽管利息很低),通常认为这是一种出于日本利益考虑的交易。(16)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但ODA的利率和偿还条件比商业机构和国际机构的贷款要优惠得多,否则,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导原则,此类贷款不具备ODA资格。1990年代,由于日元升值,此类日元贷款的偿还一度给中国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中国对此曾表示过抱怨。不过,中国总是按时偿还。最后,日本的ODA绝大部分被投向中国的经济基础设施,这往往关系到日本的贸易利益(例如,港口和道路)。但这不仅使日本也令中国直接受益。(17)
日本的不满
日本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成功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终止援助最明显、最自然的条件是受援国的经济成功。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公众舆论、媒体和政治经济领导层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对日本自身和整个地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日本的批评集中于中国自身的援助计划和突出成就。例如,中国开始发射载人太空飞船。2003年和2005年10月的中国太空飞行引起了日本公众舆论特别负面的炒作,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背负众多发展问题的国家拥有如此奢侈的预算,而日本却没有任何可与中国太空计划等量齐观之物。
中国经济成就的某些影响被日本各界人士认为对日本不利,因而成为支持终结贷款计划的论据。就生态、政治(社会失衡和混乱的出现)甚至经济(例如,由于国际经济衰退,出口导向和外国直接投资驱动的基本经济模式可能崩溃)的无法维持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这些负面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日本,比如跨国界污染、非法移民、跨国犯罪和许多制造业部门丧失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也加剧了国际市场上对稀缺原材料、食品、能源资源的竞争。最后,以其人口和地理规模,中国的经济成功不可避免会影响到日本的相对经济地位和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身份。(18)
不过,日本也认识到中国的经济成功已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小泉首相于2002年4月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声称中国经济不是威胁而是机会,这一直是小泉的官方政策。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在日本自然带来这样的疑问:日本为何还要再向中国提供ODA?
日本政府通常采用世界银行制定的经济成就指标变量,来决定何时终结各种援助计划。前身是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的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负责发放ODA日元贷款,它遵循五类标准(基于2003年数据的人均国民收入(GNI)):最不发达国家(LDC)、贫困国家(人均GNI低于765美元)、低收入国家(人均GNI 766美元至146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1466美元至3035美元)、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NI3036美元至5295美元)。(19)依据上述指标,中国被划为低收入国家。这种情况表明,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非同一般的出口并未直接转化为能让一个国家从所有贷款计划毕业的高标准。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和正在扩大的收入差距。英国在1997年后停止对华ODA贷款,此后只给予赠款和技术援助。中国如果能保持目前9%的增长率,其2008年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达到1600美元,但它仍不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尽管中国政府2006年春对其经济增长的官方重新估算可能使数据更高。然而,中国良好的经济形势至少带来了政府的预算分配选择问题,还有商业条件下的贷款可行性问题。由于中国发展形势非常好,而且经济相对开放,中国获得且承受正常商业利率贷款变得容易得多。
其次是日本影响力的丧失。日本对华ODA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方向施加影响。经济上,日本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加之来自其他国家ODA的竞争和商业利率贷款的可行性增加,日本的影响力自然消退。政治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日本的各种政治影响力也迅速消退。尽管如此,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熙德仍认为,日本ODA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平息了日本的过去,以及日美安全条约相关问题带来的麻烦,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20)2000年,日本要求中国调查船若在东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作业需“事先通知”,而暂缓提供ODA的决定促成了中日妥协的达成。不过,虽然在1995-1997年间,针对中国恢复核试验,日本仍能通过暂停赠款计划向中国发出重要的政治信号(即使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如今,鉴于中国经济的成功并因此更加果断自信,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更令人怀疑。(21)此外,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政治、经济冲突和竞争加剧,日中贸易对日本的经济复苏变得至关重要。在这一变化的背景下,日本ODA的任何政治化运作都只能激怒中国的政治舆论。
与日本丧失影响力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并不认可日本的经济援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援助知之较少,或者如前文所述,至少对ODA的性质了解不够全面,这自然也令ODA的政治价值受限。而且,这种感激和认可的缺乏已成为日本公开讨论终止对华ODA的主要依据。例如,日本参议员们在2004年11月有关ODA的报告中抱怨看不到中国记载日本对北京机场建设所做贡献的纪念牌。(22)中国政府最近认识到,日本人的这种感觉削弱了日本公众对ODA的政治支持。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承认自己没有让同胞们充分了解日本ODA的规模。(23)
第三是中国自身的援助计划。2000年前后以来,中国自身的援助计划也成为日本终止ODA的重要依据。据日本外务省统计,中国在2000年向58个国家提供了4.5亿美元的援助。(24)2005年10月,中国宣布在此后三年间以贷款和出口信贷方式向联合国千年计划捐款100亿美元。事实上,中国不仅显得有充足的预算手段提供经济援助,而且这种发展援助的非透明性(如援助条件和受援国)也令日本政府担忧。而且,这种援助有一些是出口信贷,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机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规定,这不是ODA,而是属于其他官方贷款(OOF)。2001年10月的日本对华经济合作计划表达了日方的这种关切。该计划指出:“将来日本会敦促中国提高其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透明度,鼓励中国公开这种援助的成果。”不过,至少就ODA受援国自身也提供ODA的行为模式而言,日本一定记得,当它从1954年参加科伦坡计划开始提供ODA时,自己仍是经济援助受援国。1964年以前,日本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第一条新干线)一直在用世界银行贷款。当上述批评于2000年出现时,这一点也为时任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的饭村丰所承认。(25)此外,印度如今位列日本贷款三大受援国之一,自身也有相当可观的ODA计划。
第四是中国的军备增强。中国的军备增强及军事政策尤其让人产生这样的看法:不仅中国已足够富裕、不再需要ODA,而且日本不明智地通过援助计划滋养了一个正在扩大的军事威胁。当日本于1979年就启动对华ODA计划展开辩论时,安全关切即已浮出水面,因为中国享有核大国地位,而日本禁止输出武器。由于援助能让受援国腾出稀缺资源用于军事建设,因此任何经济援助都至少间接有助于受援国的军事建设。为避免提供军事装备,大平首相于1979年公布所谓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明确排除军事援助。
随着中国军事开支自1989年开始两位数的年度增长,至少自1991年3月以来,日本政府已数次将ODA的继续与中国军事预算的扩大及更高透明度相联系。(26)1991年4月海部政府确定的ODA四原则,在1992年6月成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大纲的一部分。(27)
最后,有关尖阁/钓鱼群岛所有权和海上边界划分的东海领土争端,中国增强海军军备,加之日本声称中国军事入侵其专属经济区,成为日本各界人士要求终止贷款计划并将日本ODA重点转向内陆省份、减轻贫困、保护环境甚至改善中国人对日观感(比如通过青年交流)的重要依据。
日本ODA政策的总体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在讨论2004-2005年导致日本终止贷款计划的变化前,有必要考虑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ODA政策的总体变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几个批评性报告、ODA丑闻和公众对传统ODA政策的批评,使日本的ODA关注重点转向减轻贫困、环境可持续性和人类安全。不论是日本还是外国,政府越来越依靠非政府组织分配ODA。ODA效益、义务和保持公众的支持受到更多关注。
最后一个重要变化是外务省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有助于执政联盟政治家和公众舆论发挥更为强势的作用,后二者对中国的批评要强烈得多。对华ODA于1979年启动时主要由亲华政治家(受到亲华的公众舆论支持)推动,此后20多年里在外务省领导下由行政官员执行。现在的情况再度恢复为政治家推动决策程序,但他们的对华态度却不再友好。而且,由于政府的预算压力,ODA已普遍引起政治家的更大兴趣。日中关系的恶化使ODA政治化,成为外交政策工具。行政机构总体上成为广受批评的对象,外务省的中国学派(China School)被指责对中国太软弱。结果,中国学派的一些外交官自身变为对华强硬政策的支持者。(28)ODA的未来和外务省在其中的作用成为后者的一个重要议题,因为外务省的大部分预算与ODA有关。1960年代初,ODA占外务省预算总额比例不到20%,到2000年代已超过70%。
上述变化直接影响日本对华ODA计划的政策。最初的后果之一是拨款期缩短。在日本的受援国中,中国是唯一基于多年一次协定而非一年一次协定接受ODA贷款的国家,目的是和中国的五年计划体制相配套。但为了恢复对贷款计划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日本政府在1998年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自2001财政年度开始终止这套体制。不过,外务省实际上仍努力在中国的长期框架内运作,因为许多项目工期的缘故,这往往也更自然。
2000年,外务省由宫崎勇任主席的一个顾问小组指出,鉴于日本严峻的财政形势和公众对中国的各种批评,可以削减对华ODA。(29)外务省以此为基础着手准备对华国家援助计划,但在自民党要求下,名称改为对华经济合作计划,以此表示自民党不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30)该计划声称,在选择项目时,不仅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也要考虑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意味着它支持与环境、经济改革、消除内陆地区贫困政策、增进相互理解的人员培训有关的项目。与本文背景尤其相关的提议是,基础设施项目应由中国自身承担,贷款协定应该一年一次。
自民党于2000年12月发布的报告比外务省的报告严厉得多,它更多提到了上述各种批评。自民党与本文背景尤其相关的提议是,为增强日本援助的政治效果,将无附加条件贷款——非ODA政府贷款——纳入日本对华发展基金。(31)
2004财年的贷款安排体现了日本贷款政策的新趋势。七个项目中有六个是环保项目,占总金额的94%。它们尽管被称作“环保项目”,但是包括用于改善供水净水体系的贷款,甚至包括安装天然气管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基础设施项目的特点。(32)
贷款额的减少和偿款额的增加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对华ODA贷款额显著下降。它具体体现在:2000年是2144亿日元,2001年降到1614亿日元,2002年是1212亿日元,2003年为967亿日元,2004年降至889亿日元,2005年是748亿日元。(33)中国因此位居日本对外ODA贷款额的第四位,排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之后,而长期以来中国不是排在第一就是第二。中国在累积贷款额增加的同时,偿款额也在增加。这一变化在日本的公开讨论中几乎未被提及,日本政府提供的不完整信息和令人混淆的术语也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尽管公布达成协定时的利率,但并不透露具体某年偿还贷款时的利率构成。日方使用的术语和分类与OECD也有差异。日本的统计数据以协定为依据,而OECD的数据仅仅基于支付额。这一数字指的是净支付额,等于总支付额减去偿款额。因此,OECD统计的2002年贷款额是9亿7190万美元,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却是10亿2000万美元(1212亿日元)。(3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日本讨论终止贷款计划和协定金额自2000财年的最高值减半的同时,其对华贷款实际支付额却一直在增长:2003年对华支付总额为1149亿日元,2004年增至1271亿日元。原因在于从贷款协定达成到最终支付需要5-7年。因此,在2008年之前,实际支付额还将增长。日本媒体甚至已有报道称中国的年度偿款额已超过新的贷款协定额。(35)虽然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但两方面数字已非常接近:2003年对华支付总额为1149亿日元,而偿款额达1052亿日元(包括652亿日元的本金偿款和约400亿日元的利息)。
2004-2005年有关终止对华ODA计划的讨论
ODA对华部分乃至其总体都在重新定位。由于对中国的不满增加,新的对华贷款协定金额显著下降。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自2004年起就开始谈及终止日本对华ODA问题。2004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由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仍拒绝在两国间举行首脑峰会;夏天的亚洲杯足球赛上爆发了中国球迷反日事件;中日东海争端升级,等等。
根据笔者研究,日本官方首次在政府最高层提及终止日元贷款计划是在2004年10月。2004年10月3日,就在刚刚接任外相职位后,鹰派的町村信孝在东京的一次有关ODA会议上表示,中国“总有一天”会从日本的援助毕业,不过其内陆地区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目前为时尚早。(36)2004年11月22日,这位外相说,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从日本的ODA毕业合乎情理。(37)这段声明得到小泉首相的响应,他在11月28日赴老挝出席东盟会议途中表示,中国从ODA毕业的时间到了。(38)小泉强调:“我希望中国将来能成为捐助国。我们愿意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ODA的相关事宜。”(39)政府的表述得到日本媒体的普遍支持。即使自由派的《朝日新闻》也认为:“当经济受援国能够自立时,自然要终止援助或将援助转向别的地区和国家。”(40)2004年11月,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有关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提供ODA的报告,建议终结对华ODA,因为这种ODA不是必不可少的。(41)其原因包括中国的经济成功、日本自身的财政问题、中国军费开支的增加、中国的载人太空事业和反日教育。日本的ODA应该用于消除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的观点遭到驳斥,反对意见认为这种财富再分配工作是中国的内部问题。(42)
中国政府对日本将ODA与批评其政策相联系感到不悦,采取了对抗姿态。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被问及日本外相2004年11月22日声明时表示:“中国人民只需依靠自己的智慧、力量、团结和决心来建设一个发达的国家。”(43)中国财政部官员甚至在2005年的会谈中曾向日方表示中国不再需要日元贷款。(44)其他言论则较为谨慎。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45)他在几天后说,终止经济援助会破坏双边关系。(46)中国外交部副发言人在11月30日宣称,希望ODA能对发展双边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不负责任的言论只会有损中日关系”,“我们无法理解日本国内的言论。必须在特定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看待ODA”。(47)
中国新华社就日本终止贷款计划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外交部认为这一问题的特定历史背景如今依然存在,从而间接表示将日本的ODA视为赔偿。(48)此后据报道,温家宝总理对小泉的前述提议反应相当冷淡,他在感谢日本ODA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敦促日本首相“善始善终”、避免日元贷款计划成为新的政治问题。他们大体上达成一致,同意进行事务性谈判,从而在数年内停止新的贷款。(49)
2005年3月,日本政府最终宣布已通知中国:计划自本财政年度开始削减低息贷款规模,到2008财年逐步终止全部计划,同时继续提供用于人员培训和环境保护计划的赠款与技术援助。(50)在将来的某一时间,赠款援助也会逐步停止。选在2008年显然是因为北京奥运会,在日本看来这标志着一个国家从ODA贷款毕业,日本在1964年主办奥运会时就是如此。2005年3月,町村外相宣布与李肇星外长已通过电话交谈基本达成一致,同意新的ODA贷款协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结束。(51)4月,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就到2008年终止贷款计划达成口头共识。2006年,由于与中国的争端,尤其是东海问题和历史问题,日本政府甚至暂缓签署2005财政年度日元贷款计划。2005财年结束差不多三个月后,748亿日元(比2004年进一步减少)的协定于2006年6月23日签署。
结论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2005年决定到2008年终止所有对华ODA贷款,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它涉及对中国某些政策的批评、日中关系的恶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对日本利益的影响、日本经济和预算问题背景下公众舆论对援助普遍的厌倦等。这项决定的政治性显而易见,因为政府从未提及其终止对华ODA的一贯原则,也未说明认为中国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52)
面对中国从日元贷款毕业的必然趋势,中国和日本相关政府机构和政治家都应具有相当的政治远见,从而避免决策过程如最近那样受到日中政治关系恶化的不良影响。然而,除惯性之外,强大的政治和官僚利益也不利于这种政治远见和智慧的形成。就中方而言,当然没有兴趣与日本讨论有关对华ODA的终止问题,因为此类贷款对中国非常有益。就日本外务省而言,终止日元贷款(从而可能打开终止所有对华ODA的“潘朵拉盒子”)将使外务省丧失其最有力的对华外交政策工具,同时向中国释放更为负面的信号。不论是对于削减其他ODA,还是对于强化当前调整ODA决策的趋势,都将树立一个由外务省承受代价的先例。日本政府也不会乐见失去一个迄今为止一直按时偿还其贷款的债务国。虽然肯定还有比中国更需要日元贷款的国家,但中国良好的偿款记录却很难被取代。
缺乏远见或政治智慧导致两国间的激烈争吵,日本对华观感的恶化迫使日本决策者决定终止对华贷款,这进一步激化了已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趋于严重的历史问题(赔偿和ODA的联系),使中国更不愿意对日ODA贷款计划表达适当的谢意。贷款计划的终结既没能让人们庆祝日本的主要ODA项目圆满结束,也未带来在中日关系困难时期缓和紧张局势的可喜机会,相反却笼罩在被中方视作惩罚的阴影之下。如今日元贷款计划的终结可能给日本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以终结赠款和技术援助计划。日本2003财年对华赠款援助合计约52亿日元,使中国成为日本赠款援助的第九大受援国。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位列第五,排在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之后。(53)
但是,日中关系在更长时间内可能蒙受的最大损失是,削减ODA和很大程度上因中国威胁而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将使日本的对华参与政策进一步失衡。为增强日本的威慑力和对华影响力,政治和军事权力制衡在日本受到更多重视,而其代价则是对华参与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奖励因素被削弱。这也将增强日本对美国政策的依赖。中方不能回避对这一变化负有的责任。
最后,这种分析显示,历史问题在日中关系中几乎无处不在,仍需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处理。致使日元贷款计划终结的情况表明,双方利用历史问题实现政治目的充满风险。中国把过去的历史与日本的道德义务相联系,认为提供ODA是对中国放弃赔偿的补偿。这种说法遭到反驳。在日本人眼中,这给ODA染上赔偿的色彩,使其成为中国的对日筹码(“特定历史背景”)。许多日本人后来因而变得不友好,对华ODA的支持热度减退。同时,这给日本人造成的印象是,通过提供ODA可以跨越过去的历史。将ODA与过去的历史相联系——加之中国政府没有让其国民充分了解日本ODA的规模——也严重削弱了中国人对日本ODA的感激。为向国内证明对华ODA的合理性,日本颇费口舌地将ODA与过去的历史相联系,只会强化上述认识,从而给日本制造一种道德义务。这种义务难以依据世界银行的经济毕业标准终结,也难以因日本对中国现行政策的不满而结束。
虽然双方都必须更加努力以避免ODA赠款与技术援助出现类似的不幸情况,但ODA最终无法与双边关系的总体发展脱钩。ODA虽然有助于改善双边氛围,但仅靠ODA无法创造良好的氛围!
注释:
①日本外务省统计数据。
②Funabashi,Yoiehi (船桥洋一),Alliance adrifi ,Washington,D.C.: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9,p.407; Takamine,Tsukasa(高峰司),"A new dynamism in Sino-Japanese security relations:Japan's strategic use of foreign aid," The Pacific Review,Vol.18,No.4,December 2005,pp.439-462.
③Laura Newby,Sino-Japanese Relations:China's 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1988,p.41;徐承元:《日本の経済外交と中国》,[日]庆应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60页。
④Laura Newby,Sino-Japanese Relations:China's Perspective,p.40.
⑤Reinhard Drifte,Japo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1989: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London:Routledge,2003,pp.3-4.
⑥冈田实的电子邮件,2006年2月19日。
⑦Reinhard Drifie,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1989: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p.141.
⑧[日]国分良成:“冷戦終結後の日中関係”,《国際問題》,第490号,2000年1月,第13页。
⑨[日]五百旗头真:“反中‘原理主羲’は有害無益ごめゐ”,《中央公論》,2004年3月,第81页。
⑩徐承元:《日本の経済外交と中国》,第81页。
(11)Tanaka,Akihiko(田中明彦),"ASEAN factor in J's China policy:Japan's government loans to China 1979,"Paper for the Asia Dialogue Conference,27-29 October 1986,p.9.
(12)徐承元:《日本の経済外交と中国》,第129页。
(13)毛利和子、张蕴岭编:《日中関係たどぅ構築するか?》,[日]岩波书店,2004年,第11页。
(14)[日]冈田实:“中国にぉけゐODA研究から見るODA観と日中関係”,《国際協力研究》,第19卷,第2号,2003年10月,第24-25页。
(15)[日]宫本雄二:“对中経済援助をどぅするか”,《外交フォ一テム》,,第144号,2000年8月,第80页。
(16)[日]《参議院政府開発援助調查発見報告書》,2004年11月,第78页。
(17)Masuda,Masayuki(增田雅之),"Japan's changing ODA policy towards China," China Perspectives,No.47,May-June 2003,p.40.
(18)Reinhard Drifte,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1989: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pp.70-71.
(19)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2005年度报告,第119-120页。
(20)[日]《朝日新闻》,2001年2月2日。
(21)[日]村井友秀:“アジアの安全保障と日中関係”,《外交時報》,1998午1月,第18页。
(22)日本参议院报告书,2004年,第45页。
(23)[日]《朝日新闻》,2000年10月10日。
(24)[日]《朝日新闻》,2001年10月28日。
(25)Masuda,"Japan's changing ODA policy towards China," China Perspectives,No.47,May-June 2003,p.43.
(26)Reinhard Drifie,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1989: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pp.43-44.
(27)Reinhard Drifte,Japan'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Houndmills/Basingstoke:Macmillan/St Antony's College,1998,p.129.
(28)Takamine,Tsukasa,"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Japan's China Aid Policy: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Power," Japanese Studies,Vol.22,No.2,2002,p.203.
(29)[日]《日本时报》,2000年12月19日。
(30)Masuda,"Japan's changing ODA policy towards China," China Perspectives,No.47,May-June 2003,p.48.
(31)Takamine,Tsukasa,"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Japan's China Aid Policy: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Power," Japanese Studies,Vol.22,No.2,2002,pp.204-205.
(32)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新闻出版物。
(33)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新闻出版物。
(34)OECD2004年度报告,第120页;“政府開発援助白書2003年版”,日本外务省,东京,2004年3月,第56页。
(35)[日]《选择》月刊,2004年9月。
(36)[日]《日本时报》,2004年10月4日。
(37)日本共同社,2004年11月26日。
(38)日本共同社,2005年3月17日;[日]《读卖新闻》,2004年11月29日。
(39)[日]增田雅之:“二つのツナリォガ交錯する日中関係政策課題としての‘戦略对話’”,《東亜》,2005年3月,第3页。(http://e-asia.lazankai.org/bol/tokusyu.html?no=1)
(40)[日]《朝日新闻》,2004年12月2日。
(41)日本参议院报告书,2004年,第77页。
(42)日本参议院报告书,2004年,第79页。
(43)[日]《日本时报》,2004年11月28日。
(44)2005年10月6日的访谈。
(45)[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4年12月1日。
(46)[日]《读卖新闻》,2004年12月4日。
(47)日本时事社,2004年12月3日。
(48)日本共同社,2005年3月17日。
(49)日本共同社,2005年3月3日。
(50)[日]《朝日新闻》,2005年3月3日。
(51)[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3月18日。
(52)Masuda,"Japan's changing ODA policy towards China,"China Perspectives,No.47,May-June2003,p.47.
(53)[日]《读卖新闻》,2004年1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