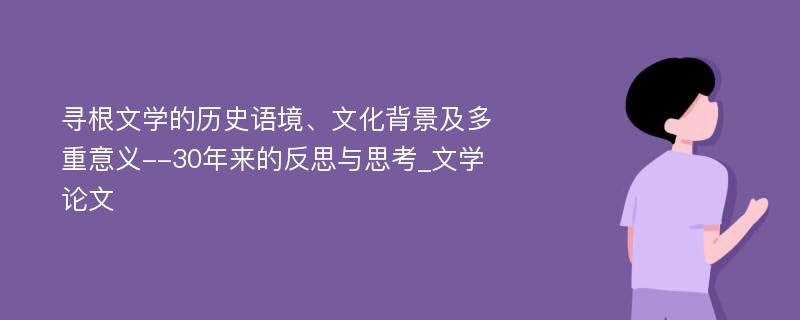
寻根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与多重意义——三十年历程的回望与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三十年论文,随想论文,文化背景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发表了《文学的根》,是为“寻根文学”的历史刻度。同年,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发表于《作家》6月号;郑万隆的《我的根》,发表于《上海文学》7月号;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发表于7月6日《文艺报》。张炜、郑义、王安忆、李锐等知青作家也都有相关文章陆续发表。随着批评界的迅速命名,“寻根文学”声势浩大地展开。这一年也是中国小说的革命年,文学观念的多元化格局迅速形成,冲击着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平分天下的旧有局面,紧随寻根文学之后,先锋小说和新写实文学几乎同时兴起。在这一次文学哗变中,由知青作家推动的寻根思潮是其中最强劲的一股美学风暴,主要作家都已经有著作发表,不少作品赢得了国家级大奖,拉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整体转向。而且,至今作品源源不断,以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为高潮。今年,是“寻根文学”发动的第三十个年头,回顾当年的缘起与演进,是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环节。 “寻根文学”的序曲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1980年《北京文学》第10期的小说专号上,颇费周折地低调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引起了出乎意料的轰动。1982年《北京文学》第4期,发表了汪曾祺的创作谈《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同年,贾平凹发表了《卧虎说》,表达了对茂陵霍去病墓前卧虎石雕的激赏,借此宣告自己的艺术理想:其一是对汉唐恢宏文化精神的推崇,其二是对古典美学风范的感悟:“重精神,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从此确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方向。还应该提到的是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八十年代初,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陆续发表了《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角公鹿》等以山林狩猎民族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顺应着整个民族感伤主义历史情绪的同时,也完美地表达了原始的自然观,以及瓦解过程中民族精神心理所承受的巨大苦痛,以抗拒遗忘的决绝姿态引起广泛的激赏。回族作家张承志以《黑骏马》等中短篇小说,表现草原牧民的生活命运,以丰沛的视觉效果与饱满起伏的情感旋律,以及富于中亚装饰风格的精致语言形式,赢得众多的读者。他们无疑是最早的寻根作家,汪曾祺四十年代以现代派的前卫姿态登上文坛,经历了三十多年沉浮坎坷的历史命运之后,以对抗战之前原生态乡土生活的诗性回顾与风俗画的抒写,迅速完成艺术转身,接续起五四以后沈从文、废名、萧红一脉乡土文学的诗性挽歌传统,也衔接起中国叙事文学的多种文体。来自乡村的贾平凹,试验了各种外来方法之后,回身反顾重新发现了被自己抛弃在身后的乡土,在现实的激变中寻找回归自然母体的精神通道。他们直接启发了经典寻根作家们的美学自觉,而且,都以鲜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与民族情感的独特心灵方式,呈现出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他们的创作和历史的巨大转折同步。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历史迅速急转弯。次年高考制度改革,由推荐改为考试入学。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决定结束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重新评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推动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道主义被重新阐释。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中,农村经济改革迅速铺开,实行联产承包制。城市经济的所有制有所宽松调整,个体户大批涌现。中美关系明朗化,政治外交全面解冻;设立特区,广泛引进外资,各大都市的空间由此迅速改观,涉外的大饭店大批兴建,不同肤色的人种混杂行走在主要商业大街,巨大的广告牌在街头闪烁。知青大批返城,带着历史的创伤与对新生活的憧憬,迅速进入一个新旧杂陈的世界。 经历了漫长的文化禁锢之后,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借鉴学习成为新的历史语境。国家大批派遣留学生,允许自费留学。外国文艺团体频繁来华演出,轻音乐兴起,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全国,外国电影占领大份额的票房。外国美术作品大批公开出版,梵·高的《向日葵》点燃了青年一代的如火激情。民办刊物《今天》创刊,《星星画会》短暂展出,朦胧诗在青年中流行,美术界率先寻根,袁运生的壁画引起争论……一系列新艺术的潮汛冲击着传统艺术的堤坝。外国文学大批翻译出版,特别是长期被封杀的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解禁,卡夫卡、海明威等欧美作家成为最早的世界现代文学思潮标记,学习现代派的技巧成为艺术探索的主要趋向。1981年,《长春》(即《作家》的前身)发表了宗璞的《我是谁》,在“伤痕文学”的感伤潮流中悄悄开启了精神心理写实的向度与政治迫害中自我丧失的记忆。与此同时,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著作以各种方式再版,像出土文物一样从尘封的文学史中赫然涌现。而川端康成、辛格等东西方边缘种族的诺贝尔获奖者,则校正着中国作家的美学罗盘,克服了对欧美文学的迷信与盲目追捧。福克纳以故乡邮票大小的一块地方走向世界,更是鼓舞了中国乡土作家的文学壮志。特别应该提到1984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同时出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轰动了中国文学界。如果说前寻根时期的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主要是在艾赫马托夫等前苏联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抒情象征中汲取诗性的灵感,而经典的寻根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马尔克斯与其他拉美作家的影响。毫无疑问,拉美作家把中国作家从俄苏文学的魔咒中解放了出来,也从文学的欧美现代化精神强迫中解放出来。文化人类学成为普遍的学科基础,宗教意识、生命哲学、叙事方式的借鉴等成为新的艺术革命向度。追寻民族生存之本、以生命伦理反抗文化制度的残酷压抑,对于民族民间原始思维的重新发现,拓展文学的表现领域,推进文学形式的变革,都冲撞着过于狭窄的旧有文学观念,形成一代归来者抵抗现代化焦虑的艺术反叛姿态。 历史的转机开启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学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以对社会历史的感兴抒发记录民族心理的苦难历程。主要的向度还是在题材领域闯禁区,随着政治反拨的幅度亦步亦趋,感应着时代巨变而抒发个体的也是整个民族的情绪。对于艺术手法的探索,则是以现代派为起点,但多数作家策略性地解说为技巧问题,以一九八二、八三年“四只小风筝”的通信引起的风潮为典型事件。另一种策略则是以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论证现代派的合法性,以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最为典型。尽管如此,所有的艺术探索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经历了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晕眩期的青年作家,本身也面临着创作上的惶惑,1984年11月下旬,《上海文学》《西湖》杂志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上海——杭州联合召开了由新锐青年作家和评论家与会的关于文学创作的研讨会。寻根文学的宣言就是在这之后不久纷纷发表,多数作家的创作也因此面目一新,主要的寻根作品迅速发表。他们汇聚了现代派的形式革命,在东西方八面来风的冲击下,试图在民族生存之本的历史深层,开掘文化再造与艺术表现的精神、艺术资源。 经典的寻根作家几乎都是知青出身,在七十年代开始写作,急剧起伏的人生曲线使他们对世界的感受尤其错杂,昔日的家园已经面目全非,生存的窘困、没有家园的失落感都需要心理的调整,与城市的心理疏离与时代的隔膜,也需要精神的自我巩固。用朦胧诗人梁小斌的诗句概括,就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知青经历形成了民间生活记忆的经验世界,这使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时空都较为稳定的乡土生活中,以审美的凝视获得精神心理的稳定感,在历史的振荡、时代的纷扰与大都市的混乱生存中,完成艺术精神的自我确立。这是“寻根文学”出现的重要心理根源,也是几代结束了放逐归来的知识者共同的心理需求,获得读者的热切反应便是历史的必然。此后不久,“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学术界兴起了文化热,大批的文化学术丛书编写出版,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最醒目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是寻根文学被接受与驳难的最基本的文化背景。 寻根文学的主要美学贡献,是把中国文学从对欧美文学的模仿与复制中解放了出来,克服了民族的自卑感,使文学回归于民族生存的历史土壤,接上了地气。尽管每个人的意向各有差异,但是都是以民族生存为本位,形成审美表现的基本视角。而对狭小窒息的当代文化的失望与批判,对民族精神再造的努力,则是一样的。韩少功浩叹:“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李杭育面对当代文化的尴尬,设想中国文化如果不是遵循儒家的规范,依照具有“宏大宇宙观”的老庄一脉浪漫主义潮流发展将会多么灿烂?!跨越文化断裂的精神探求,是在外来文化的参照下,重新发现文化传统自身的魅力。以现代意识镀亮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尽管每个人的抉择不一样。 寻根作家另一个共同的意向,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学本末关系的清理,由此完成向文学本体的回归。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更是深入阐释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宿命关系,而且这样的关系是所有母语写作者无法逾越的限制,接受限制是艺术创作的前提。这样的意向使中国的文学观念,逐渐大踏步地向着世界观的高度攀升,克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急功近利的肤浅文学观念,向着历史的纵深层面拓展的同时,也向着整体把握世界的艺术理想挺进。 作为自我巩固的艺术行为,寻根的宣言中还包括对各自艺术自我确立的感悟,并且,由此迅速开辟出自己的文学地理版图。郑万隆的《我的根》宣示以东北故乡山林中先民们古朴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坚守,完成对浮躁的现代社会心理的抵抗,《异乡异闻录》系列结集以《生命的图腾》为名出版,凝聚着他的美学理想。阿城继《棋王》之后,相继发表了《树王》《孩子王》和《遍地风流》系列,以第一人称的见闻,表现自己对民间社会的发现,对普通人英雄主义与质朴健康生命状态的敬佩与欣赏,而且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文化英雄:下棋、护林与学文化。《棋王》叙述了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以之探讨普通人和历史的关系;《树王》探讨了普通人和自然的关系,树死人亡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孩子王》探讨了普通人和文化的关系,一个普通劳动者对文化的向往与接受文化的艰辛,中国文化基本构成了个性鲜明的世界观整体。据说还有一部《车王》邮寄丢了,是探讨普通人和交通的关系吗?估计某一天会从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中冒出来。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逐渐成熟丰满,张炜的《古船》等一系列以山东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引起持续轰动,矫健的大量作品、何立伟的《白色鸟》等一系列作品,都是以质朴恬淡的生存景观抵抗人欲横流的现代化进程,记录这些和谐的生活场景瓦解破碎的过程,大有“礼失求诸于野”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共同趋向。 当然,这些寻找回归传统文化精神通道的悲壮努力并不都是有效的。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一批以湖南山地民间生活为内容的作品,以《诱惑》为名结集出版,可见对于无法抗拒的文化宿命感体验之深刻,表达了在落后愚昧的乡村传统与浮华浅薄的现代都市生存之间,精神心理挣扎的艰难,以新的方式演绎着“我是谁”等哲学人类学的命题。他的寻找以文化价值认同的失败为结局,美学回归的成功为结果,楚文化无疑为他提供了自《楚辞》开始的精神情感表达的独特心灵形式,所谓“末世的孤愤”,精神的矛盾与认同的危机都寄予在完整的、渗透着楚音的语言形式中。王安忆在寻找自己来历的同时,也探索着民族历史生存内在的稳定结构,以及转换为当代话语的方式,《小鲍庄》是探讨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文化寓言,《长恨歌》则是探讨“海上繁华梦”金钱至上的意义空间;《纪实与虚构》记叙、回顾了在这样两种空间的身份转换中个体的心路历程,以及在血脉的寻绎中,通过边缘身份的确立而完成繁难的文化认同。对于乡土与现代大都市的双重心理疏离,是她表达认同危机的主要方式。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自己时代的文化思潮,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抵抗着全球化浪潮的滔天洪水,固守着精神的方舟。 寻根文学的思潮拉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少作家的创作因此而面目改观,史铁生由“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潮流中脱身而出,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插队的故事》等知青题材的小说重新审视乡村生存。张辛欣从自我出发的写作中掉头,纪实性的《北京人》系列以对当代中国人生存的个案搜集扫描出民族生存与心灵的当代史切片。铁凝从青春写作的格局中跳转,以《麦秸垛》为象征,表现乡土人生原始蒙昧的生殖气氛。1985年,《西藏文学》推出了“魔幻现实主义”专号,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发表了《系在皮带扣上的魂》与《西藏,隐秘的岁月》,由表现藏民族剽悍的原始生存状态,改为关注这个民族的精神失落、迷茫与无望的寻找,以及世代循环的生存模式。李锐迅速写作发表了《厚土》系列,带给文坛意外的惊喜。连先锋作家刘索拉在完成了精神的反叛与情感的抒写之后,第三部中篇《寻找歌王》也以对民族民间原始艺术精神的寻找,表达对浮躁的现代生存的心理抵触。也有的作家是以反驳的方式回应这股思潮,譬如,马原以《冈底斯的诱惑》登场,在展现小说虚构本质的同时,表达了科学理性与牧歌情调的冲突,矛盾的自我分裂外化在两个主人公身上。洪峰的《瀚海》干脆宣称:“到那里(故乡)去寻根,还不如寻死痛快!”尽管反对的是艺术主张,而写实的审视则是一样的,只是放弃了对于整体结构的把握,而专注于审视生存的本相与表现心灵的体验。 此后不久崛起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作家,也是以个体精神的体验与民众生存之本的表现刷新读者的阅读经验。他们和寻根文学的学科基础有着交集,苏童对于乱伦宿命的强调,对世界不可知的感受,明显可以看到对韩少功们哲学思考的深入。余华的大量作品表现了无法抗争的命运,还有迷宫一样的文化价值罗网中别无选择的尴尬与存在的遗失;格非表现了语言自身的混乱空洞与主体的有限性,都是对历史、文化与个体认知能力的质疑;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以碎片化的情节与精粹的诗性联想,表达着对世界人生的个体感悟,延续着寻根作家主题多义的叙事实践。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是对民生问题的悲情叙事,《伏羲伏羲》中被扭曲的不伦之性与杀父的故事,明显可以看到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视野。刘震云基于民本立场的历史追问,池莉对于窘困生存的琐碎叙述,方方以亡灵的视角不动声色地展现底层市民生活的凄惨景观,都可以看到寻根文学凝视民间生活视角的延展与推进。这些作家的创作在宣告了一个浪漫主义文学时代完结的同时,也传递着新时期人道主义的文学基因,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尤其是对物质生存与精神生存的双重关注。而对民间社会的审视,则调整开拓了寻根文学的视野,当下的生存依然非常严峻,存在的困苦消解了宏大的主题与浪漫的诗意。 影响最大的要数莫言,1985年之前,莫言的创作追求唯美的效果,可以看到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遗韵,比如《乡村音乐》。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他完成了艺术自我的确立,也完成了小说文体的革命,“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版图迅速开疆破土日益壮大,至今势头不减。当然,他的艺术转变是克服创作困境的内在突破,不完全是寻根文学影响的结果,但是寻根作为一股思潮,是八十年代中文坛的主潮,所有的写作者都不能无视。而且,他艺术确立的基本情感矢量和寻根作家是一致的,其文化背景也有着广泛的重合与交集,比如对川端康成的激赏、在福克纳的启发下立志把故乡“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的缩影”和“世界史的片段”,《百年孤独》的决定性影响,等等,成为新一代世界主义的乡土作家。特别是他三十年持续不断的成功探索,主要是以乡土民众的生存为基本视角,在中国叙事传统中汲取文化资源,应该说是延续着寻根文学开辟的方向发展。当多数经典寻根作家放弃或者转变创作方向的时候,莫言却比别人走得更远,使中国小说彻底回归到了它古老的源头:边缘性、民间性与世俗性。究其原因是写作者的身份决定的,知青和农民之子的差异决定了叙事立场与文化认同的差异,同年经验的初始记忆也是文化资源择取向度差异的根源,以至于几乎无法对莫言进行文学史的归纳。“强大的本我”既浸润在潮流之中,又置身于潮流之外。 寻根文学本质上是一场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在冲决了为政治与政策服务的狭窄轨道之后,完成了文学自我回归的嬗变。尽管寻根作家的意向差别极大,但是整体完成了文学由庸俗社会学僵硬躯壳中的成功蜕变,也挣脱了膜拜欧美发达国家现代主义文学,亦步亦趋模仿学步的精神桎梏。根据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一个诗人无论他多么傲慢,其实都代表着无数个声音在说话。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制定何种发展战略,都属于历史理性的范畴。文学显然是非理性的,它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情感与广大无意识领域中的真切感受。实现现代化、与世界接轨,是中国人的历史理性经历了漫长曲折的痛苦磨难之后,在八十年初形成的全民共识;而八十年代中的“寻根文学”则是中国人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对全球化浪潮一次本能的抗争,是对百年来现代化强迫症与文化乌托邦的艺术反动,更是改革开放之初民族精神情感与广大无意识领域中真切感受的艺术呈现。所以,它是民族精神心理的重要历史标记。 寻根文学的作家跨越断层的方式,其实接续着晚清至五四一代知识者的共同努力,梁启超以小说新民,在从事政治革命的同时,也希望复活中国古代善良之思想;鲁迅试图以文学来改造国民性,早期借助进化论,主张“拿来主义”,晚期在古代神话的意义空间中完成民族精神的发现与自我确立。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被批评界迅速与阿Q类比,当成同一系谱中的人物是典型的泛文本联想。阿城对民间英雄的讴歌,则是鲁迅思想一翼的延续,其“忧愤深广”、其“沉忧隐痛”的内在情绪也是近代以来知识者的历史情绪。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和张炜、矫健等作家的创作,对于民间社会的凝视继续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维度。王安忆对乡土民众的关注与对市民社会的心理疏离,也是鲁迅等一辈文人共同的创作主题。究其终极的历史根源,是现代性的文化时间焦虑在全球空间的迅速蔓延,使一些最基本的主题延续至今,譬如溃败、譬如文化抵抗、譬如民族精神再造,等等。无论怎样和世界接轨,有三道坎都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者无法逾越的,这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民生的问题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所以,无论寻根的结果如何,如一些批评家所讥讽的“寻根变成了掘根”,但是他们悲壮努力的思想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寻根既是对民族精神之根的寻找,也是对文学之根的寻找,不仅是对文化精神的认同,也是对艺术形式的继承。经典的寻根作家在寻找寄托自己心灵世界相对应的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寻找适应自己的叙事表达方式,而且试图和文学传统重新建立独特的联系。除了在主题学领域,他们衔接起现代作家们的抒写,而且在艺术风格领域也延续着他们的革命性贡献,就连他们对边缘种族文学不约而同的情有独钟,也继续着周氏兄弟当初翻译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的动机,基本历史处境的相似性无疑是接受的心理基础,只是具体的历史情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选择认同的标准也随之变化,二十世纪实在是一个人类苦难深重的大劫难。五四引诗文入小说带来叙事模式的转型,几乎是文学史转折的形式标记,经典的寻根作家几乎都继承了这个传统。譬如,使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棋王》,就其文体来说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史传文学的传统,以弱胜强的类型故事,是抒写少年英雄的传统;《树王》也是英雄的故事,但是一个失败的悲剧英雄,故事寄托在吊文的形式中,结束于对萧疙瘩墓的凭吊;《孩子王》则是一首骊歌,送别的仪式感极强。这样的更续关系,使他们沟通了更久远的文学传统,也把诗文的精神升华到宗教的高度,具有超越情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意义。现代叙事学的传播,又使不少作家自觉地运用了叙事传统中的原型,王安忆最突出,《天仙配》是典型,建立在两种世界观差异上故事叙事,置换出张爱玲式无奈的反讽语义。庄子的哲理寓言转换为文化寓言,也是寻根作家所普遍使用的形式,最典型的是张炜的《九月寓言》。莫言干脆以神话的基本思维方式不断地置换变形,容纳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接续起志怪、唐传奇、宋人平话、元曲、明清戏剧与小说,以及近代兴起的地方戏等一派富于想象力和文辞华艳的叙事传统。当然,他们的继承关系都不是单一的,是多元复合、中外古今混融一体,因而艺术探索也就沟通了更加久远的文学与文化传统,文化史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寻根文学的作家都有着语言的高度自觉,每一个人择取与提炼的方式又各不一样,但都把文学语言提升到艺术本体也是生存本体的高度。贾平凹对母语陕南方言的自由运用,成为质朴恬淡的心灵世界最直接的外化;李杭育强调小说语言的文化韵味,以语体风格容纳地域文化的风俗;阿城对书面语延伸出来的当代口语的精准把握,显示着感觉的独特与饱满,对话成功消解在叙述语言中的叙述策略,使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形神完备。王安忆以诗文与白话两种语言的交错融合,完成对追忆与流逝的时间形式的模塑,使文化诗学的意味弥漫在字里行间。李锐以大音稀声式的浑朴风格,描摹吕梁山的民间生存与民间思想,凸显着语言文化的世界观意味。莫言更是广采博收,在诗文、民间口语与戏剧、翻译语言等多个源头汲取营养,突出对话,并且把方言融入叙述语言,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最直接地体现着独一无二的艺术个性。而且,经典的寻根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话的精神,呈现出多种话语体系交错的复调结构,以及众声喧哗的狂欢美学特征,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正是这种对规范语言法典的成功艺术反叛,使他们的创作不仅在主题思想方面,而且在艺术形式方面都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世界新艺术潮流会合,不仅是形式技巧的拿来,包括哲学(特别是语言学转向)背景的重合;也使中国文学史的连续性获得长足的发展。“五四”开始的“文的自觉”经历了长时段的断裂之后,在寻根作家经典作品的语言风格中如泉喷涌,也使被阻隔的漫长文学史暗河涌流地表。不少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已经被确立为当代经典,这是他们对五四开始的汉语写作现代化转型进程里程碑式的独特贡献。只要是用汉语写作,每一个作家都是漫长文化时间流程中一个接力的选手,谁也无法彻底脱离母语自身的限制,创造性地继承是唯一的出路。 这就是寻根文学作为一场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在历史转折的山体炸裂时刻,兴起于废墟之上、多重意义的历史贡献。标签:文学论文; 寻根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棋王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