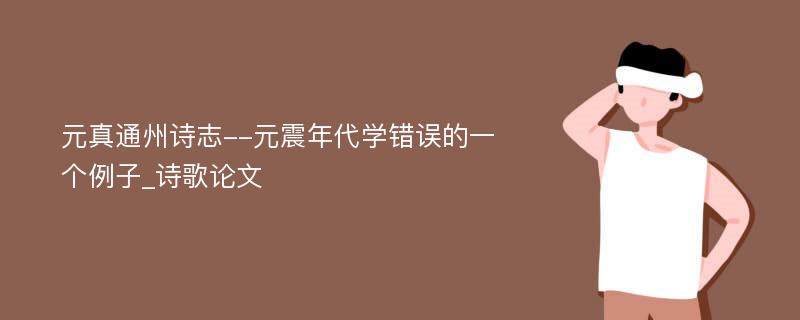
元稹通州诗歌编年——《元稹年谱》疏误举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州论文,年谱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6月版,以下简称《年谱》)是我国学术界一部有影响的元稹研究的重要著作;但它在元稹通州任上——无论是传主的行踪还是传主诗歌的系年——失误颇多,《年谱》对诗歌的编年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著者对诗歌作者生平的正确表述,更影响到读者对这些诗歌的正确理解,绝非是区区小事。《年谱》出版以来,信从者不少,引用者有人。现在冒昧地将我们不成熟的意见贡献出来,求正于海内外的方家,同时也就教于《年谱》的著者。
《年谱》元和十年“诗编年”栏内编有元稹诗篇《酬乐天醉别》《酬乐天雨后见忆》《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酬乐天见寄》等诗七首以及《酬乐天寄生衣》《酬乐天武关南见微之题山石榴花诗》《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酬乐天江州路上见寄三首》等诗六首;元和十一年编入《酬乐天见忆兼伤仲远》《酬乐天寄蕲州箪》等诗两首;元和十二年又编入《酬乐天春寄微之》《酬乐天书后三韵》《酬乐天频梦微之》等诗三首;“通州任内”编入《酬乐天叹穷愁见寄》《酬乐天三月三日见寄》两首,前后共计二十首。
《年谱》编年的理由是根据元稹白居易诗篇两两次韵的特定情况以及他们双方诗篇的内容,如元稹《酬乐天醉别》诗云:“前回一去五年别,此别又知何日回?好住乐天休怅望!匹如元不到京来。”据诗篇的内容,确是“初到通州时作”。又如元稹《酬乐天雨后见忆》诗云:“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是“初到通州口吻”,因而编入元稹初到通州的元和十年。又如《酬乐天武关南见微之题山石榴花诗》《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酬乐天江州路上见寄三首》等诗,白居易原唱作于诗人元和十年八月贬谪江州途中,所以《年谱》也将元稹的酬和诗篇编入元和十年。再如《酬乐天见忆兼伤仲远》,根据白居易原唱题下注“李三仲远去年春丧”以及李仲远卒于元和十年的事实,将元稹的和作与白居易的原唱一并定于元和十一年。
粗粗看来,理由十分充分。细细推敲,却来了问题。元稹白居易元和十年三月三十日在长安饯别之时,元稹白居易各有诗篇《沣西别乐天三月三十日相饯送》《城西别元九》纪实。分手之后,元稹独自一人骑马奔向通州,两月之后元稹到达通州,赋诗作文向白居易报告通州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心情,这就是《叙诗寄乐天书》和《见乐天诗》。白居易送别元稹以后,按捺不住自己的悲愤心情,有《醉后却寄元九》《雨夜忆元九》等诗。
但白居易收到元稹的诗文之时,大约已是武元衡被刺杀的六月,白居易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稍稍延误了时日。待到白居易的诗篇寄达通州,元稹已经染病在身,一时无暇顾及,没有及时回酬。同年八月,白居易出贬江州,十月,元稹因病移地兴元就医,两个好朋友从此失去了联系。白居易虽然不时有诗篇寄往通州,但已经离开通州的元稹并没有收到,自然不会回酬。所以白居易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的《与微之书》里说:“微之,微之!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书欲二年矣!”从元和十年三月三十日元稹白居易长安分手至白居易写信的十二年四月十日,确实已经是“已三年”不见面;而从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逆推“欲二年”,白居易不得元稹诗文当从元和十年十月间开始。
离开通州在兴元治病的元稹自然也没有收到白居易寄往通州的诗篇,他因而对白居易的思念越来越切。诗人在汉水上游的兴元有《相忆泪》《水上寄乐天》诗篇,抒发自己对白居易的思念。但白居易自然也没有收到元稹的这两首诗篇,所以几乎每诗一定回酬的白居易这次也没有回酬。
《年谱》将《相忆泪》《水上寄乐天》两诗系年“乙未至戊戌在通州所作其他诗”似乎过于笼统,元诗作于元稹移地兴元期间,亦即元和十年十月至十二年五月之间,地点在兴元。因为元稹人在兴元,故两诗才能有“西江流水到江州,闻道分成九道流。我滴两行相忆泪,遣君何处遣人求?除非入海无由住,纵使逢滩未拟休。会向伍员潮上见,气充顽石报心仇”、“眼前明月水,先入汉江流。汉水流江海,西江过庾楼。庾楼今夜月,君岂在楼头?万一楼头望,还应望我愁”的诗句。如果元稹在通州,就不好解释“先入汉江流”的诗句了。
直到元和十二年五月元稹回到通州,收到白居易写于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的《与微之书》,白居易发出“不见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书,欲二年矣”的感叹;元稹读了,激动异常,有《得乐天书》纪实:“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惊喜之后,元稹自然要把近况告诉白居易。由于有长江的便利,通州与江州间的通信要方便一些,白居易知道了元稹的真实情况之后,明白了自己寄给元稹的诗篇元稹根本没有收到,所以又把两年来自己寄赠元稹的诗篇重行寄赠,前后有二十四篇之多。顺便应该指出,《年谱》断定《得乐天书》“此诗元和十一年五月以后作”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这些情况,我们并非出于无端的猜测,而是有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为证,序云:“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马通州。二十九日,与乐天于鄠东蒲池村别,各赋一绝。到通州后,予又寄一篇。寻而乐天贶予八首,予时疟病将死,一见外不复记忆。十三年,予以赦当迁,简省书籍,得是八篇。吟叹方极,适崔果州使至,为予致乐天去年十二月二日书,书中寄予百韵至两韵凡二十四章。属李景信校书自忠州访予,连床递饮之间,悲咤使酒,不三两日,尽和去年已来三十二章皆毕,李生视草而去。四月十三日,予手写为上下卷,仍依次重用本韵。亦不知何时得见乐天,因人或寄去,通之人莫可与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又在其下用小字注云:“其本卷寻时于峡州面付乐天,别本都在唱和卷中,此卷唯五言大律诗二首而已。”
根据以上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本节我们列举《年谱》编入元和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以及“通州任内”的二十首诗篇,都是元稹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之前的“不三两日”的作品;除此而外,《年谱》还漏系《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一首;另外,根据白居易的寄赠诗篇八篇加二十四篇的数目,元稹还应该有十一篇诗歌回酬,大概由于散佚成为佚诗,根据白居易原唱诗篇的题目,我们可以代拟元稹诗篇题目如下:《酬乐天重寄》《酬乐天雨中携微之诗访元八侍御》《酬乐天蓝桥驿见微之诗》《酬乐天韩公堆寄微之》《酬乐天编诗成集赠微之》《酬乐天见紫薇花忆微之》《酬乐天山石榴寄微之》《酬乐天春晚寄微之》《酬乐天感秋怀微之》《酬乐天感逝寄远》《酬乐天梦与李七庾三十二同访微之》,这十一首诗篇,理应列入元和十三年的“佚诗”栏内。
《年谱》元和十三年“在通州四年,与白居易唱和之诗,‘里巷相传,为之纸贵’”条下转引云:“《旧传》云:‘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于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婉。’《旧唐书·白居易传》云:‘追诏授江州司马……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
根据我们上面的辨证,《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关于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的叙述是错误的,至少是以偏概全;至于“江南人士,传道讽咏,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婉”云云,不是元稹白居易音讯不通时的写真,而应该元稹白居易唱和诗篇流传开来以后的情形。《年谱》理应在引述之后,对此作出辨证,以正确引导读者。
《年谱》元和十一年条下云:“元稹寄绿丝布、白轻容给白居易。”根据是“白居易《元九以绿丝布白轻容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知》云:‘绿丝文布素轻容,珍重京华手自封。’元稹《酬乐天得稹所寄纻丝布白轻庸制成衣服以诗报之》云:‘湓城万里隔巴庸,纻薄绨轻共一封。’元稹正为通州司马,不应从‘京华’寄丝织品至江州,白所谓‘珍重京华’者,指丝织品系‘京华’所购,值得‘珍重’也。”
根据元稹的生平和白居易的《与微之书》,元和十年十月至十二年五月,元稹移地兴元,谒医求药,与白居易失去联系,音讯不通。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元稹根本不可能寄给白居易绿丝布、白轻容之类的礼物,一来一回的诗歌酬唱更不可能。朱金城先生《白居易年谱》将白居易原唱诗篇《元九以绿丝布白轻容见寄制成衣服以诗报知》系于元和十三年,甚是。
那末,元稹大约在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寄给白居易这些来自“京华”的贵重礼物呢?容我们慢慢列举证据加以说明。元和十年元稹自江陵士曹参军返回京城时,曾把保子和元荆带回京城。元稹谪官通州之日,是“一身骑马向通州”的。自通州移地兴元治病,据元稹《感梦》诗自述,也仅仅只有童仆在旁。无论是独自前往通州,还是抱病移地兴元,元稹都不可能带着“‘京华’所购”的“丝织品”。而返回自兴元通州之后,在《红荆》诗中云:“庭中栽得红荆树,十月花开不待春。直到孩提尽惊怪,一家同是北来人。”既称“一家”,自然应该包括保子和元荆在内。我们以为保子和元荆自长安来到元稹身边,大约在元稹在兴元重建家庭之后。元稹《景申秋八首》中既有“啼儿”,又有“唤魇”之“儿”,就是明证。送给白居易的绿丝布、白轻容,就是保子、元荆自长安前来兴元时带来的(保子、元荆离开长安以后,元稹在长安靖安里的家已经不复存在,故将“细软”如绿丝布、白轻容带往兴元)。当时元稹与白居易失去联系,所以无法寄赠。直到元稹回到通州,亦即元和十二年五月,收到白居易的诗书之后,才有机会寄赠。因为绿丝布、白轻容都是从京城带来,辗转千里,来之不易,所以白居易才有“珍重京华”之语。根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将白诗在元和十三年下编年的情况,元稹的《酬乐天得稹所寄纻丝布白轻庸制成衣服以诗报之》至早也应该在元和十三年内。《年谱》元和十一年谱文内构想元稹致白居易礼物以及两人互相酬和诗歌,显然不合元稹白居易这一时期两人音讯不通的事实;同样,同年“诗编年”栏内将《酬乐天得稹所寄纻丝布白轻庸制成衣服以诗报之》系人也显然有误。
《年谱》元和十二年“诗编年”栏内将元稹《酬乐天春寄微之》编入,理由是:“白诗云:‘三年隔阔音尘断,两地飘零气味同。又被新年劝相忆,柳条黄软欲东风。’元和十年白居易与元稹在西京见面,下推‘三年’为元和十二年。”
我们以为《年谱》编年有误。据元稹白居易生平,他们自元和十年三月在长安分手,十月前后元稹北上兴元失去联系,直至元和十二年五月元稹返回通州才开始互通音讯。白诗云“三年隔阔音尘断”,又云“又被新年劝相忆”,从时间推算,确实应当是作于元和十二年新年;但此时正是白居易“不得”元稹“书”之时。元稹的酬诗应该是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之前不久追和之作,不过,追和时用的是当时的语气罢了。
《年谱》元和十二年条下云:“本年秋冬间,李景俭为忠州刺史,由唐州赴忠州,至通州访元稹。”理由是:其一,“元稹《与李十一夜饮》云:‘寒夜灯前赖酒壶,与君相对兴犹孤。忠州刺史应闲卧,江水猿声睡得无?’又《赠李十一》云:‘淮水连年起战尘,油旌三换一何频!共君前后俱从事,羞见功名与别人。’据岑仲勉考证,两‘李十一’俱是李六之讹。‘李六’即李景俭,自唐、邓行军司马授忠州刺史。‘景俭由唐州赴忠任,可循汉水西上,先与通州之元稹会面,然后遄赴忠任,故有“忠州刺史应闲卧”之戏语,一会便别,故又叹其唐、邓司马之不能久任’。”
我们以为,《年谱》所据岑仲勉先生的考证有误。所谓“李十一”是“李六”之误,仅仅是推测;“一会便别”与“唐、邓司马之不能久任”没有必然联系;李景俭赴任路线,应该是顺汉水南下,逆长江西上,直达忠州,根本不可能逆汉水西上,在崇山峻岭里跋涉,绕道通州而至忠州。
据《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十一年九月,李宣为忠州刺史;据白居易《忠州刺史谢上表》《初到忠州赠李六》等诗文,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接替李景俭为忠州刺史。我们推测,唐邓行军司马李景俭赴任忠州刺史必在元和十一年九月至十三年十二月之间的某个时候。元稹《赠李十一》云:“淮水连年起战尘,油旌三换一何频!”据《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十年十月,始析山南东道为襄、复、郢、均、房节度府和唐、随、邓节度府。元和年间,唐邓节度使前有高霞寓(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六月)、袁滋(十一年六月至同年年底),后有李愬(十一年年底至十二年十一月)。据此可知,李景俭卸任唐邓行军司马而赴任忠州刺史定当与袁滋同时,即十一年年底。据元稹生平,元和十年十月至十二年五月,元稹正在兴元治病,不在通州。即使李景俭元和十一年年底赴任忠州刺史时绕道通州,两人也无法会面,又如何有《赠李六》《与李六夜饮》的诗篇?
元稹诗集中的《与李十一夜饮》《赠李十一》两诗与《喜李十一景信到》《别李十一五绝》六首诗同在一卷,另有《通州丁溪馆夜别李景信三首》在别卷,它们都是元稹为“自忠州访予”的李景信而作;又,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云:“……十三年……属李景信校书自忠州访予……李生视草而去。四月十三日……”据此可知,李景信“自忠州访”元稹在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之前不久,而这段时间,正是李景俭在忠州刺史任上。
根据我们的理解,《与李十一夜饮》诗“寒夜灯前赖酒壶,与君相对兴犹孤”两句是元稹与李景信相会夜饮时的情景,意即山间春夜,全凭酒壶之酒抵御阵阵寒意;与好兄弟您相聚,虽是人生快事,但我的兴致仍然不高。为什么如此呢?诗人接着转入三四句:“忠州刺史应闲卧,江水猿声睡得无?”那意思是说我与您景信在这里深夜喝酒谈心,好不快活!这时您的兄长忠州刺史李景俭大约闲着无事,一定早早地躺下了,但不知他在奔流不息的江水声中和此起彼伏的猿啼声里睡着了没有?因为面对李景信而又记挂着李景俭,所以诗歌中一二句中称“君”,而在三四句里称“忠州刺史”,前后称呼不一,因为“君”指李景信,而“忠州刺史”指李景俭之故;正因为李景信与李景俭是嫡亲兄弟,所以元稹的诗中才能随随便便说“与君相对兴犹孤”,如果李景信与李景俭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元稹在诗里就不好这么随便了。
同样,《赠李十一》也不难理解。按诸唐史,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乱起,唐廷委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兼招讨使,发兵征讨,十年十月,析山南东道为二,分以李逊、高霞寓为节度使,这是淮水“起战尘”之后的“一换油旌”;十一年六月,分以袁滋、郑权代替李逊、高霞寓,这是二换“油旌”;十一年底,以李愬代袁滋,这是三换“油旌”。元和十二年,李愬夜入蔡州,淮西叛乱终于平息,唐廷给有功将帅加官晋爵。元稹曾经跟随严绶以“唐州从事”的身份在唐邓平叛前线奔驰,李景信也曾跟随兄长李景俭,作为唐邓节度府的一般僚属效力平叛。在“淮水连年起战尘”的情况下,由于“油旌三换一何频”,前两任的将帅时间匆匆,难建功业,我元稹与您的兄长李景俭和您李景信也无功而返,“与君前后俱从事,羞见功名与别人”两句,就是诗人微含惋惜愠怒之意的真实流露。
应该在这里指出,《年谱》将《与李十一夜饮》《赠李十一》改为《与李六夜饮》《赠李六》显然是错误的;将它们编入元和十二年“诗编年”栏内也是不妥的,两诗理应与《喜李十一景信到》《别李十一五绝》《通州丁溪馆夜别李景信三首》一起编入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稍前的某个时候。
《年谱》通州任内“乙未至戊戌在通州所作其他诗”栏内系入元稹诗篇《和乐天梦亡友刘太白同游二首》,理由是:“白居易原唱为《梦亡友刘太白同游章敬寺》。白诗云:‘三千里外卧江城。’元诗云:‘君诗昨日到通州。’”
《年谱》在这里失察,不应该笼统系年通州任内。白居易诗有句云:“三千里外卧江城,十五年前哭老刘。”诗题中的“刘太白”即元稹白居易校书郎时同事好友刘敬质,卒于贞元二十年,下推“十五年”,白诗当为元和十三年,元诗似也应该作于元和十三年。
《年谱》通州任内“乙未至戊戌在通州所作其他诗”栏内系入元稹诗篇《和乐天寻郭道士不遇》,理由是:“居易原唱为《寻郭道士不遇》,自注:‘庐山中云母多……’江州作。”
《年谱》在这里同样失察,不应该笼统系年通州任内。元稹与白居易元和十年十月至十二年五月失去联系,他们不应该存在唱和关系。朱金城先生《白居易年谱》系居易原唱《寻郭道士不遇》于元和十三年内,甚是;我们以为元稹酬唱诗似乎也应该系人元和十三年内。
《年谱》通州任内“乙未至戊戌在通州所作其他诗”栏内系入元稹诗篇《虫豸诗(七篇,并序)》,理由是:“《序》云:‘……又数年,司马通州郡。通之地,蛇之毒百……予因赋其七虫为二十一章,别为序’云云。”
我们以为《年谱》对《虫豸诗》的系年过于笼统。首先,《虫豸诗》所述均是通州山谷间的虫豸,因此它的作年理应元稹在通州的元和十年六月至十月间和元和十二年五月至十三年年底。元和十年六月至十月间元稹“疟病将死,一见外不复记忆”,所以不太可能作《虫豸诗》;而元和十二年五月至十三年年底之间,应该是《虫豸诗》二十一首的创作时间。其次,《虫豸诗》二十一首虽然为感物寓意之作,但它的序言里多多少少流露出当时的时序,如《虫豸诗·蟆子三首·并序》云:“秋夏不愈。”又如《虫豸诗·虻三首·并序》云:“巴山谷间,春秋常雨。自五六月至八九月,雨则多虻……逮雪霜而后尽。”据此《序》所云历春夏秋冬的情况看,此诗应该作于元和十二年年底至十三年元稹离开通州之间。
《年谱》在元和十三年“诗编年”栏内将元稹《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见贺》编入,所列三条理由均是考证元稹与拜相者李夷简的关系,没有涉及编年理由。
我们以为,将元稹《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见贺》编入元和十三年固然不错,但尚嫌笼统。考李夷简拜相在元和十三年三月,罢相出守扬州在同年七月,白居易的原唱以及元稹的酬唱必定作于这一年的三月至七月之间;而白居易原唱诗云:“知己新提造化权。”元稹酬唱诗云:“尚书人用虽旬月。”据“新提”、“旬月”可知,元稹酬唱必定作于元和十三年四月无疑。
这组文章一共六篇,以辨证《年谱》的部分疏误为主要内容。本文仅是其中的一篇,共例举《年谱》的疏误约七十余处。因六篇文章互相牵涉关联,难于截然分割,拜请有关专家一并审读。限于笔者水平,本组文章的疏误定然不少,诚请教正。
收稿日期:1999-09-15
